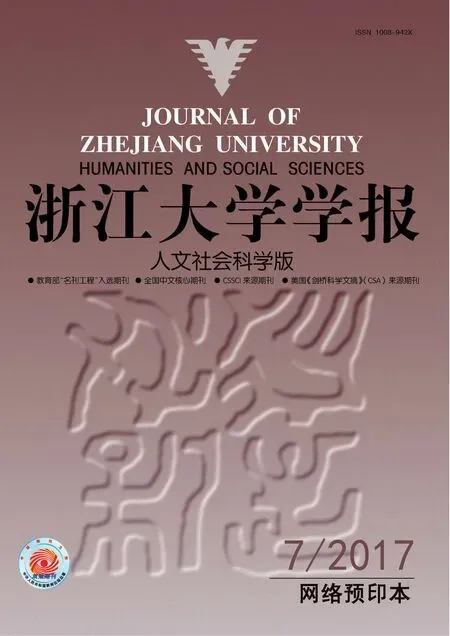内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构成要件研究
林承铎 胡 兵
(1.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学院, 北京 100872;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广东 深圳 518026)
内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构成要件研究
林承铎1胡 兵2
(1.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学院, 北京 100872;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广东 深圳 518026)
对内部人反向刺破构成要件的研究可以沿用传统刺破的“主体—行为—结果”三要件框架。在主体方面,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权利主体既可以是公司自身,也可以是股东,包括自然人和母公司;责任主体则为公司债权人。在行为方面,公司股东对公司实行了过度控制的行为,这种过度控制是中性的,不存在利用公司法人格牟取不当利益的主观恶意,是股东为了方便管理、经营而实施的,或者因公司经营与股东生活紧密相连而产生的。在结果方面,包含三个递进层面:股东与公司人格上实质同一;责任主体债权的强制实现将违背重要公共政策或法律的特别规定;反向刺破给公司债权人带来的损失要小于其所促进的社会公共利益。
内部人; 反向刺破; 公司面纱; 构成要件
一、 引 言
自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20条将刺破公司面纱理论成文化,刺破公司面纱(或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理念就已深入人心。而随着我国经济生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刺破公司面纱已出现扩张适用的趋势,其理论和判例复杂多面,反向刺破公司面纱(Reverse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RVP,以下简称“反向刺破”)便是其中的典型情形。在传统刺破公司面纱(以下简称“传统刺破”)的情境下,公司债权人向裁判机构请求否定公司独立人格,使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反向刺破则与之不同。在反向刺破的情境下,既可以是公司自身或公司股东主动寻求刺破公司面纱,以使公司享受原本只有股东才能享有的特权或债务豁免,这在理论上被称为“内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Insider Reverse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RVP-I,以下简称“内部人反向刺破”);也可以是股东债权人请求刺破公司面纱,使公司对股东的个人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情形在理论上被称为“外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Outsider Reverse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RVP-O)。关于内部人反向刺破,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是促进和实现特定的重要政策目标和立法目的,以及维护重大社会公共利益[1]。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法理与传统刺破完全不同,它因主要考虑社会公共利益而偏向于维护公司或其股东的利益,且可能导致对公司债权人的不利益。实际上,我国审判实务中曾出现过相关案件,如2001年的日本月亮人针织有限公司与南通日出服装有限公司设备转让合同纠纷案*参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通中经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书,转引自胡道才、吴建斌主编《参阅案例研究·商事卷》第1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以下简称“月亮人针织公司案”),但由于固守传统观念——股东既然选择了公司制度,那么他在享受了有限责任的特权和公司经营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就应该承受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带来的不利益,再加上公司法理论在内部人反向刺破问题上的欠缺,我国法院尚未有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请求的判决。对此,实在令人遗憾。
根据笔者研究所及的文献,国内深入研究内部人反向刺破构成要件的文章或著作非常之少,即便是对反向刺破的研究也乏善可陈。一些文献阐述过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问题,但大多是粗糙的总结,绝少经过详细的研究论证。相比之下,美国学者对内部人反向刺破的研究则要深刻且丰富得多,如Crespi[2]、Bainbridge[3-4]、Thompson[5]等对内部人反向刺破均有非常独到的理解,对其构成要件亦有相当精辟的分析。这与美国丰富的内部人反向刺破司法实践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在对美国内部人反向刺破实践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以之为鉴,尝试对我国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以期为我国未来法律完善相关制度提供参考。至于外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构成要件,将留待另文探讨。
二、 美国法上内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构成要件
(一) 美国法院实践的回顾
1981年,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对Beverly Roepke v.Western National Mutual Insurance Co.一案*Beverly Roepke v.Western National Mutual Insurance Co., 302 N.W.2d 350 (Minn.1981).(以下简称“Roepke案”)的判决,首开美国法院适用内部人反向刺破原则的先河。不过,由于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强调本判决意见仅限于该案特有的事实,该案的判例规则并未立即在随后的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得到遵循、效仿。
Roepke案最先被引证是在两年后的Rademacher v.Insurance Co. of North America一案*Claretta Rademacher and Sisters of the Order of St.Benedict v.Insurance Co. of North America, 330 N.W. 2d 858 (Minn. 1983).(以下简称“Rademacher案”)中,而Reopke案创立的内部人反向刺破原则的第一次充分应用则是在几乎与Rademacher案同时发生的Kuennen v.Citizens Security Mutual Insurance Co.一案*Deborah Kuennen v.Citizens Security Mutual Insurance Co., 330 N.W. 2d 886 (Minn. 1983).(以下简称“Kuennen案”)中。Scott法官在Kuennen案的判决书中大胆地适用了“同一性程度”(the degree of identity)标准来决定是否应该刺破公司面纱,而这一标准本是在传统刺破中适用的。与Roepke案一样,这两个案件都是出自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之手,都是原告企图依据该州汽车保险政策请求保险赔偿金;而与Roepke案不同的是,这两个案件的法官都根据各自所特有的事实拒绝了原告反向刺破的请求*在这之后的1985年,明尼苏达州上诉法院在Leidall v.Grinnell Mut. Reinsurance Co., 374 N.W. 2d 532 (Minn. App. 1985)一案中再次拒绝了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请求。。
使内部人反向刺破原则得到法院广泛接受的是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1985年对Cargill, Inc.v.Hedge案*Cargill, Inc.v.Hedge, 363 N.W. 2d 315 (Minn. 1985); 358 N.W. 2d 490 (Minn.App. 1984).(以下简称“Cargill案”)的判决。在该案中,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首次引用Roepke案支持了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请求,并对Roepke案有所扩展。这也是内部人反向刺破的适用第一次突破了汽车保险金赔偿案件的情形。
Cargill案之后,内部人反向刺破原则在明尼苏达州的地位逐渐确立并得到稳固。在随后的司法实践中,内部人反向刺破请求也根据个案具体情况的不同或被支持或被拒绝。内部人反向刺破的适用范围也经由个案得到了相应的扩张。
除明尼苏达州之外,在美国其他州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内部人反向刺破均得到广泛的支持和适用,比如密歇根州的James Wells v.Firestone Tire and Bubber Co.案*James Wells v.Firestone Tire and Bubber Co., 421 Mich. 641, 364 N.W. 2d 670 (Mich. 1984).,新泽西州的Gelber v.Kugel’s Tavern, Inc.案*Gelber v.Kugel’s Tavern, Inc., 10 N.J. 191, 89 A.2d 654 (N.J. 1952).等。具体适用的情形包括高利贷法的适用、产权转让限制、利润损失、破产管理以及工伤赔偿中的法定侵权豁免等[2]。
即便在一些拒绝适用内部人反向刺破的州法院,如肯塔基、纽约、得克萨斯等,也并非毅然决然地否定该原则,而只是认为内部人反向刺破并不能适用于个案的特定事实。换言之,这些拒绝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请求的地方法院并不绝对地否认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效力,只是在将该原则适用到具体案件中时十分谨慎,要求非常严格。
在联邦法院层面,新近发生的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v.Sebelius案*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v.Sebelius, 904 F.Supp. 2d 106 (D.D.C. 2012).(以下简称“Tyndale案”)的判决一改联邦法院之前的态度,果断支持了原告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请求,令人耳目一新。Tyndale案的判决意义重大,它借助在此之前各州法院在内部人反向刺破领域的丰富实践经验积累,使内部人反向刺破理论进一步完善,使美国法院对该理论的适用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国内学者廖凡在其《美国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从代表性实践出发,对美国内部人反向刺破的发展演变亦有过相应的介绍[1]。不过,受限于写作的时代背景,对内部人反向刺破在美国联邦法院层面的最新发展变化,廖文未能涉及;并且对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或者说适用条件,也未能有清晰且连贯的分析。
从上述美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尽管各州及联邦法院对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态度因各州及联邦法律之差异而有所不同,但不难发现的是,对该原则的广泛接纳和适用应是美国司法实践中不可阻挡的趋势。同时,丰富的审判实践为我们通过典型性判例深入研究美国法上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代表性判例
1.Cargill案
Cargill案发生于1983年,历经三审,最终于1985年10月25日在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得到终审判决。
本案中,被告S.Hedge和妻子A.Hedge通过分期付款购买了一个面积为160英亩的农场,然后把自己拥有的财产都过户到了他们设立的家庭农场公司(Hedge Farm, Inc.)名下,A.Hedge是该公司唯一的股东。后因S.Hedge从Cargill公司购买农场生产所需的物资和服务而无力偿债,Cargill公司向法院起诉了Hedge夫妇和农场,并获得了针对S.Hedge和农场的清偿判决。然而,在农场被执行拍卖给Cargill公司后的法定回赎期内,A.Hedge要求豁免执行包含他们家的宅地(homestead)的农场部分。她提出,根据明尼苏达州宅地豁免法,家庭农场公司的存在应该被忽视,农场中的80英亩土地应该视为被告个人宅地。
在判决中,最高法院再次确认了“同一性程度”标准在内部人反向刺破案件中的重要性。法院一方面承认被告和妻子遵守了公司的法律形式,如保存公司会议记录、填写公司纳税申报表、以公司名义与生产信贷协会交涉等;另一方面仍然认为,由于Hedge一家与农场的日常运营有着紧密的联系,农庄就是他们的住房,他们和农场不存在租约也不支付租金,A.Hedge是农场唯一股东,一家四口都是农场的董事,没有人从农场拿过薪水,该农场公司在实质上成为Hedge一家的“另一自我”(an alter ego)。而且,法院认为,宅地豁免政策不仅仅是为了债务人的利益,更是为了明尼苏达州的利益。因为该州的福利和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州居民的个人独立感和对故乡、家族之热爱。宅地豁免法的这一宗旨为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提供了比Roepke案更强烈的政策动机。而对于作为农场债权人的原告Cargill公司将因反向刺破请求而受到的不利影响,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总结道:任何允许宅地豁免情况下带来的不公平都仅仅是这一豁免政策与生俱来的。
2.Tyndale案
Tyndale案起因于2010年奥巴马政府《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atientProtectionandAffordableCareAct,简称“平价医疗法案”)的签署生效。该法案规定了所谓的“雇主强制令”,要求全职雇员多于50人的企业必须为雇员购买医保。而根据该法案的授权,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进一步规定了“避孕药强制令”,要求对妇女的医保强制覆盖避孕药品、绝育手术及术后教育与咨询等预防性医疗,而宗教雇主(教会及其附属组织)可以豁免这一规定[3]。
“避孕药强制令”引起了各州一大批由怀有宗教信仰的人所拥有的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宗教组织的不满和反对,他们纷纷以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Kathleen Sebelius为被告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其中最早也最典型的便是Tyndale案*据统计,“避孕药强制令”出台后,有48个类似的反对该规定的诉讼在美国各州被提起。典型的有Conestoga Wood Specialties Co.v.Sebelius, 917 F.Supp.2d 394 (E.D.Pa., 2013);Hobby Lobby Stores, Inc.v.Sebelius, 2013 WL 3869832 (W.D.Okla. 2013)。其中,18个涉及营利性雇主。而截至2013年3月,18个涉及营利性雇主的案件中有12个已经获得了法院授予的针对“避孕药强制令”的临时禁制令。参见S.M.Bainbridge,″Using Reverse Veil Piercing to Vindicate the Free Exercise of Incorporated Employers,″ Green Bag,Vol.16, No.2 (2013), p.238。此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4年6月30日做出判决的Burwell v.Hobby Lobby Stores, Inc., 134 S.Ct. 2751 (U.S. 2014) 中,明确支持了封闭持股的营利性公司以宗教信仰为由豁免“避孕药强制令”的主张。参见商群《当宗教成为私权的堡垒》, 2014年7月11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224, 2016年3月22日。。在该案中,原告Tyndale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包括圣经评论、家庭事务方面的基督小说在内的基督教书籍出版的营利性公司,它有260名雇员,为他们提供自我保险医疗保健计划。Tyndale信托拥有Tyndale公司84%的表决权股;Tyndale家庭基金会(一家非营利性宗教慈善机构)拥有Tyndale公司绝大部分无表决权股,而分红比例占96.5%。此外,同一组人既是Tyndale信托的受托人,又担任Tyndale公司董事会成员,而且每一个人都要求签署了一份“信仰声明”,以表明他们都持有确定的宗教信仰。
Tyndale公司及其他原告质疑“避孕药强制令”效力最有力的理据是该规定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和《宗教自由恢复法案》(ReligiousFreedomRestorationAct, RFRA)。被告律师抗辩称设立公司的雇主无权援引宗教信仰自由条款来反对破坏他们生意的政府规章。而Walton法官则坚定地支持了原告Tyndale公司的诉求。他在判决中指出:“Tyndale公司的信仰和它的所有者的信仰是不可分的。Tyndale公司是一家由基督教信仰联结起来的四个组织共同拥有的封闭持股公司。公司中到处渗透着基督教的准则、祷告和活动,公司所有权结构的设计也是为了使其绝不偏离传播信仰的使命。法庭更没有理由怀疑,Tyndale公司对提供包含避孕药物的保险持反对态度是公司所有者的宗教信仰的自然反应……因此,由于Tyndale公司并没有提出任何自己的不同于或更高于其所有者权利的宗教信仰自由,它有资格主张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虽说奥巴马医改是为确保美国公民医保全面覆盖,但这一强制性规定带来的利益是否就为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RFRA下的权利提供了正当性理由是值得质疑的。而其实在制定法案时,政府就已经通过“祖父条款”*“祖父条款”(grandfather clause),又称不回溯条款、保留条款或例外条款,是指新的法律、法规中规定的某些限制,不适用于已经开始的活动,并允许其继续进行。削弱了“避孕药强制令”的效力。因为根据法案,全职雇员少于50名的雇主、被承认的反对医保观念的宗教派别或分支的成员以及规章定义的宗教雇主均获得了豁免。
(三) 评述
Cargill案和Tyndale案都是美国在适用内部人反向刺破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案例,一个是明尼苏达州在内部人反向刺破实践中的经典总结和扩展;一个是联邦法院放弃之前的保守立场,在适用内部人反向刺破上的突破性创举。更为重要的是,处理这两个案件的法官在判决书中都采用了相同的分析路径,从而确立了适用内部人反向刺破的“三要素法”*“三要素法”是笔者自拟的说法,意指法院在判定是否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请求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因素,即a three-pronged version of RVP-I。。
在Cargill案中,Simonett法官首先审查了“Sam Hedge个人与农场的同一性程度和农场作为股东的‘另一自我’的程度”*Cargill,Inc.v.Hedge, 363 N.W. 2d 315 (Minn. 1985), at 479.;然后,确定本案有比Roepke案中还强烈的政策理由(明尼苏达州的宅地豁免政策)来支持反向刺破;最后,没有农场的其他股东受到损害,而对于像Cargill公司之类的债权人的利益损害,仅仅是宅地豁免政策与生俱来的可能后果。类似地,在Tyndale案中,Walton法官实质上主要考虑了三个问题:第一,股东的信仰和行为与Tyndale公司的日常运营以及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是否存在实质的同一性,以至于公司有效地成为股东的“另一自我”?第二,反向刺破Tyndale公司的面纱是否能促进重要的公共政策?第三,政府在确保公司雇员获得强制的医保范围中的利益有多强大?
剥离上述两个案件的具体案情,不难发现,法官在具体判断是否应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请求时,都有意或无意地考虑了三个因素或标准:(1)“另一自我”标准。而被请求刺破面纱的公司是否构成其股东的另一自我,法院则主要根据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同一性程度”来衡量。Walton法官在Tyndale案中的分析就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模型。对于“同一性程度”,他考虑了以下方面:Tyndale公司的章程是否包含关于宗教信仰和目标的目的声明条款;所设计的所有权结构是否为确保即便最初设立者退休或去世仍能保持宗教目标的延续;董事和高管是否有义务分享设立者的宗教信仰,如果是,他们是否签署过相关书面文件,如信仰声明;宗教活动是否构成公司集会的一部分;公司的雇员是否能参加这些宗教活动;公司的大部分盈利是否用作慈善或符合设立者的宗教信仰的用途等[4]。(2)促进重要的社会公共政策的要求。Cargill案中明尼苏达州宅地豁免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该州居民对家乡的认同感和依恋感,以促进该州的福利和繁荣,附带地保护了债务人。Tyndale案中,“出于宗教信仰动机的行为应该被接受为人们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一种方式,即使这种行为发生在商业活动中”*Attorney Gen.v.Desilets, 636 N.E.2d 233 (Mass. 1994), at 237-238.。从这一意义上来说,Tyndale案中公共政策因素的效力要远远高于Cargill案中的宅地豁免政策。毕竟宗教信仰自由是源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而非州法。(3)避免对第三方利益的损害。内部人反向刺破最大的风险在于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不当损害,如Cargill公司收回的债务将因法院的判决而减少。但法院关于“该减损是宅地豁免政策与生俱来的后果”的论断显然是草率且说服力不足的。而Tyndale案中,政府方面提出的其在确保美国公民得到全面医保中的利益将受损的抗辩则显得较为牵强。正如Walton法官所认为的,“避孕药强制令”的效力在其制定之时即因“祖父条款”而被削弱。如果政府利益在强制令规定的例外条件下没有受到影响,或者这种影响被排除在考虑范围外,那么在Tyndale公司与其股东实质同一的情况下,也应该认为政府利益不会受到影响,或这种影响应该不予考虑。
Cargill案和Tyndale案形成的“三要素法”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体系。对上述三个要件的分析不是无序的,而是层层递进的,是一个由表及里、由行为到结果的思维过程。无疑,“三要素法”为此后美国法院适用内部人反向刺破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分析模型*实际上,美国各州法院在判例中适用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条件并不统一。除明尼苏达州法院和联邦地区法院(Tyndale案发生在哥伦比亚地区)采用的“三要素法”外,尚有密歇根最高法院在Wells v.Firestone Tire & Rubber Co.(421 Mich. 641, 364 N.W. 2d 670)案中采用的“经济实际标准”(economic reality test)以及学者M.J.Gaertner提出的“统一利益标准”(unitary interest test)。而其实,正如M.J.Gaertner自己所承认的那样,“统一利益标准”只是“经济实际标准”的变种。参见M.J.Gaertner,″Reverse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Should Corporation Owners Have It Both Ways? ″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Vol.30, No.3(1989), p.698。。总而言之,内部人反向刺破理论在美国法上的实践是丰富的,与传统刺破公司面纱一样,其影响已经在并将继续在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蔓延。“三要素法”或许并不完美,但仍为我国公司法上反向刺破公司面纱构成要件的构建带来诸多启示,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三、 我国内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构成要件框架的确立
目前,我国在反向刺破理论方面的法律实践以及对其构成要件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我国还尚未出现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法院判决,而前文提到的否定案例——月亮人针织公司案,相关法院则以公司自我否认人格是为了逃避债务、转移风险,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为由拒绝支持反向刺破的主张。也就是说,法院在考察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之前即已直接否认了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效力。不难理解,法官的判断受传统观念的支配,即一个人既然选择了公司制度,那么他在享受了有限责任的特权和公司经营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就应该承受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带来的不利益。然而,以笔者之见,在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公司数量不断增加,公司组织结构也因经营管理的需要而日益多元化、复杂化,请求刺破公司面纱(无论是正向还是反向)的内在动因千奇百怪,这决定了刺破公司面纱理论及其判例的复杂多面性,固守传统观念不利于我国的司法实践适应定纷止争的现实需要*如前所述,本文主旨在于对内部人反向刺破构成要件的研究,而这一探讨是建立在对内部人反向刺破效力的肯定的前提之下的。对内部人反向刺破效力的探讨非属本文研究范围,故此处不做深入分析。。
在理论界,内部人反向刺破之正当性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为内部人反向刺破理论构建统一的构成要件,以规范法官的分析进路,增强法院判决的可预测性。总结国内学者对内部人反向刺破构成要件的研究,笔者发现,无论是内部人反向刺破还是外部人反向刺破,大家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主体—行为—结果”的三要件分析框架。追本溯源,“主体—行为—结果”三要件分析框架是朱慈蕴教授在其代表作《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一书中所创立的,继而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均普遍认同并采用的传统刺破构成要件的分析框架[6]。一开始,笔者有两个疑惑:将传统刺破的构成要件分析框架用于反向刺破构成要件的分析是否合适?在学者们高度默契的背后是否存在心照不宣的理由?笔者曾试图打破上述三要件分析框架的窠臼,重构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分析框架,然而以失败告终。细思之下,笔者发现,沿用传统刺破的三要件分析框架来分析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其合理性或许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按照三段论的思维模式,只有某一民事主体从事的某一或某些行为造成了违法或违约的结果,才可能涉及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行为—结果”的三要件分析框架正与这一思维逻辑相吻合。内部人反向刺破的适用也不能逃脱这一法律逻辑推理的过程。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笔者在试图重构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时,任何一个全新要件的提炼最终都可以纳入“行为”或“结果”范畴的原因。
其二,比较美国判例法,从法院在适用内部人反向刺破时采用的“三要素法”中,我们其实可以抽象出两个方面:一是“控制因素”或“利益和所有权的统一”;二是“衡平因素”。不管美国法院的法官愿不愿意,事实上,内部人反向刺破构成要件的分析已然落入其传统刺破下“二要件标准”的框架之中。控制因素下更多的是事实判断问题,衡平因素下则更多涉及价值判断或法律衡量[7-8]。美国法上的控制因素大致相当于我国法上的行为要件,衡平因素大致相当于结果要件。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美国法院还是我国理论界,对内部人反向刺破构成要件的分析都不由自主、或多或少地受到传统刺破构成要件分析路径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绝非偶然。反向刺破与传统刺破同根同源,最终均导致股东与公司或母子公司各自独立性丧失的结果,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因此,通过对主体、行为、结果三个层面要件的分析来决定是否正向或反向刺破并不存在根本性障碍。
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运用“主体—行为—结果”的三要件分析框架来研究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成为可能。本文对内部人反向刺破构成要件的探讨即遵循这一模式展开。
四、 内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主体要件
朱慈蕴教授把公司法人格否认(传统刺破)的主体要件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公司法人格的滥用者;一是公司法人格的主张者,即因公司法人格被滥用而受到损害,并有权提起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之诉的当事人[9]。的确,刺破公司面纱总是在特定情形下的特定法律关系中被提出,必然涉及两方当事人。但抛开公司法理论中“主观滥用论”与“客观滥用论”的争议*在公司法学界,对于传统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中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是否需要具备主观标准一直存有争议。早期学者多持“主观滥用论”,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改采“客观滥用论”。参见冯果《公司法要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公司法》第20条中的“滥用”一词并不必要。,“滥用”一词的表述在内部人反向刺破情境下显然是不妥当的,内部人反向刺破不涉及“人格滥用”的情形。也有学者将反向刺破的主体简单地区分为原告和被告。这一区分太过草率,殊不知,在内部人反向刺破诉讼中,提出刺破请求者并非一定以原告的身份出现,被刺破者也并不一定以被告的身份出现。笔者倾向于把内部人反向刺破的主体要件分为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两个部分。权利主体是指在争议解决过程中有权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请正向或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当事人,该当事人客观上享受了刺破公司面纱带来的利益。所谓责任主体,是指权利主体的相对方,需对权利主体承担民事责任或承受公司面纱刺破带来的不利益的主体。
(一) 权利主体
内部人反向刺破,顾名思义,其权利主体是“内部人”。自然,“内部人”范围的确定,或者说内部人反向刺破权利主体的适格性,就成为必须讨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权利主体可以是股东,也可以是公司本身[10]。但这里面还存在以下疑问:(1)公司本身是否能够提出反向刺破的主张?(2)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的公司实际控制人(以下简称“非股东实际控制人”),多表现为公司的董事或高管,是否为内部人反向刺破的适格权利主体?(3)这里的“股东”是包括母公司,还是仅指自然人股东?这一问题亦可转述为: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是否包括子公司?
1.公司本身的适格性问题
否认公司本身作为内部人反向刺破权利主体的适格性的观点主要认为,公司提起反向刺破请求,意味着公司在主张自己不是“人”,这在法理和逻辑上说不通。笔者以为,这一理由不具有足够说服力来否定公司本身的权利主体地位。客观上,“法人”是民商事法律上创造的概念,是法律拟制的产物*笔者认为,虽然国内越来越多的观点倾向于把法人作为一客观存在的实体,即所谓“法人实在说”,而这一主张也具有其自洽的一整套理论逻辑,但把法人视为客观存在的独立实体,而非法律拟制的产物,是从实用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立场做出的一种带有人为倾向的制度选择。或许这种选择更有利于公司法的理论发展和制度构建,但从本源上来说,法人概念由法律创造,法人这一主体是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而形成、固定下来的。,是为便利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而设。法律赋予公司“人”的资格的前提是公司与设立它的股东各自人格的独立。如果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相互独立性不复存在,那么公司作为“人”的正当性也就丧失,公司法人资格的拟制也就可以被打破。因此,在适当条件下,为保护更为重大的利益,维护实质正义,应该允许公司主张自己不是“人”。
美国学者Thompson在20世纪90年代初做的一项实证研究显示,在164起公司自己主动提出反向刺破主张的诉讼中,公司胜诉的比例占13.41%。虽然胜诉的比例比股东主张反向刺破要低(股东反向刺破的胜诉比例是25.42%),但就案件数量来说却将近三倍于股东反向刺破案件(59起)[5]。从这项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以下三点:第一,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效力得到美国不少法院的承认;第二,公司作为权利主体提出反向刺破请求的情形非常之多;第三,美国法院对内部人反向刺破的适用十分严格。此外,笔者认为,拿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胜诉比例与传统刺破相比没有实质意义,两者也没有可比性*有学者根据Thompson的统计数据,将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胜诉比例与传统刺破相比较,认为其远远低于传统刺破的胜诉比例,一般很难成功,进而认为公司和股东不得请求揭开公司面纱。参见朱慈蕴《论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要件》,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5期,第75页。。一方面,传统刺破理论出现较早,已发展得十分成熟,美国各级法院大都遵循“二要件标准”进行适用;而内部人反向刺破出现较晚,发展很不成熟,各州及联邦法院态度并不统一,即便是承认其效力的州和联邦法院在适用时都十分谨慎。另一方面,传统刺破尚且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突破,是一项例外,案件数量不会太多;而内部人反向刺破更是对传统观念的突破,甚至颠覆,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案件相比传统刺破更少,而且对其适用又须严格把握。从这一角度看,13.41%的胜诉比例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以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胜诉比例低为由而否定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效力和公司作为权利主体的适格性,是不能成立的。
此外,与传统刺破的情形相同,在内部人反向刺破情境下提出刺破公司面纱主张的公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是美国法语境下的封闭型公司)。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一人公司情形下,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股东个人行为或生活更有可能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相互交织而难以区分,公司独立人格名存实亡的可能性也较大。当然,在股权高度集中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但在实践中比较罕见。即便出现,反向刺破主张得到支持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鉴于我国当前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的现状,出于严格限制内部人反向刺破的适用的考虑,笔者认为,在我国将内部人反向刺破的适用限于一人公司的情形较为妥适。
2.非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适格性问题
笔者认为,某一主体能否作为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权利主体,应以其对公司是否具有所有权利益为标准。因为,内部人反向刺破最终可能使得公司享有一般情况下只有公司股东个人才享有的特权,从而得以豁免对公司债权人之责任,这种特权的专属性特征要求以该主体具有所有权利益为必要。这是严格适用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要求。股东应既包括股东名册上登记的实名股东,也包括隐名股东。
《公司法》第216条第3项将“实际控制人”定义为:“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对于非股东实际控制人,虽然实质控制公司的经济决策、经营行为及财务政策等,但他们并不具有所有权利益。因此,非股东实际控制人并不能成为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权利主体。以此为标准,对公司不享有股权但实际控制公司的董事或高管无权提起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请求。
3.母公司的适格性问题
关于母公司的适格性,实质上就是内部人反向刺破能否在母子公司情境下适用的问题。从内部人反向刺破案件的整体情况来看,内部人反向刺破所依据的重要的社会公共政策或法律的特别规定,主要是基于保障人权等方面的考虑而赋予特定条件下的自然人股东以特权,而这种特权是公司等法人组织无法享有的。但并不能就此排除社会公共政策或法律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如促进一国某一产业的繁荣、扶植某一弱势行业等,而赋予具备一定条件或资格的公司等法人组织某些特权或豁免。比如,美国西南部经济低迷的某州为了促进本州石油生产,繁荣该州经济,制定了一个法规,禁止做出对任何在本州从事石油生产的公司实施惩罚性赔偿的裁决。这一保护仅限于那些在该州拥有或租借石油开采权的公司,得豁免惩罚性赔偿的范围限于与石油开发直接相关的事故[11]。而且在美国,母子公司情境下内部人反向刺破请求获得支持的案例也有不少,典型的如上述判例Tyndale案、Wells v.Firestone Tire和Rubber Co.案*该案的原告James Wells是被告耐火石轮胎和橡胶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员工,在工作中因卡车爆胎而受伤。原告提起第三方产品责任诉讼,向作为轮胎制造商的被告请求损害赔偿。该案一审和二审都拒绝了被告的反向刺破请求,密歇根最高法院则一反前两审的态度,运用“经济实体理论”(The economic reality test)最终支持了被告的内部人反向刺破请求。参见James Wells v.Firestone Tire and Bubber Co., 421 Mich. 641, 364 N.W. 2d 670 (Mich. 1984)。等。鉴于此,母公司作为内部人反向刺破权利主体的适格性不应予以排除。同理,上述公司本身的适格性问题中的“公司”自然也就包括子公司在内。因此,在下文中,除有特别说明者外,所指“股东”均包括母公司在内,“公司”均包括子公司在内。
有趣的是,内部人反向刺破通常被公司内部人作为防御性的抗辩手段,但是从美国司法实践来看,这并不意味着公司内部人只能作为诉讼中的被告。在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Kathleen Sebelius等为被告的系列案中,很多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封闭型公司的控制股东就通过主动援引内部人反向刺破,主张“避孕药强制令”妨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宗教自由权利。在这里,内部人反向刺破仍然是一项防御性抗辩手段,但主张者却充当了原告的角色。当然,这一现象的产生与美国自身的司法体制有很大关系。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内部人作为原告提出反向刺破主张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
(二) 责任主体
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责任主体是公司的债权人,包括自愿债权人和非自愿债权人。有人提出,内部人反向刺破主要作为防御性抗辩手段,不存在责任主体,让谁承担责任的问题,只是无过错股东及其利害关系人要求予以豁免,提供保护或者获得利益*参见孙建《反向揭开公司面纱研究》,南京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但这一观点笔者不能赞同。内部人提出反向刺破请求,使公司得以豁免或减轻对其债权人之债务,对公司债权人来说,虽无具体法律责任的承担,但是承受了债权减损的不利益,承担了经济交往过程中债务不履行的风险,实为内部人反向刺破之责任主体。
另一方面,从逻辑上分析,公司债务人也可成为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责任主体,因为在内部人反向刺破情形下,公司债务人仅对公司负担债务的预期被打破,面临可能需要对公司股东承担债务的风险。但这一做法并没有实质意义。即便公司债务人需对公司股东承担债务,其债务负担并未实际增加,只是履行义务的对象发生了改变,公司债务人的利益几乎不会受到减损。现实中也几乎不会出现公司股东通过反向刺破要求公司债务人向自己承担债务的情形。确立公司债务人的责任主体地位反而有过分保护公司或股东之嫌,与严加限制内部人反向刺破的适用的主旨不符,故而笔者认为不宜将公司债务人纳入内部人反向刺破责任主体的范围。
五、 内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行为要件
对于行为要件的考察,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更多涉及的是事实问题的判断。在内部人反向刺破中,内部人依据特定的法律规定或公共政策主张刺破公司面纱的前提是,股东对公司实行高度所有或过度控制,以至于实质上可以将两者视为同一主体。在此前提下主张反向刺破,才有可能使公司享有依法只有股东方可享有的利益或豁免。所以,公司股东对公司实行了过度控制的行为是适用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行为要件。与我国传统刺破中的股东滥用公司控制权不同,传统刺破理论中的过度控制必须是“控制本身具有不正当的甚至非法的现象”[12]124,而内部人反向刺破行为要件下的股东控制是中性的,股东对公司的控制行为是一系列事实行为的总和,这种控制不存在利用公司法人格牟取不当利益的主观恶意,是股东为了方便管理、经营而实施的,或者因公司经营与股东生活紧密相连而产生。这在现实中是大量存在的,尤其是在一人公司的情况下。
实践中,股东对公司实施过度控制行为的表现形式又是复杂多样的,不可能尽数列举,须就具体案情进行综合判断。相关的考虑因素可以包括(但不限于):母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子公司是否有独立的公司治理结构;子公司的管理层与母公司之间的紧密程度;公司的日常经营是否有来自股东的指示;公司的收益是否大部分归股东支配,或者其收益是否主要来自于为股东提供商品或服务;个人股东的生活与公司密不可分,如公司的经营场所即为股东及其家人的住所、股东财务与公司财务不分、股东及其家人的生活消费主要依赖于公司的经营所得等。比如,某石油开发集团公司A将石油钻探设备的安装、调试和运营业务承包给其全资子公司B。B公司80%以上的总收入来自为A公司提供的服务,且B公司只在A公司占重要份额的市场中从事经营获利。B公司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就是A公司的前任副总裁,而且仍然是A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此外,B公司几个关键的高管是A公司以前的员工,B公司60%的董事是A公司现任或前任的高管。以上这些因素足以判断A集团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B存在高度所有或过度控制,两者实质同一。又如,甲在自己所有的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开了一家一人公司,主营照相、摄影、彩扩等业务。甲将自己所有的两室一厅的房屋过户给其所设立的摄影公司,作为经营场所。甲是该公司唯一股东,兼任经理,公司所有日常事务均由甲独立打理。由于甲没有另外的房子,甲及其妻子、儿女的日常生活起居都是在公司里。公司的所有器材、设备和办公用具都是甲用自家的存款购置的,公司虽有独立的账目,但实际上无论是公司的日常支出、收入,还是甲一家人的日常支出、收入,都经过该账目,即公司财务与甲的家庭财务实际不分,公司的收入构成甲一家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该案件取材于叶海燕《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兼谈我国公司人格反向否认制度的构建》,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53页,稍有改编。。显然,甲一家人的生活与其所设公司的日常运营相互渗透,密不可分,甲对其公司行使着高度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否认该一人公司独立人格的存在。
在考察传统刺破公司面纱的行为要件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公司形式要件的齐备程度,即很大程度上将注意力集中于股东是否遵守了公司形式,而这一因素与内部人反向刺破实质上并不相关。换言之,在内部人反向刺破情境下考察股东对公司形式要件的遵守程度意义不大。因为在内部人没有使公司遵循必备的法律形式,而是将它作为内部人的“另一自我”进行经营的情况下,仍允许内部人反向刺破明显是于理不合。这将违反“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这一最根本的衡平法则。在公司内部人没有遵守公司形式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债权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自己是在直接与该内部人而非公司进行交易。这样的话,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依赖公司独立的法律状态,除非该债权人明知或明确意识到该公司没有遵循形式要件的事实[2]。当然,Crespi的分析自有其局限,即合理相信自己是在直接与内部人进行交易行为只适用于自愿债权人,不包括非自愿债权人。但该局限并不影响这里的讨论。即便重要的公司形式得到遵守,仍然可能存在内部人反向刺破的适用。除此之外,传统刺破公司面纱的行为要件中的诸如“欺诈公司债权人”、“规避合同或法律义务”等行为,在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行为要件中均无由存在。
由此观之,尽管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行为要件中的行为类型并不如传统刺破那般丰富,但是对股东对公司的高度所有或过度控制行为的判断,仍然需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因素。而这一判断过程既依赖于案件的具体情况,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没有统一的标准可循,因此也对法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六、 内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结果要件
传统刺破公司面纱的结果要件考察的是公司法人格滥用行为带来的损害,以及滥用行为与损害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价值取向、责任流向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内部人反向刺破原则下结果要件的考察视角也异于传统刺破。内部人反向刺破的结果要件考察的是股东的过度控制行为是否造成股东与公司实质同一的事实状态,不执行内部人反向刺破是否将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损害,以及执行内部人反向刺破是否给公司债权人或公司其他股东带来损害。因此,内部人反向刺破的结果要件也依次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1.股东对公司的过度控制行为使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达到人格上实质同一的事实状态。
这实际上是对前述行为要件附加程度上的要求,即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或控制必须达到使股东与公司实质同一的程度,或可称程度要件。如此一来,对内部人反向刺破行为要件的考察,更多的是对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或控制程度,或者说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同一性程度的判断*本文对“内部人反向刺破不涉及‘人格滥用’的情形”与“股东和公司实质同一作为内部人反向刺破的结果要件”的理解和分析,从根源上牵涉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中“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情形,是仅限于‘人格滥用’还是同时包括‘人格混同’”,以及“‘人格混同’与‘人格滥用’是并列情形还是种属关系”等问题,与吴建斌教授“‘人格混同’与‘人格滥用’是并列关系”、“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并非仅适用于‘人格滥用’,起码应当扩及‘人格混同’场合”的观点不谋而合。参见吴建斌《公司法人格否认成文规则适用困境的化解》,载《法学》2009年第7期,第128-135页。。因此,在内部人反向刺破案件中,裁判机构在判定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有客观上的过度控制行为之后,应该衡量股东的控制行为是否使公司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几近于完全融合而无法将公司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这里的“股东与公司实质同一”不等同于我国传统刺破理论中的“公司形骸化”*实际上,国内公司法人格否认(传统刺破公司面纱)理论关于行为要件的概括十分混乱,正如朱慈蕴教授所承认的那样,“过度控制”、“人格混同”和“公司形骸化”的用语本身即存在交叉重合之处。参见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在具体应用时仍然会出现模糊不清、难于判断的情况。,两者在外延上存在重大差别。
2.公司债权人债权的强制实现将导致股东失去基本生活所依等违背重要社会公共政策或法律特别规定的结果。
以上述甲开设主营摄影、照相的一人公司案件为例,摄影公司从某摄像器材公司购进一批照相器械,合同价款为56万元。后甲经营失策,合同到期后摄像公司迟迟不能还款。器材公司遂经由诉讼途径获得了要求摄影公司还款的生效判决。执行过程中发现摄影公司账户钱款远远不足,于是准备拍卖或变卖摄影公司的所有设备以及公司所有的两室一厅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制拍卖该房屋以完全实现器材公司之债权,甲及其妻子、儿女必将陷于流离失所、生活无依的境地。而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关于强制执行时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的特别规定之意旨,应使该房屋免于强制执行才合乎保障人权之基本理念。
内部人反向刺破作为一个衡平原则,其成立的根本依据在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实现或促进,集中表现为特定的公共政策目标或立法目的的促进和实现。内部人反向刺破正是在公司债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存在冲突的情境下产生的。在这一利益平衡的过程中,公司债权人的债权虽得到承认但不得不被置于次级劣后的地位。显然,与传统刺破的结果要件明显不同的是,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这一结果要件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不良结果的预判,这一结果在内部人反向刺破情形下具有发生的必然性,内部人反向刺破即是通过对案件当事人的现实利益进行调整以防止未来不良结果的发生。故而,此一要件在内部人反向刺破案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3.反向刺破给公司债权人带来的损失或不利影响要小于赋予公司只有股东才能享有的法定特权或豁免所促进的社会公共利益。
这一点实为上一层面的逻辑结果。众所周知,当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冲突时,个人利益需要让位于国家/集体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毋庸置疑,这是人们进行利益衡量或价值评判时应时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法律对复杂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一般逻辑。又如前所述,内部人反向刺破原则的意旨在于促进和实现特定的公共政策目标或立法目的,但反向刺破的成就必然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一定的减损,而公司作为债务人却附带地享受了反向刺破带来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呈现间接性的特征,即裁判机构通过赋予公司只有股东才享有的特权或豁免而间接地遵循了重要公共政策或法律特别规定,实现这一联结的桥梁便是股东与公司人格上实质同一的事实状态。换言之,内部人反向刺破中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冲突。因此,在决定是否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请求时,裁判机构就不能像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面临直接冲突时那样,认为社会公共利益一律优先于个人利益,而是应该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损害与赋予公司特权或豁免所促进的公共利益进行审慎的比较。只有在反向刺破给公司债权人带来的损失或不利影响小于赋予公司特权或债务豁免所产生的社会积极效应时,裁判机构才应该支持内部人的反向刺破请求。这一要件实质上是提醒裁判者在适用内部人反向刺破时,应充分考虑反向刺破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损害,尽量将这种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个层面的要件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遵循依次递进的逻辑,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内部人反向刺破结果要件的整体判断。
七、 结 语
如前所述,内部人反向刺破是一项以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为根本依据的衡平制度,客观上偏向于照顾公司或其股东的利益,而非保护公司债权人之利益,相反,可能损害公司债权人之利益。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刺破制度制约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理念,是刺破公司面纱理论的一项重要创新。
由于国内法院固守传统刺破的观念,司法实践中至今尚未出现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案例,笔者结合美国的司法实践对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在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中,结果要件的考察比行为要件更为重要。在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中,支持法官做出反向刺破判决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内部人反向刺破的结果要件。质言之,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的成分要高于事实的考察。这一点与传统刺破更加侧重于行为要件的考察有所不同。也正因为这一点,国内法院不敢轻易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请求。这种故步自封的做法固然不可取,但是,从慎重适用的角度看,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内部人反向刺破的同时,在具体适用时也要严格把握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在法律的特殊规定下或出于维护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方能支持内部人反向刺破请求。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内部人反向刺破的行为要件中的过度控制因素或股东与公司人格实质同一的考量应采取客观判断标准,综合一系列事实情况来决定,不涉及当事人主观恶意的考察;结果要件方面,不能仅仅考虑权利主体的特殊利益,还应平衡责任主体乃至其他第三方的利益保护。总而言之,内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并非不可捉摸,可以经由理性分析得以把握。我国法院在面对内部人的反向刺破请求时,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勇敢地迈出步伐,而不是望而却步、拒之千里。
[1] 廖凡: 《美国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理论与实践——基于案例的考察》,《北大法律评论》2007年第8期,第632-548页。[Liao Fan,″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Reverse Piercing of the Corporate Veil in U.S.: A Case-based Analysis,″PekingUniversityLawReview, No.8(2007), pp.532-548.]
[2]G.S.Crespi,″The Reverse Pierce Doctrine: Applying Appropriate Standards,″JournalofCorporationLaw, Vol.16, No.1(1990), pp.33-69.
[3]S.M.Bainbridge,″A Critique of the Corporate Law Professors’ Amicus Brife in Hobby Lobby and Conestoga Wood,″ 2014-04-10, https://ssrn.com/abstract=2399638, 2016-03-22.
[4]S.M.Bainbridge,″Using Reverse Veil Piercing to Vindicate the Free Exercise of Incorporated Employers,″ 2013-03-06, https://ssrn.com/abstract=2229414, 2016-03-22.
[5]R.B.Thompson,″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A Empirical Study,″CornellLawReview, Vol.76, No.1(1991), pp.167-188.
[6]朱慈蕴: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Zhu Ciyun,TheJurisprudentialStudyofDisregardofCorporatePersonality, Beijing: Law Press·China, 1998.]
[7]L.C.Heilman,″C.F.Trust, Inc.v.First Flight Limited Partnership: Will the Virginia Supreme Court Permit Outsider Reverse Veil-piercing against a Limited Partnership?″ 2004-08-10, https://ssrn.com/abstract=574181, 2016-03-22.
[8]E.Youabian,″Reverse Piercing of the Corporate Veil: The Implications of Bypassing ′Ownership′ Interest,″SouthwesternUniversityLawReview, No.33(2004), pp.573-596.
[9]朱慈蕴: 《论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要件》,《中国法学》1998年第5期,第73-81页。[Zhu Ciyun,″On the Application Conditions of 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ChineseLegalScience, No.5(1998), pp.73-81.]
[10]叶海燕: 《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兼谈我国公司人格反向否认制度的构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53-56页。[Ye Haiyan,″Reverse Piercing of the Corporate Vei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verse Disregard System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in China,″Journalof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No.1(2013), pp.53-56.]
[11]M.J.Gaertner,″Reverse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Should Corporation Owners Have It Both Ways?″WilliamandMaryLawReview, Vol.30, No.3(1989), pp.667-704.
[12]朱慈蕴: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年。[Zhu Ciyun,TheoriesandPracticesoftheSystemofDisregardofCorporatePersonality, Beijing: People’s Court Press, 2009.]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Insider Reverse Piercing of the Corporate Veil
Lin Chengduo Hu Bing
(1.International Colle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Junzejun Law Firm Shenzhen Office, Shenzhen 518026, China)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Insider Reverse Piercing of the Corporate Veil (RVP-I)″ include three parts, namely, subject element, behavior element and consequence element. With respect to subject element, the subjects of RVP-I include subjects of right and subjects of liability. A subject of right could be the corporation itself or its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or a patent company; while a subject of liability refers to creditors of a corporation, whether they are voluntary or involuntary ones. With respect to behavior element, a shareholder must have conducted behaviors of excessive control over the corporation to be pierced if any subject of right intends to apply for the use of RVP-I. Such excessive control over the corporation shall be neutral and a sum of a series of factual behaviors. It shall not be out of subjective malice of any shareholder, who may seek illegal interests by taking advantages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Instead, such control should be conducted just for the convenience of corporat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r due to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rporate operation and the daily life of the shareholder(s). Consequence element contains three sub-elements featuring a progressive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as below:
Firs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hareholder and the corporation to be pierced has reached a de facto status in which the personalities of the two became completely identical in essence due to the shareholder’s excessive control over the corporation. Secondly, some inequitable consequences against critical social policies or special legal rules (such as the loss of basic life dependences by a shareholder) will be caused by enforcement of a creditor’s rights. Finally, the losses or adverse effects caused by RVP-I to a creditor of the corporation are less than the public interests which will be promoted by granting the corporation some legal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that can only be enjoyed by its shareholder(s).
In this paper, the greatest innovation i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RVP-I.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in China, it is nearly impossible to find any papers or books dedicated to an in-depth study on RVP-I. Under such conditions, this paper has made an attempt to study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RVP-I. With rigorous studies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s,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of analyzing the three elements (subject, behavior and consequence) is adopted in the paper to give a thorough study on the subjec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VP-I and the rich judicial exper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other important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e research methods-comparative law study. Faced with the lack of RVP-I precedents in China, we resorted to the numerous judicial prece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lated to the subject, from the first supporting RVP-I case judged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Minnesota in 1985 to the latest series cases against the Secret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caused by 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summarizing the analysis thoughts of the US courts in applying the RVP-I principle. Meanwhile, we have studied a lot of related papers written by American scholars who have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es on RVP-I and acted as a continuous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new ideas to us. This paper is not simply intended to introduce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of the RVP-I practices or theoretical researches in the US, but to give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RVP-I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 referenc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VP-I principle in China.

insider; reverse piercing; corporate veil; constitutive elements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6.03.223
2016-03-2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7-07-29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33-6000/C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11XNF011)
1.林承铎(http://orcid.org/0000-0002-0533-0135),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民商法、经济法研究; 2.胡兵(http://orcid.org/0000-0003-0522-0339),男,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人民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