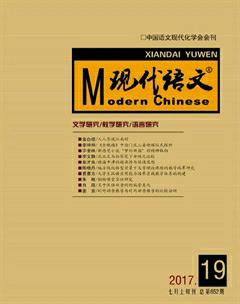论经学家王昶的词学理念
摘 要:作为经学家,王昶以重考据的态度编选了《明词综》等词选;作为词学家,王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醇雅”词论。将两种身份结合起来,通过对其清代诗经学的解读,可以看出经学家王昶推崇的词风是平和醇雅的一派。
关键词:王昶 经学 词学理念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称兰泉先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乾隆十九年(1745)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著有《春融堂集》,编有《湖海诗传》《明词综》《国朝词综》《琴画楼词钞》等。
王昶是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师从惠栋。作为一名经学家,他们自我的身份认同首先是经师,经师、文士之分被他们一再强调。文学与思想密不可分,文学是表现思想的途径之一。这些经学家往往在经学研究之外也从事各种文体的创作,其中一些经学家在文学方面不乏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过,经学家的文学观并不是纯文学的,而是把文学安置在经学或道学的体系中,使之成为沟通人与世界,传递真理与智慧的一种有效工具。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之下,王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词学观。
一、作为经学家的王昶
王昶早年求学于经学家惠栋,深受惠栋影响,钻研经学儒术,以汉学为宗,探究音韵训诂之学;也热衷于当世诗词的搜集和整理,先后编纂《湖海诗传》《青浦诗传》《明词综》《国朝词综》《琴画楼词钞》等,以宣扬沈德潜的诗歌“格调”说和浙西词派的词学理念。
乾嘉学派推崇的是一种无征不信、证据优先、事实重于义理的朴实学风,有时也被称为“乾嘉朴学”。朴学的学术特色是力求屏蔽主体,主张从材料、事实出发,探本求源,取真求实。这一重考据的学风成为有清一代的主流学术,在词学方面则催生出词籍整理、词韵修订、词律编纂等一系列风潮。这一时代风气对王昶产生重要影响,他编成《明词综》《国朝词综》,其中《明词综》共收明代词人387家,词作604首,大致反映了明代词坛创作的实际风貌,在编选时,做了大量的文献考证,在诸如作者生平著述的考证以及评论资料的选辑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二、作为词学家的王昶
王昶不仅是经学家,还是清中期著名词学家。他的词学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编纂词集,先后编成《明词综》和《国朝词综》,不仅搜集了大量明清词的资料,为后世留下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并在编撰过程中体现了自己的词学观念;二是词集作序,他为友朋、门人作序表达对词的一些基本看法,是研究他的词学思想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始资料(这些序文均收录在他的《春融堂集》中);三是随感评论,在编撰《明词综》和《国朝词综》时作的一些札记,除收集和记录一些文献资料外,主要是随感性的评论,简短而精练,能反映作者的真实思想(详见《西崦山人词话》)。
从整体来看,王昶的词学思想以崇“雅”为核心,以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作标准为准则,如他《琴画楼词钞自序》中批评元明词人时,专门提到“宋末诗人”一类,认为他们“于社稷沧桑之故,江湖萍梗之意,隐然见于言外”[1],并反问“岂非变而复于正与骚雅无殊者欤”[2]。他所指“骚雅”的含义,与朱彝尊有了一些不同,更接近于“醇雅”的意思。他更看重南宋雅词清冷的意象和悠长的韵味,强调一种清闲幽雅的生活情趣。他对姜、张为代表的南宋词的理解,也偏向于一种清丽幽雅的词风。
在王昶的词学论著中,提到较多的有七个人:南宋的姜夔、史达祖、张炎、王沂孙,宋末元初的张翥,清代的朱彝尊与厉鹗。他论词时提到次数较多的作品是姜夔的《暗香》《疏影》,认为它们最能代表清丽幽微的词学风貌。至于这些作品背后的复杂情感,则很少强调。总之,他对南宋雅词的理解明显偏重于“幽洁妍靓”的风貌特征,这与早期浙派词人的观点不同。
基于這种理解,王昶对雅词的创作有了一种新的、有别于前人的看法,那就是将清雅的风格与闲适悠然的生活联系起来,强调后者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类似的表述在《西崦山人词话》中也有。如他在谈到施绍莘的创作时就说:“施子野绍莘居松江之佘山,筑小园,有半闲精舍、春雨堂、无梦庵、诗境散花台、太古斋、霞外亭、三影斋、罨黛楼、语花轩、旁室轩、蕉雨轩、西清茗寮、众香亭、秋水菴、聊复轩、妍稳阁,极山水花竹之胜。又有歌童善三弦者曰停云,善琵琶者曰响泉,善头管及搊筝者曰秋声,善箫笛者曰永新,善摘阮吹笙者曰松涛霓裳,每作小词一解辄使歌之。”[3]王昶还认为,这种富庶、清闲的生活不仅保证了词作者有一种良好的心态和清雅的创作环境,而且从大的方面看,还可以使作者避免受到各种世俗事物,包括各种现世观念的冲击,保持一种娴静与优雅的状态,孜孜于雅词的创作。
可见在王昶的观念中,清净的环境与闲适的生活是创作雅词的重要因素。他的《青浦诗传自序》在谈到词的创作时,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又附以词二卷,亦皆清虚骚雅,微婉顿挫,足为倚声者法,可谓盛矣。盖吾乡溪山清远,与三吴竞胜,而地偏境寂,无芬华绮丽之引。士大夫家云烟水竹间,起居饮食,日餐湖光而吸山渌,襟怀幽旷,皆乾坤清气所结。往往屏喧杂、爱萧闲、励清标、崇名节,居官以恬退相师,伏处以孤高自励。性情学问,追古人于千载之上,从容抒写,归于自得。故如明中叶以后,空同、历下、公安、竟陵,纷呶奔走,四方争附其墰坫,以此哗世炫俗。而吾邑士大夫附丽者独少,此固昔贤自守之高,而为家乡后进读其诗仰企其人,当如何流连跂慕奉为轨则欤。”[4]
除此之外还有一重要因素,就是其编纂《明词综》的过程中,他对明词的弊端有了比朱彝尊更为深入、切实的体会,因此对雅词的推崇也更为明确。除了要求继承白石、玉田、碧山的醇雅词风外,他还提出三方面的要求:一是守律,所谓“守律也严”,具体说来,在词律方面,词之所以有词律,主要是为了与词乐相配合,守律的主要目的就是“和以人声而无不协也”[5],为的是词与乐的相和谐,据此提出了“诗雅故音雅,音雅故乐雅”[6]的观点;二是题材内容上,所谓“取材也雅”;三是词语方面,则是要“汰其粗厉亵媟者”[7]。
就整个清代而言,词学的发展有一种“以诗论词”的特征和渐趋强化趋势,主要是儒学诗教对词学的不断渗透。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刚的“肌理说”都活跃于这一时期,其中沈德潜的“格调说”论诗以儒家诗教为旨归,而王昶又是“格调派”的副将,深受沈德潜诗学的影响,因此,在他的词学观念中不免会有儒家诗教的印迹。
三、经学家王昶的词学观
对清代经学家来说,经学包举古今一切,只要不背离经学的本体地位,侧重修辞的文学也可以有适当的地位。明末陈子龙已将风骚言情之旨通之于词,清初朱彝尊进一步指出词中儿女之情可通《离骚》、“变雅”之义。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昶,他既是浙派词人,又是沈德潜诗学的传人,同时也和张惠言一样是汉学大家。他认为词其实就是诗之变体,故反复表达此种观点:“词,《三百篇》之遗也。”而姜夔、张炎等人“以高贤志士,放迹江湖,其旨远,其词文,让物比兴,因时伤事,即酒食游戏,无不有‘黍离‘周道之感。与《诗》异曲而同工,且清婉窈眇,言者无罪,听者落泪”[8]。已经将《诗经》比兴之义赋予了词。
他明确指出词为“三百篇”之苗裔,并以词的题材内容区分雅俗两类:“柳永、周邦彦辈不免杂于俳优”[9],是俗的一类。而姜、张诸人属于雅的一类,其作“与《诗》异曲而同工”[10]。同时,他又强调风雅正变的区分,并将创作题材和内容作为区分的主要标志。他在《国朝词综自序》中指出:“且夫太白之‘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黍离》行迈之意也;志和之‘桃花流水,《考盘》《衡门》之旨也。嗣是温歧、韩偓诸人,稍及闺襜,然乐而不淫,怨而不怒,亦犹是《摽梅》《蔓草》之意。至柳耆卿、黄山谷辈,然后多出于亵狎,是岂长短句之正哉!”[11]这里他区分了三类词人,第一类是李白和张志和,属于“正”的一类,是最高境界;第二类是温庭筠、韩偓,在可以接受范围;第三类是柳耆卿、黄山谷辈,属于“亵狎”,已经违背了“雅”的原则。
应该注意,王昶的词多作于早年,而词论都发于晚年,是自觉以经学贯穿文学。他告诫汪中“不审足下之穷经,将取其一知半解、沾沾焉抱残守缺以自珍,而不致之用乎?抑将观千古之常经,变而化之谓之通,推而行之谓之事业乎?”[12],其意见是要以经为根本之学,同时要求诗歌应该与史同教,有“为恶者惧,为庸众者愧,用以力奋于善”[13]的功用。论词,仍是以《诗经》为标准,认为“乐而不淫,怨而不怒”才是词统之正。
如果单看王昶的词论,固然可以说他在尊词体,但如果结合他的经学、诗学论述,则不能不说他是以《诗》义衡量、解释词这一文体。虽然王昶和张惠言对词的宗主各异,但在贯通《诗》学、主张比兴上却是一脉相承的。著名经学家许宗彦就说:“自周乐亡,一易而为汉之乐章,再易而为魏晋之歌行,三之长短句。要皆随音律递变,而作者本旨,无不滥觞楚骚,导源风雅,其趣一也。故览一篇之词,而品质纯驳,学之浅深,如或贡之。命意幽远,用情温厚,上也。辞旨儇薄,冶荡而忘反,醨其性命之理,則大雅君子弗为也。”王少寇述庵先生尝言:“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所以为高。亡友阳湖张编修皋文为《词选》,亦深明此意。”[14]许氏之意,王、张二氏论词相承之处在于“命意幽远,用情温厚”,都能以《诗》之比兴贯通于词。
王昶身处乾隆盛世,继承的是强调雅正的盛世诗学,对《诗经》的理解也是如此。他说:“《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郑君注云:‘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发。然风以述治道之遗化,颂以美盛德之形容,则其源固周弗出于正者,唯出于正,是以直陈之为赋,曲陈之为比与兴,无所之而不宜。诗有六,要归于雅焉,可知矣。”[15]雅正之说落实到词论上,他所推重的是南宋词人的“社稷沧桑之故,江湖萍梗之意”[16],感情是“哀时感事”[17]“阂周哀郑”[18],表现手法是“缘情赋物”[19]。
另外,王昶还明确提出修养与人品的问题,以人品论词品,以为词人的为人与修养决定了词的雅俗与高下:“余常谓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如晁端礼、万俟雅言、康顺之,其人在俳优戏弄之间,词亦庸俗不可耐。周邦彦亦不免于此。至姜氏夔、周氏密诸人,始以博雅擅名,往来江湖,不为富贵所熏灼,是以其词冠于南宋,非北宋之所能及。暨于张氏炎、王氏沂孙,故国遗民,哀时感事,缘情赋物以写闵周哀郢之思,而词之能事毕矣。世人不察,猥以姜、史同日而语,且举以律君。夫梅溪乃平原省吏,平原之败,梅溪因以受黥,是岂可与白石比量工拙哉!譬犹名倡妙伎,姿首或有可观,以视瑶台之仙,姑射之处子,臭味区别,不可倍蓰算矣。”[20]乾隆时期处于太平盛世,不存在“闵周哀郢之思”,因此他的标准就集中在“清雅”这一点上。
王昶对于“醇雅”词风的提倡以及对于闲适风雅生活氛围的看重,可以看出,他推崇的词风是风雅中平和的一派,是盛世士大夫和缓心态的反映。
(本文为2015年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人才国内外访学研修重点项目[gxfxZD2016225]。)
注释:
[1][2]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一),塾南书舍,清嘉庆12年刻本。
[3]王昶:《西崦山人词话》(卷一),稿本。
[4]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5]王昶:《国朝词综自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6][7]王昶:《赵升之媕雅堂诗集序》,《春融堂集》(卷三十八)。
[8][9][10]王昶:《姚茝汀词雅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11]王昶:《国朝词综自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12]王昶:《与汪容夫书》,《春融堂集》(卷三十二)。
[13]王昶:《与顾上舍禄百书》,《春融堂集》(卷三十)。
[14]许宗彦:《莲子居词序》,见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734册,清嘉庆刻本。
[15]王昶:《赵升之媕雅堂诗集序》,《春融堂集》(卷三十八)。
[16]王昶:《琴画楼词钞自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17][18][19]王昶:《江宾谷梅鹤词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20]王昶:《江宾谷梅鹤词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陈海银 安徽巢湖 巢湖学院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 23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