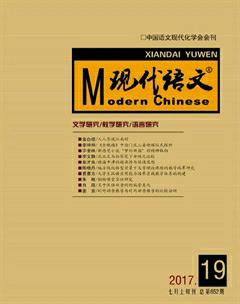旧瓶与新酒
沈从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文体家,是已成定论的,故以文体为核心的沈从文作品艺术研究一直是一门“显学”。除此之外,沈从文可否被称为“思想家”?对于民族性格的改造、文学经典的重造、现代知识分子的建构等命题,他的思考方式、文化心理、生命哲学有怎样的独特之处?随着这些问题的提出,沈从文的思想价值的重估已经逐渐成为沈从文研究的热点。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在沈从文思想研究方面有所贡献的论著有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赵学勇的《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吴立昌的《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影响较大的论文有凌宇的《从苗汉冲突的撞击看沈从文》、赵园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张清华的《抗拒的神话和转向的启蒙》。这个时期的沈从文思想研究带有鲜明的文化启蒙的印记,多从肯定的角度凸显沈从文思想的现代品格。例如,赵园认为沈从文有旧式文人的文化保守性一面,但他关于人的改造的思想,以及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经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反复对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正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凌宇认为沈从文虽以“乡下人”自称,但他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而是从西方文化中获得理性启示,在苗汉文化比较中取证,从而获得现代意识的乡下人;与“乡下人”的现代品格相应,“人性”——“生命”是沈从文思想的核心。张清华从“浪漫派”与沈从文的关联出发,梳理了西方原生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从文化发展史的历史逻辑上认定沈从文的“湘西神话”与“历史记忆”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而是在反思现代性危机的前提条件下对审美、文化、历史的观照,并以此作为对“五四”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文化语义和话语操作中的“当前化”和政治化后果的中和,是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文化参照系的反转。19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期,沈从文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受到了学界的进一步关注,代表性的著作有周仁政的《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张新颖的《沈从文精读》、吴投文的《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代表性的论文有刘一友的《沈从文与楚文化》、王继志的《沈从文美学观念中的‘超人意识》、刘洪涛的《沈从文小说价值重估》、吴正锋的《论沈从文与存在主义的关系》、贺桂梅、钱理群的《沈从文<看虹录>研读》。这个时期的沈从文研究有意淡化文化启蒙色彩,强调了沈从文思想的独特构成因素,凸显了巫楚文化、儒释道的非理性精神在沈从文思想中的分量。最近十年间,沈从文研究的成果与史料的重新发现是分不开的:裴春芳对《摘星录·绿的梦》的发现,使《看虹摘星录》得以恢复本来面目;解志熙的《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感时忧国有‘狂论——<战国策>派时期的沈从文及其杂文》为我们呈现出了沈从文“浪漫派”文人与杂文家的双重面影。尽管解志熙在沈从文与“启蒙”的关系上认同了以往研究者的定论,认为沈从文通过理想人性的文学抒写来启发民族性之改造的人文理想,是继承了“五四”之启蒙的“人的文学”的正统,与鲁迅的乡土写实小说之改造国民性的旨趣是一脉相承的。但他对鲁迅和沈从文在民族性改造方面的同中之异还是做出了区分:鲁迅的小说以及杂文对国民性多严苛的批判;而沈从文的多理想化的书写,是源于他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使他不能赞同用革命斗争来改造中国社会,而期望用人性改良来完成民族国家的重建。李斌的《沈从文与民盟》以史料为据,梳理了沈从文与民盟的关系,凸显出了沈从文对“人民革命”的态度和其自由主义文人的立场以及这种立场与他建国前后人生选择的关联,从另外一个角度呼应了解志熙的观点。总体来讲,最近二十年的沈从文思想研究淡化了“启蒙”的视角,凸显了非理性精神在沈从文思想中的分量,对“乡下人”的经验与“自由主义”立场给沈从文带来的局限性有进一步的探究。在最近二十年的沈从文研究中,“启蒙”的视角之所以被淡化,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来自文学研究的外部条件的变化。从社会思想的宏观角度来讲,当今中国,有三股思潮在结构启蒙。它们分别是国家主义、古典主义和多元现代性。[1]从文化的角度上讲,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问题和“文化热”已经被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所取代,有人预言,“启蒙”“民族国家”作为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相联系的旧物将不可避免地被扔到了历史的故纸堆。
二是研究对象的内部因素。沈从文是一个情感型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浪漫因子、神秘气氛,这是沈从文不同一般的标志性特征,所以一些論者指出,从“启蒙”的视角和“人性——生命观”的路径解析沈从文,会抹杀沈从文的创作个性,应该从“非理性”的角度去研究沈从文。[2]
针对以上两个困境,笔者的理解是:面对“后工业化”“后现代”等花样翻新的一系列现代理论的冲击,中国学术界的唯“洋”是从,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的风气会造成理论的膨胀化和所指的不及物性。有些理论根本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有些理论则是用“新”的外衣掩盖贫弱、陈旧的内容。所以,不妨从20世纪一些经典理论出发,深入挖掘它的内在深度与延伸性,并发觉被这些理论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形式所遮蔽的丰富的文学精神、民族特色和介于可以言说和不可言说之间的专属作家的那个“个我”——与历史联结的“个我”,将会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既然“启蒙”和“现代性方案”是20世纪中国不能回避并经过历史验证的理论体系、话语方式,那么就不妨选取之作为阐释的视角和问题意识的构成框架,承接1980年代学人的研究思路,深入探讨一些迄今还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赵园认为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主要限于“诚实坚实”“勇敢雄强”这些属于意志品质的方面,而不及于“人格独立”一类更具现代特征的内容,“同时代作家大多是由批判奴性——封建依附性开始了‘国民性的思考的,沈从文的思想却另有起点。因而在看似相近的思想趋向间,也仍然显示着思考者思想根柢(尤其是文化思想)的不同。这‘同中的‘异也许更有研究价值。”[3]后来的研究者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更加深入的挖掘,因此沈从文对启蒙所作出的独特思考也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最近几年的沈从文研究中,解志熙独出一帜,强调了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生命主义对沈从文“人性——生命”观的影响,深化和细化了沈从文“人”学思想研究。但能否以此和之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沈从文的“人”学思想做一个系统的归纳和研究?再者,沈从文通过人性改良来重建国族的启蒙之路就真的没有价值和意义了吗?笔者认为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其次,19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启蒙的视角会遮蔽沈从文的特殊性,非理性精神才是沈从文小说的思想价值的核心与基石。其实,理性与非理性、感情与意志,如果从更大范围上讲,都可以被启蒙的人文内涵所统摄,(以赛亚·柏林认为)从更大范围来讲,浪漫主义本身也是启蒙的一部分,是一种“反启蒙”的“启蒙”,反对的是启蒙运动中的普世理性,继承了启蒙价值中的自由和个性创造,并在情感和意志的基础上将之发扬光大。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并不是在启蒙文学业已完成,反而暴露出理性主义的枯燥、对宗教观念的偏激,与自然的割裂、与道德根源的脱节等缺陷后才出现的。从文学功用上讲,它与理性主义一同担任了启蒙的任务。这也正是“五四”启蒙运动不同于西方启蒙运动的显著特点,也即各种分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话语逻辑,并有可能相辅相成、相反相悖的思想观念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五四”启蒙的思想资源。沈从文这个“浪漫派”作家与启蒙的交汇点就在此处。沈从文的地域特色、宗教情绪、历史语境写作、人与自然的观念都与原发的浪漫主义文学相接近,他的“工具重造”“文运重建”“民族品德重造”等又都是他对“五四”启蒙文学的续接,不同的是,“五四”启蒙文学以整体性的反传统意识作为“现代性”扫除障碍,而沈从文则以重建“湘西神话”、返回历史、从民族古井中汲取泉水等文化策略扫除障碍,表现出了“向后转”的价值取向。
总之,对“生命——人性”的推崇,对理想人性的重构、对民族国家的重建是沈从文毕生所着力思考的问题,也是他思想内部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启蒙的视角,可以凸显沈从文在处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湘西经验与现代理性等命题时的审美眼光,并将“都市”“湘西”互参的文化心理格局统摄到一个相对宏大而又自洽自足的体系,在与“五四”启蒙的顺向延续和横向对比中显现沈从文文化策略的独特性,从而全面整体地分析沈从文的思想价值。
注释:
[1]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2]刘洪涛:《沈从文小说价值重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3]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马新亚 湖南长沙 湖南省文联 41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