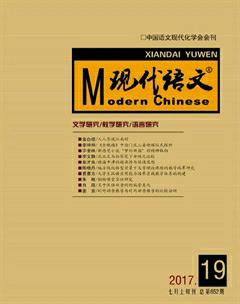新感觉小说“梦幻田园”的精神取向
摘 要:从20年代的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始,到30年代周作人、废名的自然浪漫,再到新感觉小说的都市田园轻歌,“田园”被文学家用作表达对现代文明自觉不自觉的反思、质疑、否定和背离的文学元素。在缤纷的上海画卷中,以都市文学的审美差异、情感取向和多元的价值态度为审美视角,用都市人的生存困惑为底色,闪念着田园的梦幻,书写着安宁与平静的祈愿,找寻着回归初心的精神救赎之路。
关键词:新感觉小说 梦幻田园 精神取向
在深受现代都市文明和商业文化挤压的背景下,新感觉派作家们书写着压抑扭曲的都市现代情绪,体悟着都市的异化与乡村的梦幻。在精神的游移中,进行着思想的快闪与深挚的田园文学想象,表达着都市现代情绪的文学指向与独异的精神价值取向。
一、梦幻田园的现实背景——妖冶的罂粟花
上海这座新兴的国际化畸形发展的殖民化的大都市,犹如一束美丽的罂粟花,奔放妖冶中充满了无尽的诱惑,浪漫华美中充盈着罪恶,安慰迷离中满含着艰涩,微甜香郁中预示着麻醉。新感觉作家的都市故事、都市风景、现代情绪的书写,探讨的是都市人内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无限纠结:横流的物欲、倒错的价值观让都市人深陷困惑、迷失直至绝望,饱受生理与心理极大的摧残折磨,最终走向人格的分裂与分化;优裕的都市物质的歆享中,不无自得的自怡中,精神却被放逐到深深的孤独虚无之中,都市人自动被动地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沦变多余人和零余者,“危险而华美的城市,一只倒覆之碗,一朵毒蛇缠身的花。”[1]
刘呐鸥以《都市风景线》为题,通过病态的现代上海景观,在错杂的场景(赛马场、夜总会、电影院、大旅馆、小轿车、富豪别墅、滨海浴场、特别快车)快闪中,展现都市人空虚糜奢、腐朽堕落的生活常态,表达都市人的现代文明感受和情绪,言说对都市之恶的反叛、悖逆而又依恋难舍。在《礼仪和卫生》中,红男绿女唯乐是图,无顾及追逐着本能欲望。可琼当着丈夫律师姚启明的面公开了与秦姓画家的私通关系,还动员自己的妹妹去满足丈夫启明的欲求;《热情之骨》法国青年比也尔近来遭遇到的尽是不愉快的事情,但第一次看到东洋花店女郎玲玉便不由自主为之倾心。在正义道德可以用金钱置换的时代和地域里的都市人的精神隔绝中,玲玉用自己的贞操向自己所心许的人换点紧急要用的钱来;《游戏》中都市的一切如死掉一样,人如蚂蚁,街灯像肺病的患者的脸;都市的《风景》太古一样沉默的大沙漠,“一切都会的东西都是不健全的”。
穆时英作品中,都市人充盈着极度的幻灭感。经济的畸形繁荣所导致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都市人由于生存竞争而产生的信任滑坡、情感危机的对立,使得中小资本家、职员、知识分子成为被生活压扇了的和被生活甩出正常轨道的“都市贫血者”。《黑牡丹》中的舞女在都市的夜色中,像一朵有着倦态的憔悴的花,被裹挟在生活的污泥浊水中,离开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这些人竟然不知怎样去生活;《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全是都市的失意者:商业大亨胡均益、昨日黄花黄黛茜、失去工作的缪宗旦、失去爱情的郑萍和怀疑一切的学者季洁;《白金的女体塑像》中谢医师成为节欲独身和性欲亢进的变态人;上海成为一座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上海狐步舞》);既有黑社会的凶杀、珠宝掮客的骗局,又有母子乱伦、肉体出卖(《中国一九三一》)。施蛰存笔下的人物多是生活在都市底层的小人物舞女、小商人、小职员,他们被强力挤压、情状残酷:《鸥》中洋行小职员寂寞无聊,饱受生活的煎熬、压抑;《薄暮的舞女》素雯,被迫与“咬人家肩膀和手指的水鬼跳舞”;穷苦的村姑《阿秀》被卖入大城市后,只能是去法工部风化处领取一張秘密卖淫照后沦为妓女;《魔道》《夜叉》《旅社》中的人物面对现代都市社会的压迫,只能通过幻想、生病等手段逃离生活和现实。
二、梦幻田园的文学想象——虚拟与外化
都市文明和商业文化的强力挤压,都市人难以安身立命。在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享乐与隐忍、乡村和都市的徘徊中,肉身无寄、灵魂无依。作家只能通过寻求虚拟与外化的自然与家园来给予抚慰,在渴求生命的本真与人性归属的乡村诉求中完成都市人的文学人生想象。
刘呐鸥的梦幻田园有两个特点:一是把田园的底色安置在都市的漫反射的光影中。《热情之骨》中,比也尔只能通过对美丽宁静的法国南部乡村小景的回忆慰人慰己,“我家乡的小村是围聚在橙树的绿林中的。而且我也曾在阳光和暖的橙树下献给了真实的心肠,也曾在橙香微醉里尝了红唇儿的滋味。我每喝香橙水,闻到了那种芳烈的气味,就想起一对像地中海水一样地碧绿的眼睛”;《游戏》中街上喧嚣的杂音“都变做吹着绿林的微风的细雨”,轨道上的辘辘的车声幻化为骆驼队的小铃响。喧嚣的都市欲望常常被刘呐鸥的乡村小景所遮蔽,用片断的甜美冲淡都市孜孜的欲望,大自然只是都市男女释放激情的理想驿站,《赤道下》用异域情调实现人与自然的亲近与谐合,用“永远地浸透在这碧海上的美玉般的小岛的风光里”的乡村想象混淆都市的现实感知。企望有一处傍路开着一朵向日葵,期望映照着带黄的秋初阳光,用一头小毛驴,再配上毛驴上那位摇动着腰肢的纯情小姑娘来构筑《风景》;二是田园只是对农村现实的浮光掠影式的文学想象而已,是都市人的偶尔的一次远足,一段即兴的小景,是永远走不回的家乡,难以到达的远方。“茅舍,石桥,柳树,一切的风景都只在眼膜中占了片刻的存在就消灭了”。《风景》的车站只是在郊外第三个小站的“忽然飞过”“车中是满着,含着阿摩尼亚的田园的清风”,车外是拿着小竹竿向着天风大声叫喊的牧牛童和李树下像得了老鹰的攻袭警报一样的鸡群向着瓜田里争先地飞走。只是乡村中国的背影外加上关于西方的文学想象:为脱离了沉重的城市重压的束缚,在心理做一次怡然自得的家的遐想;像一次都市人野外普通的遇合,女的剪着短发身着欧化的短裙,“人们总知道她是从德兰的画布上跳出来的。但是最有特长的却是那像一颗小小的,过于成熟而破开的石榴一样的神经质的嘴唇”,以及“明亮的金属声音”;从站长的眼中你可以知道这一对男女,一个是要替报社去得会议的知识,一个是要去陪她的丈夫过个空闲的week-end。刘呐鸥的田园叙事尽管简略,但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都市人对都市的一次叛逆,对都市生活的一种逆向延展,是对田园的一种别样注解。“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者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适合这种描写的方法。在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端,但是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带着‘非中国‘非现实的缺点。”[2]
穆时英的田园梦幻试图通过一些掺杂在田园牧歌中的异样的音符来表征都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侵害,反映都市人身上难以割舍的乡土恋曲、萦绕的情怀:虽久居都市,不同层面地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思维,但在内心的某些时空界域仍然给田园乡土留下一个情段,形成相当的能量集聚,适时凝聚为一种强力反弹,给都市和都市文化一个有力的回应和反击。穆时英的梦幻田园有三个特点:一是都市经验的乡村回溯。《黑旋风》是后都市的田园缅怀,“我”和朋友们对都市女人和汽车的仇视源于相同的贫困和江湖气;《咱们的世界》中“一眼瞧见他穿了西装就不高兴,再搭着还有个小狐媚子站在他身旁,臂儿挽着臂儿的,我就存心跟他闹一下”;二是都市和西方的元素的呈现。舞女《黑牡丹》穿过田野一路奔跑,来到圣五的乡舍,但这田园的乡舍有明显的城市印痕:田原里充满了烂熟的果子香、麦的焦香,轻风如阿摩尼亚赶跑了压在“我”的脊梁上的生活忧虑,大树底下的老人抽着的纸烟,郊外的空间好像是米勒的田园画;三是田园乡土的脆弱易逝。无论是《公墓》宁静美好的郊外,还是《田舍风景》的世外桃源,只是作家的一个希望、一种由衷的慨叹而已,作家笔下的田园梦幻只是为哀伤的恋情做的一个铺垫,优美而脆弱,仿佛一碰即碎。新感觉派小说中的人物没名没姓没家世,突然出现在文本中,突然从一个城市游荡到另一个城市。家在何处?乡土在哪里?家与乡土只能出现在特殊境遇下的幻觉之中,像《街景》中的“家”、《上海的狐步舞》中“捡煤渣的媳妇”,只在字面上有对乡土田园的隐喻性表现,但也表现出穆时英独特的乡土观念和对都市生活的逆袭。
施蛰存曾这样申述自己“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看一点书,种一点蔬菜仰事俯育之资粗具,不必再在都市中为生活而挣扎,这就满足了”[3]。
他的作品对乡土田园的书写实际上分为两个层面:因为乡村曾经的偏僻落后、贫穷愚昧,使得乡土人有了逃离乡土现实、改变命运现状、向往都市新奇的精神追求、追逐和渴求。然而真实的都市生活并不如所愿,当失望、恐惧和厌倦重重来袭,都市了的乡村人难以承受物质的欲求和精神的困怠,于是有了重返乡土再吟牧歌的想望,所有这些既为作家也为人物提供了一个文学想象地和精神栖居地。早期的《江干集》多描述乡村传统与形态因为都市文明的诱惑与侵染,慢慢消解式微,于是有了乡村对都市的强力植入和对都市的水土不服。《渔人何长庆》中的小渔村是个远离都市喧嚣的世外桃源,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生活和谐。渔姑菊贞难拒都市的诱惑来到上海,结果成了“四马路的野鸡”。后来长庆领回菊贞,重过和谐安宁的乡村生活。菊贞经管长庆的鱼摊,正直地做买卖,到后来他们有了儿子,儿子长大后,也会每天到鱼摊上来照料生意了。菊贞成为长庆的贤内助,作者在喧嚣、粗俗的都市为自己的精神寻求归宿。此外,《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两部小说集中描绘了都市的失业、失意人,患病的女人、家庭主妇;写了都市人对上海生活的不适、对田园生活的眷恋。《花梦》中的桢韦感于“如何销度这孤寂时光”;《妻之生辰》中的妻“过着一种怎么阴郁的生活”;《雾》里的素贞小姐有“很深的忧郁”;《港内小景》中主人公的“心之寂寞”,《蝴蝶夫人》中教授的“哀老之感”,《特吕姑娘》中女店员的忧郁病。用田园的宁静祥和与诗意的铺排,对举出都市与乡村的文化之境、显性与隐性的空间之情,呈现出一种自由的状态和乡镇故事中的都市情绪,表达出对乡村单纯生活的向往与挚爱。《雾》里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传统理解,《春阳》中被当作了外化于上海的一种乡村背景存在。
三、梦幻田园的文学精神取向——抉择与拯救
都市与田园的二元分化,使得新感觉作家在对都市文明的现代化中进而催生的都市病产生一种“反都市”和“逆都市化”的文学处置与想象,在发现乡村、圆梦田园的文学行动与追寻中弥平圆满精神家园的建构,体现了新感觉作家的精神价值取向。
理想与现实矛盾中文化观的抉择。“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更揭示了人在飞向远方、高空与落脚于大地之间选择的困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决与回归、躁动与安宁、剧变与稳定、创新与守旧……两极间摇摆的生存困境。”[4]在价值选择的双重困境之下,进不是退不能的直面与质疑之中,爱不得恨不能的纠结之后,新感觉作家试图打破乡土中国的二元分化,以对田园的梦幻色彩和笔触,找寻如何分离以及分离之后如何皈依陌生异质现代城堡的路径。作为都市的双面人、中间者,他们试图用梦幻田园的话语模式诠释自己对都市的理解、对乡土的言说。在乡土体制下的富裕家境,乡土背景中的西方都市文学的熏染之下的接受与适应。“国学”在前,“西学”在后的文化先行结构,传统文化在他们内心深处形成潜移默化的积淀,即便有后来“西学”的不断冲击,也总是难以抹去传统文化的印迹。“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最重要的基础是:国家、民族、土地;这些是他创作的根,是无法逃脱的。”[5]再加上西方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使得他们在情感态度上往往表现出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倚重。于是便有了刘呐鸥、穆时英对都市的暧昧,既有便捷与舒适的沉醉念念不忘:“啊……上海的华尔兹令人留恋”“上海啊!魔力的上海!”“你所吹的风是冷的,会使人骨麻,你所喷的雾是毒的,会使人肺痛”,但是“你是黄金窟哪!”“你是美人邦哪!”“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又有对现代都市的逃离远走的怨怼情怀:《赤道下》与世隔绝的小岛、碧海蓝天中中的身心修养,夫妻间琴瑟相合,整个天地都是属于我们的爱一般地。《田舍风景》为读者打开了一副美丽的山水田园画卷。
精神拯救中的人文关照。首先体现在价值观留恋中的生命力吁求。施蛰存身处乡村的视点立场对都市人的畸形病态予以谴责和创痛,刘呐鸥、穆时英对都市人的精神状态和疏离的都市秩序与成法发出了警示和抗拒。城市人在歆享现代文明之时,乡土的温煦越走越远、越来越淡,厚重的生命力渐次淡薄而萎缩。城市的发展所伴生的现代城市病,终究要依靠社会文明本身来解决。用乡土的价值观念来拷问审视都市的邪恶与堕落,用乡村人对故土的重返、都市人对牧歌的追寻来安放历经都市洗礼的不安的灵魂,是新感觉作家的一种文学选择,更是一种精神的皈依。用贫穷作为底色,用淳朴作为主调,调和富有与艰涩、欺诈与诚实、邪恶与正义,“于是在都市对乡村的一系列强硬对话中,一种近乎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被建立起来:都市——物和欲的象征,是‘人性丑陋的供养地;乡村——情与真的故乡,是圣洁灵魂的寄附处”[6]。其次表达了新感觉作家深刻的人文关怀。这无疑是新感觉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情怀的承继与发扬。通过对都市人生活状态和遭际命运的关注上升为对社会民生的关怀,并将社会问题的发现、诊测投注至问题的揭示与文化文学上的解决。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的贫富对照,包蕴着对富裕繁华罪恶丛生的上流社会形态的暴露讽刺,更难能可贵的是对苦难的城市底层的叹惋与悲悯;《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命运起伏跌宕反映出社会的失衡与都市的危机不安,表达了作者对都市命运的深切关注;《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从一个校对员的视角,探讨了社会公平的命题,书写了以林八妹为代表的都市特殊人群的不公的社会人生;杜衡的以描述普通人生存现状的作品有《蹉跎》《墙》《人与女人》《在门槛边》《再亮些》《重来》,通过现代都市文明渗入传统家庭并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与颠覆,表达了女性人生的艰难和无奈,反映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四、结语
新感觉派作家基于乡村与都市的挣扎徘徊,在缤纷的上海画卷中,用都市人的生存困惑为底色,闪念着田园的梦幻,在内心形成了强烈的“反都市”情结。在对梦幻田园的向往和留恋之中,表达出人类对生命归宿的诉求,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这为中国都市文学的发展提供具有独异特色的表现方式与文学视点。
注释:
[1]慕容雪村:《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2]杜衡:《關于穆时英的创作》,现代出版界,总第9期,第10-11页。
[3]施蛰存:《北山散文集(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
[4]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30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5]施蛰存:《沙上的脚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6]叶中强:《从想象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毕金林 河南南阳 南阳理工学院师范学院 47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