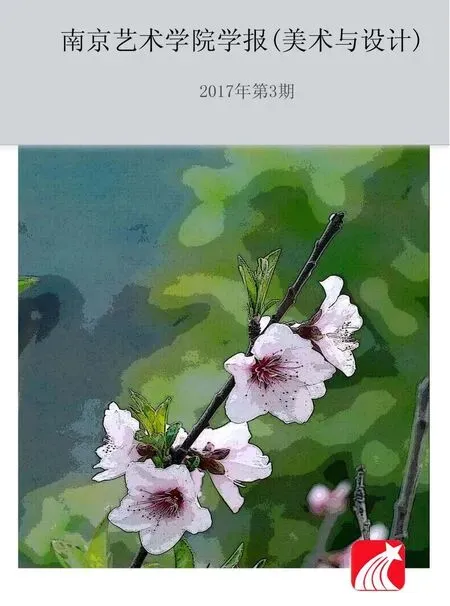非衣与招魂
——马王堆、敦煌、吐鲁番及丝路沿线墓葬文化关系研究
王晓玲(昌吉学院 美术系,新疆 昌吉 831100)
非衣与招魂
——马王堆、敦煌、吐鲁番及丝路沿线墓葬文化关系研究
王晓玲(昌吉学院 美术系,新疆 昌吉 831100)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以其样式独特、图像神秘而颇受学术界关注。T形帛画的名称和功能一直是学者们争讼不已的两大主题。本文基于T形帛画图像本身,结合考古资料、丧葬礼仪、宗教意识和民俗文化背景,认为非衣图像叙事空间主要由冥都和仙界构成,而不是地下、人间和天界;非衣反映了鬼神信仰,铭旌源于儒家文化,二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混同;非衣在丧葬礼仪中被视为亡魂栖息物,起着招魂、引魂入棺与圹的作用。但铭旌意在标识死者身份、名讳。在墓室空间,非衣正面向下,服务于亡灵,充任亡灵转生神仙的程序示意图,而铭旌正面向上,不具备此功能。非衣类图像首现于湖南楚墓,在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地区广泛传播,经由敦煌而止于吐鲁番,清晰地呈现了不同地域的丧葬文化传播演化的脉络与相互之间的关系。
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考古;丧葬礼仪;民俗信仰
一、非衣诸说评议
1972-1974年, 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了T形帛画,(见图1)保存完好;3号墓也有出土,虽画面漫漶,比较残破,但画面构图、主体形象、绘画主题和1号墓所出大致相仿。两幅T形帛画出土时均覆于棺盖上。至于其性质,学界人言言殊,或曰非衣,或曰铭旌,甚至还有画幡、画荒、旐诸说。其中,后面几种说法论据不足,难以成立,学界多不取,兹不复赘。笔者不揣浅陋,仅就非衣和铭旌二说略作申论。

图1 马王堆1号墓T形帛画
先说非衣,持此观点者以唐兰、俞伟超①俞伟超.《关于帛画》,《文物》,1972年第9期,第60页。、史树青、商志②商志 .《马王堆一号汉墓“非衣”试释》,《文物》,1972年第9期,第43页。等先生为代表。唐兰认为:“帛画就是竹简里的非衣”,又言“非”即“菲”,是古代障蔽门扉的草帘,“非衣等于是扉衣,是挂在门扉上的衣”。[1]此说或有不妥。其一,帛画是丝织品,不是草制品;其二,非衣的T形与草帘的形状恐难关联;其三,汉代扉衣与非衣的尺寸是否匹配,亦属未知。史树青以1954年长沙晋周芳命妻潘氏墓出土的一件石刻衣物券上所记“绮飞衣一双”为例,指出飞衣“应是非衣的同音同义词”[2]。史先生所言依石刻衣物券,可以信从,但“似为妇女穿的长大的衣服”之说不能成立,因为马王堆3号墓的墓主人为男性,亦有非衣出土。俞伟超、金维诺、商志 等先生均认同非衣说。巧合的是,2006年,青海柴达木盆地发现了一幅西汉早期帛画,亦呈T形,画面图像和马王堆T形帛画酷似。论者据此两点将其定性为非衣。

图2 武威磨咀子M23号墓
马王堆1号墓出土简244和简245上分别记有“非衣一,长丈二尺”和“右方非衣”之语。马王堆3号汉墓简390也有“非衣一,长丈二尺”的记述。经稽核,马王堆1号墓和3号墓所出随葬物品,除了“土牛”和“土马”之类未见实物外,其余差不多能与遣策上的名称对应上①《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第43页。。是故,马王堆1号墓和3号墓出土的“T”形帛画与“非衣”是对应的,“T”形帛画为非衣无疑,青海柴达木帛画也同样为非衣。
当然,对简上所记非衣与T形帛画实物是否对应的问题,学界尚有异议。②朱青生主编.《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贺西林《从长沙楚墓帛画到马王堆一号汉墓漆画与帛画——早期中国墓葬绘画的图像理路》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第459页。然则,若T形帛画不是非衣,那么竹简上所记非衣又当为何物呢,惜论者未予指明。
再说“铭旌”(又称明旌或旌铭,简作“铭”)。此说指T形帛画为铭旌,以顾铁符、马庸③马庸《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与作用》《考古》1973年第2期,第119页。、金景芳④金景芳《关于马王堆汉墓帛画的名称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8(创刊号),第215页。、贺西林等先生为代表。顾铁符引《周礼•春官司常》“大丧共铭旌”和《礼记•士丧礼》“为铭各以其物……书铭于末,曰某氏某之枢”之说,并结合1959年秋在武威磨咀子23墓出土的覆棺物为例,(见图2)认为它们就是铭旌⑤顾铁符《关于帛画》《文物》,1972年第9期,第56页。。马庸、金景芳和贺西林等先生均认同此说,但对磨咀子汉墓出土覆棺物并未提及,难免美中不足,令人扼腕。

图3 吐鲁番人首蛇身图像
而金维诺、刘晓路和裴建平等先生的观点颇有不同。金先生言:T形帛画就是非衣,非衣形制同于铭旌,二者都可悬挂,二者间存在着一定联系;非衣上的画像不仅用来别死者,还可用于招魂,故非衣与复衣也存在联系。⑥金维诺《从楚墓帛画看早期肖像画的发展》,《中国美术史论集(上)》,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3,第16页。此说甚是。惜金先生仅从铭旌与非衣外形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联,而未触及非衣和铭旌、非衣和复衣之间内在的联系纽带。裴文将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磨咀子汉墓、阿斯塔那古墓群类似帛麻覆棺物命名为旌幡,(见图3)并认为他们之间存在传承关系。这种旌幡要么只题写铭文,要么是日月和铭文,要么绘制死者生前形象,用来招魂复魄和引魂升天。⑦裴建平《人首蛇身”伏羲女娲绢画略说》《文博》,1991年第3期,第83-86页。裴文可贵之处在于把山东、甘肃和新疆的类似覆棺物联系在了一起。然,非衣与旌幡之间如何联系,惜未予指明。刘文认为,非衣是旌幡发展的第二阶段,甚而认为,广州、临沂、武威发现的类似帛画皆为马王堆非衣的变异,武威乃旌幡和铭旌唯一并存之地,也是非衣消失之地。⑧参见刘晓路《帛画的流布、变异与消失》,《美术研究》1993年第1期,第59-62页。此说有以偏概全之嫌忽略了新疆的出土物,也忽略了旌幡、铭旌和非衣的内在联系与区别。
二、非衣与铭旌、旌幡、复衣之关联
《周礼正义》云:“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析羽为旌。”[3]《汉书》:“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应劭解曰:“旌为旌幡。”[4]不惟《汉书》,《史记》《春秋谷梁传》《谷梁传注疏》《后汉书》等典籍中也都有相关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卷一一七将“绥解为旌幡;《春秋谷梁传》中解麾为旌幡……诸如此类记载表明,九旗中的旌是旌幡;九旗之外的绥、麾是旌幡;旒旗谓铭,也是旌幡。概言之,在古代,旌幡是各种旗的总称,旗有九种,旗、旌为其中两种。⑨参见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五十三《司常》,中华书局,1987年,第2200-2207页。但《礼记疏》曰:“铭,明旌也。神明之精。铭音名旌音精。”可见,铭旌又作明旌,强调此类旌专用于鬼神之道,而不完全等同于绥、麾、旒旗等。
又《仪礼》云:“天子乘龙,载大旆。”郑玄注曰“大旆,大常也,王建大常,缪首画日月,其下及旒交画升龙、降龙。”[5]由此可知,天子级别的旗谓大常大常上不仅有日月,还有交龙图像及旒,一般的“常就只有日月图像。不论是马王堆还是临沂金雀山,抑或磨咀子和吐鲁番古墓,都不够天子级别。但是,这些墓出土的类似覆棺物上,大多数有日月图像。如吐鲁番人首蛇身交尾图像(图3)。磨咀子的一些同时有日月图像和铭文,也有只有铭文的。
所幸《周礼•夏官•司马》给出了答案:“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郑玄注曰:“死则于烝先王祭之。”是知,出现日月图像的,至少说明以下问题:一是墓主人是能使用大常的有功之臣;二是有功之臣的铭旌上出现日月图像亦符合丧葬礼制;三是出现了铭文和日月图像共现的旗,或日月、交龙共现,或日月、交龙、铭文共现的旗都属于常旗(大常、常)级别,亦曰铭旌。如是,马王堆和吐鲁番所出既有日月图像,也有交龙图像的,应该也是铭旌无疑。但是,马王堆出土竹简将其命名为非衣。
依非衣出土时的情景,或可找到问题的答案。
何介钧对非衣出土时的情景有如下描述:“非衣画,以细绢作地,因天长日久,出土时呈棕色。画幅全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顶端横裹—根竹竿,上系丝带,可以张举。中部、下部的四角各系一条长约20厘米穗状的青黑色麻质绦带。‘非衣’出土时,覆盖在内棺盖板上,画面向下,上端系带处置一玳瑁壁,壁上系着麻质的带。”[6]据此可知,非衣如旗,可以张举悬挂。
刘晓路先生依《说文解字》卷十一所谓“非,违也。从飞下翅,取其相背”之说,认为非衣是不能穿着的衣服,而不是能“飞”的衣服。但,凡是旗,遇到风就会飘扬,如《洛阳伽蓝记》中有“荣三军皓素,扬旌南出”之语。[7]“扬”者“飘扬”也。在三体石经①三体石经,三国(魏),存高38cm,宽32cm,现藏故宫博物院。中,“非”被写为“”,“非”是象形文字“”的今体,最初指鸟展翼飞翔。“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沙”[8]中的“沙”,就是“飞沙”。“非”通“飞”,非衣即飞衣②王晓玲《上天衣考》,《美术与设计》.,2016年第6期,第38页。。因此,非衣除了喻指不能穿的衣服之外,还喻指可以飘扬的旗。是知,非衣与铭旌皆旗类物也。
非衣与复衣因招魂而关联。《礼记•丧大记》:“复,有林麓,则虞人设阶;无林麓,则狄人设阶。小臣复,复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赪,世妇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9]《礼记•杂记》:“诸侯行而死于馆,则其复如于其国。如于道,则升其乘车之左毂,以其绥复。”《六臣注文选》曰:“旒旗谓铭,旌幡也。”[10]《法苑珠林》:鲁哀公葬其父,孔子问:“宁设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伯桃。伯桃荆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尸。愍魂神之寒,故改作魂衣。吾父生服锦绣,死于衣被,何用衣为?”[11]2788
由《丧大记》知,复衣因亡者级别不同而分为卷、屈狄、玄赪、弁服、襢衣、税衣等。《杂记》则说明,如遇“死于馆”之类的特殊情况,复礼也不能免,还应该如同死在自己国家一样。但是,可以用绥来代替复衣。不过,能用作复衣的绥,是亡者生前乘车之绥,属于亡者熟知之物。《六臣注文选》释旒旗为旌幡,而《法苑珠林》则表明,在复衣之外,还有魂衣。魂衣乃死者灵魂避寒之衣。它出现在“羊角哀往迎其尸”的叙事场景中,说明魂衣也可充当复衣。是故,丧葬礼制既规定,举行复礼时,需各用其服,又说明,如遇特殊情况,可用绥、魂衣等充当复衣,只要是亡者生前熟悉之物且能标识身份地位,就可用作复衣。而绥为旌幡,旌幡几近于铭旌,亦属旗。可见,旗亦是非衣与复衣产生联系的纽带。
综上可知,非衣与铭旌、旌幡、复衣都以旗为链接纽带。金维诺先生也断言:“可能在迷信鬼神的楚国,很早就流行这种画蟠……生前可预制,临死可作‘复衣’以招魂……死后可代替明旌以识别死者。”[12]然,非衣如何招魂,与铭旌有无区别,区别在哪,非衣招魂结束后,为何画面朝下等问题,金先生都未予指明。如若扬汤止沸,惟有再探其功能。
三、非衣之招魂功能及其转换
关于非衣之图像及功能,学界同样众说纷纭。鲁惟一④Michael Loewe, Ways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79, p. 31.和谢柏珂⑤Jerome Silbergeld, Mawangdui Excavated Material, and Transmitted Texts: Cautionary Note, Early China 8, 1982-83, pp.83-87.佥曰:试图通过不同文献材料的拼凑来阐释马王堆T形帛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受此启发,笔者推想,如果将非衣和铭旌纳入丧葬礼仪过程,通过非衣和铭旌在丧葬礼仪中的功能及其功能转换问题,或许能找到一些更加接近事实的线索。
在战国至西汉早期,古人的死亡观念中存在亡魂知返意识,故需招魂。古人的招魂过程一般由初亡招魂和入圹招魂两个阶段构成。《礼记•檀弓下》曰:“复,尽爱之道也,有祷祠之心焉”。招魂原因在于亲人不舍亡者,寄望通过招魂使其复生,同时,招魂归来受飨,拔除不祥,免为孤魂野鬼而遭困厄。遗憾的是,古文献关于非衣的记载甚罕,除了马王堆一、三号墓竹简和晋周芳命妻潘氏墓石刻衣物券之外,别无所见,更不用说记载非衣的招魂功能了。然则,非衣与铭旌联系甚紧,惟有还原非衣和铭旌参与丧葬礼仪的过程及细节,由此可推想非衣招魂功能之一二。
《周礼·春官宗伯》:大丧,共铭旌,建廞车之旌。及葬,亦如之。
《礼记·檀弓下》: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
《礼记·丧服小记》:复与书铭,自天子达于士,其辞一也。男子称名,妇人书姓与伯仲,如不知姓则书氏。
《仪礼·士丧礼》:为铭,各以其物。亡,则以缁长半幅,<赤+巠>末长终幅,广三寸。书铭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长三尺,置于宇西阶上。《仪礼注疏·士丧礼》:亡,无也。无旌,不命之士也……今文铭皆为名,末为旆也。
《法苑珠林》:幡,招魂置于乾地,以魂识其名,寻名入于闇室,亦投之于魄。或入于重室。[11]
从《春官宗伯》可知,初丧和送葬时,铭旌出场;《檀弓下》表明,丧礼中使用铭旌,是为了别死者;从《丧服小记》和《仪礼注疏》可知,虽然铭旌被广泛应用于天子到士的社会阶层,但是铭旌的尺寸和颜色需与亡者身份地位相符;不命之士,则无铭旌;从《士丧礼》可知,铭旌在初丧场景中是用于悬挂的,及至唐代,流行铭旌上写名字,把铭旌末端做成燕尾状。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上已有很多燕尾状铭旌招魂的图像。如河南南阳针织厂墓、唐河县电厂墓的骑马史掮燕尾状铭旌。《法苑珠林》表明,至少到唐代时,出现了用幡招魂的丧葬仪式,幡能招魂在于亡魂识得幡上名讳。据此,铭旌上的亡者名讳,也具招魂功能。有意思的是,记载这一社会现象的文献,不是儒家经典,而是佛典。这一点和上天衣在当时主流社会中的情况是一样的。①王晓玲《上天衣考》,《美术与设计》,2016年第期,第35-37页。这一点说明,儒学只认可铭旌以别死者的作用,而不认可铭旌的招魂功能。
至此,需要提醒注意者有三,其一是非衣图像上的日月和交龙图像非常符合铭旌类常旗的诸多表征;其二是非衣有悬系丝带,可以像铭旌一样悬挂使用;其三是非衣上的图像,除了日月、交龙图像能象征亡者身份外,墓主画像确实能够起到“皆画其象”“象其事”[13]的功效,起着和幡上题记一样的招魂作用。因此,初丧时,非衣充当复衣,招魂复魄;吊唁时,以别死者;送葬时,引魂入圹。非衣的功能在招魂与以别死者之间转换。
不过,铭旌随葬时,正面朝上,非衣则不同。
四、非衣的后续功能与道者的神仙思想
非衣画面的朝向昭示其观者与众不同。“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爵(雀)玄武顺阴阳”的汉代铭文铜镜,青龙胯下墨书“青龙在左”,白虎胯下墨书“白虎在右”的陕北神木大保当M16门扉画像,说明在墓葬中随葬物品出现的位置具有很强的预设性和较为固定的程式,通常情况下都遵循左(东方)青龙,右(西方)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对应方位来安排四神,星象常被安排在象征天宇的墓室顶、棺盖或墓志石涵顶部②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第1-14页。。虽然非衣和铭旌出土时都覆于棺盖上,但铭旌正面朝上,与非衣正好相反,正面朝下。一般认为,马王堆非衣由地府冥界、人间宴飨、天上神仙世界三部分组成。若然,则非衣覆棺时就应该画面朝上,至少可以向吊唁者宣示其身份和生前的权威与富贵,而不是画面朝下了。画面朝下,昭示其随棺入圹后观者不再是吊唁者和亲属,而是亡魂。如果非衣仅仅具有招魂、安魂、护魂和标识死者身份的功能,只需画上墓主人画像,而无需再画上如此繁复精美,且构思严整的其他图像了。可见,非衣在墓中发挥作用的是它的全部图像,而图像的服务对象则是墓主亡魂而非其他。
对此,姜生认为,非衣传达了墓主的道者③姜生《马王堆帛画与汉初“道者”的信仰》《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第177页。信仰和灵魂升仙转生的完整仪式和程序。④同上,第176-189页。唯其文对非衣底部的悬罄、鸱鸮、丹蛇以及翼龙翅膀上的仙人等图像未作研究。在贺西林先生看来,亡魂复魄入圹之后非衣将协助亡魂升仙。⑤贺西林.《从长沙楚墓帛画到马王堆一号汉墓漆画与帛画——早期中国墓葬绘画的图像理路》,朱青生主编《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第499页。惜贺先生未对亡魂如何借助非衣完成升仙过程予以解答。是故,有必要将姜、贺两位先生未及之问题置于丧葬礼仪当中,重读图像重构非衣各个阶段的叙事空间及其所蕴含的形解销化思想,揭橥非衣图像的后续功能。
《周礼》云:“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魄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所发扬于上为昭明。”《礼记•郊特性》亦云:“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14]而且,汉代人的厚葬风俗中包含着“不死其亲”的浓烈意识。往往把亲人的死亡看做魂魄的短暂分离。认为人因阴阳和合而生,阴阳分离则亡。人死,必然魂魄分离。阳为魂,阴为魄,魂魄聚则生,散则死。魂魄分离后,魂升于天,魄降于地。但是,如果死后也能魂魄聚合,不分离,就能再生。据姜生先生考证,辛追夫人和其子均为当时“道者”,深信形解销化之术坚信生前修炼得道、死后亡魂接受仙官指点(接受道书)并服食玉浆就能形解而成仙。而形解就是尸解尸解的核心价值是人死后魂魄合一,不留尸体,让尸体也成为像灵魂一样的东西(魄灵),升入天界,转生神仙,实现长生。
汉代人深信灵魂不灭。然则,辛追亡魂为何还要拜访禺疆获取不死之药?唯图肉身不死而形解,作为升仙之阶。因为汉代人认为,人死后虽然难免皮毛朽败,但只要精气仍在,魂神仍能 “复假此形而以行见”[15]186所以,墓主亡魂需服食使魄体不死之药后,魄体得以化为魄灵,并和魂合一,成为魂灵,恢复生前人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柱杖老妇(魂灵现身,假此形而以行见)的形象登天梯,上悬圃,受道书,饮玉浆的辛追夫人。但这里仍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作为道者,辛追夫人服食不死之药而重获人形,已经实现了死而不留尸体的形解销化愿望,缘何还要受道书,饮玉浆?唯图魂灵变形而神。是故,墓主人升仙而神的想法,反映了当时流行的道者信仰。
非衣图像所表现的重点乃由冥府而往天界的过程。画面下部为冥府和仙界,由三个叙事空间构成。画面上部,即鸱鸮和凤凰以上,构成天界。天界有两个叙事空间。整个升仙过程,也有两道程序,每道程序又包含若干步骤。画面底部冥府主要描绘了双鲛鱼、禺疆、丹蛇、鴟龟、长角神兽以及鱼暗示的海,组成墓主灵魂在冥府拜访禺疆的叙事空间;鼎等器皿、侍者、悬罄、羽人、壁翣组成服食不死之药的叙事空间;双豹、天梯、悬圃、侍者和拄杖妇人构成受道书、饮玉浆的仙界叙事空间。至此,墓主灵魂从冥府获得了上升天界的所有条件,完成了升仙成神的第一道程序。画面上,第一道程序的终结者是华盖下的鸱枭。第二道程序的接力者是凤和凰。华盖、凤凰、天门和司閽构成了升仙的叙事空间;神兽、云气、仙人、应龙、树木、九阳、三足乌、坐于应龙翅膀的仙女、月、蟾蜍、人身蛇尾神和几只禽鸟组成了升仙成神的叙事空间。其中,从乘应龙的仙人到人身蛇尾形象,是墓主灵魂最终转生神仙而因此获得长生的关键环节。赤青两条穿壁而过的龙构成了冥府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凤凰、左右对称且衔铎带而立的两条应龙和两位司阍及铎,启动了墓主魂灵在天界的旅程。毋庸置疑,四条向上跃动的龙,使非衣的整个画面呈现出由冥府向天界运动的升腾之势。
《易经上•乾传第一》载:“九五,飞龙在天。”“时乘六龙以御天。”《说文解字》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风而潜渊。”以及人们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16]或“亦将控飞龙而驾庆云”。[17]干宝《搜神记》载有陶安公骑赤龙而升天的故事:“陶安公者,六安铸冶师也。数行火。火一朝散上,紫色冲天。公伏冶下求哀。须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至时,安公骑之,从东南去。城邑数万人,豫祖安送之,皆辞诀。”刘向《列仙传卷上•萧史》载有秦穆公之女弄玉及其丈夫箫史成仙后乘龙凤而升仙界的故事:“萧史善吹箫,作凤鸣。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作凤楼,教弄玉吹箫,感凤来集,弄玉乘凤、萧史乘龙,夫妇同仙去。”《水经注集释订讹》卷十八和《仙传拾遗》也对此传说记载甚详。据出土帛画《人物龙凤图》、《人物驭龙图》可知,早在战国或更早的时候,龙凤已成为升仙的工具和象征。不仅如此,《山海经》、《周易》等,均有“神人乘龙”的记载。《三海经》中有138位神是人首蛇或龙身。可见,至少在汉唐时期,龙蛇之身实为神的特征。[18]
非衣底部表现的是冥府叙事空间。此空间由长角神兽、鲛鱼、玄龟、鸱枭、禺疆、丹蛇、鼎、特罄、鸱枭、壁翣、羽人构成的冥府世界。鸱枭在汉代被认为是会带来厄运的恶鸟,因为它的出现,尤其是其鸣叫声,往往和鬼魅即将现形联系在一起。但鸱鸮还是兼司死亡和再生的神①叶舒宪,《经典的误读与知识考古——以诗经鸱鸮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页第10期,第61页。。因此,墓主灵魂一旦从棺中外出显形,就会被鸱枭第一时间感知,并发出鸣叫声,从而让掌管冥府的禺疆神得知墓主灵魂即将来访的消息,及时保护并奉送不死之药。龟象征冥界,但也是长生、不死,活力永不衰竭的象征②朱彦民著,陈洪,李治安主编.《商代社会的文化与观念》,、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丹蛇为墓主灵魂寄主。《史记•高祖本纪》张守节正义引《陈留风俗传》云:“沛公起兵(约前209年)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宫招幽魂,于是丹蛇在水自洒,跃入梓宫,其浴处有遗发,谥曰昭灵夫人。”汉高祖着人招皇妣之魂入梓宫,却看到一条戏水的丹蛇跃入准备好迎接皇妣之魂的梓宫内,而在丹蛇沐浴戏水的地方还发现了遗落的发丝,意味着皇妣之魂已经寄托丹蛇之身而归。由此说明,丹蛇为灵魂化身的看法是得到了汉代皇家主流观念认可的。马王堆1号墓墓主灵魂入圹后,须像颛顼一样,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找到蛇或鱼(鱼妇是颛顼死后借蛇而化,颛顼复苏之体便以蛇或鱼显形③田春,《中国古代人鱼图像与传说的互释与演进》,《美术学》.2015年第2期,第99页。,辛追的寄主是丹蛇)等寄主托魂,才有机会转生神仙。如果灵魂不能及时托生鱼或蛇体,很可能在入圹后精气消散,遭遇灰飞烟灭的结局或成为幽魂而不能转生。丹蛇和龟所戴绶带为长寿和加官进爵④杜廼松著,《青铜器鉴赏与收藏》.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350页。之征兆,亦为墓主及亲人愿望之一。丹蛇盘绕于禺疆身畔,表明墓主灵魂托生之丹蛇正在等待不死之药。
羽毛帷幔与圆壁构成壁翣⑤贺西林《从长沙楚墓帛画到马王堆一号汉墓漆画与帛画——早期中国墓葬绘画的图像理路》,朱青生主编,《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壁翣上左右两位人面鸟身神,有人⑥孙作云《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画幡考释》,《考古》1973年第1期,第59页;贺西林:《从长沙楚墓帛画到马王堆一号汉墓漆画与帛画——早期中国墓葬绘画的图像理路》,朱青生主编:《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第461页。称之为羽人,也有的⑦商志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非衣”试释》,《文物》1979年第2期,第44-45页。称之为句芒。观两位人面鸟身神立于壁翣上,解释为得道升仙羽人似乎更近乎常理。栖于华盖下的怪鸟,多数学者佥言之为飞廉①杨辛、于民:《西汉帛画》,《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2期第103页。郭学仁:《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内容新探》,《美术研究》1993年第2期第65页。,亦有人称之为枭②孙作云.《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画幡考释》,《考古》1973年第1期:第58页。,还有人言为屏翳。窃以为,此鸟两眼大而圆,尖喙,其特征最与鸱枭接近,也与幽都③幽都一词,出自屈原《招魂》。氛围极其相配,该怪鸟在此象征墓主魂魄将获得再生,与鸱鸮的司职正相吻合。而不可能是鸟头鹿身或鸟身鹿头有角而蛇尾豹纹且无再生或护佑意义的风神飞廉,也不可能是云雨之神屏翳。
特罄是单枚使用的大型罄。一是非衣上的罄刚好是单枚,二是特罄因其“以其若出水之上”的特点,[19]又曰“浮罄”。禺疆所在之地为幽都水府,正是悬罄的处所。悬罄一旦响起,则预示着墓主灵魂即将穿越冥府,需要在此司职的仙官做好准备。因此,悬罄可能被作为冥府之主禺疆向众仙官通知不死之药已准备妥当的“鸣以聚众”的器物。另外,此处的特罄没有和其他乐器,如钟、笙一起出现,似与宴飨气氛不符。鼎乃禺疆盛放仙药之器皿。罄和鼎的组合场面也与墓主人贵族身份相符合,钟鸣鼎食是贵族方可享受的礼遇。
是故,上述诸神物,都被统一纳入冥府氛围,不死、再生、长生是冥府叙事空间传达的主题,与墓主亡魂的长生诉求非常一致。而绶带和罄鼎也与墓主的尊贵身份相符。
豹、天梯、县圃、仙官、拄杖妇人、道书、玉浆构成了完整的仙界叙事空间。豹乃守卫昆仑仙山④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水经注校(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县(悬或玄)圃(天梯、玉璧和两只豹象征昆仑县圃所在的昆仑仙山,即“帝之下都”)山门的神兽⑤姜生.《马王堆帛画与汉初“道者”的信仰》,中国社会科学.2014第12期:第177页。。《水经注》:“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玄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为太帝之居。”[20]2可见,墓主灵魂到达昆仑山就到了仙界,如若墓主人想成神,需要经过不死的凉风之山,成仙的悬圃,登上太(天)帝之居(九天)而神。
先说乘龙仙人。关于乘坐在应龙翅膀上的仙人有嫦娥说⑥游振群:《T形帛画形制与“非衣”之名的再思量》,第27页;安志敏:《马王堆新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考古》,1973年第1期,第47页⑦周世琦:《马王堆汉墓帛画日月神话起源考》,《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第99-104页;龚维英:《嫦娥化蟾蜍非古神话原貌》,《湖南考古集刊》第3辑,第243页。、常羲说⑦、托月女神说⑧何介均,张维民《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45-148页。、金沙神说⑨林河,杨进飞,《马王堆汉墓飞衣帛画与楚辞神话南方神话之比较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5第3期.以及墓主灵魂说⑩王伯敏,《马王堆一号汉墓并无“嫦娥奔月”》,《考古》1979年第3期,第274页;傅举有:《马王堆缯画研究》,《中原文物》1993年第3期第103页。等,人言言殊。但嫦娥奔月神话中绝少言及乘龙一事。而非衣图像信息却表明该仙裸足乘坐应龙,且衣服颜色和人身蛇尾者衣着非常相似面貌比拄杖的辛追形象年轻。是故,王伯敏认为此仙人乃墓主灵魂,几近确凿。墓主灵魂在冥界获得不死之药后,获得了魄(肉身)不死的机会,成为魄灵服食琼浆玉液、受道书后,魄体变得轻盈,年轻,魄灵获准进入天门,成为仙人,乘坐应龙遨游天界。
次说九阳。对于非衣图像的九颗红色圆,其中一颗有金鸟,为太阳无疑。剩下的八颗,因没有金鸟且与十日神话不符,诸论蜂起。有九阳代烛说⑪萧兵,《马王堆帛画与<楚辞>》,《考古》,1979第2期:第172页。、苍龙星象说⑫刘宗意.《马王堆帛画中的“八个小圆”是苍龙星象》,《东南文化》1997第3期:第107.页。及九阳说⑬钟敬文:《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8页;姜生《马王堆帛画与汉初“道者”的信仰》,《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第180页。等。拔众出类者为九阳说。该说引《远游》:“朝濯发于汤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阳”以及《吕氏春秋•慎行论》:“禹至交阯...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远游》明言九阳之存在《吕氏春秋•慎行论》确指九阳所出之山是“羽人裸民之处”,是“不死之乡”。与辛追慕求的长生、升仙愿望十分契合。

图4 敦煌莫高窟285窟
再说人身蛇尾形象。对该形象的论说,主要有伏羲说⑭钟敬文:《马王堆汉基帛画的神话史意义》,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艺论集》( 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年,第124 页;孙作云:《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画幡考释》,《考古》1973 年第1 期,第55 页;刘惠萍:《伏羲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179 页。,女娲说⑮郭沫若:《桃都、女娲、加陵》,《文物》1973年第1期,第3页;孙世文:《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人首蛇身图考》,《东北师大学报》198年第1期,第81页;林巳奈夫著,蔡凤书译:《对洛阳卜千秋墓壁画的注释》,《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第93-99页。、烛龙说⑯安志敏,《长沙新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考古》,1973第1期:第45页。、镇墓神说⑰顾铁符,《关于帛画》,《文物》,1972第9期:第57页。和墓主灵魂说⑱Michael Loewe, Ways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79, p. 59.墓主变形而仙①姜生.《马王堆帛画与汉初“道者”的信仰》,《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第177页。等。人言言殊。伏羲和女娲出现需要特定的场景。山东武梁祠出现的有题记的伏羲女娲和神农、尧、舜、禹等古帝王在一起,且头戴饰有金博山的通天冠②孙机.《仙凡幽明之间——汉画像石与“大象其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9期,第85页。。根据孙机先生的论证,在其他祠堂出现的戴通天冠,无金博山的人首蛇身形象是不是伏羲或女娲,兹存疑。但可肯定的一点是,非衣上的人首蛇身形象和鹅、九阳、月亮、翼龙共存于一个叙事空间,此为天界无疑。烛龙,即烛阴,逴龙。虽然人面龙身,口中衔烛,但身处幽阴,与天界无涉。镇墓神就更无可能。帛画上方的人首蛇身形象,蛇尾通红,人首发呈股状,披在肩头及蛇尾上。从汉画像石和《女史箴图》等存有女性题材的图像可知,汉代时,妇女一般在洗漱打扮时,才可能披发。而股状下垂,无蓬松感的头发是湿水之后才有的状态。这种湿发状态,和汉高祖皇妣之魂的丹蛇形象极其相似!据此,图中形象很可能是墓主神灵的湿发形象,即墓主魂灵到达天界后,又完成了一次蜕变。这次蜕变使墓主魂魄化出蛇尾,成为自由来往于天地的神。
此外,帛画的T形,除了助力飞升,还用于通神。马王堆一、三号出土的两件非衣,从外形看均为T形,均有墓主形象,均画面朝下,覆于棺盖上。《说文解字》曰:“‘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上、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段注曰:“天悬象著明以示人,圣人因以神设教。”
墓主灵魂只需按图索骥,通过以下过程:拜访禺疆寻不死之药;仙官处服神药,魄体重生,魂魄合一为魄灵;上天梯,登天界,受道书,服玉浆;登天门,游天界,化出蛇尾,就能完成转生程序③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年,第871、873、877.页。,转生成神④参见姜生《马王堆帛画与汉初“道者”的信仰》,《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第182页。,实现道者信仰的终极价值。东汉王充在《论衡•论死篇》中云:“神者,伸也。申复无已,终而复始”。虽说王充是无神论者,但他对神的认识,实乃道家长生成神的真谛。

图5 敦煌魏晋墓
五、“非衣”与河西、吐鲁番丧葬文化的关系
与马王堆1号墓和3号墓非衣最接近的是山东临沂金雀山4号、9号墓和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所出非衣。“从西汉初期开阳县尉墓的棺盖上发现帛画残留,证实当时使用帛画附棺葬较为普遍。”[22]此言不虚。甘肃武威、张掖高台、河北怀安、广州象山、山东临沂、新疆吐鲁番等地都发现了非衣帛画及其残片。非衣随葬始于战国中晚期,盛于两汉,衰于唐西州时期。长沙陈家大山楚墓《人物龙凤图》和子弹库楚墓的《人物驭龙图》是现存最早的非衣帛画,最晚出的是吐鲁番唐西州时期的人首蛇身上天衣。符合三礼规制的铭旌以武威磨咀子遗物和画像石燕尾状图像为代表。非衣源于楚文化,在发展、流传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原文化、神话传说和土著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具体图像和载体都已经随着时空变迁而变化。惜铭旌出土实物较少,但铭旌葬仪已经衍化出招魂幡等多种样式,并内化为民俗,一直延续到了当代。
非衣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变化,其特有的T型,演变成了吐鲁番上大下小的梯形。同时,出现了与佛教、祆教等外来文化相融合的现象。酒泉、嘉峪关的棺盖画和吐鲁番的上天衣,既有非衣的T形特点,又与莫高窟285窟(见图4)和敦煌魏晋墓(见图5),以及河南、山东等地画像石上的人首蛇身胸怀日月的图像极其相似,折射出此类图像与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联系。甘肃武威M4、M15 和M22东汉墓、张掖高台2003GMN10魏晋墓、河北怀安东汉五鹿充墓和个别吐鲁番西凉墓,“书铭于末”或铭文与日月图像结合的样式,反映了儒家铭旌礼仪规制。墓主驾龙驭凤升仙和日月图像是陈家大山和子弹库楚墓帛画,马王堆非衣,嘉峪关毛庄子魏晋墓和新城M1、M6棺盖画,敦煌魏晋佛爷湾砖墓,山东、河南、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和画像砖,河南洛阳、辽宁集安等地的壁画墓的共同特征。T型为马王堆非衣和酒泉嘉峪关棺盖画、吐鲁番上天衣所共有。画面朝下是马王堆非衣和山东临沂金雀山非衣、嘉峪关魏晋墓棺盖画、吐鲁番上天衣的共同特征。敦煌莫高窟285窟和神木大保当M11号墓门门柱上的图像都胸怀日月,但神木大保当的身生毛羽、人身鸡脚的句芒和蓐收①王炜林,《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彩绘画像石》,《收藏家》1998年第4期:第6页。形象为特例。神木大保当M11号墓的人身鸡脚形象又与隋李和墓棺盖上的图像发生了联系。陕西北周匹娄欢墓、李诞墓、隋李和墓和嘉峪关魏晋墓棺盖上绘制人首蛇身图像的做法,可能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无法排除前者的外来文化因素。李和墓棺盖图像很可能受到了祆教的影响②陈财经,《隋李和石棺线刻图反映的祆教文化特征》《碑林集刊》2002年第2期:第98页。,敦煌莫高窟285窟中的人首蛇身图像以及西王母、东王公等道教人物与佛教壁画同处一窟。吐鲁番上天衣中的日月图像样式,难以摘清新疆克孜尔等石窟中日月天图像样式的影响。
职是之故,非衣在地上空间的丧葬礼仪活动中,起着招魂、引魂入棺与圹的关键作用;在墓室空间,非衣是墓主人转生神仙的程序示意图。除了湖南地区之外,在东起山东,西到青海、甘肃、新疆的众多地方,尤其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地区,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丧葬遗物。说明这些地方的丧葬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③此文在撰写过程中,获得了敦煌研究院杨富学、王志鹏、王惠民、张元林,以及吐鲁番学研究院吕恩国等多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诚致谢意!
[1]唐兰.关于帛画[J].文物.1972(9):59.
[2]史树青.关于遣册[J].文物.1972(9):70-71.
[3]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五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7:2200-2207.
[4]汉书[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58.
[5]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二十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30.
[6]何介钧.马王堆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45.
[7][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
[8]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M].上海:上海有正书局,1931:51.
[9]崔高维校点.礼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48.
[10][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五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45.
[11][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2]金维诺.从楚墓帛画看早期肖像画的发展[J].中国美术史论集(上)[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3:15-17
[13]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39.
[14]王梦欧.礼记今注今译[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353.
[15]姜生.马王堆帛画与汉初“道者”的信仰[J].中国社会科学.2014(12):177.
[16]庄子.南华真经卷[M].四部丛刊景明世德堂刊:7.
[17]葛洪.抱朴子·内篇[M].四部丛刊景明本:26.
[18]王晓玲、吕恩国.伏羲女娲图像辨析[J].艺术科技.2015(1):251.
[19]尚书详解(卷六)[M].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66.
[20]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水经注校(卷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
[21]赵宪章,朱存明.美术考古与艺术美学[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140.
[22]徐淑彬.临沂金雀山1997年发现的四座西汉墓[J].文物.1998(12):24.
(责任编辑:梁 田)
J509
A
1008-9675(2017)03-0046-08
2017-03-07
王晓玲(1971- ),甘肃酒泉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昌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