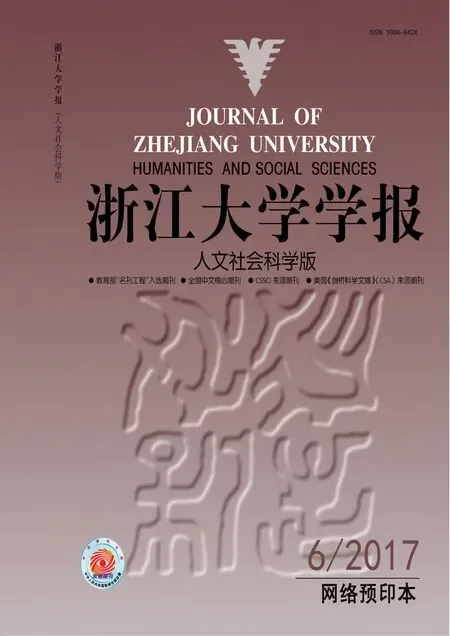论股权多重转让中善意取得规则的修正适用
吴勇敏 张桂龙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8)
论股权多重转让中善意取得规则的修正适用
吴勇敏 张桂龙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8)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7条第1款规定“一股二卖”纠纷应参照适用善意取得规则。但股权与物权变动模式相去甚远,股权登记对抗主义与善意取得制度亦抵牾颇多,股权多重转让参照适用善意取得规则将面临适用上的窘境。为增进法律体系的和谐并促进股权登记、鼓励诚信,第27条的修正适用需在登记对抗主义的前提下寻求先买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均衡点。由于我国现阶段股权外观效力的缺陷,股权多重转让中更需注重对先买人利益的保护,并妥当刻画先买人的可归责性标准与第三人的“善意”标准。可归责性标准可以在个案中具体衡量,第三人“善意”标准可以从承担有限的调查义务逐步过渡到善意推定,再到登记对抗主义,逐步消解善意取得对登记对抗的制度异化和干扰。
股权多重转让; 登记对抗主义; 善意取得; 修正适用
一、 问题之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将善意取得制度引入股权领域,其中,第25条、第27条分别规定了“隐名出资”、“一股二卖”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106条处理。然而,学界对股权能否适用善意取得规则却仍存争议。赞成者认为,特定情形下会发生股权善意取得*比如股权连环让与中的前手交易被认定无效或被撤销,或者擅自处分共有股权的情形。参见郭富青《论股权善意取得的依据与法律适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2页。,而股权的真实权利归属与股东登记外观的偏差,是产生权利外观并成就善意取得的原因[1]41。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体现了商法外观主义对利益平衡的优势,确保了在无权处分问题上法律技术的一贯性[2]47。批评者认为,股权变动异于物权变动[3-4],股权工商登记也无法承载权利外观功能[3,5],而且股权二重让与中,后受让人的替代既无法理基础,也无现实可能性*一股二卖中,前受让人已经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无法为后受让人办理变更程序,否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整个过程中,后受让人都保持善意不知情的情形,在实践中极为少见。参见王涌《股权如何善意取得?——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8条的疑问》,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第32-33页。,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亦是其制度羁绊*对交易安全的一味追求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存在价值冲突,参见陈彦晶《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质疑》,载《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113页。。另有部分学者则主张修正化适用,认为股权善意取得规则应在信赖责任框架下引入类型化的可归责性要件,以弥补股权外观可信赖度的不足[6],或者将各方风险和注意义务的分配纳入考量范围[7]。
为厘清股权善意取得的制度机理,应对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重新审视股权善意取得理论尤为必要。具体而言,股权变动的法律定位、时间节点及其效力,股权善意取得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06条的正当性,股权善意取得的理论依据和具体适用等核心问题亟待澄清。本文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7条第1款为中心,探讨股权多重让与中善意取得规则的机理。
二、股权参照物权善意取得规则的适用困境
(一) 股权变动的特殊性
1.股权变动模式的学说之争
关于股权变动模式,学界可谓歧见纷呈。有观点认为,股权转让合同仅产生履行义务,而非股权的当然变动,股东名册是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工商登记具有对抗效力[8]313,这也是股东名册立法功能和地位的体现[9]。另有观点认为,股权转让采意思主义,股权转让合同一经生效,股权即被继受取得。有关股权变更记载、登记的手续均不是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10-12]。亦有学者认为,纯粹债权形式主义和意思主义均有缺陷,应将公司受通知与认可程序嵌入意思主义的框架中,即股权变动于公司认可之时*关于纯粹债权形式主义和意思主义的缺陷以及修正意思主义的体系,参见李建伟《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动模式研究——以公司受通知与认可的程序构建为中心》,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第19-29页。。
2.股权变动遵循“公司确认+登记对抗”模式
依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45条,股权转让与债权转让并称为权利转让,均可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然而,股权变动究竟是纳入债权还是物权的参照体系予以适用仍然不甚清晰,这也是上述分歧的关键所在:第一种观点以物权变动的视角来审视股权,后两种观点则立足于债权变动的视角。因此,求解股权变动模式及时间节点,首先在于确定股权转让的权利参照体系。本文认为,物权变动的比照解释并不合理,有学者甚至批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物权式”的立法,使股权成为物权的延伸[13];相形之下,以债权为股权变动的权利参照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股权表现出相对权的性质,与债权的部分品格相契合,而与物权的绝对权性质扞格不入。股东是公司的成员,系与公司之间合同的相对方[14]265-266。股东权是股东地位上的权能和义务的集合体[15]204。股东地位随股权转让而转移[16]254,原股东的法律地位被受让人完全承继而退出其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其次,股权变动在程序上亦截然不同于物权变动,而表现出与债权转让相似的特性。股权变动涉及出让人、受让人、公司、其他股东等多个主体,需经历股东同意、股东优先购买、通知公司办理股东名册记载、工商登记等多道程序,这与物权人一般可以依其意思而径直处分其所有物的模式有相当大的差异,而股权转让中的通知程序则与债权转让程序相似。
本文认为,虽然股权变动表现出意思主义的特征,但与债权转让又有所差异,以通知和确认程序为核心的修正意思主义的解释路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80条,未经通知的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依据反对解释,未经通知,受让人亦可对债务人外的第三人发生债权让与效力[17]73。据此,当事人仅依意思表示就可取得债权,让与通知仅具有对抗效力。然而,股权转让经通知后并不意味着受让人可以当然取得股权:办理股东名册记载所涉及的公司确认程序是公司法上的重要议题,公司在某些情况下说明正当理由后可拒绝办理股东名册的记载[18]233-235。因此,公司确认程序的完成才能表征股东与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开始。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32条第3款,工商登记是股权变动的外部对抗要件,据此,股权变动可以简单概括成“公司确认变动+登记对抗”模式。可见,股权与债权和物权的变动模式旨趣不同,参照物权善意取得规则将面临适用上的窘境。
(二) 善意时点判断上的无所适从
根据以上分析,股权转让并非沿着物权变动的路径,而大体上是债权让与的轨道,这使《物权法》第106条的参照适用缺乏理据,而且有一种错误的导向,似乎把股权变动引导到类似物权变动的交付或登记的路径上去。然而,若依《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7条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06条的逻辑,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股权善意取得应参照动产或特殊动产的“交付”规则,抑或不动产的“登记”规则?从而便有“交付”的解释路径和“登记”的解释路径的探讨。
1.“交付”解释路径的缺陷
股份有限公司无记名股票可适用动产善意取得的交付规则[10]261,有学者甚至认为善意取得仅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16]225。然而,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而言,何谓交付?有学者论称: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时,即为股权交付、股东身份转移之时[8]313。然而,此种观点有待商榷。
首先,经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后的股权欠缺绝对对抗力,与善意取得的最终权利状态不符*依《物权法》第106条第1款第3项,善意取得时点系于动产或不动产的交付或登记时,依《物权法》第6条,交付或登记是动产或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因而《物权法》第106条善意取得的一般性前提是,若经交付或登记,动产和不动产物权已经发生绝对变动,足以对抗任何人。。德国法以股东名册为权利外观基础确立股权善意取得制度[19]161-166,从而保障了股东名册上所记载权利的效力。然而,依我国《公司法》第32条第3款,未经工商登记之股权“无法获得公司法排他性的保护”[11]15,无法达到善意取得后的稳固权利状态,股东名册和通知也无法承载权利外观功能。
其次,股权的逻辑起点不同于动产和特殊动产,不能简单参照交付规则。基于现有特殊动产物权变动模式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20条明确了奉行登记对抗主义的特殊动产以交付为善意取得时点*该司法解释的理由在于,现有特殊动产以交付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因此善意取得时点同样应以物权变动时点为准,登记仅是对抗要件。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454页。。姑且不论该规定的合理性,特殊动产所遵循的“交付生效+登记对抗”变动规则与股权的“告知生效”变动规则有所不同,特殊动产多重让与规则亦不能适用[17]。事实上,股权无须交付或登记,股权的变动以股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或股权继承中的继承人在股权转让合同生效或继承发生后,向公司发出股权业已变动的告知通知为生效条件。当然,此处所称的“告知公司即发生股权变动”是以股权转让或股权继承符合法律规定或章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为前提的。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变更均是公司在得知股权变动后向新的股东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而已。无论公司在收到股权变动的告知通知后是否履行这项义务,都不影响股权变动效力的实现。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系股权变动的对抗要件,这与动产交付生效的规则亦相去甚远。
2.“登记”解释路径的疏漏
有学者认为股权善意取得要求股权已经登记[2,11],然而若依不动产登记规则予以参照适用,则会陷入适用前提上的悖论。
首先,股权与不动产物权在变动时点和变动规则上有所差异。依《公司法》第32条第3款第2句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3条,工商登记系股权变动的对抗要件,股权变动于工商登记变更之前。“用物权变动理论去套股权的善意取得似有草率,二者的前提条件——登记的公信力基础也不一样”[7]140。《物权法》第106条中登记的规则是以登记生效主义为前提的,而股权变动则是基于登记对抗主义,仅能对抗公司交易相对人等,并不能对抗股权的第二受让人,因为股权的登记仅作为公司登记事项。
其次,经工商登记的股权并不具有不动产登记那样的绝对效力。《公司法》第32条的逻辑前提是“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法效果是“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可推出的唯一等价逆否命题是:可对抗第三人的股权必定经过登记或变更登记,而不可反面解释为“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股权一定具有对抗效力”。试举一例,于“一股二卖”情形,若第一受让人已记载于股东名册,而第二受让人基于虚假材料进行工商登记,此时第一受让人仍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股东名册记载等事实提起异议,请求变更登记。此时,经登记的第二受让人则不具有对抗第一受让人的效力。实际上,登记对抗主义下的登记,并非赋予自己取得物权的权利,而仅是具有否定他人物权变动的权利[20]96。
三、 股权登记对抗主义与善意取得的制度冲突
(一) 转让人并非无权处分
善意取得的前提系无权处分,股权多重转让中是否涉及无权处分,则有三类代表性的观点。肯定意见认为,股权多重转让如同债权多重转让,后一转让在法教义学上构成无权处分[5]。此外,根据《公司法》第73条的表述,股权在办理公司登记前已经发生变动,造成股权真实归属和外观的分离,从而使无权处分成其可能[1,11]。否定意见认为,依《公司法》第32条第3款,未登记的股权对第三人而言视为不存在,股权的第二次转让系有权处分[12]。亦有基于适用角度的折中观点,认为登记对抗与善意取得规范可以发生竞合*如尹田认为,受让人既可主张登记名义人为有权处分,亦可主张登记名义人系无权处分而适用善意取得规则。参见尹田《物权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为求解上述理论争议,需从登记对抗主义的法律构成中寻求答案。
登记对抗要件主义旨在解决意思主义结构下物权多重转让中的权利归属问题,是对无权利法理这一近代法前提的突破*参见[日]近江幸治《民法讲义Ⅱ:物权法》,王茵译,渠涛审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不再标注版本),第50页。无权利法理即罗马法谚云“任何人不得向他人转让大于自己本身所拥有的权利”(Nemo plus juris ad alium transferee potest, quam ipse habet)。。日本法关于登记对抗的具体法律构成历经百年争鸣,涌现出无权处分和有权处分这两类构成理论*有权处分构成理论如债权效果说、相对无效说、不完全物权变动说;无权处分构成理论如相反事实主张说、公信力说。参见[日]近江幸治《民法讲义Ⅱ:物权法》,第51-52页。。前者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出卖人因第一次转让而成为无权利人,因信赖出卖人名下的登记且善意无过失的第二买受人可以取得所有权[21]52。后者的代表性观点认为,无权处分论忽视了二重买卖中两个受让人居于平等地位,均可对世主张绝对性的消除妨害等请求权,但相互之间不得主张所有权,唯有先登记者取得完整所有权,登记对抗的意义便在于此[22]33-34。日本判例中逐渐形成了背信恶意者排除理论[21]62,从而使得以善意为基础的无权处分的法律构成日渐式微。
我国司法实践中擅长运用善意取得制度,而对登记对抗制度则疏于适用[20],《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7条也是直接建立在善意取得的制度框架上,却忽略了登记对抗主义与善意取得的制度性差异。登记对抗主义旨在赋予第三人否定物权变动的权利,而非有权利取得的效果[20],其前提是从相对无权利人处取得权利;而善意取得是法律规定的从绝对无权利人处直接取得权利的制度*相对无权利的登记名义人至少曾经具有权利,而绝对无权利的登记名义人自始便缺乏真实权利对应关系。参见郭志京《也论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3期,第103页。。登记对抗主义处理的多是怠于登记的效果问题,而不动产善意取得涉及的常见情形却是登记错误下的真实权利关系不对应问题[23]。多重转让中的登记名义人具备处分权,系登记对抗主义下的必然逻辑推演[24]。据此而言,在同样遵循登记对抗主义的股权多重让与情形下,转让人亦难谓无权处分,否则有悖于登记对抗主义和善意取得的制度机理。
(二) 第三人范围不同
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出台前,《公司法》第32条第3款即赋予了股权工商登记的对抗效力。多数观点认为条文中的“第三人”应指善意第三人,不包括恶意和重大过失的第三人,公司内部股东以及已经对变更事项知情的人[8]。这一观点鲜有异议*反对者的观点参见施天涛《公司法论(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
然而,登记对抗主义并不排斥知情的第三人,知情并不一定恶意,否则正当竞争将无从谈起[20]。因为“知道”无关伦理上的善恶,而且公信力说论及的“恶意者”实质上无异于通说和判例确立的“背信恶意者”[22]35-36。日本不动产登记采形式审查,难以排除不正当第三人,因此立法上对第三人做出两项例外规定*即“以诈欺或胁迫妨碍登记申请的第三人”(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4条)和“有为他人进行登记申请之义务者”(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5条),参见[日]近江幸治《民法讲义Ⅱ:物权法》,第54页。。另外,还可援引诚实信用原则排除背信恶意第三人[22]49-50。
此外,从我国立法体系的前后观照而言,“善意第三人”和“第三人”的语意是严格区分的*《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多处出现“第三人”,均未冠以“善意”;《物权法》中出现的“善意第三人”是有特定含义的,其与《物权法》第106条确立的善意第三人的主客观标准相关联,涉及特殊动产、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浮动抵押领域。,“善意取得”和“善意地取得”亦是泾渭分明:如前者必须以有偿法律行为前提,并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股权的多重受让人理论上可能“善意取得”股权;而后者可以包含赠予、继承、拍卖等情形,破产债权人、扣押债权人等则可能基于“善意地取得”股权而非“善意取得”股权。
综上,登记对抗主义较善意取得制度下的第三人范围更为广泛,不仅涵盖“善意第三人”,而且囊括了“知情的第三人”和“善意的第三人”等。而且,这种第三人范围的设计还有激励商事登记的制度性功能。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台湾地区有关规定为:“公司设立登记后,有应登记之事项而不登记,或已登记之事项有变更而不为变更之登记者,不得以其事项对抗第三人。”和相关判例亦未有善意恶意之别,旨在促使公司办理登记,贯彻登记效力[25]74。
(三) 股权外观可信赖度不足
善意取得制度立基于权利外观理论,权利外观的可信赖性是其制度运行的前提。然而,对于股权外观的可信赖度问题,理论和实务上却莫衷一是。
图书馆在图书的借阅及归还读者图书就已经是大工程。近年来,一方面由于职工职称评聘要求科研必须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文章,所以科研是热门话题;另一方面大学生科技创新课题启动,两者都给图书馆带来大量数据,这些数据的产生为大数据技术到来做足了前期准备工作。
部分学者认为,股权工商登记无法成为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因为工商登记簿缺乏公信力,其所公示者并非必然指向股权归属关系,亦缺乏为应对登记错误而设立的救济程序等[5]。但实务部门是认可股权工商登记的公信力的*如《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起草部门就认可登记簿的公信力,参见刘晓燕《规范审理公司设立、出资、股权确认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答记者问》, 2011年2月16日,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1/02/id/441068.shtml, 2017年2月6日。代表性案例见“四川京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与深圳市合众万家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股权确认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29号判决,法宝引证码CLI.C.1783274。另有实务观点认为,股权工商登记涉及法律的强制规定和公权力的干预,其法律效果体现为登记事项的推定真实状态以及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参见江必新、何东林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公司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47-448页。,并力求审查的审慎性*如反复比对原始档案、严格核查签名真伪等,参见傅燕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应审慎审查》,载《中国工商报》2009年12月8日,第3版。,而非仅流于证据效力。比较法上的经验也表明登记对抗主义下的登记簿具有合理信赖度[26]。另有观点认同股权工商登记的部分可信赖度:虽然股权工商登记的可信赖性供给存在缺陷,但股权工商登记是法定的强制事项,进而激励人们进行公示,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登记权利的名实统一[6]。
本文以为,股权工商登记虽然具有一定的可信赖度,但与善意取得制度下的可信赖性仍有差异。首先,有限的形式审查难以保障股权外观的真实性,实践中虚假股权纠纷大量涌现。从《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可以看出,我国对股权并不进行实质审查,不仅股权工商登记的正确性难以保障,股东名册的真实性亦难以保证。纵有配套规定力图保障股权登记的真实性,但我国缺乏像德国那样的股权审查制度*在德国法上,股东名册须储存于商事登记法院,并由公司执行人或公证人制作与呈交,真实权利人可提出异议登记。股东名册具有股东资格证明作用和权利外观功能。参见张双根《德国法上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之评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第161-166页。,而且股权工商登记和股东名册的双重公示还会造成权利外观上的混乱*表现为任一公示形式难有充分的外观效果,两者的结合也无法发挥功效。参见杨祥《有限公司“一股二卖”善意取得之质疑——对〈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适用的限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82-83页。,进一步削弱了股权工商登记的可信赖度。实践中,股权登记被伪造的案例层出不穷,“崔海龙案”*参见“崔海龙、俞成林与无锡市荣耀置业有限公司、燕飞、黄坤生、杜伟、李跃明、孙建源、王国强、蒋德斌、尤春伟、忻健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1号判决,法宝引证码CLI.C.2454398。即是典型著例,就连实务界人士也坦承我国公司登记制度上的缺陷导致了股权登记上的混乱局面*如我国法律未要求股权转让须进行公证,也不要求各方现场签字等,导致股东身份的真实性存疑。参见“崔海龙、俞成林与无锡市荣耀置业有限公司、燕飞等四人以及孙建源等五人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法宝引证码CLI.C.330017。。其次,登记对抗主义体现为一种交易规则,而非以可信赖性为前提。纵观我国《物权法》,登记对抗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集中在登记制度不完善的领域中*如特殊动产、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浮动抵押等领域。。登记对抗主义正是登记缺乏公信力时有限维护交易安全的一种规则,其所谓的推定乃消极推定,而非登记的权利真实,第三人基于法律拟制的规则行事,而非出于对登记簿的真实信赖[20]。股权工商登记作为商事登记,着眼于公司的对外关系,并不彰显股权的变动。
四、 股权多重转让参照适用善意取得规则的路径修正
我国现行法一直对善意取得存在“制度性偏爱”,并试图寻求其与登记对抗的制度融合: 《物权法》规定了登记对抗下的第三人范围限于善意第三人,《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20条更明确将此处的善意第三人和善意取得制度相联系,《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7条亦是这种法律逻辑的延伸*有学者认为,由于《公司法》第32条第3款未对登记对抗下的第三人范围做出进一步限定,构成法律漏洞,司法解释便类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予以填补。参见戴孟勇《民法解释学在大陆的实务应用——一个对照观察》,见张双根、田士永、朱庆育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这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应对第三人和股东不诚信行为的一贯思维,即从法感情上排斥恶意第三人,并强调善意第三人的调查义务[20]。但多重让与中善意的后买受人并非基于善意取得而取得所有权,登记对抗制度本身就蕴含着所有权的效力,多重让与中的权利取得规则需排除善意取得的异化干扰[27]。不仅如此,司法解释的这一制度异化亦不符合法律效力位阶,同样也有悖于司法解释不能创设法律的原则,因此,股权的多重让与仍然应在登记对抗的制度路径上进行解释。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善意取得制度全无意义,善意取得制度本身也蕴含着对利益分配的考量。立法的目的就在于调节社会利益、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以协调社会正常秩序,并最终凝结为法律制度中的具体利益[28]56-58。股权多重转让中的权利取得规则设计,既要注重制度的逻辑演绎,也需在不同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就具体利益格局而言,多重买受人的主观状态、注意程度等均可成为影响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善意取得制度在这方面有许多制度性尝试。从制度利益上看,登记对抗主义旨在通过赋予第三人否定权以激励股权登记,并导致竞争性交易的发生;而善意取得意在保障交易安全,通过强化调查义务以保护真实权利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竞争性交易和登记的积极性[20]。激励登记和鼓励诚信都是重要的立法目标,登记对抗和善意取得制度对此各有侧重。如果全然遵循善意取得的制度路径,促进登记的立法目标便会被打破;若不加限制地贯彻登记对抗主义,虚假和恶意交易便会盛行。
因此,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不变的情形下,不能盲目地倚重某一制度来处理股权多重转让中买受人的权利取得问题,而应注重法律制度的逻辑推演并寻求制度借鉴和利益衡量的空间。具体而言,在制度逻辑上应以登记对抗主义为法律适用的主线,以“有权处分”为制度基点;但同时在利益衡量层面上又需要扩展善意取得制度的应用空间,注重先买人可归责性、第三人主观状态和注意标准的考量。这样的考虑既能符合各方利益,也能契合立法目的,对鼓励股权登记、遏制恶意交易也大有裨益。
(一) 先买人可归责性
多重让与中先买人的利益被多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所认可*如美国和法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参见吴一鸣《论“单纯知情”对双重买卖效力之影响——物上权利之对抗力来源》,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2期,第111-112页;再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0条。,而先买人的失权须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比如善意取得。传统善意取得的制度缺陷在于对真实权利人可归责性的忽视[2,7],这在我国立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德国立法经历修订,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已经成为善意取得制度的重要构成要件。基于可信赖程度的差异,同样作为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载体的土地登记簿、商事登记簿、股东名册的外观效力依次递减,真实权利人可归责性的标准和受让人善意的标准则逐级递增[3]。在德国公司法上,当登记错误可归责于真实股东,或登记错误不可归责于真实股东时,经过3年期限,不知情第三人可以善意取得股权[7]135。从德国法上可以看出,权利外观效力越弱,第三人取得最终权利的构成要件越复杂,真实权利人越难失权。依此逻辑,我国股权外观的可信赖度较德国更低,因此更需要注重刻画真实权利人可归责性的标准。
(二) 第三人的主观状态和注意标准
善意取得制度与第三人的主观状态和注意标准相关联,又因动产和不动产的区分而在适用上有所差别,股权多重转让中的善意标准引起了学者的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登记对抗下适用善意取得应弱化善意要件并进行善意推定,由第三人证明其恶意[20]。而主张适用股权善意取得的学者认为,明知和重大过失均为恶意[9],应基于工商登记进行善意推定[11]。另有观点认为,考虑到信息获取成本的差异性和商事外观主义理念,股权对内转让中的善意应指不知且无一般过失,股权对外转让中的善意应指不知或无重大过失,未查询工商登记视为重大过失[12]。
本文认为,在立法不变的前提下,我国在处理股权善意取得问题时可以从赋予第三人有限的调查义务逐步过渡到善意推定,再到完全的登记对抗制度,逐步消解善意取得对登记对抗的制度异化和干扰。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7条第1款的主要目的在于应对司法实践中大量的不诚信股权交易,通过仅赋予善意第三人否定权而将明知的第三人排除在外,虽然危及交易安全,但大幅抑制了交易的进行[20]。另外,由于登记规则本身具有风险提示和减轻调查义务的作用,现阶段善意的标准应以调查义务的有限性为前提,如工商登记的查询和有限的公司内部调查即达到了认定善意的注意标准。
然而,从长远来看,促进股权登记、贯彻登记效力也是矢志不渝的立法目标。何况《公司法》的效力层级高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在登记对抗主义和善意取得存在制度冲突的前提下,原则上应倾向于登记对抗制度的一体化适用。因此,为弥合登记对抗和善意取得的制度裂痕,应对善意做扩大化解释以契合登记对抗的制度内涵。
依《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18条,善意取得中的善意必须贯穿交易的始终,但本文认为在参照适用的股权领域,则应区分初始知情、嗣后知情、完全不知情三种情形。股权外观效力上的缺陷使我国法在现阶段更需关注真实权利人的失权问题,而第三人的主观状态深刻影响着权利的最终归属。日本法和法国法上,登记对抗下的第三人主观范围经历了从无限制到限制的发展轨迹*日本法上是背信恶意者排除说,法国法上是恶意者排除说。参见郭志京《也论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3期,第95页。,美国法和法国法上多重让与中后受让人的单纯明知会构成妨碍权利取得*美国和法国通过修法将“知情”作为权利取得的重要考量因素,参见吴一鸣《论“单纯知情”对双重买卖效力之影响——物上权利之对抗力来源》,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2期,第112页。。我国《合同法》第52条关于恶意串通的规定是合同无效的情形,股权领域恶意串通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鉴于股权外观效力的缺陷和对真实权利人的保护需要,初始知情或重大过失不知情的第三人不应取得最终权利;而嗣后知情或者完全不知情的第三人应被推定为善意,但并非基于善意取得而是依据登记对抗规则而取得权利。随着股权登记制度的完善,摒弃善意取得因素的登记对抗制度应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登记对抗制度的应有之义。
综上,股权登记对抗主义与善意取得制度扞格不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7条将善意取得制度引入股权多重让与领域,尤显疏漏之余,徒生司法实践的困境。该条文的修正化适用需在股权登记对抗主义的前提下开展,并综合考量先买人的可归责性与第三人的主观状态和注意程度,如此,法律体系方能一以贯之。如此衡量的意义在于,既能实现激励股权登记并贯彻股权登记效力的长期立法目标,又通过为第三人取得权利设置难度,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股权的多重让与,从而保护股权外观效力缺陷状态下的善良先买人。
[1] 胡晓静: 《股权转让中的股东资格确认——基于股权权属与股东资格的区分》,《当代法学》2016年第2期,第36-44页。[Hu Xiaojing,″The Identity of Shareholders in Share Transfer: A Distinction Based on the Equity Ownership and Shareholder Eligibility,″ContemporaryLawReview, No.2(2016), pp.36-44.]
[2] 朱晓娟、姚篮: 《论中国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一般结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45-55页。[Zhu Xiaojuan & Yao Lan,″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the Equity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Limited Companies in China,″JournalofBei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SocialSciencesEdition), No.5(2013), pp.45-55.]
[3] 余佳楠: 《我国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缺陷与建构——基于权利外观原理的视角》,《清华法学》2015年第4期,第109-124页。[Yu Jia’nan,″The Deficiencies and Construction of Equity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Limited Companies in China:A ′Rechtsschein′ Perspective,″TsinghuaUniversityLawJournal, No.4(2015), pp.109-124.]
[4] 王涌: 《股权如何善意取得?——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8条的疑问》,《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第30-34页。[Wang Yong,″How Could Equity of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Be Acquired in Good Faith?——A Query about Article 28 of the Thir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CompanyLaw,″JinanJournal(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 No.12(2012), pp.30-34.]
[5] 张双根: 《股权善意取得之质疑——基于解释论的分析》,《法学家》2016年第1期,第131-147页。[Zhang Shuanggen,″A Critique of Good Faith Acquisition of Equity: An Explanatory Approach,″TheJurist, No.1(2016), pp.131-147.]
[6] 石一峰: 《非权利人转让股权的处置规则》,《法商研究》2016年第1期,第95-105页。[Shi Yifeng,″Disposition Rules of Non Obligee’s Transfer of Shares,″StudiesinLawandBusiness, No.1(2016), pp.95-105.]
[7] 张笑滔: 《股权善意取得之修正——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例》,《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第130-143页。[Zhang Xiaotao,″The Correction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Stock Right,″TribuneofPoliticalScienceandLaw, No.6(2013), pp.130-143.]
[8] 刘俊海: 《现代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Liu Junhai,ModernCorporationLaw, Beijing: Law Press, 2008.]
[9] 杨祥: 《有限责任公司“一股二卖”善意取得之质疑——对〈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适用的限缩》,《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74-88页。[Yang Xiang,″Ques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in ′Equities Being Sold Twice′,″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Law, No.3(2015), pp.74-88.]
[10] 李建伟: 《公司法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Li Jianwei,CorporationLaw(2ndEditio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 郭富青: 《论股权善意取得的依据与法律适用》,《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7-16页。[Guo Fuqing,″On the Basis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to Equity and Its Legal Application,″JournalofGansuPoliticalScienceandLawInstitute, No.4(2013), pp.7-16.]
[12] 姚明斌: 《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法律构成》,《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8期,第82-93页。[Yao Mingbin,″Legal Constitution of Good Faith Acquisition of Corporation Equity,″PoliticalScienceandLaw, No.8(2012), pp.82-93.]
[13] 邓峰: 《物权式的股东间纠纷解决方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评析》,《法律科学》2015年第1期,第178-189页。[Deng Feng,″A Continental Property Right Perspective on Shareholder’s Dispute in China: Also Comments o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Ⅲ ofCorporateAct,″ScienceofLaw, No.1(2015), pp.178-189.]
[14] A.Dignam & S.H.Goo,Hicks&Goo’sCases&MaterialsonCompanyLaw(7th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5] [韩]李哲松: 《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C.S.Lee,CorporationLawofSouthKorea, trans. by Wu Rihuan,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00.]
[16] 施天涛: 《公司法论(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Shi Tiantao,CorporationLaw(2ndEdition), Beijing: Law Press, 2006.]
[17] 周江洪: 《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之法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评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72-81页。[Zhou Jianghong,″Legal Theory of Multiple Transaction for Special Movable Properties: Commenting on Article 10 of theJudicialInterpretationofContractofSalesby Supreme People’s Court,″JournalofSoochow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ScienceEdition), No.4(2013), pp.72-81.]
[18] D.French, S.Mayson & C.Ryan,Mayson,French&RyanonCompanyLaw(29th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 张双根: 《德国法上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之评析》,《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第156-176页。[Zhang Shuanggen,″Analysis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Shares in German Law,″GlobalLawReview, No.2(2014), pp.156-176.]
[20] 郭志京: 《也论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3期,第95-113页。[Guo Zhijing,″Also on the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Doctrine in Chinese Real Right Law,″JournalofComparativeLaw, No.3(2014), pp.95-113.]
[21] [日]近江幸治: 《民法讲义Ⅱ:物权法》,王茵译,渠涛审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Koji Omi,CivilLawLectureNotesⅡ:PropertyLaw, trans. by Wang Yin, Rev. by Qu Tao,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22] [日]铃木禄弥: 《物权的变动与对抗》,渠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Rokuya Suzuki,AlterationandConfrontationofRealRight, trans. by Qu Tao,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9.]
[23] 程啸: 《论不动产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释义》,《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第74-84页。[Cheng Xiao,″On the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the System of Real Estate Acquired in Good Faith: Interpretation on the Article 106 ofPropertyRightsLawofPRC,″StudiesinLawandBusiness, No.5(2010), pp.74-84.]
[24] 冉克平: 《论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物权的变动——兼析法释〔2012〕8号第10条的得与失》,《法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153-162页。[Ran Keping,″On Change of Right over Motor Vehicle and Other Special Movables,″LawReview, No.4(2015), pp.153-162.]
[25] 梁宇贤: 《公司法论(修订六版)》,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Liang Yuxian,CorporationLaw(6thEdition), Taipei: Sanmin Book Co., Ltd., 2006.]
[26] 龙俊: 《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136-153页。[Long Jun,″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Doctrine in Chinese Real Right Law,″ChineseJournalofLaw, No.5(2012), pp.136-153.]
[27] 李宗录: 《登记对抗主义下多重所有权变动论》,《法学论坛》2015年第6期,第141-148页。[Li Zonglu,″The Theory of Multiple Ownership Changes under Registration Antagonism,″LegalForum, No.6(2015), pp.141-148.]
[28] 梁上上: 《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52-65页。[Liang Shangshang,″Stratified Structure of Interest and the Unfolding of Interest Measurement,″ChineseJournalofLaw, No.1(2002), pp.52-65.]
Modified Application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in Multiple Equity Transactions
Wu Yongmin Zhang Guilong
(Guanghua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8, China)
According to Paragraph 1 of Article 27 ofJudicialInterpretationⅢofCompanyLaw, the people’s court shall refer to the application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when handling the disputes over multiple equity transactions. However, this application would create unnecessary troubles. Moreover, equity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doctrine conflicts with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in many ways.
First of all, applying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which typically is applicable in the field of real property, to the field of equity transactions may face difficulties. Article 32 of theCompanyLawconstitutes the legal basis for changes in equity interests, according to which, changes in equity interests follow the rule model of ″the company’s approval +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Thi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hanges in the real property ownership. In addition, the abuse of the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in the field of equity changes might lead to confusion of third party in terms of ascertaining the time node.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equity changes, neither referring to the delivery of movable property nor the registration of real property can be logically consistent. In addition,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sets of rules.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hinges upon the theory of right appearance, aiming to safeguard transaction security. The premise of the application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is ex right disposition, third party’s good faith as well as trustworthiness of right appearance. However, equity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rule acts more as a trading rule, aiming to promote equity registration and implementing effectiveness of registration. Accordingly, the nominal registrant who transfers the equity in multiple transactions still have the right to dispose the equity, and consequently the third party does not need to be bona fide during the transaction. Additionally, under Chinese law, equity register and stock ledger are not reliable enough in terms of right appearance, and thus does not fulfill the premise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In views of all the conflicts listed above, Paragraph 1 of Article 27 ofJudicialInterpretationⅢofCompanyLawessentially violates Article 32 ofCompanyLaw, and also does not follow the hierarchy of the legal effe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harmony of legal system , promote equity registration as well as deter transactions in bad faith, modified legal application of Article 27 ofJudicialInterpretationⅢofCompanyLawshall focus on the intrinsic logic of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doctrine, 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 of first transferee and the third party.
Specifically, from systemic logic perspective,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doctrine should be the main thread in legal application; while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weighing specific interests, considering the first transferee’s accountability, third party’s subjective state as well as duty of care. Under German law, the effects of right appearance have inverse correlation with both first transferee’s accountability and third party’s subjective state. Due to the drawbacks of the appearance of equity under Chinese law, which leads to relatively lower trustworthiness, the interest of first transferee deserves more protection in multiple equity transactions. In this sense, the criteria of the first transferee’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third party’s subjective state should be adjusted properly. Given the institutional and habitual preference for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in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assessment of the criteria of the third party’s good faith may be carried out in several separate stages. Nevertheless,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rule shall be the center. Specifically, the criteria of good faith may be improved gradually from the third party’s limited investigation obligation, to the presumption of good faith, and finally the absolute legal application of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rule, and thus reduce the interference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progressively.
multiple equity transactions;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doctrine;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equity; modified application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7.02.064
2017-02-06
1.吴勇敏(http://orcid.org/0000-0002-3865-4216),男,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法学研究; 2.张桂龙(http://orcid.org/0000-0002-1371-4665),男,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7-06-09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33-600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