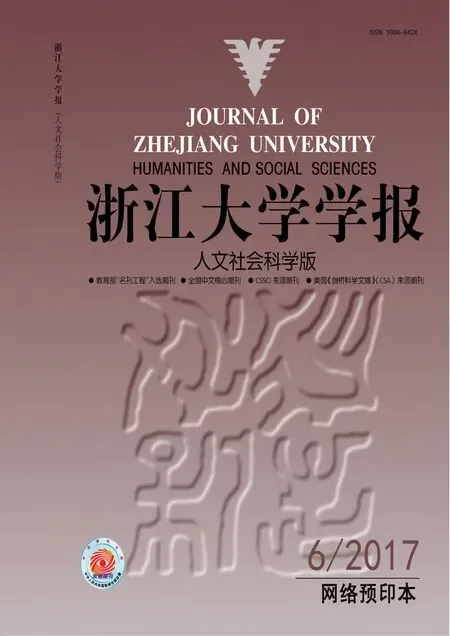政府与市场:英美两国基层医疗卫生系统改革进程对我国的启示
赵大海 陆露露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政府与市场:英美两国基层医疗卫生系统改革进程对我国的启示
赵大海 陆露露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英美两国的基层医疗卫生系统改革分别走了一条由政府全面管制到逐步市场化运行和从自由市场到政府管制的相反道路,这为我国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基层医疗卫生系统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基层医疗卫生系统改革应坚持政府管制为主与市场为辅的原则,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保障机构的公益性运行。为实现该目标,政府应调整大医院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大医院之间的竞争关系转变为协作关系;统一与明确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投入依据、水平与监管,以消除机构和医务人员的逐利行为动机;政府应进一步出台支持私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的政策,允许部分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合法转为私立机构。
政府与市场; 基层医疗卫生; 卫生改革; 英国; 美国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各国政府及学术界长期争论和纠结的议题。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一直是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内容[1-2]。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3]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政府与市场的宏观理论关系已相对明晰,但在具体的资源配置实践中,如何划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既让两者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让“两只手”形成合力,目前尚未有清晰的答案。
本文以英国和美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改革与发展为例来探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世界各国均将医疗卫生系统改革作为政府推进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中国将)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探索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4]。诚然,对于作为世界难题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各国尚未探索出完备的解决办法,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均被各国视为医疗卫生系统改革的突破口,而且推进改革的基本手段要么是市场化,要么是强化政府管理。其次,从世界范围来看,医疗卫生系统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系统,在政府或市场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方面存在着两个较为极端的国家,即号称商业医疗国家的美国和免费医疗国家的英国,前者以市场为最主要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方式,而后者主要以政府规划来配置医疗卫生资源[5]。
鉴于此,本文基于英国和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与发展的历程,试图厘清政府和市场在该进程中的界限,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政策建议,更为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进程中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 英国基层医疗卫生系统由政府全面管制到逐步市场化运行
英国在“二战”之后,实施了全民免费的医疗卫生制度。具体而言,1948年,英国议会颁布了《国家卫生服务法》,通过联邦政府税收统一支付各类医疗卫生服务,建立起了以完全依靠政府规划手段和完全依赖联邦财政投入为特征的国家卫生服务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其宗旨是根据病人的需求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6]。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而言,英国实行严格的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GP)制度:除急诊之外,全体国民的首诊必须在居民签约的全科医生处,只有获得全科医生的转诊许可,才能到医院就诊。此外,全科医生的收入由政府全额支付[7]。因此,英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二战”之后是完全基于政府规划手段来配置资源的。
英国所有国民首诊必须在全科医生处以及免费的医疗政策,时至今日未有改变;但全科医生所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机制,到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基于社区保障法案(1990年),英国于1991年实行了全科医生基金模式(GP Fundholding),到1997年,57%的全科医生选择了该模式。该模式的最主要特征是在政府完全管制的基层医疗卫生制度中引入市场机制,称为“半市场”的基层医疗卫生管理制度,主要表现在:与非基金模式的全科医生相比较,基金模式的全科医生实行类似于“承包制”的政策,政府按照覆盖区域的人口数量给予全科医生固定的年度财政预算,由全科医生自行购买大多数的常规医疗服务和药品(急诊不包括在内);预算结余,归全科医生所有。相关研究显示,相较于非基金模式的全科医生,该模式下的住院患者数量降低了5%,而且缩短了患者的等待时间。此外,在该模式下,英国全科医生的房屋面积、管理水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配备等在短时间内都得到了提升[8]。然而,在实施了两年之后,英国的审计委员会于1993年宣称引入市场机制后,全科医生因过度重视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联邦政府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目标,该模式最终在1998年被联邦政府废止。该模式的废止在学界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论,学者们认为全科医生基金模式和英国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市场机制的废止完全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是政党利益的牺牲品[9]。
随后,基于NHS规划(2000年)的实施,英国所有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重组为初级卫生保健信托(Primary Care Trusts,PCTs)。到2004年,英国所有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又全部转为完全按照政府指令运行的PCTs。当时,英国联邦政府宣称:打破上届政府采用市场来进行基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政策,回归到传统的计划和政府配置资源方式。PCTs直接向全民提供社区卫生服务以及其他初级卫生保健等服务,并逐步发展为英国最大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每年联邦卫生财政预算经费的80%都花费在了PCTs上。相关研究发现,PCTs实施之后,英国的医疗卫生质量得到了提升,相较于2000年,2009年英国男性的预期寿命增长了2.3岁,女性增长了1.7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4.7‰(2000年为5.8‰),为历史最低水平。但与此同时,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是:相较于PCTs建立之初,运行十年后的机构规模越来越庞大,其管理成本迅速增长[10]。PCTs在英国运行了12年,于2013年被联邦政府废止,其依据在于,英国联邦政府认为私有化是实现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必然途径。基于健康和社会保障法案(2012年),英国将超过600亿英镑市值的PCTs全部转给了新成立的超过200个临床委托集团(Clinical Commissioning Groups,CCGs)。对CCGs而言,66%的机构是由私立医疗服务提供者来负责的[11]。如此一来,自2013年至今,英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已主要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与此同时,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市场来运行与管理的模式,英国国内也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综上所述,自“二战”以来,英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方式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完全的计划方式,半市场半计划方式,再回归到完全的计划方式和以市场为主的方式。这一发展路径是不是正确的道路,目前尚未有定论,且英国国内也存在较大争议。
二、 美国基层医疗卫生系统从自由市场到政府管制
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完全采用市场的方式配置资源,居民通过自愿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可以到任何医疗机构就诊。此外,政府对医疗卫生机构几乎没有财政投入,没有医疗保险的居民只能自行负担医疗费用[12]。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林登·约翰逊政府(1963-1969年)提出了反贫困计划,其举措是建立老年人医疗保险、穷人医疗保险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3]。通过这三项方案,美国联邦政府正式开始干预医疗卫生系统的运行。因此,美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20世纪60年代的建立,本身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干预医疗卫生系统运行的主要标志。
时至今日,对整个美国医疗卫生系统而言,绝大部分医疗卫生机构仍然为私立机构,而且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也仍然为私立机构,但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均被界定为严格按照联邦政府标准运行的非营利性医疗服务提供者。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进一步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干预,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界定为联邦政府认证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FQHC)。该机构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项要求:机构设置的区域必须是联邦政府认定的医疗服务缺乏或弱势群体聚集的区域;必须可以提供全方位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无论居民有无支付能力,必须向所有人提供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是基于患者家庭收入和规模的支付能力;机构董事会成员至少有51%必须由该机构的患者担任。对于FQHC收治的无支付能力的病人,联邦政府会通过现金资助和老年人医疗保险等多种方式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补偿*详见https://www.ruralhealthinfo.org/topics/federally-qualified-health-centers, 2017年2月9日。。
在21世纪初期,由于美国经济形势的不景气,伴随着无医疗保险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扩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尤其是收支平衡面临着巨大挑战。基于此背景,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财政投入。全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联邦政府年度财政投入经费由2001年的11.6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6亿美元。随着联邦政府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扩张计划实施和财政投入的迅猛增加,截至2015年,全美共有超过1 250所联邦政府认证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超过8 000所社区卫生服务点,当年收治患者近2 500万人次。此外,美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自建立至今未有变化,主要是无医疗保险者或穷人医疗保险者,两者分别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总服务人次的40%和35%。因此,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美国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主体,已建立起由联邦政府财政支持和全面监管的全国健康安全网络。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对美国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的提升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随着医疗服务成本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社区卫生服务所需的联邦财政投入也不断增加。2015年,患者支付费用占全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年度总收入的4%,其余费用均直接或间接由政府承担*详见http://www.kff.org/other/state-indicator/distribution-of-revenue-by-source-for-community-health-centers/?currentTimeframe=0&sortModel=%7B"colId":"Location","sort":"asc"%7D, 2017年2月9日。。以减少无医疗保险者数量为主要目标的奥巴马医疗保障改革方案,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缓解联邦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财政投入的压力[14]。
综上所述,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方面,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的自由市场机制,逐步发展到由联邦政府全面财政投入和管制。随后,美国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健康安全网络,无论居民有无支付能力,都可以享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其全体国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得到了巨大提升。但与此同时,包括奥巴马医改方案在内的一系列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卫生改革也遭到了不少争议,譬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成本不断提升、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不断增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效率低下等问题。
三、 英美两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的共同经验与教训
英美两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有一些共同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与其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均由联邦政府通过法律或法规形式予以清晰界定。英国虽然经历了多次基层医疗卫生系统改革,但其功能定位,即服务对象是全体国民,而且所有国民首诊必须在全科医生处是没有变化的。与之对应的,美国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至今,其服务对象也基本未有变化,一直是无医疗保险者和穷人,即社会的弱势群体。由此可知,英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改革,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加强政府管制,只是运行手段的变化,与机构的功能定位无关。除此之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大医院的功能是完全分开的,两者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是相互协作和补充的关系。具体表现在:英国大医院收治的病人都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诊而来(急诊除外);美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收治的病人主要是那些由于没有医疗保险或没有支付能力而无法在大医院诊治的患者。此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大医院的合作与补充关系,也是由联邦政府通过法律或法规的形式予以保障的。
第二,政府和市场必须共存,不应对基层医疗卫生系统实行笼统的政府化或市场化。无论是英国通过全面的政府规划来配置基层医疗卫生资源、确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还是美国通过完全自由市场机制来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均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道路[15]。与此同时,美国的基层医疗卫生系统由完全市场化转变为由联邦政府严格管制和财政投入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虽然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得到了迅速提升,但对联邦政府所造成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其机构运行成本迅速增长的问题也不断暴露;而英国在全面管制和市场化道路之间的反复更是证明,对基层医疗卫生系统实行笼统的市场化或政府化,均难以解决公平和效率的平衡问题。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居民提供免费或廉价的医疗卫生服务,又尽可能不给政府财政造成过大的支出压力,是英美两国不断调整政府和市场具体关系的目标。
第三,政府和市场的主次关系是由当时改革进程的主要矛盾来决定的。美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和发展的初衷就是为了对无医疗保险者和穷人提供廉价的医疗服务,因此,必然以政府管制手段为主,市场手段为辅。英国当前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的目标就是为了提升效率,因而,市场是其更为侧重的运行手段。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做如下假设:美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导致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其可持续性面临挑战。基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经验,如果经济增长放缓,联邦财政压力凸显,届时美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可能会向市场寻找出路;但由于美国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主要面向弱势群体,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回归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又是不可能的。而英国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的进程中,已发生过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关系的相互转变,随着未来市场机制在基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中公平性降低等问题的进一步暴露,不排除英国会降低市场地位以使政府更多地管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可能性。
四、 英美两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进程对中国的启示
英美两国的改革进程对我国有以下启示:
第一,当前我国基层医疗卫生系统改革需坚持以政府管制为主、市场为辅的原则。我国医疗卫生系统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公益性不足和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鉴于此,中央政府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改革作为推进医疗卫生体制全面改革的突破口,鼓励居民“小病到社区”,缓解大医院“看病难”的问题[16];严格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零差价,缓解居民“看病贵”的问题。此外,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运行,不仅是解决当前我国整个医疗卫生系统主要矛盾的重要手段,也是满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基本要求。由于当前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正面临公益性功能定位转变等一系列基础问题,涉及诸多医疗卫生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基本问题,因此,我国基层医疗卫生系统目前必须坚持以政府管制为主、市场化手段为辅的运行机制。但随着我国医疗卫生系统改革的推进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排除会进一步提升市场的地位。当然,基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提供服务主要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特征,过多的市场化手段也是不可行的。
第二,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运行需要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大医院之间的竞争关系转变为协作关系。如上所述,英美两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该国医疗卫生系统中都是功能清晰和独立的机构,而且与大医院是相互补充、相互协作的关系。而对中国而言,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2009年)已首次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界定为主要提供公共产品的公益性机构,但中国的大医院*本文大医院是指二、三级医院。依然提供诸如治疗感冒、发烧等基本医疗服务。此外,我国没有英国那样首诊必须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严格规定,因此,我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大医院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方面依然存在竞争关系。此外,又由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业务水平无法与大医院竞争,进而导致了大医院“看病难”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患者数量不足的问题,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保证收支平衡的逐利行为。因此,必须要解决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大医院之间的竞争关系,将其转为协作和补充的关系;否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功能必定无法实现。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大医院之间由竞争关系向协作关系的转变,必定是政府的职责,也必须依靠政府的推动,仅靠市场机制是无法解决的。
第三,统一与明确的财政投入依据、水平与监管是保证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据英美两国基层医疗卫生系统改革进程的分析可知,虽然两国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投入依据和水平等方面均有变动,但其投入的依据、水平和监管均由联邦政府通过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界定。与之相应,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我国政府财政每年基于机构所覆盖或服务的常住人口数量进行一次性财政投入,尽管各地的人均投入水平有较大差距,但在投入依据方面是明确的。对基本医疗服务以及机构的固定资产与日常其他业务开支等方面,中央政府却没有明确规定,而各地政府对该方面的投入依据复杂多样,而且投入水平不足,主要依靠机构的基本医疗业务收入维持运行[17-18]。此外,虽然各地均已出台了一定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和财务监管政策,但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益性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前提下,这些办法起到的作用仍不够明显。譬如,政府虽然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进行了经费拨付,但对其所开展的公共卫生服务的实际绩效并没有明确的考核;因此,机构依然“重基本医疗而轻公共卫生”,诸如居民健康档案造假等现象较为普遍[19]。综上,本文建议,有必要在彻底厘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固定资产、负债、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的成本的基础上,由中央政府出台科学合理的、统一的财政投入依据、水平与监管规范,并保障财政投入的到位,从而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益性的切实运行。
第四,发展私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及不过分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是实现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长期稳定发展的保障。上文已述,美国的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均为私立,英国的私立机构也占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66%,而我国绝大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公立机构,其绝大部分财政投入又归地方政府(县级政府)负责[20]。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及其提供的服务内容被中央政府界定为统一的,由于各地财政存在巨大差异,该项改革在各地推进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较大阻力,甚至面临失败的可能[21]。英美两国的经验教训正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需的财政投入过大且持续增长,迫使联邦政府不得不更改政策(不断扩大联邦财政投入或采取市场化的举措)。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出台鼓励、培育私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的政策,甚至允许部分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合法转为私立机构,让私立与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私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仅可大幅降低财政投入,而且只要政府监管得当,完全可以保证其公益性运行[22]。因而,政府需要做的核心工作不再是建立过多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而是逐步鼓励市场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建立和运行方面发挥作用,政府应将工作重心放到监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运行上[23-24]。
综上所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过多的政府管制或过多的市场机制均无法起到公平且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作用。英美两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基层医疗卫生系统的改革进程,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供了较好的经验教训,更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1] 林毅夫: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4-5页。[Lin Yifu,″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Markets,″JournalofChinaNationalSchoolofAdministration, No.6(2013), pp.4-5.]
[2] 张明澍: 《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两个主要方面》,《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6期,第62-70页。[Zhang Mingshu,″Two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Markets,″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 No.6(2014), pp.62-70.]
[3] 佚名: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 “看不见的手” “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4年5月28日,第1版。[Anon.,″Xi Jinping Presided over the Collective Study of the Politburo, Emphasizing Both the ′Invisible Hand′ and ′Visible Hand′ Should Be Used Well,″People’sDaily(OverseasEdition), 2014-05-28, p.1.]
[4]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CP Central Committee(ed.),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sSeriesofImportantSpeechReaders(2016), Beijing: Xuexi Press,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5] 解亚红: 《西方国家医疗卫生改革的五大趋势——以英国、美国和德国为例》,《中国行政管理》 2006年第5期, 第109-112页。[Xie Yahong,″Trends of Health Reform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ase Studies o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ChinesePublicAdministration, No.5(2006), pp.109-112.]
[6] M.Roland, B.Guthrie & D.C.Thomé,″Primary Medical Care in the United Kingdom,″JournaloftheAmericanBoardofFamilyMedicine, Vol.25, No.S1(2012), pp.6-11.
[7] P.C.Smith & N.York,″Quality Incentives: The Case of U.K. General Practitioners,″HealthAffairs, Vol.23, No.3(2004), pp.112-118.
[8] D.Baines, K.Tolley & D.Whynes,″Prescribing, Budgets and Fundholding in General Practice,″ https://www.ohe.org/publications/prescribing-budgets-and-fundholding-general-practice, 2017-02-09.
[9] A.Kay,″The Abolition of the GP Fundholding Scheme: A Lesson in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BritishJournalofGeneralPractice, Vol.52, No.475(2002), pp.141-144.
[10] L.Hay,″The Legacy of Primary Care Trusts,″ http://www.healthcare-today.co.uk/doclibrary/documents/pdf/676_Legacy_PCTs.pdf, 2017-02-09.
[11] H.Holder, R.Robertson & S.Ross et al., ″Risk or Reward? The Changing Role of CCGs in General Practice,″ https://www.kingsfund.org.uk/sites/files/kf/field/field_publication_file/risk-or-reward-the-changing-role-of-CCGs-in-general-practice.pdf, 2017-02-09.
[12] R.A.Stevens,″Health Care in the Early 1960s,″HealthCareFinancingReview, Vol.18, No.2(1996), pp.11-22.
[13] M.J.Bailey & S.Danziger,″Legacies of the War on Poverty,″ http://www.jstor.org/stable/10.7758/9781610448147, 2017-02-09.
[14] S.Atsas & K.Kunz,″Policy Review: The US Affordable Care Act,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CommunityDevelopment, Vol.45, No.4(2014), pp.409-422.
[15] 蔡立辉: 《分层次、多元化、竞争式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管理改革及分析》,《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69-82页。[Cai Lihui,″Public Administration Reforms and Analyses on the Health Care Services Provided by Multi-methods,″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 No.6(2009), pp.69-82.]
[16] 章伟芳: 《中国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领域中职责的历史变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195页。[Zhang Weifang,″The Chang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Primary Health Care,″JournalofZhejiang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No.6(2012), p.195.]
[17] 赵大海、张智若: 《我国社区卫生机构功能定位转变的效果评估研究》,《西北人口》2013年第3期,第121-125页。[Zhao Dahai & Zhang Zhiruo,″Evaluations on the Reforms of the Community Health Institutions in China,″NorthwesternPopulation, No.3(2013), pp.121-125.]
[18] 郁建兴、翁翠: 《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中的地方政府——基于宁波市江北区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41-48页。[Yu Jianxing & Weng Cui,″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s of Primary Health Care System in Rural Areas: A Case of Niangbei District, Ningbo City,″JournalofZhejiang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No.6(2008), pp.41-48.]
[19] 王军、刘国恩: 《健康档案管理的“瓶颈”》,《中国社会保障》2011年第6期,第82-83页。[Wang Jun & Liu Guoen,″Bottlenecks of Health Records Management,″ChinaSocialSecurity, No.6(2011), pp.82-83.]
[20] 张宏翔、张明宗、熊波: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和地方公共卫生投入》,《财政研究》2014年第8期,第33-37页。[Zhang Hongxiang, Zhang Mingzong & Xiong Bo,″Fiscal Decentralization,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Public Health,″FinanceResearch, No.8(2014), pp.33-37.]
[21] 赵大海、张智若: 《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县级财政的压力与对策》,《甘肃社会科学》 2013年第1期,第230-233页。[Zhao Dahai & Zhang Zhiruo,″The Fiscal Burdens of China’s Health Care System Reforms on the County Governments,″GansuSocialScience, No.1(2013), pp.230-233.]
[22] 姚瑶、刘斌、刘国恩等: 《公立医疗机构比私立医疗机构更利他吗?》,《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年第4期,第94-103页。[Yao Yao, Liu Bin & Liu Guoen et al.,″Is the Public Hospital More Altruistic than the Private Hospital?″ResearchesonEconomicsandManagement, No.4(2015), pp.94-103.]
[23] 陈忠、史策: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7期,第43-47页。[Chen Zhong & Shi Ce,″Researches on the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s of the Primary Health Institutions,″ChinesePublicAdministration, No.7(2014), pp.43-47.]
[24] 杜创、朱恒鹏: 《中国城市医疗卫生体制的演变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第66-89页。[Du Chuang & Zhu Hengpeng,″The Evolution Logic of the Urban Health System in China,″SocialScienceinChina, No.8(2016), pp.66-89.]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Experiences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imary Health System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to China
Zhao Dahai Lu Lul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has been recognized as crucial to reform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in China. Based on an extensive analysis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primary health system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or the last half century,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and identify the outcomes of vary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n the two countries’ primary health systems. Based on the findings, we hope that this paper provides proper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national policymakers in China.
The analy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primary health care systems in the UK and the US show that three common experiences have been offered to the reforms on China’s health care system. First of all, the function and position of primary health institutions among the health care system are defined by the federal law and regulations.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mary health institutions and hospitals which is cooperative rather than competitive is also regulated by the federal law. Secondly, the government must coexist with the market. Specifically, the free-market reform or fully planned reform on the primary health care system in the US and UK has been proved impractical. Thirdly, the prior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present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the country’s health care system.
Notably, the profit-driven mechanism has been confirmed as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China’s health care system. Moreover, the public-oriented mechanism of the primary health care system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China’s health care reforms. Regard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mary health care system 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the first role in the primary health care system reforms, while the market also takes its supplementary responsibility. To realize the public-oriented operation of the primary health care system in China, three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as follows. Firs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mary health institutions and hospitals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rivals into partners through can celations of basic health care functions of hospitals. Secondly, providing sufficient subsidies is indispensible to ensuring the public-oriented operation of primary health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inputting sufficient subsid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uniform subsidy evidence, methods, surveillance, and the full-cost accountings of primary health institutions. Thirdly, to strive to develop private primary health institutions is crucial for the long-term and stable operations of the primary health system in China. Specifically, increasing private primary health institutions is not only indispensible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rket in the health care system, but it is also relieving the fiscal burdens on the local government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primary health; health reform;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7.02.093
2017-02-0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CGL135);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2YJCZH301); 上海交通大学SMC-晨星学者计划项目(B类)
1.赵大海(http://orcid.org/0000-0003-0121-0272),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公共经济、公共政策与卫生政策研究; 2.陆露露(http://orcid.org/0000-0002-8386-8096),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研究。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7-06-30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33-600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