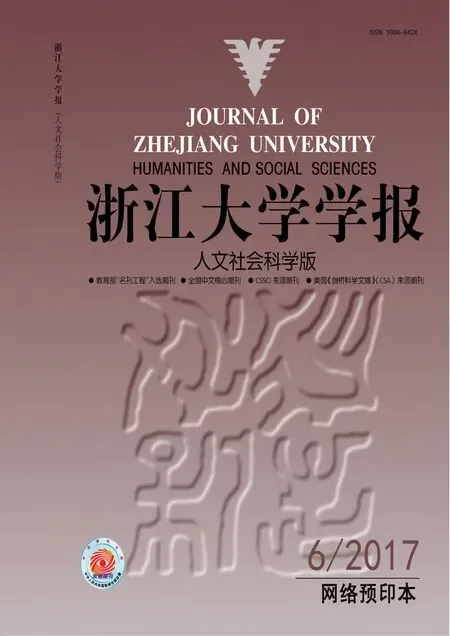作品、市场、社会:文学公共领域形成初探
胡振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英语学院, 北京 100029)
作品、市场、社会:文学公共领域形成初探
胡振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英语学院, 北京 100029)
18世纪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为理解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既能从社会宏观层面,又能从具体作品的微观层面进行解读的综合视角。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核心是作品的文本生产及其社会传播。从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互动关系出发,可以明晰文本生产过程;从作品、市场、社会三者相互建构的过程出发,可以厘清文本传播的社会意义。在印刷技术进步、版权制度确立、图书市场形成这些时代背景下,作者的文本创作开始从阅读市场及社会阅读期待中确定作品的风格及内容;书商的谋利行为借助市场调节手段,促使作者根据读者的阅读期待进行文本创作;读者的阅读消费实况则对作者、书商的相关努力进行直接评断。作者、书商、读者三者身份相互建构,相互影响,最终以谋求个人主体性为出发点,以共同构建社会公共性为终点,合力推动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
作品; 市场; 社会; 文学公共领域; 作者; 书商; 读者
18世纪的欧洲被后人视为受智慧女神、理性女神眷顾之地。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启蒙时代”,各类学术流派与新锐思潮纷纷涌现,百家争鸣,并融入后续的思想洪流,共同造就了当下的现代性。论及启蒙时代,不应忽略的一点是,自15世纪中叶起,印刷机日益广泛使用,这为启蒙时期书籍出版及知识传播奠定了技术基础;而18世纪《安妮法令》(StatuteofAnne)的颁布划清了作者权利及其创作收益的法律界限,为作者、读者、书籍、图书市场创造了良性互动的可能。在诸多因素合力下,“一种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领域——作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前身的文学公共领域已经形成”。“它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这种公开批判基本上还集中在自己内部——这是一个私人对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经验的自我启蒙过程……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1]34
哈贝马斯认为,文学作品最初是作者个体经验的书写,具有私人性;等到作品出版进入流通市场,成为众人阅读之作后,便成为“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之载体,进而积极参与了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的演变。在他看来,文学公共领域就是个人(个体)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需要看到的是,正如个人与社会相互建构一样,个人主体性的价值是在社会公共性之中得到体现的,谋求社会公共性的认可成为个人主体性的原动力;同时,社会公共性是由无数的个人主体性构成,并为个人主体性的发展指导方向。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的过程一方面体现在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文本生产与文学批评的互动中,另一方面体现在作品、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文本传播与社会影响的互动中。在启蒙时代,文本传播培育了阅读公众,读者阅读各类印刷物,对时政及文学作品进行理性批判,由此逐渐形成公众意识与社会思潮;潜在的市场激励推动文学创作者们敏锐地把握阅读期待,借助便捷的文本传播方式,用作品影响读者,进而引领社会思潮。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互动以文学作品为载体,以各类印刷物的出版为表现;作品、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以阅读市场为载体,以印刷技术、版权制度参与创建的阅读市场之形成过程为表现。前者与后者分别成为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文本内在因素与文本外在因素。本文将聚焦作品、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探讨文学公共领域之形成过程。
一、 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
1709年,英国女王颁布世界上第一部保护书籍作者著作权的法令,并于1710年4月10日正式执行,后世称之为《安妮法令》。该法令是对之前实行多年的书籍版权规定的重大修正。早在1556年,既身为行业协会,又作为商业实体运营的皇家特许出版公司(Stationer’s Company)就从女王玛丽一世那里取得了出版书籍的特许专营权,自此,英国书籍出版及权益都由该公司垄断。公司从作者手中购买手稿,并享有永远的版权专利。特许专营权对推动当时的书籍出版及图书市场的培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作者不能自行出版及销售作品,权益受限,因而相关方的博弈在所难免。经过多次调整,最后在1695年取消了该公司的特许专营权。随后《安妮法令》颁布,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拥有专有权,作品在1709年出版的,作者拥有21年版权;1709年后出版的作品则有14年版权。该法令还规定皇家特许出版公司所印刷的作品必须提供9份样本,分赠英国不同的图书馆。
《安妮法令》对书籍版权时效的重新界定意味着作者对个人作品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确保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这必然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写出更多符合读者预期且有阅读市场的作品,推动图书市场的进一步繁荣。作者、读者、书籍、图书市场有机融合在一起,共荣共生。但需要看到,《安妮法令》不仅只为图书市场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罗杰·沙尔捷如是发问:“在旧制度社会中,日益增加的印刷物的流通如何改变了社交形式,催生新的思维模式,进而改变了人们与权力的关系?”[2]3在他看来,图书市场的繁荣表象之后,孕育着从形式到内容、从意识到社会形态的革命性改变。迈克尔·麦基恩进一步指出,《安妮法令》在为图书市场的繁荣奠定基础的同时,无形之中提升了思想的价值,并改变了其存在方式:“在专利与版权存在之前,思想的价值通过保守秘密及严格的个人与精英群体运用而保存。然而,一旦可以拥有思想,思想的价值就在于以公布于众的方式与自身脱离关系,这不仅体现在剩余价值创造的经济意义层面,而且也体现在如是意义层面,即名义上的所有权真正意义取决于你拥有他人的知识,取决于他人获知你的思想,并无法从中攫取物质利益这一特点。”[3]201抽象的思想栖身于某部作品之中,通过读者的理解,完成从作者到读者的信息、知识传递,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众多作品的出版、发行成就了阅读市场,这一切也自然成为社会运行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应该看到,作品、阅读市场、社会三者各有内在驱动力,即由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构成的内动力。作品虽然是作者个人的思想成果,但付诸印刷出版,就是要谋求参与社会公共意识建构的可能性;阅读市场的繁荣和形成取决于无数具有个人主体性的作品的共存,越与社会共识相匹配的作品就越在阅读市场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要调节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各自内动力之间的平衡。具备内动力的作品、阅读市场与社会彼此之间有机联动,互为因果,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厘清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
文学公共领域是在启蒙时期形成的。18世纪先贤肩负开启民智之职责,如是担当的先决条件显然在于当时的作者既要拥有足够的言论自由,又要获得便利的思想传播方式与途径,更要有一个成熟的阅读市场体系,即“知识世界主义运动能否实际获得成功取决于有无足够的自由出版和广泛发行书籍的组织运营”[4]108。启蒙思潮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并非哲学家专有,恰如罗伯特·达恩顿所言:“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它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他们为超越了法国法律边界的思想市场投资。”[5]3因此,启蒙思想家创作的作品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思想的表述(抽象)以作品形式(具象)呈现,借助阅读市场的调配(抽象的商业动机与具象的商业模式)而实现自身最大价值(抽象的社会影响力与具象的阅读市场回报)。不难看出,整个传播过程是作品得以出版的历程,也是书籍的历史,涉及这一过程中所有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相关之物[6]67。细观书籍作品的传播路径,我们能看到阅读市场与社会这两股力量分分合合地影响着18世纪各类作品参与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的过程。
书籍作品与阅读市场、社会之间有机互动的事实促使唐纳德·麦肯齐倡导“文本社会学”研究,不仅研究“书籍的物质形式、文字之间的注释等,以及文本空间的排列在传情达意时如何拥有某种表述功能”,而且“要考虑文本在自身创作、传播、阅读消费每一阶段所涉及的人类动机与互动”,并“提醒我们注意外在体系及其复杂结构在影响往昔与当下社会话语形式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转引自E.H.Jacobs,″Buying into Classes: The Practice of Book Selec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33, No.1(1999), p.44。。“文本社会学”关注的不仅是文本生成的过程与结果,还包括由印刷技术、版权制度等推动、保障文本价值的外在体系。作品文本、外在体系、社会话语的共同核心是“人类动机与互动”,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最终是由分别对应作品、外在体系、社会话语的作者、书商、读者实现,由这些既有个人主体性,又有社会公共性意识的个人来实现。这个建构过程可从分析书商(阅读市场)和读者(社会)构成的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作者创作(作品)开始。
二、 文学公共领域形成中的作品因素
忠实记录18世纪文豪约翰逊言行的詹姆斯·鲍斯威尔提到了一件事:约翰逊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完成不朽的《英语辞典》,但从书商那里获得的稿酬非常低,只有区区1 575英镑,而且包括他必须支付给10年来提供帮助的编写助手们的报酬。当鲍斯威尔对此深感不平时,约翰逊却表示理解。“‘我也感到很难过,’约翰逊回答道,‘不过这样很好。书商们是慷慨大度、思想开明的人。’”鲍斯威尔说:“在所有的场合,约翰逊对书商的评价都足够公正。他认为书商是文学的赞助人;他们确实通过那部字典最终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但这项耗费巨大的工程能够冒险开始并且终于坚持完成,要归功于书商,他们也不能确定出版这部字典一定不会亏本。”[7]304-305约翰逊客观看待书商买断版权、作者权利受损这在当时司空见惯且备受争议之事。作者、书商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难免在利益上产生冲突,形成对立,但在18世纪阅读市场逐步成熟、繁荣之际,这种对立事实上又化为合力,“书商和作者都在追求金钱上的报酬和知识上的利益,两者的平衡是18世纪出版业的动力源泉”[8]158。18世纪各类作者借助自己的作品实现个人价值,获得物质收益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共识的形成以及阅读市场的繁荣。这种互动既是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成为当时商业发展的动力之一,因此成就了如下事实,即“商业,而不是宗教已成为提升民众读写能力的主要动力”[9]280。
莱因哈特·科泽勒克认为,书籍是极权主义催生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成就法国革命这两个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事件的在场者、亲历者、参与者[10]8。书籍在这一时期能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原因在于作者本人的独立思想,在于作者对旧制度的深刻反思以及与旧制度的勇敢决裂。18世纪启蒙学者、作者的新锐思想与阐述勇气是之前大多仰赖贵族恩主资助的文人难以企及的。在我们深入探究启蒙作家思想发展脉络时,需要注意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以版权制度为核心的阅读市场为思想的独立性创造了可能。“版权,即在被视为商品的文本中保障市场化权利的实践,是某种特定现代机制,是印刷机的产物,是中世纪末、文艺复兴初作者创作的个性化表现,是17、18世纪成熟市场社会的发展。”[11]3《安妮法令》的颁布标志着现代版权制度的开始,它将作者、书商、读者各自不同的诉求以符合阅读市场发展规律的形式凝聚,进而成为社会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版权制度的确立是商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调整,它在保护作者权益的同时,为作者更为积极地参与社会意识建构指引了方向;它在激励书商谋取商业利益的同时,为书商通过社会共识引导阅读市场创造了条件;它在推动读者参与阅读市场建构的同时,为读者通过阅读预期与社会共识影响作者创作提供了可能。应该看到,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与依托版权制度而形成的阅读市场密不可分,这一最直接的体现正如罗伊·波特所言,在18世纪,“文学成为能以任何形状和尺寸流通的商品”[12]87。文学以商品形式促使作者、书商、读者在阅读市场中实现了个体利益,同时又成就了阅读市场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学界普遍认为,1755年约翰逊那篇《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是文人的独立宣言。约翰逊在信中表露的不卑不亢、自信自豪的独立人格是基于阅读市场开始繁荣,并足以让作者凭借作品而不是恩主的提携而生存这一事实的。可以说,18世纪文学成为商品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创作者成为具有个体独立性的现代作者。在马克·罗斯看来,“现代作者的突出特点……就是所有权;作者被视为原创者,因此也就是某种商品即作品的所有人”[11]1。罗斯提到的所有权首先体现在思想独立性方面,作者能根据自己的理解与认知阐述不受恩主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个性化观点,这是阅读市场得以繁荣发展的基础;同时,所有权体现在社会价值交换过程中,现代作者能凭借得到阅读市场认可的作品参与价值分配,获得个人物质利益。所有权界定了现代作者的特征,使作者成为18世纪阅读市场及商业社会的独立参与者。也应该看到,所有权是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的一个内动力,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的汇聚点。
由印刷技术、版权制度、作品所有权等元素共同构建的阅读市场影响了18世纪作者在文本创作时的关注点与注意度,他们的所思所想也构成现代思想的起源,影响延及当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随着英国的财富和力量的稳步增长,又出现了英国这支新的思想和文学劲旅,其特点是强调对实际事物的观察,迎合中产阶级的趣味。实际上,欧洲思想和文学力量的模式已在这个时期确立,18世纪以后全部的发展情况都是从这种模式产生出来的。”[4]10118世纪作家对实际事物的观察、对个体差异的尊重后来成为文本的关注焦点,这与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读者有密切关系,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详细论述了这个观点。尽管瓦特的个人观点并不完全为学界接受,但公认的事实是,作为商业社会组成部分的阅读市场是以商业利益为驱动力,阅读市场的走向必然影响作者的创作。18世纪各种新思潮涌现的背后,是人们突破旧思想禁囿、开拓未知世界的勇气。这种对自我认知的自信,以及依托社会共识进行认同阐述的过程自然促使作者顺应市场需求,在借助作品描述外部世界多样性的同时,也反映了商业社会及阅读市场的形成过程。作者将自己个性化的思想形成文字,并以书籍形式成为供读者阅读的客体,让各阶层读者通过阅读书籍而接受作者的思想。因此,也就不难理解,18世纪40年代之后,关于作者创作的法律、社会与市场层面的思考使文学作品成为“作者本人的客体化过程”[11]121。
阅读市场由具备购买力的读者组成。读者根据自己个人偏好选择书籍,同时也受他人及群体的影响选择阅读物。自18世纪起,满足读者阅读期待成为作者实现个人商业收益的前提,成为作者创作的航标。书籍使作者与读者关系日益密切。18世纪思想家致力于社会启蒙,唤醒民众独立思考,根据理性自我判断。启蒙作家往往借助源于真实生活的虚构世界为读者及民众理性推理与批判提供研习机会,同时也借助深受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培养读者的想象力,培养读者对他者的理解与同情。出色的文学家通过情节安排与文字表述,将各种不同感官体验汇聚,突破了读者原有的认知,丰富了读者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渠道,也为作者的进一步创作提供了可能。应该看到,作者与读者是相互影响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指出,“读者人数的增加对文学家的视野产生影响,同理,书报杂志流通的日益增多也影响到文学家对社会的看法”[13]91。这种影响的表现就是,作者尊重读者现有的认知结构与能力,以提升读者的理解与感知为己任,这也就成为18世纪启蒙的意义所在。阅读市场的繁荣、读者的增加、不同阅读期待的共存,无疑促使作者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字驾驭能力,既要让文本细致入微,紧扣人心,又要让文本高瞻远瞩,成为读者的现实生活指南。不同作者在文本中阐述了自己关于自我、群体、国家乃至世界的不同理解与想象,进而“创建了一个特定模仿区域”,彼此竞争的想象在其中得到充分展示[14]344。这个特定模仿区域成为不同思想的汇聚地,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文学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
三、 文学公共领域形成中的市场因素
18世纪欧洲大陆是启蒙思想传播的主阵地,英国则是物质消费和商业文明发展的主场,此时的书籍在英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在其他国家[15]。用罗伊·波特的话来说,“英国发现它被印刷物淹没了”[12]94。印刷物成为各类信息来源渠道,并成为可消费的商品,在日益发展的商业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国家,由各类印刷物建构的阅读市场承载了思想传播进程,催生了启蒙运动的萌芽和发展。阅读市场的形成同样也是受商业利益驱动的社会合力之必然结果。当我们习惯性地把书籍视为联系作者与读者的纽带,即将其视为作者思想的成果和载体、可参与交换的商品,以及未来政治、宗教冲突的起因时[5]1,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即出版商、书商等人在思想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关注他们在谋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如何成功培育作为社会共识重要组成部分的阅读市场。书商作为出版活动的组织者,对作者个人创作方法的形成以及读者阅读习惯的养成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也是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的重要参与者。
不可否认,“印刷是传播开明思想和价值观的巨大发动机”[12]91,借助印刷技术,无数传播新思想的书籍面世,这极大地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需要看到的是,印刷技术并不直接决定或支配历史进程,在书商、出版商手里,它首先是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书商的逐利行为推动了阅读市场的繁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可靠的商业运行体系,从而为影响18世纪的社会意识的建构创造了条件。此时的书商和作者共同认识到,在商业社会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就是让书籍有更多的读者,在社会中有更大影响力。因此,作者潜心创作符合读者期待的作品,书商努力培育阅读市场,两者的合力推动了出版行业的质变,其结果就是读者群体的扩张,读者类型多样化,出现了诸如书店、图书馆等为人们提供阅读便利的机构,促使阅读俱乐部的成立和个人藏书的盛行。诚如约翰·布鲁尔所言,这些进步和现代商业、文明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启蒙时期的学术发现、教育普及、经济繁荣、文明开化,以及高度商业化的公共文化事业的兴起,皆与“到处都可以看到书籍”的现象是密不可分的[8]Chapter 3-Chapter 4。在公共文化事业的建构过程中,书商同样扮演重要角色。
“启蒙运动时期的出版业是在经济、技术、法律和智力背景下发生的共同协商、共同合作、时常伴有竞争的活动。”[16]7在18世纪的出版和销售实践中,阅读市场的繁荣取决于读者数量及其购买力。威廉·圣·克莱尔进一步推论,读者数量是由取得印刷材料的方法决定的,而取得印刷材料的方法取决于价格,价格又取决于知识产权的管理,即建立在图书业与政府关系基础上的运营体系[17]42。《安妮法令》对版权期限进行修改,用法令对书商旧有利益进行调整。短时期内,书商利益受损,但需要看到的是,随着知识产权管理方式的改变,作者的版权利益得到保障,垄断让位于竞争,其结果就是,读者更容易获得书籍,且能读到更高质量的作品,最终阅读市场繁荣,各方受益。书商、作者、读者在商业社会中的良性互动及协助合力是启蒙运动得以蓬勃发展、文学公共领域得以形成的前提。虽然18世纪各类著作、学说涌现,各种商业利益汇聚,但各方谋求个人利益之举参与了被后世称为启蒙思想的共同价值观的建构。
学界公认,“出版业的扩张和阅读群体的成长……成为推动18世纪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18]189-190。书商作为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不仅促进了阅读市场繁荣,而且还使阅读逐步成为国家现象,改写了国家文化版图。有学者认为,18世纪英国出版业的显著特征就是出现了各种技术及传播方式,进而促使出版业获得真正的国家地位[19]Chapter 1。也就是说,一方面,出版业的影响力已经波及英国全境;另一方面,出版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英国国民的文化、认知建构。此时的书商不再局限于组织出版,而且搭建图书销售网络,借助图书馆的创建、期刊连载、印发书目等方式培养民众阅读习惯,培育阅读市场。书商从事的工作超越了自身行业及自身利益局限,成为社会共识的主要建构者之一。阅读市场的繁荣为读者提供了更多选择,既有高深的学术专著,又有普及知识的期刊。阅读市场的活跃不仅促使作者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力,而且也推动读者的学识和读写能力提升。与此同时,爱德华·雅各布斯指出,18世纪英国书商采用各种宣传及分销手段出售书籍,为读者提供购买选择,这在当时可谓创新之举。这些举措的意义不仅在于直接提升国民读写能力,而且还间接提升了读者根据自身选择参与国家政治治理的意识。书商为吸引读者购买而将内容概述印在书籍封面的宣传方式及其文字表述方式也成为后来英国政治选举的常用套路[20]45-46。书商搭建起的全英图书销售网络自然成为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布兰宁在对法国旧制度文化进行系统解读时强调,“书籍的生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并且阅读在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21]140。革命性变化的结果之一是启蒙价值观的形成:“启蒙运动共同的核心并不存在于一个固定的学说,也不存在于一个普适的改革程序,或者某种制度结构、某个特定领域、某类学派思想,而是存在于启蒙运动的拥护者们所坚持的一套普遍的价值观念……共同的价值观。”[16]15我们知道,这些启蒙价值观逐步成为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基石,成为当时社会的准则。难以想象,这些开创性的思想体系如果没有印刷技术的支持,没有书商有系统的出版组织,没有以书籍为载体的阅读市场的繁荣,那么再具深远影响力的个人思想也难以成为社会思潮,进而改变整个人类历史。书商的谋利之举成就了阅读市场,也成为社会共识的重要建构力量。
四、 文学公共领域形成中的社会因素
随着18世纪启蒙运动的推进,阅读市场日渐繁荣,进而出现了“书籍的文明化”,这意味着“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固定概念:文字变成了标准的、经过授权的文本,作者从此成为创作者,书籍成为一种资产,读者则是有选择权的公众”[22]21。有选择权的公众首先是经济独立,其次是思想独立的个体。阅读市场的繁荣由具有选择权的读者承载,作者创作的作品、书商出版的书籍最终借助读者的选择而实现了商品及思想价值。在印刷术带来的众多社会变革中,最重要的是产生了一种接受思想力量的新型公众。这个新型阅读公众往往是根据自己的独立思想选择作品,是静默、独处的个体,常常互不相识,其联系纽带仅仅是书店、图书馆或讲演厅。在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看来,“阅读型公众的性质本身决定了,他们不仅更加分散,而且和聆听型公众相比,他们还更加原子化和个性化”[13]78。很久以来,人们通过聚集在一起聆听专人讲述的方式接受外部信息。当印刷技术用更有效的方式让更多人知晓信息时,聆听这样的信息传播方式轰然坍塌,读者逐渐自行决定选择信息内容及获取方式。信息获取方式的改变赋予了读者更多的个人主动性,“社会可以被认为是一群分离的单位,个体先于社会群体——这样的观念似乎与阅读型公众更协调,而不是和聆听型公众更兼容。论坛从公共广场讲演转变为新闻报纸和小报以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性质就不太可能顺从古典模式了”[13]78。个人阅读习惯的养成逐渐培养了读者的隐私意识及独立判断能力[23]Chapter 2,这些正是个人主动性形成的基础。读者日益成熟的独立选择必然带来政治参与方式及政治结构的变化。阅读市场的繁荣推动了作为政治公共领域前身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现代政治制度也是在此过程中发轫,现代文明社会也在此间定型。
在18世纪英国,“阅读成为这个民族大部分人的第二天性”[12]95。英国社会因本国国民这个第二天性而改变了国势。记录所见所闻并盛赞新气象的威廉·格斯里(William Guthrie)在《地理学、历史学和商业的入门:当代世界中数个王国的现状》(1770年伦敦出版,18世纪后期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序言里自豪地写下如是文字:“一个人如果真正关注社会和他的国家的繁荣,就一定会赞同,当今是一个繁荣的时代,在英国全土,知识和文明正在飞速发展和全面传播。”*转引自[美]理查德·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启蒙编译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格斯里将英国与历来敌视英国并对英国抱有偏见的其他欧洲国家进行比较,在纵论彼此政治、文化状况长短之后,他认为,英国伟大之处在于知识不再只是贵族、学者独享之物,而是惠及所有普通人。后世的理查德·奥尔蒂克指出了这个现象背后的政治意义:“民众阅读群体成长史实际上就是英国民主发展史”[24]3。当知识不再成为权贵禁脔,而成为民众平权之物时,英国社会面貌真正为之一新,其结果就是,科技、文化知识日新月异并得到广泛传播,教育全面普及,英国引领了时代潮流。物质丰富,文明开化,社会繁荣,凡此种种让英国国民日渐自信,有独立的见解,并争取、捍卫个人权利,个人主体性得到强化。同时,英国国民对政治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借助各种方式表述个人观点,参与构建社会公共意识。
书籍出版与民众阅读是启蒙运动发展的基础,人类历史进程也因此而改变。罗伯特·达恩顿研究了《百科全书》出版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这样说道:“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的根本原则——特权,又根据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建立了一种新秩序。这些抽象的术语今天听起来有些空洞,但在当时对法国的革命一代却充满了意义。《百科全书》的历史展现了它们是如何以印刷物的方式被表达出来、如何在社会体制中传播、如何具体体现在制度中以及如何与一种关于世界的新见解结合在一起的。”[5]532需要看到的是,无论启蒙作者的思想如何深邃,书商如何努力,作品的意义“只能由读者或受众来实现”[25]81。启蒙运动的成功在于唤醒读者、受众、民众的意识,形成推动民主进步的社会共识。也正因为如此,启蒙作家选择普通民众(而非之前的贵族恩主)作为自己作品的潜在读者,为读者提供各类新见闻、新思想。读者们也就作品引发的话题展开探讨,在咖啡馆、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就此展开评论,以公众舆论的方式影响社会意识与风气。作者则从公众舆论中捕捉读者的各种信息反馈,为自己的新作品定好主题与基调,以引发下一场舆论探讨。以读者为主体的社会既是文学公共领域的起点,又是终点,也是其价值最终得以体现之所在。
五、 结 语
纵观18世纪,对后世产生最具深远历史影响的不是宫廷权斗或战场征伐,而是由思想而起的启蒙运动。然而启蒙运动并非抽象概念,它是由随处可见的印刷物、书籍,以及容纳作者、读者交流、对话的咖啡馆、沙龙具体呈现的。印刷技术、版权制度本为商业社会阶段产物,却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者、书商、读者在这一时期的个人创作、出版谋利、阅读消费之举本为个人行为,并重新创建、界定了私人领域,“但漫长的私人领域创建过程最终以公共领域形成,并完全占据主导为结束”[26]195。在18世纪,作者、书商、读者的个人选择构建了由作品、市场、社会为具象的文学公共领域。在文学公共领域形成过程中,人们的实践理性借助以作品为载体、以市场为动力、以社会为对象的理性批判话语取代了旧有的社会共识。在民众以更规范、更深入的批判话语参与更广泛的社会舆论建构时,应运而生的文学公共领域成为现代民主政体的前提,进而影响了人类的文明进程。
启蒙思想的传播载体是这一时期出版的书籍文本,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则是以书籍文本的传播为依托,文本此时已具备多重特点与意义,既是个体思想产品,又是可出售的商品,更是推动文学公共领域形成,进而影响社会变革的动因。在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并行但又彼此影响的文本的内在及外在因素:作品、市场、社会之间的互动构成文本外在因素,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互动构成文本内在因素,前者从社会宏观层面,后者从具体作品的微观层面聚焦文本推动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过程,两者的交汇点是文本,即由作者书写而成的文字,最初是作品,随后成为阅读市场中的商品,流入他者手中,进而成为社会公共意识的组成部分。应该看到,文本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分析模型实际上是对作者、作品、读者、书商、阅读市场、社会等之间互动关系的概述,在现实中,这些互动关系彼此建构。作者从个体层面用作品参与社会层面的意识建构,个体作品在书商的助力下参与阅读市场的建构,个体读者汇聚成社会整体。文本内在与外在因素相互建构的过程实际上也揭示了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也是对作品、市场、社会三者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明晰文学公共领域形成过程的原因所在。
[1] [德]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J.Habermas,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 trans. by Cao Weidong et al., Shanghai: Xuelin Press, 1999.]
[2] R.Chartier,TheOrderofBooks, trans. by L.G.Cochrane,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美]迈克尔·麦基恩: 《英国小说的起源(1600-1740)》,胡振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M.McKeon,TheOriginsoftheEnglishNovel, 1600-1740, trans. by Hu Zhenmi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5.]
[4] [英]J.S.布朗伯利编: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6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J.S.Bromley(ed.),TheNewCambridgeModernHistory:Vol.6, trans. by World History Research Team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8.]
[5] [美]罗伯特·达恩顿: 《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叶桐、顾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R.Darnton,TheBusinessofEnlightenment:PublishingHistoryoftheEncyclopédie, 1775-1800, trans. by Ye Tong & Gu H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6] R.Darnton,″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Daedalus, Vol.111, No.3(1982), pp.65-83.
[7] J.Boswell,LifeofJohnson:Vol.1, edited by G.B.Hi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4.
[8] J.Brewer,ThePleasuresoftheImag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9] M.Spufford,″Literacy, Trade and Religion in the Commercial Centers of Europe,″ in K.Davids & J.Lucassen(eds.),AMiracleMirrored:TheDutchRepublicinEuropean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 R.Koselleck,CritiqueandCrisis:EnlightenmentandthePathogenesisofModernSocie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8.
[11] M.Rose,AuthorsandOwners:TheInventionofCopyright, Cambridge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 R.Porter,TheEnlightenment, 2nd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13] [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E.L.Eisenstein,ThePrintingPressasanAgentofChange, trans. by He Daoku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14] C.Flint,″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and Print Culture: A Proposed Modesty,″ in P.R.Backscheider & C.Ingrassia(eds.),ACompaniontotheEighteenth-CenturyEnglishNovelandCulture,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9, pp.343-364.
[15] N.McKendrick, J.Brewer & J.H.Plumb,TheBirthofaConsumerSociety:Commercializationof18thCenturyEnglan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1984.
[16] [美]理查德·谢尔: 《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启蒙编译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R.Sher,TheEnlightenmentandtheBook:ScottishAuthorsandTheirPublishersinEighteenth-CenturyBritain,Ireland,andAmerica, trans. by the Enlightenment Translation Institute,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7] W.St.Clair,TheReadingNationintheRomantic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 I.Woloch,Eighteenth-CenturyEurope:TraditionandProgress, 1715-1789(2ndEdition), New York &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2012.
[19] J.Feather,TheProvincialBookTradeinEighteenth-Century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0] E.H.Jacobs,″Buying into Classes: The Practice of Book Selec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Eighteenth-CenturyStudies, Vol.33, No.1(1999), pp.43-64.
[21] T.C.W.Blanning,TheCultureofPowerandthePowerofCulture:OldRegimeEurope1660-178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2] C.Hesse,″Books in Time,″ in G.Nunberg(ed.),TheFutureoftheBoo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3] P.Saenger,SpacebetweenWords:TheOriginsofSilentRead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4] R.D.Altick,TheEnglishCommonReader:ASocialHistoryoftheMassReadingPublic, 1800-1900, Chicago & Lond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7.
[25] R.Hume,″Texts within Contexts: Notes toward a Historical Method,″PhilologicalQuarterly, Vol.LXXI(1992), pp.69-100.
[26] R.Chartier,TheCulturalOriginsoftheFrenchRevolution, trans. by L.G.Cochra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Books, Market and Society: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Public Sphere
Hu Zhenm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18th Century literary public spher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for those who want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an civilization. This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is comprised of two aspects, namely, the macro aspect of society and the micro aspect of individual books. The focu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literary public sphere is on the textual production of books, and their social dissemination. We can have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ocess of the textual production of books in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authors, the books and readers. We can define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books in the interaction among books, market and society. Against the historic background of the application of printing technology, the establishment of copyright system and the formation of book market, the writing process of authors commenced to define styles and contents of their books from the actual demands of reading market and social reading expectations. The profiting business of the booksellers could prod authors to undertake the writing in line with the reading expectations of readers through the means of market adjustment. The actual reading consumption of readers would pass the direct judgment on the concerned efforts of readers and booksellers. The interaction among authors, booksellers and readers serves to define their own identity and exerts influence on each other. Ultimately, their efforts start with the pursuit of their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end with the combined striving for the social commonality, which jointly usher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literary public sphere.
The theory of public sphere of Habermas is of great inspiration for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s studies, which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analytical perspective adopted frequently by scholars all around the world. Although Habermas ha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public sphere″ in his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 he did not present a convincing argumentation for the nature of the literary public sphere and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Henceforth, the creative aspect of this paper is to center on the textual production of books and their social dissemination, and to star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identity of authors, booksellers and readers in the 18th Centur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consciousness of books, market and society. In the meanwhile, the paper is to choose the study of textual books as the entry point in order to present two analytical models, namely, the internal factor and the external factor of textual books of literary public sphere. The paper is also to display and represent the abstract process of 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social commonality, two driving forces of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public sphere through concrete social phenomena. The study of literary public sphere provides not only the mixed and shifting perspectives from macro and micro aspects, which might enable scholars to have an insight into the writing motives of the 18th Century authors, but also a model of new argumentation concer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experiences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This study will enable us to understand how the sages and forerunners of the 18th Century managed to condense Zeitgeist into the textual books through the effort of summarization and converging, and to project the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ublic sphere onto the real life through the reading process of readers, which ultimately construct the new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The restoration of this process will surely serve as a good reference to China, a country confronted with similar issues at present.
books; market; society; literary public sphere; author; bookseller; reader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6.09.242
2016-09-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WW02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胡振明(http://orcid.org/0000-0003-0961-858X),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7-06-27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33-600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