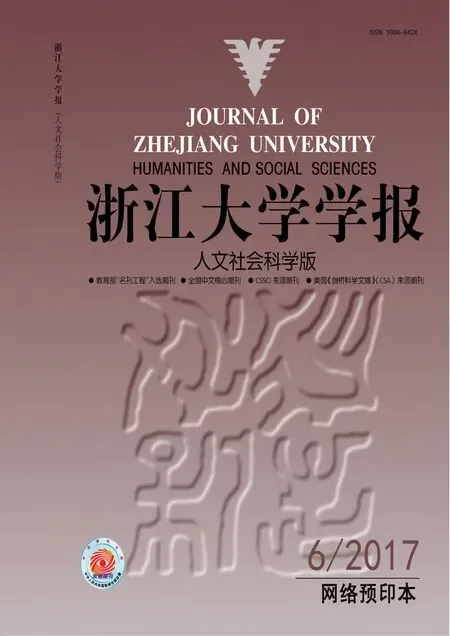马克思与现代公民权
王小章
(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与社会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36)
马克思与现代公民权
王小章
(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与社会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36)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个体只是“一定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向“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也即人的解放迈进的进程。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民权一方面显示出其历史性的局限,但同时也是一大历史性的进步,是迈向人的解放所无法逾越的、非常关键的台阶,并且还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争取和捍卫自身利益、推动人的解放的事业中可以利用的武器。同样,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下,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社会权利的发展一方面显示出与马克思一样关注实质性平等的一面,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其助长消费主义文化、瓦解社会力量、强化国家权力这一与人的解放相背离的一面。
马克思; 公民权; 社会权利; 人的解放
很多人都熟悉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权或公民权的著名评判: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1]40,而“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则被“贬低为维护这些所谓人权的一种手段;因此,citoyen[公民]被宣布为利己的homme[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被降到人作为单个存在物所处的领域之下;最后,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1]43。于是,“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意义”[1]312。根据这种评判,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对这种人权或公民权,马克思是持否定贬斥态度的。事实上,一直以来,大多数人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但是,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公民权的态度真的就那么简单明了吗?这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在现实的政治社会话语中又有意无意地回避“公民”这一词汇的我们来说,是值得再认真考察分析的。实际上,就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在批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又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从而导致公民和现实的个人分离的同时,又指出,要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必须让“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1]46。这至少提示我们,马克思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民权并不是要终结公民权,而是要改造公民权,不是要“公民”消亡,而是要公民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扎根重生。
一、 作为政治解放的公民权
在现代政治中,公民权(即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尽管围绕这个概念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但近代以来的各种公民权理论和实践中无疑包含着一些基本一致的意涵,即都将公民权看作个人在某一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与这一资格相联系,个体具有某些基本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既反映也规范着公民、政治共同体(国家)、统治者三者之间以及公民个体的公民身份与其整体人格之间的基本关系:统治者与政治共同体(国家)的关系不再是“朕即国家”式的浑然不分,而是相互分离的;无论是对于政治共同体(国家),还是对于统治者,公民都不再是完全隶从的关系;与这种非隶从的关系相联系,公民身份不再等于公民个体的整体人格,个人在公民身份之外还有私人身份,而在这种私人身份之下或多或少不受干涉的独立自由则是法律肯定和保护的一项公民权利(甚至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这些基本一致的意涵体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公民权的基本特征[2]。那么,对这样一种公民权,或者说公民权利体系,马克思究竟是怎么看的呢?
需要先说明的是,在马克思依据《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而使用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概念时,他是从比较狭义的角度将公民权利(droits du citoyen)看作人权的一部分的。也就是说,他将公民权利等同于公民“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的“政治权利”;而人权的另一部分,即“与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不同的droits de l’homme[人权]”,则属于与政治共同体(国家)相对的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具体如被《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布为“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等[1]39-40。依据《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解释,马克思还对这些权利的具体所指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自由是可以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权这一人权;私有财产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平等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安全是社会为了“维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给予的保障[1]40-42。显然,马克思在此所评说的这些与政治权利相对的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实际上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在公民身份之外、私人身份之下所拥有的权利。而就这些权利受到现代国家的法律肯定和保护而言,它们与旨在维护它们的政治权利一样,都属于与公民身份资格相联系的公民权利(citizenship rights)。
回到上面的问题:对这样一种公民权或公民权利体系,马克思究竟是怎么看的?要真切完整地认识和把握这个问题,必须联系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观点。
从应然的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看作自由自觉的实践者,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1]162。但与此同时,他吸取黑格尔的观点,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而将人的这种本质看作是一种需要在历史过程中展开、实现的现实可能性,而不是单个的孤立个体所固有、既成的静态的东西。消极的、形式意义上的自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然权利”,但积极的、实质性的、作为人的潜能的充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则是需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趋近的目标。也就是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正是生产力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形态的历史发展,为人的自由实践、人的全面发展,也即人的类本质的实际、现实的实现拓展了广度和深度。正是在此意义上,在应然意义上作为自由自觉的实践者的人,才在实然意义上也即“在其现实性上”,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26-35。而以此观点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历史就隐隐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进程或逻辑:“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3]107-108换言之,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不乏各种顿挫回旋,但总体上呈现为从个体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状况,过渡到由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全面确立和肯定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而迈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571的社会状况的进程。
以这样一种人类历史发展观来审视资产阶级国家所确立的公民权利体系,马克思首先承认这些权利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成果,是“政治解放”的表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主义者鲍威尔并没有分歧。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并不是后者将公民身份、公民权利的获得视作政治解放,而是后者将政治解放等同于人的解放,将人作为“公民”的解放,即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公民身份和相应权利的获得,看作人的解放的完成。这是马克思不能苟同的。“鲍威尔的错误在于,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供的条件只能表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1]25-26站在人的解放,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角度来看,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无疑是明显的。这个局限就在于,政治革命只是市民社会的革命,政治解放只是市民社会的解放。在封建制度下,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市民生活的要素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在这种国家与市民社会混沌不分的情形下,市民社会被牢牢束缚在封建体制之下。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从而使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却没有改变市民社会本身的内部关系,反而听命于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要求,并通过国家法律的方式正式承认和肯定了这种内部关系,特别是私有财产关系。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民权利体系则是这种承认和肯定的正式表征:“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他就是国家通过人权予以承认的人。”[1]45但是,由于市民社会本身的内部关系没有改变,由于私有财产“按其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这个市民社会成员的现实生活必然受制于市民社会的财产关系。换言之,这个市民社会成员的“独立性”必然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从而,自由、独立等在实际上也就只能是有产者的特权,进而,这个市民社会成员也就必然是“利己的人”,资产阶级国家承认和肯定的那些权利也只能是利己主义的权利。在一一点评平等、自由、安全、财产这些权利后,马克思揭穿了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利己主义本质:“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身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1]42
从实现人的类本质、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揭示资产阶级国家所肯定的这些权利的实质和局限,揭示它们不过是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市民社会成员自私自利的权利,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联系人类历史发展的应然与必然,马克思实际上又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国家或现代政治确认这些权利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马克思憧憬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人的解放。但他深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需要现实的前提和条件,在工业的、商业的、农业的、社会交往的条件还不具备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的解放,这就是历史必然性。因此,考量一项实践、一个事件、一项制度是否具有历史进步性,是否有价值,不在于它是否一劳永逸地实现了、完成了人的解放(这种观点是非历史性的),而在于它是不是促成了人的解放所必需的这些条件。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热情地赞扬了资本主义及其担纲者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历史意义,肯定了在政治革命、政治解放中得到确认的公民权利的巨大历史进步性:
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即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遗产分割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的胜利、启蒙运动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勤劳对游手好闲的胜利、资产阶级权利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年革命是17世纪对16世纪的胜利,1789年革命是18世纪对17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发生革命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5]74
质言之,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消灭了在16至18世纪时已变成了工业发展桎梏的一切封建财产关系,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通过政治革命,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实现了“个人自由和市场自由”,用一种“建立在公民权之上的政治制度代替了它之前对一个绝对君主的服从”[6]35-36。没有这些自由,没有对这种公民权利的肯定和确认,各种生产要素就不可能自由流动,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也不可能从封建制度下“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而成为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商品,进而也就不可能有为“第三阶段”(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创造条件的第二个阶段,即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就此而言,政治解放即近代公民权的确立虽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的解放的最终完成,却是迈向人的解放无法逾越且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台阶。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肯定了政治解放是“一大进步”,并且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1]32。
二、 作为斗争武器的公民权
马克思不仅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国家所确认的这些权利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同时还指出了这些权利的另一种价值:这些权利,特别是狭义上的,也即马克思所说的“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的公民权利,可以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争取自身利益、推动人的解放的事业中用作斗争武器。
如上所述,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些属于政治自由范畴的公民权利实质上只是维护人权的手段,而所谓人权,无非是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的利己的权利,这些权利之实际、现实的效用与私有财产紧密结合,因而在其普遍性的形式下潜藏着的是有产者特权这一实质。但是,由于政治革命完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尽管这种分离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国家作为“总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利益代理者的角色,但毕竟赋予了国家以相对的超越性和独立性,从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就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所认可的合法公民权利来维护、争取自身的利益,进而推动人的解放。
马克思始终坚决反对要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放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而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忠顺奴仆、听任资产阶级剥削的“政治冷淡主义”[7]339-345;另一方面,则坚持主张在反对资产阶级、争取自身和人类解放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利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包括利用和争取资产阶级国家所赋予和肯定的各种权利来服务于自身的目标。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恩格斯说:“当时德国工人应当首先争得那些为他们独立地组成阶级政党所必需的权利: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来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但是它现在由于害怕竟不赞成工人们享有这些权利。”[8]5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为工人阶级争取、捍卫和利用这些权利。早在1842—1843年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即为捍卫出版自由而抨击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数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在科隆创办出版《新莱茵报》,则是自觉地在“民主派”的旗帜下积极灵活地利用新闻出版自由,以服务于无产阶级事业[8]5。
在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争取自身和人类解放的斗争中,必须形成和发展工人自身的组织。这些组织既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手段,也推动了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表征着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在马克思看来,社团以及由社团成长起来的工会不仅作为组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它们还是警察统治和官僚制度的一个缺口,可以摧毁奴仆规约和贵族对农村的统治,是使“臣民”变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的一种手段。因此,马克思非常重视这种结社权及工会组织。在就国际工人协会的目标、活动等接受《世界报》记者兰多尔的采访时,马克思非常明确地解释了为什么将协会的国际总部设在英国:“理由很明显:结社权在这里(笔者按,英国)是已经得到承认的东西。”“在英国,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途径对英国工人阶级是敞开的。”而在德国和法国,结社权要么困难重重,要么根本不存在。马克思还指出,国际工人协会的目标是“通过赢得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利用这个政权来达到社会目的”[7]616,而“在和平的宣传鼓动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发疯”[7]611。
马克思同样重视选举权。在应法国工人党的请求而起草的《法国工人党纲领(草案)》的“导言”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资料集体占有形式的确立,这种集体所有制只有通过组成独立政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而无产阶级要建立政党组织并展开有效的革命活动,“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7]568。由此,马克思赞成法国工人党提出自己的最低纲领参加选举,以此作为组织和斗争的手段。而作为马克思终生最亲密的战友和合作者,恩格斯无论在马克思生前还是身后也一直同样重视利用选举作为工人政党斗争的工具与手段。1893年,在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恩格斯对德国工人党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将取得的成果充满信心:“我深信,我们将比1890年多获得70万张选票,也可能是100万张。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得到的票数如果不是250万张,也将是225万张。”[8]561“如果选举到1895年才举行,那么我们将会得到350万张选票。而全德国的选民是1 000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700万。如果在总数700万选民中有350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8]562
总之,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意味着承认现状。但是,既然这种现状为我们提供了反对它的手段,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是不承认现状。”[7]225
三、 如果马克思看到公民权在20世纪的发展
如上所述,马克思一方面着眼于人的解放的高远目标,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所肯定的公民权的局限;另一方面,又立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肯定这种公民权所表征的政治解放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肯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所承认的公民权服务于自己的事业。
马克思生前看到的、其分析和批判现实针对的,只是基于19世纪之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囿于19世纪之眼界的权利体系,未能看到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权的发展。但是,在认识领悟了马克思的理论观念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合乎情理地假设和推理,假如马克思看到20世纪公民权的发展,那么从他的理论视角和立场出发,他会怎么看。
许多人都知道,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H.Marshall)曾联系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公民权的历史发展,将公民权利划分为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他进一步指出,18世纪肯定了民事权利,主要包括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安全权等,它意味着等级制度在法律上的寿终正寝,意味着人身依附等束缚在法律上的解除,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自私自利之权利的人权。19世纪承认了政治权利,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抗议的权利等等,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所指的狭义的公民权。而20世纪发展起来的则是社会权利,这是一种赋予每一个公民在实际收入上的普遍权利,这种实际收入的获得与公民自身的市场价值无关。从消极的角度说,社会权利的发展是为了应对并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成员在现代社会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如贫困、严重的不平等、疾病、社会排斥等;从积极的角度说,它们意指一系列积极的应享权利:获得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失业补偿、低收入补偿、养老金、残疾人救济金等)、拥有工作、获得健康服务、拥有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住房、享受基本的义务教育等[9]。社会权利的发展是公民权在20世纪发展之最显著的特点。因此,所谓马克思会如何看待20世纪公民权的发展,实际上主要也就是马克思会如何看待社会权利的发展。
笔者曾经指出,尽管马歇尔的模式在今天看来已显得不够精细和灵活,且他以英国社会为基础的观点所具有的普遍性也已受到了很多质疑,但无可置疑的是,马歇尔道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趋势实际上也是合乎逻辑的,因此可以说体现了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也就是说,20世纪之所以需要发展出社会权利,是因为民权和政治权利只关注形式平等,而忽视了这些权利之真正实现所必需的现实条件和前提(譬如缺乏打官司的费用,人们就无法在法院中有效地捍卫自己的权利;缺乏必要的教育,人们也无法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因而是不自足的,而作为一种“在实际收入上的普遍权利”的社会权利,则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实质性的补充和支持[10]。换言之,社会权利与民权、政治权利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它所着眼和强调的不是形式平等,而是实质平等。就此而言,可以认为,社会权利的发展在精神上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家公民权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如上所述,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公民权的关键就在于,资产阶级国家通过“人权”予以承认并以“公民权利”予以维护的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所谓人权,无非就是作为以市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的成员自私自利的权利,这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权利,其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不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市民社会的局限也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国家所肯定的权利的局限。这种局限的最明显、最突出之处就在于,它只关注形式上的权利平等,而无视权利的真正实现所需要的现实社会条件。比如,要使自由这种权利真正落实到现实的人的现实行动中,这个人就必须具备一系列精神(如教育)、物质(如经济条件)前提,缺乏这些前提条件,自由对他而言就是空的,就是画饼。而在既存的市民社会结构中,这些条件在成员中的分布存在着结构性(阶级)的不平等。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利体系实际上是以形式上的权利平等,承认、肯定并维护了有产者实质上的特权,承认、肯定并维护了市民社会中实质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结构上就表现为阶级分化、阶级对立。而要克服这种局限,就必须实现实质的平等。
事实上,早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即《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中,马克思即明确指出了克服只注重形式平等的权利体系之弊病的方法。针对《纲领》认为在劳动资料成为社会公共财产之后,集体应该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观点,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7]435。首先,所谓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来计量,于是,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因为它虽然不再承认阶级差别,但它将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和工作能力作为“天然特权”加以默认,“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7]435。其次,由于每个劳动者的具体生活状况不同,比如,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没有,一个子女较多,另一个较少,因此,即使在提供的劳动相等从而在生活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劳动者事实上的所得也必然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而“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马克思指出,“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7]435。也就是说,为了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权利也即市民社会成员权利的局限,真正实质性地保障和实现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社会就必须认真地面对社会成员之间所有先天和后天的条件以及实际需要的差别,并根据这些差别给予区别对待,而不能无视这些实质性的差别,只给予形式上平等的权利。当然,马克思承认“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7]435。要充分做到这一点,从而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在当时,甚至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都是不现实的,只有到了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有可能。不过,我们不妨暂时不谈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无比高远的目标,而仅仅从马克思所关注的实质平等的角度,回过头来平和地思考一下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即马克思会如何看待社会权利在20世纪的发展?是否可以说,社会权利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马克思“权利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的思想,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是按需分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之有限度的实践呢?甚至,换一个角度说,社会权利的发展本身不无资产阶级国家从自身立场出发而从马克思的理论中获得的启发和教益吧?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社会权利的发展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既有的两个分配原则,即按资本分配(利润或剩余价值,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然是主导性的)和按劳分配(工资,这在马克思看来当然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支付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而非劳动的价值)之外,又增加了一定程度的按需分配的成分。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马克思会无批判地肯定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权利实践。即使承认社会权利是按需分配原则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之有限度的实践,毕竟那也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限度的实践”;即使承认社会权利的发展包含着资产阶级国家从自身立场出发而从马克思理论中获得的启发和教益,毕竟也是从“资产阶级国家立场”出发而获取的教益。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构想,要彻底克服资产阶级国家之权利体系以形式上的权利平等承认、肯定并维护市民社会实质上不平等的弊病,首先必须改变造成这种弊病的根本制度性原因,即经济基础,也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从根本上维护这一经济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而现在的社会权利实践恰恰是在维持既有制度体系的前提下展开的。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下,这种社会权利实践必然呈现出至少两方面的弊病或局限:
第一,马克思曾经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1]189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要么为赚钱所驱使,要么是纯粹的消费者,而不是一个以自身潜能充分全面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为取向的解放了的实践主体。而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从根本上变革既有财产制度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社会权利实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按需分配是应该与“各尽所能”紧密相连的,并且,着眼于人的解放这一根本价值目标,按需分配所要推动的就是人本身的全面发展,人的真正自由的实践,换言之,应该推动人类向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4]88-89。但在20世纪乃至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中,社会权利(或者说社会权利旗帜下的“福利”)实际上只是人们的一种新消费品,也就是说,它所体现并且助长的是20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消费主义文化,而不是以自由而全面的实践为价值取向的人的解放。
第二,如前所述,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历史发展之第三阶段的社会形态,应该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也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社会的分裂将不复存在。但不是国家吞没社会,恰恰相反,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7]195,是国家权力让位于社会的力量。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指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46就此而言,按需分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显示的是社会的力量。但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权利恰恰是“福利国家”的实践,是在既有国家制度下,由国家权力实施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实践。在“福利国家”体制下,公民确实有“权利”获得国家提供的福利保障来满足其生活需求,但是,当公民向当局提出福利申请,证明自己符合当局提出的条件因而有资格获得所要求的福利待遇时,实际上就是在申明自己对既有之国家权力秩序的承认。公民承认并依赖国家,国家通过提供福利、看护公民而强化自身的力量和权威,就像一个父亲通过照看自己的孩子而获得和巩固自己的权威一样。并且,就像托克维尔所预言的那样,国家这种“父权”不以教导人如何长大成人为目的,而是以把人永远看成孩子为目的。它要充当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使每个公民逐渐失去自我活动的能力,习惯于接受一切,并将这一切看作恩惠。逐步地,它把公民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然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11]869-870。在此意义上,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权利实践确实有些像不少左翼思想家批判“福利国家”时指出的那样,是资产阶级国家招安工人、诱使工人放弃反抗既有秩序的一种手段[12]8-11。它诱夺了公民的自由意志和自由行动,削弱、瓦解了社会力量,强化、巩固了国家权力。这和马克思所说的“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目标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不过,一个较好的现象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鉴于“福利国家”的种种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强调社区、结社等社会力量作用的“福利社会”的思想和实践呈现出日益发展的态势,并隐隐有取代“福利国家”的迹象[13]122。如果马克思泉下有知,对这种迹象也许会表示某种有保留的首肯吧,就像当年他有保留地肯定政治解放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一样。
[1]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Central Complic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ed. & trans.),CollectedWorksofMarxandEngels:Vol.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2] 王小章: 《中古工商城市与近代公民权的起源:韦伯城市研究的政治遗产》,《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99-120页。[Wang Xiaozhang,″The Medieval Cities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Citizenship: The Heritage of Weber’s Sociological Study on City,″SociologicalStudies, No.3(2007), pp.99-120.]
[3]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Central Complic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ed. & trans.),CompleteWorksofMarxandEngels:Vol.30,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4] 王小章: 《从“自由或共同体”到“自由的共同体”——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Wang Xiaozhang,From″FreedomorCommunity″to″CommunityofFreedom″:Marx’sCritiqueandReconstructio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4.]
[5]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Central Complic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ed. & trans.),CollectedWorksofMarxandEngels:Vol.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6] [法]傅勒: 《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朱学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F.Furet,MarxandtheFrenchRevolution, trans. by Zhu Xuepi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6.]
[7]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Central Complic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ed. & trans.),CollectedWorksofMarxandEngels:Vol.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8]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Central Complic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ed. & trans.),CollectedWorksofMarxandEngels:Vol.4,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9] [英]T.H.马歇尔: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见郭忠华、刘训练编: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T.H.Marshall,″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Guo Zhonghua & Liu Xunlian(eds.),CitizenshipandSocialClass,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10] 王小章: 《公民权视野下的社会保障》,《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92-96页。[Wang Xiaozhang,″The Social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izenship,″ZhejiangSocialSciences, No.3(2007), pp.92-96.]
[11] [法]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A.de 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Ⅱ), trans. by Dong Guoli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1.]
[12] [德]克劳斯·奥菲: 《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C.Offe,ContradictionoftheWelfareState, trans. by Guo Zhonghua,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13] [英]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A.Giddens,TheThirdWay:TheRenewalofSocialDemocracy, trans. by Zheng G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Marx and Modern Citizenship
Wang Xiaozhang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Sociological Scienc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Marx believed that human history, on the whole, is such a process: from the individual being just ″the accessory of a definite and limited human conglomerate″ to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people on the basis of the dependence of object″ through the bourgeois’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then to ″a real community in which the individuals obtain their freedom in and through their association.″ In suc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one hand, the modern citizenship in a bourgeois state shows its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represents a historical progress. Marx’s critique of modern citizenship in the modern bourgeois state is not to end the citizenship, but to transform citizenship.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modern citizenship lie in that the person whom the bourgeois state recognizes through ″human rights″(droitsdel’homme) and protects through ″citizenship rights″ (droitsducitoyen) is just a member of ″civil society″ rather than a member of the ″human society.″ The so-called human rights are just the egoistic rights of members of a civil society. Such rights only focus on formal equality, while ignoring the real social conditions need to realize these rights. However, in the existing structure of the civil society,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conditions among its members is structurally unequal. Therefore, the human rights system of the modern bourgeois state, as a matter of fact, recognizes and preserves the privileges of the propertied class through the formal equality of rights, and consequently the substantial inequality in the civil society.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modern citizenship is that it replaces the absolute obedience to a monarch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rights of citizenship, liberates its members from the feudal relationship of personal dependence, and makes them become members with personal freedom in the ″civil society.″ Without the personal freedom that modern citizenship affirms and recognizes, there would be no free flow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no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hence no material precondition towards ″a real community in which the individuals obtain their freedom in and through their association.″ In this reg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itizenship is an insurmountable step towards human emancipation; in addition, the citizenship in the modern bourgeois state also provides the weapon for the proletariat and its political party to fight for and defend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to promote the human’s emancip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arx’s theory, how would he se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tizenship in the 20th century,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itizenship? In terms of its emphasis on the substantive equality, social citizenship is consistent with Marx’s view in the spirit,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Marx would have no criticism against the practice of social citizenship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rights shows at least two disadvantages: First, in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social rights became new goods for consumers in the 20th century. What social rights reflect and encourage is consumerism, rather than human emancipation with freedom practice as its value orientation. Second, the social rights of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were a practice that was carried out and enforced by the state power. When citizens file applications to the authority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ey are eligible for the welfare rights, they are actually expressing their consent to the existing order of state power. Therefore, the social rights did not become the conditions for citizens’ freedom; on the contrary, they lured and seized the citizens’ free will and free action, thereby collapsing the social forc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tate control.
Marx; citizenship; social rights; human emancipation

栏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6.06.123
2016-06-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SH005)
王小章(http://orcid.org/0000-0001-7670-992X),男,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社会理论研究。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7-06-30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33-600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