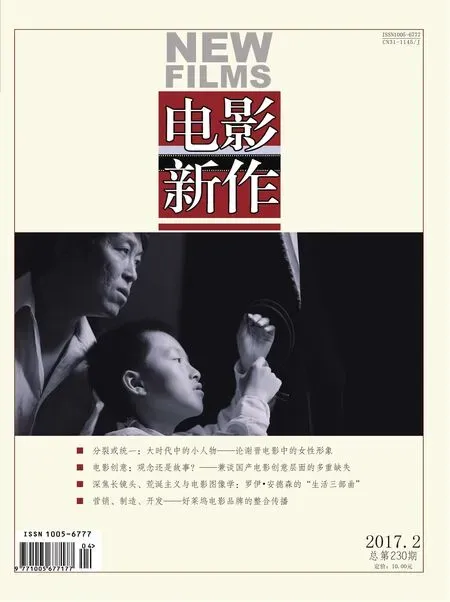分裂或统一: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论谢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陈旭光 罗昌亮
分裂或统一: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论谢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陈旭光 罗昌亮
文章从女性形象的朔形与历史流变的角度将谢晋电影分为四个阶段,以谢晋电影的四个阶段为纬,以女性形象的精神状态、人物造型与意识形态表征、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等为切入角度,探讨谢晋在不同阶段的艺术创作过程中,面对不同的时代环境而进行或呈现的适应、妥协、调整、突破、创新、契合、疏离等关系样态,分析谢晋电影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谢晋电影 女性形象 精神状态 个体与集体
谢晋曾说过:“我一贯注重人物”、“在我看来,一个剧本,人物好了,其他方面还是可以修改提高的,如果人物缺乏表现力,我是不大选它的”①,谢晋非常重视塑造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成为谢晋表达思想内涵的重要渠道,挖掘人物形象成为分析谢晋电影的一大途径。纵观谢晋电影,太多女性形象跃入眼帘:吴琼花、冯晴岚、宋薇、赵秀芝、胡玉音……魅力独具、灿若群星的女性形象系列构成谢晋电影的重要风景线,也是阐释谢晋电影的重要途径。“谢晋写人,最主要是写人的独特命运,他尤其擅长对女性独特命运的描写。在他的影片中,最有光彩、最富魅力的是那些有着独特命运的中国妇女的美好形象”。②女性形象,是谢晋电影的闪光点,也是谢晋电影文化价值与审美指向的承载体。谢晋的艺术创作的严谨态度、反思历史的批判情怀、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以及时代的影响,促使了这些女性形象的产生。谢晋以其六十年的创作历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连缀成一条线索,一条谢晋电影发展过程的线索,进而是一条分析谢晋电影的线索。这些女性形象处于不同的电影文本,具有不同的思想、命运、性格,承载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涵义,又因谢晋电影始终不变的严谨态度、极高要求的电影品质、铁肩担道义的道德责任感而具有某些较为稳定的内核。
一、适应与妥协:对于政治的规避(1955—1975)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逐渐整合为一个高度统一的一体化格局。由于政治运动对电影体制、电影生产与电影批评的制约以及电影本身对政治话语的过分依赖,在全社会和电影界形成了一种以政治为中心、电影服务于政治的电影观念。由于这种政治电影观有利于强化国家和政党的权力,而在1949年至1979年间的中国内地电影界获得了唯一的合法性”。③在这一阶段,电影是一门艺术,更是意识形态的载体。电影功能侧重于传播新中国的国家理念,完成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建立。个人表达让位于政治诉求是电影的宿命,甚至在后期发展为个人表达淹没于政治诉求之中。
谢晋与夏衍、蔡楚生、史东山、汤晓丹、郑君里、吴永刚、张骏祥、凌子风、水华等电影工作者一样,抨击旧社会、歌颂新中国、书写革命历史、赞美劳动人民等等成为“先天的”、注定的、无法更改的主题。女性形象作为符号,成为谢晋电影表达这类主题的承载物。当然,谢晋也在表达政治诉求的过程中融入个人表达,只是个人表达与政治诉求的关系时而融合、时而矛盾。当二者融合时,谢晋便获得荣誉(如《红色娘子军》和《女篮五号》),而当二者矛盾时,谢晋受到批判(《舞台姐妹》)。

图1.《红色娘子军》
在这一阶段中,谢晋的电影包括体育片、喜剧片、伦理片、革命战争片等。尽管类型不同,但是女性形象无一例外地在精神状态上界限分明:旧社会的女性凄苦消沉,而新时代的女性幸福乐观。例如,《红色娘子军》中在地主家的吴琼花悲苦凄凉、参加革命后的吴琼花满怀希望,她追捕南霸天受重伤,在没有麻醉剂的艰难情况下动手术,党代表洪常青关切地问:觉得怎么样?她用勉强可以听见的声音回答:“行!不要紧……这……比挨地主的鞭子好多了”,前后对比的言语表达了人物处于不同处境的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
壁垒分明的精神分界源于电影人物与电影故事的碰撞、源于导演与政策的碰撞、源于艺术与政治的碰撞。精神界限原本模糊不清且难以言说,而在艺术创作之中如此彻底地割裂两种精神,直白地划分真与假、好与坏、善与恶,自是政治的需要、意识形态的诉求。从这一意义来说,女性形象是表达国家意志的个体,是所要传达的政治理念的化身。
女性形象的精神状态的界限分明带来精神状态的畸变,她们的精神状态脱离实际生活、日常常识而具有难以置信的思想境界,于是《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春苗》中的正面女性形象具有超出身份、地位、年龄、学识等的精神觉悟。在《舞台姐妹》中,春花不断发问:“为什么姐妹们台上、台下的命运会一样的悲惨?”;“为什么‘牛’跟‘牛’还要斗角?”;“为什么人死了却反而热闹得像办喜事?”等等。这是现实生活在电影世界的真实反映,是政治作用于现实生活进而作用于电影艺术的真实反映。
女性形象的精神状态界限分明,而性别意识却模糊不清,她们的性别意识遭受“阉割”从而存在生理区分但失去精神区分,即她们在生理上具有女性特征却在精神上不具有女性特征。例如,《春苗》中,春苗作为女性,并未呈现女性特有的语言、动作、思想等,而是一心为了劳苦大众甚至忧国忧民。性别意识的模糊不清,是时代作用于电影的结果,当时整个社会重视集体,要求个人以集体为重、为集体服务,个人只是集体的一分子甚至是集体的代表符号。例如,《女篮五号》中的林小洁代表的是生长于新中国的一代,《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代表的是整个受苦受难的贫民阶级,《舞台姐妹》中的竺春花代表的是整个自强自立的民间艺人甚至穷苦百姓……她们的精神状态不是具有个人感情(诸如友情、爱情、亲情),而是具有革命之情、阶级之情、国家之情、民族之情等等。在政治挂帅的年代,谢晋电影(包括整个电影界)必须以政治为中心,这是必然选择,尽管也是无奈选择。
女性形象精神状态的界限分明、畸形化及性别意识的模糊不清是导演与时代、政治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是现实生活在文学艺术中的投射、是个人思想对意识形态的妥协。
女性形象的精神状态作为内在思想外在地表现于人物造型,于是女性形象的人物造型也界限分明:正面形象的人物造型必是高、大、全,反面形象的人物造型必是假、丑、恶,即正面形象与反面形象在外表、语言、行为等等方面截然不同。例如,《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坚毅、顽强、疾恶如仇从而是正义人物的代表,而南霸天凶狠、毒辣、残害大众从而是邪恶人物的代表。正面形象与反面形象之间截然对立。女性形象的人物造型是政治对于艺术形象的潜在规定,是表达国家意志的现实需要。
女性形象作为个体,又与集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呈现鲜明特点。女性形象作为集体中的个体,却很少具有个人特征而只具有集体特征。正面的女性形象作为个体,是集体的缩影、服务者与奉献者,所思所想以集体利益为重、一言一行以集体为行动指南,如进行革命战斗(《红色娘子军》),建立政权、巩固政权(《春苗》),发展生产、开展体育活动(《女篮五号》《大李、小李和老李》)……反面的女性形象作为个体,也很少具有个人特征而只具有集体特征,她们或者代表旧时代(《舞台姐妹》中的女老板)、或者代表剥削思想、或者代表错误路线(《春苗》中的女巫医)。
女性形象的个人感情也淹没于集体感情:个人的爱情被剥夺(如《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与洪常青的爱情戏份被删)、个体的友情被替换(个体友情成为组织感情)、个体的亲情被泛化(个体亲情扩大为阶级感情、革命感情、国家感情等)。女性形象作为个体,对应于作为个体的导演;女性形象服务于电影中的集体,对应于导演服务于现实中的集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女性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发展而趋于极端。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文革时期),《海港》《春苗》《磐石湾》中的女性形象在极权政治的要求之下沦为符号化的意识形态传声筒。这三部电影的女性形象的精神状态、人物造型、与集体的关系等,与前期电影的女性形象相比均趋于极端。例如,《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会违反组织纪律而向南霸天射击,而《春苗》中的春苗高度服从集体要求,因此不可能出现春苗违反组织纪律的场景。《女篮五号》中,林洁因自己的遭遇而反对女儿林小洁从事篮球事业,这与集体意志有悖,而到《春苗》中,春苗妈对待春苗时不可能做出违背集体意志的举动,而是处处维护、支持与集体意志相符的春苗。在《海港》《春苗》《磐石湾》中,尽管手法纯熟、叙事严谨,可是人物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化身,语言、动作、思想均服从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在银幕上直接出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字样以进行直白的政治宣传。这是政治作用于艺术的结果,反映了那一时期的电影、导演与政治的关系。
二、调整与突破:规避之中的变革(1977—1979)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逐渐发生改变:政治上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经济上改革开放,中国正处于新旧时代交接的转折时期。此时,整个时代的人性复苏与自我觉醒也体现于电影创作之中,中国电影开始转折,逐渐摆脱作为政治手段的角色,政治对于电影的影响逐渐减弱。不过,由于时代变革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因此政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电影的探索和创新。
谢晋曾说:“电影是艺术。既然是艺术,就有它自身的规律,不能被概念性的东西左右”④,谢晋在这一阶段努力恢复电影作为艺术的功能与特征。谢晋尝试突破禁区,在题材、人物、思想等方面进行改变,他在遵守政治要求的前提之下,打破束缚电影的桎梏,恢复电影作为艺术应有的功能与特征。不过,由于政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扼制电影的探索和创新,于是谢晋电影处于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两个时代交替的夹缝之中,女性形象从而具有双重性质甚至矛盾性。

图2.《青春》
女性形象的精神状态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具有追求高尚品德、向往美好生活、热爱社会主义等“永恒不变”的集体感情,另一方面较少专注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逐渐显现个人感情。女性形象之间不再相互对立,而是出现融合局面。她们信奉路线纲领、革命大义、国家意志的同时,也注重博爱、真情、人性等情感。以《青春》为例,“它(指影片《青春》)是两个时代、两种观念、两种政治与美学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叠加与博弈的产物,是一座连接历史裂缝的浮桥”。⑤在《青春》中,亚妹进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献身于党的事业、接受老一辈党员向晖的教育,这些均符合“文革”电影的主题要求,而《青春》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以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为纲,而是表现人性、人情,以向晖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不是向后辈讲述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而是以无私而真挚的感情和行动帮助亚妹,而亚妹在恢复听力、开口说话之后也无私而真挚地帮助思想落后的阿燕。
女性形象的言行也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言行高尚、为国为家,另一方面更具人性、人情。《青春》中向晖的言行符合社会主义精神且热情真挚,《啊!摇篮》中李楠对敌人疾恶如仇但也认为照看孩子是婆婆妈妈的事情。女性形象的言行不是二元对立、绝对分化,而是互帮互助。《青春》与《啊!摇篮》中几乎没有反面的女性形象,女性形象之间彼此促进、彼此勉励。
文革电影的“三突出”原则扼杀电影的艺术性,而谢晋电影以减弱矛盾(《青春》与《啊!摇篮》都不注重敌我矛盾冲突)、淡化阶级斗争、表达人性人情等等类似于“换药不换汤”的方法,打破“文革”电影的人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革”电影的弊病。女性形象的双重性质是谢晋无奈之中的明智之举,反映艺术家在艺术、政治、人性的碰撞之中的选择方式。在不同的境况之下,艺术家有不同的选择,而在当时特殊的年代里,谢晋的选择出于艺术家的良知、出于对政治变革的把握。
女性形象作为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也呈现双重性质:女性形象仍是集体的一员,但是开始表现个人特征。女性形象一方面是集体的代言人,一言一行、所思所想均符合集体的要求、代表集体的意志,另一方面更具个体性、自主性、情感性。女性形象的生存、成长、发展均在集体的帮助之下完成,例如在《青春》中,亚妹的听说能力在代表集体的海军医生的治疗之下得以恢复,《啊!摇篮》中赵玉霞参加代表集体的红军之后免遭丈夫虐待,而她们获得新生、发展之后,全心全意地投入集体的革命、建设、斗争之中,从而与集体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女性形象与集体高度一致的同时,也出现裂隙。她们开始具有友情、亲情甚至爱情,开始表达个性、人性、人情,而这些是“文革”电影的禁忌。谢晋以巧妙的手法突破这些禁忌,还原电影作为艺术的特征。
谢晋以一贯的政治主题来贯穿电影,体现政治对于导演的限制,但谢晋以温和手法破除电影的陈旧观念,体现导演对于政治的突破。在这一阶段,谢晋电影突破“文革”电影的敌我分明、叙事夸张、人物虚假等等惯常而教条的叙事模式,代之以淡化敌我(《青春》并不存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而以情感为中心,《啊!摇篮》的战争场景成为叙事背景)、双重叙事(《青春》以向晖和亚妹为主角而采用两条叙事线索,《啊!摇篮》以李楠为主角而采用闪回镜头交代其以往经历)、以情感人(《啊!摇篮》充分表现了亲情、友情、爱情)等等手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物的精神风貌。在当时,谢晋电影的突破引风气之先,当大多数导演还在拍摄诸如《十月风云》(张一导演)、《严峻的历程》(苏里、张建佑导演)、《大浪淘沙》(伊琳导演)、《大河奔流》(谢铁骊、陈怀皑导演)、《黑三角》(刘春霖、陈方导演)等具有以往的浓重政治痕迹的影片时,谢晋拍摄的《青春》却以清新的风格、动人的情感、变革的观念等因素而给银幕增添一抹亮色、吸引大量观众,而第四代导演在拍摄《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小花》时纷纷进行创新已是两年之后,即1979年。谢晋电影的突破之路也更加深入,例如在《青春》中并没有讲述爱情,而在《啊!摇篮》中,李楠与肖汉平的爱情已成叙事内容,而且《啊!摇篮》比《青春》在人性美、人情美等方面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
谢晋电影的女性形象由前一阶段的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发展到这一阶段的自我意识的苏醒、叙事手法的改变、人性人情的呼唤,只是仍然受到政治的限制,这是因为谢晋电影处于两个时代交接的夹缝之中,谢晋电影既要遵循以前的电影观念,又渴望恢复电影的特征、本质。谢晋在政治要求之下进行创作,只是在两种政治思想的作用下,谢晋电影表现出双重性质。
三、创新与契合:谢晋电影的高峰(1980—1986)
此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伴随前一阶段的转折而发生巨大改变,政治在大众生活中逐渐丧失直接的支配作用,逐渐较少干预艺术,国家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也不再只是政治文化,而是各种文化思潮相继产生。于是,电影有了更大的空间、更宽松的环境、更自由的表达。
在这一阶段,谢晋与其他第三代导演(汤晓丹、成荫、凌子风等)及第四代导演(吴贻弓、谢飞、杨延晋、吴天明、郑洞天等)一起,改革以往电影的弊端,表达对人性的呼唤、对真实性的渴求、对人生的热情等主题。“严格地说,在新时期以前,谢晋电影尽管已经以其煽情的故事、流畅的叙事、精巧的镜头语言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但是他当时的电影作品仍然是当时整个大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成就并没有超过参加这一大合唱的前辈和同辈们,如崔嵬、郑君里、谢铁骊等,但是,到了新时期,谢晋电影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却以其鲜明的个性使他独立于他人之上,几乎无人能够与他所产生的影响和取得的荣誉相比。”⑥确实,当谢晋与第四代导演在“表现他们对‘文革’经历和历史的个人化的反思和重新审视”、“贯穿着人道主义的思考及人性的温情和暖意等”⑦之时,谢晋在电影的深刻性、准确性、影响力等方面均出类拔萃。谢晋电影与媒体、大众、评论家、政治达成一致,谢晋电影达到空前辉煌。谢晋电影在遵守政治的前提之下,在个人性、自主性、艺术性等方面走得更远,而这些也充分体现于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之中。
在这一阶段,谢晋的作品包括《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秋瑾》《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在这些电影中,女性形象的精神状态走向自我觉醒、人道主义。正如有学者所言:“我认为可以把他所意指的人道主义更准确地称为‘家道主义’。他贯注于影片中的人道主义始于‘家道’,终于‘家道’,它基本上就是‘家道’”。⑧尽管女性形象有时仍是高尚品德的化身(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某一阶级的代表(如:《芙蓉镇》中的李国香),但她们身上多了作为人本身的特征(例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是高尚品德的化身,但是她也追求爱情)。女性形象的精神状态大多是真、善、美,她们心底善良、品质高洁甚至忧国忧民的同时也追求幸福、追求自主;她们拥护政治的同时寻求自我完善;她们表现一如既往的爱国热情的同时注重自身发展。女性形象的性别意识开始复苏,一大表现是她们追求爱情,而前两个阶段中的电影几乎不涉爱情。爱情不再是电影禁区,而是普遍主题。女性成为真正的女人,而不仅仅是阶级代表、组织代表。女性形象的性别意识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性的复苏,反映了政治的影响对于大众的减弱,对于艺术的减弱。

图3.《天云山传奇》
在前两个阶段中,女性形象的精神状态整体上是积极向上,她们对社会主义怀有真挚感情,对社会主义生活无比热爱。而在这一阶段,她们在积极向上之中夹杂反思,反思“四清”、“反右运动”、“文革”甚至人性、社会、历史等。例如,在《天云山传奇》中,宋薇在“反右运动”时因无知而背叛爱情,但在“文革”结束之后因觉醒而忏悔爱情。又如在《高山下的花环》中,梁大娘为国奉献而呈现高尚品质,而吴爽的丑陋行为表现了人性复杂乃至阴暗。这些反思因符合政治要求而被允许,符合导演思想而被表达。当然,这种反思是“适度”反思,即对具体事件进行反思,而反思结果也通常归之于道德:以道德来抚慰因政治而遭受迫害的心灵、以道德来弥补政治事件的错误甚至以道德来概括政治事件产生的原因,这种“适度”反思是谢晋电影的局限性。
在这一阶段,女性形象的精神状态在整体上呈现一致性,但也有不一致性,尤其体现在电影《芙蓉镇》中胡玉音这个角色之上。与这一阶段的其他女性形象(诸如《天云山传奇》的冯晴岚、《牧马人》的李秀芝、《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大娘)相比,胡玉音更具真实性、可信性,谢晋没有拔高其作为卖豆腐的女子的思想,而是将其放置于真实的处境之中而赋予其真实的思想。胡玉音没有冯晴岚的舍己为“人”(罗群)的爱情精神、没有梁大娘为党为国的崇高品质,因此她的精神状态少了神性多了人性从而更符合现实。
“回顾谢晋的优秀影片,无一不是从伤痕累累的心灵中提炼出美的元素,尤其是中国妇女受到几千年封建思想重重束缚和摧残的各种悲惨命运。那些可悲可敬的复杂性格、美好心灵,给我们提出了多少值得深思和回答的问题。”⑨确实,谢晋在提炼“美的元素”的时候没有盲目歌颂,而是夹杂深层思考,而这也反映在女性形象的言行之中。女性形象不再只是专心于革命事业、国家建设、阶级斗争,而是更多具有自我思想、个人生活、人性色彩。女性形象思索自己、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在遵守政治要求(当然,她们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同时表达自己。女性形象的真实、深刻、感人促成了谢晋与大众、政治的交流,促成了谢晋电影的成功。反过来说,谢晋作为导演,在进行电影创作时,面对着艺术、大众、政治、文化等因素时,经过精益求精、认真思索、不断创新而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这反映了谢晋与艺术、大众、政治、文化等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这一阶段,谢晋塑造女性形象之时侧重人性、人情,着重表现个人行为甚至家长里短。例如,在《天云山传奇》中,影片描绘女主人公宋薇的内心活动:她听到过去恋人罗群的消息,脑海出现“闪电式”“幸福热恋”的回忆,耳边响起连续“我们永远在一起”的画外音。在当时,这种个人思考、爱情回忆的画面与语言难能可贵。谢晋顺应时代而进行改变,这是创新之举,因为在那时,大胆而真实地塑造女性形象需要勇气、远见,需要冲破落后思想、艺术偏见。谢晋面对时代,在遵循时代规则的前提之下,侧面地、间接地、巧妙地打破了规则。
女性形象作为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逐渐疏远。从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说,她们天生与集体保持密切联系,这是她们无法改变的事实,只是在这一阶段,她们的个人性成为影片重点。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之中,她们与集体是“如胶似漆”的状态,那么此时,她们与集体是“若即若离”的状态。她们不可能彻底反抗集体,而只能反抗集体的某一路线或某一代表,只能在遵循集体的前提之下成为独立个体。这是她们无法逃避的命运,也是电影中所有人物的命运,又是电影之外大众的命运。同时,她们的中心逐渐从集体(党、革命、国家、民族等)转为自我,甚至在影片中通过呈现个体来呈现集体。她们作为个体,开始具有自身的思想而不仅是集体的思想,开始具有自己的关系(她们与家人、与朋友等)而不仅是集体中的“同志式”关系,开始具有自己的感情而不仅是阶级感情、组织感情。女性形象作为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反映了大众作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二者是相互对应。也许,谢晋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并无进行映照、对应的考量,但其电影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时代背景的接近、电影的主题指向等等因素决定这种映照、对应。
值得一提的是,从前三个阶段的影片表现的时代背景来看,除了《秋瑾》以清末为时代背景、《舞台姐妹》以新中国建立前后为时代背景,其他影片都是以新中国建立到对越自卫反击战之间的年代为时代背景。在时代背景如此集中的众多电影之中,女性形象的精神状态、言行举止、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却有巨大不同,甚至呈现对立,而在时代背景相同的不同影片(例如:《春苗》与《芙蓉镇》)之中,这种不同甚至反差更为明显。这种反差,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政治,也体现了谢晋的沉浮、挣扎及其面对政治束缚而作出的努力、创新。
四、多元与疏离:衰年变法(1988—2002)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发生巨变:政治体制不断改革,政治进一步从大众生活中退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各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消费文化兴起……如果说在前三个阶段之中,谢晋电影面对单一的政治影响(在那个年代,各个方面的因素均可归结为政治因素),则在这一阶段,谢晋电影面对政治、市场经济、文化思潮等多元化影响,因此其电影的主题与内涵也呈现多元化:从伦理、政治等主题走向哲学、人性、宗教、国家、民族等主题。
在这一阶段,当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在视听语言、反思历史、反思文化和认识人性等方面不断创新且获得巨大成功时,谢晋电影也力求在电影主题、电影手法等方面进行思索、挖掘。不过,谢晋的“衰年变法”并不成功,其电影在主题的深度性、广度性、大众性等方面不尽如人意,并没有取得以往的轰动效应,其面对政治变革、文化思潮、商业经济、大众评论的影响而力求变革却力不从心,呈现出与大众的疏离性。
女性形象也不再仅是政治分子,而是呈现多元化:异国漂泊的留学生(《最后的贵族》中的李彤)、朴素善良的羊角大娘(《清凉寺钟声》)、身陷囹圄的囚徒(《女儿谷》)……女性形象的精神状态也呈现多元化,包括漂泊无根、大爱、拯救与自我拯救、个人追求……她们的精神状态的政治因素减少甚至没有,而是有了更多、更广阔的主题。精神状态的多元化,原因之一是文化思潮的多元化。中国打开国门,各种文化思潮涌来,谢晋作为一个善于学习、不断创新的艺术家,在这些文化思潮的影响之下而进行改变。随着政治影响力对于艺术的减弱,文化思潮的影响力便增强。
女性形象的精神状态也呈现疏离化,这种疏离化主要体现于对时代的疏离。她们的精神状态与时代精神存在隔阂,如:《女儿谷》讲述的是女子监狱里女囚犯们的故事,她们的精神状态对于大众来说太过陌生,从而无法与时代精神融合、与大众思想同步,因此无法引起大众的共鸣。
女性形象对于大众的疏离,源于谢晋对于时代的疏离。从电影内容来看,除了《秋瑾》,前三个阶段的电影内容都含有谢晋的经历,尤其是第三阶段中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表现的正是谢晋饱经忧患的时代,而这些电影也成为谢晋的代表作,同时获得大众认同。只是在第四个阶段,谢晋表现的是自己以前较少涉及的领域(当然,这并不是说导演没有经历的生活便是无法成功表现的内容),缺乏自我认同,因此无法在塑造女性形象的过程中驾轻就熟,产生疏离感在所难免。
在这一阶段,女性形象的言行不再是宣扬政治口号、谈论政治路线,而是更为真实地表达个人诉求、个人感情。例如:《清凉寺钟声》的羊角大娘绝不会圣人般宣扬政治口号,而是充满爱心地抚养“狗娃”;《女儿谷》的女性们也没有因为囚犯的身份而被塑造成反面政治形象。女性形象的言行呈现多元化,依人物形象、电影主题、思想内涵等的不同而不同,而不再仅有政治言行。她们因精神状态的多元化而表现出言行的多元化,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时代的多元化。女性形象的言行也呈现疏离化,她们的行为于观众来说不太真实甚至遥不可及。《最后的贵族》中李彤是生于贵族家庭的留学生,她的生活于当时大多数观众来说太过陌生;《女足九号》中罗甜为了兴趣、为了祖国而踢球,而这种心态却与当时全国人民大力发展经济的现实相悖。在电影中,女性的言行趋向个人化、小众化,因此她们的表达与大众脱节,从而与大众产生隔阂。
女性形象作为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进一步分离,这种分离程度相较于前一阶段更加彻底。女性形象远离集体,集体成为背景而发挥甚小作用甚至毫无作用。女性形象作为个体而成为影片主体,“形象大于思想”。⑩她们成为影片的表现对象,“人”的因素在影片中凸现。女性形象作为个体,也与电影之外的集体(大众)疏离,精神状态与言行举止均与大众存在陌生感,没有与大众切合。尽管谢晋创作电影之时努力与时代同步,例如他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拍摄《鸦片战争》,在2002年足球世界杯时拍摄《女足九号》,但是他在思想上、精神上无法与时代同步,于是人物形象的思想与内涵、影片的主题与内涵也无法与时代同步,从而无法获得认同。
在这一阶段,谢晋电影面对的不仅是政治的影响,还有多元的文化思潮及市场经济等的影响,因此谢晋电影的主题、思想、女性形象等趋于多元化。在这一阶段,谢晋面对时代变化,在把握时代精神时显得力不从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代疏离。谢晋努力适应时代变化、接受外来思想、进行艺术创新,尽管没有达到以前的高度,但其努力不容否定。
结语
从女性形象的角度将谢晋电影划分为四个阶段,是因为四个阶段的女性形象具有不同的特征和意识形态含义。第一阶段(1955—1975),女性形象是革命的“棋子”、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她们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无意识的传声筒,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被动塑造者。第二阶段(1977—1979),女性形象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只是政治对于她们的影响仍根深蒂固,她们仍是集体的代表但开始呈现个人特征、仍然对于社会主义充满真挚感情却开始表达个人情感,于是女性形象具有双重性质甚至矛盾性。第三阶段(1980—1986),女性形象进一步从集体脱离而成为独立“个人”,“个人”开始自我思考,从以往热情甚至盲目的革命理想转变为反思、自醒甚至痛悔,女性形象符合时代氛围,引起广泛共鸣,谢晋电影达到高峰。第四阶段(1988—2002),女性形象作为“个人”,更具独立意识,更具多元化,从单一的政治思维走向多元的人性思维,她们的思考内容从以往相对单纯的“集体”、“国家”发展到“大爱”、“救赎”、“历史”、“存在”等更为多元而宏大的主题。女性形象呈现多元化的同时也呈现疏离化,无法获得广泛共鸣。四个阶段的女性形象各不相同,这是谢晋电影面临政治、文化、商业等多元合力之下的必然结果,毫无疑问,这是阿尔多塞所说的“历史的多元决定”的结果。
谢晋在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长期与社会同步、与时代同步,从而获得巨大成功。谢晋的创作生涯与时代环境密不可分,从其电影的女性形象的角度可以发现他与时代环境产生不同的互动关系:谢晋创作的《疾风劲草》《黄宝妹》《红色娘子军》《大李、小李和老李》等影片因适应政治需要、大众品味等而获得认可,却因《舞台姐妹》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而受到政治批判,继而在拍摄《海港》《春苗》《磐石湾》等影片时在政治的要求之下妥协;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之中,影片《青春》《啊!摇篮》既有为符合政治要求的调整,也有对于艺术手法、主题思想的突破;改革开放之后的影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秋瑾》《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中开始对政治进行反思甚至批判、对电影艺术进行创新从而与时代契合,表现出艺术家的责任和良知;当改革开放更加深入,各种文化思潮涌进、市场经济兴起的时代背景之下,谢晋拍摄《最后的贵族》《清凉寺钟声》《启明星》《老人与狗》《女儿谷》《鸦片战争》《女足九号》等影片之时,面对时代环境的巨变而在主题、思想、内涵上走向多元化、疏离化。谢晋与时代环境的互动关系对于现在的艺术创作者来说具有借鉴意义,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注释】
①谢晋:《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②见张铭堂:《谢晋电影之谜》,收入《论谢晋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③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1905—200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
④谢晋:《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⑤石川:《青春:两个时代的美学边界》,《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第54页。
⑥尹鸿:《论谢晋的“政治、伦理情节剧”模式》,《电影艺术》,1999(1),第44页。
⑦陈旭光:《电影文化之维》,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4页。
⑧见应雄:《古典写作的璀璨黄昏》,收入《论谢晋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⑨见陈荒煤:《对真实人性、美好心灵的探索与追求》,转引自谢晋:《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
⑩谢晋:《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昌亮,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电影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