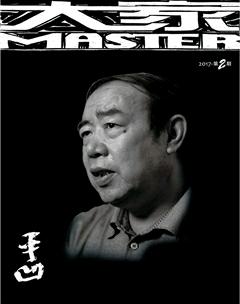大梁坡上的生活
帕蒂古丽

我们家在老沙湾大梁坡的屋子,盖在高高的土坡上。前些日子,白天装修,夜里,我和弟弟打了地铺,躺在埋着我们胎衣的地方,心里安宁得就像躺在爹娘的怀里。小时候进进出出的庄稼地,长满芦苇的河坝上,那些记忆都回来,一片一片落满院子,栖息在苞米叶子上、棉花杆子上和葵花的盘子上。
花了二十年时间书写,现在,我终于把自己写回大梁坡。这个村庄,对于别人可能只是一个村庄,对于我,却是一本打开的书。我回来,就是向故乡索要一份记忆,一份丢失的记忆。
坐在屋子的门槛上,用父亲的目光看那些荒草。我是在荒草中长大的,却从没有这么长久地凝视它们。孩童时代只顾着在一路奔跑中长大,似乎奔跑的方向,就是长大的方向,奔跑的速度,就是长大的速度,遥不可及的远方,充满了诱惑。成长中的奔跑,不会为谁停留,我甚至不会停下来,等一株荒草长大、追上来。童年的我,像一只惊慌失措的鸟。任何事物,都是匆匆地从眼角掠过。
现在,我用父亲的目光,打量大梁坡,村里的房子沿着一个椭圆形的大坑排列着,似乎从来就是为了我从这一头打量起来一览无余。坑里一直种着棉花,无论地分给了谁家,都种棉花。似乎这块地就属于棉花,从我穿开裆裤到现在,几十年来没有变过。
我大学毕业不久,就当了记者,离开大梁坡的第二年,父亲用嫁我的五百元彩礼钱,开垦了房子西南面,靠着河坝的十几亩地,这块地,用尽了他最后一点力气。等我抱着孩子,带着一架为他买的收录机回来,只赶上为他送埋。
我的婚礼父亲没有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来,父亲本来可以用那五百元钱买车票,到塔城参加我的婚礼,可他把钱用在了开垦荒地上,他想着我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在读书,他雄心勃勃,准备把他们都培养成“国家的人”,结果他走了,把他们全部留给了我来负担。
我们个个都像父亲,都留恋大梁坡,都想在年纪大了以后回来。这里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大梁坡有父亲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邻居,邻居呼唤孩子的声音,跟他们的父辈一样,邻居吠叫的狗,似乎还是多少年前,我们听着入眠的那一只。
早上起来,看着葵花的脸盘渐渐亮起来,一点点仰起来,转向太阳。雪山在远远的地方,就像画在天幕上。站在房顶,能看到海子湾水库的大坝。二十八年前,这条路扬起黄尘,运送父亲埋体的拖拉机,突突突地驶过。埋葬了父亲后,就是那条路,带着我们迁徙,让我们兄妹六人,朝着六个方向,走了几十年。现在,都该回来了。回到当初,回到没有离开过的大梁坡,回到另一个梦境,等父亲的声音,远远地叫醒我们。
三弟弟每天盘算着,口袋里的钱还能做多少事情。他盘算着盘一个大炕,叫兄弟姐妹们都回来,像小时候一样,大家一起并排睡在大炕上,这是他一辈子的理想,现在快要变成現实了。
三弟弟现在盘算的,父亲在他这个年纪也盘算过,大弟弟想的,跟父亲一模一样。一旦回到这里,日子似乎只有一种单纯的过法。这是真正的重来,地里种的,院子里养的,一样都不多,一样都不少。大地就这么古老,村庄也这么古老,日子还很悠长……还来得及,把过去的时光,再从头过上一遍。
最小的四弟,打算第一个回来。他是六个孩子中,最早离开这个家的。
冬天,我倚在门框上,看着大三弟带着孩子,在雪地里撒欢,我猛然想起,这个院子里,从来没有过四弟弟童年的脚印,他六个月就送给了姨姨家,被姨夫裹在被子里抱走了。
这个夏天,四弟久久地钻进茂密的蒿子里,似乎在寻找什么,我看见淹没过我们童年的蒿草,幸福地淹没了他。
白天种菜拔草,晚上一起睡在大炕上,这些小弟弟没能经历的村庄岁月,我们要为他补回来。我们从小欠了他这样一份日子。谁也无法把过世的爹娘还给他,我们现在只想把大梁坡的生活,原原本本还给他。
大梁坡的狗
回到大梁坡后发现,要想在村里来去自由,得先跟村庄里的狗搞好关系。
回大梁坡村的家,路只有一条,必须从邻居家门口过,邻居家的大白狗从来不拴。大白狗刚产了崽子,凶得简直像一头母狼。我不认识大白狗,它也不认识我。只好来去坐车,根本不敢下地。进自己家的门,还要经过邻居家的狗认同,回乡真不容易。
怎么过大白狗这一关,四弟弟的说法是:把它喂熟。大白狗的窝,在我家和邻居家之间,临近我家的大门,所有来我家的客人,都要过它这道关。养熟了,等于咱家养了狗。
要想喂熟,先得从生开始,这狗根本无法近身,每次狭路相逢,即便我是坐在“铁壳子”里,它都要来咬个不停,一直咬到大门口,我没法下车,只好对着邻居家大喊:“图拉訇,挡狗!”
图拉訇用维吾尔语骂了一句,大白狗撤退了。图拉訇大喊着:“你骂它,用维吾尔语骂它,声音要大,骂得凶一点,他就会怕你。”
我一边发抖,一边用维吾尔语骂狗,狗果然低下头,不叫了,乖乖进了狗窝。
后来我发现行走在大梁坡,你得不断变换语言方式,跟村庄里的狗对话。维吾尔庄子里的狗,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通用,回族庄子的狗,只理会回族话,你可以说甘肃话、宁夏话、青海话,如果你说普通话,它立刻能辨别出你是个外来客,就不会那么客气了。
汉族庄子的狗,即便不出狗窝,也可以从来人的武威口音、张掖口音、天水口音分辨得出是谁来了。汉族庄子的狗,对说河南话、陕西话的人十分顺从,庄子里操这两种口音的人居多,当然它也不排斥山东话。狗的器官很灵敏,如果你明明满口的大葱味,却说着一口河南话,它反而会起疑心。
现在到了大梁坡,你千万不要以为大梁坡人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过去大梁坡人养狗,多半是为了放羊、捕狐狸、追野兔、逮野鸡,现在狗的作用类似于石狮子,是为了迎客和装点门面。
在家里坐着,只要院子里的狗叫了,就是在给主人报信,有客人来了,赶紧出来迎客。
村庄各户人家的院子,根本用不着狗来看,田晓武家的摩托车扔在地边上,从四月扔到了八月,忙完收割,田晓武想起来摩托车还在地头,带了扳手、榔头和起子,敲打了一下,又把摩托车开回来了。
阿布麦提去了县城,家里的母牛扔在河边五六天,等他回来去河边牵牛,母牛下的牛犊都在河边欢蹦乱跳了。
玉努斯家的车没油了,扔在村道边一个礼拜,钥匙插在锁孔里,也没人去动。
村里人太太平平,谁也没空惦记别人家的东西。如果有外人打村庄里任何一家的主意,村庄里的狗就闻得出来。村庄里的人听得出来,迎客的狗叫声和狗的斥责声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不管去哪个庄子,都能变换着语言方式,跟狗准确地对话,进进出出再也不会有狗冲我恶吠。
邻居家的那条母狼一样的大白狗一见了我,就侧着身子温柔地躺下去,亮出两排大号黑纽扣一样的乳房。我一开始不明白大白狗何以跟以前“判若两狗”,四弟开玩笑说,狗的意思是你给了它许多好吃的东西,为了表示感恩,它也把身上最好吃的东西亮给你。
说笑归说笑,狗把最柔软的地方亮给我,至少狗表示它认识我、信任我,如果村里的狗都不认你,那你就算不上大梁坡人。
爬犁
她从外婆家走了出来,矮矮的,像外婆家低矮的烟囱。穿着胖嘟嘟的棉衣,脖子缩得像只小狗熊。她呼着哈气,越走越近,朝着这边的沙枣林走过来,她曾经看到给大舅舅送埋的亲人路过那片沙枣林,妈妈站在那里,用头巾捂着脸,肩膀不停地颤动。那是初夏,沙枣花的香味包围的初夏。现在是严冬,四处白茫茫一片,只有雪片寒冷的气味。
她拉着一架小爬犁,一直朝着沙枣林这边的小沙包走过来。雪在她的脚底下嘎吱嘎吱地响。她的嘴上不再有哈气,外面冰冷的空气吃掉了她嘴上的哈气。他拉着爬犁上了很高很高的雪坡,她认得那个大雪坡,夏天是一座沙包,大舅舅的双拐,就被孩子们埋在沙包边缘的沙子里。大舅舅满脸眼泪粘着沙子,眼睛上都是红血丝,他的嘴巴哭得干裂出血。
她希望在雪坡下面看到大舅舅陪着她。夏天大舅舅在这里陪她玩沙子,现在他躺在沙枣林后面的墓地里。
她眼睫毛和眉毛上结满了霜,雪娃娃一样,一次一次地把爬犁拉上雪坡顶峰,爬在爬犁上,呼啦一下子从坡顶俯冲下来。她爬上滑下,滑掉了整整一个上午。
太阳从坡顶滑向沙枣林的时候,她似乎看到大舅舅拄着双拐,立在沙枣林下看着她。除了他,似乎再也没有人陪她在沙坡边玩过。
她那么熟悉大舅舅拄着双拐的站姿。她玩爬犁的时候,他却不能来陪她了。她这样想着的时候,觉得白色的大雪坡,像一座巨大的坟。
她从小被外婆娇惯,大舅舅也总是保护她,可小舅舅不怎么待见她。他喜欢跟她抢东西。小舅舅跟她一起去沙包上滑爬犁,总是让她给他拉爬犁。坐在爬犁上的总是他,他一个人滋溜滋溜的滑下去,让她帮他把爬犁拉上来,然后他坐在爬犁上,滋溜滋溜滑下去。她站在寒风里,看着他一次次像飞一样滑下去,她看呆了,感觉雪中的爬犁像长了一对翅膀,载着小舅舅飞下雪坡。
舅舅不在家的时候,总是把爬犁藏起来。这一天,外婆和小舅舅、外公都出门了,就她一个人在家里。她偷偷把爬犁从仓房里拉出来,拉到了雪坡上。
谁也没看到,她像一个长了翅膀的小雪人一样,从雪坡上飞下。雪在她四周飞溅,她闭上眼睛张大嘴巴,幻想着地上的雪都变成甜甜的白砂糖,飞进她嘴巴里。
小舅舅滑爬犁时,嘴里总是含着从大队商店里买的橘子味水果糖,坐爬犁没有她的份,水果糖更没有她的份。她看着爬犁在雪里飞,水果糖的气息和雪的气息搅和在一起。
她期待小舅舅能给她玩一次爬犁。她期待的事情没有发生,雪地上的雪也没有变成白砂糖,要吃糖只有外婆大铁锅里的糖稀。用糖萝卜煮啊煮啊,从早上煮到晚上,糖萝卜就变成了糖稀。每次,等外婆把糖稀煮好了,她也在外婆的诵经声里睡着了。
熬过糖稀,一连几天,屋子里总是弥漫着一股焦煳气息,她的嘴巴里也是糖稀的焦煳气息。小舅舅不喜欢这种气息,只有小舅舅不在家的时候,外婆才会给她做糖稀。她一直盼着小舅舅出门,外婆好给她煮糖稀,吃了糖稀,再偷着玩小舅舅的小爬犁,让雪坡上散发出糖稀的味道。
她虽然没有吃到糖稀,却拥有了一次滑爬犁的机会。整整一个上午,她很满足地从雪坡顶上,坐着爬犁一次次地往下滑,沙包是她的,爬犁是她的,雪中的整个世界都是她的。尽管那个爬犁,只属于过她那么一个上午。
事隔几十年后的冬天,走过外婆家原来的房子时,我又看到了那排沙枣林、那个大雪坡,看到了她在北风里,冻得像红萝卜一样的小脸蛋。她侧着小小的身体,用冻红的双手紧紧地拽着拴在爬犁上的麻绳,在雪地里吃力地往前走。
我看到她的孤独,一个孩子童年的孤独。
我一下子认出了她,她就是五岁时候的我自己。
记忆的侵犯
他的目光那么专注和坚定地看着我,好像要拔出多年前在我身上撒下的一些钩。从他熟悉的问候语和看我时用力的表情,我能感受到,他和我在相逢的同一时刻,我们一起紧紧拥抱了过去。那个被稱为“记忆”的奇妙东西,骤然飞临我们头顶,栖息在我们紧挨在一起的肩头,在我们之间倏然滑落,化成深秋的雨水,洒落在我们的眼眶和脸颊。
无数死亡的记忆复活,掺杂着重逢的喜悦,就这样他紧紧拥抱了我,这个少年时代的见证者,也深深地拥抱了他自己。
这个年龄的男人,拥抱我和拥抱自己同样需要勇气,少时那些记忆给了他这一刻的勇气。紧接着他颓然地丢开我,似乎那股勇气一下子抽离了他的身体,像被什么东西抛下一般,他愣在院子里不知所措,有些惊异地看着我,似乎在惊异我如何从天而降,惊异刚才的那股突如其来、冲破世俗的力量。
我明白他目光坚定,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目光,才能集聚足够的力量,穿透那么深重的岁月,调动那些久远的记忆。
我眼前闪过一个镜头:在他家的羊圈里,他让五岁的萨吾列和七岁的我,还有六岁的古丽尼沙为他挠脊背,他的身体已经发育得很强壮,肩膀宽阔,膀大腰圆。
童年的我,连同那个羊圈里的气味,还有他油腻的脊背上的体味,一下子紧逼过来,白花花的脊背在黑暗的羊圈里让人眼花缭乱。
我没想到,自己还保存着这样一个镜头,也没想到这个镜头,会在几十年后再见到他时显影,我有点慌乱地看向他。
我有点晕眩,羊圈里的那个镜头,恍然是梦。
他有点奇怪地对我点头说:“铁辽喀孜就是我,我就是铁辽喀孜。”
从我有点疑惑的目光中,他似乎看出了一种怀疑,像是在对自己做一个自我肯定。我不知道,那一刻,他是不是把过去那个青春年少的铁辽喀孜,和现在站在我面前苍老的铁辽喀孜连接在了一起,他的话像是为了让我和他一起,认领几十年前那个镜头。
铁辽喀孜的语气,让我确认羊圈里的那一幕真的发生过,一个小伙子,把三个年龄加起来跟他一样大的女孩关进羊圈里,逼着女孩们为他挠痒痒,他背对着我们,两条胳膊搭在羊圈凸凹不平的墙壁上,很享受地轻轻呻吟。
他只是发出低微的呻吟,他用声音侵犯了我们的耳朵,除此以外,他对我们没有做任何侵犯的动作,他可能还没有学会该如何侵犯。
他不会知道,此刻,这件往事突如其来,侵犯了我的记忆,那声音和镜头,竟然储存在我的记忆里那么久,只是为了在再次遇见他时显现出来。
铁辽喀孜穿着短袖衬衫和棉马甲,站在无遮挡的院子里,他的衣服和暴露在冰雨里的胳膊被淋湿了,他浑然不觉地说:“没错,你就是大梁坡的那个小小的古丽,你没有变。”
尽管我已经年过半百,可在他面前,我确认地点点头。
他被无边无际的冰雨包围,我想把他拉回来躲避一下,让墙壁为他阻挡一下冰雨。我知道,我们无法阻挡记忆的侵犯,就像无法阻挡漫天的冰雨无边无际地降落下来,我和他花白的头发,都被记忆的冰雨淋湿了。
修改
有时候,我怀疑子我回到大梁坡,似乎是为了把过去的生活,用我现在的生活修改掉,涂抹掉。
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不可能是过去的。那个我偶尔回来,在夜色中小解的当儿,挨着我,看着曾经熟悉的夜空,远远的一点零星的光点,这时,我很真实地是我。
冬夜,看着一轮冰月挂在天际,地上无垠的白雪呼应着银白的月色,那个时候,我有一片刻像是回到了儿时。这样的时候已经不多了。
总有现在的我看着过去的我,或者过去的我看着现在的我。来来去去地奔走在大梁坡,她们互相熟悉着,有时候彼此靠近,有时候截然分开。有时候故人和回忆使她们黏合在一起,相互拥抱,合二为一。
我在试图一点一点,用现在心满意足的生活,抹去过去的苦难,而苦难不会真的消失。
那一次,我长久地回头,看我曾经读书的小学校路口,一个戴着白头巾,背有些佝偻的老年女人,站在路边茫然张望。
弟弟问我眼睛向后在追着看啥,我说,那个老年女人会不会是我们走失的母亲。他惆然地说,不会吧,是个捡棉花的。
我看到女人不见了,大片的棉花地里,棉花已经摘尽。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像是一个棉花桃子炸裂后,被掏走了棉花,我的心在刺眼的天光下变得干硬瘪塌。
我的心就这样被掏空过一千次一万次,母亲还是没有回来的迹象。
我只想在大梁坡盖了房子,等母亲回来,只要房子还在原来的老地方不变,母亲的魂若回来,就必定能找到我们。
不管我们的生命经历过什么沧海桑田,母亲也会认出我们。只有在母亲眼里,我们还是昨天的那个孩子,也只有母亲的存在,才能证明我们还是过去的我们,母亲能帮助我们完全回到过去。
也许我的回来,并不完全是为了更改过去不堪的生活,而是为了把现在的生活和过去的生活接合起来,还原一个完整的大梁坡。
我期待送给自己和母亲一个完整的家园。
回家路上的谜
从沙湾县城往大梁坡走,三十公里路,路两边的棉花,显出一场大雪普降的样子,似乎提醒着,天冷了,该摘了棉花做冬衣了。
棉花,以云的轻,围裹出最深重的暖意。高出来的棉花杆子,像从雪地里戳出来的树枝丫,给人一种春天化雪的假象,秋阳悬在半空,懒洋洋的,有种倦意。
摘了棉花后的棉田,像融雪后的大地,露出大面积的棕红,这就像一个反季节的预示,冬天很快就要赶来了。
路边的玉米,像是我长在地里的幼年记忆那么茂盛葱绿。玉米结实的样子,像母亲怀抱着婴儿。童心未泯的秋玉米,像是故意长出那么长的胡须,假扮成老头儿跟人逗乐。
红旗农场的酒葡萄也开始采摘了,搭了架子的葡萄地里,葡萄藤缠绵在架子上,像是一个穿着翠裙的女子,拥吻着挺立在地上的葡萄架,看着让人有一丝醉意。
每次去大梁坡,看到通往海子湾村的那条岔路,我就想象着路尽头,可以看见绿树土房的那个村庄海子湾,我不知道自己似乎有什么东西,遗落在那个与大梁坡毗邻的村庄,那一窝窝树,总是那么充满诱惑地朝我招手。
我曾坐在父亲赶的毛驴车上,从那条路上,那个黑魃魃的树窝子路过,父亲大概累了,一路上一言不发,只有他甩開的鞭子,在我头顶盘旋,那些树像我的头发一样在风里竖起来。毛驴车上拉的是父亲砍来的柴火,我坐在高高的柴火垛子上,心绷得紧紧的。风从柴火垛子上刮过,星星在天幕上一跳一跳的,惊魂不定。
我很想一个人下车,沿着那条土路,进入那个过去经常出没的村子,又担心村里已经没有人认识我,会奇怪我从那里来,来村里干什么。
小时候,去那个村子,似乎回回都是有理由的,打醋、买盐、买茶叶,我买过的第一块巧克力,就是在那个村里的商店,我第一次看戏,也是在那个村里,看蒋凤珍在戏台子下,粉白着脸子,跟那台上甩着水袖的花旦学唱戏。
穿过那个村子,就是海子湾水库大坝,上了水库大坝,就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对了,那个村子,是一个出口,是通往远方的必经之地,而往老沙湾镇的方向走,似乎是往后退,因为过了镇子,就离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边缘不远了,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有一个冬天,我趁晚上父亲睡了,偷了他口袋里的两块钱,第二天,村里的孩子去海子湾村买东西,路过我家门口,我跟了去,结果到了商店才发现,两块钱不见了,我空手而回。
回来父亲没有问起我,去商店干什么,这倒让我很惊奇,平时我做了错事他会呵斥我,这次却任由我去,也让我很奇怪。我怀疑父亲发现我偷了他的钱,趁我熟睡着的时候,悄悄又把钱重新偷了回去。
我那种说不出来的失落情绪,持续了半个冬天,起初我很懊悔偷了那钱,以为自己是我在路上把钱弄丢了,替辛辛苦苦的爹爹心疼,后来,我看爹爹从未提起自己丢钱的事,就判定钱一定是被爹爹拿回去了,又不戳穿我,让我自己领悟一个人平白无故丢了钱的感觉。
父亲去世后,这件事成了一个小小的谜,再也找不到答案了。我总是想去海子湾村兜兜,大概就是要寻找丢失在那段路上的谜底吧。
语言的弹坑
我喜欢村庄里的宁静,你可以像一个哑巴一样生活,来保持一颗心的敏感。
当语言的区域太宽广的时候,我会追逐语言追逐得很疲累,为省下一点体力,我喜歡保持静默。追逐那些虚无缥缈的声音,漫无边际的话语,太耗费体能,就像挖土和填埋一样,铲平那些语言的土丘,填平语言制造的沟壑会让人筋疲力尽。大片语言和声音轰炸过后留下的空洞,让我感觉世界的虚空和不真实。
不要用语言和声音填平我们之间的空隙,不要用嘈杂填埋我的空间。当语言抽离,声音消失,那种感觉像是要忍受一切,被你抽离后整个世界的坍塌,让人恐惧。
带着杂音的语言像是一阵急雨,在地面留下小小的浅坑,像天空下了一阵石子,粗砾地打在我铺开的思绪上,思绪从一块完整平滑的丝绸,变成千疮百孔的破网,兜不住任何细密的思想颗粒,那种华丽被撕开肢解,变得支离破碎。
心蜷缩成一团,像被用力揉皱的草纸。你的话说完了,我该把自己扔进垃圾桶里了,因为我有价值的部分已经被喧嚣和嘈杂损耗殆尽。
语言的矿坑,显出过度开采后被废弃的荒凉,残留着无用的残渣,脏污的废水,处处是被肆意践踏过的印记,所有的根系被革除,大地的营养被抽离,一切生命都无从生长。
我不是怕语言和声音,我是怕语言和声音过后,就像弹雨和炮火过后留下满目疮痍,语言的弹孔和声音的坑洞,坠漫满我的全身。
我的世界遍体鳞伤,无法收拾。
光线的重量
我真不希望村庄里有灯。在大梁坡,当我潜入黑暗就是潜入记忆深处。
我说过无数次,当你看到我独自坐在大梁坡的一间黑房子里,千万不要开灯,手按下开关,就像扣动了扳机,我会被送命的。
你走进我的房间,替我打开灯的那一瞬间,我的大脑里的电源就像被切断了,思维完全短路,我只看见你的嘴不停地在我面前张合,手不住地比画,我全然听不到你在说些什么。
我满脑子只想世界上最后一件我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情——那就是把灯关上。我失魂落魄地扑向电灯开关,就像濒死的人奔向一线生机。
灯光重新变暗,一个死而复生的我,又回到了这个世界。我的记忆恢复,视力恢复,听觉恢复,我又变成了之前黑暗里的那个我。
中间被光线切断的那段记忆被删除了,再也无法恢复,我左思右想,不知道你向我叮嘱和解释过一些什么,或者吩咐了一些什么事情。我努力回想,只有你的表情和在眼前比画的手势,我无法恢复你说话的内容。
有的时候,你把手伸向开关的瞬间,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我感觉自己的魂飞了出去,好不容易从黑暗里聚拢的自己,又在光线中散开,追不回来那些思维碎片,分崩离析。
我的重心顿时脱离了既定的轨道,像失重的陨石一样从宇宙跌落,我无法收集那些飘散在心际的物质,我的世界轰然离开我,抛下我,我感觉自己在下坠,我的星球在向着茫茫天际坠落,没有人能够救我。
我起身去追,我想把光线堵住,那样我的魂就会回到我的身体里。我关掉了电灯,手按在开关上的那一瞬,我突然无限悲伤,我发现,我追不到它了,我看到了那些被满屋子亮堂堂的光线赶跑的东西,看到它们飞离我而去的背影,那是我刚才在黑暗里养出的一截思绪,像一匹撕裂的锦缎,悲切地飘扬着飞远。
我看见了我的灵魂被光线撕开的样子。
光线是有重量的,一个人怎么能背着一屋子沉重的光线而浑然不觉。光线有锋芒一样的质感,它一根根扎在我的眼球上,一线窗帘缝隙漏进来的光,都会像匕首一样刺进我的眼球和身体里。
坐在光线里,我万箭穿心。我脆薄的身体承载着一立方一立方光的重量,我变得越来越重,重到能被我看见的东西都被光线挤压在我的身体上。
我只有闭上眼睛躲避光线,躲进想象的黑暗里,以减轻这光亮无限的重量。
我用我的灵召集的阴魂,黑暗里他们聚集在我周围,我像一个被催眠的人,与我前世的记忆相遇,与另一个世界的幽灵对话,恰好在这个时刻那盏万恶的灯被点亮了。
我好不容易汇聚的记忆,我脑海里没有见过光的事物全都死了,光线像刀一样切断了我与另一个世界的连接,我用意念的魔法打开的与另一个宇宙的通道,统统被关闭,灯光一下子把我切换到了这个世界,那个世界瞬间消失,我猝不及防跌落到了现实。梦境失落,想象幻灭的感觉恍如一梦,我无所适从。
上一世,我一定是一个穴居者。我适宜于独坐在黑暗里,感谢上天给我这样一方安全的黑暗,那是我最自如的时候。
我眼睛里的记忆之光,足够照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