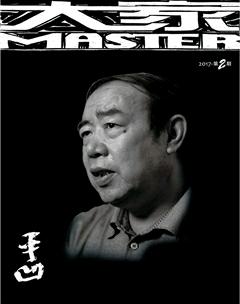谁是沈东武?
李振

走在大街上,随意拉住一个人,问他:沈东武是谁?这可能会让人莫名其妙,甚至送上一个白眼,因为这不符合人们接受一个人的规则。可是沈东武偏偏就以这种方式进入了王东的生活——怪异、无礼、莫名其妙、非同寻常,好像他压根就没把王东放在眼里,当然也没把自己当回事儿。
魏思孝的小说《沈东武》开始于一场漫无边际的回忆:“那时我二十出头,正处在人生少见的艰难时刻。如今我是这么看待生活的,总有一段难熬的日子,让你自我怀疑。不过当你再经历多一点,会发现,那只是生活的常态。”这段话对于王东或沈东武来说都很适用,一个是正在文学路上艰难挣扎的青年作家,一个是过了今天没明天的无业游民,好像他们的生活变得好起来就可以被称作奇迹,而继续艰难下去才是理所当然,才是“常态”。魏思孝显然不是一个写励志鸡汤的文艺青年,他写的是那些注定要被人们遗忘的社會烟尘,所以到最后也只能看着沈东武们因为宿醉或肉体的垮塌而步履蹒跚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在沈东武的生活里,死亡大概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沈东武在农村长大,出生之前还有两个姐姐。之所以强调出生之前,是因为等到沈东武出生,大姐已经夭折,二姐也被送人。七岁那年,一个叫张超的孩子因为溺水死在他面前。也许年幼的沈东武并不清楚死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死亡或者生命中的人就那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对于沈东武来说已是司空见惯,反正十几岁时母亲的离世让他清楚再也没人关心他了,仅此而已。以致后来父亲失踪,沈东武没去报案,因为在他看来,“能不能活着回来,他人无能为力,要看沈胜利自己的造化”,这不是别人能掌控的事,更不用说他沈东武了。沈东武的生活就那么一点点溃败下去,不能说更糟,因为本来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似乎有过朋友,但既不敢拔刀相助,又不敢一块挨揍。可是对于青春期的少年,尤其是沈东武这样的,除了义气之外还能给予别人什么呢?所以,朋友也渐行渐远。等他进了高中,情况貌似有所改善,至少他和一群来自农村的同学可以通过武力来挽救可怜的自尊。当然,武力也换来了在异性上更大的选择权,只不过这种选择被老师发现,也就很快结束了沈东武的学生时代。于是,游荡在社会中百无聊赖的沈东武才能在某个深夜与王东相遇,才能让王东觉得尴尬又感激,才能让王东羡慕,羡慕他的不腐朽和直白地写明喜怒哀乐的脸。可是,这又能怎样呢?
是的,这又能怎样呢?
这几乎是魏思孝所有的小说抛给我们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许只是读者的问题,因为它对于魏思孝、王东或沈东武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它真的就像曹寇在《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的序中所说的那样,像啐一口痰。痰当然不能咽下去,那过于体面,过于像距离沈东武十万八千里的成功人士,它必须要被响亮地啐出,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某种邪恶的快感。这很重要,因为他们需要以此来对抗空洞的生活,来掩盖一个人面对自己刺骨的绝望,来让自己显得更加不可救药以换取心里短暂的舒展,就像一个醉鬼在夜里摔碎一只空酒瓶,这种行为完全无用却能让他欣慰地相信自己成就了某种传奇。但是魏思孝清楚这没有意义,这就让事情变得更加残酷。当一种永无指望的生活被如此平淡地叙述,甚至在讲述中流露出一丝自我嘲讽的得意,这就像沈东武面对张超的死并没有什么深刻印象,连他的脸都记不起来了。那么,还有比这更加廉价更加无聊的生死或生活吗?小说在此显出一种奇妙的双重逻辑,一是小说本身的故事,故事里那些以无聊和无感打发绝望的人们在各自动作着,显现出一种现实生活的艰难;一是小说的叙述,它呈现出的淡然、习以为常让故事不断发酵,这不是面对生活的大惊小怪或极尽阐释,而是作者把自己置身其中的某种更加凄凉的对痛感的无奈、习惯和充满绝望的不以为然。那么,这两个层面的痛楚扭合在一起,制造出一种有着强烈带入感的底层青年的悲剧现实和精神世界。
当然,还要说王东。没有王东,沈东武的故事也就不复存在。
王东在小说里扮演着十分复杂的角色。他一方面参与了沈东武的生活,一方面又成为为沈东武著书立传的人。可是,“沈东武,他压根不是一个值得你去铭记的人,时间流逝,他曾带给我的些许感动,也变得不值一提……我将现在为沈东武著书立传归结为命运的捉弄”。即使此时“我对小说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每个生命个体都值得记录,故事要让位于人”,那么王东成为沈东武的“代言人”,也绝非是简单的巧合或是“命运的捉弄”。
小说似乎在用力地制造某种偶然,以便使王东和沈东武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仅仅从最开始的一幕,王东和沈东武就注定要被绑在一起。不管是王东小说里那个因交不起房租被女朋友逼迫出来抢劫的沈东武,还是那晚被王东打断了排便从黑影中跳出来的沈东武,最终都要跟着王东回到住处。小说很好地呈现从拒斥到认同的关系——面对沈东武想去王东的住处上厕所的要求,他先是婉拒,然后是进一步的确认“对,没人会同意”,但在离开后的一转身,“看到漆黑的角落里,烟头在闪烁”,这个人又变得无法拒绝。此时的王东到底在想什么?同情?吸引?还是看到了一个蹲在漆黑的角落里抽烟的自己?因此,不管王东在心里或口头怎样表达着对沈东武的厌恶,但他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二人隐秘的灵魂共鸣。那些被摆在纸面上的性格差异,那些不一样的行事做派,包括王东自己的辩解“我对他这个人一点深入了解的兴趣都没有”,都无法实现王东内心深处和行动上对沈东武的拒绝。当我们确信沈东武身上并不存在某种十足的吸引力时,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一种来自身份与处境上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也许被王东或沈东武下意识地拒斥,因为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和站在对面令人厌恶和莫名其妙的人有着相同的嘴脸。可是现实就是如此的奇妙与令人尴尬,王东带着陌生的沈东武回到住处,而沈东武又二话不说搬起王东的家当就让他住到自己更宽敞的房子里——当我们还在魏思孝“莫名其妙”的说辞中恍恍惚惚的时候,王东和沈东武却以类似多年老友过命兄弟的方式相处起来。
于是,我们看到了王东和沈东武相似的人生——在空虚无聊的夜晚自我麻醉地找乐子;都有女朋友无情离去的失败感情;伴随着沈东武斗殴后的逃亡,王东也决定去外地碰碰运气;他们的父亲相继离世;打过几份工,但也无法长久……直到他们几年后又在青岛相遇。对于这几年,小说写道:“一个年轻人该有的困境,都能在沈东武身上找到。这并不是短时间内的运气不佳,而是持续如此,让一个正处于人生最美好时光的小伙,毫无招架之力。沈东武不无绝望地想到,他的余生也会在这样的状况下度过,甚至还要糟糕。可是对照现实,还能糟糕到哪里去了。过了一阵子,沈东武发现他的人生的确还有下降的空间。”话虽然说得俏皮,但里面又藏着多少残酷和绝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人生并不仅仅属于沈东武,王东的日子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王东又何尝不是另一个沈东武?
经由王东之口,魏思孝在小说里表达了不少对于小说创作的理解,比如“每个生命个体都值得记录,故事要让位于人”,比如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人和事让写作更加旺盛——这一切都在《沈东武》中得以体现。从《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里的十八个短篇到《沈东武》,就像王东为沈东武立传,魏思孝所进行的不也正是同样的事情吗?他为一个又一个的沈东武立传,慢慢地呈现出底层青年群体性的生活细节。其中没有浮夸的、按捺不住的愤怒,没有马后炮式的同情和怜悯,既无为某个阶层代言的野心,也不是为了颠覆某些看上去更加光明和正确的价值观。他只是要写下那些熟悉和有意思的人,写下他们并不如意的生活,记录下那些转眼就可能被人们遗忘的沈东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