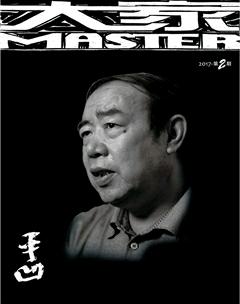一种文学史视域与“自由”困境下的反思
黄文倩

利维斯(FrankRaymondLeavis,1895-1978)在《伟大的传统》中曾说:“所谓小说大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随后,利维斯点评了包括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以及约瑟夫·康拉德(10seph Conrad,1857-1924)等人及其代表作,分析他们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继承与转化的意义与价值,阐释作家们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历史和人性的见识——一致与不一致的深刻感受力与世界观(即使有时候是碎片且难以统合的),日后,若还能够生产出新的所谓“大家”,亦是在长河般的文学史谱系下,才能相对理解、定位与推进。
当然,我并没有在暗示台湾70后、80后的代表作家与作品,已到达能够被典律化的阶段。从文学史的视域来说,一个作家和一部新作,其意义并不只于在场性,两岸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性历史的非断裂与纠葛,一直是后发展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更为隐秘且核心的特质,而承接且吸收这样的历史与存在(包含自觉与不自觉的遮蔽或回避)并开展其深度与潜能。之于作家既需要时间,也得有机缘、胆识与综合悟性。同时,作为一个从小生长于台湾历史的在场存在者与同辈人,选择与综述“我辈”的意义亦为不易。这一方面是因为审美距离过短,其思想、情感及价值仍有待日后的历史与人民考验,另一方面我较不认为该以过于自由、主观或策略性的生产来强化他们的价值——至今我们已明白,任何一个学者或批评家的静态与所谓的文明标准应有所节制。总的来说,批评家自觉地在文学史的材料视域下进行融合,参照式分析与理解不同阶段与地区的文学特殊性,促进两岸读者对他们的兴趣与反思,是我目前并非自我感觉良好的工作。
2015年至2016年间,我因缘际会地主持了两个与前述相关的文化与学术工作,自觉积累并反思台湾同辈甚至更年轻一代的文学作品。其一,应中国大陆《名作欣赏》的邀请,担任“台湾80后现场:新主体的发生、困境与再探求”专栏主持人,于此组织、推荐与评介80后的台湾代表作家——包括刘梓洁(1986—)、神小风(1984—)、郑聿(1980—)、崔舜华(1985—)、敷米浆(1982—)、言叔夏(1982—)等人及其作品。其二,2016年12月,由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主办,台北人间出版社协办,亦由我幕后统筹规划与落实:“叩问与新生——两岸80后青年阅读当代文学/小说十家论坛”,邀请两岸各五位80后的文学青年,来点评与阅读两岸70后的作家代表作。这批作家包括伊格言(1977一)、黄丽群(1979一)、徐誉诚(1977一)、张耀升(1975一)、林婉瑜(1977—)等小说家与诗人。
诚然,这些作家及其相关作品不能完整概括台湾70后、80后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正如同陈国安在其专书《小说新力:台湾一九七〇后新世代小说论》论述台湾70后世代时,已运用到的一些纵横的认识框架——认为他们是文学奖、高学历、“后解严”、台湾认同、网络社会的一代,也是晚近台湾经济衰退与多元文学思潮下的一代。而如果再加上解严后的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背景,本文实不认为我能够以更短的篇幅,对他们做出精确的综述与价值判断。因此笔者仅能先选择我相对较有认识基础,且有一定程度欣赏的70后、80后共七位小说家,包括70后的胡淑雯(1970—)、伊格言(1977一)、黄丽群(1979一)、徐誉诚(1977一)、张耀升(1975一)及80后的刘梓洁(1980一)、陈又津(1986一)等人及其代表作(在文类上,仍以小说为主。因为我认为晚近台湾的现代诗虽有不错的表现,但就思想、美学与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来说,小说的深入性与丰富性仍更高一些),来略谈一些台湾这两个世代/代际的文学特色与意义。自然,也包括我们所共同分享的美学、社会与主体困境。
从社会条件与历史语境来说,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70后,是深受台湾解严(1987—)、后现代与后殖民思潮下成长与发展的一代。对这一代的作家们而言,他们在父辈的美援国际背景及稳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长大,普遍高学历。同时西化式(尤其美国式)的“民主”与“自由”已是一种常识与感性,在许多学理还没进入70后的知识视野前,70后已经习惯于所谓的投票形式、少数服从多数,以及突出自我或个体优先的“自由”价值与感觉结构,对政治、国族、集体甚为冷感。整体上接近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但身处于当中的我们,很少认为它是一种“支配型意识形态”。这种强调普世、人性、温情的个体思想,到了90年代后,又慢慢发展出对地区性及本土化的高度认同与重视。总的来说,影响至文学生产与创造性的工作上,很大程度上就形成了弃守大叙事的文化历史感,重视日常、生活与个人感觉的主体性,以及体贴边缘、特殊、细腻与精神幻化的人物观。
具体到代表个案:以胡淑雯(1970一)来说,她毕业于台大外文系,当过新闻记者、报社编辑、妇女运动工作者,代表小说《哀艳是童年》《太阳的血是黑的》颇受台湾文学文化圈好评,后者还曾入围多项奖。她的作品最好的特色之一,跟她曾身为社运工作者的背景有关——在处理底层、弱势、白色恐怖等视野与题材,胡淑雯有一种自觉的进步视野。
伊格言(原名郑千慈,1977一)则曾就读于台大心理学系、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但均肄业,后来转至学风较自由开放的淡江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硕士论文处理的是:“现代主义、畸零人与战后台湾乡土小说”,很明显地,他的研究趣味也反映在他的创作特质与人物书写的偏好。代表作有《瓮中人》《噬梦人》《零地点》《拜访糖果阿姨》等等。他的小說的取材与思想,有很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异想、边缘与特殊性(如科幻)的色彩,同时在较好的作品中,又企图展开一种兼容台湾当下历史与普世价值特性的视野。例如《零地点》想象核灾在台湾爆发后的社会与人性的状态,具有跟进经典意识的末日预言倾向,同时也企图以这样的文学再次介入与警醒台湾社会。与此同时,伊格言又有极为个人化与小抒情的《拜访糖果阿姨》,两者的书写期间相当接近,并不构成矛盾与张力。我曾在2016年一次与伊格言的对谈中,和他讨论过这种书写与主体状态的选择与实践。对于伊格言来说,看似大叙事与个体的小叙事并不矛盾,他认为它们都如同舞台剧或表演艺术一般,是一种作家之于材料的选择、处理与体现。当然,这是就作家“艺术”立场上的一种世界观与实践,或者说,做一个清醒的做梦者的意志。从一般读者的角度,也由于伊格言小说的百科全书与异想的性质甚高,非经过专业训练的读者,恐怕难以综合地感受与理解他的作品,其作品的解放意义乃明显以具有“自由”余裕的精英读者为对象。
黄丽群(1979一),政大哲学系毕业,曾获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短篇小说首奖,林荣三文学奖短篇小说二奖等等。作品亦曾入选台湾多部重要年度文学选集,代表作有小说集《海边的房间》,散文集《背后歌》《感觉有点奢侈的事》等等。黄丽群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精致质感,她长于从日常与小叙事间,发掘资本主义时代下的废与美、日常与救赎的可能与不可能的微观哲理性。同时或许因为大学攻读的是哲学,黄丽群对于台湾晚近社会的虚无主义、现代美学与责任等关系,仍有其自身的焦虑、反省与思考。但体现在其代表作的关键特色,更倾向于以细腻的日常与颓废之美为救赎。
徐誉诚(1977一)则是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毕业,作品亦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宝岛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推荐等等。代表作专书《紫花》及中短篇小说《与情爱无关》。他还是公开的出柜者,《紫花》主要的题材与视野为同志及情欲书写。然而,我目前仍认为徐誉诚最好的作品是尚未收入与出版成专书的《与情爱无关》。这一篇作品在整体上,已意识到新一代的白领弱势者与台湾新自由主义和民主困境的相互生产关系,具有一种早年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洞察力。然而徐誉诚目前似乎并未想再朝这个方向发展,而更愿忠于小我或去集体性的自我。这种倾向性本身亦能看出台湾70后世代的共同困境(容后述)。
至于張耀升(1975一)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英文所及台湾艺术大学电影创作所。除了以文学为业之外,近年来主要从事编剧与影像相关工作,他的小说曾获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等奖项。在文字创作上,张耀升比较特别的是精且少产。200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缝》后,2011年后才再出版长篇小说《彼岸的女人》,以及具有报道文学性质的散文集《告别的年代:再见!左营眷村!》——以一个本省人的立场来访问与观察外省底层荣民。张耀升早年代表作《缝》大抵可以说处理到了小叙事意义上的“罪与罚”的视野,但在结构上以台湾式的家庭伦理为历史范畴,对于保守家庭中的情感依附、支配、隐形控制与报复,张耀升有一种高度的同理心与心理洞察的才能。尔后的《彼岸的女人》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基调,企图在爱与欲、罪与罚间继续发展对人性的心理幽微处的兴趣与秘密。
除却以上五位70后代表作家的概观,我曾在2015年春夏之际的一篇论文中,以胡淑雯《浮血猫》、黄丽群《入梦者》及徐誉诚的《与情爱无关》等小说为例,讨论他们作品中的新世纪台湾“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视野及意义。这三篇作品仍是我目前较肯定的70后的代表作,我曾指出过的观点至今仍未变异。概括如下:
第一,不同于中国大陆新世纪以来,由李云雷等批评家和创作者,有自觉地发展与建构“底层”理论与书写的实践,胡淑雯、黄丽群、徐誉诚等作家,虽然有这方面的尝试,其作品也屡屡受到台湾文化圈的关注或得到重要的文学奖项。然而,严格来说,这类佳作仍然只是他们作品中的“灵光一现”。优点是由于没有批评界与理论界的干预或影响,鲜少产生问题小说的概念先行的弊病,读者因此也得以较自然地、形象化地被触动,或多或少打破我们每天可能听说、遭遇,甚至也身在其中却早已麻木的灵魂。因而见识到新世纪以来,台湾社会的一些新的关键困境的横切面与主体困境。
第二,从主人公及题材的性质来说,胡淑雯《浮血猫》写的是底层老兵,黄丽群《入梦者》写的是长相平庸,甚至丑陋的青年男性,徐誉诚《与情爱无关》发掘的则是蜗居在都会下层、担任基层工商小职员、总是觉得自己很胖需要减肥的年轻女孩。综合来说,就是:老、丑、胖、青等相对弱势者的困局。虽然他们已无温饱问题,但在新世纪以降的台湾现代社会里,这些人民如何安顿与发展他们的人生?跟台湾社会与现代性发展呈现出什么样的相互生产关系?
第三,胡淑雯的《浮血猫》是她的名篇,不少研究者曾做过一些评述,基本上时常将它视为一种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书写。它的情节以对比、反衬的方式推进,写一个国民党时代的外省老兵,和一个杂货店小女孩殊殊两个阶段的互动故事——殊殊6岁时曾被这个老兵性骚扰,但对当时的殊殊而言,她并不觉得有什么道德羞耻,一切只是孩子的一场纯真的冒险。然而,当年身边的“大人”们,却因为自身的各种或道德或阴暗的动机,觉得殊殊一定深受伤害,因此以私刑暴打、教训了这个老人。长大后的殊殊对此一直心怀歉意,在一次同坐公交车中,她再度认出了当年的老人。“选择”跟踪他回到下层贫民窟般的家,佯称自己是社工人员,在老人的“要求”下,替他洗澡,甚至手淫。而老人也在这样的“安慰”后,重新有了活着的感觉,老人甚至开始上市场买新的衣服,也一并买了一个廉价的发夹,打算送给那个“社工”女孩,每天痴痴地期望她再来看他。因为一次的被关爱与被手淫,他似乎开始有了新的生活希望。
第四,黄丽群《入梦者》写一个长相平庸,也就是现代世俗意义上的年轻丑男的生活困境。但它在艺术上的特色,是将这样的困境,跟新世纪已蔚为主流的网络世界联系在一起。由于长像太“抱歉”,主人公性格非常猥琐,除了在快餐店打工的时间外,总是蜗居在计算机网路的世界里,甚至发展出了一种人格分裂的行为——在网络的世界中,给自己申请了另一个女性的账号,以这个账号写信给自己,同时自己再回信给“她”。每天不断往复这样的行为,甚至在虚拟的世界里,幻想着跟“她”的诸多共同点——共同亲密的分食,甚至缠卷地做爱,不断地自我幻化延续着自己跟“她”在网络世界的交往。然而,现实中的他仍是个丑男,在长期三更半夜使用计算机下,白天的工作质量也受到影响,甚至最后被快餐店的干部开除,只能改去便利商店打工。而他终究也蓦然惊醒,但却不是后悔,而是更加犬儒,觉得一切也没什么,继续过着百无聊赖、毫无希望的生活。这可以视为一种台湾新世纪底层生活的“简单”代表作。非以内涵的深刻而以“简单”和“真”取胜,它诚实且敏锐地碰触到美丑也是一种社会阶级与权力的问题,丑是一种弱势者的困境,在现代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例如细瘦、有型、酷帅)下更形不堪。所以,隔了一层可以虚拟的网络世界,反而能成就一种假性的救赎。这种主题跟契诃夫当年的《吻》有点类似——长相平庸的军官,自觉到外貌的平庸,他因此无法开展合理的两性关系,只能活在幻想的世界里想象一种温存。而当他最终发现一切只是他的幻想,契诃夫选择的是让这个军官生气——仍有力气也仍要对生活表达不满,即使他根本不可能改变他的外貌与现实。然而,黄丽群《入梦者》的写法和意识倾向,最值得注意的恰恰是她赋予这个角色的认份与妥协。
第五,徐誉诚《与情爱无关》从命名来说,既是小说中人物状态的实质,也是一种反讽。因为整篇作品虽然仍从情爱甚至爱欲出发,但是主人公们的关系早已貌合神离,相依与身体交融也无法救赎彼此的孤独和意义。小说主要处理一个跟男朋友蜗居在城市下层,从事基层会计工作的女孩的生活和生命意义的发展困境。它的题材的特色处,乃是将对情爱的需求与匮乏,与现代性中以瘦为美的审美观,及对女性的压迫联系在一起,女主人公因此总是觉得自己很胖、总是想减肥,身体常处在饥饿的边缘。这种肉身恒常得不到饱食的空虚,跟她的情爱的空虚同属一个隐性的感觉结构。这篇作品的进步性及复杂的推进在于,比起胡淑雯及黄丽群的前作,他并没有将新世纪以降的这些新型的现代性下的弱势者的困境,继续以情爱/爱欲来作为解决或中和的手段,而是将女主人公,甚至各主人公的困境,自觉地放至台湾新世纪以降的“民主”运动与选举文化下来理解。换句话说,当连主人公也意识到,她/他的困境“与情爱无关”,而根本就是台湾社会问题的缩影的时候,这篇小说中的情感与意识均达到更高的张力。
因此,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尽管想相信人的生命仍应该要有一些时代价值,但最终仍以空泛的感觉模糊一切(好在整体上仍有一种尖锐的張力)。可以进一步这样理解——台湾的后现代思潮,为主体带来意义追求的解构与看似多元的空间,也难以形成一种中心价值或相信任何精神价值,所以无论是在情爱还是在爱欲上都可以轻易向外发展。但是,后殖民的思潮,所召唤的却是另一种本土、国族集体性与某种群体价值的再形成。然而活在现代都会蜗居的相对弱势的年轻人而言,这种本土与国族的集体性的强化,跟他们实际在生活中所遭受到的贫乏、窄小的困境与感觉,实有明显的落差与断裂——蜗居在城市/都会下层,依附在现代性体制,从事基层、超时且过劳的工商工程服务等工作,是不可能让主体有能力或状态,投入什么国族或本土的视野以获得安顿的。相对来说,这类具有某种理想主义性质的本土国族力量,对城市/都会底层的青年的人生,其影响也难在短期发生作用。徐誉诚充分地将这种都会下层年轻人,间接地被两大“后学”思潮(后现代与后殖民)影响,却跟他们实际的生活与感觉的断裂尖锐地再现出来。有鉴于这种类型的主体,在台湾现代城市/都会里的状态恐怕不在少数,因此这种尖锐书写也就更有其进步意义。
总的来说,胡淑雯《浮血猫》、黄丽群《入梦者》及徐誉诚的《与情爱无关》,在开发台湾资本主义现代性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视野,有一定左翼意义上的进步性。他们在操作这样的题材时,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主人公们的“宅”的倾向。在这里,“宅”并非家的意义,而与窄小的空间、自我内缩与幻化、封闭与孤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生命出口的追寻上,胡、黄都不约而同地,更多地继续选择与相信以个人与封闭式的情感/情欲,作为主人公们的救赎,使得本来可能更具有社会分析性质与效果的主体解放视野,仍然在作家们对左翼思想、美学渊源及典律素养较薄弱的情况下,明显地让作品中的矛盾、尖锐的现实张力相互抵消。反而是在徐誉诚的《与情爱无关》的逻辑中,作者以克己的敏感与直觉,终于意识到——弱者、底层所以难以展开更有意义的情爱/爱欲交流,真正的困境关键恰恰是台湾社会现代性的“单向度”(马库塞语)体制,以及空泛的、维持现况的“民主”“自由”的形式与意识形态。作品因此最终将女主人公推向孤绝与虚无时,生成一种内在的尖锐张力,预告了日后可能发生新的转折或契机。
此外,相对于台湾的70后、80后的作品的整体特质由于尚在起步,目前更难以粗糙定调。但是大致仍有两个主要且重要的面向可供关注:第一,延续了台湾新世纪以来的新乡土写作的基调,创造性地回归本土/乡土的类型。这方面的作品,可以近年在台颇受好评,且成功地被改拍成同名电影的刘梓洁(1980)代表作《父后七日》为代表。第二,延续台湾解严后所擅长处理的小叙事、日常与个人化的视角。但在题材上,扩充出同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因为工作、婚姻,流动、移居至台湾的新移民与新二代的视野。这种题材一方面符合台湾文化圈在长年去大叙事的“自由”意识下的重视与关怀边缘特殊性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能暂时回避与搁置两岸、现代民族国家、历史清理以及转型世代正义的更大矛盾。其书写的重点与特质,目前较多以叙事者/作者的个人家史或回忆来展开叙事,在珍重关爱各式移民迁徙历史偶然性的碎片与细节间,体现新二代与父母辈的生命史与生活化景观。于此企图发展与形塑出新一种台湾主体意识的新内涵,80后的陈又津(1986一)的《准台北人》可为代表作。
在刘梓洁的个案上,我曾在《后现代台湾的“局外人”、乡土温情与“搞不定”——读刘梓洁《父后七日》及其它中,已综述过其作之于文学史和80后的关键特质与特殊性,略引概括如下:
出生于1980年台湾彰化的刘梓洁(EssayLiu),大学/本科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的社教系新闻组,硕士曾念过具有进步视野与意识自觉的台湾“清华大学”的台湾文学研究所。她奠定重要性与代表『生的作品,是2006年荣获自由时报林荣三文学奖散文首奖的《父后七日》。2010年,她还以此作改编后的剧本,获得第四十七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同年,获得第十二届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编剧。目前累积的创作已成书者有:《父后七日》《此时此地》《亲爱的小孩》及《遇见》,创作文类仍以散文、小说为主。
以一种散文化的小说修辞来说,刘梓洁的《父后七日》的叙事特质已不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台湾散文的刻意诗化与浓烈化。例如早年台湾女作家简姨(1961一)的《母者》(获1992年第15届《中国时报》文学奖散文首奖),或90年代马华留台派的代表散文家钟怡雯(1969一)的《垂钓睡眠》(1998年)等,无论就内容及形式来看,都有很明显且自觉的文字艺术化的操作与表现,也因此形成与推进了台湾现代散文语言的精英化特质。然而,一般比较没有受过专业阅读与文学训练的读者,恐怕很难进入那样“艺术化”与高度风格化的文学世界。刘梓洁《父后七日》的成功,恰恰在于它的浅显易懂与高度白话流畅。
此外,《父后七日》在思想上较有深度与特色之处,在于作者对新世纪台湾的存在与“荒谬”的理解与推进,同当年加缪《局外人》一般,能够冷静且清醒地,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平视所看见的现实,并且体现了台湾新世纪以降的80后作家不同于前人的灵光——尽管《父后七日》与加缪的《局外人》都从一个长辈的死亡与奔丧写起,他们的叙事者都很自觉,意识到主体的内在感觉跟外在现实感觉与结构的断裂。如同萨特在评述加缪《局外人》时所言:“荒谬既是一种现实,又是某些人对这种事实的清醒的意识。”荒谬的人“即那些不惮于从根本荒谬的现实中得出必然的结论的人们”。又说:“局外人就是与世界对抗的人。”萨特自然有着“存在”先于本质的信念,因此他理解与认为一个真正“荒谬的人”并非只有虚无的主体。然而,由于早年外省作家在台湾的“离散”处境,无论是郝誉翔的《逆旅》或骆以军的《远方》,重点都须处理20世纪跟随着国民党来台湾的父辈们颠沛流离的生命史——无论是旧时王谢,还是寻常百姓,都被卷入过轰轰烈烈的战争与军旅的大历史,以至于当他们“回不去”,那种青春不在与今昔对比的新现实,总是为作品沾染上伤感与忧郁,也影响了新的一代(如郝誉翔与骆以军)在精神与主体上的开展。而到了本土台湾作家刘梓洁这样的父亲书写中,更多的带有一种奠基于土地,或用时兴的话——“接地气”的素朴能量,因此叙事者与父辈的关系,即使是終究仍须告别,便比较能生产出一种抵抗虚无的情感。
然而,不可忽视的困境是,新世纪以降,在台湾后现代的多元与重视本土性的思潮与历史语境下,刘梓洁的这种写法,一方面虽然接受与尊重回乡奔丧的“仪式”,自觉消解她难免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与更复杂化的理性视野,中和以唯心式的天真、喜感与纯情,但也使得作品中本来也存在的台湾乡土社会的青年外移与回乡“过客”的问题,遭到再一次的搁置——“我”不管如何善意地理解乡土和人民,“我”终究已是“局外人”,“告别”后还是得离开,“我”的归途仍是台北与城市。换句话说,上了城的小知识分子,无论你如何认同台湾的乡土/本土性,最终仍是有家归不得,“台湾主体性”在此只形成了一种“仪式”与表演。也因此,仔细阅读与考察刘梓洁的其他作品后,我并不惊讶地注意到,她创作更大宗的倾向,主要仍跟都会、城市化中的女性命运、都会男女的日常与世俗生活(如《亲爱的小孩》《遇见》),以及都会女子的旅行及自我探索等有关(如《此时此地》)。这当中不乏较严肃的社会化的题材与主题,例如都会女子的生育困扰,借精生子、代理孕母,而自由自在的个人式的爱情,玩味爱与不爱的意义、爱跟性的关系等等,才是刘梓洁感兴趣探索的书写面向。从较高与理想的文学典律观来说,一个作家书写最多的题材与类型,并不代表就最有意义与价值。但这种书写的综合表现,能够让我们进一步地反衬出刘梓洁在《父后七日》中以唯心情感、以虚代实为依归的主体困境,而这也正是台湾目前社会与主体困境的一种重要秘密与征候。
而值得关注的还有陈又津的《准台北人》,这是她的第二本书,第一本书是《少女忽必烈》。她的父辈为早年大陆来台的外省人,后来辗转与来自印尼的母亲结合。父母辈之于台湾既是移民,也是“遗民”,因此已很难用所谓的外省第二代来概括陈又津(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外省第二代的背景中,主要有一方是台湾人),所以晚近改采“新二代”来重新认识与发现他们之于台湾的特殊性。陈又津跟早年的朱天心一样,自觉意识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无坟可上”,无论跟父系的中国大陆或母系印尼华侨的传统与历史均双双断裂。而作为80后的她,又几乎没有早年国民党在台所推动与建构下的“复兴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化中国”的影响。对历史与传统的相对疏离,陈又津的最佳书写选择与策略,反而巧妙地呼应了台湾文化圈偏好接纳与吸收的边缘与特殊性的立场,一种尊重日常寻常细节的非世俗的眼光。一个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惧的少女,拣拾大历史的碎片但不为供奉或引为资源。因此陈又津不会像老派的作家(如白先勇、朱天心、张大春等)焦虑于联系国共冷战与复古传统,影响所及自然也难以深入面对新移民与新二代的社会问题。即使她的首部代表作《少女忽必烈》敏锐地碰触到台北的“都更”议题,她采取的叙事方式仍是大幅度地漫游与观看。整合她后天的知识背景(陈又津是台大戏剧研究所硕士)为小日常延伸一些创造性想象,从而以一种轻软却不完全虚无的张力,精神式地抵抗和反思台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主体困境。尽管在作用于现实的干预力量必然极为薄弱,但在年轻一代的读者接受中颇受好评。
到了《准台北人》,陈又津明显地以白先勇的《台北人》为典律参照。然而更自觉凸显的是不同于早年外省上层的“旧时王谢”的景观与视野。在书名上,“准”台北人,有着一种企图归属但仍不属于的立场,如果说“台北”在早年白先勇的《台北人》的建构下,仍可作为一种外省人在台湾的最后的一丝风华与衰败的纪录与见证(如《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日》《国葬》与《一把青》等等),到了陈又津这里,发掘与安顿的则转向当年随国民党来台更为大多数的无背景的、弱势的、无言的、底层的外省人的景观——既被大历史放逐,亦无感于被大历史放逐的沉默的众生。
《准台北人》因此也可视为一种昆德拉式的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的书写,小说以能相互独立但又合为一体的分节为叙事结构,展现作者从一种“新二代”的立场,还原父母辈作为“新移民”的艰辛生命史与主体意义。诸如“长假”“生病快乐”“董事长”等三节写父亲及病,“三重埔”写台北下层的居住地景,“混血儿”写自小身世与孤独处境,“捡破烂”写底层的父亲的工作,“咸光饼”写父亲的一种庸常生计,“结缘书”写台湾一般的庙里、车站、骑楼等地常供应的免费小读物,其内容大致跟励志、宗教与信仰相关。作者细细碎碎地为这些百姓、拾荒者与极容易被视而不见或丢弃的人事物的意义辩护——“垃圾堆里面,多少还是有些美丽的事物吧”(陈又津《准台北人》),字里行间确实有着观看与体贴底层的生动及善意。但凡此种种将“寻根”“美学化”的环节,却也令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阿城《棋王》中的拾荒老者对“棋王”之于“旧”的阐释:“说什么是旧?我这每天捡烂纸是不是在捡旧?可我回去把它们分门别类,卖了钱,养活自己,不是新?”以旧辩证为新,从儒道的文化与历史意义上,能开发出一定的深度与厚度,但是能否仅仅采用回望个人家史与日常想象?是否保存与己同在的寻常百姓的细碎、温暖与无言的尊严,就能扩充“新移民”与“新二代”更为宽广的解放与救赎意义?我以为,作者或许仍过于珍重与固着她“少女”式的羽毛了。即使本来就并非是社会分析式的创作,《准台北人》实不能说已充分展开“新移民”与“新二代”的形象与感性多样性。因此这种新兴主题之于21世纪的台湾主体性与文学的参与水平,仍有待来日继续观察与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