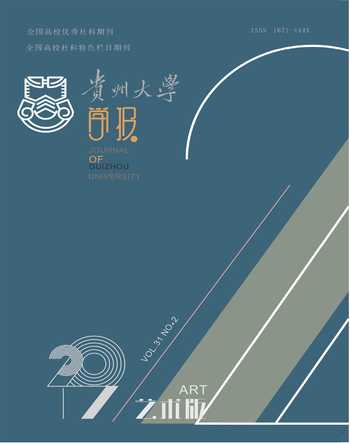一个停滞的段落
赵斌
摘 要:对于强调“地方性”的艺术文本而言,存在一个难以超越的“既定的二元规范”:在影片的意义表达层面,当代艺术家很难再为地方文化提供更多全新的图景;对批评家而言,他们很难为理解这类作品提供全新的知识,或创造全新阐释的可能性。最终,关于此类作品的分析,很可能重新落入一种矛盾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本文以影片《塔洛》中主人公返回乡村的段落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停滞”在影片叙事中的作用和意义,进而把这种停滞推向更广义的领域,思考如何理解“边界”及其机制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和解释上述现代性焦虑提供了自反性的角度。
关键词:塔洛;现代性;停滞;悬置;二元结构;去功能化;图像学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7)02-0010-07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7.02.002
在民族国家有关现代性的意义框架之中,电影叙事实践,特别是那些关联所谓“地方性”生活方式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遇到一种由现代性的结构局限(二元结构的意义框架)所帶来的超越的冲动和焦虑。
这一框架由意义和审美的二重性构成。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主要关注前者。
万玛才旦的影片《塔洛》所代表的,正是这样一种拥有现代性焦虑的典型作品。这种焦虑不仅仅植根于导演创作的思想当中,也体现在批评话语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之中:对于艺术家的创作而言,存在一个难以超越的“既定的二元规范”,即,在影片的意义表达层面,当代艺术家很难再为藏地文化提供更多全新的图景;对批评家而言,他们很难为理解这些电影提供全新的知识,或者创造全新阐释的可能性。最终,关于影片的分析,很可能重新落入一种矛盾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
一方面,在美学层面,影片提供了质感鲜明的藏族生活景观,这一景观的呈现,借助类似纪录的影像产生了强烈的现象学特质,为陌生的藏族生活场域提供了不同于主流叙事的诸多陌生感。当然,在一个信息和图像传播异常活跃的时代,在一个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旅游已经不再奢侈的时代,这种陌生感也是极为有限的。
另一方面,在意义层面,《塔洛》讲述的无非是“底层男人落难”的故事,当然,落难并不单纯是事件性的,它关联了更多的身份焦虑或者身份失落,同时,塔洛的落难也是由于欲望被点燃而引发。因此,落难也可以看作陈旧的“欲望之原罪”主题的结果。而这一悲剧性的结果,恰恰被放置进了藏区,放置进了山上/山下,旷野/城镇,男人/女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符号秩序当中。
我们知道,在电影的两次进城构成的线性结构中,塔洛回乡的素材在中部跳跃出来。与其说叙事表现为由身份证引发的动作线索,倒不如说更像一种呈现旷野/城镇双重地标的空间展示;同样地,两处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段落,主人公毫无表情的朗诵如同诵经,冗长的话语重复,提供了一种对政治意义的抗拒——这已经是一种明显的、现代艺术的展示策略。但是,在美学层面,无论导演如何呈现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故事,影片的叙事从总体结构上都难以超越“背离乡土”和“城市的堕落”这一悲剧性的意义指向。这一意义指向,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史中,至少已经存在了七十年。
因此,我们不能高估这部影片在意义呈现层面的探索性价值。从意义阐释的角度来讲,这部电影也很难再为此类电影批评提供多少新鲜的养分——严肃的学术期刊中有关此片的各类陈词滥调,毫无悬念地讴歌着有关故乡、情怀、身份等主题词。
当然,从更久远的历史来看,大部分艺术文本都很难直接转化为某种思想认知的文本。毕竟在文本的历史当中,那些超越性的杰作极其稀缺,况且它们依然依赖批评家对文本的阐释和介入。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电影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电影本身的意义呈现,而在于通过批评的介入,它有可能成为一个经典案例,为我们思考当下创作和理论阐释的局限提供一把破局的钥匙。
下文对于《塔洛》的分析,将远离美学和惯常的意义阐释,而是把电影文本导向一种广义的政治学,因而,有可能到把类似涉及地方性文化及其视觉景观的再现问题,提高到一个更加现代的立场和思考层次上。也就是说,《塔洛》这类特征明显的作者电影,其政治功能已经与传统古典叙事完全不同。古典叙事依靠隐喻功能,在文本世界中构造一个小小的世界,这是一种服务于寓言的叙事体制,但《塔洛》虽然仍部分地属于这种体制(例如,影片还像古典电影一样,以一个事件的发生作为契机),但是它更多地属于一种新颖的陌生样态,这种样态的特征就在于,在叙事的美学方面呈现陌生感,具体说,与奉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古典叙事艺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而具有现代电影的鲜明特质;同时,在意义呈现方面,此类影片仍然在既定的“现代性焦虑”框架中徘徊。
面对这种全新的样态,我们基本的态度应该是,不再把“突破这种现代性焦虑”、“为现代性的生存方式提供某种电影化的超越”视为艺术作品深度的判断标准,转而把影片“是否为理论阐释提供文本链接的可能”当成艺术作品价值的标准。换句话说,此类影片有可能以恰当的标本或案例的形式,构成关于艺术的政治学知识的内在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在下文中,我只能重点分析影片中一个冗长的、停滞的段落。
一、一个停滞的段落
这个段落指的是塔洛离开城镇返回旷野后的素材。
很显然,按照创作的规律,这个段落承上启下,为塔洛后面的返城行动提供了外在和内在动机。就外在动机而言,我们看到的是羊群的主人对塔洛充满暴力的身份规训,但在内在动机方面,塔洛为何决定接受诱惑返回城镇(从导演安排的冗长的段落来看,显然不想把回城的原因简单归结为爱情),影片的呈现就暧昧和模糊许多。
因此,这是一个停滞的、空的段落。
按照我们的观影惯性,我们可以自行添加丰富的解释。其中最容易想到的便是欲望——对女性以及由女性所暗示的外面的世界的欲望,引诱他最终走向无望的深渊。但是这种解释不能是概念化的,我们不知道在塔塔短暂的心理现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就作者电影的规范而言,这种难以言说的暧昧具有合法性。但作为阅读或批评,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尝试把它说清楚。说的过程其实是一种按图索骥的过程,由此才能把关于塔洛这一人物个体的分析带向终点。
影片中的这个段落前后均连接着城镇空间,因此它首先是一个嵌入动作进程中的时间性的存在,进而也是荒野/城镇两重结构中的空间性存在。因此,我们不妨把这种段落的区隔理解为本雅明或福柯意义上的文化权力的边界。对该段落以及前后两段叙事中有关权力及权力机制设定的各种边界的思考,是理解本片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影片为我们提供了众多的关于权力的视觉呈现(例如开端所展示的派出所的段落长镜头)。概括来说,这些权力和权力机制的表现,既涵盖了民族国家的普遍的政治权力,包括五十年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力,也指涉了更加久远的藏地宗教权力,以及日常生活中由放牧劳作发展出的政治权力。
权力的重要作用就是设定众多的边界,因此考察边界问题就成为我们反思影片所提供的权力机制图谱的一个可行方案。与二元对立的叙事传统天然契合,边界总是表现为对立,例如,在宗教生活领域中广泛存在的创造与救赎的对立。
严肃的批评,必须首先以考古学的方式回溯到产生这一对立的历史源头,分析的结论可能是:影片以不自觉的方式呈现了这种对立机制,从而也提供了模糊甚至摧毁这些对立的可能,最终使这一边界的对立失效。
如果分析的结论的确如此,这种分析,将对目前关于现代性意义的二元对立式的呈现方式进行彻底反思,这将凸显此类电影以及对此类电影进行分析和阐释的知识所拥有的价值。
在此,追溯便成了电影批评工作一个重要的方案。理解这部电影,诠释这部电影的政治学价值,首先在于理解藏族文化(乃至更广义的宗教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创造与拯救的对立。之所以说是普遍存在,是因为它并不以具体的宗教而相互区隔,而是在各类宗教文化(乃至更广义的文化文本)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共性。例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曾对伊斯兰和基督教最初文本中上帝的两种工作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的路线同样适用于他对卡夫卡小说《审判》和《城堡》中的主人公K的分析意大利哲学家乔吉利奥·阿甘本将其追溯至拉丁文“诬陷者”(Kaluminator)和古罗马的地理边界坐标纵线kador,用以讨论古罗马法律术语的历史演变,人格,即person,被以同样的方式追溯至古代贵族家庭存放的先人面具。,同样适用于对“人格”这一概念的历史分析。
对于藏地文化所涉及到的边界问题,如果我们仅仅从一种预判出文化差异或对立的角度来理解,而不把这种文化回溯至古代源头,藏地文化只能沦为主流现代文化的增补。之所以我们会陷入关于藏/汉文化的二元对立结构,正是源于这种追溯的缺失。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明白,藏族与汉族的文化差异,旷野与乡镇的差异,再或者故乡与他乡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一个共时性的空间差异,还是一种历时性的时间差异——即,是一种现代与其源头的差异。因此,回到古代源头的回朔性思考不可或缺,对阿甘本而言,原因在于“开启现代性之门的钥匙隐藏在远古和史前”,所以我们有必要“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且根据某种必要性来引证它”;福柯的观点并无二致,“对过去的历史研究不过是对当下理论探究投下的影子”,在这一点上,本雅明说得更加明了,“过去只有在其历史的确定时刻才是可以理解的”参见阿甘本《何谓(为)同时代》中译文第7节,艺术中国,http://art·china·cn/exclusive/2014-10/31/content_7336320·htm。
因此,在对待土地(乡土)的问题上,与第五代电影人的乡土情结不同,万玛才旦的乡土没有一丝一毫理想化的影子;就电影批评而言,在一种类似新古典主义的批评不厌其烦地呈现现代性焦虑、含蓄讴歌传统理想生活范式的时刻,我们必须重视《塔洛》中停滞的段落,它为我们思考现代性这一概念提供了源头和转着点。
在万玛才旦的访谈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导演的创作是以精神世界的反思为起点的[1]。在这里,离开家乡、闯入城市的作者身份与离开藏区、闯入城镇的塔洛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因此我们对于塔洛形象的分析,应该让位于对边界问题的分析,也就是反思“肉体的、欲望的人”与“人之上的、超人的事物(如,宗教生活方式)”之间的边界问题。因此,闯入城镇的短暂时刻,只是一种征兆,是人对最后的边界的攻击。进城时折叠的山路,针对的是山上与山下、荒野与城镇、传统与现代分隔开来的那些界限。自由的跨越边界,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宗教或至高权力(这些在影片中以藏区背景、护身符等形象呈现),塔洛的对立者只是公安干警和雇主等。因此,关键的不是人与神性(神圣)之间的冲突,而是在神性的问题上(以山脉等某种视觉化景观为表征),人与“人的谎言”(女人的谎言、塔洛自我的欺骗)之间的残酷斗争。因此,重要的不是对于某种现代性之罪的表达,而是对塔洛这一传统守望者的细致描摹。在通向现代性的大门之外守候的塔洛,正是由于持续地坚持对现代性的审慎的关注(以特殊的方式背诵毛主席语录等),才能在某种政治规训之外生活,而没有落入由现代性政治所规训的好人或坏人之中,他既不是所谓重如泰山的人,也不是轻于鸿毛的人。
因此,停滞的段落之前所有的素材,均致力于呈现某种悖论或者欺骗。这种欺骗就在于现代性守护者的存在。派出所干警、理发馆的女人、照相馆的老板,连同那些极具诱惑力的全球化景观(照相馆的背板),所有这一切的存在,其目的就是诱使塔洛进行自我誣陷,从而进入现代生活的大门,而这一大门毫无疑问地通向由KTV所暗示的“世俗的迷失和堕落”。塔洛跨越或推翻的,就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神性之间建立起来的界线和区割。
边界的设定是为了区分事物,但并不能阻断事物之间的隐秘联系,并且这一联系会以各种伪装的形式继续发挥作用(不妨联想一下拉康对征兆或捕鼠器的分析):土地或原始生殖创造的意向,在塔洛所生活的藏区消失了,但作为其象征的护身符和嗷嗷待哺的小羊仔,从未缺席。
与其他宗教类型一样,藏传佛教及更广义的宗教文化形态,都以经文的形式呈现神性权威(或先知)。在影片的开始段落,对塔洛而言,毛主席语录在相同的意义上呈现了另外一种相同的权威。宗教的和政治的两种权威,开启了神学和广义政治学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机制,不管这两种工作的起源是什么,创造和拯救都是确立此种意识形态的两种基本要素。同时,神性的行为作为人类反思自身问题的场所,也反映了人类行为的两种基本要素。更重要的不是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别,而是它们之间的联系。
创造与拯救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从阿奎那到阿甘本的这一命题,在《塔洛》当中以另外一种质问方式存在:“乡土”和“对现代性的拯救”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问题的答案并不像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创造在先,拯救在后。在阿甘本看来,“拯救不是对堕落的造物的一种拯救,而是使创造变得更易理解,它赋予创造以意义”。在此,我们可以说,正是有了现代性的(世俗的)堕落,我们才能够指认出一个模糊却又清晰的、作为创造者的神圣乡土。拯救,作为对修复的一种迫切要求而出现,而在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上,拯救先于任何恶行而出现。在影片中,拯救的文本正是通过塔洛惊人的记忆力得以延续,没有什么比这一细节更好地表达了拯救先于创造的事实。
二、作为物象或静物的山脉
乡土与现代性的边界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又如何清除或推翻边界所设立的对立呢?仅仅考古式地追溯对立机制,并逆转对立双方的位置是不够的;诗歌与哲学的对立,创作与评论的对立,影片中旷野与城镇的对立,这些在今天已经取代了创造与拯救的对立,经由宗教传统的世俗化进程,这些领域逐渐失去了对原始关系的记忆。这一从传统至今的历史进程,已经被一种明确的空间关系(旷野与城镇,传统物象与现代景观)所压抑。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现在越发明显地表现出了一种特别适用于精神分析的特征。
今天,在现代性的思想框架里(这一框架很显然同时影响着影片的创作和对影片的阐释),这两种被割裂的神圣行为,迫切需要找回它们之间失去的历史延续性和统一性,它们通过“成为对方”而自我确立,例如,只有通过城市才能发现乡土,只有通过批评才能理解创作,但这其实仍然是分裂的:批评家模仿艺术家已经放弃的创造性工作,试图取代艺术家的地位,而失去创造性的艺术家则奋不顾身地致力于拯救工作,虽然他什么也拯救不了,因此,创造和拯救都不再触及它们之间本应存在的、细若游丝的联系。
在两次进城的段落之间,导演安插的是上文提及的返乡段落。这个段落的意义,从情节逻辑的角度来说,无非是塔洛回到乡村,在短暂的犹豫彷徨之后卖掉羊群,为再次进城做准备。很显然,从这个角度说,这个段落非常孱弱,因为人物的欲望是一种含混的心理驱动力,在电影中很难直接对其进行情节化的表现。在短暂的犹豫里,塔洛经历了什么,内心发生了什么,无法清晰地呈现。因此,这一段也是脱离整体线性叙事的段落,它停滞不前,似乎失去了动力。
但我们明白,当同类问题层出不穷时,我们便需要自觉寻找停滞的原因,并试图理解它。停滞意味着“不运作”或者“运作的失效”——这既是叙事体制意义上的,也是在更普遍的人和社会行为意义上的。
就叙事体制而言,此段形成了影片叙述中的失控点。在心理感知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看做“眩晕”,在意义表达上,则构成了典型的“迷图”,或者说,这个段落制造了阿甘本意义上的“悬置”或“停歇”。实际上,这些略带差异的概念本身,都是对古典意义上“叙事与意义”运作的某种颠覆。“迷图”迷图,Mimesis,是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1994年)中的关键概念,常被错译为模拟或模仿,但其真正内涵指的是在不同的文化或形式系统内出现的相互模仿,这种模仿创造出了错误、含混和矛盾状态。是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在论及东方视觉艺术时的一个比喻性概念,用来指涉艺术图案中那些形式与意义无法协调的点或区域,隐藏在区域背后的是意义表达和意义阐释的失效。从迷图中,霍米巴巴看到的西方殖民文化与新艺术(东方的或现代主义的)相遇时所构成的冲突,它使得艺术史(形式系统)的差异与断裂得以表面化。有意思的是,德勒兹、朗西埃、齐泽克三位思想巨匠均在电影中找到了相同的征兆,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希区柯克的《迷魂记》(Vertigo)。三人对此经典作品中的“眩晕段落”品头论足,从各自的角度阐释了其中蕴含“形式错误”:德勒兹把这一错误理解为“动作—影像”终结并转向“时间—影像”的历史节点;朗西埃则认为这一错误暗示了古典电影机器试图调解自身与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之一种)之间矛盾的无奈尝试;齐泽克则从精神分析角度把“眩晕”理解为意识形态的崩溃点,这一崩溃点暗指了作为象征秩序的古典主义法则的实效,“眩晕”作為真实界的内核刺破了形式的束缚,以扭曲的、错误的和不可理解的方式诡异现身。
迷图(或眩晕)也好,悬置也罢,无非是艺术形式中细微的混乱或无伤大雅的纰漏。论及这些概念的思想家,显然没有将问题局限于艺术家个人智慧或技巧的范畴,而是将其升格为历史和哲学话题。迷图或悬置,背后的真义需要我们反思:今天谈论一部不甚完满的影片,我们往往能描述现象,指出问题,却极少寻找根源,这造成了评论中某种普遍性的误导和暗示——艺术家似乎只要使其技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而事实是,如果叙事问题根源于艺术史(形式系统)的断裂和转向,那么,任何试图解决问题或弥合裂隙的尝试注定无力回天。多地性呈现无法超越现代性意义表达的窠臼、经典类型难以本土化、商业叙事与深刻的意义逻辑无法协调、消费/审美/艺术政治相互矛盾——诸如此类反复发作的顽疾,无一不是艺术史断裂和转向问题的具体症候。
作为一种具体症候,我们仍然需要探寻其背后的机理。这种叙事体制上的问题,仍然需要回到人类实践的考古学中予以理解。
我们首先应该观察到的是该段落里那些有关山脉的黑白影像。
正确理解该段落的黑白影像,有必要参照当代图像学对安塞尔·伊士顿·亚当斯黑白风景(静物)摄影作品的哲学阐释。亚当斯的风景作品,被视为某种终结和延续之作,即在古典主义绘画历史结束后,它以大画幅摄影的方式,以山脉等自然景观为对象,试图在艺术领域恢复和拯救那些在世俗世界中逐渐消失的宗教般神圣的客体。危险和冷峻的山脉,对于迈进现代城市的当代人而言,自然显得威严甚至危险。
亚当斯的摄影,赋予物以神圣感,强迫观看者通过静态的凝视,剥离情感,把看的欲望提升到“物”的高度。这便是拉康在分析凝视时,对“升华”概念的解释。我们可以说,神圣就是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某种属性。对亚当斯摄影的大量图像学研究,探讨了实在界的形象(如静物)被使用的各种方式。山脉比土地更好了触及了生殖和抚育问题,因为在宗教或文化的传统中,山脉不再具有种植、放牧、提供洞穴等实际功能。宗教的意识形态策略是,将山脉镶进画框或诗歌,使其与特定的功能区分开来,从而让它处于悬置状态。悬置的形象因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功能——展示的功能,它展现了自身的善(完整)。由此,山脉的其他使用方式可以借“去功用化(inoperality)”这一概念予以精确阐释。
自本雅明赋予电影等机械复制时代的大众艺术品以一种展示的属性之时,展示开始作为一种有价的视觉范式,统领了这个时代的视觉文化。在广告或色情作品中,商品或身体的拟像只具有展示性而无实际用途,它们正是在这一点上施展了“有距离的凝视”才拥有的诱惑力。纯粹的山脉形象进入画框,其意义的生产遵循同样的逻辑——它展现了生殖的善;神圣的山脉是显性的视觉形象,它只具有展示性功能,而远离了实际的属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山的词源学流变同样能观察到意义的演进过程。因此,神圣是与无用性联系在一起的。
对山脉这一悬置的、无用事物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探讨画框或诗歌中的山脉的多种使用方式。《塔洛》中对山的再现,并不意味着用独特的方式使用了山脉形象,而是再次表明山脉的存在超出了任何可能的用途(至少绝不服务于情节逻辑,也不太可能服务于塔洛的心理逻辑),由此,也超出了旷野/城镇原有的二元对立框架(这一框架在结构主义那里被确立,此二元对立甚至可以被看成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土地/战争”结构的转换或移置),并因此带来了消解这一异化的对立框架的可能性。
影片中山脉的神圣或其他与神圣相关的含义,不过是将非功用性独立出来,移置进了一个特殊领域(即宗教的神圣领域),由此开启了一种对山脉等物象的全新使用方式。当然,在千百年的主流艺术史中,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永恒的俗套。因此,神性并不是某种源头性的东西,并不是在古典时代终结、现代来临时陨落的东西;并不是说随着历史演进才出现了世俗化,世俗化本在神性的源头处就已经封存于人类实践和意识之中,宗教意识形态在某个时刻对其进行了干预,通过悬置和区分,把功能性的人類活动独立出来,移置到了自身(宗教文明)的领域之中。列维·斯特劳斯的“过剩的能指”概念以同样的方式对该问题进行了解释,认为宗教神圣的本质实为“空洞”,并因此可以加载各种象征性内容,即“零度象征价值”的能指(链)可以以多变的方式对应人类活动和客体,只不过在宗教文化中,宗教通过仪式性的过程使其悬置,把它们独立出来,并将其再符码化,这一分析的逻辑实际上也为拉康的精神分析研究移置现象所利用。
从这部影片中,我们应该更多地发现去功用化的积极意义。即,山脉等无用的物象创造了停滞,这一停滞是一种敞开,它停止了原有的行为或对立模式,使其失去效力,因而开启了新的可能性,但这种新的可能性不是对旧的对立(城镇、世俗化)的完全否定,而是对旧的对立的一种展示。这里要做的是使目的性的行为实践(例如塔洛再次闯入城镇)变得无效,从而开启一种对山脉(神圣或乡土等意素)的新的使用方式,这不是对原有使用方式(这一方式或许能追溯到陶渊明,在现代至少能追溯到沈从文)的禁止,而是始终立足于旧的使用方式并使它暴露出来。
因此,银幕上的山脉不是被移置进一个更崇高的实在领域;相反,它以无用的、停滞的姿态,把自己从曾使自身与自身分裂的二元对立中解放了出来;以迷人的视觉方式,通向自身真理的存在。在这里,二元对立充当了逻各斯思维的面具,创造了依附于物象(山脉)的各种边界及其机制。有意悬置并暴露这些边界,意味着破除这些边界的尝试,意味着凿开了进入新的可能性的裂隙。
影片中这一停滞的段落,除了山脉的物象展示,还存在一些被忽略的细节,无论这些细节在导演的创作初衷里是否重要,在批评阐释中都居于重要的位置。这些看似不重要的细节包括了饮酒、放牧、吃肉等。对于饮酒、放牧(或怠工、拒绝放牧)的动作而言,我们猜想,导演只想寥寥几笔再现日常生活,或者以饮食和饮酒暗示欲望的复苏。当然,我们不必要拘泥于导演的初衷,我们要记住的是,艺术家常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再现某种现实,而他自身,连同他的观众一起,早就无法从当下的现实追溯到历史的源头。饮酒、怠工或拒绝放牧,悬置了牧民的劳作,使得主人公从工作的理性目标及作为自身身份(放羊的)的界定中解放了出来(就像影片的整个第二段落从整体性的情节逻辑中崩离出来一样)。因此,“吃,不是为了果腹;穿,不是为了蔽体或防寒;醒来,不是为了工作;走路,不是为了去某个地方,说话,不是为了交流信息;交换物品,不是为了买卖”参见阿甘本《公牛的饥饿》第7节,豆瓣网,https://www·douban·com/note/153317829/。塔洛此刻的无用的动作,模糊了作为人的理性边界,完成了对过往价值和权力的消解。塔洛依附于自己的藏地,又与这个生存空间保持距离(或者说,城镇故事开启了塔洛背叛的起点);我们也一样,既依附于这个被称为现代的时代、又以充满焦虑的姿态与现代性保持着距离,这都是如出一辙的悬置与消解的关系——这绝非简单的形式逻辑的移置和推演。
借用悬置、停滞和去功用性的概念,并不是要逆转或抛弃现存的权力关系,而是使其体制自我暴露,进而寻找对其进行反思的策略。在这一点上,概念的革命性使用,已经在政治哲学领域开花结果,迈克尔·哈特在论及当代工人“反物质生产”(如罢工)时,提倡在其与“拒绝劳动”的马克思传统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系:反物质劳动并不是倡导工人回到新形式的劳动中去,而是要对现有劳动形式进行彻底拒绝。因此,与“拒绝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是对未被(资本家)占有的劳动的重新指认,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揭示。马里欧·特隆蒂以同样的逻辑阐释了反物质生产,“停止工作是对既定的具体劳动的拒绝,是工作过程的暂时停滞,作为一种持续的威胁,其内容来源于价值创造的过程。”[2]
三、停滞之后
拒绝劳动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反抗了情节模式,倡导一种停滞的叙事段落(例如现代电影随处可见的反动作段落)之后带来了什么?
或者更广义地说,停滞和边界消解之后,带来了什么?
这些在历史的现在时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显然没有答案。如上文提及的,宗教把悬置和非功用性剥离出来,放到一个独立的神圣领域,使其静止化,对对象的多元使用方式因此转化成了一种永恒的僵死的东西,从而阻碍了开放性和可能性。那么,新的可能性到底是什么?
这一问题在不同的领域被置换成不同的质问:
对电影叙事而言,我们的问题是,艺术家如何提供解决现代性焦虑的叙事智慧;对于批评家来说,则是如何在《塔洛》这类无法超越现代性意义框架的文本中发现有关“前现代与现代之关系”的新的阐释话语。面对回不去的“美好的前现代”,面对无法抽离的“堕落的现代”,艺术家的创造性日渐枯竭,对于表达全新的超越性意义一无所知,甚至失去了兴趣;批评家的拯救工作才刚刚开始,但对于如何理解现代性同样一无所知。这在当代构成了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批评最核心、最致命的话题,没有之一。
但是,追溯现代性的起源,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进入了由现代性概念本身所编织的二元对立的虚假逻辑之中,忘记了现代与过去之间真实的演进逻辑。我们不知道塔洛在城市启蒙之后会走向哪里,如同我们不知道在现代电影叙事借“停滞”消解了动作叙事之后会走向何方。
一定程度上,我们对事物的无知,恰恰源于我们对已知事物的认知方式,甚至可以说,我们对事物的无知,界定了我們的认知范围;我们对有关世俗/现代性(政治上的、文化上的、艺术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等)的无知(例如对它与神圣/前现代之间存在的关系缺乏理解),界定了迄今为止对“世俗/现代性”的有限的认识;这种可怜的有限性之外存在的广袤领域,正是导致我们现代性焦虑的全部来源。
人类在实践中建立了知识的前提、结构和谱系,并依此进行知识的再生产,那么,划定无知领域(例如在文化研究领域明确提出现代性焦虑,或在艺术创作中承认超越现代性意义框架的不可能性)的边界,恰是构成知识的前提,在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当下时刻,无知领域并不包含任何而对我们而言有意义的东西,但我们要在“已知/未知”这对关系中对知识进行检验与反思,使无知一路伴随并回应着我们的知识,如影随形。对现代电影的创作、现代艺术的批评,乃至现代人对现代生活的自省而言,情况皆是如此。
参考文献:
[1] 万玛才旦,刘伽茵或许现在的我就是将来的他——与《塔洛》导演万玛才旦的访谈[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05)
[2] Mario Tronti The Strategy of Refusal[EB/OL] http://libcom·org/library/strategy-refusal-mario-tronti
——来处已然消失 归途无所觑见
——以万玛才旦的《塔洛》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