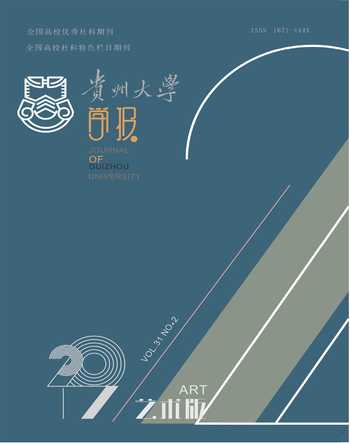非虚构电影与新有声电影
曾耀农
摘 要:卡罗尔作为西方后现代电影理论家,以其新颖独特的思想对非虚构电影、朋克电影、结构主义电影、新有声电影等进行了独特的研究,1990年以来在中国得到了一定范围的传播,对中国近期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有一定的影响,但也产生了一些误读与嬗变。
关键词:卡罗尔;电影理论;传播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7)02-0021-04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7.02.004
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艺术哲学与影视美学教授,著有《电影理论的哲学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令人困惑的电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和《恐惧的哲学》(洛特律治,1990)等著作,并发表了大量影视理论方面的论文,尤其在对后现代电影研究领域卓有成就。
在西方电影研究领域,盛行着一种“大理论”。“大理论”是对电影的宏观分析和总体把握,由路易·阿尔都塞、雅克·拉康和罗兰·巴尔特等欧陆风云人物的时髦思想所建构。卡罗尔对这种“大理论”颇有微词:“正如经典的本质主义理论那样,大理论对于真正的理论化是一种障碍,因为它被表现成一种统一的或总体化的系统。在它的旗帜下,电影理论家致力于把每一种电影现象都归于他或她至少还熟悉的正统观念所认定的法则和类型中去。理论化变成了针对电影问题的某种更大的统一理论的惯用法,不管怎么说,这种程式毫不令人惊奇地滥造出同样的答案或者极为相似的答案。简言之,最终的结果是导致理论的贫困。”[1]1针对“大理论”存在的缺陷,卡罗尔认为需要抵制将电影理论加以总体化的诱惑,从而跟随着碎片式的理论化的引导率意而行。“在电影理论热衷于探索,将电影现象加以普遍化或做出总体解释时,或致力于在电影理论中进行分隔、追踪以及对各种机械论、设计、模式、规则进行描述时,我们都应该支持。”[1]59
相对于“大而无当”的“大理论”,卡罗尔更欣赏“碎片式”的电影理论:“这种从碎片式的理论化立场而来的思考是实践性的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因为我凭直觉感到,就我们的所知而言尚不足以开始制订一种统一的理论,或者说,甚至不足以构成可能导致建构一种统一理论的问题。因而在这种状况持续存在期间,大家最好还是集中精力去研讨更易于把握的、小范围的理论化问题。”[1]83为了研究“碎片式”的电影理论,卡罗尔主张采用阐释学的方法:“电影理论遵循着规则与范式,而电影阐释则顺其自然,处理偏常的例证,研究背离规范、超越规范或重新构想规范的东西。”[3]61在研究西方的后现代电影时,卡罗尔主要使用阐释学的方法。他不是从理论框架出发,而是从电影文本出发,将西方的后现代电影划分为几种类型,如非虚构电影、解构主义电影、新有声电影、朋克电影、新心理剧电影以及新象征主义电影等。“在我们论及的后现代电影的范围内,我们只能从总体上,在借鉴其他艺术门类与之相类似的活动的基础上,评说电影行当里已被视为后现代的那些行为。”[2]88對后现代电影,卡罗尔的评说是阐释式的,并带有批判色彩。
一、研究非虚构电影
在电影产生之初,比如卢米埃尔兄弟所拍摄的《火车进站》、《婴儿午餐》等影片,即是非虚构电影。后来,现实主义影视编导总是想方设法地将幻象与真实区别开来,而后现代主义影视编导总是否认幻象与真实的区别。
针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卡罗尔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攻击非虚构电影并不是根据纪录片局部的怀疑论。”他认为,那种关于非虚构电影中的客观性的争论,表明了对纪录片的怀疑与否定,而怀疑纪录片便是怀疑历史:“大概在后现代主义者拼凑的精神中,他过分强调一系列引证向我们再确保,一般的怀疑主义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论。”[1]420
为了阐述自己的思想,卡罗尔吸收了另一位电影研究专家温斯顿的观点。卡罗尔认为,温斯顿提出非虚构电影客观性的局部保护,都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包围与攻击,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我想他期望我们认识促使全球的后现代主义者怀疑主义的逻辑力量,局部地保卫纪录片的客观性,而认识历史和语境的观点的方法,缓和与客观的理性标准的对立。”[1]421卡罗尔认为,温斯顿所提出的观点,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可是,温斯顿提出的关于纪录片客观性的局部怀疑主义用各种防守方法,来对抗基于全球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怀疑主义的观点,是毫无用途的。“后现代主义者摆事实,下结论,讲道理。保守是显而易见的。当后现代主义者引起要求逻辑损害控制的争论的时候,像我自己一样,认识上的保守性才被意识到。”[1]422卡罗尔认为后现代电影理论是一种颇为保守的观点,逐渐丧失了现代主义的先锋性。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自己的见解,卡罗尔例举了一些非虚构影片来进行分析,如《细蓝线》、《语言联合》、《我和罗杰》、《谢尔曼的行军》以及更早的一些电影,如《带着电影摄影机的男人》、《动物世界》、《赫德》、《夏日记》等。卡罗尔认为这些影片经常以极端的不同的方式,展示某种我们已经在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熟悉的,具有反映性和作者主观性的主题。他认为非虚构电影也能包含后现代的因素:“我主张历史故事,并由此引申到非虚构电影(或者至少是那些故事性的非虚构电影),即不需要按照它们的叙事(或“比喻的”)结构,并以之为必要的虚构,也不需要把它们当作是对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强加或歪曲。”[1]410一个历史学家可以把叙述的一系列事件作为一个悲剧,而另一种叙述却可以把同样系列的事件作为一个喜剧,而无论是喜剧性事件还是悲剧性事件,都是虚构的,都是比喻性写作。它们仅仅属于有序的叙述,而不是现实存在物。“如果在非虚构电影与虚构电影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差异,那么,非虚构电影那些对客观或是真实的要求,并不比虚构电影那些要求会更好。”[1]400
二、研究朋克电影
朋克电影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孕育于新浪潮音乐,两者对世界见解相近,虽然都产生了轰动效应,但都缺乏道德敏感和感情因素。卡罗尔认为,朋克电影的很多作品都以廉价的好莱坞电影为样本,它们感兴趣的是行动而非思考,从而卸掉了借娱乐之名进行反省的沉重负担。
作为后现代主义电影的一个分支,朋克电影中的女主角大都具有阳刚之气,男主角则面无表情,沉默冷酷。此外,光顾这个世界的常客还有梦游症病人、歇斯底里患者和邪恶的人物。朋克电影将超然物外和狂妄不恭结合在一起,银幕上到处游荡着自私自利的人物。他们贪得无厌、不顾廉耻地渲泄欲望,并不因其粗俗坦率造成的恶劣影响而愧疚。它们常用廉价的超8毫米胶片拍成。米切尔1978年执导了《红色意大利》和《绑票》;贝思和斯科特夫妇1979年拍摄了《黑箱》,1980年执导了《活板门》;约翰斯通于1980年摄制了《不眠的夜晚》;维维安迪克1980年执导了《她已备好枪》和《格里拉会谈》。
在介绍了朋克电影文本及特征之后,卡罗尔对此类后现代电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卡罗尔认为,朋克影片对人的卑劣品质和罪恶的青少年形象都予以了赞扬,而不是像传统电影那样对作恶者严词谴责。拙劣的鉴赏力、野蛮无知的口味和令人憎恶的逻辑都被进一步夸大,被强化成为朋克自身的象征。它们在勾勒阴谋策反资产阶级文化的情节时,改头换面地套用好莱坞电影特有的暴力行为。在风格上,朋克电影的制片家毫不掩饰的套用低级杂志中违反逻辑的主题谈话,还生吞活剥地抄袭了粗糙甚至粗俗的结构。
朋克电影的对话有表现性而无内省性,其目的旨在为结构和世界上某种实际存在的情感样式,即城市朋克们异化了的精神气质,寻找客观的桥梁和媒介。卡罗尔说:“朋克电影制片人常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他把已消亡的文化残余修补粘合,是表现一度繁荣的文明碎片的、建立在废墟上的艺术。”[3]72朋克电影是对其他流派的再加工,其模仿的尺度既像结构主义但又有些距离,把麻醉的主题提高到了文体的高度,并对电视节目也产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研究解构主义电影
卡罗尔认为,解构主义电影来源于结构主义电影。结构主义电影,其实就是形式主义电影。“提起结构电影的成就,不禁令人想到这场运动的三部杰作:斯诺的《波长》(1966),弗兰姆顿的《佐思定理》(1970)和埃尔尼·格尔的《从容的速度》(1970)。斯诺的影片是在形式上接近结构电影的范例,弗兰姆顿则给电影带来了全身心的创新色彩,格尔机智巧妙地对两者兼有亲近的表示,在制作过程中,看上去犹如栩栩如生的抽象派绘画。”[2]90卡罗尔认为,真正体现了结构电影全部实质的是霍利斯·弗兰姆顿的《怀念往昔》(1971),这部影片包括一些独到的逼真的描绘,每幅画面都开始于一个慢慢曝光的燃烧着的金属热片,每个镜头一直持续到各自的图像变成灰烬。
作为后现代主义影片的一种样式,解构主义电影比结构主义电影更为极端。“对他们来说,解构倒更意味着解析、粉碎、搅乱占支配地位的电影制作习惯。也就是说,对以往的习惯而言,这种拆解通常具有破坏性的意义。”[2]89卡罗尔认为,可以归属到解构旗帜下的还有重新发现电影、纯视觉电影、新有声电影等等。总之,解构,像是一个口号,标志着1970、1980年代各种先锋艺术的突出倾向。就是今天,解构还是这类影片的一种主要的内驱力,一种主要的活力源头。“解构主义回答了内容的要求,夷平了占统治地位的电影潮流。其方式是拆解占主导地位的电影,而拆解占主导地位的电影所凭借的,就是为观众提供认清它技巧的必要知识。”[2]90
为了更好地分析解构主义电影,卡罗尔对其主要类型——重新发现电影进行仔细研究。卡罗尔认为,重新发现电影是由一些旧电影、照片、电视节目以及碎片构成的,构成的方式是将它们重新拍摄、重新剪辑、重新组织。这种制作方式令评论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抽象派拼贴画。一旦影像从原来的文本关系中被拨离出来,并被挪动,放在一个新的通常是分离性的背景中,这个影像就能把它最初未曾被人注意、神奇的特点显露出来。1958年,由布鲁斯·康纳制作的影片《一部电影》,便是将原先所拍电影碎片加以东拼西凑,使正在接近启示性的狂热的当代文化——波普艺术的幻想形象化和具体化。卡罗尔认为,重新发现电影具有一种可接近度,这是其他先锋电影探索所缺乏的。运用重新发现电影的解构主义艺术家寻找现成的艺术品充当他的艺术材料,但有人可能会重新设计叙述或风格的样式,这种叙述或风格是他希望拆解的。在重新设计的过程中,通过夸大、重复、分离、反义以及浓缩等策略,他可以实现他的解构目的。“对有抱负的解构艺术家来说,重新发现电影的重要性建立在这种事实的基础上:这种风格为选定解构对象和文本交合游戏提供了现成的操作方式。”[2]95
四、研究新有声电影
20世纪60—7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阶段。学生游行、反对越战、反对种族歧视与性别压迫等都出现于这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到处弥漫着不满情绪,后现代主义电影中的一个支流——新有声电影也诞生于这一特殊时期。
卡罗尔认为,新有声电影被语言统辖着,语言比影像更为突出。“新有声电影实践者们对通过语言去表达政治、思想、文化意义之类内容,也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3]70新有声电影与结构主义电影的重要差别体现在它们对叙述的不同态度。结构主义电影是反叙述的,或者说对叙述漫不经心。结构主义电影更关心的是电影的拍摄技艺和视觉效果。而在新有声电影那里,叙述却粉墨登场,再度唱了主角。在新有声电影那里,叙述作为一种拥有社会意义的表现形式,是一个重现的课题。新有声电影的典范作品,例如安东尼·麦考尔和安德鲁·廷德尔的《争论》(1978),彼德·沃伦和劳拉·马尔维的《斯芬克斯之谜》(1977),麦考尔和廷德尔等合作完成的《弗洛伊德与少女杜拉》(1968)等等都倾向于信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谈论独特的政治观念。大多数新有声电影为的就是教育正从事着“有意义实践”的观众,维护政治的支配作用,这种支配作用不仅表现于经济上,而且也反映在两性关系中。
卡罗尔经过文本解读后认为,让·戈达尔的作品对新有声电影有着重要的影响,新有声电影从戈达尔那里获得了风格上的策略。戈达尔在《我所了解的她的二三事》(1966)中将现实与幻想、纪实与虚构杂糅在一起,在《激情》中将摄影棚拍摄与影片真实风格结合在一起,与戈达尔一样,新有声电影也对这种杂烩式的手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把电影分割成碎片,这些碎片标志了不同的风格,代表着不同的媒介(照片、影片、剧场、电视等等)。这样的大杂烩意味着一种新的观念已经诞生:观众所面对的表现形式,其结构的偶然性要远远大于必然性。在戈达尔的作品中,新有声电影为电影找到了一种新的模式,这种电影既充满理智又散漫零碎,既是对抗的,又是政治的,还是商业的。
卡罗尔经过比较,认为萨莉·波特的《恐怖人物》是新有声电影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恐怖人物》对侦探风格与歌剧情节剧全部进行了解构,并且试图对掠夺进行一番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卡罗尔对新有声电影的前景表示忧虑:“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新有声电影已不能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同时,对艺术理论和政治理论——拉康、阿萨舍尔及女权主义的混合物,进行简单的置换,既不能使新有声电影为那些未经专门训练的观众所理解、接受,也没办法吸引他们。”[3]71新有声电影如果失去了观众,失去了市场,便会失去生存的根基。
五、在中国的传播
卡罗尔的后现代主义电影理论,在美国乃至西方影视界均有突出的地位。他的电影理论著作也较早被译成中文,在中国报刊发表和出版社出版。陈山与张洪曾将卡罗尔的论文《后现代电影:结构与解构》译成中文,在沈阳的《艺术广角》1991年第2期上发表,臧永清与张洪也联合将卡罗尔的论文《后现代电影流派两种》译成中文,在长春的《电影文学》1991年第8期上发表。由卡罗尔与大卫·鲍德韦尔联合主编的《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专著,被麦永雄、柏敬泽等译成中文,由中国权威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0年10月出版发行,使中国学者较全面地了解和分析他的后现代电影理论。黎萌认为:哲学家诺埃尔·卡罗尔所提出的电影悬念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卡罗尔从一般意义上的叙事性联系的刻画,过渡到对叙事性悬念的刻画,满足了观众欣赏叙事作品中的“期待视野”。这一理论在今天的人工智能叙事中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陈晓云则说:诺埃尔·卡罗尔认为大理论在学术上已经失去效用,已经死亡。他提出“碎片式的理论化”是改变这种现代西方电影理论困境的可行途径,即把大理论的某些主要问题砸碎,集中精力去研讨一些更易于把握的、小范围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站在某个立场上来建构一种统一的或者是易于理解的电影理论。
卡罗尔探讨的核心问题涉及到电影理论的前景。在他介绍自己所提倡的电影理论框架之前,卡罗尔首先考察了他所归纳的电影研究的五个主要障碍:电影理论与电影阐释相互混淆;将电影理论视为不可分割的铁板一块的概念;对政治正确性的强调;当代电影理论家中反对真实的话语的偏见;与所谓的形式主义者相对立的诉诸感情的悲情故事(ad bominem jeremiads)。卡罗尔还维护对电影理论作辩证论说的必要性,并试图通过用一种简略的方式,让那些提倡电影理论的认识论态度的人和那些提供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的人之间的争论重演,从而阐明他心目中的那种辩证冲突。中国电影怎样才能在全球化的浪尖上站稳脚跟?怎样既有民族性又具全球化?怎样才能在强势的西方电影话语面前另辟蹊径,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当下电影业界都很关心的话题。卡罗尔的后现代电影理论,对中国电影理论家是富有启迪的,尤其是他对西方后现代电影进行分类,更为中国电影创作界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1] 〔美〕大卫·鲍德韦尔,诺埃尔·卡罗尔.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M].麦永雄,柏敬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 〔美〕诺埃尔·卡罗尔.后现代电影:结构与解构[J].陈山,张洪,译.艺术广角,1991(02).
[3] 〔美〕诺埃尔·卡羅尔.后现代电影流派两种[J].臧永清,张洪,译.电影文学,199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