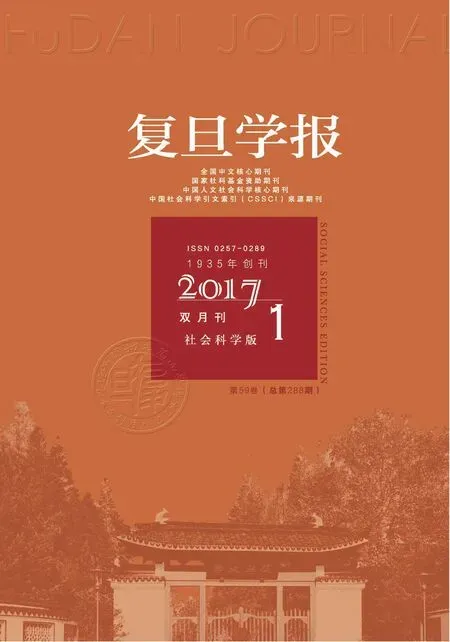大赋铺陈用字考论
易闻晓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阳 550025)
YI Wen-xi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大赋铺陈用字考论
易闻晓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阳 550025)
大赋以铺陈为本,落实于造语用字。赋体文学研究必当基于文字的语用考察,要在四言散语一顺,一于名物铺陈,一于描写铺陈。名物铺陈广致奇异,用字繁难,同旁类聚,排比堆砌。描写铺陈或避重异形,字类繁复,尤在双字联绵本于音义的形变、本于声韵的形义之变,以及转音以变形义,肆加偏旁,繁滋复赘。四言散语一顺铺陈对于大赋用字具有句式规制作用,双字为“词”及四字为句多以单字类合,表现于描写铺陈双字乃至四字并列的声韵和形义关联,不是口语“双音词”的书写记录,而大半出于赋家临文的组字创造,反映字类虚实转化的语用功能。
大赋铺陈 四言一顺 名物描写 单字组合 化实为虚
东汉班固《两都赋序》托言“赋者古诗之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刻本,1977年,第21页。,站在《诗》学的经义立场,将汉赋纳入《诗》学流变的系统,要求赋体创作发挥《诗》的讽喻功用,反映了赋论的“《诗》学本位”,深刻影响着后世赋论。*易闻晓:《汉赋“凭虚”论》,《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其说远溯《诗》义“赋比兴”之“赋”,并“不歌而诵”、赋诗言志*《汉书·艺文志》:“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55~1756页。,卒指屈原、荀子“贤人失志之赋……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第1756、1756页。。荀子《赋篇》归于说理述志,其后复有《佹诗》一章,章炳麟谓“诗与赋未离也”*章炳麟:《国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6页。,清赵维烈《历代赋钞》不取*赵维烈:《历代赋钞·凡例》,康熙立敬堂刻本。。西汉小赋如梁孝王门客公孙诡《文鹿赋》、羊胜《屏风赋》等仿效荀赋,四言短制类《诗》,篇少无足轻重。而在荀子前,屈原《离骚》“以篇幅之长、造语之衍、名物之多、情感之厚,比兴之广,绝异《诗》之四言短制、分章合乐、比兴点缀、怨而不怒,从此创立一体”*参拙文《汉赋“凭虚”论》,《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开启宋玉,弃情赋物,以赋命篇,汉赋承之,卒成一代文章之盛。清赵维烈《历代赋钞》断自宋玉,*赵维烈:《历代赋钞·凡例》,康熙立敬堂刻本。晚清姚华《论文后编》亦谓“宋玉之所为”者,乃成“赋之文”而“悉授于汉,一谓之赋”*姚华:《弗堂类稿》论著甲,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29~30页。。班固亦指屈原、荀卿之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第1756、1756页。,继以东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以迄左思三都之作,并西汉枚乘《七发》,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曹魏何晏《景福殿赋》,前汉王褒《洞箫赋》,后汉傅毅《舞赋》、马融《长笛赋》、曹魏嵇康《琴赋》,西晋潘岳《笙赋》之属,乃在大题苞括*《西京杂记》卷二假托司马相如答盛览云:“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程毅中点校:《燕丹子·西京杂记》合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巨制铺陈、凭虚假设、名物纷呈,描写繁复,多用散语,四言一顺,于题则畋猎、郊祀、京都、宫殿、江海、音乐,是为大赋之实,亦《文选》范囿所存。盖自西汉司马迁所称相如“虚辞滥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73页。,扬雄所谓“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班固:《汉书·扬雄传》,第3575页。,经班固《两都赋序》所论,迄东晋谢灵运《山居赋》自序,“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谢灵运:《山居赋序》,顾绍伯:《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9页。,乃至晚近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所论,“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或写都会、城郭、游射、郊祀之状……奥博详实”而未“动人哀乐*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3页。,大赋为制及所范围,了然无疑,不待今人屈指计议。在此需要说明的只是宋玉赋开启汉大赋,若《高唐赋》,几乎汉大赋构篇,造语、用字等都已预为定型,因而从源头上视为汉大赋的系列,可谓顺理成章。
一、 繁复易形的铺陈需要
赋主铺陈,乃是赋之为体的本质要义,在大赋创作的语用层面,铺陈落实于用字,这不惟语言文字学基于材料整合的系统结构和静态分析,而且尤在创作学的语用考量,因而从创作学出发抵达语言文字的根本,在此不再存在文学与语言的分野,创作学的语用视角消解了现代学科的隔阂,至少大赋的文学研究有了新的路向和开广的维度,藉以进入大赋铺陈的博阔空间。历来对于“赋”的训释皆显示大赋铺陈的体制本质,《说文·貝部》谓“赋,敛也,从貝,武声”*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31页。,段玉裁注谓“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2页。,《诗·大雅·烝民》“明命使赋”毛传谓“赋,布也”*孔颖达《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世界书局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97年,第568页。,并在敷布之义。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谓“物以赋显”*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86、126页。,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训赋为“铺”为“富”,指“赋者,用居光大,亦不可以小言”*王芑孙:《读赋卮言》,《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清程廷祚《骚赋论》所谓“赋家之用,自朝廷郊庙以及山川草木,靡不摅写”*程廷祚:《骚赋论》上,《金陵丛书》本。,对于大赋铺陈之旨,悉所深契。大赋以大题巨制“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假设陈词,预设无尽广阔的铺陈空间,例如《上林赋》,凡上林地理、山水、物类、羽猎及其仪仗、过程、场景以为铺敷,爰使览者竦动,飘飘凌云*《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奏《大人》之颂”,而“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第3002页)。。这就需要博资典籍,广搜名物,谲怪恢奇,并以夸诞形容,缛藻复沓,要在四言散语一顺,一以名物铺陈,一以描写铺陈。
大赋铺陈用字,首在名物铺陈,广致奇异,纷呈叠至,望之繁难。按《说文·口部》“名”训“自命”,从“口”从“夕”会意,以“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说文解字》,第31、282、205页。,推及事物*参易闻晓:《类推思维的文学推衍》,《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字专名,即有“名字”,名副其实,则字以代物。大赋名物铺写,即在用字,多于四言一顺铺排,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于是玄猨素雌,蜼玃飞蠝,蛭蜩蠼蝚,獑胡豰蛫,栖息乎其间”,四言一顺,罗列众物,而以“栖息乎其间”结归一句,固谓散语为然。《后汉书·班固传》“猨狖失木”李贤注引郭璞注《山海经》曰:“猨似猴而大,臂长,便捷,色黑。”*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50页。李善注谓雄玄雌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86、126页。。蜼读wèi 。《说文·虫部》:“蜼,如母猴,卬鼻长尾。从虫,隹声。”*《说文解字》,第31、282、205页。玃读jué,《说文·犬部》谓“玃,母猴也”*《说文解字》,第31、282、205页。。蠝读lěi,《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本赋作“”,张揖索隐仍作“蠝”,谓飞鼠,郭璞谓鼯鼠,飞且生,一名飞生。*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32页。蛭音zhi,《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本赋司马贞索隐援顾氏引《字林》谓“蛭,蜩,二兽名”。顾氏又引《神异经》云:“西方深山有兽,毛色如猴,能缘高木,其名曰蜩。”*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32页。蠼,同“玃”,避重两用,亦以四字同旁从“虫”,王充《论衡·遭虎篇》亦见*王充《论衡·遭虎篇》:“行山林中,麋鹿、野猪、牛象、熊罴、豺狼、蜼蠼,皆复杀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0页。。蝚同“猱”。獑音chán,《玉篇·犬部》:“獑,獑猢……似猨。”*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犬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0页。《集韵·衔韵》谓“类猿而白,腰以前黑”*丁度等编,赵振铎校:《集韵校本·衔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23页。。“豰”,李善注呼谷切,引郭璞曰:“穀,似鼬而大,腰以后黄,一名黄腰,食猕猴。”*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6页。蛫读guǐ,《类篇·虫部》谓“蛫,猿类”*司马光:《类篇》,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6页。。
凡此灵类,以四字之式连续铺排,或二字一物者玄猨、素雌、飞蠝、獑胡,或以一字一物者蜼、玃、蛭、蜩、蠼、蝚、豰、蛫,凡十二之众。从创作用字的角度看,一字一物则一字一名,若“蛭、蜩、蠼、蝚”,名副其实,四字构为一句,名物的铺陈就是字类的排比;二字一物也是两字组合相加,若“玄猨、素雌”,甚至四字三物者“蜼、玃、飞蠝”,在字面为四,以与“蛭蜩蠼蝚”对举一顺,并列不碍。明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猱》:“猱,《尔雅》云:‘猱蝯善援,貜父善顾。’注云:‘猱蝯便攀援。貜父,貑貜也,似猕猴而大,色苍黒,能攫持人,好顾盼。’《说文》云:‘夒,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陆玑云:‘猱,猕猴也。楚人谓之沐猴。老者为玃,长臂者为猨,猨之白腰者为獑胡。獑胡猨骏捷于猕猴,其鸣噭噭而悲。’”*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卷四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由此可知赋家对于猨类种属的博识,其间雄雌、少长、黑白及臂之长短,与善援、善顾、能持,先民造字以别属类,乃从牡牝、形色,性状,或视犬类,或虫,分别造字,一字一物,迥异于现代造词如“雄猿、母猿、黑猿、白猿、长臂猿”的简单类加,所以即猨之类,名字为众,赋家类聚,以资铺陈,乃在识字之多。
自汉及晋,大赋所见名物奇异而字形繁难者,动植土石并有,飞走畜虫甚众。如鳱鴠(hàndàn,鸟,枚乘《七发》、《淮南子》亦见)、蚑蟜(qíjiǎo,虫、毒虫,《七发》)、(kūn,大鸡,鸡三尺为,《七发》)(jiāojīng,水鸟,《七发》)、麕(jūn,同“麇”,獐子,出《诗经·召南》,《七发》)、麖(jīng,大鹿,牛尾,一角,《七发》)、(táo tú,《山海经·海外北经》谓“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山海经》,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45页。,《子虚赋》)、(jùnyí,锦鸡,《子虚赋》)、褭(yǎoniǎo,古良马,《上林赋》)、犛(máo,牦牛,出《国语·楚语上》、扬雄《羽猎赋》)、甝虪(hánshù,白虎、黑虎,左思《吴都赋》)、豜豵(jiānzōng,三岁猪、一岁猪,出《诗·豳风·七月》、左思《吴都赋》)、(tiáoyóng,《山海经·东山经》谓“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见则其邑大旱”*《山海经》:“独山末涂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其中多鳙,其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见则其邑大旱。”第113页。,郭璞《江赋》)。凡此等等,其物既异,字则生僻,望之不识,心乃畏难,但在赋家铺陈,正以搜罗异物,广致难僻,乃见取资之广,博识多方。
大赋四字一顺的名物铺陈多见同旁字的类聚,如《子虚赋》“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鹓鶵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虫蜒豺犴”。这些同旁字以同一类属并列,如木从“木”、兽从“犬”、兽长脊从“豸”、虫从“虫”,本以物类相属。及张衡《西京赋》“鸟则鹔鸹鸨,鹅鸿鹍”,则两句八字同旁,并从“鸟”右,仅“”在下,若“鹅”作“”,则益加整饬。字形整饬乃是大赋四言名物铺陈基于物类相属,并有意利用汉字同旁相从造成的视觉美感,在于绵密繁复,厚实拙重,是为大赋所尚,迥异于六朝小赋及唐代律赋灵便绰约的“诗化”表现,*《“赋亡”:铺陈的丧失》。固以名物奇异,用字遂多繁难。至于左思《吴都赋》“,鹤鸧,鹳鸥鹢鸬,泛滥乎其上”,则益类聚繁难,以见博物之广、识字之众。
不仅名物铺陈,而且形容描写益为彰显大赋用字的特点。或在一篇之内避重异形,大赋形容描写既多,用字不免重复,因而选用异体以避重形,乃是赋家创作的用字考量,反显字类之多。例如《高唐赋》“水澹澹而盘纡兮”,“澹”《说文》训*许慎:《说文解字》,第231页。、“澹澹”李善注并谓“水摇”*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65、266、252页。。同篇又有“徙靡澹淡”,李善注谓“澹淡,水波小文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65、266、252页。,风摇水生文,义与“澹澹”无异,同篇盖取避重。厥后张衡《东京赋》有“渌水澹澹”。“澹淡”则《七发》、《上林赋》、班固《西都赋》、张衡《南都赋》、潘岳《西征赋》递相祖述,而“澹澹”罕用,乃见赋家用字之癖。《上林赋》用之,连并“汎淫泛滥,随风澹淡”,则“汎”、“泛”亦以避重取异,尤以一句重字,不可见于才短。《说文》“泛,浮也,从水,乏声”,又“汎,浮也,从水,凡声”*许慎:《说文解字》,第233、230页。,特两取其声,于义无别。段玉裁注《说文》“泛,浮也”,引《诗·邶风·柏舟》“汎彼柏舟,以汎其流”,谓“上‘汎’谓‘汎汎’,浮貌也,下‘汎’当作‘泛’,浮也”,徐灏笺谓“此亦强为分别,《广韵》‘汎’、‘泛’同”*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年徐氏刻民国三年补刻本,第436页。,虽《广韵》不尽古义,然单表动作,叠拟形容,如“澹”谓摇,“澹澹”拟摇貌,转用而已,然“汎”、“泛”避重,反见字多学博。又宋玉《风赋》“被丽披离”,善注并谓“四散之貌”,盖联绵仍音变形避重,以为凑句,然亦两形炫博。复举《七发》“温淳甘膬,脭醲肥厚”与同段“甘脆肥膿”,“膬”与“脆”、“醲”与“膿”,并同义异体。《玉篇·肉部》“膬,同‘脆’”*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肉部》,第36页。。《释名·释形体》:“膿,醲也,汁醲厚也。”*刘淇著,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2页。避重用字,亦见博识。
大赋形容描写用字易形,更主要在于联绵字因声易形,一本于音义的形变,即音义不变而字形有异,乃是异体的书写,不属孳乳;二本于声韵的形义之变,即仍已有联绵字之音,更改偏旁以表新义;三则转音以变形义,以与既有联绵词声母相同或相近发生转韵,或首字转,或次字转,或二字并转。后二者并属孳乳。本于音义的形变如“粲爛”出《风赋》,《上林赋》祖之,《东京赋》、《思玄赋》并作“燦爛”,扬雄《甘泉赋》倒转作“爛粲”,“粲”从“米”,义为精米,引申为鲜明貌,加“火”配“爛”,同旁相从,整饬美视。本于声韵的形义之变,新形义本之于旧而有所转移。兹举首字A音起头者如“晻藹”(阴貌,《离骚》)、“闇藹”(木荫水波藹然,《高唐赋》)、“薆”(香馥,《上林赋》)、“暗藹”(众盛貌,《甘泉赋》)、“菴藹”(物盛貌,《蜀都赋》),并有盛、郁义,随所不同。首字B音起头者如“觱沸”(泉出貌,《诗·大雅·瞻卬》、《诗·小雅·采菽》),转形音作“滭弗”,仍义(《上林赋》)、咇茀(状香氣盛发,《上林赋》)。案“觱”、“滭”、“咇”,《广韵》并帮母质韵,“咇”又并母质韵,当从前者,泉涌香散,并存“出”义。首字C音起头则如“潺湲”(水流貌,屈原《九歌·湘君》)、“婵媛”(枝相连貌,张衡《南都赋》),流水连绵不断,本此义转;又“婵娟”(女曼妙貌,《西京赋》)、“蝉蜎”(修竹猗靡随风貎,成公绥《啸赋》;烟艳飞腾貌,木华《海赋》),并其修美飘柔,随物赋形。其所易形,多有本从。或如“咇”则前此未见,疑出作者自创,从“口”从“必”以转形发义。
转音以变形义乃是联绵字孳乳的重要途径,清郑珍谓“屈宋滥觞,喜作体物语,汉晋……文士模山范水,以意鱼贯,肆加偏旁,或且文无定形,形无定义,繁滋复赘,眴惑心目,纷难解矣”*郑珍、郑知同:《说文新附考》,王锳、袁本良点校:《郑珍集·小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1~382页。。但赋家“肆加偏旁”,乃是由于描写形容的语用需要,本诸既有联绵字更改偏旁以表新义,并非漫无方的。例如“流离”(《诗·邶风·旄丘》)、“流”训水行相连不绝,“离”亦训连并,“流离”并来母联绵相从,状水行不绝随下无方,复拟人众离散。转作“藰莅”(《上林赋》“猗狔从风,藰莅芔歙”),次字“离”支韵平声转“莅”至韵去声。“藰”草名,“莅”义临,“藰莅”拟风临草木,本“流离”水不绝漂散义,盖风、水不断,所至四散。又转“浏漂”(马融《长笛赋》“正浏漂以风洌”)李善注谓“浏漂,清涼貎”*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65、266、252页。,盖亦从风得义。“流离”又转“流丽”,次字“丽”转霁韵平声。“流丽”状流畅华丽。“丽”义偶物骈俪*《荀子·乐论》“鼓大丽”王先谦《集解》引《方言》郭璞注谓“偶物为丽”。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55页。,“累而成文”*《荀子·正名》:“累而成文,名之丽也。”《荀子集解》,第423页。,丽藻连属,故谓“流丽”。“林离”晚出,声韵近“流离”,状水盛四散下洒不绝。木聚连接为林,与“离”义连并双声联绵,转作“憭栗”(宋玉《九辩》),空旷连延,寂寞生惧。又转作“飂戾”拟风疾(张衡《思玄赋》)、“嶚剌”(张衡《南都赋》)拟连山高峻*此段考释,参易闻晓:《辞赋联绵字语用考述》,《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等等。相类者如“澎湃”(“湃”滂母怪韵,《上林赋》),转“滂濞”(“濞”至韵,《上林赋》)、“澎濞”(王褒《洞箫赋》)、“滂沛”(“沛”泰韵,扬雄《甘泉赋》),并旁纽转者如“淜滂”(“淜”并母旁纽,宋玉《风赋》)、“滂渤”(“渤”并母旁纽,《七发》)、“漰渤”、“漰沛”等。凡此都以双字联绵双声(包括旁纽)转韵易形,爰使字类剧增,用于形容描写。
二、 散语四言的用字规制
大赋造语,要在四言一顺散语铺陈,是《高唐赋》首创,它继承了《离骚》托物言情的名物铺陈,但舍弃了《离骚》句中虚字连接字词以成复杂结构和句尾虚字以重感叹的长句结构,而以四言散语一顺叙物。叙名物如“秋兰茞蕙,江离载菁,青荃射干,揭车苞并”,只以四字为读,直接呈现名物,无需句法结构,形成绵密复沓的铺陈效果;形容描写如“蜲蜲蜿蜿、煌煌荧荧、悠悠忽忽、縰縰莘莘、徙靡澹淡、岩岖参差、窐寥窈冥”,叠用联绵,至汉大赋而为常。尽管大赋如扬雄《甘泉赋》犹援《骚》语叙物,汉代骚体也间用散体大赋句式,但四言一顺铺陈固为散体大赋造语之常态。“四言一顺铺陈”显示赋体铺陈本质并落实于用字的特征,不仅在于名物铺陈,更在于描写铺陈繁复堆砌,且对于大赋用字具有句式规制作用。例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描写水势云:
这可以看作大赋散语四言一顺铺陈的典型段落,自始至“肆乎永归”,接云“然后”,显见前此一气贯注,略无暂歇,形容叠至,丽藻纷披,源源不竭,衍衍无穷,但当代刊本莫不中间断句,致使气势顿跌,最是无识。
应当讨论四字散语的构句功能。所谓散体赋,不惟夹杂叙述如《高唐赋》开篇“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的简略交代,以及对话如《子虚赋》、《上林赋》子虚、乌有、亡是公的相与辩难,而且更在四字为句的一顺铺陈,并无作意属对及严谨押韵,甚且不押。这种散语四字之式并不要求双音2+2的结构均等,而有参差错落,所以不能形成严格的属对,相对于六朝赋大多使用骈语及唐代律赋益以平仄格律,大赋之称“散体”,正在四字散语的绝多使用。上引《上林赋》四言一顺铺陈中,大多是所谓“联绵词”的2+2组合,如“汹涌”“澎湃”构为四言,只是由于四言句式的规制作用才成一“句”,实际上是使两个形容二字的组合以“句”的形式直接呈现,根本无需“主谓宾”的语法结构。但如“沸乎暴怒”,“沸乎”却不成“词”的形态,虚字“乎”只是凑足二音以足四言*何丹:《诗经——四言题起源探论》,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4~28页。,显见“用字”的构句作用,其“字本位”的考量乃是赋家创作的语用需要。而“横流逆折”,在“词性”和双音二字结构上则与“偪侧泌节”的联绵形容并不一致,但两个四言却前后一顺,赋家对此了不关心,正以“横流逆折”充当描写,与“偪侧泌节”形容同功,在此四言连用规制字面的对举。进而言之,抑且“转腾”为动作字,“潎洌”为形容字,并列成句,显用“转腾”形容,赋家的创制并不计较所谓词性的转化,只用“转腾”二字组合二音以与“潎洌”二字并列。搜寻适当字以就四言,才是相如“含笔腐毫”*《文心雕龙·神思》:“人之禀才,迟速易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94页。的艰辛所在。
从“字本位”的语用角度看,散语一顺铺陈的四字造语,实际上就是以字凑句,表现为联绵字或并列二字的临文组合、联绵,与并列字的排比以及四字单义并列。西晋郭璞《江赋》描写江水一句足为例证:
全句描写铺陈都是以字凑句。首先考察貌若联绵者。按照“联绵词”的现代定义,乃是字无定形,依声用字,并且二字联绵为一,拆分无义,这假定了联绵双音结构的先在及其稳定性,因为“联绵词”以音定字,所以字形只是表音的符号,推至本初,逻辑上必然是先有口头语音的联绵,文字是其符号的“反映”,这或许受到西方“语音中心说”的影响。然汉字初创,一音一字,字必有义,即使完全借用已有文字代替其音,选字亦与其字本义绝多相关。至于大赋描写铺陈用字,可以明确说很少属于“口头语音”的反映,而是因其描写表意选字易形,更重要的则是赋家铺陈的临文创造。较为普遍的情形,是就既有文字搜取声韵相关者并列组合,由于二字声韵的关联,所以视若联绵,并非先有口语而但为记音而已。这就要求具有音义相近文字的相对数量,才堪用资选择,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厥初生民以音指物,语音与物存在某中约定的关联,然以初音缅邈,唯以语感可推。例如“明”母字“冥”、“蒙”、“梦”、“昧”、“邈”、“漠”、“迷”、“茫”、“漭”、“漫”、“緜”、“”、“淼”、“眇”、“渺”、“藐”、“緬”、“湎”、“瀰”等,都有幽暗蒙昧渺茫义,故以同“明”声者如“溟”,幽深以命海,音义若契,于是临文命意,就其字类撮合以足二音,形成所谓“标准音步”即“韵律词”*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页。,因为“发一字未足舒怀,至于二音,殆成句矣”*成伯璵:《毛诗指说·文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77页。,是以足二成“词”,但归二字组合。即于“明”母字类,则随所组合“冥茫”、“渺茫”、“迷茫”、“迷蒙”、“蒙昧”,《文选》赋所见则“冥邈”(陆机《叹逝赋》)、“茗邈”(张协《七命》)、“溟漭”(《江赋》)、“冥蒙”(左思《吴都赋》)、“緜藐”(《上林赋》)、“緜邈”(陆机《文赋》、左思《吴都赋》)、“眇”(《江赋》)、“緬邈”(潘岳《寡妇赋》)、“渺湎”(《江赋》)、“渺瀰”(《海赋》)、“淼漫”(《吴都赋》)、“淼茫”(《江赋》)之类,用为描写铺陈。《江赋》此句四言二字连用具有声韵关联者如次:
澩灂,叠韵联绵。“澩”,《广韵》胡觉切,匣母觉韵入声,李善胡角反,《说文》谓“夏有水、冬无水曰澩”*许慎:《说文解字》,第232、232、230、234页。,《广韵·巧韵》训“动水声”*周祖谟校:《广韵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01页。,《吴都赋》“澩”、王褒《洞箫赋》“捎”并用。“”同“澩”,《说文》谓“澩……从水,學省声……,澩或不省”*许慎:《说文解字》,第232、232、230、234页。。“灂”,《广韵》士角切,崇母觉韵入声,《说文》训“小水声”*许慎:《说文解字》,第232、232、230、234页。,多“瀺灂”连用,《上林赋》有之,李善注谓“小水声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52、227页。。“澩灂”,《广韵·巧韵》释“澩”单举此例,疑本赋始并。


泧漷,双声联绵。“泧”,《广韵》呼括切,晓母末韵入声,又《广韵》许月切,晓母月韵入声,又王伐切,李善注呼活反。《广韵》训“水大”*周祖谟校:《广韵校本》,第91、91、203、480页。。《广雅·水部》“泧泧,流也”王念孙疏证:“《说文》:‘,碍流也。’引《卫风·硕人》篇‘施罟’,今本作‘施罟濊濊’,并字异而义同。”*王念孙:《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4页。“漷”,《广韵》虎伯切,《集韵》忽郭切,晓母铎韵入声。《说文》谓“漷,水,在鲁”*许慎:《说文解字》,第232、232、230、234页。。《集韵》训“漷”单举本赋例,训“水势相激貌”*丁度等编,赵振铎校:《集韵校本》,第1504页。,始并。

漩澴,双声叠韵联绵。“漩”,《集韵》旬宣切,邪母仙韵平声。“澴”,《广韵》户关切,匣母删韵平声,本水名,源出河南信阳县南。又《集韵》荧绢切,匣母霰韵去声,《玉篇·水部》训“聚流”*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第91、91、88、91页。。
滎瀯,叠韵联绵。“滎”,《广韵》户扄切,匣母青韵平声,《集韵》翾营切,清韵,《说文》训“绝小水”*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32、227页。。“瀯”,《集韵》维倾切,清韵,单举本赋例,训“水回貌”*丁度等编,赵振铎校:《集韵校本》,第510、1561、1116、740页。。“滎瀯”本赋始并。
溭淢,叠韵联绵。“溭”,《广韵》士力切,崇母职韵入声。淢,《广韵》雨逼切,云母职韵入声,《说文》训“疾流”*许慎:《说文解字》,第229、226页。,张衡《南都赋》“淢汨”连用。《广韵》释“淢”、《集韵》释“溭”单举本赋例,训“波势”*周祖谟校:《广韵校本》,第91、91、203、480页。、“水貌”*丁度等编,赵振铎校:《集韵校本》,第510、1561、1116、740页。,始并。
濜溳,叠韵联绵。“濜”,《广韵》慈忍切,从母轸韵上声,《集韵》谓“濜,水名,在襄阳”*丁度等编,赵振铎校:《集韵校本》,第510、1561、1116、740页。。溳,《广韵》于敏切,云母轸韵上声,《说文》谓水名,“出南阳蔡阳,东入夏水”*许慎:《说文解字》,第232、232、230、234页。。《玉篇》、《集韵》释“濜”单举本赋例,训“水势”*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第91、91、88、91页。、“水波貌”*丁度等编,赵振铎校:《集韵校本》,第510、1561、1116、740页。,始并。
凡上所见《江赋》本句四言中二字联绵者,除“濆瀑”或出“澎湃”、“澎濞”之转而有其本除外,其他10例悉以从“水”字类声韵相关者临文选字组合,而字、韵诸书所举,惟取本赋,或阙,盖既前无本从,后以繁难不克祖述,显属作者组字自创,一惟用字而已。剩余“漰湱”、“潰濩”、“潏湟”、“淴泱”、“瀹”五组以无声韵关联,遍检《文选》赋一无所本,必以近义临文组字。总之可推“漰、湱、澩、灂、、、、、潰、濩、泧、漷、潏、湟、淴、泱、、、(《玉篇·水部》同“”)、瀹、漩、澴、滎、瀯、渨、、濆、瀑、溭、淢、濜、溳”诸字,当为作者类辑同旁,然后根据声韵关联组字,声韵关联之字不足,则将就近义组字。由于散语一顺的四言规制,只以四字凑句,无论“”、“漩澴滎瀯”、“渨濆瀑”、“溭淢濜溳”联绵两两并列,还是“漰湱澩灂”、“潰濩泧漷”联绵、并列组合,在赋家创制的“字本位”语用层面,实际上都如“潏湟淴泱”一字一义,四字组合为句,以为排比,充任描写铺陈,是为大赋铺陈描写用字的突出特征。
三、 化实为虚的形容描写
大赋铺陈之于名物、描写并多,名物为实,资于博识,描写为虚,要在用字。郑珍所谓“自屈宋滥觞,喜作体物语……繁滋复赘,眴惑心目”,也指描写形容,尤其四言一顺的散语铺陈,排比堆砌,繁复炫耀,必以字类之多、取资之众,除去祖述取用,往往临文自创。不妨说大赋描写形容词语丰富,但在实际创制中,“词语”固非口语书面记录,“词汇”的积累不是“来源于生活”,而是取自典籍,这在汉字是特殊的。它不惟像表音拼写文字那样只是作为“符号的符号”忠实于口语语音的记录,所谓“文字”,在汉字造就“书面语”或“文言”之后,就形成区别于口语语音的自我结构和功能。不用说汉字对口语影响的反作用,只就“书面”的书写与创制,本质上就是文字的运用,而单音独字表义充当“词”的功用,所以“遣词造语”就是用字。如果一定要对字、词强为区分,也不便落实于单字,因为单音独字表义即“词”,所以胶着于双音两字勉力为说。实际上只是基于双音“音步”的“韵律构词”才导致“词”的“双音化”,所谓“双音词”趋多在现代以来一直被作为汉语词汇发展的口实,但是双音为词也必定成于两字组合,惟字才是“构词”的根本,转化为书面写作的问题,就是两字如何组合为一。
在大赋散语四言铺陈中,两字组合以为形容,必有赋家临文的用字考量,要在化实为虚,则字类可用甚众,否则捉襟见肘,不克铺陈。上文考察《江赋》用字如“澩灂”,“灂”本“小水声”,辞赋多“瀺灂”连用,马融《长笛赋》李善注谓“瀺”为“水注声”*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50、114、250、250、250、241、271页。,而“濜溳”并水名,三者并列组合为“词”,实际上都是二字凑合,盖赋家欲赋水势,只就从“水”字类为用,将名物二字并列,以为描写形容,化实为虚。然取名物字转为形容,也还在于名物字本身造字的音义所据,如“澩”、“灂”,都为小水,而命以为小者,本初以声模拟,声小故拟命名,命名就是形容。
相类者复如《文选·扬雄〈甘泉赋〉》“梁弱水之濎濙兮,蹑不周之逶蛇”,“濎濙”,李善注谓“小水貌”*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50、114、250、250、250、241、271页。。“濎”,《集韵》他定切,透母径韵去声,《玉篇》谓水名*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第91、91、102、103页。,本赋取与“濙”并。“濙”,《汉书·扬雄传》本赋作“濴”,《广韵》余倾切,以母清韵平声,《玉篇》注谓“水泉貌”*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第91、91、102、103页。。《集韵》释“濎”单举本赋例,训“小水”*丁度等编,赵振铎校:《集韵校本》,第1256、704页。,始并。“濎”以命水,本有所拟,“濴”为貌亦是,“濎濙”指“小水”,亦以其貌谓然,汉字非如表音文字定性以形,因而所谓“词性”十分灵活,对于文学创制尤所适宜。反之如《七发》“揄弃恬怠,输写淟浊”、“恬怠”、“淟浊”用形容语指名物,则化虚为实。但赋家用字转实为虚,有时难以判断,这不仅影响阅读,在注家也是颇费斟酌,不免误注。兹举马融《长笛赋》为例。《文选》李善注本赋略云“兀狋觺……嶰壑澮……森槮柞樸”,其中“兀”、“澮”、“森槮”考述如次:
森椮:李善注谓“木长貌”*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50、114、250、250、250、241、271页。。李周翰曰:“森、槮、柞、樸,皆木名。”*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26页。《全汉赋评注》仍之,并误。《说文·林部》:“森,木多皃。从林,从木。”*许慎:《说文解字》,第176、126页。《文选·陆机〈文赋〉》“发青条之森森”,李善注引《字林》曰:“森,多木长貌。”*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50、114、250、250、250、241、271页。《说文·木部》:“槮,木长貌。从木,参声。”《楚辞·九辩》:“萷櫹槮之可哀兮”洪兴祖补注:“櫹槮,树长貌。”*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86页。“森”、“槮”,并《广韵》所今切,生母侵韵,“森椮”同叠韵联绵,实同“森森”、“参参”,必非二木之谓,善注得之。张衡《思玄赋》:“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参参。”《文选·束晳〈补亡诗·华黍〉》“芒芒其稼,参参其穡”李善注:“参参,长貌。”*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50、114、250、250、250、241、271页。赋用联绵,字无定形,则取合义用之,“森槮”为然,连同凡上所述,可见大赋铺陈用字的若干重要特征。
“赋”以“铺”、“富”为训,铺陈繁富乃是大赋体制的本质特点,名物和描写的铺陈落实于造语用字,创作的语用显示着文学和语言的不可分离,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语用是为根本。赋学研究必当具有语用的维度,由于汉字之于汉语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大赋创作的语用就以用字为本。“字本位”的语用研究不惟通合文学和语言的领域,而且表现为深细的文本考辨,具有实学的品格。文学的审美通过实学的考辨才能获得切实的证明,这就是本文之于赋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YI Wen-xiao
(CollegeofLiterature,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550025,China)
[责任编辑 罗剑波]
A Research on the Words Used in Dafu Elaboration
The rhetoric of elaboration, which focuses on the use of words, is the essence of Dafu (big prose, a kind of non-poetic style of writing in the Han Dynasty). The research of pros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agmatic study of words, especially on the four-character sentence making with the aims of objective elaboration and descriptive elaboration. Objective elaboration expresses the singularity with knotty characters, similar components and parallelism. Descriptive elaboration shows the avoidance of repetition and the variety of type in disyllabic morphemes varied in sound and sense, and in phonology varied in glyphs and sense, or transferred sound to different glyphs and sense with casual components. The elaboration of four-character sentence-making specified the pattern for the character-using in Dafu. The phrase with two single characters and the sentence with four show their coordinating rhyme, glyphs or sense created by the author to present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the blankness-actuality conversion.
Dafu elaboration; four-character sentence-making; objective description; single character combination; blankness-actuality conversion
易闻晓,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汉大赋语词考述”(项目批准号:092D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