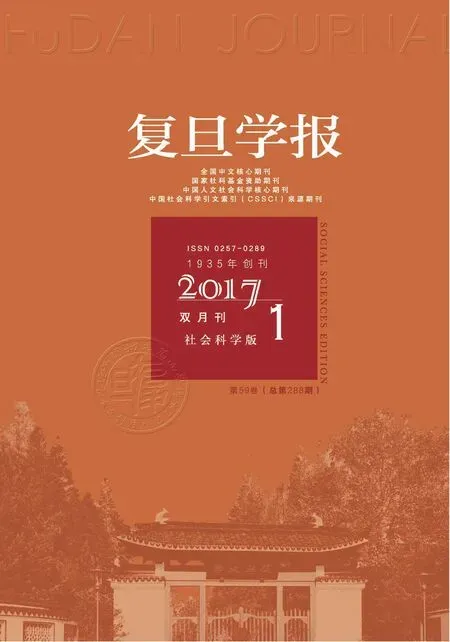《望厦条约》订立前后中美往来照会及翻译活动研究
屈文生
(华东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1620)
QU Wen-she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翻译理论研究
《望厦条约》订立前后中美往来照会及翻译活动研究
屈文生
(华东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1620)
美国在19世纪中期开始将注意力聚焦在亚洲。近代中美外交关系的第一页由1844年美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顾圣使团”掀开。美国公使顾圣在抵达澳门后,先后同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钦差大臣耆英展开了约半年之久的照会交涉与谈判。顾圣与程矞采间的照会往来主要围绕“北上进京”的主题,双方间发生过多次直接交锋,程矞采的态度坚决而强硬。在第二阶段,耆英主要采用了怀柔政策,顾圣在双方外交折冲中占据上风。以中美双方在《望厦条约》订立前后的照会交涉为中心,文章对顾圣使团的翻译活动作了梳理,伯驾承担的翻译任务最多,裨治文次之,然后是卫三畏;赫宁茨则主要是在徐亚满案中承担情报搜集翻译工作。使团译者不仅为使团展开照会交涉与谈判提供了优质的翻译服务,还提供了重要情报,为美国在华展开商业活动和建立外交关系立下了功劳。
顾圣 程矞采 耆英 照会 中美外交 翻译史
1843年1月24日,曾任美国第六任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其向众议院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美国同中国缔结条约的计划,建议国会拨款4万美金派使团出使中国,以在美国和大清帝国间建立外交关系。鉴于英国已通过战争方式在中国获得了贸易权,大清帝国海禁的符咒业已打破,亚当斯认为,“大清帝国的荣耀、利益和傲慢会提醒大清皇帝以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把英国军队借助武力强行获取的接近中国政府的权利,平等地给予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Kenneth W. Rea,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841-1912: The Collected Articles of Earl Swish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77) 57; Hunter Miller,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4, Documents 80-121: 1836-1846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4) 638.美参议院最终以96对59票的投票结果,批准拨款4万美金,并决定当年即向中国派出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Ping Chia Kuo, “Caleb and The Treaty of Wanghia, 1844,”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1 (Mar., 1933): 34-54; Kenneth Chen, “The Cushing Mission, Was it Necessary?”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1939-1940): 3-14.
该使团公使大臣Caleb Cushing的汉译名在《望厦条约》中文官本*Hunter Miller,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p. 577-599.,以及《中外关系史料》所收美国使团与中国官员往来照会的原始档案*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8年,第5~59页。内,均为“顧聖(顾圣)”二字,但在《筹办夷务始末》所载各奏折中,这一名字被改为“顧盛(顾盛)”(均为口字旁)。后世众多中国近代史研究作品,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该人名写作或译作“顾盛”。关于顾圣人名翻译一节,此前未受到学界重视。
《望厦条约》中文官本“顾圣”二字,应是使团译者伯驾(Peter Parker)等人为公使的姓氏Cushing精心译出的谐音中文名,而“顾盛”盖是中方对原译名“顾圣”的改写,究其原因,大概是“聖(圣)”字过于美好。

图1 《望厦条约》原始档案内的“顧聖”二字
“圣”字能使人联想到“圣上”“圣王”“圣主”“圣君”“圣旨”“圣帝”“圣训”“圣人”“圣贤”“圣典”“圣制”“圣母”“圣法”等一系列词语。因此,“圣”字译名的改写,不排除避讳的考量与晚清大员对外国人抵触心理等因素的影响。翻译常受历史语境影响,人名翻译时常关乎外交,关乎政治。*人名翻译不当可能引发外交冲突。关于中英外交史上一起由Lord Napier人名翻译而引发的外交风波个案研究,可参考王宏志:《律劳卑与无比:人名翻译与近代中英外交纷争》,《中国翻译》2013年第5期。
出于尊重原始史料计,本文将遵从Cushing的人名旧译“顾圣”,并将该使团称为“顾圣使团”(The Cushing Mission)。
一、顾圣使团的译者
关于顾圣使团的译者,以往研究成果提及的主要是伯驾、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这三位美国在华传教士。但从已发掘的档案来看,担任顾圣使团译者的,除以上三位主要译者外,至少还有一位随团译者赫宁茨(Stanislas Herniss),其承担的翻译工作在过去完全被忽略。
伯驾虽非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却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医生。他183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同年来到广州,起初在广州西关十三行商馆区开设了一间专科性质的“眼科医局”,后又在丰泰行7号开设博济医院。*陈瑞林:《十三行、啉呱、医学图画与近代中国写实绘画的兴起》,载赵春晨、冷东主编:《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第483页。关于伯驾,另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64~83页。他曾为林则徐翻译过滑答尔(Emeric de Vattel)《各国律例》片段,由于行医的关系,他又与日后议定《望厦条约》的中方代表耆英、黄恩彤、潘仕成等人,较为熟悉。耆英及潘仕成的父母,均曾请伯驾诊病。*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67页。黄恩彤曾在《抚远纪略》中称“名医伯驾者,在粤久,治病辄愈,药不索直,人皆爱之”。*黄恩彤:《抚远纪略》,载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5),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428页。因为“人皆爱之”,他后被比作“很重要的外交润滑剂”。*[美]爱德华·V. 吉里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伯驾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就主张美国应向中国派出使团。他曾于1840年12月回到美国,次年4月,曾敦促时任国务卿的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向中国派出一位大臣,并就此征求过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等人的意见。在华盛顿活动期间,伯驾与韦伯斯特的侄女哈丽雅特·韦伯斯特(Harriet Webster)结婚,成为韦伯斯特的侄女婿。*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新教传教士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9~262页。当时,顾圣与外交委员会其他成员曾提议宜由约翰·昆西·亚当斯出使中国。但亚当斯说,如果他本人使华,那他就无法再在参议院支持拨款动议。亚当斯没有答应出使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这时向中国派出大臣,还为时尚早。*John W. Fost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3) 77-78.1842年11月,伯驾再次回到广州。
1844年,伯驾被顾圣使团委以“公馆联合汉文知事”(Joint Chinese Secretary to Legation)职务,成为中美交涉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顾圣告诉伯驾,希望其不仅是中文秘书,还要成为他的机要顾问,他们之间将没有秘密。伯驾曾多次翻译顾圣收发的照会文书(见下文表1),并随着事情的进展往返于广州和澳门两地。顾圣曾打算学习满文和汉字的书写形式,伯驾因此还为其寻找过满语老师。*[美]爱德华·V. 吉里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第105~107页。此外,伯驾可能早在1841年就对《南京条约》的草案有所了解。*因为他在伦敦与朋友渣颠(William Jardine)见过面,此人是东亚鸦片贸易机构的支持者,曾为英国外相巴麦尊起草《南京条约》草案提供了指导方针。参见[美]爱德华·V. 吉里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第101页。正因如此,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顾圣都对伯驾的帮助给予极高的评价。*[美]爱德华·V. 吉里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第113、298页。伯驾在华的地位,后来俨然超过了美国在华领事福士(Paul S. Forbes),因为顾圣在最后一次照会耆英时明确提出,此后中国致美国朝廷的照会、公文、皇帝玺书,均由伯驾而非福士收接。1846年,伯驾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黄恩彤曾致信祝贺)。*[美]爱德华·V. 吉里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第113、298页。再往后,他先后担任美国在华代理公使(1847~1855)和驻华公使(1855~1857)。
裨治文*[美]雷孜智著,尹文涓译:《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53页。比伯驾大三岁,是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遣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于1830年2月25日抵达广州,比伯驾到中国早四年多时间。裨治文曾深受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及美国在华商人欧立芬(David W. C. Olyphant)等人的影响。*苏精:《裨治文在十三行1830~1833》,载赵春晨、冷东主编:《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第385~405页。资料表明,裨治文抵达广州次日上午,便拜访了马礼逊,并决定学习广东方言,但学习中国语言四年后,还无法开口讲话,也不能提笔写书,故与马礼逊的语言能力不能相提并论,当然客观上讲,编辑《中国丛报》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与精力。*苏精:《裨治文在十三行1830~1833》,第394~395页。马礼逊去世后,裨治文曾协助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 R. Morrison)及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校正马礼逊的《圣经》中译本。*K. S.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7) 95-96.
裨治文在顾圣使团中亦任“联合汉文知事”,兼任公使馆的牧师。顾圣受裨治文的帮助巨大。丹涅特(Tyler Dennett)曾经说过,从《中国丛报》和《望厦条约》的仔细比较中,可以看出顾圣在1844年的交涉中,不但多亏有裨治文的翻译工作,而且还多亏有他作为顾问。*[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73页。顾圣专使回美国后,曾在1845年2月10日写信给裨治文,除通知他国会已批准《望厦条约》外,还提到他已向美国政府代为裨治文和伯驾请功,因其为美国政府做出了“无法估价的服务”。*Eliza Bridgman,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Anson D. F. Randolph, No. 688 Broadway, 1854) 130~134.裨治文在《望厦条约》签订后,得到美部会的积极回应,不顾一切地壮大了传教队伍。*参见[美]雷孜智著,尹文涓译:《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第206~207页。此外,他和卫三畏编辑的《中国丛报》在此后影响也变得更大。
卫三畏于1833年10月抵达广州,被美部会任命为广州传教站印刷工。与此前抵达中国的马礼逊及裨治文等传教士面临的困境一样,卫三畏在中国也无法公开传教,只能设法迂回而行。卫三畏认为印刷出版可能是扭转困境的利器,*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第75页。他曾提到,造成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互相憎恶和摩擦的原因,是他们无法理解对方的语言和愿望。*[美]卫斐列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5~66页。卫三畏在《望厦条约》订立后曾两次(1853、1854)随美国舰队远征日本,并担任翻译工作;后来在美国驻华使团任职,曾七次代理驻华公使职务,并参与订立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1877年,他返回美国,担任耶鲁大学首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他著有《中国总论》(TheMiddleKingdom),该书于1848年初次出版,后于1883年修订后再版,他正是因此书而跻身于著名汉学家之列。
除以上三位传教士外,顾圣使团的译者还有一位赫宁茨,鲜有人提及。赫宁茨是荷兰裔,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在出航期间,他熟练地掌握了葡萄牙语,在使团结束时,他已经可以部分地阅读和书写中文。*[美]雅克·当斯著,周湘、江滢河译:《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784~1844》,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10页。有据可考的,是他曾在徐亚满案交涉中数次提供过情报翻译服务。
顾圣在其发回美国国会的公文中,曾将赫宁茨的名字拼为“Stanislas Herniss”,*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ond Session of the Twenty-Eighth Congress, Begun and Held at the City of Washington, December 2, 1844, in the Sixty-Ninth Year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I (Washington: Gales and Seaton, 1845) 67-68.但此人的姓氏在他处常被拼为“Hernisz”。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赫宁茨是顾圣的私人秘书。此人的翻译活动主要在《望厦条约》签订前后,特别是在徐亚满案发生后,顾圣曾下令赫宁茨搜集整理了这一时期清政府官民对徐亚满案反应的情报。从解密档案(美国第28届国会第2次会议档案)来看,明确署名由赫宁茨翻译成英文的文件共三件。赫宁茨搜集并翻译的情报,为顾圣使团的决策提供了帮助。
赫宁茨在《望厦条约》订立后回到美国,出版了《习汉英合话》(AGuidetoConversationintheEnglishandChineseLanguagefortheUseofAmericansandChineseinCaliforniaandElsewhere)*该书由位于Boston 的 John P. Jewett & Co.出版社在1854年出版。一书,以满足美国人高涨的中文学习需求,因为美国人有到中国新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展开贸易往来的需求。他还担任美国东方学会理事(Member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成为一名汉学家。此外,赫宁茨在担任顾圣使华团外交随员(attaché)之后,还曾担任过美国赴巴黎使团的外交随员。
综上,顾圣使团的译者包括先前已在广州、澳门或传教或行医或办报的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卫三畏,也包括使团随员赫宁茨。显见的区别是其中三位为在华传教士,*美国长老会宁波布道站印刷所主任、专业印工柯理(Richard Cole)曾在后来严词批评顾圣使华严重妨碍了传教工作。参见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第358页。一位为使团随员。不太显见的差异是,卫三畏和赫宁茨的身份与伯驾和裨治文完全不同。从现存档案来看,在中方致美方每一件照会的翻译文本(英文)内,译者凡署名伯驾与裨治文的,他们的名字后大多附有“Joint Chinese Secretary”、“Joint Chinese Secretary to Legation”或“Joint Chinese Secretary to the United States Legation to China”,即“汉文知事”字样。卫三畏与赫宁茨的名字后,从未见署有类似称谓,可见担任使团正式官员的只有伯驾与裨治文二人,而卫三畏与赫宁茨则大概只能被称为“汉文协事”。伯驾与裨治文在顾圣使团的地位大概与马儒翰在订立《南京条约》时的身份相当,而卫三畏和赫宁茨扮演的大概是类似于罗伯聃(Robert Thom)与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的角色。*关于《南京条约》的译者,参见屈文生:《早期中英条约的翻译问题》,《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
除此之外,有学者还提到,顾圣还聘请三名中国人润色中文译文。为了便于澳葡当局联络,使团又聘请一名葡文翻译。*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第168页。上述赫宁茨已掌握葡萄牙语,这名葡文翻译到底是另有其人,还是就是指赫宁茨,尚不得而知。润色中文译文者之中,应该有梁进德,王宏志教授提到他曾从旁协助裨治文,辅助顾圣使团和中国签署《望厦条约》。梁进德是第一位中国人传教士梁发的儿子,10岁时便跟随裨治文学习英语和希伯来文。顾圣使团离开后,通过潘仕成的介绍,梁进德还曾直接为耆英工作,直至1847年离开,重新跟裨治文读书和工作。*王宏志:《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上篇:英方的译者)》,载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201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92页。
在顾圣使团使华以前,中美两国并无正式的外交往来。在此之前,美国在华传教士虽也曾为美驻粤领事做过一些翻译工作,但他们的翻译活动在那时的贡献及影响力,是无法与后来为顾圣使团在华的交涉和谈判中所开展的翻译活动相提并论的。那么顾圣使团的译者除了将《望厦条约》的文本翻译成中文之外(拟另撰文论述),到底还翻译过哪些重要的照会文件?这些译者是如何跨越语言的障碍并推动早期中美外交开展的?其中的翻译问题在中美早期外交史的构建中,又发生过怎样的影响呢?
二、往来于中美双方间的照会交涉及照会翻译活动
从1844年2月24日抵达澳门起,至8月26日离开,顾圣使团在中国共居住185天。其间顾圣与大清官员间的照会往来,从内容看,主要围绕使团是否可以北上进京、徐亚满事件的处理及《望厦条约》文本协商等三大主题;从时间来看,又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于顾圣与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1783~1858)之间,第二阶段则发生于顾圣与钦差大臣耆英(1787~1858)之间。往来于双方间的照会约计71件(包括非正式函件及备忘录等)。
长期以来,学界对顾圣使团的译者针对上述三大主题在以上两个时间段的中美交涉中,究竟承担过什么样的具体翻译任务这一问题,多停留在演绎、想象或不得而知的困惑层面,对于使团译者在中美交涉中发挥的具体作用,也无法作出确凿的描述。*如《伯驾与中国的开放》一书作者吉利克(Edward V. Gulick)曾持如下悲观看法:“作为顾盛(圣)的翻译,伯驾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永远无法彻底弄清楚”。参见[美]爱德华·V. 吉里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第112页。
从现已解密的美国第28届国会第2次会议档案等英文史料来看,这一期间绝大多数照会的翻译件(汉译英),都署有英译者的名字,这为我们研究顾圣使团译者的具体翻译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客观依据。但顾圣使团照会的翻译不限于汉译英,还包括英译汉,令人遗憾的是,依据现有的史料,只有汉译英文件署上了译者姓名,英译汉文件内并无任何译者的信息。
(一)顾圣与程矞采间的照会交涉及翻译
程矞采致顾圣的中文照会共计13件,其中伯驾独立翻译或主译为英文的照会件数最多,共计8件(这些照会的汉字篇幅长短不一,短则数百字,长则千字有余)。卫三畏翻译了3件(其中两篇较长,均逾千字,另一篇很短)。裨治文翻译了2件(一篇接近千字,另一篇很短)。具体见下表1。

表1 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致美使顾圣照会:译者、照会时间及照会事项简表
资料来源:“译者”及“照会时间”两栏,参见PublicDocumentsPrintedbyOrderoftheSenateoftheUnitedStates, pp. 2-33;“照会事项”一栏,参见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目录页第84~87页。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中华书局1959年)、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1964年)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编的《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1968年)集中选编了顾圣致程矞采的照会翻译件(共12件,见表2)。由于顾圣致程矞采的照会翻译件档案内均未署上译者的姓名,故无法确定它们具体由使团的哪一位译者所译,虽然个别情况下,也可依译文完成的时间、主题和翻译风格作些推测。

表2 美使顾圣致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照会:照会时间及照会事项简表
资料来源:有关“照会事项”一栏参考了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目录页第84~87页。
以上表1和表2所示的25件公文,便是往来于顾圣与程矞采之间的全部外交照会。在以上照会中,为达到防御美顾圣使团北上进京及不与美国缔订条约的目的,程矞采不惜通过作伪等手段,在照会内容上动手脚。特别是程矞采私自对《南京条约》的修改,曾招致顾圣使团的严重不信任,给顾圣发难提供了借口,为此双方交涉几近决裂,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顾圣在随后与钦差大臣耆英交涉或谈判时,提出非分要求。由于往来于程、顾间的照会极其重要,笔者已另完成了论文《笔尖下的作伪与藉口:〈望厦条约〉订立前顾圣与程矞采照会交涉文本研究》,故其中详情在此不再赘述。
(二)顾圣与耆英间的照会交涉及翻译
往来于顾圣与耆英间的照会共计46件,其中耆英致顾圣的共24件,顾圣致耆英的共22件,分别见表3和表4。

表3 钦差大臣耆英致美使顾圣照会简表

(续表)
资料来源:有关译者姓名,参见PublicDocumentsPrintedbyOrderoftheSenateoftheUnitedStates, pp. 2-33;“照会事项”一栏参考了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目录页第86~92页。
在以上耆英致顾圣的24件往来照会中,从其中能够确定译者的17件公文来看,伯驾在该交涉阶段承担的翻译任务仍最多(9件),裨治文次之(6件),然后再是卫三畏(2件),另有7件照会暂时无法确定译者。至于赫宁茨,他主要在徐亚满案中承担情报搜集翻译工作。

表4 美使顾圣致钦差大臣耆英照会简表
资料来源:“照会事项”一栏参考了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目录页第86~92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顾圣与耆英间的通信并非全部以照会形式展开,如上表所示,在46件信件中,照会37件,半正式函件7件,此外还有2件备忘录。在发给司法部部长约翰·尼尔森(Hon. John Nelson)的信中,顾圣曾提到,他和耆英的通信有两大特点:一是对许多问题他们是在半正式的照会中(semi-official communications)讨论的,这类照会不但在篇幅和形式上有别于其他照会,在文体上也与正式公文有所区别;二是耆英的半正式照会一律是用满文(uniformly addressed in Manchu)拟写的。*See 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40.所以,以上半正式函件的中文本,也应该是从满文中翻译过来留档的。
三、《望厦条约》订立前后顾圣与耆英间若干重要照会交涉研究
在往来于顾圣与耆英的46件照会中,中美双方围绕顾圣职衔及照会平行文本、徐亚满案、税册重加厘定、国书呈递、《望厦条约》的溯及力问题及《新定章程》的订立等六点尤其值得深入研究。
(一)围绕顾圣职衔、照会平行文本的交涉与翻译
4月29日,刚刚奉谕旨由两江总督调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的耆英,在获悉顾圣急于北上进京,且意在北京而非澳门与大清商定条约之后,其时他虽人还在苏州,便向顾圣发出了第一件照会,旨在提请他在粤静候面商一切。*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24、32、33、32、33页。耆英抵粤后致顾圣的第一份照会,是在他到达广州当日(即5月31日)递出。*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24、32、33、32、33页。以上自江苏发出的照会由伯驾等人(Peter Parker, &c.)译为英文,*See 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 67.抵达广东后发出的第一件照会则由裨治文译为英文,供顾圣阅览用。
在同美国使团的最初交往上,耆英并未参照中英《南京条约》第11条业已确立的邦交平行原则,换言之,他最早发出的照会并未使用对等的平行文本。相反,他在一开始仍试图沿用旧章。他虽将美国国名抬高一格写,借以表示他或他的秘书认为是对这名称的适当尊敬,但其在同一公文中把中国及皇帝的名称抬高了两格。*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67页。在对美国使团正使顾圣职衔称呼上,他使用的则是“米利坚国公使”字样。顾圣对于这一称谓并不接受,遂将照会退给替耆英传送公文的吴委员。*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24、32、33、32、33页。
在6月3日照复耆英时,顾圣表示,“兹前后所来公文二件,本公使恝然送回,殊非所忍”。但他声称退回照会文件事关“国体”,是情非得已之举。*参见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 67.对于这起纷争,吴委员当场信誓旦旦地说:“来文间有不合之处,或属抄写错误”,他表示钦差大臣耆英对美国“断无存不相亲敬之意”。但顾圣仍明确要耆英“请即按为两大国公同利益,该平行礼款更正”。*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24、32、33、32、33页。
就这样,耆英最早致顾圣的两件照会均被退回。6月9日,耆英特地致美使顾圣照会(译者为伯驾),对先前两件照会未用平行文本作解释说:“前载途次所发照会二件,填写贵公使衔姓中有舛错之处,实未接到贵公使来文,无凭照写所致。现据贵公使照会前因,本大臣即饬吏更正缮写送回备案,幸勿介怀。”*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24、32、33、32、33页。在重新发出的照会中,耆英将原照会内“右照会米利坚国公使顾”一行,改为“右照会亚美理驾联国钦奉便宜行事全权驻中国公使大臣顾圣”。*有趣的是,这里的“米利坚国”改为了“亚美理驾联国”。美国译名在顾圣与程矞采、耆英的照会文件及《望厦条约》官本内并不统一,还有诸如“联国”、“米国”、“亚美理驾合众国”、“亚美理驾会邦国”及“大合众国”等。关于美国国名的翻译史,可参见梁建:《从“花旗国”到“美利坚合众国”—— 清代对美国国名翻译的演变考析》,《历史档案》2013年第1期。在此后顾耆间的各照会内,顾圣的职衔有时也写为“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奉差遣全权善定事宜公使大臣”,或“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奉便宜行事全权驻中国公使大臣”。在《望厦条约》正本内,“亚美理驾联国”被改译为“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
这次交涉以顾圣一方胜利告终,顾圣对此流露出的喜悦有据可考。6月13日,他在向美国国务卿厄普舒尔(Hon. A. P. Upshur,此时他已经过世近4个月,但远在中国的顾圣可能还不知道)提交的报告中谈到:“在耆英4月29日及5月31日最初递给我的两件照会中,中国政府名高出美国政府名一个汉字格。由于中国素有借此方式体现公文往来双方之尊严与地位的传统,我是绝不会选择屈服于任何丝毫有损美国尊严的文字或表达的,因此我冒着可能即刻中止一切谈判的风险,将上述函件退给了耆英。”*See 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34.此外,顾圣在美使团与大清成功签订《望厦条约》后两天(7月5日),在一封写给时任美国司法部部长约翰·纳尔逊(U.S. Attorney General John Nelson)的信中,曾列出使团取得的16条重大成就,其中第12条就是《望厦条约》确立了“中美间官吏与人民彼此平等交往的规定,故美约较《虎门条约》更佳”。*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9页。顾圣称《望厦条约》在形式上实现了中美间的绝对平等,它包含有《南京条约》及其附约《虎门条约》都没有囊括的条文。*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5, p.555.
总之,顾圣在与耆英的首番外交折冲中占了上风,而这次大获成功的经历,为其日后在华多轮交涉中延续强势的表现垫足了底气。8月23日,顾圣在返程前致美国时任国务卿卡尔霍恩(Hon. John C. Calhoun)的一封信中,再次强调他同代理两广总督程矞采及钦差大臣耆英间的公文往来,始终是建立在“绝对平等往来”基础之上的。*参见See 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99.很显然,《望厦条约》第30条所规定的“嗣后中国大臣与合众国大臣公文往来,应照平行之礼”,是顾圣对他自己在这次交涉中所取得战果或利益的固定化。
需要说明的还有一点,《望厦条约》的中文官本后又使用了“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圣”字样,*Hunter Miller,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599.这传递出两点信息:
一是美国国名的汉译由“亚美理驾联国”或“亚美理驾合众国”改为了“大合众国”或“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缘由或与英方在《南京条约》内争取确立“大英国”译名的动机相当,“大”字的使用是美国顾圣使团刻意争取的结果——意在与条约另一方“中华大清国”中的“大”字相对等抗衡;类似地,法国的译名在中法《黄埔条约》(1844)内也被确立为“大佛兰西国”,而此前常被译作“弗兰西国”。
二是《望厦条约》汉译本对顾圣官职的改译,体现出谈判双方对顾圣身份主要是“钦差大臣”而不止是“公使大臣”的强调。从顾圣与程矞采、耆英间照会的各英文档案文本来看,顾圣在使团中的职务具体是“Commissioner and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to the Imperial Court”——把顾圣担任这长串职务分解开来,分别就是“Commissioner”(钦差)、*李定一先生及茅海建教授等人将“commissioner”一词译为“委员”。参见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92页;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520~521页。“Envoy Extraordinary”(特别公使)以及“Minister Plenipotentiary”(全权大臣)。在《望厦条约》英文官本内,美方曾将顾圣的职务在行文上加以明确,具体写作“Commissioner Caleb Cushing,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of United States to China”,*Hunter Miller,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559.强化了顾圣的“钦差”身份。相应地,《望厦条约》中文官本确定的“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圣”,也明显强化了顾圣的钦差身份,直接略去了英文本内“Envoy Extraordinary(特别公使)”这一职衔。
(二)围绕徐亚满案的交涉
在耆英与顾圣间众多的交涉公文中,围绕徐亚满案(美国花园投掷砖石事件及徐亚满之死)的照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参见屈文生:《〈望厦条约〉订立前后中美关于徐亚满案照会交涉研究》,《法学》2016年第8期。徐亚满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中美《望厦条约》内容的重大变化。领事裁判权成为双方谈判后期最为紧要的一个话题,而徐亚满案的解决直接关乎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为把杀死徐亚满凶手的责任推开,顾圣不惜强词夺理地把徐亚满事件的全部责任归于徐亚满本人、投掷石头的匪徒、未及时制止暴动的官弁兵役。然把徐亚满事件的责任推在他们身上,并非顾圣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他拟在中国确立领事裁判权的手段。他诋毁官弁兵役的逻辑以及他想要说明的是:美国人完全信赖中国大皇帝、甘愿受中国政府保护,但奈何地方官经常失职,如此,美国人只有自己保护自己,并只接受自己祖国的管辖。在中国,美国法律并没有依附于美国领土,而是依附于美国公民的人身——他们每个人都代表着美国主权的一个浮岛。*[美]络德睦著,魏磊杰译:《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2页。
(三)围绕“税册重加厘定”的交涉及翻译问题
顾、耆间关于“税册重加厘定”的协商晚至7月10日才达成一致,但早在6月22日,顾圣就此问题曾致耆英照会称,他将税饷例册赍呈,以为附粘大清大合众国条约之后。*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37、37、37、49、49、49、51页。将《望厦条约》后所附“应完税则”*Hunter Miller,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p.601-625.,与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后所附“海关税则”*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1, 2d ed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7) 357-382.相比较,可发现顾圣在6月22日照会内赍呈的“税饷例册”,几乎就是《虎门条约》附件“海关税则”的翻版。这是因为顾圣本人基本赞成《虎门条约》中的税则,他曾提到“据本大臣鄙见,自谓贵国与大英国议和时,所定之饷例册,俱属允当合宜。其中所载,本大臣多已允行”。*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37、37、37、49、49、49、51页。
稍有不同的是,在这件照会中,顾圣特别提到要降低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参”(ginseng)和“铅”(lead)等货物的关税——因为这两种货物大多从美国运来。顾圣在照会中提到,他希望耆英在闲暇时对此酌夺,又进一步说:“近有一本国商人,因不知此例,致为白铅一项,曾受亏折。”*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37、37、37、49、49、49、51页。
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将顾圣的原文“But there are some few articles of imports which come to China chiefl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on which the duty is disproportionately high. Among these areginsengandlead”,译为“但内有进口货物数款,如洋参、白铅等,多是由本国运来,所定之税,比别货略多”。紧接着,他又将顾圣照会内“I am informed, also, that it is the wish of your Government to havespelterconsidered as saleable only to the officers of the Treasury”一句,译为“近又闻贵国规制,于白铅一款,只归官商承买”。*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37页;See 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43.换言之,译者把这里的英文“lead”和“spelter”都译为了“白铅”。前者是一例明显的误译,因为“lead”和“spelter”显然是两种货物,顾圣对它们明显是分别提出的。中文对这两个单词的翻译本是有别的,一般是“lead”译为“黑铅”,而“spelter”则译作“白铅”。
7月3日,耆英就“参”、“铅”减税一事照复致顾圣(译者为裨治文)。*See 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44.耆英在照会内提到,“现经委员等连日会议,将洋参一款,每担按上参二成、下参八成折算”。*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37、37、37、49、49、49、51页。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每向中国出口一担(一百斤)人参,其中二十斤按照上等参来征税(每百斤三十八两),剩余八十斤则按照下等参来征税(每百斤三两五钱)。笔者在查阅档案后发现,在《望厦条约》所附税则“上等洋参”一栏后,附小字“除净参鬃的。原例作人参”,这和此前《虎门条约》附件“海关税则”内相关条文无异;但在“下等洋参”一栏后,《望厦条约》所附税则后在原有的“即洋参鬃。原例作人参鬃”后,则新加了一行小字“每百觔(斤)按上参二成下参八成折算”。*Hunter Miller,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613.这自然正是顾圣通过照会交涉为美国商人争取到的利益。
至于黑、白铅一款,耆英表示,“每担照旧例减税一钱二分,作为二钱八分,均已平尤”。*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37、37、37、49、49、49、51页。至于白铅是否应归官商承买,耆英承诺另行备文知照,届时将“中国例禁出入口货物一并查明”*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37、37、37、49、49、49、51页。后再一并作答复。7月10日,耆英再次照复顾圣,确认将洋参“每担按上参二成、下参八成折算收税,黑白铅一项,减为每担税银二钱八分”,并对“白铅一项应专归官商采买”予以确认,对出入口违禁货物也一并附列清楚。*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37、37、37、49、49、49、51页。查阅档案可发现,《望厦条约》所附税则“洋生铅、洋熟铅”后,较原《虎门条约》下附小字“黑白同例”后多了一行小字“白铅止准卖给官商”。*Hunter Miller,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622.此外,《望厦条约》所附税则末尾,多出一条内容为“进口违禁货物;鸦片”(CONTRABAND;Opium)的条文*Hunter Miller,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p.576 & 625.,则是耆英在照会交涉中为大清力争到的权益。
顺便提一句,《望厦条约》对诸如“担”“两”“钱”“分”的翻译分别是“picul”“tael”“mace”“kandareen”。*See 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75.
(四)关于国书呈递的交涉及国书的翻译
顾圣使团赴华前,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曾向顾圣发出过指令,史称“韦伯斯特训令”。据此训令,顾圣使团要在中国获得英国人已经获得的五口通商特权,并进京谒见皇帝(递交泰勒总统致道光皇帝的国书)。在整个韦伯斯特训令中,最为清晰的是最后一段文字:韦伯斯特希望,也相信,顾圣会成功缔结一个与中英已经缔结的条约一样的条约;使团应坚持为美国争取最惠国待遇(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如果中美缔结的条约能够包含更为全面更为规范的条文,就可以使美国与中国的交流再迈出一步,成为调整美国与欧洲各国关系原则一样的和约。*Kenneth W. Rea,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841-1912:The Collected Articles of Earl Swisher, p.61.
对于谒见皇帝及递交国书这一任务,韦伯斯特提醒顾圣,美国侨民应永远遵守中国的商业法规,但绝不能让中国人将使团理解为是在向中国朝贡,使团不可向中国皇帝行磕头礼(这也是所有西方使团的顾虑),但是可以向中国皇帝行等同于觐见俄罗斯皇帝一样的礼节。不过,韦伯斯特认为,进京谒见皇帝的这一使命,应被视为使团的砝码而非目标(more as a lever than as an object)。*Kenneth W. Rea,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841-1912:The Collected Articles of Earl Swisher, p.61.
秉承这一原则,顾圣在抵达澳门后,在向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发出第一件照会时就表示:使团拟同中国钦差大臣商议章程(条约);他不日将进京向中国皇帝呈递国书;云云。*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5、41、49、50、50、50页。此后,顾圣每不顺心时,必提北上进京,而所以要进京,理由就是要向道光帝亲自呈递美国总统的亲笔国书。直到6月24日,双方在澳门会晤时,顾圣还提出晋京朝见皇帝。对此,耆英的态度是:他不会阻挠顾圣进京,但也绝对不会为他进京提供任何方便。如果顾圣坚持赴京,他便无权再与其展开会谈。*See 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39.6月25日,顾圣答应停止北上,但同时申明:“然他日西洋别国,倘有使臣进过京后,则凡有本国使臣之到中国者,均应以格外恩礼,款接北上,故先行申明在案,以免临时又复有推阻之事。”*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5、41、49、50、50、50页。
6月27日,顾圣再次提到美国伯理玺天德亲笔国书一事,并询问耆英是否“有权承此国书”(whether you are authorized to receive this letter),他是否还要“另行别法转陈黻座”(or whether I shall seek some other means of transmitting the same to the Emperor)。*See 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53.
7月2日,耆英就国书一事半正式致信顾圣,他说:“现在和约俱已定议,指日告成,我两人应均为快贺……惟尚有一事,亟需奉询。查贵大臣初到粤时,曾于照会前护督部堂程案内,叙明有玺书欲进京呈献御览。现在贵大臣既已停止北上,所欲递玺书,或可勿庸呈递,或照现议条约内载所有国书及一切文书,或交钦差大臣、或交总督之处,缘连日委员会议,尚未议及此款。但此乃要事,必须与现定和约一并复奏,即请贵大臣明日光降……并祈将玺书赍至敝寓,交本大臣接收,以便同约册一并恭呈大皇帝御览,实为善妥。”*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5、41、49、50、50、50页。
7月3日,耆英又说:“所有贵公使承准贵国国书一章,贵公使午后光临,即希赍来,本大臣即当接收,附奏恭呈大皇帝御览”。*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5、41、49、50、50、50页。同日,顾圣表示:“至转赍国书,亦惟有照贵国合仪之处而行”。*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5、41、49、50、50、50页。
7月5日,顾圣致耆英函(未见英文原本,译者不详):“昨送上敝国国书时,尚未译便,兹将译文赍上,祈即查收。在本大臣因既属呈递大皇帝御览,若照本国文字,恐辞不达意,是以凂友转求本处士人,删好誊正赍阅。然一经删定,则词语难免略有增减,但要义则谅无遗漏耳。”*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5、41、49、50、50、50页。在这封重要函件内,顾圣对延请本地“士人”翻译润色美国国书一事作了特别说明。
7月7日,耆英在收到国书后致顾圣函:“顷由潘道台处寄来贵国伯理玺天德国书汉译一件,词意甚美,固由汉文翻译之精通,亦由原书情词之周匝。本大臣开阅之下,不禁为之神怡心旷也。除仍照前议将译汉书移附入原书一并代为呈奏外,专函布复,即颂安佳。”*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51页。
只要阅读泰勒国书英文本,*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Labor, Bureau of Statistics, Monthly Summary of Commerce and Finance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4)2350-2351.便可发现其内容空洞,用词平淡无奇,远不及韦伯斯特指示那般庄严而有力(dignified and able)。*John W. Fost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 p. 81.但国书汉译本却辞藻华美,符合当时中国对外关系之“体制”。*汉译本参见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872~2873、2841~2842页。不仅如此,中译本还增加了许多英文原文中没有的赞美大皇帝的话语,又将中国皇帝和美国总统亲笔签字、美国国会批准等内容省掉。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泰勒的国书究竟是顾圣命使团的译者(伯驾等人)译出后,经广州或澳门读书人(士人)润色而成,还是耆英秘传通事(通事是中国人)译成后,再加悉心修改的?按照顾圣的说法,美国国书是美方主动“凂友转求本处士人”,既然耆英在7月28日(六月十四日)向皇帝上奏“美使呈出国书停止北上折”时,却又曾指出,“其国书系属夷字,猝难辩(辨)认,究竟如何措辞,容俟奴才秘传通事,译出汉文,如何进呈之处,悉心酌议,再行请旨遵办”。*汉译本参见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872~2873、2841~2842页。若根据耆英的这个说法,泰勒的国书汉译文是耆英经“秘传通事”译出后“悉心酌议”而成的。
研究者如对照往来于双方之间71件照会英文原文及中文译文等史料,可发现每当其中部分照会汉译本被程矞采及耆英作为向皇帝上奏的附件时,它们便常常会被多多少少地改动为不同的版本或中译本。这就提醒我们,泰勒国书汉译本的翻译过程可能是以下情形:国书英文原本先经顾圣使团译者(伯驾等人)译出,然后再经当地读书人润色,待顾圣将润色后的译本递交到耆英处后,耆英又对该文本作过稍许改动。
(五)关于《望厦条约》的适用地区和溯及力问题交涉
中美双方依据《望厦条约》解决的第一件纠纷是“合众国人筑设船厂”案,它发生于顾圣尚未离开澳门返回美国之前。这件事的缘由是:香山县民人杨亚芳在香港岛对面的尖沙咀建起了一间打铁店,另一香山县民郑亚维则在此建起一间造船厂,他们的目的都在于为美国商人修理船只。后来,美国木材商“末士唵美利”(Mr. Emery)与“末士非沙”(Mr. Frazer)也在此租地筑设船厂一间,修补船只。耆英在获悉此事后,于8月4日专门向顾圣发出照会称:依据中美现定《望厦条约》,条约内只有合众国兵船损坏准其修补之文,并无筑设船厂、建盖铁铺之议。*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56页。
耆英还特别强调,尖沙咀不在中美议定的五口通商码头之列,尤其不可允许美国人在此租地建屋,他认为以上中美两国四人均违反了《望厦条约》规定。他责成广东布政司会同按察司立饬该地方官……确切查讯究报,并严禁嗣后内地民人再在该处擅行筑屋设厂。他同时照会美国公使顾圣,提请其查核现定条约,一律禁止商人等勿听内民引诱,致滋事端。*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56页。
8月8日,上述唵美利和非沙二人致信顾圣请求援助。*See 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p. 81-82.8月10日和13日,顾圣分两次致信上述二人,希望他们尽快从尖沙咀撤离,并表示美国人在华开设工厂,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并明确指示他们只能将船厂搬至其他地方。*See 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 83.8月14日,二人再次致信顾圣,希望公使能为他们求情,请求中国方面能宽限他们6个月时间,以便他们挑选新址和搬场。*See 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 84.
同日,顾圣决定帮助该二位美国人。于是法科出身的他在照复耆英时利用法学中“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理称:“本大臣查非沙等起建船厂,原在未定条约之先,若与成约不符,亦非故犯……前者英吉利人在九龙建厂,贵大人有给六月之限。兹非沙等原非故犯,于理亦宜宽待,似与英人一体给限六月。”*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57、56页。顾圣还称:“若令即行迁徙,必致血本大亏。但本国已于成约,自当遵成约而行。为望宽限时月,俾得搬迁,不致失所。”*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57、56页。
就这样,这几家在香港附近建造的船厂和铁铺因违反了《望厦条约》条文,最终均被取缔。在这起事关《望厦条约》适用范围和溯及力问题的交涉中,双方均表现出了良好的理性思维和契约精神。耆英所提诉求有理有据。顾圣的答复则充分体现出了他的法律人素养,他以船厂建立时间发生于“未定条约之先”,利用“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法律原则,尽可能地保障了美国在华侨民的财产利益。
(六)关于《新定章程》的照会
在中国期间,顾圣还为住在广东的外国人制定了《新定章程》。*K. S.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 p. 144.8月15日,顾圣就《新定章程》照会耆英时称:“前者贵大臣在澳与本大臣面派幕宾伯驾并布政使黄大人同议新定章程,以保合众国商民居住省城者。现据幕宾伯驾所报,议定各款,大概均属妥适,准堪保护本国商民,不致与贵国民人生端滋事……惟是章程内第一、二两款,似宜小为更改。”*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57、57页。也就是说,《新定章程》中的前两款,对于顾圣希望耆英能“行文布政使照此小为更改”。*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57、57页。
对于这件照会,耆英似无疑义,他认为《新定章程》的订立对于解决“中外杂处”的现状意义重大。在广东地区张贴的告示中,可以发现官方对这一章程制定所报良好愿望:“现在所定章程、界址分明,往来无虞错杂,范围严密,彼此胥就防闲,从此匪徒绝窥伺之缘,而莫生觊觎;远商有藩篱之限而永庆绥安”*卜永坚:《香港早期文书——英国国家档案馆藏F.O.233 /185号档案释文(上)》,《田野与文献》2011年第2期(总第63期,香港),第10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关系史料》内所收录的“新定章程”和香港学者卜永坚整理出的档案文献,在细节上有不少差异。*卜永坚:《香港早期文书——英国国家档案馆藏F.O.233 /185号档案释文(上),第11页。
四、结 语
美国在19世纪中期开始将注意力聚焦于亚洲,近代中美外交关系的第一页,由1844年美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顾圣使团”掀开。在1844年《望厦条约》订立前后,“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顾圣在抵达澳门后,先后同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钦差大臣耆英展开了约半年之久的交涉。在第一阶段,顾圣与程矞采间的照会往来主要围绕“北上进京”的主题,双方间发生过多次直接交锋,程矞采的态度坚决、强硬,顾圣亦毫不示弱。在第二阶段,耆英主要采用了怀柔政策,双方不会形成直接冲突,多数时候,顾圣在双方外交折冲中占据上风,虽然在此期间,也有过耆英据理力争地为大清及大清商民争取到权利的时候。
在出使中国前的一个晚上,顾圣曾在马萨诸塞州的邦克山(Bunker Hill)上说,他肩负着拉近新旧两个世界之文明的重任。文明与学问是从东方照亮文明世界的,但是现在知识开始回潮,要从西方返回到东方。中国不再是老师,美国人和欧洲人已是文明的化身与老师。*Kenneth W. Rea,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841-1912:The Collected Articles of Earl Swisher, p. 60.在中国亲身经过约半年的照会交涉与谈判后,顾圣渐渐确信,促成中国人不关心贸易和外交关系的原因,并非他们希望不受打扰的纯粹无害心理,相反,他渐趋将这种不关心视为文明优越感的证据——这种文明优越感,就是英国人自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华开始长久以来所说的中国人的“傲慢”。这刺激他几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完全是对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荣誉和尊严的侮辱。于是,无论美国最初在塑造其与中国的关系面临过怎样的犹豫,到了顾圣完成使华的使命时,美国没有原则地接受并采取了欧式的帝国主义制度和帝国式的欧洲主权话语,即主权只能由具备正当系谱的国家——欧美“国际社会”的成员——才能获得。*参见[美]络德睦著,魏磊杰译:《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第133、139~140页。顾圣使团借助其在同中方照会交涉中逐步占领的优势地位,最终在《望厦条约》内确立了不平等、不对等的制度——比如并非“韦伯斯特训令”内容的领事裁判权条款,就从来不是互惠的,中国人在美国并不享受相同的特权。
最后,依据现有照会中英文本,顾圣使团译者的翻译活动频繁、翻译质量总体良好。在构建早期中美外交关系上他们不仅为中美交涉排除了语言障碍,为使团提供了优质的翻译服务,还提供了重要情报,为美国在华展开商业活动和外交立下了功劳。为顾圣使团效力半年之久的经历,为他们各自此后在华传教势力的壮大、政治地位的确立或在汉学界地位的奠定做足了铺垫工作。
QU Wen-sheng
(SchoolofForeignStudies,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Shanghai201620,China)
[责任编辑 罗剑波]
Research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S and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f Caleb Cushing’s Mission to China in 1844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rted to pay more diplomatic attention to Asi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very first page of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Empire began in 1844 when Caleb Cushing’s Mission was sent to China. The communications, or public dispatches, between Commissioner Caleb Cushing,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of United States to the Court of Taou Kuang, and Ching, acting Governor General of Kuang Tung and Kuang Se, focused on the Cushing’s plan of proceeding to Peking. There was a war of words between Caleb Cushing and Ching, who declined the Mission’s proposal and deliberately or negligently committed errors occasionally. Tsiyeng chose to tenderly cherish men from afar, and Caleb Cushing prevailed over Tsiyeng, who was the opposing sid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nd conflicts. This research article provides an in-depth description of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public dispatches between China and US before and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Wang-Hiya.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show that Peter Parker, medical missionary and the Joint Chinese Secretary to Legation in Macau, did most of the translation jobs,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in the second place, and S. Wells Williams in the third place. Stanislas Herniss, an attaché and an interpreter, translated a few notices and supplied relate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case of Sue Aman’s death.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s rendered by these missionaries, in particular, facilitated the communications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in Chin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Empire.
Caleb Cushing; Tsiyeng; Ching; Communications; China-United States relations; translation history
屈文生,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早期中英中美不平等条约的翻译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4BYY015)、教育部霍英东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