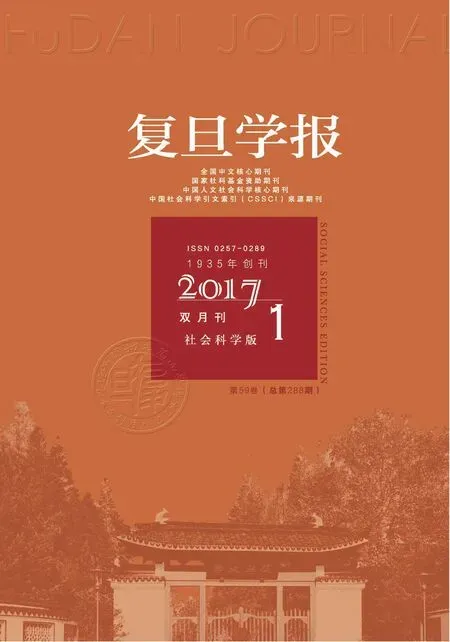《理想国》与《礼记》社会经济思想的比较
马 涛 邵 俊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MA Tao SHAO Ju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经济思想史研究
《理想国》与《礼记》社会经济思想的比较
马 涛 邵 俊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柏拉图的《理想国》和《礼记》社会经济制度的设计,是中西方古代思想家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反思的结果,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两书的经济制度的设计与经济观念进行了比较。柏拉图设想建立一个正义、共和的理想城邦,城邦内“正义”的体现就是经济上财产共有、政治上共治和社会福利的共享。《礼记》虽推崇“大同”社会,但强调“大同”只存在于远古的“五帝之时”,更推崇维护现实私有财产和个体利益的“小康”社会。柏拉图生活在雅典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比较活跃的时期,《理想国》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分工与交换,重视对商业贸易和货币的讨论,反映的就是这一经济形态的特点。中国先秦时期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故《礼记》中对诸如分工、交换、商业贸易以及货币问题的讨论很少见到,讨论最多的是土地和赋役问题,这彰显了东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研究重点的不同。柏拉图的“理想国”鼓励商业贸易,小康社会则强调国家要对市场进行严格的管制,凸现了政府主导地位和作用。《理想国》与《礼记》作为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代表,对东西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理想国》 《礼记》 社会经济思想的特点
古希腊与同时期的中国先秦都是战乱频繁、世乱年荒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复杂、尖锐,各种形式的社会经济制度理想的设计也应时而生。随着社会的进步,要求结束动荡、分裂的局面,建立统一、稳定、和谐的社会成为这一时期东西方共同的社会理想。在经济思想领域,古希腊与先秦的思想家们都顺应形势,提出了各自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设计,这集中反映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先秦儒家典籍《礼记》中,它们一起构成了人类古代社会经济理想的“双璧”。考察《理想国》和《礼记》反映出的社会制度设计,不难发现其中既有许多相近成分,也因历史传统和时代背景的不同又有着诸多差异,这些差异一直影响到之后东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道路。
对于《理想国》和《礼记》,以往的研究多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儒家的政治哲学,代表论文有胡伟希:《作为政治哲学的儒家社会乌托邦——兼对〈礼记·礼运〉的分析》*胡伟希:《作为政治哲学的儒家社会乌托邦——兼对〈礼记·礼运〉的分析》,《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诸多学者对《理想国》与《礼记·礼运》之乌托邦社会理想进行比较研究,代表论文有张海燕:《柏拉图〈理想国〉与〈礼记·礼运〉的乌托邦思想比较研究》、黄小晏:《中西早期和谐观的比较研究——以〈礼记〉“大同社会”与柏拉图“理想国”为中心的考察》、杨晓林:《理想国、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论柏拉图和孔子的政治理想》、刘丹枕:《论柏拉图〈理想国〉的蓝图——兼与孔子的德治思想比较》、朱清华:《本体论的差异——柏拉图的哲人王与先秦圣王的比较》*张海燕:《柏拉图〈理想国〉与〈礼记·礼运〉的乌托邦思想比较研究》,《河北学刊》1994年第5期;黄小晏:《中西早期和谐观的比较研究——以〈礼记〉“大同社会”与柏拉图“理想国”为中心的考察》,《理论学刊》2008年第5期;杨晓林:《理想国、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论柏拉图和孔子的政治理想》,《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社会科学专辑”;刘丹枕:《论柏拉图〈理想国〉的蓝图——兼与孔子的德治思想比较》,《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朱清华:《本体论的差异——柏拉图的哲人王与先秦圣王的比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这些论文正如题目所突显的那样,主要是探讨了《理想国》与《礼记·礼运》的德治思想、正义思想以及治国理念,主要观点是:《理想国》与《礼记·礼运》都是在批判现实的改革冲动中作出的理想化设计,都强调社会内部的有序是维持和谐状态的基础。但因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的不同,《礼记》推崇“德治”,主张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的和谐社会,而《理想国》则主张“智治”,强调哲学家治国,主张建立神本主义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也有的论文就《理想国》与《礼记·礼运》的正义观进行了比较。*参见王菁菁:《柏拉图与孔子的正义观:比较与启示》,《行政与法》2013年第6期。但从经济思想特点的角度对《理想国》和《礼记》的比较研究尚未见到。本文研究的主旨在于试图弥补这一欠缺,通过对《理想国》与《礼记》社会经济思想特点的比较,彰显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
一、《理想国》和《礼记》社会经济制度设计的比较
柏拉图认为希腊城邦之所以陷入混乱,与财产私有作为追求的目标有关。他认为私有财产和家庭容易养成人们利己和贪欲之心,从而引发社会的矛盾和纷争。柏拉图设想建立一个正义、共和的理想城邦,城邦内的经济安排都要服从于“正义”这一原则。城邦内“正义”的体现就是经济上财产共有、政治上的共治和社会福利的共享。城邦的治理者和护卫者(即哲学王和护卫国家的战士)因是由金子和银子铸造,所以应实行共产制,以德性来节制自己的私欲。国家的管理者不应该拥有私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城邦的正义。对管理者而言,应改由国家每年提供生活费用:“首先,任何人都不能拥有任何私人财产,除非那是完全必要的东西;其次,任何人都不能有这样的住房和仓库,大家想进而不能进;至于生活必需品,数量根据这些节制又勇敢的战场竞争者的需要,按规定,他们将相应地从其他城民那里以工资形式领取,作为保卫城邦的报酬,定额就这么多,到了年终,既无剩余也无短缺;他们每天在一起吃饭,如同营地上的战士一样,过集体生活;金子和银子,我们对他们说,这一来自天神的神圣礼物,将永远存在于他们的灵魂中,他们并不需要人间的金银,……否则,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地产,有了房屋,有了货币,他们将会成为一批家庭管理人和农夫,而不是城邦的卫士,并且会演变成一帮充满敌意的暴君,而不是其他城民的盟友,憎恨人又被人憎恨,暗算人又被人暗算,如此度过自己的一生,害怕自己城邦中的人远远超过害怕外来的敌人,此时,他们和其余的城邦都已跑到了崩溃的边缘。”*柏拉图著,王杨译注:《理想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28、180、190页。柏拉图的 “理想国”强调财产共有制,为防止私人感情妨碍公共精神之建立,还主张平时三餐就餐于公共食堂,实行共妻共子:“所有这些妇女必须属于所有这些男人共有,任何一个女性不得和任何男人单独同居;她们的孩子同样属于共有,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柏拉图著,王杨译注:《理想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28、180、190页。强调只有财产共有才能保持统治者人性的纯洁和社会各等级地位的稳定。统治者成员的一切财产共有,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纠纷了。他相信,金钱乃万恶之源,没有了家庭,取消了私有财产,生活就会“非常幸福,胜过奥林匹克冠军们所过的那种幸福生活”。*柏拉图著,王杨译注:《理想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28、180、190页。
柏拉图提出城邦正义的体现是财产共有与当时斯巴达城邦的经济财产制度有关。当时的斯巴达,除奴隶外,所有的公民都生活在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下。吃饭实行共餐制,禁止货币和金银流通。斯巴达人认为金银是万恶之源,消灭了金银货币,人们也就不能聚敛财富了,贪婪的人性也会淡化,所有的罪恶也都会远离斯巴达。斯巴达人认为社会财产公有了,男女的结合也可以做到是出自爱的需要而非私人的占有欲。在柏拉图的眼里,如同斯巴达人一样,世俗的金银被视为罪恶之源,私有制容易加剧私欲的泛滥和纷争,城邦和城邦之间的战争将难以避免。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柏拉图才推崇公共食堂共餐制。共餐制是当时斯巴达城邦中的一种制度,斯巴达人希望通过这一制度消除人们对财富的欲望。罗素就认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许多规定,“实际上是在斯巴达已经实现过了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60页。
在“理想国”中,社会各等级的分工有所不同。由手工业者、商人、农民组成的生产者等级专门从事经济活动;第二个等级的战士平时训练,战时保卫城邦的安全;哲学王是城邦的最高统治等级,他们负责管理城邦。财产共有仅适应于城邦的统治阶层,生产阶层则因给城邦提供了一切物质生活资料,可拥有私有私产,但也要有所限制,他们的私有财产还可以在市场上按规定的契约进行交换。奴隶不是公民,处在三个等级之外,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理想国”里有市场存在,自然也就有私人财产的买卖和商人的经商活动。柏拉图之所以不允许第一和第二等级的上层统治阶层拥有私人财产是因为他们处在社会管理者的地位,若拥有私有财产会败坏他们的道德素质;之所以允许生产者阶层持有一定的私人财产是为了弥补他们不能从事城邦管理的缺憾,鼓励他们努力从事生产活动。柏拉图认为城邦的正义就是城邦内的各个阶层各安其位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和谐相处,大家在尽心尽力地努力工作的同时也就增加了社会上他人的福利。
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提出的社会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的“天下”指人间社会,“公”可理解为公正、公平。《礼运》是《礼记》第九篇,孙希旦注曰:“言礼之运行也。”*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81页。该篇开头就借用孔子之口说道:“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郑玄注 “大道之行也” 曰:“谓五帝之时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23页。“五帝之时”是指夏以前的原始部落时期,即儒家所称的尧舜时代,此时的社会特点是“天下为公”,社会管理者由公众选举产生,政治事务由有德有才的人来担任,群体内部讲究忠信和睦,把道德教化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它要达到的社会理想是:价值观念上人们把财富(“货”)视作公共财物来使用,“恶其弃于地”但不必“藏于己”;人们歌颂劳动,以力“不出于身”为可恶,但出力不是为了自己;劳动不是个人谋生或谋利的手段,而是人们为社会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社会则保障每个人“壮有所用”,即保障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就业并充分发挥其才能。在“大同”社会里人们之间相互关爱,社会承担了对丧失了劳动力的老人和矜、寡、孤、独、废、疾者以赡养照顾,对幼小未成年人抚养的公共事务。孔子盛赞 “大同”之世“天下为公”,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大同”是一个社会风俗美善与百姓安居乐业的世界,社会公道、公平,群体内部忠信和睦,人际关系上呈现仁爱之心。这是儒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思想的发挥。
《礼记》强调“大同”社会只存在于远古的“五帝之时”,与现实无缘,它更推崇维护私有财产和个体利益的“三代之英”的“小康”社会。“三代之英”指夏商周三代的“圣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统治的时期:“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致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礼运》虽首称大同,但讲大同的只有一小段文字,绝大篇幅讲的都是小康,阐述小康之世制礼作乐的意义。在“小康”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占据着支配地位,价值观念上强调“货力为己”的个人本位,家庭是占有私有财产的单位,社会特征则是“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实行宗法世袭制,人“各亲其子,各子其子”,重家庭亲情,家庭和社会的界线明显。这种家庭宗法关系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则是“大人世及”的君主及贵族世袭制。“货力为己”反映了财产的私有状况。在私有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必然会出现矛盾和斗争,因而社会管理需要通过礼制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礼就成了治世之本。孔子通过“大同”、“小康”将人类社会自古至今的发展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明确概括出这两个阶段在经济、政治、社会组织以及道德习俗等方面的不同。“货力为己”不但在社会内部产生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在外部也必然会引发掠夺战争,于是“城郭沟池以为固”,“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国家也就成了对外进行侵伐或防御的暴力工具。“小康”社会因为存在着私利、争夺、冲突和战争,国家就必须实行一套有效的控制、调节制度,这就是 “礼”。在《礼运》的作者看来,“大同”社会虽然尽善尽美但已远离,“小康”虽不够十分完美但却使人感到亲切、现实。这就与《理想国》推崇经济上财产共有、政治上的共治和社会福利的共享的制度设计有了很大的不同。
二、《理想国》与《礼记》中经济形态与经济观念的不同
柏拉图生活在雅典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比较活跃的时期,故《理想国》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分工与交换,重视对商业贸易和货币的讨论。柏拉图认为一人而为多数之事不如专心于一事,形成合作分工。他借助苏格拉底的口说:城邦之所以产生,“依我看,是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做到自给自足,相反,每一个人(生来)需要很多东西;……正因为如此,当某人为了某事招呼另一人,而另一人为另一事又有求于第三人,因为大家需要很多的东西,于是就把许多人集中在一个居住地,作为社会成员和帮手,我们命名这种集体居住点为城邦”。*柏拉图著,王杨译注:《理想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58、58、58~59、59、60~61、61页。柏拉图把城邦的起源归因于专业化和分工,他像亚当·斯密一样阐述分工的理由:“一个人与另一人进行交换,如果他换出或换进某一东西,他肯定认为这东西比自己的好。”*柏拉图著,王杨译注:《理想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58、58、58~59、59、60~61、61页。是不是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把各自的工作贡献给公众?“例如某人是农夫,他为四个人准备粮食,在准备粮食的这份工作上消耗四倍的时间和劳力,让其他的人共享自己的劳动果实;或者,丢下这种工作不管,只用四分之一的时间为自己生产四分之一的粮食,至于其他四分之三的时间,他把一份花在准备房屋上,一份准备衣服,一份准备鞋子,和其他人没有任何相干之处,而是只靠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柏拉图著,王杨译注:《理想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58、58、58~59、59、60~61、61页。他得出结论:分工可使每人精专一业,产量可增加,物品也精美。我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无非是吃、住、穿等,这都需要由专门的生产者来生产和提供,但一个人不可能提供出足够多和足够好的东西,这就需要分工,有了诸如农夫、瓦匠和织工的存在。柏拉图还论证分工需要建立在人不同禀赋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并非完全相像,本质上,的确各不相同,事业上,这人擅长做这种工作,那人擅长做那种工作。”*柏拉图著,王杨译注:《理想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58、58、58~59、59、60~61、61页。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劳动的效率,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每个人在城邦里应该从事与自己的性格禀赋相适合的或自己的能力最擅长的工作。
“理想国”有商业贸易存在。由于人需求的多样性,一国之内缺少某一产品,需要进口,这就要有专司海外贸易的商人,而海上贸易必须用船,因此造船工和驾驶商船的舵手、船员便是不可缺少的了。不仅如此,“如果这个使者空手出发,随身不带点对方所需要的东西,只是从他们那里把这里的人所需要的东西运来,他就算空手而去”。因此,“居住在这里,人不仅有必要为自己生产出足够的物品,而且有必要为那里的人生产出种类上、数量上都为对方所需的物品。”“我们这个城邦就需要更多的农夫和其他手工业者。……还进一步需要一批经营进口和出口货物的使者。这些人就是商人,……如果商人的生意发展到海上,我们将需要另有一批数量很多、精通海上事务的人。”*柏拉图著,王杨译注:《理想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58、58、58~59、59、60~61、61页。柏拉图认为城邦之间和城邦内部既然存在着分工,就必须有专司输入和输出、从事购买和售卖的商业贸易和商人了,这就肯定了商业贸易存在的合理性。有了市场,就有交换和货币:“为了进行这样的交换,市场和钱币将由此产生。……一方面和那些需要出售某样东西的人用钱做交换,另一方面和那些需要购买某样东西的人做生意,把钱换回来。……这一需要就会为我们在这个城里造就一批商贩。”*柏拉图著,王杨译注:《理想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58、58、58~59、59、60~61、61页。专业化和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为保证分工的有效实施,就必须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由货币充当货物交换的媒介。市场交易,互通有无,可以更好地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柏拉图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提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是“为了便利交换而设计的一种‘符号’”,“他反对使用金银,他认为国内货币拿到国外是无用的……依照这个理论,货币价值原则上与制造货币的材料无关”,熊彼特据此把柏拉图作为货币名目论的“最先为人所知的倡导人”。*[美]约瑟夫·熊彼特著,朱泱等译:《经济分析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1~92页。
“理想国”中的分工也包括社会职业的分工,城邦需要“有许多人专搞音乐,还有诗人和他们的助手、史诗歌手、戏剧演员、舞蹈家”*柏拉图著,王杨译注:《理想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64、62、137页。,社会职业的分工可以使“理想国”中的人生活得更美好。柏拉图强调建立城邦的目的就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在这里,人们不仅要穿得好,还要吃得好,他们会有各种调味品,住得也好,还有很好的精神生活,如“喝着葡萄酒,头戴花冠,并唱起颂扬天神的歌曲”。*柏拉图著,王杨译注:《理想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64、62、137页。城邦内部也需要进行很好的管理。人们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也需要制定许多法律契约。这些法律契约内容包括:“关于手艺人的合同、诽谤、人身攻击、呈文上诉、召集审判官,或者,如果市场上或港口有什么税金必须征收或确定,以及一般性的市场管理、城区治安、海港税务制度以及其他所有这样的领域。”*柏拉图著,王杨译注:《理想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64、62、137页。国家管理和社会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需求。
先秦时期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故《礼记》中讨论最多的是土地和赋役问题,对诸如分工、交换、商业贸易以及货币问题的讨论很少见到,彰显了东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研究重点的不同。
《礼记》对小康社会中土地制度的设计是与政治等级相对应的,体现的是一种分封制的特点。如《王制》篇规定,天子制定爵位,公、侯、伯、子、男,共五等。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共五等。不同爵位分享不同数量的土地。天子的禄田方圆千里,公、侯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到五十里的,不能直接参加天子的朝会,附属于就近的诸侯,叫附庸。天子的三公所拥有的禄田,与公侯相当;天子卿与伯相当,天子的大夫与子男相当,天子之元士与附庸相当。普通百姓一户可授田一百亩,百亩田地以其土质肥瘠与耕者的勤惰分出等级:上等农夫足以养九口,次等农夫可养八口,三等农夫可养七口,四等农夫可养六口,下等农夫可养五口(“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凡安置民众,须根据土地的广狭确定,使得土地广狭、城邑大小、安置民众的多少配合得当,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这基本上是周制井田制的缩影。国家分九个州,每州方圆千里。每一州建立方圆百里的封国三十个,方圆七十里的封国六十个,方圆五十里的封国一百二十个,共计二百一十个。但每州的名山、大泽不分封给诸侯,属国家所有。八州,每州有二百一十个诸侯国。还有一州是天子的直辖属地。王城内分配给公卿大夫的土地是禄田,不得买卖和继承;王城外分封给诸侯的土地可以世袭(“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
《王制》篇对赋役制度也有明确设计,特点是轻徭薄赋:“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 其政策大意是:凡征用民力干活不能太累,伙食标准参照壮劳动力;家有八十岁老人,可有一个儿子不参加公家力役;九十岁,全家人都可以不参加公家力役,以方便供养老人;凡有残疾或有疾病如无人照料而无法生活的,可免一人的力役;居父母之丧,可三年不服公家力役;遇到亲属去世,可三个月不服公家力役;迁移他国,可有三个月不征力役;从其他诸侯国迁移来此居住,可一年不服力役。对农工商也有政策设计,如:“古者公田,籍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政策规定:借农户助耕公田,不再向农户征收赋税;市场,只收交易场所的地皮税而不征收所得税;关卡,只稽查货物是否合法而不收税;山林水泽只要符合季节法规,允许平民进入从事采伐渔猎;征调百姓从事无偿劳役一年之中不能超过三天。“薄赋敛”的思想在《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侧”的一段短文中有生动的体现:“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耳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残暴苛刻的赋敛政令比吃人的老虎还要可怕!《大学》篇则进一步把 “薄赋敛”的政策主张进行了理论总结,强调治国“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聚敛之臣搜刮百姓,失民心而动摇国本,比强盗危害更大。《大学》强调要用正确的理财方法,“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生之者众”、“为之者疾”强调增加社会生产,以开其源;“食之者寡”、“用之者舒”强调控制开支以节其流,轻徭薄赋,放水养鱼。它发挥有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思想,认为轻徭薄赋即可增加百姓的财富,又能得民心,在国家遇到财政困难时,百姓才愿意、也有力量支持国家。百姓手中的财富,就像放在国库中的财富一样,“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近人郭嵩焘所说的“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255页。颇得儒家理财理想之精粹。《大学》的理财论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理财问题的,所探讨的不仅是国家的财政问题(“理国财”),也包括了富民的“理民财”,强调理民财是理国财的基础,因为民富了国才能富。它所谓的“财恒足”不仅是指国库的“财恒足”,而是指国民财富和国库财用两方面的“恒足”,即荀况所说的“兼足天下”。这一观点与现代经济学中供给学派提出的通过减税富民、增加税基,最终才能增加政府的税收总量(即“拉弗曲线”)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其理论意义、现实意义都是巨大的。
小康社会中也存在市场,但强调要对其进行严格的管制,凸现的是政府主导的地位。如《王制》篇中对商业市场管制有详细的设计:“有圭璧、金璋不粥(鬻)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在上述政策中,严禁大璧玉、金饰玉器等贵重物品上市交易;国君赏赐的衣物、车骑不得买卖;宗庙祭器,不得买卖;祭祀用的牲畜,不得买卖;军用器械,不得买卖;日常器皿不合规格的,不得买卖;军用战车不合规格的,不得买卖;布帛的精粗不合规格的,幅宽不合规格的,不得买卖;色彩不合规范的服装器具,不得买卖;用锦纹、珠玉制成的器物不得买卖;日常必需的衣服、饮食不得买卖。这些禁限规定包括了三种情况:第一,对于表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物品,不许商人经营,不许市场出售,只能由官府手工业或其他官府机构生产,直接供给贵族使用;第二,民间日用的布帛、用器可以出售,但达不到质量标准的禁止出售,以维护市场的秩序;第三,对于最基本的消费品如“衣服饮食”也禁止出售,目的是为了维护自给自足的经济。这就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鼓励对内对外的商业贸易有着很大的不同。
三、简要评论
《理想国》与《礼记》在中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就西方而论,产生于16世纪的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就是柏拉图“理想国”在近代的延续和深化。在《乌托邦》一书中,作者指出,财产的私有制是造成社会罪恶产生的根源:“在私有制下,既不可能谈到正义,也不可能谈到社会安宁。每个人尽可能把一切攫取为已有,不管社会财富多么充足,这种财富落在少数人手里,其余的人们的命运就只有贫困……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就必须铲除私有制。一切局部性的改革,都只是治标的办法,不能治好社会的疾病。”*[英]托马斯·摩尔:《乌托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78页。在对私有制批判的基础上,《乌托邦》设计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即财产共有、公共消费;人人自觉劳动,以劳动带来的快乐为最大的幸福。“乌托邦”中因财产共有、公共消费,也就不需要货币了,货币只有在对外贸易中才使用。到19世纪又出现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们都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财产共有制。
《礼记》的大同社会不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近现代,同样有深远的影响。道教的《太平经》所提出的财产公有、无盗贼、无战争的理想国,东晋时代鲍敬言的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近代天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浸润着《礼记》大同思想的深厚影响。孙中山在讲民权主义时强调说:“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2页。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毛泽东。毛泽东在评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时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的人民共和国。”中国要实现大同社会只有一种可能,即“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页。
柏拉图的“理想国”仅是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空想,其中既有斯巴达社会制度的影响,也在许多地方重现了希腊上古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氏族制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柏拉图《理想国》所提出的共产社会的主张在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如伊索克拉底的《布西里士》、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都有所反映,柏拉图可能受其影响。如其中阿里斯托芬的《公民大会妇女》就特别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要求必须把一切私产收归公有,所有的土地、钱财收归公有;指责一人富别人贫、某人占有许多耕地、他人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某人役使无数奴隶,别人甚至连一个也没有,这实在是不公平的。甚至声称:“我要造成人人共享的同一的生活资料。”同时提出一系列母权制的设想,如经济由妇女管理,男女相互公有等。这个喜剧正是在柏拉图创建学园前两年第一次在雅典上演的,当时《理想国》正在酝酿之中。另外,原始公社制度离开当时不过数百年,它的许多痕迹尚保留在当时的奴隶制度中。这些可能都是柏拉图“理想国”思想的来源。上述引文转引自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8页。,其中所设计的共产共妻制既有违人性,也不具可操作性。柏拉图主张在“理想国”中消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共有(这种共有也仅限于统治者内部的共有),不仅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可能实现,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没有建立在产权清晰界定基础上的市场竞争机制,人类社会必然会出现整体的经济贫困而无法持续。取消家庭、实行共妻共子,不仅理论上荒谬,更不合人性人情。按照柏拉图的“共妻”学说,在统治者和护卫者内部家庭已经取消,女人为男人共有,因为取消了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儿童也为社会共有,婚姻与生育抚养子女不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国家的公事,应当由治理者按照法律制定一些措施,把这些事统统管起来。国家设立专门的儿童养育所,配以专职官员和保姆。柏拉图从追求国家至善的角度来论证了妇女、儿童公有的合理性:一是它有利于优生,以保证护卫者在精神和体质上都永远成为公民中的优秀分子,而且要一代强似一代;二是它有利于城邦的团结,认为实行了财产、妻子、子女的公有制度,就不会有“我的”与“非我的”之分,国家也就不会陷入分裂之害了。在共有制的社会里,护卫者既不用谋取一家私利而操劳,也将摆脱一切罪恶的羁绊,如争执诉讼、结党营私等。这些主张显然仅是产生于哲学家头脑中的空想产物,完全忽略了人性的多面性和情感的丰富性,是不现实的。在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已经消亡,母权制已经让位于父权制,两性关系上早已脱离了杂交、群婚、对偶婚阶段,建立了一夫一妻制文明社会的时代,实行共妻制是一种历史文明的倒退。柏拉图晚年所撰写的《法律篇》中财产共有思想有所改变,他虽然认为最好的社会和最好的法律应该是“‘朋友之间真诚地共享财产’最大限度地普及到整个城邦”,妇女、孩子、财产全是公有的,个人私物应从生活中消失,但他承认这很难实现:“现在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一个共妻、共儿童和共产的社会)是否事实上在今天的某个地方存在着,或者将来什么时候会存在。”*[古希腊]柏拉图著,张智仁、何勤华译:《法律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0、148、153、152、156页。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一个大大降低理想程度的“次优”国的建议。在“次优”国里,国家把“房屋和土地分成相同的份数”分配给公民,“在这些份数中,土地和房屋应该分配得尽可能相等。”*[古希腊]柏拉图著,张智仁、何勤华译:《法律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0、148、153、152、156页。允许私人占有和继承财产,容许奴隶制的存在,因为生产活动要由奴隶来承担。也允许人们“占有供日常交易用的铸币。这是一个人几乎无法避免的,因为他要与做工的人和其他所有必不可少的人保持往来(我们必须付工钱给奴隶和那些为钱而工作的外国人)。”*[古希腊]柏拉图著,张智仁、何勤华译:《法律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0、148、153、152、156页。土地分配后不允许变动或进行买卖,“任何买卖他所分配的土地或房屋,他就应该受到与罪行相应的惩罚。”*[古希腊]柏拉图著,张智仁、何勤华译:《法律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0、148、153、152、156页。立法者要确定贫富的限制,避免使人过穷或过富。公民的财产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可按财富占有的多少分四个等级,依次为最低财富的四倍、三倍和两倍,如果有人超过这个份额就应将多余的部分交还城邦,不然便要受到处罚。*[古希腊]柏拉图著,张智仁、何勤华译:《法律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0、148、153、152、156页。禁止公民从事贸易、手工业和放债活动,这些活动是由暂时居住于城市中的异邦人承担的。允许公民各有妻室,在婚姻问题上也应考虑城邦的利益,最好是富人和穷人结婚。如果富人只和富人结婚,整个城邦居民在财产和地位上便不相等了,但法律对此只能建议,不能强迫。显然,在柏拉图的“次优”国里,已是一个财产平均分配的类似《礼记》的“小康”社会。
在儒家的理想社会中,秉持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倾向,“天下为公”,“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是包括全社会成员的(在“理想国”中共产主张仅限于统治阶级内部,被统治阶级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货”是财富,“恶其弃于地”说明大同社会里的人对生产成果和社会财富十分关心和爱护,“不必藏于己”又蕴含着社会财富应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奉献精神。“大同”社会也讲“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幼有所养”,它是以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强调人要“亲其亲”、“子其子”,只是“不独”而已。“男有分,女有归”,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血缘关系分得清清楚楚,与柏拉图的“共妻”论相比更符合人性和人情。“大同”社会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不存在“共妻”“兽性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个人融化于集体之中,对所有社会成员的一视同仁、友爱相处。“大同”社会推崇天下为公的贤人政治、博施济众的仁爱平等、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大公无私的财富观念和积极奉献的劳动态度。“小康”社会则反映了周制分封制的特点,强调社会财富的私有产权和家庭的存在,注重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调控地位,讲究人伦道德的礼仪、太平安宁的社会秩序,这一文化观念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迥然有别于西方的中国道路。
MA Tao SHAO Jun
(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责任编辑 吕晓刚]
The Comparison ofTheRepublicaandTheBookofRites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s
The desig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in Plato’sTheRepublicaandTheBookofRiteswere the reflections on the reality of social turbulence by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thinkers respectively, both of which ha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human thought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esig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in the two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conomic thoughts. Plato envision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 with justice and republic, in which the justice meant the sharing of property, democracy and the sharing of welfare.TheBookofRitesadvocated a society of universal harmony. However, it stressed that such a society only existed in the age of the Five Emperors, and was unreliable in modern society.TheBookofRitesgave more support to a well-off societ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Since Plato lived in a period when commodity economy and foreign trade in Athens were active,TheRepublicaemphasize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exchange in the economy and the discussion of commercial trade and the currency. Because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agriculture-based natural economy before the Qin Dynasty,TheBookofRitesfocused on land, tax and corvee issues instead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exchange, commercial trades and currency issues.TheRepublicaencouraged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s whereas a well-off society emphasized that the state should strictly control the market, highlight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two works,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s, would continue to have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astern and Western social-economic formation.
TheRepublica;theBookofRites;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s
马 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邵 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经济思想的起源:古希腊与中国先秦经济思想的比较”(项目批准号:13YJA790084)的中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