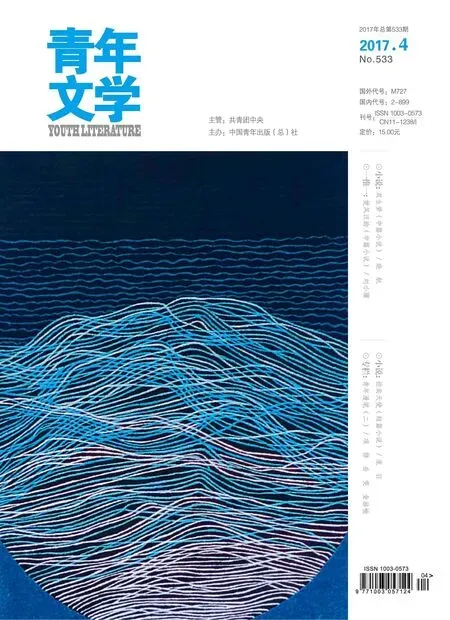迷雾中的爱情
⊙ 文 / 欧阳德彬
迷雾中的爱情
⊙ 文 / 欧阳德彬
欧阳德彬:生于一九八六年,文学硕士。在《钟山》《山花》《香港作家》等刊发表小说近百万字。著有散文集《城市边缘的漫步》。现居深圳。
一
张潮乘高铁从鸟城到萍水,受到东道主的礼遇,美食与美景招待,这全托同行的大人物们的福。他也曾背着帆布双肩包独自四处游荡,找廉价的路边摊填饱肚子,边狼吞虎咽边迎着陌生人敌意的目光,惶惶若丧家之犬,那就是另一番光景了。这几年,他待在鸟城一间出租房里画地为牢埋头写作,终日与回忆与想象相伴,一心想成为小说家,日子单调而充实,很少出远门。翔哥说偶尔出去见见世面,对写作大有好处,何况同行的都是鸟城文化界的名流。那几位大人物,张潮以前在一些文化场合见过,他们是台上的嘉宾,他是台下的听众。年龄差距较大,总感到拘谨,即使面对面也不敢放开交谈,也难找到共同话题。一行十余人,简直是中老年团,他年纪最小。几年前,他通过考研躲进校园,一毕业,又不得不离开,却发现自己深中文学之毒,平时除了写作,什么工作也不想干。
每次有随团公费出游的机会,翔哥总设法带上张潮,在鸟城始发的高铁上,坐在前排的他还偶尔转过头来传授超越平庸写作的要诀,顺便递过来一把黑皮花生。张潮觉得,如果没有遇见翔哥,自己不可能在生活成本极高的鸟城待下来。据说每年都有几十万人在鸟城混不下去了,逃到老家去,再也不回来。鸟城,不是谁想待就能待的地方。
张潮这个年纪,在车上坐久了就觉得无聊,随身携带的那本日本小说也没趣味,便东瞅瞅西望望,看看有没有养眼的年轻姑娘。同排靠窗坐着一名捧读书本的姑娘,戴着蓝色口罩和盖住耳朵的大耳机,给他一种神秘感,唤起他一睹真容的欲望。南国的夏天戴着口罩,这样的装扮,不是很奇怪吗?因为与她隔着一条过道,还有一名喋喋不休讲子女考试成绩的大叔,要与她搭讪不大方便。临近下车,张潮才加到她的微信。她说她叫彦洁,她家就在他们要去的萍水学院,父母是那里的老师。如果以后有时间,可以带张潮在校园里转转。
张潮眼看着接近而立之年,过了寻求艳遇随便浪荡的年纪,更感兴趣的不过是陌生人的生活罢了,那种自己未曾体验过的生活。她说她在鸟城一家航空公司上班,前天飞行箱的搭扣弹伤了指甲,感觉一种生活结束了。出于写小说的职业敏感,张潮意识到她的这句话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述,便一心想写一篇空姐题材的小说。那些拥有别样生活的人,总能唤起他难以抑制的了解的渴望。
鸟城到萍水也就是四个小时的车程。高铁速度确实了得,只是盒饭价钱高昂且难以下咽,简直是公开抢劫。他们这才聊了一会儿,还没切入正题,就到站了。她左手拎着提包,右手牵着飞行箱。他把她遗落在座位上的手机递给她,说现在手机比行李还重要呢。她笑了笑,就下车朝不同的出站口走了。

⊙ 李瑶瑶·你好,鸵鸟
出了萍水车站,考斯特中巴已在雨中等候,这也托大人物们的福。大人物都是这样,走到哪里都有人盛情款待,不用自己掏钱。张潮紧了紧帆布双肩包的带子,抬头望了一眼水雾蒙蒙的夜空。翔哥像是窥破了他的心思,对他说,你以后也会成为大人物的,只要你不停地写下去。不知什么缘故,张潮想起自己在鸟城城中村租住的狭窄单间和简易书桌上穿行的蟑螂,感觉自己永远成不了大人物,一辈子只能给大人物拎包。
翔哥总说,在鸟城待久了,到哪里都不习惯。夜幕下的萍水没有鸟城的花样霓虹,到处墨黑的感觉,只有明亮的车灯穿透雨帘,给这座三线小城增添一抹亮色。酒店准备了丰盛夜宵,当地特产红糖米酒已经温热,客套话连篇的官方接待拉开序幕。张潮在等待,等待酒酣脑热之际偶然迸出的更加真实的言语。可惜,东道主酒桌素养很高,口风很紧,中规中矩。倒是同行的大人物们尽情戏谑,沉浸在鲜花和掌声的海洋,如同盖茨比一样在自己的派对上逍遥风光。
夜宵后,张潮独自待在宽敞豪华的酒店房间,想着如果彦洁在就好了,那样的话,可以干些更有趣的事。他拉开落地窗帘,外面是雾气笼罩下的一片湖泊,蛙鸣声中更显得寂寥。
第二天到萍水学院参加项目合作仪式,通往图书馆学术报告厅的水泥路铺上了红地毯,两侧站着迎宾小姐,殷红横幅上写着老套的“热烈欢迎鸟城领导莅临指导工作”。报告厅内空气有些憋闷,会上的陈词滥调让他窒息。大人物们真是了不得,碰见官员聊文学,碰见作家聊政治,总是显得高人一筹。他隐约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圈子的局外人,便中途溜出,到校园闲逛。
校园里夏雨绵绵、冷冷清清,学生衣着打扮土里土气,一群学生吵吵闹闹的,在玩电视娱乐节目上流行的“撕名牌”游戏,虚掷着青春。他给彦洁发了微信,说自己就在萍水学院的校园里。她回了微信,说她打完止痛针到校园找他。校园里没什么景致,连咖啡馆也没有,又不知从哪里升起一阵水雾,显得空旷荒凉。雨渐稠密,找了个屋檐避雨。不远处的池塘边,两名个头不高挺着肚腩的中年男人正在钓鱼。他的心情有些低落,此时唯一能让他开心的事,就是她来。
他想着她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她到来时的穿着、表情、走路的姿势,雨伞上的蕾丝和花饰。等了一会儿,她还没有来,倒是等来了那个钓鱼的中年男人。中年男人走过来,命令他去给他钓鱼的朋友打伞。张潮说自己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你另请高明吧。他猜他应该是一位校领导,平时就是这样使唤学生的,居高临下的架势惹人厌恶。在官本位的国度,这不足为奇,小人物的尊严时时遭受践踏。难道自己看着就像个给人打伞的小人物?中年男人和他朋友收拾了渔具,钻进一辆黑色别克轿车,在一阵刺鼻的尾气中走了。张潮望着车尾,心里一个劲地咒骂。
她来了,举着一把没有花饰的黑伞,虽然戴着口罩,但也能从精致的眉眼和细腻的脖颈看出是一名秀气的姑娘。
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了,你肯定有公务要忙。你们这些大人物,接待规格就是不一样,听说我们市宣传部门的领导也来了。她的笑声透过口罩传出来。
张潮想,她如果没戴口罩,就能看见她迷人的笑容。她的眼睛很大,黑葡萄一样。在他的经验里,有这样一双眸子的姑娘,肯定是美人。她好像读懂了他的心思,赶忙说自己的牙龈肿痛还没有好,最近只能戴着口罩见人啦。我在鸟城的工作,整天飞来飞去,都是不规律的作息给害的。
我以前总觉得空姐是光鲜的职业,鸟儿一样在高空飞翔。那种感觉真棒!最重要的是,空姐都很美。
你怎么没去开会?她避开他的奉承。
领导讲话实在无聊,报告厅空气也憋闷。他答。
不去不怕惹单位的领导不高兴?他问。
不怕。我没有单位,也没有那些束缚。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混在他们当中罢了。对,一个小人物,混在一群大人物中间。
才不信,那个团队里都是大人物。开会时桌前都摆着桌签,看起来真是不得了。
他们如果是鸟城里的大鹏,我就是榕树里看不见的麻雀。
她被逗乐了,黑色的眸子注视着他,就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他感觉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到亭子里躲雨的,除了张潮和彦洁,还有蚊虫。她说她脖子上被虫子咬了一口,也不知是什么虫子,疼得厉害,她的血型最招蚊虫了。她轻轻扯着一端衣领让他看。他果然在她白皙的脖颈上看到一个蚊虫留下的黑点,周围一片绯红。他拿出双肩包里瓶装的利比滴,倒在拇指肚上,涂在那个黑点上。
雨天水雾弥漫,不远处半山坡上的竹林云遮雾罩,像是仙境。迷雾渐渐从山腰蔓延下来,包围了池塘、树木和屋檐下避雨的人。那雾气是一种微妙的情愫,缠绕着这对萍水相逢的男女。
你那天在高铁上读的是什么书?张潮问。毕业后的半年来,他靠给出版社写书评赚取润笔费过活。
东野圭吾的奇幻温情小说《解忧杂货铺》。
你也有很多忧愁?
是啊。工作上的,感情上的,真是发愁。我这次休假回家,牙龈肿了,回去要打针,也顺便调整一下心情。她说。
嗯,大概生活在鸟城的人,没有不烦恼的。
在鸟城的时候,我不开心时就去鸟城大学的操场上跑步,那是我宿舍周边唯一的一片开阔地,穿过学府天桥就到了。她说。
呀,我天天经过学府天桥,可惜没遇见你。
遇见又能怎样,也不过是陌生人。
是啊,鸟城真是奇怪的地方,碰见了也认识不了。没想到能在离开鸟城的高铁上结识。
张潮口袋里的手机响了,翔哥发来微信,说是仪式快结束了,要坐中巴回酒店,下午去参观当地的风景名胜。必须跟团走,这是集体出游的不便处。他跟她告别,心里有种说不清的不舍。跟她相处的片刻,仿佛乌云凝结成了石头,夏雨也慢了下来。对,她总是戴着天蓝色口罩,在高铁上就戴着,还没看到她不戴口罩的样子,只能等回到鸟城再约了。
回到鸟城,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他问。
当然可以,如果我没在上班的话。她眼睛里满是笑意,又带着一丝挑衅。
下午横穿孽龙洞,还有些趣味,毕竟这是张潮第一次钻进溶洞。几位自诩钻洞无数的大人物对溶洞不感兴趣,找茶馆消遣去了。传说古代此洞住着一条孽龙,兴风作浪为害一方,后被当地道士持剑降伏。不知是真的有此迷人传说,还是因旅游开发杜撰。溶洞很深,要走三四公里才能从另一个洞口出来,湿答答的岩壁按照各自的节奏滴水,姿态各异的钟乳石随时准备敲打游人的脑袋。每过一个转角,都另有景致,有时通道狭窄,仅能弓腰前行,有时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中国古代志怪典籍常有提及,道家修仙多选择深山岩洞,武侠小说中也难免洞中觅得绝世秘籍从此称霸武林的套路。洞中灯光下弥漫的蒙蒙水雾,倒像是仙气。
从溶洞出来,大家去爬山,小雨依旧连绵,只好穿上东道主精心准备的塑料雨披。几位生性洒脱的大人物,不想被雨具束缚,径自漫步雨中,竹林七贤般谈笑自若。翔哥花了两块钱买了根油光水滑的竹棍,辅助爬山。虽坐了高空缆车,也还有很远的石阶要爬,凌绝顶殊为不易。在山脚坐上大巴返程时,有摊贩索要竹棍,原来要反复出售,怪不得磨得油光水滑。翔哥太喜欢那根竹棍,准备带回鸟城去。他就这样,衣冠楚楚出行,丐帮帮主一样归来。
那天晚上,没想到彦洁发微信问他还能不能再溜出来。他说当然可以,你也可以来我房间,迎宾馆某某房。当然,这后半句是玩笑话,谁也不会当真。他想,拇指肚按着她的脖颈的一秒钟,已经是最亲密的动作了。
二
在鸟城的中心,那个门口与楼下都有保安把守的高档小区,伫立着几十栋高层住宅,翔哥独自住在其中一栋的顶层。他常常站在阳台上,遥望海湾对岸建造在山腰上的城市。这时张潮拿来了厚厚一沓小说打印稿,翔哥要帮他挑选出来一些推荐给杂志发表。
翔哥对他说,你没日没夜地写,发表不出来有什么用呢。翔哥退休后,眼睛害了玻璃体浑浊的病,不能看很多文字,这会儿他坐在阳台上的帆布扶手椅上,皱着眉头翻读着张潮——这名说话没大没小的学生的习作。翔哥记得有次聚餐时张潮对他说,我今后不称呼你老师了,称呼你翔哥,这样显得你年轻,显得我老成。
张潮站在翔哥经常叉腰站立的阳台上,遥望远方,隐约可见海湾对岸建造在山腰上的城市。当他俯身注视楼下火柴盒般的低矮建筑时,忽然冒出一种奇怪的念头:何不纵身一跃,沉入鸟城永恒的虚空里?这个念头让他恐惧又着迷,不由得后退几步,坐到翔哥扶手椅旁边的沙发上。
在鸟城的这几年,张潮租来的住所从来不会高于五层。因为他总是担心,那些单薄的摩天大厦会不会在鸟城夏日的狂风中倒掉?如果停电或电梯失灵怎样逃走?这些奇奇怪怪的念头困扰着他。当他住在城中村低矮的砖石民房中,才可得到暂时的安宁,就像一只躲进地下的土拨鼠。这种嗜好就是卑微出身的铁证。
这几篇可以投给杂志。剩下的就当是练笔吧。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废稿写了两抽屉。翔哥把文稿分拣成了十字交叉放置的两摞,上面较薄的那摞是他觉得可以拿出去发表的小说。张潮注视着他烟灰白的头发,恨不得把自己无聊漫长的岁月分给他一些。如果不是结识他,自己的生活肯定更为不堪。
张潮第一次见到翔哥,鸟城尚未散去春寒,雨落在脸上,比北方的雪还凉。他在绿皮火车低等车厢蜷缩了两天一夜,才从北方来到鸟城。他站在鸟城大学教学楼后面一棵巨大的榕树下,等待翔哥的到来。大榕树的根须瀑布一样垂下。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那种奇怪的树木。他无心观赏亚热带风光,心里踌躇不安,张望着教学楼门口。翔哥在短信里说他正在教学楼开会,让张潮在门口等他。张潮不知道这位在鸟城大学中文系当导师的前辈作家肯不肯接纳他,允不允许他这个逃往南方冒昧求教的文学青年旁听。
没多久,果然见一个清瘦矍铄的身影在教学楼门口闪现。张潮还没反应过来,翔哥朝他挥了挥胳膊,示意跟他走。走近了,才看清他面目清俊,看起来有些严肃。张潮那时还没意识到,面前的这位作家,将影响自己的文学和命运。那天他请张潮到教工餐厅吃了顿饭,介绍了两名研究生跟他认识,其中就有林。第二天,翔哥帮他开了证明,填了表格,办了一张鸟城大学的校园卡,这样他就可以凭卡到食堂吃饭和进图书馆看书。张潮在学校旁边的小区里租了一个房东原本用于储物的小单间。那个单间太小了,放不下一张标准的单人床,干脆直接睡在凉席上。
那年秋天,林说有个同学不住宿舍,你可以帮他交上住宿费,搬到学生宿舍去,可以节省不少房租。有一天,在宿舍楼下的小饭馆里,两瓶青岛啤酒下肚,张潮问隔壁宿舍的林,为什么舍友嘲笑我,说我干吗不到鸟城郊区随便找个工厂在流水线打工,偏偏赖在学院里?张潮眼前浮现出舍友傲慢的神情,那个身材矮小、颧骨高耸的南方人,若是打架的话,经不起一拳头。
林坦诚地回答,因为我们都是研究生,你是旁听生。
张潮说,他不见得读过很多书,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学作品,有什么资格嘲笑我?
林说,因为他是中文系研究生。你是旁听生。
张潮说,研究生好考吗?
林说,只要把教科书死记硬背,狗都能考上。
一个暴雨之夜,张潮背着书包顶着黑伞从自习室返回宿舍。他穿过学府天桥,踏上一条树木茂密的小径。簕杜鹃攀缘在路两边的围墙上,在暴雨中剧烈挥舞,撒下一地残红,排列成神秘的图形,随雨水漂流。他碰到一只被淋湿的猫,它走路的姿势像一只老山羊。他穿过小径,走到马路上的时候,险些被藏身水下的道牙绊倒。一辆汽车擦身而过,溅起飞扬跋扈的污水。他看到丧生车轮下的雨伞,裸露着肋骨半浸在水中,如同死去的蝙蝠。
他绕过一棵棵光滑颀长、留着爆炸头的怪树,步履凌乱,神情慌张。封堵一切的雨帘告诉他,他的生活没有出路,除了去打工,或者做给人代笔的小丑,而考研、重新成为一名学生,便是对那种生活的反抗。铁栅栏里的一棵凤凰木挥舞着高高在上的枝叶,它从来不会在农人的院落里驻足。他觉得,杨树和槐树才属于种植粮食的人,以及生活支离破碎的流亡者。
张潮前前后后考了三次,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年,翔哥就退休了。
年轻人,该找个女朋友啊。翔哥的催促把他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主要是害怕麻烦,影响我写作。再说了,我还没写出名堂来。张潮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个问题他早考虑过多次,答案成竹在胸。
你不也是一个人过日子?张潮想这样反问,却没说出口。老年人的感情,复杂到难以捉摸的地步。
我跟你不一样,你还年轻。翔哥说。
张潮想起自己最近的一次恋爱,他在她的梳妆盒里放了三百块钱,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觉得蜷缩在逼仄的出租屋里取暖,是出于一种低等生物的本能,不过是软弱的体现。所以他从不带她来自己隐秘的“藏身洞穴”,只在酒店里颠鸾倒凤。可那次,她带他去了自己的房间,整夜的纠缠,花样百出,云遮雾罩。当他第二天醒来发现她紧紧抱住自己的胳膊,就悄悄逃走了。
她很美,娇小的身材罩在宽大的纯棉睡衣里。白天的时候,她是一名公司文员,穿着白衬衣、黑裙子的工作套装,下巴上抵着文件夹,工作日总是赶最早一班地铁,准时出现在职员办公室。因为这三百块钱,他把她激怒了。你这个嫖客!活该一辈子打光棍!手机听筒里传来她愤怒的声音。
三
彦洁打开飞行箱的那一刻,锁扣弹到涂成蓝色的指甲上,一声脆响,一阵生疼。她感觉什么东西要失去了,却又想不出来是什么。那是她在鸟城航空的最后一次飞行。飞完这一次,就再也不飞了,或许,以后连飞机都不想坐。公司的宿舍还能住一个月,辞了职,她便不好意思继续住下去。同事,仅仅是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同事,不过是另一种陌生人。
接下来便是租房子找工作。鸟城到处是隔成单间的出租房,满大街都是手下有两三个职员的小老板。可她感觉自己太累了,需要人帮忙。去投奔谁呢?返程的时候是空机,她望着空荡荡的座位,在寻找一个答案。那时候,在鸟城,她想不出任何人可以投奔。现在,她休假归来,觉得自己应该联系一下那个在高铁上偶遇的男人。时间匆匆像流沙,真的来日方长吗?上次不是说好,回到鸟城就联系吗?怎么一个多月过去,还没收到他的信息。
她记得一个月前,她休假从鸟城坐高铁回萍水老家。长时间的不规律作息害得她牙龈肿痛,不得不戴上一个蓝色口罩。她喜欢蓝色,蓝天的颜色,连指甲都被赋予那种淡雅的色彩。她坐在临窗的位置,戴着罩住耳朵的大耳机听山口百惠的歌,双手托腮向外张望,窗外飘过的不再是密密麻麻的建筑丛林,而是南方乡野的绿树山峦。火车进了隧道,便什么也望不见了。她只好低头看书。邻座的中年男人转过头朝她说着什么。她摘下耳机,卡在脖子上,原来那个男人问她哪一站下。她说萍水。那个男人就显得很兴奋,说自己也在那儿下。他说他在鸟城做电子产品生意,要赶着回老家开儿子的家长会。他吹嘘自己儿子的成绩有多好,以后肯定能考个好大学,长舌老太婆一样絮絮叨叨个没完。她对这些话题不感兴趣,应答只是出于礼貌。
在跟那个男人交谈的时候,她看到了坐在过道那边的年轻男人。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色短袖,胸前有一只简笔勾勒的黑骏马。他的帆布双肩包没有放到行李架,而是搭在膝盖上,座位前的小板桌放了下来,上面竖着他正读的书。书名太小,她看不清,只看到墨绿色的封面。这时她看见他也扭头看她,只是隔着个过道和那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罢了。她没想到他会站起来找她攀谈,说自己也到萍水下,是跟着鸟城的一个团队到萍水学院开会的,原来他早就注意到她,听到了她的讲话。她惊讶地说自己家就在萍水学院,爸妈都是学校老师。他说出身那么好,干吗还要去鸟城工作。她说年轻人都想去鸟城。他转换了话题,说自己住在鸟城大学附近。她说她也住在附近,学府天桥旁边,晚上经常去学校的塑胶田径场跑步。他说他天天经过天桥从学校到出租屋去,怎么没遇见过你呢。她笑笑,说遇见了也不认识。
她还记得,他把打开着微信二维码的手机递过去,让她加他为好友,说他的微信名就是真名,到了萍水,还可能遇得到。这时,她看清了他手里的书,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
你也喜欢日本文学?她问。
嗯。石黑一雄是移民到英国的日本作家,跟奈保尔、拉什迪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他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书。
中年男人夹在中间有些不自在,主动提出换座。他便拎着双肩包坐过来。她把口罩的左端从耳上摘下,右端还挂在耳上,这样方面说话,又能遮挡因为牙龈发炎微微肿胀的脸颊。他坐在右边,照样看不见她的脸。
现在,她站在学府天桥上,望着天桥下车辆的洪流,她想着要不要主动联系他。他是怎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看样子他身边应该不会缺少女人。
天空下起了小雨,她掏出包里的遮阳伞,默默站在天桥上,意识到在鸟城走进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如此艰难。不远处的建筑施工队在挖掘海边潮湿的土地,种下更多的摩天大厦。庞大的地铁项目还在施工,越来越多的钢铁蜈蚣在城市的地下急速穿行。不知鸟城会不会许多年后坍塌,亚特兰蒂斯一样从世界上消失。迷雾渐渐升起来,萍水那天见到的一样的迷雾。天桥下窗玻璃上贴着深色贴膜的汽车悄无声息,幽灵船一样划过滨海大道,仿佛鬼域的灵柩。迷雾中的摩天大厦和打伞的路人都不再拥有重量,一点微风就可以把他们吹离地面。
他曾说鸟城是一只猎食的大鸟,追赶着他,逼他夺路奔逃。是的,那个在都市丛林中逃亡的猎人偷走了她的一部分生活,永远消失在鸟城的迷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