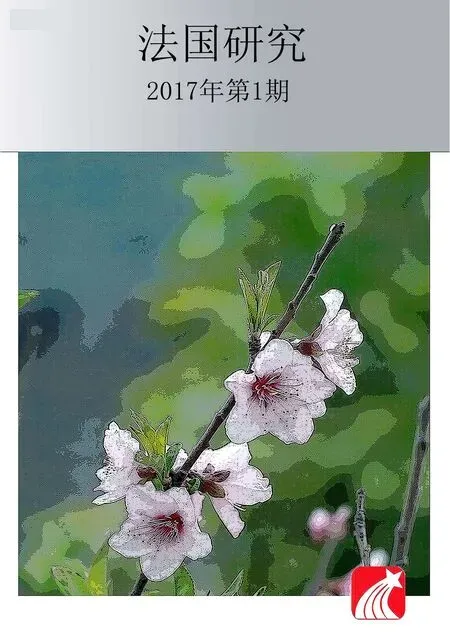波德莱尔与多多青年时期的写作
杨玉平
波德莱尔与多多青年时期的写作
杨玉平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法国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歌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波德莱尔在当代中国被视为颓废诗人,备受冷遇。1957年7月,为纪念《恶之花》初版百年,《译文》推出了波德莱尔专刊,对波德莱尔及其作品做了较全面的介绍。这期专刊对1960、1970年代的中国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多多视波德莱尔为精神导师,从此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并自称为象征主义诗人。本文以多多青年时期的写作为例,分析波德莱尔与多多之间的精神与艺术关联。
波德莱尔 《译文》 多多 影响
1991年,多多在复刊后的《今天》上发表了《1970——1978的北京地下诗坛》一文。在这篇回忆性的文字里,多多叙述了1970年代北京地下诗坛的写作状况和自己开始诗歌创作的原因。多多承认西方现代派诗歌,尤其是波德莱尔(Baudelaire)对自己的影响,不止一次提到波德莱尔在自己的诗歌道路上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我在很早就标榜我是象征主义诗人,因为我读了波德莱尔,没有波德莱尔我不会写作,所以说波德莱尔影响极大。”[1]多多:《多多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269页。后文凡出自《多多诗选》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按照多多的说法,尽管自己的诗歌风格多年来有所变化,波德莱尔对他的影响始终存在。的确,在多多的作品中,波德莱尔的影子挥之不去,而且波德莱尔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多多青年时期,即1970年代的写作出发,探寻波德莱尔与多多之间的精神与艺术关联。
一、 1957年的“波德莱尔专刊”
首先,多多是怎样读到波德莱尔的?
自1920年代波德莱尔被介绍到国内以来,这位法国诗人赢得了无数中国作家和读者的青睐,很多研究已经证实了波德莱尔与中国现代诗歌的深厚渊源。但新中国成立后,波德莱尔却被视为颓废作家的典型,备受冷遇。从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来看,这种差异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建国后,西方现代派普遍遭到排斥,波德莱尔也不例外。而且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背景下,波德莱尔“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显然没有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波德莱尔的作品在中国似乎已没有未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56年开始的“双百”运动使波德莱尔在中国的命运骤然出现转机。文学界的许多人士借此机会呼吁改变建国以来忽视西方文学的态度,要求译介更多的西方文学作品,重新构建与西方文学的联系,提高当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水平。读者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拓宽阅读范围,了解西方文学的强烈愿望。1957年7月,为纪念《恶之花》()初版一百周年,茅盾主编的《译文》发行了一期波德莱尔专刊。《译文》是当时负责介绍外国文学的唯一官方杂志。除了一帧波德莱尔版画像、《恶之花》初版里封面,专刊的主要内容包括《译文》编者按、诗人陈敬容从《恶之花》选译的九首诗、法共作家阿拉贡(Aragon)纪念波德莱尔的一篇文章(译者是沈宝基)和苏联翻译家列维克(Levik)关于波德莱尔的评论(译者是何如)。
专刊显示了《译文》编辑部对待波德莱尔的态度。编者按认为,中国读者并不了解真实的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的艺术价值在中国还远未真正揭示出来。至少,对波德莱尔的诠释是不正确的。编辑部决心否定长期以来将波德莱尔视为西方颓废派代表的结论,重建波德莱尔在中国的形象,即波德莱尔是一个历经磨难、勤奋创作的伟大诗人,理应在中国重新得到译介和研究。
50年代的阿拉贡是一位蜚声世界文坛的共产主义作家。1957年3月,阿拉贡在《法兰西文学报》()上发表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一文,向《恶之花》百年致敬。波德莱尔是阿拉贡崇拜的诗人。在这篇文章里,除去对波德莱尔诗歌艺术的热烈赞美,阿拉贡的远见卓识在于明确指出了波德莱尔对于现代诗歌的意义:波德莱尔是法国诗歌的继承人,但他摒弃了传统诗歌的美学观,为诗歌开辟了新的领地,《恶之花》蕴含着现代诗歌的未来。
与阿拉贡的文章不同,苏联批评家列维克的文章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作为波德莱尔艺术的辩护人,列维克明白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证明波德莱尔在政治上的正确性。列维克从波德莱尔的政治活动入手,指出波德莱尔是一位民主人士。而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恶之花》就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波德莱尔耽于丑恶的描写正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腐败面貌的证据。列维克还引用哥蒂埃的评论,说明波德莱尔不是颓废主义者,他的“颓废”代表着一种美学观念和一种风格。
陈敬容从《恶之花》选译的九首诗分别是(按照发表顺序):《朦胧的黎明》、《薄暮》、《天鹅》、《穷人之死》、《秋》、《仇敌》、《不灭的火炬》、《忧郁病》和《 黄昏的和歌》。陈敬容的翻译形象地展示了波德莱尔这位象征主义鼻祖的风采,给读者带去了当时诗坛程式化象征无法创造的“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
由于建国前出版过不少《恶之花》的选译本,因此,除了1957年的波德莱尔专刊,当时的读者应该也有机会看到其他一些译介波德莱尔的著作,最著名的当属戴望舒的《恶之花掇英》。这本书在1947年由怀正文化社出版,收集了戴望舒翻译的二十四首波德莱尔的诗作。而商务印书馆1971年在北京出版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专辑》属“内部发行图书”。在这本书里,波德莱尔被斥为颓废诗人,但他的主要文学观点和创作特色也得到了介绍。
二、象征主义诗人多多
为什么波德莱尔如此重要?在一次访谈中,多多将流亡与写作联系在一起,他这样描述自己觉醒的痛苦历程:“开始是无知的孩子,然后变成自觉的抵抗者,然后又从抵抗者变成流亡者。我的流亡时间应当是从1972年——我真正写作开始。”(2005:267)波德莱尔,这个现代社会的流亡者,完全符合多多当时的审美需求,让他毫无困难地进入波德莱尔的精神世界:“我真正的诗歌写作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之前也看过一些现代诗,没有这样着魔的感觉。我在《世界文学》上看到陈敬容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的9首诗,一下子把我给迷住了。”[2]刘敬文等:《多多: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载《晶报》2007-11-10。
多多说自己于1972年开始动笔写诗,并于年底拿出第一册诗集。其实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点古体诗。因此,1972年是他写新诗的开始,也是他具有真正诗歌意义的写作的开始。《无题——和波特莱尔》映证了多多与波德莱尔的关系,即波德莱尔为他指出了写作的道路和方法。在诗的开头,年轻的诗人就用极具象征意味的诗句描绘出对波德莱尔的迷恋,表明自己成为象征主义诗人的决心:“尾随着太阳绿色的光芒/又在我微妙的心里,把象征点燃:”。[3]多多:《无题——和波特莱尔》,载Julien BLAINE, éd. Poèmes et arts en Chine, Les « Non-Officiels », Revue Doc(k)s hiver 81/82, 1982, p. 85.波德莱尔的《应和》被称作象征主义宪章。多多应该读过戴望舒翻译的《应和》,但他对象征的表述更近于尼采(Nietzsche)。这一点并不奇怪。在写诗之前,多多感兴趣的是哲学,因此他对尼采并不陌生。尼采被认为是一位象征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波德莱尔的读者,尼采这样解释象征的含义:“在这里,万物爱抚你,同你交谈,奉承你:因为它们想要骑在你的背上。在这里,你也骑着每个比喻奔向每个真理。”[4][德]尼采:《尼采全集》第4卷,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87页。象征主义揭开了世界的秘密和存在于诗人与世界之间那种妙不可言的神奇感应。
附上我视觉中的一切影像
是这样深刻的与丰富的
好像许多陌生人/从他们的声音里
慢慢向我走来[5]多多:《无题——和波特莱尔》,载Julien BLAINE, éd.Poèmes et arts en Chine, Les « Non-Officiels », Revue Doc(k)s hiver 81/82, 1982, p. 85.
多多的这几句诗表现出对象征主义的深刻理解,传达了发现后的难以言传的喜悦,纲领般地确定了自己写作的原则,即象征、应和与意象。最后,他回到写作的内容,他要仿效采集“病态的花朵”的波德莱尔,创作自己的《恶之花》:“好像山谷中/那些有病的荆棘/红色的,黑色的/它们秘密开遍我的周围……”[6]同上。
三、无处不在的意象
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是象征主义最重要的写作方法。对中国诗人来说,意象是他们熟悉的写作手段。汉字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语言符号,具有独特的意象审美特征和思维特征。在一次访谈中,多多说,中华民族“天然的就是意象主义的一个民族。”(2005:271)多多的写作正是从意象开始。他在1972年写下的第一句诗,“窗户像眼睛一样睁开了”就是一个生动的意象。《无题——和波特莱尔》可以说从头至尾,皆是意象,而且色彩斑斓,构成一幅诗的画卷:“绿色的光芒”、“狂奔的野兽”、“金色的尘埃”、“有病的荆棘/红色的,黑色的”。的确,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意象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意象携带的象征意义往往具有约定俗成的内涵。在当代文学中,政治抒情诗将这一特点推向极端。承载象征功能的意象数量有限,象征意义被固定化,没有给个人创造留下任何空间。而象征主义诗歌则将意象与个人情感对应起来,具有明显的个人化色彩。另外,与波德莱尔发掘丑恶意象,从“恶”中提取美的“审丑”倾向不同,中国古典诗歌偏爱美好意象,追求“审美”。从多多的作品来看,那些无处不在的意象偏离了中国诗歌传统,更具有波德莱尔式的“恶之美”。
多多为什么要书写恶?年轻的多多具有惊人的洞察力,他从混乱而血腥的社会动荡中看到了罪恶的源头和本质。他的心灵之眼张开了。对于身处丑恶世界的诗人来说,书写恶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别无选择。书写即记录,记录恶是诗人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波德莱尔书写恶的最著名的作品当属《腐尸》。多多的抱负使他不满足于简单地模仿《腐尸》中的丑恶意象。多多对恶的理解应该更接近于列维克对《朦胧的黎明》和《薄暮》两首诗的评价。列维克认为,波德莱尔的这两首现实主义杰作描绘了现代社会的恶,波德莱尔对恶的兴趣也是《恶之花》的目的之一,即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因此,多多诗中的恶与其说是现代社会人堕落的产物,不如说是一种残酷的暴力的意识形态的结果。多多认为,“意象就具有认识能力,一切都包括在其中。”(2005:270)诗人通过一系列具有个性化内涵的意象创造了自己的象征体系,而这个体系反映了他对社会的认识。
《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1972)利用“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干燥的喉咙”、“野蛮的眼罩”、“发黑的尸体”、“肿大的鼓”、“冒烟的队伍”等意象共同制造出一种笼罩全诗的的恐怖。在《年代》中(1973),“血淋淋的犁”的意象同样表现了暴力带来的恐怖。(2005:17)多多往往不直接表现恶,而是利用阴暗病态的意象来暗示或象征恶。在他眼里,大自然受伤了:“月亮亮得像伤疤”(《大宅》);(2005:9)或者像个恶魔:“花仍在虚假地开放/凶恶的树仍在不停地摇曳 ”(《夏》);(2005:16)或者像个疯子、刽子手:“庄稼被点燃,树木被逼疯/花的世界躺满尸体”(《我记得》);(2005:44)人类也远离健康:“我看到残废在河岸上捕捉蝴蝶”(《蜜周》) 。(2005:7)总之,中华民族病了:“浮肿憔悴的民族哦/已经硬化弥留的躯体”(《无题》)。(2005:2)
波德莱尔的诗经常利用黑色作底色,制造沉重压抑的氛围。有时黑色源于时间,例如黄昏或深夜;有时源于光线,例如黑暗;有时则源于诗人恶劣的情绪。1957年的译诗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多多的诗也被黑色笼罩着。除了个别作品(如《无题——和波特莱尔》),多多的意象有一个主色调:黑色,如“发黑的尸体”(《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黑色花丛”(《日瓦格医生》)、“黑色的殡葬的天使”(《乌鸦》)。然而,黑色并不是多多诗歌中唯一的色彩。在诗人努力营造的大块黑色中,有时会闯入点点红色,与黑色形成鲜明对比。《祝福》(1973)的第一节有这样的句子:“那黑瘦的寡妇,曾把咒符绑到竹竿上/向着月亮升起的地方招摇/一条浸血的飘带散发不穷的腥气”。(2005:1)这几句诗呈现了一个可怕的场景。夜(月亮升起)和“黑瘦的寡妇”的意象铺垫了黑暗的底色。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上,侵入一片红色(浸血的飘带)。但这不是象征幸福和欢乐的红色,因为这是血的颜色,散发着死亡与恐怖的气味。在《无题和波特莱尔》中,多多宣布他“那些有病的荆棘”是“红色的,黑色的”。他的选择与波德莱尔不谋而合。在《西特尔岛之游》中,波德莱尔写道,“可是对于我,一切都是黑暗和血泊。”[7]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专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398页。
多多还有一些意象直接来自波德莱尔。在《诗人1》中,多多描绘了灵感来袭的幸福与痛苦:“披着月光,我被拥为脆弱的帝王/听凭蜂群般的句子涌来”。(2005:14)“蜂群”的意象出自《朦胧的黎明》:“这正是那种时辰:邪恶的梦好像群蜂/把熟睡在枕上的黑发少年刺痛”。[8][法]波特莱尔:《朦胧的黎明》,陈敬容译,载《译文》1957年第7期,134页。多多不仅借用了“蜂群”(群蜂)的意象,还借用了这一意象蕴含的侵略性和凶恶性。诗如“蜂群”一般无法抵挡。
四、波德莱尔式的诗歌
《玛格丽和我的旅行》(1974)这首诗的题目令人想起戴望舒翻译的波德莱尔的《邀旅》,而它的内容也的确是波德莱尔式的幻想之旅。在这首诗中,多多邀请一位名叫“玛格丽”的女子与他一起去梦想中的国度旅行。“玛格丽”不是个中国名字。文革期间,与一位外国女子或有一个外国名字的女子同行远游国外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多多出国要等到1989年)。因此,这是与一位幻想中的女子进行的一次幻想之旅。多多为什么要把自己幻想中的旅伴叫做“玛格丽”?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在波德莱尔的《秋》中,诗人在最后一句深情款款地唤出情人的名字“玛格丽”。
在《邀旅》的开头,波德莱尔向情人发出远行的邀请,语调甜蜜而热烈:
逍遥地相恋,相恋又长眠
在和你相似的家国![9][法]波特莱尔:《邀旅》,载戴望舒译《戴望舒译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28页。
而在多多诗中,同样是女子和爱情激起了诗人远行的欲望,开头那个热切的邀请仿佛接续了《秋》的最后一节:“像对太阳答应过的那样/疯狂起来吧,玛格丽:”。(2005:26)多多显然希望自己的“玛格丽”摆脱波德莱尔的“玛格丽”如“一轮秋阳”般的忧郁气质。他的“玛格丽”热情、充满活力,不是波德莱尔那一朵“苍白的雏菊”,而是远行的良伴。
波德莱尔年少时曾被迫出国旅行,后来也只去过像比利时这样的邻国。相比真正的旅行,他更耽于幻想之旅。少年远游的见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想象。为了增加旅行的诱惑,波德莱尔不倦地吟咏“那边”的美丽,他一扫平日的忧郁,用欢快的笔调描绘了一个天堂般的幻想之国的绚烂景色:
神秘的娇媚
却如隔眼泪
耀着你精灵的眼睛[10][法]波特莱尔:《邀旅》,载戴望舒译《戴望舒译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28页。
多多的写法如出一辙,他兴致勃勃地列举了他的旅行计划:
一起,到海边去
到裸体的海边去
到属于诗人的咖啡色的海边去(2005:26)
《邀旅》中第一节之后便是以副歌形式出现的两句诗:“那里,一切只是整齐和美/豪侈,平静和那欢乐迷醉。”[11]同上。副歌之后又是对异国景色的描绘,之后又是副歌,如此反复。多多的诗中虽未出现明显的副歌,但他遵循这一模式,以不断的请求间隔开对异国风光的描绘,从形式到语调都和波德莱尔在《邀旅》开头的呼唤十分相似:“肯吗?你,我的玛格丽/和我一起,到一个热情的国度去”, (2005:27) 或“跟我走吧,/玛格丽,让我们”。 (2005:27)
波德莱尔笔下“和你相似的家国”带着东方的神秘气息:
深湛的明镜,
东方的那璀璨豪华,
一切向心灵
秘密地诉陈/它们温和的家乡话[12][法]波特莱尔:《邀旅》,载戴望舒译《戴望舒译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28-129页。
而多多梦想的“热情的国度”就是传说中的东方:
我们会寻找到印度的月亮宝石
会走进一座宫殿
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在象背上,神话般移动向前……(2005:27-28)
当时,多多并未去过外国,东方诸国的神奇景色只能依靠想象。这些景色与波德莱尔描绘的景色有很多共同的元素:城市、船、落日,而且都处在现实与梦幻、真实与想象之间。
与波德莱尔的诗不同的是,多多的这首诗实际上讲述了两段旅行。在诗的第二部分,他要带玛格丽去中国乡下。多多的安排显示出诗人的爱国主义。他忘不了人民的痛苦,悲惨的现实始终萦绕在他心头,那是一个诗人熟悉的苦难世界。两段旅行形成鲜明对比,原本欢愉的想象变成悲痛的叹息。
《太阳》是阿拉贡在纪念文章中唯一完整引用的波德莱尔的诗。多多非常喜欢《太阳》。1973年,多多写了一首《致太阳》,并说《致太阳》是受《太阳》的启发写出来的。我们将两首诗比较一下,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首先,“太阳”都进入两首诗的标题,成为诗中的主角。其次,两位诗人都将“太阳”人性化了,都赞美太阳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好处。两个“太阳”都具有普世性,都具有君王风范,都拒绝等级,将爱赋予每一个生命。
在形式上,《太阳》的最后两节对《致太阳》产生了影响。沈宝基的译文中有一个“让”字句:“他让忧愁消失在天际;/……/他让最微贱的事物具有高贵的命运,”[13][法]波特莱尔:《太阳》,沈宝基译,载《译文》1957年第7期,158-159页。多多诗中反复出现了这个句式:“你让所有的孩子骑上父亲肩膀/……/你让狗跟在诗人后面流浪/ ……让我们劳动/ ……让我们信仰”。 (2005:24)
多多提到《太阳》和《致太阳》的关系,其实这首《致太阳》与波德莱尔的另一首诗,即《穷人的死》,也有明显的联系。《太阳》赞颂了太阳的美德,《穷人的死》通过穷人之口赞颂了死亡的美德。在波德莱尔笔下,死亡毫无可怖之感。相反,它给穷人的痛苦带去慰藉,鼓励他们继续生活。“死亡”被赋予与“太阳”同样的价值。
在《穷人的死》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中,穷人们用第一人称“我们”叙述。在《致太阳》中,诗人也使用第一人称“我们”。在句法方面,《致太阳》从《穷人的死》借用了一些句式。第一个是“给”字句。尽管这个句式只出现了一次(死亡给人安慰唉![14][法]波特莱尔:《穷人的死》,陈敬容译,载《译文》1957年第7期,139页。),但由于它是《穷人的死》的第一句,奠定了全诗的基调,所以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句式在《致太阳》中反复出现:“给我们家庭,给我们格言/ ……/给我们光明,给我们羞愧/ ……/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劳动/……/给我们洗礼,让我们信仰”。 (2005:24) 多多借用的另一个句式是表示肯定的“是”字句。《穷人的死》中多次出现这个句式,以确定死亡的价值:
它是神灵的光荣,美妙的谷仓,
是穷人的钱袋和他的老家乡,
是通向陌生天庭的一道门廊。[15]同上,139-140页。
在多多的诗中,也出现了这个句式:“你是上帝的大臣/……/你是灵魂的君王”。 (2005:24)
《穷人的死》和《太阳》中的某些词汇或近义词也出现在《致太阳》中,例如“死亡”、“生命/出生”、“希望”、“晚上/黑夜”、“睡眠/长睡”、“天使/上帝的大臣”、“梦境”、“神灵/上帝”、“太阳”、“孩子”、“父亲”、“国王/君王”,等。这一现象主要是三首诗之间相似的语义场造成的。
从分行的角度讲,《穷人的死》是一首十四行诗。《致太阳》虽然不是一首十四行诗,但它分四节,每行四句,4/4/4/4的分行模式与十四行诗4/4/3/3的模式十分接近。这一点也印证了多多自己的说法:“《致太阳》实际上可以说包括从分行,从形式都是比较类似波德莱尔的。”[16]梁晓明:《多多访谈》,载《中国诗刊》2006年第1期。
五、借用词汇与修辞
从写作之初,多多就刻意使用具有异域色彩和内涵的词汇。《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这首诗题目中的“干酪”对读者来说就比较新鲜,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干酪是什么东西。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当然,这些词汇主要来源于他阅读的西方书籍。他甚至奉行“拿来主义”,直接从陈敬容的译诗中拿来词汇,放进自己的作品。在《朦胧的黎明》中,“穷妇人”“垂着消瘦冰冷的乳房”,[17][法]波特莱尔:《薄暮》,陈敬容译,载《译文》1957年第7期,134页。多多的《图画展览会》中“初次见到阳光的女人”则拥有“冰冷削瘦的乳房”[18]程光炜等(编):《朦胧诗新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121页。。在《秋》中,波德莱尔写道:“爱情,在它的岗位上张着命运的弓,”[19][法]波特莱尔:《秋》,陈敬容译,载《译文》1957年第7期,140页。陈敬容的翻译虽然失掉了原作具有色情意味的暗示,但“爱情”与“弓”形成的关联还是引入注目。在《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里,多多为”弓“赋予了负面的含义,强调八月酷暑的险恶:“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 (2005:1)《朦胧的黎明》中有一句“街头灯火在晨风中摇曳”[20][法]波特莱尔:《朦胧的黎明》,陈敬容译,载《译文》1957年第7期,134页。,描绘清晨寥落的景象,多多几乎将整句搬进《无题》:“马灯在风中摇曳”, (2005:3) 暗示席卷中国的政治风暴。而《忧郁病》中的“哑默”(一群哑默的肮脏的蜘蛛[21][法]波特莱尔:《忧郁病》,陈敬容译,载《译文》1957年第7期,142页。)出现在多多的《乌鸦》中,营造了一种压抑的气氛:“是一个哑默的/剧场一样的天空”。 (2005:15)
拟人化是波德莱尔常用的一种修辞方法。波德莱尔通过将名词大写的方式来实现名词的拟人化。但汉字是象形文字,不存在大小写的差异。为了表现拟人化名词的内涵,陈敬容将需要拟人化的名词加上引号,因此她的译诗中出现了“美”(他们引导我走向“美”的大路[22][法]波特莱尔:《不灭的火炬》,陈敬容译,载《译文》1957年第7期,141页。)、“劳动”(当“劳动”在又冷又亮的天空下[23][法]波特莱尔:《天鹅》,陈敬容译,载《译文》1957年第7期,137页。)、“苏醒”(而你们歌唱“苏醒”[24][法]波特莱尔:《不灭的火炬》,陈敬容译,载《译文》1957年第7期,142页。)这样的形式。陈敬容的处理方式肯定给多多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多多似乎走得更远。在《钟为谁鸣——我问你,电报大楼》里,某些拟人化的名词有引号,有些则没引号。名词拟人化不是中文固有的修辞方法,因此多多的使用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
知识像罪人,被成群地赶进深山
只有时间在虚假的报纸后面
重复导演的思想和预言 (2005:10)
通感是中国文学固有的修辞方式,但多多笔下的通感往往和破碎、阴暗的画面联系在一起,使他的通感具有了《恶之花》的意味:“掺进紫黑色的吻里/月亮亮得像伤疤”(《大宅》);(2005:9)“天是殷红殷红的/像死前炽热的吻”(《我记得》)。(2005:43)
六、“恶魔主义”
从译介到中国的第一天起,波德莱尔就被视为恶魔诗人。他的“恶魔主义”被诠释为对既定社会制度的反抗。但到了1957年,列维克特别强调波德莱尔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竭力否认他的“恶魔主义”,认为那是:“……反对波特莱尔的官方报刊制造出来的毁谤和迫害所产生的说法的回声,那些官方报刊散布关于他的骇人听闻的不道德行为的谣言,这种谣言迎合了颓废主义者阵营中的波特莱尔信奉者,他们企图在诗人的头顶上形成一种“撒旦式的光轮”。”[25][苏]列维克:《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何如译,载《译文》1957年第7期,165页。“骇人听闻的不道德行为”、“撒旦式的光轮”,列维克恰恰指出了波德莱尔的“恶魔主义”。波德莱尔自己曾宣布,“最理想的雄性美就是撒旦——弥尔顿式的撒旦。”[26]Charles, Baudelaire.Œuvres complètes t. I. Paris : Gallimard, 1975, p.658.
多多首先用笔名宣告了自己的恶魔主义。今天叫做“多多”的诗人曾有个笔名叫“白魔”。《白魔》是英国剧作家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的代表作。韦伯斯特的悲剧情节险恶,展示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白魔》围绕女主人公维多利亚,讲述了十六世纪意大利宫廷的爱情阴谋和权力斗争。维多利亚是一个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她美若仙子,却制造谎言,酝酿谋杀,从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被作者称为“白魔”。 据知青回忆,《白魔》是当年地下读书运动的书目之一。多多选择“白魔”做笔名,很可能源于这部著作,他要给拥有美丽外表的诗歌赋予一颗黑色的灵魂。无论怎样,“白魔”——一个白色的魔鬼——明确宣示了作者的恶魔主义。
波德莱尔恶魔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颓废,他通过酗酒、吸毒、沉湎肉欲等为社会不齿的行为来表达对当时资产阶级道德的蔑视和挑衅。如果说《无题——和波特莱尔》是多多的象征主义宣言,那么《手艺 ——和玛琳娜·茨维塔耶娃》(1973)则是他的颓废主义宣言:“我写青春沦落的诗/(写不贞的诗)/写在窄长的房间中/被诗人奸污/被咖啡馆辞退街头的诗/”。 (2005:25)“沦落”、“不贞”、“奸污”都是赤裸裸的恶行。诗人的意图十分明显:他要和《恶之花》的作者一样,拒绝“把墨水和道德搅和在一起”,用“骇人听闻的不道德行为”来挑战时代的道德,实现对社会的反抗。
多多的爱情诗歌实践了他的颓废主义。在当时的主流文学中,爱情成了禁区,更别提性爱了。《蜜周》(1972)是一首带有多多自传性质的情诗,其中某些诗句大胆地描绘了男欢女爱:“你的眼睛在白天散光/像服过药一样/我,是不是太粗暴了?……再野蛮些/好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女人!”(2005:4)《诱惑》(1973)则鼓吹一种颓废的爱情观:“如果被春天欺骗/那,该怎么办?/……/那也情愿。”(2005:11)而《感情的时间》(1973-1980)中露骨的描写就更惊世骇俗了:
噢,我记得,我记得
你胸前的痣,涂错的口红
松开裙子,你在房间中走动
因害羞,而弯曲的双腿
在抵抗中,变得鲜红的乳头……[27]多多:《多多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40页。
多多的某些作品颠覆了一些圣词的象征意义。在《祝福》(1973)中,“祖国”不再是“人民”的保护者。由于迷信,她失去了独立和骄傲,惨遭抛弃,被迫流亡:“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在伦敦的公园和密支安的街头流浪。”(2005:2)在《无题》(1973)中,人民的形象是病态的,他们有一张“粗糙的脸”和一双“呻吟着的手”,(2005:2)生活在一块失去理性的“醉醺醺的土地”上,(2005:2) 感受不到任何快乐,在他们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苦难”。(2005:3) 领袖的形象被彻底庸俗化了,他“牙齿松动”,(2005:3) 打着呼噜,一副衰老相。多多的诗明显带有亵渎。而亵渎神圣正是波德莱尔恶魔主义的一部分。
列维克说波德莱尔的“颓废”首先是“精美”、“精炼”、“精致”的同义词。”从形式的角度讲,多多的诗恰恰具备这些特点。尽管表现的主题往往可怖,他的诗却异常精美、细腻、雅致。
波德莱尔恶魔主义的本质是通过诗歌来实现“以恶制恶”。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诗歌作为美的载体,历来是与“善”结合在一起的。《恶之花》使多多发现了“恶”的价值。恶魔主义宣扬的颓废恰恰与当时主流价值观尖锐对立。这种对立使恶魔主义成了多多实践反抗的有力工具。因此,在诗歌的世界里,他情愿把自己装扮成恶魔,堕落的撒旦,并乐于提供犯罪的证据。玩世不恭的外表隐藏着反抗的愤怒与沉痛。对他来说,恶魔主义没有任何疯狂的地方。
结论
波德莱尔的艺术漫步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他的作品既携带传统的因子,又蕴含现代的元素。他的诗并不晦涩,但有时亦可做多重诠释。波德莱尔在创新的同时,保持了与传统诗歌的血缘。对年轻的多多来说,这些特点既符合他求新寻异的期待,又没有超越他的欣赏与接受能力。在政治抒情诗一统诗坛的时代,阅读《恶之花》使多多发现了一种新的诗歌语言。从阅读到模仿再到创新,不论是艺术上的象征手法还是精神上的恶魔主义,多多青年时代的写作都明显带着波德莱尔的印记。
1970年代的诗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多多的例子再次证明了艺术发展的一个规律:危机往往是艺术获得新生的机会。诗歌由于其短小的形式,成为文学实验的最佳工具。多多借助西方现代诗歌的经验,结合中国社会特有的条件,在创建新的诗歌语言的道路上,做出了重要而有益的探索。
多多与芒克、根子被称为白洋淀“三剑客”。在三人当中,多多最后一个开始写作,但只有他坚持到了今天,并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诗人。是波德莱尔让他走上了诗歌创作之路。如果说当初诗歌是多多履行反抗的工具,那么后来诗歌就逐渐成为他全部的生命。因此,多多在1970年代对诗歌本质的思考深刻、宽广、严肃,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并超越了个体的经验。《无题和波特莱尔》中有这样几句诗:“那些有病的荆棘/红色的,黑色的/它们秘密开遍我的周围……”[28]多多:《无题——和波特莱尔》,载Julien BLAINE, éd.Poèmes et arts en Chine, Les « Non-Officiels », Revue Doc(k)s hiver 81/82, 1982, p. 85.我们难道没有从中窥见多多渴望成为另一个波德莱尔的雄心?
(责任编辑:张亘)
[Résumé]La poésie chinoise moderne a une relation étroite avec le symbolisme français. Pourtant, après 1949, date de la fondation de la R.P.C, Baudelaire se voit condamné comme décadent. En juillet 1957,, pour célébrer le centenaire de la première édition des,consacre un numéro spécial à Baudelaire, qui fait l’objet d’une présentation importante. Ce numéro spécial exerce une grande influence sur la poésie des années 1960 et 1970. Duo Duo, disciple de Baudelaire, s’engage désormais sur la voie de la poésié en tant que symboliste. Nous analysons ici le lien intellectuel et artistique entre les deux poètes.
【项目】本文是天津市社科项目《法国象征主义与文革地下写作》(TJWW12-0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