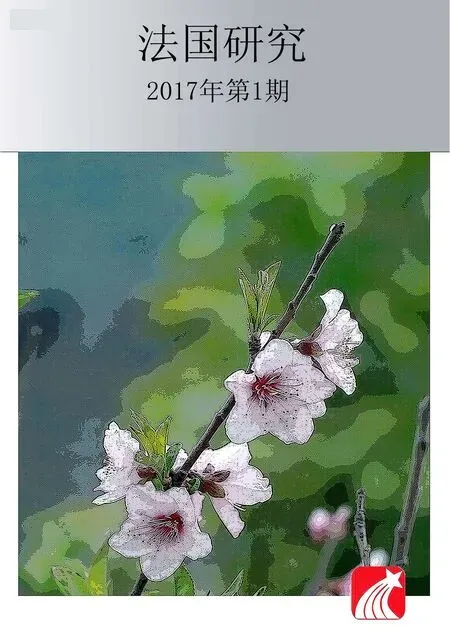“文学性”的法国历险——以罗兰•巴尔特为中心
江飞
“文学性”的法国历险——以罗兰•巴尔特为中心
江飞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结构主义时期的罗兰·巴尔特,尽管并没有对“文学性”问题进行专门探究,但在其“文学科学”理论中表明,文学符号是一种含蓄意指符号,“文学性”与变“直接意指”为“含蓄意指”的“新颖性”有关,“象征性符号系统的结构”正接近于他对当代西方文学的认识以及心中所构想的新颖的“文学性”。作为试图建立批评科学的“批评家”,他认为“文学性”问题只能在符号学领域才可能被提出和解决,而要理解文学就必须“走出文学”。 通过互文、延宕和读者漫游,“文本”概念逐渐取代“作品”概念,文本变成了泛化的、平面的、没有结构、没有中心的文本,“文学性”问题被更加开放的“文本性”问题所取代。“走出文学”是超越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的时代要求和历史必然,它使我们对“文学”和“文学性”的理解更为开放,但同时也潜藏着消解文学的危险。
罗兰·巴尔特 文学性 文本性 含蓄意指 互文 读者漫游
自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在美国将结构主义火种送给列维-斯特劳斯之后(1942),法国便在这位“结构主义之父”的带领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结构主义运动。不仅人类学从19世纪自然科学的绑架中被解救出来,投向语言科学的怀抱,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禁不住诱惑,纷纷加入到这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革命之中,打头阵的便是有勇有谋的“四个火枪手”:罗兰·巴尔特、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和路易·阿尔都塞。诸多学者已谈论过这场“革命”的意义,但我还是想提提多斯的说法,他说,“尽管结构主义有时也钻进死胡同,但它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方式,以至于如果不考虑结构主义的革命,我们甚至都不会思考问题了。”[1][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8页。无论是对人类认识方式的革新,还是对“文学性”问题的思考,这无疑都是一次重大却并不浪漫的法国历险。本文仅以罗兰·巴尔特为中心,来考察“走出文学”的时代要求与学术追求。
一、含蓄意指符号、新颖性及零度写作
结构主义时期的巴尔特,尽管并没有对“文学性”问题进行过专门探究,但我以为这一问题实际上已渗透到他理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在他后来总结性的“文学科学”理论中,这自然是在他接受索绪尔(格雷马斯介绍给他)、叶尔姆斯列夫以及雅各布森乃至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影响之后,也是在他与皮卡尔的新旧批评论争之后。在《批评与真理》(1966)中,他认为,文学科学不是关于内容而是关于“形式”(forms)的科学,“它的对象并非作品的实义,相反地,是负载着一切的虚义。”[2][法]罗兰·巴尔特:《批评与真实》,温晋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68页。后文凡出自本书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这虚义即是由符码所构成多元意义。而要给这些多元意义以科学地位,则必须借助语言学模式,因为“文学科学的模式,显然是属于语言学类型的”,“语言学可以把一个生成的模式给予文学”,(巴尔特,《批评与真实》:268)正如转换生成语法以假设的描写模式解释无限句子的生成过程。如果说语文学只能解释词语的字面意义的话,那么,语言学则能够使模糊性语言有章可循,而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相比,正是这样一种缺乏明晰性的模糊性语言,一种超越字面意义的象征语言,一种可生成多种意义的复调语言,这是巴尔特的文学观,也是新旧批评之争的焦点。如其所言,“雅各布森强调诗歌(文学)信息构成的模糊性。这就是说,这种模糊性不是指美学观点的诠释‘自由’,也不是对其危险性作道德观点的审查,而是用符码使之形式化,把模糊性构成符码。文学著作所依附的象征语言在结构上来说是一种多元的语言。其符码的构成致使由它产生的整个言语(整个作品)都具有多元意义。”(巴尔特,《批评与真实》:265)可以说,这种模糊性和多元意义既来自于文学所使用的自然语言本身,也来自于文学符号的结构特性,因为,在巴尔特看来,文学符号是一种含蓄意指符号。
在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中,“符号”大多指的并非是直接意指(denotation)的初级符号,而是含蓄意指(connotation)的二级符号,它们是两种表面上相互依存而彼此之间又存在结构性分歧的两级符号系统。这种“含蓄意指”的符号除了前面所言的“政治神话”,当然还包括具有典型特征的神话体系——文学。在巴尔特看来,文学是由言语活动(初级系统)构成的二级系统(“寄生系统”),这正如洛特曼所言的“第二模式系统”。言语活动是文学的“梦和直接的本质”,而寄生系统则是主要的,“因为它对于这个整体具有最后的理解力,”这种合二为一的关系正造成了文学话语的特殊性和含混性,而对文学的解读也就必须是在这两个系统之间不停地回转,因而文学意义也是一种复杂的、间接的二级意义、寄生意义。对文学问题巴尔特不吝笔墨,而对于“文学性”问题,巴尔特却言之甚少,惟有在《文艺批评文集》的序言中他这样简略地写道:
任何写出的文字,只是当其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改变初级讯息(message)的时候,才变成作品。这些变化条件便是文学的存在条件(这便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们所称的“literaturnost”,即“文学性”)。而且就像我的信件一样,这些条件最终只与二级讯息的新颖性有关系。[3][法]罗兰·巴尔特:《文艺批评文集·初版序》,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9页。后文凡出自本书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可见,在巴尔特看来,“文学性”与改变初级讯息(“言语活动”,直接意指)成为二级讯息(“文学”,含蓄意指)的“新颖性”有关。何谓“新颖性”呢?巴尔特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又语焉不详,大抵可以把握的是:“新颖性”是文学的基础本身,是一种“奢华的沟通”,“是为赢得他人对你作品的欢迎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巴尔特,《文艺批评文集·初版序》:11)换言之,要新颖就要避免平庸。由此,巴尔特过渡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修辞学,它曾一度被理性主义、实证主义所压制,而现在,“它是借助于替换和意义移动来改变平庸的艺术”,“其双重的功能就是使文学避免转换成平庸性的符号和转换成新颖性的符号。”(巴尔特,《文艺批评文集·初版序》:12)在这里,修辞似乎与俄国形式主义的“手法”概念尤其是“陌生化”之间形成了某种呼应。难道“文学性”就是“修辞性”?巴尔特又不免犹疑起来,“修辞学只不过是提供准确信息的技巧”,它“不仅与任何文学有关,而且与任何交际都有关。”(巴尔特,《文艺批评文集·初版序》:12)这是否意味着所有新颖性的交际符号都可能变为文学性的作品呢?巴尔特并没有回答。既建立,又拆除,既肯定,又否定,既确定,又游移,这正是巴尔特独特的写作风格,或者说是他“善变”的学术风格的体现。
必须说明的是,巴尔特对“文学性”的理解是与对“文学”与“写作”关系的理解密不可分的。如其所言,“结构主义逻辑的延续只能求助于文学,不是作为分析客体的文学,而是作为写作活动的文学。……因此,只有经历了结构主义阶段,才能把自己转变成一个作家。”[4]转引自[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290页。可以说,文学、写作、作家与结构主义以“语言符号系统”为中介,构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性的论域,其中,“写作”无疑是理解“文学性”的关键。这里的“写作”是指巴尔特所特定的“不及物写作”(intransitive writing),是一种消除了外在的干预性、价值评判和一切功利色彩的“中性写作”或“零度写作”,也即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5][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8页。后文凡出自本书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写作”之人是“作家”(author),而不是“作者”(writer),作家“与一种总是前期的言语活动过着长期的姘居生活”,并在这个充满言语活动的世界中最终实现“将索引的象征转变成纯粹符号的行为,”(巴尔特,《文艺批评文集·初版序》:11)可以说,这种写作是自身便蕴含意义的形式,也就是“文学神话的能指”,文学概念赋予它以新的意指作用。这样的写作最终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其目标仅仅在于: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巴尔特的文学“写作”思想看起来像非常自由地借用了形式主义者对日常语言和诗歌陌生化的区别,而他对“写作”的强调和特定阐释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修辞学的过分普遍性,并使这种“新颖性”或“文学性”自始至终寄寓在语言符号结构本身,而不是文学或作家或写作之外。顺便说一句,“零度”,或许可以认为是结构主义者共同寻找、共同信奉的一种科学的、自由的形式美学,无论是对于列维-斯特劳斯、雅各布森还是巴尔特。[6]如多斯所言,“列维-斯特劳斯在寻找家族关系的零度,雅各布森在寻找语言单元的零度,而巴尔特在寻找写作的零度。”(《从结构到解构》,97页)。雅各布森在《零度符号》(zero sign,1939)中认为,语言不仅在能指层而且在所指层都“能够容忍有和无之间的对立”(《雅柯布逊文集》,钱军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252-262页),零度符号是具有特定价值的符号,不是无所指的能指,而是有“零所指”的能指。这种无意义的“零度符号”什克洛夫斯基称之为“空洞的词”(empty word),而在拉康之后,我们可称之为“滑动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或洛特曼的术语“偶然的词”(occasional words)。这些词只是一种能指游戏,主要目的是为了扰乱正常的语言组织,依靠特定的话语条件的语境和它们的构成系统而存在,其拼写组合对诗人和读者而言都是无可怀疑的,可以说,“无意义的诗”作为“零度符号”就是完全自指性的符号,是“诗性功能”的极端体现,这可以说是其“无意义”的意义。
在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中,他虽然并不否定作家个人的主体性和选择自由风格的可能,但他更强调语言结构始终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支配力量,对作家具有先在的强制性与约束力,“作家拒绝了传统文学语言的虚伪本性,激烈地偏离、回避反自然的语言、对文字(写作)进行颠覆,是某些作家试图拒绝作为神话体系的文学所采取的釜底抽薪之举。诸如此类的每一种反抗都是作为意指作用的文学的谋杀者。”[7][法]罗兰·巴尔特:《神话修辞术》,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96页。可见,作家以一种朝向语言结构本身的方式来实现对文学神话的意指作用的反抗,由此,文学话语便简化为单纯的符号学系统,文学意义便是指向其符号系统自身的意义:在这里,巴尔特实际上和雅各布森一起站在了“诗性功能”的战壕里。巴尔特对现代诗的看法同样也表明了这一点。
巴尔特将现代诗与古典诗相对立来谈,在他看来,古典诗是一种有光晕(aura)的诗,是一种集体性的、被说的、严格编码的、具有直接社会性的语言,而现代诗则是一种氛围(climat),一种客观的诗,是排除了人的因素的字词迸发而产生的一种绝对客体的诗,“现代诗共同具有的这种对字词的饥渴,把诗的语言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和非人性的言语。这种渴望建立了一种充满了空隙和光亮的话语,充满了记号之意义既欠缺又过多的话语,既无意图的预期,也无意图的永恒,因此就与一种语言的社会功能相对立了,而对一种非连续性言语的直接依赖,则敞开了通向一切超自然之路。”(巴尔特,《写作的零度》:32)可见,现代诗歌的语言不再承担古典式的社会功能,而是发挥语言潜在的一切可能性的诗性(审美)功能,它摧毁了语言的关系和一切伦理意义,它是“一种语言自足体的暴力”,是“一种梦幻语言中的光辉和新颖性”,——又是“新颖性”!虽然雅各布森未必同意现代诗的“反人本主义”特性(诗歌信息也是主体间交换的符号),也未必承认诗歌完全取消了社会功能,但是,在“(现代)诗是语言符号结构而成并指向符号自身的独立自足的诗”这一点上二人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如巴尔特所言:“当诗的语言只根据本身结构的效果来对自然进行彻底的质询时,即不诉诸话语的内容,也不触及一种意识形态的沉淀来讨论自然时,就不再有写作了,此时只存在风格,人借助风格而随机应变,并不需要通过历史的或社交性的任何形象而直接面对着客观世界。”(巴尔特,《写作的零度》:34)这不是说诗歌否认了意识形态、历史性或社会性的存在与意义,而是说诗歌凭借其自身的象征性符号系统的结构便享有了意义的各种可能性。我们似乎可以说,这种“象征性符号系统的结构”正接近于巴尔特对当代西方文学的认识以及心中所构想的新颖的“文学性”。[8][法]巴尔特在1975年的一次访谈中,被问及“30年来,文学是否似乎已从世界上消失了”时,他回答说,因为“文学不能再掌握历史现实,文学从再现系统转变为象征游戏系统。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看到:文学已为世界所淹没。”转引自李幼蒸:《罗兰·巴尔特: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见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50页。
二、批评家、内在批评及“走出文学”
在巴尔特的“文学科学”理论中,文学是一个矛盾的符号系统:“它既是可理解的,又是可质问的;既是说话的,又是缄默的。它通过重走意义之路与意义一起进入世界,但却又脱离世界所指定的偶然意义。”[9][法]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活动》,载《文艺批评文集》,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可以说,它只向世界提问,却并不做出回答,意义最终只是“悬空的意义”,正因如此,文学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某一意义应该或曾被接纳,而是要说明某一意义为什么可能被接纳”,[10][法]罗兰·巴尔特:《文学科学论》,载《文艺批评文集》,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页。也就是说,我们遵循语言学规律不是为了解释作品的确切意义(作品也不存在什么确切意义),而是为了描述(describe)作品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这才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历史存在(无论现在还是未来人们都能理解)的“客观性”的源泉。而要发现这种“客观性”,则必须依赖于一种与众不同的内在性批评,或者说,需要一种元言语活动的揭示。
正如斯特罗克所言,“结构主义为了解释文本或文本群的结构,最先尝试了一种‘内在的’批评形式,而且始终表现出了一种心无旁‘物’的态度。”[11][英]约翰·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渠东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4页。这种内在批评的形式和态度也正是巴尔特的新批评与以皮卡尔为代表的学院批评的分别所在。在《两种批评》与《何谓批评?》中,巴尔特指出了法国当时所存在的两种批评:一种是继承朗松实证主义方法的大学批评,一种是以萨特、巴什拉尔、戈德曼等人为代表的解释性批评,是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现象学有关的意识形态批评。前者虽然拒绝意识形态批评,但在巴尔特看来,朗松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不满足于要求使用任何科学研究的所有客观规则,而是以对人、历史、文学、作者与作品具有整体的信念为前提。”[12][法]罗兰·巴尔特:《何谓批评?》,载《文艺批评文集》,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05页。它不理会文学的本真存在,而且还使人相信文学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仿佛文学只不过是对“翻译”作家所表达的感觉和激情,这些都掩盖在所谓的严格性和客观性之下,于是,意识形态就像走私品一样悄然进入科学主义的言语活动中,所有的“外在性”(诸如趣味、作者生平、体裁的法规、历史等)也都变成了所谓的“客观性”,正因如此,作为内在性批评的解释性批评,如果研究的是作品之外或文学之外的东西(如精神分析学研究作者的秘密、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品的历史处境),那么,学院派也同样接受。而不可接受或被拒绝的正是一种在作品之内进行研究的内在性分析,比如现象学批评(阐释作品而不说明作品)、主题批评(重建作品的内在隐喻)和结构分析(把作品当作一种功能系统)。巴尔特主张的自然是结构分析,因此他的内在性的新批评似乎可以称之为结构主义批评,比如《论拉辛》(1963)、《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1966)《流行体系》(1967)便是其结构主义批评活动的杰出作品。
这种内在性批评同样也是一种矛盾的言语活动,“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是历史的又是存在主义的,既是整体性的又是自由的。”[13][法]罗兰·巴尔特:《何谓批评?》,载《文艺批评文集》,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09页。也就是说,批评家的元言语活动必须接受其所处时代的历史赋予和更新,也必然依据存在性的组织需要来进行选择(比如词语、知识、观念等),而他自己的快乐、抵制、困扰也都置入活动中,因此,批评语言也不是旧批评所要求的明晰性语言,而是如文学语言一样的模糊性的、象征性的语言,[14]巴尔特、福柯、拉康等结构主义者批评话语的风格也表现出对明晰性的抵抗,这正如约翰·斯特罗克所言:“拉康的语言不仅使那些积极配合的读者们感到沮丧,而且也不太可能被准确地翻译出来,他的语言到处充满了语词游戏和喻指,他想证明,无意识只有通过能指而不是所指,才能构建一串语言表达的链条。”(《结构主义以来》,20页)在我看来,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乃至后结构主义的德里达也同样如此,修辞手法和修辞效果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如果说这种明晰性是法国这个特定国度的民族品德,甚至是每个法国人都应具有的真实心灵的标志,那么,他们以语言的模糊性取代明晰性,无疑包含着对坚信这种“品德”的主流资产阶级话语权威的反抗与解构。它是关于一种话语的话语,是在第一种言语活动(文学言语)之上进行的二级的或元言语活动的言语活动:
文学恰恰是一种言语活动,也就是一种符号系统:它的本质不在它的讯息之中,而在这种“系统”之中。也就在此,批评不需要重新建构作品的讯息,而仅仅需要重新建构它的系统,这完全像语言学家不需要破译一个句子的意义,而需要建立可以使这种意义被传递的形式结构。[15][法]罗兰·巴尔特:《何谓批评?》,《文艺批评文集》,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9页。
在巴尔特看来,批评关注的对象不是作品本身,而是生产体系,不是意指本身,而是意指过程,其根本任务不是发现“真实性”,而是去发现某种“可理解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说,批评不需要去说普鲁斯特有没有说“真话”,而只要描述他建立了怎样的一种严密一致的、有效的、可理解的符号系统。批评的过程主要是对能指的解码和诠释,而不是对所指的揭露,所谓“重新建构它的系统”,即“不去破译作品的意义,而是重新建构制定这种意义的规则和制约。”[16][法]罗兰•巴尔特:《何谓批评?》,《文艺批评文集》,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8页。换言之,批评不是对作品意义的翻译,而是揭示生成作品意义的一些象征的锁链和花环,一些同质性的关系。因此,批评家不是作品价值的评判者,而是一位“细工木匠”,他的工作是将一件复杂家具(文学作品)的两个部件榫接起来,“使其所处时代赋予他的言语活动适合于作者根据其所处时代而制定的言语活动,也就是说适合于逻辑制约的形式系统。”(同上)可见,批评家的批评是与作家写作同等地位的一种创造活动,是一种逻辑意义上的纯粹形式的活动:这才是“真理”。虽然巴尔特一再说“批评不是科学”,但实际上,文学批评已经在文学科学的强力影响下成为了科学,惟有如此,才能接近文学的真相。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同样致力于探索文学科学的雅各布森,其批评实践努力专注于语法而悬置意义的良苦用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尔特和雅各布森都可称之为是真正建立批评科学的“批评家”。
虽然学院派的旧批评也口口声声尊重文学的真实性,强调文学包含着艺术、情感、美和人性,以文学对象自身为本位来研究文学,不求助于人类学或历史学等其他科学来寻找“文学性”,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像循规蹈矩的评判官那样行使“批判”功能,狭隘的资产阶级“良好的趣味”决定了他们只是想保护一种纯粹美学的特殊性而已,“它要保护作品的绝对价值,不为任何卑下的‘别的东西’所亵渎,无论是历史也好,心灵的底层也罢;它所要的并不是复合的作品,而是纯粹的作品,隔断一切与世界和欲望的联系。这是一个纯粹属于道德范畴中腼腆的结构主义模式。”(巴尔特,《批评与真实》)(巴尔特,《批评与真实》:251)最终,这种道德结构主义模式的“独特的美学,使生命哑口无言,并且使作品变得毫无意义。”(巴尔特,《批评与真实》:240)相比之下,巴尔特对文学和文学性问题的理解更加开放,也更符合于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从结构主义处理方式向活跃的意识形态领域转换”的文化逻辑和时代要求,[17][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355页。他说:
事实上,文学的特性问题,只能在普遍符号理论之内提出:要维护作品内在的阅读就非了解逻辑、历史和精神分析不可。总之,要把作品归还文学,就要走出文学,并向一种人类学的文化求助。[18][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251页。
在他看来,“文学性”问题只能在符号学领域才可能被提出和解决,而要理解文学就必须“走出文学”,正如要理解作品就必须把作品真正归还给文学,而不是让其遭受文学之外的各种所谓“权威”或“真理”的奴役。问题是:要走到哪里去呢?巴尔特指出的方向是像逻辑学、历史学和精神分析学这样的文化人类学,它们都是内在性批评的典范,都具有系统的严密一致性,或者说,都符合巴尔特的科学化乃至“文艺复兴”的梦想。事实上,法国结构主义也可说是语言学和人类学杂交的产物,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将结构语言学应用于神话等人类学研究,拉康借结构语言学重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阿尔都塞借结构语言学保卫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人类学的文化求助”或者说文化符号学援助,能使对“文学”和“文学性”的理解更为开放,但我以为,“走出文学”同样潜藏着消解文学的危险,无论是像雅各布森那样以语言学为符号学的中心模式,还是像巴尔特那样将符号学置入语言学门下,“走出文学”即意味着走入符号的海洋,正如文学符号汇入逻辑的、历史的、精神分析的等文化符号之中,而当我们埋头为维护文学作品的内在阅读而费尽心力的时候,抬头忽然发现,其他各种符号在“语言学的符号学”的光照之下,也都成为含蓄意指符号,也正以其同样系统化的内在特性(即使是无意识也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而为人们争相“阅读”:文学符号的“文学性”湮没于各种非文学符号的“语言性”中,成为想象的“语言的乌托邦”,文学、“写作”、批评和文学读者都不再享有优待,因为医生也是破解密码的占卜者,城市也是一种写作,城市中移动的人即使用者也就是一种读者,如此等等。[19]参见《符号学与医学》、《符号学与城市规划》等文章,载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78,167页。当然,从某种意义来说,这虽然有违文学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的文学本体研究理想,但一定程度上却实现了索绪尔曾设想的“在社会生活的核心研究符号的生命”的远景。
1970年,当巴尔特的《S/Z》和雅各布森分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文章(与琼斯合作)同时出版的时候,[20]Jakobson ,Roman and L.G.Jones.“Shakespeare’s Verbal Art in ‘Th’Expence of Spirit’.”SWⅢ: Poetry of Grammar and Grammar of Poetry.By Stephen Rudy. Ed.The Hague, Paris and New York: Mouton Publishers, 1981,pp.284-303.该文写于1968年,1970年由Mouton(The Hague-Paris)首次出版单行本。巴尔特一定听到了来自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的“死亡丧钟”,当然,我们也可理解为这是后结构主义以“文本性”的名义为结构主义所敲响的丧钟。
三、互文、延宕及读者漫游
如果说“结构主义不上街”是存在主义者对巴尔特这样的结构主义领袖的嘲讽,那么,巴尔特则以《作者之死》(1968)对此做出了隐喻性的回应,并以《从作品到文本》(1971)一文开始了从结构主义“文学性”向后结构主义“文本性”的转变。正如1968年那群充满自由欲望的中产阶级造反大学生们,虽然对鼓励秩序、等级、中心的“结构主义”嗤之以鼻,但他们却仍是革命的形式主义者,终究只能将象征性的反抗寄托于充满文学性的“语言无政府主义”之中。[21]“所谓文学性,不是别的,而是通过对语言的风格化使用,不停逃脱日常语言的约束和追赶,尽可能获得一种意想不到的震惊效果。1968年的语言风格正是这样。”参见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北京:三联书店,2006,338页。从追求语言秩序的结构理论到破坏语言(社会)秩序的造反行为,从作品到文本,从“文学性”到“文本性”,这成为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向的“革命”底色。
考察20世纪层出不穷的文本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俄国形式主义并没有明确使用文本这个概念,但是他们将作品与作家、社会的分离,确立了作品的自律性,并将其固定于语言学的模式下,这已经是现代文论形态的文本概念。”[22]张良从、张锋玲:《作品、文本与超文本——简论西方文本理论的流变》,载《文艺评论》2010年第3期。无论雅各布森提出的“文学性”,还是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无疑都开始聚焦于“文本”这一层面上的语言操作。当然,雅各布森等人当时所使用的术语还是“作品”(work),其延续的依然是此前的传统观念,也就是说,“文本”是作品中由词语交织而形成的编织物(“文本”一词从拉丁文词源上来说就是“编织物”[textus]),是构成作品的物质性基础,而“作品”则蕴含了高于“文本”的意义(思想)指向和作者以及读者(批评者)的精神投射。虽然在“普希金的作品”与“普希金的文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根本不同,但实际上“某某作品的文本”更符合他们(尤其是作为语文学家的雅各布森)心中所设想的价值等级。
而到了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时期,伴随着“语言学转向”和“科学主义”的急切脚步,“文本”地位发生了逆转,它变成一个比“作品”更客观的语言结构,曾经至关重要的“价值、作者和美学三个要素都被结构主义批评置于一边,‘作品’概念也就丧失了立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文本,作为结构主义的科学研究对象,它无关价值、作者和美学,而只有客观的确定性。”[23]钱翰:《从作品到文本:对“文本”概念的梳理》,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这种转变意味着真正“以文本为中心”的新的批评范式的建立。对于新批评来说,他们追求去除了“意图谬误”(作者)和“感受谬误”(读者)的文本本体的“语义结构”,对于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语言诗学来说,他探求根据对等和平行原则而构成的文本的“语法肌质”,“肌质”(texture)成为他们对“文本”的共同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虽然对“作者”置之不理,但根本上都并未否认“作者”对“文本”的创造者身份(这由他们的批评文章的标题即可见出),并相信即使是含混多重的意义,也都存在于某个特定文本的语境和结构(无论语义结构还是语法结构)之中,批评者的任务正在于借助于语言科学客观合理地揭示出文本意义生成的条件,换言之,“文学性”由传统文学作品的审美(精神)特性转向了文学文本的语言(符号)结构的特性,可以说,这是一种结构化、语言化、具有向心力的“文本性”。虽然结构主义的“文本”还保持着相对封闭的结构,但其内部已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一些消解性的因子,比如不确定的多元意义,对等或平行要素之间的差异,读者(批评者)阐释的能动性等。
1960年代,“文本”概念逐渐取代“作品”而居于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主导地位,但对于法国结构主义内部来说,“作品”并未销声匿迹,有时还等同于文本而使用,但单个文学作品(文本)不再是研究对象,而是被“文学性”所取代,正如托多洛夫所言:“结构主义的研究对象,不在于文学作品本身,他们所探索的是文学作品这种特殊讲述的各种特征。按照这种观点,任何一部作品都被看成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结构的体现,而具体作品只是各种可能的体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主义这门科学所关心的不再是现实的文学,而是可能的文学。换言之,它所关注的是构成文学现象的抽象特质:文学性。”[24]Todorov,Tzvetan. Introduction to Poetics, Trans. Richard Howard.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1, p.6.在这里,“文学性”不再是新批评的“语义结构”,也不再是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体现于诗歌文本的语法结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结构”,每个作品(文本)都只是这种“抽象结构”的转换生成物,对他而言,这个“抽象结构”也就是他从传奇故事、侦探小说等散文文本中抽象出的叙事模式(语法)。然而,他经过叙事语法分析而获得的所谓“抽象结构”,只能是大而化之的、没有多少创新意义的“可能的”解释,[25]如托多洛夫在《〈十日谈〉的语法》中最后总结出的模式是:“从四平八稳的局势开始,接着某一种力量打破这种平衡,由此产生了不平衡局面;另一种力量进行反作用,又恢复了平衡。”见[法]托多洛夫:《散文诗学——叙事研究论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59页。这恐怕是他借用语言学进行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比如人物是个名词、动作是个动词)。真正对“文本”概念、文本与作品关系以及“文学性”、“文本性”产生颠覆影响的依然是巴尔特,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先锋者们。
若问“何谓文本性”,即问“何谓文本”,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种问法而已。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语言学和超语言学(metaliguistic)这两种意义上来界定“文本”,那么,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界定“文本性”。事实上,在《从作品到文本》中,巴尔特也正是在跨学科(interdecipline)的前提下引出“文本”这一研究对象的,尽管他在文中也认为对超语言学的怀疑是文本理论的一部分。[26][法]罗兰·巴尔特:《从作品到文本》,杨扬译,蒋瑞华校,载《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在文中,巴尔特给“文本”(text)列举了七条特征,涉及方法、分类、符号、复合、限度、阅读、愉悦等七个方面。可以说,这是自巴赫金最早界定“文本”内涵[27]巴赫金是在超语言学意义上使用“文本”一词的,他把文本释为“任何的连贯的符号综合体”,并认为它是所有人文学科以及“整个人文思维和语文学思维的第一性实体”,以此区别于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而对于人文科学而言,“没有文本也就没有了研究和思维的对象”,其意图在于捍卫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巴赫金的文本概念与“话语”、“表述”经常同义使用(“作为话语的文本即表述”)。见[俄]]巴赫金:《文本问题》,《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白春仁、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295页。之后最为完备的“文本性”概括,由此出发,我们就能顺藤摸瓜地把握到“文本”在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可能命运。
在巴尔特看来,时间并非区分“作品”和“文本”的标准,古典作品可能会是“某种文本”,而当代作品则可能根本不是文本,因为“文本”并非是时间廉价的馈赠,而是一种方法论的领域,换言之,“文本”并不像图书馆中的某部作品一样具有感性的、静态的、可触摸、可掌握的现实(物质)质地、空间和重量,它只是方法论领域中的客体对象,而并非确定的实体。同时,“文本”并不停留于确定的某处,或栖身于某个作者或某种体裁的分类之下,而是存在于来往穿梭的、永不停歇的生产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文本是一种敞开的、不断运动的、不断“织成”的话语存在,是将其他文本织进自身的一种“编织物”,这些文本之间不存在等级秩序,只存在差异和相互指涉、相互投射的关系,因此,“文本”是一个复数。正如乔治·巴塔耶,其无可归类的作品正如其无可归类的身份(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神秘主义者?),我们与其说他创造了诸多作品,不如说他创造了文本,甚至永远是同一文本,“文本”的这种兼容并包、打破传统分类、动态延伸的特性,正是“互文性”的体现,这可以说是文本的一个首要特性,是“文本性”的主要构成部分,托多洛夫甚至断言,“所有的文本性都是互文性”。[28][法]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11页。
在这里,巴尔特的同行,尤其是“太凯尔”集团的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对他的这种文本主张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克里斯蒂娃是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启发下首次提出了“互文性”概念(intertextualité)(《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1967),如其所言:“‘文学词语’是文本界面的交汇,它是一个面,而非一个点(拥有固定的意义)。它是几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作者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以及当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体间性,诗学语言至少可以进行双声阅读。”[29]转引自王铭玉:《符号的互文性与解析符号学——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研究》,载《求是学刊》2011年第3期。简而言之,“互文性”就是文本间性,是符号系统的互文性结构,按巴尔特的理解,一个文本就是一个交织了多个互文性文本的多元化的“大文本”。如果说克里斯蒂娃是借巴赫金的“对话”原则而将主体间性和历史性隐蔽地纳入到“文本”中的话,那么,巴尔特则更坚决地在文本中剔除了“作者”的声音,作者的话语不再具有父亲式的权威,他只能以“客人”的身份返回文本“游戏”,因为“文本中的我,其自身从来就没有超出那个名义上的‘我’的范围。”这自然是已经“死去”或“隐退”的作者,正如福柯所言,“作者在文学作品中缺席、隐藏、自我委派或者自我分割,这是文学的特性。”[30][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101页。当然,他们都共同强调了:一个文本内部不是静寂无声的,而是回荡着过去或现在已完成的其他各种文本的回声,它们平等对话,“众声喧哗”,它们以其自身的能指作为引文和参照,最终构成一个连绵不绝、无边无际的能指的立体复合体。这些“其他文本”早已越出了文学文本的边界,而成为“文化文本”的链条,这个“文本”由此而成为吸收和转化了各种文化文本的“超级文本”,可能它还与文学有关,但更可能只是五花八门的引语集合,五颜六色的文化拼盘,由此也正落入英美“文化研究”的胃口之中,在那里,文学“文本”只是政治性和批判性的社会表征,而不再是语言性或“诗性”的结构生成。值得注意的是,巴尔特在《从作品到文本》中只有一处提及“文学文本”(“文学文本永远是似是而非的”),其余皆只称“文本”,这似乎就已喻示着在从作品到文本的转变过程中,“文学”在“文本”面前越来越丧失其重要的主语地位,甚至丧失其无关紧要的“修饰性”:“文本”的博大胸怀也越来越包容了与“文学”相关却也更加“似是而非”的文化内容。
自克里斯蒂娃和巴尔特的“互文性”观念诞生后,热奈特、里法泰尔、孔帕尼翁等人又相继探讨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指涉关系,比如热奈特提出“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概念,并指出五种类型的跨文本关系。[31][法]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如果说,新批评的批评实践和雅各布森的诗歌语法批评主要关注的是相对封闭的单个文本结构,那么,建立在“对话”原则之上的“互文性”文本(互文本)则从文本之内(如巴尔特、克里斯蒂娃)和文本之间(如热奈特)这两个维度打破了封闭的语言结构,而具有了指向世界、指向外在社会文化现实的可能,即“互文本正意味着语言学模式的文本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文本的相互关联”。[32]王一川:《语言乌托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252 页。与此同时,福柯将文本视为一种“话语”形式,复活了文本与文化语境尤其是社会制度、知识范型、意识形态等权力场域之间的密切关系;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戈德曼将文学结构对应于经济结构,阿尔都塞将文学置于意识形态和科学知识之间,马歇雷则视文本是“无意识”的意识形态“生产”的产物,充满着被压抑的、未说出的裂隙和沉默,如此等等。总之,这些曾经被雅各布森等结构主义者们以“文学科学”的名义驱逐出“作品”或“文学”的文本或话语,在后结构主义时代以“文本(话语)间性”的形式重返文学领域,文本与世界重新接通,而要理解这样的陷入意识形态围攻的文本,必须凭借的是阿尔都塞 “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而非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语言分析和语法细读。
伴随着后现代生存境遇的日益符号化,符号学的一路狂飙突进,追求“对符号的接近和体验”的“文本”理论和“互文性”理论也随之持续扩张,正如德国学者普菲斯特(Manfred Pfister)所言:“互文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志,如今,后现代主义和互文性是一对同义词。”(1991)[33]Broich ,Ulrich.“Intertextuality.”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Practice.By Hans Bertens and Douwe Fokkema. Ed.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 John Bejamins Company ,1997,p.249.在此语境中,“文本”终于超越语言学的框架限定,而进入超语言学的“符号帝国”中,它甚至超越了法国解释学家利科(Paul Ricoeur)为“文本”定义的“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34][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学科》,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48页。一条短信,一则微博,一部电影,一首歌曲,一支舞蹈,一张照片(图片),一份菜单,一个手势,一个梦,等等,都是文本;在电影《无极》和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之间、在西方某个画家的绘画文本和中国的象形文字文本之间,也都构成互文本;甚至整个社会、历史、文化都被视为“文本”,正如“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历史”和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文化诗学”所主张的“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历史“作为一种文学虚构”而具有文学叙事的意味,文学与历史都是文本性的,彼此构成互文关系,文学文本成为各种社会文化力量、各种历史话语流通、各种意识形态汇聚并“商讨”的场所,文学性与历史性在“文本”这同一艘船上相互拥抱,彼此融通。
可以说,“互文性”不仅将“文本”从结构主义和语言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更赋予它覆盖一切、消融一切的“权力”,其结果自然是文本的泛化,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界限愈发模糊。无所不在的文本构成我们所身处的后现代景观,传递给我们生活的各种“意义”,而不断指涉的互文本又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对确定或终极意义以及意义生成过程的寻找,于是,我们生活在文本里,或者说,文本就是我们的生活。在泛文本观念中,文学文本不再享有任何优先或特权,和所有的符号文本一样,都存在于滔滔不绝的互文本中,它不再承担作者的创造性和成为审美作品的责任,“而是游弋在一种文化空间之中,这种文化空间是开放的、无极限的、无隔离的、无等级的,在这种空间中,人们将重新发现仿制品、剽窃品甚至还有假冒品,一句话,各种形式的‘复制品’——这便是资产阶级所从事的粗俗的实践活动。”[35][法]罗兰·巴尔特:《显义与晦义——批评文集之三》,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61页。当然,这也是中国的文本制造者们正“不得不”从事的实践活动,在各种题材雷同的文学文本、桥段相似的电影电视文本以及抄袭剽窃的学术文本中,我们已深刻感受到了“互文性”带来的巨大解构作用和震惊效果。
显然,巴尔特也以能指的嬉戏和所指的延宕表达了对德里达解构理论的附和与敬意。如果说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挖掘出确定的和可理解的所指、内涵和意义的话,那么,文本则纯粹是能指的自由游戏,是符号的动态链条,“能指没有必要作为‘意义的第一阶段’,情况恰好相反,它的物质通道受到关注是作为它的结果而引人注意的。同样,能指的无限性不再依赖于那些无法言喻的所指,而依赖于‘游戏’(play)。”[36][法]罗兰·巴尔特:《从作品到文本》,杨扬译,蒋瑞华校,载《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略有改动。可以说,文本正是能指嬉戏的舞台,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是确定的,而是滑动的,所指永远走在“延宕”的路上:这正是德里达的热爱。诚如郑敏所言,“结构主义及一切形式主义要通过美的规律飞向不朽的形式,而德里达寻求自由的运动不再是线性的,他曲折往返于对立之间,解构任何对立的主奴关系,破坏直线,以无形无质无量的踪迹织成无形的网,在不停的解构与新生、再解构中得到自由运动的快感。”[37]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44-45页。这种快感实则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境界,一种矢志不渝、追寻自由的现代精神。相较而言,巴尔特的阅读文本的愉悦和快感则是相对狭隘的享乐主义美学。当然,这不是说读者阅读无关紧要,恰恰相反,他们虽然都强调“文本”是无限开放的、互文性的、无法确定阅读和理解的踪迹网络,但也都承认读者解读(非传统解读)文本及文本性的可能。
问题是,“如果意义的意义指涉无穷,无休无止地在能指和能指间游荡,如果它的确切含义是某种纯然又无限的模糊性,它使所指的意义没有喘息,没有休息,而是与自身的机制合为一体,继续指意,继续延异,”[38][法]德里达:《文字与差异》;转引自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16页。那么读者该当如何呢?此时的读者解读(比如德里达对柏拉图文本的解构阅读)自然不可能找寻到文本的稳定意义,因为意义永远在无法抵达的后退过程中,文本已是没有中心、没有结构、无边无际的文本,读者惟有对文本间性现象进行揭示(一如意义的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既是构成“文本性”(textuality)的必要要素,又是消解文本性的帮凶,因为他已不再对意义、文本性等怀有明确的期待和追求,在巴尔特看来,读者只是“相当空闲的主体”,阅读不过是一次无目的的、悠闲自得的“漫游”:
这个相当空闲的主体沿着有溪流流过的峡谷闲逛。他所见到的东西常常是复杂的和不可还原的,这个东西常常从异质, 不连贯的物质和平面中显露出来。光线,色彩,草木,热量,空气, 一阵阵声音的爆发,鸟的尖叫,来自峡谷对岸孩子的啼哭,小径,手势,近处远处居民的衣着。所有这些偶发事件部分是可辨认的它们从已知的信码出发,但它们的结合体却是独特的, 构成了以差异为基础的一次漫游,而这种差异复述出来时也是作为差异出现的。[39][法]罗兰·巴尔特:《从作品到文本》,杨扬译,蒋瑞华校,载《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
如果说阅读作品的读者是在消费和阐释作品的意义中而获得快乐的话,那么,阅读文本的读者则是在“以差异为基础的一次漫游”过程中享受到“闲逛”本身的快乐,这是一种“游戏”、生产、参与的快乐,而不是阐释的快乐。无论巴尔特还是德里达,无疑对“阐释”都抱有警惕,甚至否定,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表明的那样(1964),“传统风格的阐释是固执的,但也充满敬意;它在字面意义之上建立起另外一层意义。现代风格的阐释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它在文本‘后面’挖掘,以发现作为真实文本的潜文本。”[40][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7页。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新批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阐释,都试图在文本之“后”(或者说“之下”)挖出潜在的意义,他们不相信所看到“文本”,而相信文本之下深藏着的另一个“文本”,为此,他们进行历史分析、结构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精神分析等等,在“文本世界”之外创造出“另一个世界”,以此实现了对文本的征服,对意义的占有,对阐释学权威的炫耀。然而,解构主义的阅读却是一种“反对阐释”的阅读,读者只是漫游者而非阐释者,那些光线、色彩、草木、热量、空气等等都以本来的不同面目,从文本的平面中牵连不断地显露出来(取消了文本的深度结构),读者仿佛是在透明的玻璃上滑行,并融入其所听所见所感(觉)的风景之中,如此,文本就成为了巴尔特在《S/Z》中所赞赏的“可写性(writerly)文本”,或者说差异性的文本。这是在“埋葬”了作者之后“新诞生”的读者,独享着“生产者”的角色,他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欲望重新拆解信码而使文本面目全非,犹如巴尔特对一个严密的现实主义文本《萨拉辛》的所作所为一般。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巴尔特最后的走向——“享乐”。正如德里达在解构活动中获得了自由的快感,正如桑塔格热切地呼唤“艺术色情学”的出场,当然少不了尼采、拉康、德勒兹的某种启示,巴尔特最终将伦理学植入解构哲学之中,文本成为色情的、欲望的文本,阅读便是享受文本的愉悦,仿佛做爱。
走笔至此,“文学”似乎在法国历险中已不知去向,这恰如此刻文学在世界文化潮流中的某种境遇。在超越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时代,雅各布森所苦苦追寻的“文学性”问题被巴尔特所倾心的更加开放的“文本性”问题所取代,互文、延异、读者漫游,已使文本变成了泛化的、平面的、没有结构、没有中心的文本,暗藏着斑斑驳驳、所指延宕的“踪迹”,散发着能指狂欢的后现代欲望。“走出文学”之后的文学,仿佛虚实相生的幽灵,徘徊于各种符号、各样文本的挤压之中,是继续与意识形态眉来眼去,还是向日常生活俯首称臣,在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中曾有意悬置的这些问题,在他死后再次摆在了文学、时代和我们的面前。
(责任编辑:张亘)
[Résumé]A l’époque du structuralisme, Roland Barthes, même ne se destinant pas à l’étude spécifique visant la « littéralité », tient à préciser dans ses thérories de la « science littéraire » que le signe littéraire correspond à un signe connotatif. La « littéralité » est liée donc désormais avec l’ « originalité » provenant de la transition de la « dénotation » à la « connonation » alors que la «structure des signes symboliques » se rappoche aussi bien de sa perception de la littérature occidentale que de la « littéralité » originale. En tant que critique ambiteux de fonder la science de sa discipline, il est persuadé que le problème de la « littéralité » ne puisse se résoudre que dans le domaine de la sémiotique. Il est indispensable de sortir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la comprendre. Par l’intertextualité, la différance et l’errance du lecteur, l’oeuvre sera remplacée par le texte.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 (AHSKQ2014D102)、安徽省2016年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2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