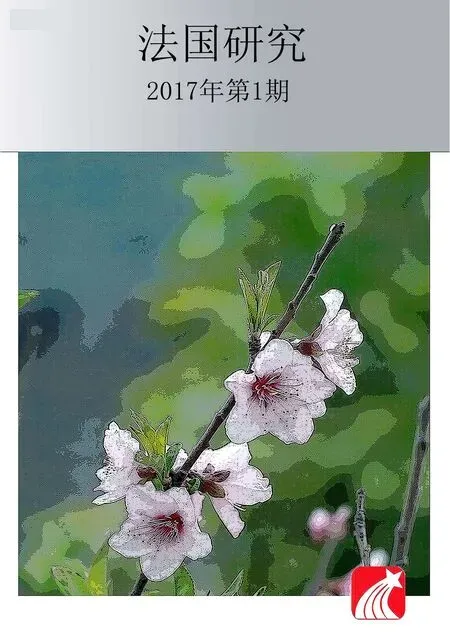二战后法国诗歌风貌
巫春峰 陈吟秋
二战后法国诗歌风貌
巫春峰1陈吟秋2
1、天津外国语大学、2、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
较之二战前的诗歌,二战后的法国诗歌在思想理念、创作手法、哲学依据等方面都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以二战后法国的精神危机为背景,援引大诗人伊夫·博纳富瓦和菲利普·雅阁泰的言论,以比较诗学为研究视角,重点阐述瓦莱里和超现实主义诗人所信奉的诗语言魔力和意象滥用是如何一步一步转化为用诗语言来言说世界的一种可能性以及意象的中庸性,力求揭示当代诗歌独具一格的景观。
二战 博纳富瓦 魔力 死亡 意象 此在
从时间角度看,“当代”这个词的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究其原因,是它囊括的范围比较大,在这里我们将采取诗评家庞松在他的散文《栖居在诗人》里面所划定的界限,即“1945年后,当弗里德里希称谓的专制性幻想的超现实主义者开始退去的时候”[1]Pinson, Jean-Claude. Habiter en poète : essai sur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Seysse: Champ Vallon, 1995, p. 13.。众所周知,1945年正是二战结束的时候,本文以二战为出发点,以诗歌的魔力到其可能性为中轴线,着重论述在西方精神文明遭受严重危机的背景下,法国当代诗歌的演变及传承。
一、对诗歌魔力的质疑
二战后崛起的新一代诗人,因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和形势的严峻性,都以清醒的意识审视诗歌语言以求重新恢复它的声誉。超思索主义[2]为了与超现实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超思考主义一代”只是笔者所用名字,并没有在法国的批评界形成统一的说法。这一代诗人大都出身于20年代,都经历了炮火的洗礼,亲眼目睹了战争的血腥和人类的脆弱,时而在作品中痛斥法西斯国家的野蛮行径。博纳富瓦,雅阁泰(Philippe Jaccottet),加斯帕(Lorand Gaspar),杜博歇(André du Bouchet),杜班(Jacques Dupin)等诗人不仅仅写诗,而且每个人都对诗歌的权力、诱惑、语言以及与其他艺术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反省。他们想通过这些呕心沥血之作强烈地表达诗歌还是有可能的愿望,它依旧能带领在黑暗中迷失的人们走向光明,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被词语表面的诱惑所蒙蔽。
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概念主义,扬弃体系化的知识,没有一位诗人试图去定义诗歌,或者构建一个框架来约束它,更多的是以开放的眼光探讨诗歌到底能做些什么。传统用来论述创作技巧和原则的诗艺(Art poétique)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访谈录(entretiens)[3]博纳富瓦著名的《诗歌访谈录》(Entretiens sur la poésie)和雅阁泰早期的文集《与缪斯的会谈》(Entretien des muses)。,这种以“对话”为主导精神的诗歌创作姿态揭露了诗人摒弃语言所构建的体系,欲挣脱仅仅由语言(langue)组成的枷锁和逃离语言的樊笼,以及重新审视人类与他者关系的迫切需求,正如博纳富瓦言说的那样“诗歌的真正开始……就是我喜欢称之为言语(parole)的时候”[4]Bonnefoy, Yves. Entretiens sur la poésie. Paris:Mercure de France, 1992, p. 34.。在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一言一语之间,他者的在场和诗人思想碰撞产生的火花让诗歌得到了久违的呼吸,话语的及时、具体、鲜活性给诗歌注入新的活力。
二战后的法国诗歌是多元的、思辨的、战斗性的。任何想将其归为一个流派的分类法都注定是徒劳无功的,相比之前的象征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当代诗歌极好地诠释了中国所推崇的“和而不同”。“和”之处主要体现在他们都选择了对本初元素的写作,渴望完成晚年的兰波(Rimbaud)所授予的任务,即“紧紧地拥抱粗糙的现实”。纵观法国当代诗歌,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法国诗人们已经如饥似渴地转向了那些许久没有观察而且也不屑观察的现实世界:“诗歌从来没有在它的言语里吸收过如此广阔,丰富,强度,深度的现实”[5]Jaccottet, Philippe. L’Entretien des muses. Paris: Gallimard, 1987, pp. 300-301.。这个有血有肉的感官世界,这个孕育了万千生命的大地重新成为诗人关注的焦点:比如雅阁泰自然清新的诗中对一川一流、一花一鸟、一木一石的大篇幅赞美之词,将世界的灵动与生机,隐遁与显现,有形与无形表现地淋漓尽致;蓬热的完全物化,从柳条筐到无花果,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物体尽收诗底;罗兰·加斯帕的成名作《物质的第四种状态》()拒绝用冰冷的、科学的眼光看待客体而注重挖掘事物的内在性(en-soi),对广袤的沙漠情有独钟是他一直以来想融入自然的真实写照。写作中心因此从超验的触不可及移至经验的息息相关,从神圣的绝对转为平常的相对,从理想变为现实。摒弃一切浮华与谎言,在战后死一般的沉寂和绝望中,这些归于本心的诗人像是手中拿着冰冷锤子的斗士,无情地砸向已将我们封闭许久的知识框架之墙,将我们从这个自足自闭的狂热世界里解放出来,让我们呼吸一口尘世的空气。
超思索一代从灵魂深处感受到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引起更多的共鸣,因为商业网络化的社会急剧膨胀,各种所谓的思想层出不穷,正如雅阁泰所言:“很明显(诗人)关心的是用相对坚实、恒常、静止的本初事物来对抗思想的脆弱传播”(Jaccottet,:302)。这个对物质和金钱崇拜不断加剧的现代文明有可能使我们失去与“原始、天然、本初” (Jaccottet,:302)世界最简单、最肉体的接触。与本源的痛苦决裂,带来一种远离精神家园的漂泊感。“这种人与世界的致命距离”(Jaccottet,:303)所引起的焦虑、担忧、创伤感日益加剧,不断侵扰着现代人,使得他们的存在感日趋式微。
东方元素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哲思,在此形势之下可以被看做是缓和症状的一剂良药。众所周知,从古至今,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它一直被回本溯源的思想所萦绕着,也就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所言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这个共同的根,实际上正是大道效仿的自然,或者用雅阁泰的话说“不仅仅是我们脚下的大地,而且还是基质、遗产,在我们身后,先于我们,本源” (Jaccottet,:302)。加斯帕直截了当地用“共同的根”[6]Gaspar, Lorand. Arabie heureuse. Paris: Deyrolle, 1977, p. 141.来形容中国人眼里孕育了万物的自然。
这些诗人都具有土地情怀,对大地有着无尽的向往之情。而这种情怀正是当代法国诗歌的鲜明特色,正如雅阁泰所总结的:
因此,当代诗歌的很大一部分,通过这一种回归出生地以及本源而占据着优势地位,从诸多角度看,它的预言者荷尔德林早就领悟到了这种必要性。丝毫都不惊讶我们曾经试图将他们中几个最具代表性的与前苏格拉底的希腊诗人进行比较。在伟大的逻辑思维运动发展前,在他们看来,有形事物既存在着,而且也具有无限性(Jaccottet,:305)。
在二元论的思想之下,二战前的诗人瓦莱里和布勒东都不屑于关注此在事物,却转向形而上的虚无空间寻觅无限的踪迹。相反,超思索一代都认为世界充满奥秘和神韵,每一次相遇都是惊喜和感动,就像雅阁泰进一步揭示的那样,“不是考虑列一个详尽的有形世界的清单,而是如此深入地关注可见世界,以至于注意力必然以触及界限而告终,也就是触及到有限世界时而蕴含,时而隐藏,时而拒绝或者揭示的无限”(Jaccottet,:304)。
这些诗作就像一泓清泉滋润了战后无数饥渴的心田,也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赞誉,这一代诗人无一例外都获得过法兰西学院的诗歌大奖。博纳富瓦和其他诗人在与瓦莱里的去人性化、布勒东的推卸责任和巴尔特的“作者之死”(此时的巴尔特还不相信诗歌的存在及其道德价值)作不懈斗争的同时,赋予了诗语言一种伦理要求。伦理与美学有机的结合,是这一代诗人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他们企图通过这样的伦理观顽强地将大地从遮蔽它的幻想里面抢夺出来,并将它与“太一的记忆”(Bonnefoy,1992:328)相衔接。
博纳富瓦抨击任何形式的文本主义(textualisme)[7]文本主义盛行于结构主义发达的六十年代,受马拉美和瓦莱里的诗学影响,他们将诗歌看做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间只有纯粹的能指游戏,与所指、现实、价值没有丝毫联系。,认为文本主义“过分地被代数和语言的几何学所魅惑”(Bonnefoy,1992:215);抨击瓦莱里“没有认识在场的奥秘”,抨击超现实主义“拒绝言说感官世界”,抨击概念“试图构建一个没有死亡的真理”[8]Bonnefoy, Yves. L’Improbable. Paris:Mercure de France, 1959, p. 138, p. 209, p. 17.。通过如此多的抨击,一种誓不妥协的力量跃然纸上,它谴责所有将诗歌与此在(ici-bas)和生命在场相背离的行为。在《反对柏拉图》(Anti-Platon)这本书里,他明确地写道:“涉及到物体”。斜体字是法语中指示词(cet),指向的是现实中有血有肉的每一个生命,而生命的跳动恰恰是由死亡来呈现。
但是瓦莱里忘却了死亡,这个芸芸众生不可避免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永恒存在的本质诗歌,博纳富瓦为此援引波德莱尔来强调死亡的价值:
因此,将至高无上的价值赋予只是死亡的物质,将生命通过死亡放置在死亡的视野之下,我觉得我能这么说,我认为,波德莱尔创造了死亡,从此以后我们知道它不再是对于拉辛暗中爱慕的理念的否定,而是生命在场的深层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唯一的真实。波德莱尔会竭力在他诗歌中言说这个绝对的外界,语言的玻璃窗外的狂风,死亡所神圣化的此时此刻。[9]Bonnefoy, Yves. L’Improbable, op. cit., p. 162.
这段话从另外一个侧面阐述了死亡除了自身的否定性之外还赋予所有当下存在一种深层意义,正是在死亡阴影笼罩之下,生命之光才能闪现地如此耀眼。受到波德莱尔名篇《死尸》以及《恶之花》中将这种有限性、可腐败性转化为美的启发,博纳富瓦认为消亡生命的真谛即死亡本身。他轰动一时的成名作《论杜弗的动与静》(Du mouvement et de l’immobilité de Douve)被视为一部反理念的杰作,在这部诗集里,杜弗被刻画成一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没有固定轮廓的事物,然而正是这个否定性拯救了杜弗,因为在它背后蕴含的是世界的“在场”,一个人类永远无法彻底领悟的精神维度。如果说“一动一静是谓道”,那么杜弗与中国宇宙生命的原质“气”其实并无二致,这一点将在日后详细剖析。至于理念的鼻祖柏拉图,他如此说道“我们想成为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来反对他。因为理念的梦幻在诗歌里隐患巨大,那就是词语不再引起丑闻”[10]Ibid., p. 138.。想要对抗在概念化世界中那种虚幻的延续,就要在诗歌语言中制造丑闻,正如下面两句诗:“我见你折断,同时享受着这死亡哦!比闪电更美,当她将鲜血溅落在白色的窗棂上”,“超越死亡走向生命/最纯粹的在场就是洒出的鲜血”[11]Bonnefoy, Yves. Poèmes. Paris: Gallimard, 2003, p. 42 et p. 56.。有鲜血溢出,就必然有伤口,有撕裂,有新生命的绽放。语言所遭受的暴力同样也是用来破坏瓦莱里理想主义的力量,它无情地撕开了美的面纱,使得隐藏其后的理念无处藏身,而最终能够在宇宙万物的内在性中抓住生命的颤动(血象征着人的肉体)。在这种悖论中,致命的创伤既摧毁又赋予生命,正如狂风席卷一切但却埋下生命的种子那样,因为它使得我们重新建立起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哪怕它是可消亡的,是终将逝去的。
这种死亡观与庄子“鼓盆而歌”的思想有着诸多亲似性。死亡和生命实则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华裔诗人程抱一的观点让我们看到中西思想的契合 :
要想让生命包含成长和变化,死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它不是有必要的话。如上述我们所提及的,在时间的进程中,是死亡的观点使得每一个时刻和所有时刻具有唯一性。[12]Cheng, François. Cinq méditations sur la beauté. Paris : Albin Michel, 2006, p. 48.
我们也可以用博纳富瓦在《反对柏拉图》里面的一句话来诠释程抱一对死亡的解读:“一个男人把卡片混在一起。一张上面写道:“永恒,我恨你!”;另一张写道:“愿这个瞬间拯救我”;第三张继续写道:“必不可少的死亡””[13]Bonnefoy, Yves. Poèmes, op. cit., p. 37.。死亡给与每个个体价值的思想也可以成为解读雅阁泰的一把钥匙:“在我身上,通过我的嘴,从来都只是言说死亡。所有的诗歌都是奉献给死亡的声音。愿我们的废墟赞扬、歌颂。愿我们的失败闪耀。”[14]Jaccottet, Philippe. La Semaison. Paris: Gallimard, 1984, p. 28.我们可以看到死亡在被诗歌吟唱,并转化为正能量之前,它萦绕在雅阁泰的脑海中,就好像写诗的过程是驱魔术。
然而,对死亡的批判就不得不提到西方的概念化思想,这也是威胁和摧毁诗歌的另一个恶魔。与理念同出一门,概念自身最大的缺陷就是将世界极端地抽象化,实物失去了它的原貌,只剩下几个线条描述其本质。因此概念凭借数学公式化的语言与感官世界完全割裂、脱节,在那里只有无尽的冻结。博纳富瓦认为法语正是这样一种抽象化的语言,它完全脱离时间和有限性的束缚,与死亡和此在背道而驰。几乎所有的感官世界元素都被抹杀掉了,因为这些卑微低下的有限物体不足以登入诗的圣殿,它们只会玷污这个纯粹概念的文本世界。
沉湎于无拘无束想象的超现实主义也是被质疑的对象之一。博纳富瓦以兰波的之名谴责这种行为:
你们要记得:当兰波写道:我 !我以前对自己说是魔法师或者天使,免除一切道德,我被贬入凡间去寻觅一个义务和紧紧拥抱粗糙的现实。当他说在已经创造了所有的盛会,所有的成就和所有悲剧之后,他应该深埋他的想象力,放弃他艺术家的荣耀,当他如此的放弃对于附加美的任何追逐。他发现了生存之美,在他看来,远胜于想象之美(Bonnefoy,1992:31)。
他要揭示的,就是超现实主义没有领悟兰波为何在《地狱一季》里面突然地转变态度,他渴望赤脚行走在大地上与其肌肤相亲,就像耕作的农民。在这个仅仅是幻象所构成的光怪陆离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不好的在场,通过它,实物在呈现我们眼前的时候已经缺失了”(Bonnefoy,1992:31)。博纳富瓦屡次提到的意象世界(monde-image)得益于“一个来源与和我们生活不同的地方,甚至见证了可能存在的另一个世界”(Bonnefoy,1992:12),以致于“用唯一真实的意象来替代所有,尤其是他者”(Bonnefoy,1992:80)。若想越狱,结束流亡,重归彼岸,唯有诉求词语的魔力,因为他们被看作是彼岸遗留的踪迹和碎片。在如此情况下,词语被赋予形而上的力量就不足为奇。雅阁泰在谈及意象时还举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体验:
我任由自己在图像中穿梭。几乎片刻之后就产生了一个(……)超越于现实世界的运动,一次对于有形界限的僭越;就在那时我看见了亡者之魂就好似白色的野兽在饮啜永恒之水。现在,我重新怀疑起带走我的那股冲力。在它身上让我感到不适的是我被带入了彼岸,进入了无形之中;因为这就像一次逃逸。[15]Jaccottet, Philippe. Une transaction secrète : lectures de poésie. Paris: Gallimard, 1987, pp. 329-330.
这段话值得我们去深思。毋庸置疑,“象”是诗歌不可或缺的成分,亦如中国诗歌里面的寓“意”之“象”。但是在西方的视野下,这个象完全可以是主体凭借幻想创造出来的,它没有中国所推崇的主客交融。西方诗人在挖掘幻想力潜能的时候有可能给我们打开的只是通向虚幻世界的一扇门。在意象面前,当代诗人进退维谷,一方面不能完全摈弃,一方面不能完全受其魅惑。深陷困境,他们竭力寻求类似中国儒教里的中庸:一个刚好处于张力的位置。
二、从魔力到可能
语言的魔力就是把双刃剑,既是巨大的,又是破坏性的,因为它遮蔽了此在此刻(ici et maintenant)的生命体验。然而,在夹缝中求生存,有一条路还是有可能的,“这个超于意义的词语,这个词语深部不可预见的沸腾所喷发的力量”(Bonnefoy,1992:187)应该彻底颠覆,诗人要树立起意义和真实世界的大旗,用来对抗自我封闭、虚幻的文本世界。博纳富瓦所说的赋予我们生存的意义(sens)实则是对丧失价值的世界所感到的一种迫切责任感,将世界重新看作是孜孜以求的“真正的地方”(le vrai lieu),此在的生活也重获它的合法性。因此魔力的问题慢慢向转变,正如雅阁泰所说:“一种言说世界但不解释世界,因为这只能使之僵化和化为乌有,而展示出它拒绝回答,生机勃勃因为无法捉摸”[16]Jaccottet, Philippe. Eléments d’un song.Paris: Gallimard, 1961, p. 153.。
我们看到当代诗歌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斗士,不屈不饶地斗争就是为了大地不再逝去,生命的有限性获得意义,在场重新涌现。博纳富瓦称他的诗歌是“大地的神学,一种将大树看成是媒介,泉水是象征性启示的思想”[17]Ibid., p. 48.。大地不再是瑕疵世界,它集超验与内在为一体,是唯一的马拉美口中“真正的世俗栖居之地”。朴实无华的大树不再是瓦莱里笔下所有树的“范型”[18]Bonnefoy, Yves. L’Improbable,op. cit., p. 99.,而是眼下这棵树, 它枝繁叶茂、纵横交错、光影交织,不按任何给定的秩序生长,不服从任何概念性的束缚,是马拉美和瓦莱里秩序井然的统一体世界突然闯入的“偶然”,然而正是这种“无限的分散、分裂”,从根到干,从干到枝,从枝到叶,“破坏了植物形式上的秩序;这种完全无形和碎裂的本质拒绝目的性,抹去了平衡”[19]Richard, Jean-Pierre. Onze études sur la poésie moderne. Paris: Seuil, 1981, p. 267.。泉水“无形”的形象更是不言自喻,它象征生命世界的活力,云水相接的化境。如此诗歌既不美化也不掩饰,而是无限可能地接近一个偶然的、难以捉摸的、灵动的世界。它不再将自我看作是一个最终目的或者无懈可击的真理,而更多的是一个充斥不确定、摸索和究诘的不稳定空间。博纳富瓦一本书的题目《不可完成》(Inachevable)以及雅阁泰的《一言难尽》(Tout n’est pas dit) 都巧妙地阐释了对于诗歌、人和语言三角关系的无尽探索,因为在他看来,诗歌或许只是生命和词语瞬间偶遇的媒介,生命体悟的来临和退隐都疾如闪电,惊若奔雷。
诗人所处境地也如出一辙,从此,他们不再是全知全能的创世神,他们在表达时感到困难,灵感枯竭,在黑暗中摸索,没有任何火光的指引,他们一直倍受疑惑和匮乏的折磨,甚至时常沦落到沉默不言的地步。诸如“预言家”“魔术师”“先知”等掌握人类命运的传统光辉形象已经消失殆尽,加斯帕如是说:“诗人就是无知者。身处未知的矿层,在无名运动的推进中,他寻求恰如其分的语言,就像肺寻找空气”[20]Gaspar, Lorand. Approche de la parole suivi de Apprentissage avec deux inédits. Paris: Gallimard, 2004, p. 62.。雅阁泰亦是如此,可以说他是这一代诗人中最持怀疑态度的一个,诗语言中充斥着的犹豫不决和脆弱感无时无刻不在缠绕着他:“我们口吃的人破碎的声音,一阵微风如稻草散落”[21]Jaccottet, Philippe. A la lumière d’hiver : précédé de Leçons et de Chants d’en bas ; et suivi de Pensées sous les nuages. Paris: Gallimard, 1994, p. 130.。他还毫不隐晦地将一个诗集命名为《无知者》(Ignorant),其实这正是对于被无能和痛苦所困恼的一代诗人最贴切的比喻。
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无知者”是一个弃智、去智的过程,舍掉思想里负面、繁琐、糟粕的杂质,回归到赤子般的纯真,既不想拥有也不想研究世界,而是凝神静气地去聆听它、凝视它、呼吸它,从而领悟世界发出的“呼唤”。深谙禅宗要义的雅阁泰认为“是最好的我听见了这次呼唤,最终我只信赖它,不去关心接踵而来可能会令我分神的所有声音”[22]Jaccottet, Philippe. Paysages avec figures absentes, op. cit., p. 22.。这种在自然面前极度谦卑的态度已与“受神启示者”形象相去甚远,它更接近一个朴实的织布工人一针一线重新编织被撕裂的世界,或者接近时刻警惕的牧羊人:“像牧羊人那样守护,呼唤所有在他睡着的时候可能的迷失者”[23]Jaccottet, Philippe. L’Ignorant : in Poésie 1946-1967. Paris: Gallimard, 1971, p. 64.。并非诗人想一直处于这种警惕的姿态,只因语言的魔力能在片刻间掀翻一切。相比以前诗歌的狂热,寒冷成为意识清醒的象征:“愿寒冷通过我的死亡站起并具有意义”(Bonnefoy,1992:90)。
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经验世界中的感性事物高于抽象概念的词语,物的开放性要远胜于文本世界的自足性,人与物的关系永远是“在一起”(avec):“我们和这棵树、这汪清泉在一起,我们和我们身体里沸腾的血液在一起,我们是故乡的孩子”(Bonnefoy,1992:241)。血液因感知到清泉流淌泛起的阵阵涟漪而产生相似的反应,阐释了心灵上的一种共鸣,意识上的一种共通。一向将主体大写(Sujet)的人已经与物相交相融,变成物的一个忠实对话者,通过对话,达到互动、蜕变、升华的目的,对话的双方都打破自我的桎梏,从封闭、单一、自恋中走出来迎接他者的到来:
首先,对他者要有信心,因为只有在面向他者异于自我这一艰难事实面前,我们才能重拾有限的意义,也就是说意识到我们自身的相对性以及我们 “自我”的虚妄,他者否定了自我,那么,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写作中与之交谈-我强调一下这个词-哪怕是在沉默中的交谈,就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写作处于十字路口的时刻(Bonnefoy,1992:34)。
雅阁泰的名言“自我的隐退是我发光的方式”[24]Jaccottet, Philippe. Poésie 1946-1967. Paris: Gallimard, 1998, p. 76.,受到了这代诗人高度赞扬,它言说的是与自我(le Moi)为中心的传统西方理念背道而驰的处世方式。这个自我形象与禅宗的“虚心纳万象”实则是一脉相承的:表面上是虚其心,实则是心灵上的充实盈满,自我已经丧失了他的轮廓,离开了他所栖居的坚硬外壳,化成无形的气,飘忽不定,永远介于万事万物间来言说大地。
在意象上,意识到圣言(le Verbe)在形而上和本体论等方面所隐藏的巨大风险,正如我们在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那里所揭示的那样,超思考主义诗人也采取了折衷的手段,他们以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意象然后再重新赋予其意义,既包含对语言的爱也对其持怀疑态度:
正如你们所见,意象就是拥有词语的人的欲望,他能让词语按其意愿言说,但是,在他所感受到极大的自由面前,他也忧心忡忡,因为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要想真正理解大地,唯有像生命所需要的那样去体验之,即在时间的流淌中,在已接受的此在所强加给我们的限制中(Bonnefoy,1992:98)。
对博纳富瓦而言,并不因意象是彼岸(ailleurs)的载体而彻底地摒弃意象,而是另辟蹊径,以此拯救处于危难境地的诗语言:
关于诗歌,我一直倾向于突出一个辩证的观点,在第一个梦幻阶段,诗歌沉湎于其中,但是为了紧接着以在场之名批判之,为了使它简化、普世化,最终使其等同与简简单单的存在,这个存在也同样具有无限性,但是这次是内心感知的(Bonnefoy,1992:98)。
在辩证的视角下,诗人首先肯定其魅力,继而用清醒的意识拯救将要逃逸的意象。同样,在这个问题上,雅阁泰也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重新让黑夜的隐喻在我身上孕育,宛如一个黑色的公主,在其周围唤醒了最古老、最天真的渴望。然后,当我让她如同一个陌生人而不是谎言通过的时候——因为这种幻想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深层的——就好像她的经过在我身上打开了什么东西——一种内在的眼睛,如果大家愿意的话。[25]Jaccottet, Philippe. Une transaction secrète : lectures de poésie, op. cit., p. 329.
意象的悖论之处,就在于它使诗人打开了智慧之眼,直抵事物的内在核心。从这一点来看,语言是有奇妙的魔力,但是精妙之处在于如何使用它:“语言的魔力是它能够重新构建一个在世存有的结构,与脱离肉体的科学眼光相悖;因为在这些基本的词里面有一种力量驱使我们回忆起还有存在的可能即意义,地方,在场而不是缺席”(Bonnefoy,1992:22)。博纳富瓦为了进一步阐明他的意思又继续补充道:“我不得不沉思我生存中的一些事件,它们所要传授的东西自我启示,介乎于我的独特性和所有生活的恒常性之间”(Bonnefoy,1992:22)。为了更好地理解话中深意,兼顾将各位诗人熔于一炉的目的,我们摘选了杜博歇一首诗歌来加以阐明:
山, La montagne,
被白日饮啜的大地, la terre bue par le jour, sans
墙并未晃动。 que le mur bouge.
山 La montagne
宛若气流中的断层 comme une faille dans le souffle[26]Du Bouchet, André. Dans la chaleur vacante. Paris: Gallimard, 1991, p. 10.
当今两大诗评家让·皮尔埃·理查(Jean-Pierre Richard)和约翰·杰克森(John E. Jackson)都对这首著名的诗歌做过精妙解析,我们以二位的赏析为依据,试图挖掘出新的东西。这首无题诗出自诗集《在空的热量中》,单从名字看就已经蕴含一种东方的禅意:一切皆为空,不能执于象,要有佛心慧眼才能得其真宰。
正如当代的其他诗人一样,杜博歇也是一位好散步的人,这首诗很可能是诗人在闲庭信步的时候心与山相交的产物,颇具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神韵:“存在不是一个终点,相反,存在是散步运动中突然的涌现,与散步者的一种分离”[27]E.Jackson, John. La poésie et son autre. Paris: José Corti, 1998, p. 115.。这就是博纳富瓦所说的“生存中的一些事件”,事件由于是个体生命在某个时刻的偶遇,所以被烙上“我的独特性”的印记。“我”的生命体验不是一层不变的,山也不会因一次相遇而失其魅力,它的内在美是无穷无尽的,诗人两次使用不同的意象来修饰山的情状就是最好的佐证。那么“生活的恒常性”在这首诗中所为何物?山的庞大、厚重、坚不可摧等特征早已沉淀在集体的无意识当中,正是这些传统形象构成了“生活的恒常性”之根基。然而,“被白日饮啜的大地”和“气流中的断层”向我们展现的更多是一种气体化、液体化的山脉,表面上看令人匪夷所思,实则将山从陈词滥调的泥沼中拯救出来,令人耳目一新。再进一步,我们试图澄清何谓“介乎于”:就是使意象不偏执于一方,换而言之,一味强调“我的独特性”将重蹈超现实主义滥用意象之覆辙;而囿于“生活的恒常性”使诗歌灵性尽失、味同爵蜡;事实上,用“气象”这一中国美学的特色词汇来修饰杜博歇的山可揭示其蕴涵的深层意义,象与气合,气与象汇,表达的乃是宇宙活泼泼的化境。无怪乎杜博歇将他的一部诗集命名为《气》(Airs)并在诗句间留下大片的空白,与中国水墨画“虚”的部分遥相呼应。细细品味,眼下的这两个意象不正是中国山水画的诗性再现?傍晚时分,雾霭开始弥散,群山渐渐被袅袅升腾的雾气所包围着,不消片刻,有棱有角的整片山群都沐浴在变幻多姿的云雾中,此时天地连为一片,了无痕迹,妙合无垠,诗人极目远眺,心驰神往,明心见性,一句“被白日饮啜的大地”把山从日常生活面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整首诗遁入化境,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气默契相通。正当作者忘我地陶醉于此情此景中时,忽然风起云涌,缭绕的云雾迅速开始消散,由上及下,由里及外,渐渐露出庞大而黝黑的山脊,刚才融于一片的一元空间顿时向纵深发展,就好像一块巨大的织布中间被撕裂了一个口子,并且裂痕向深度和长度无限延伸,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及的那样,伤口处就是生命的震颤,是“他者”的不期而至。如果说前一个意象描写的是山静止、被动、虚化的情状的话,那么后者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动态、主动、实体的形象,诗人除了将意象放置于张力网中还力图在两个意象之间创造出动静相宜、张弛有度的生命力场。唯有如此,西方所惯用的意象才会放射出真正的光芒,它既不囿于物的皮相,又不将物完全异化,而是两者有机的结合,在实与虚的化境中领略天地之大美。
结语
让·皮尔埃·理查在《现代诗歌的十一位诗人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写道:“选择这些诗人是因他们都与事物有着本初的接触”[28]Richard, Jean-Pierre. Onze études sur la poésie moderne. Paris: Seuil, 1981, p. 7.。诚然,法国当代诗歌是一个没有主要流派,没有灯塔式的标志人物,没有洞见未来的通灵人,没有沙龙,没有社团,没有宣言,没有狂热情感,没有华丽辞藻,没有颠覆一切的豪情壮志的时代,然而,在这下半叶斑驳陆离、零零碎碎的诗歌风景中,有一条无形的脉络将他们贯通一气,血液中流淌着的是对大地深深的爱,对人类存在的深入探究,对诗歌本质的深刻反省。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这些诗人都或多或少的将目光转向了东方的禅宗思想,尤其是中国的“气”文化,期盼汲取新的滋养来拯救深陷困境的法国诗歌。他们都研读过中国古典诗歌以及短小精悍的俳句,李商隐、米芾、老子等名字时不时跳跃在他们的字里行间,当然,他们诗歌生根发芽的土壤还是西方的,只不过在干涸之时,洒下来自东方的些许甘露。法国当代诗歌和中国文化以及诗歌的碰撞和融合尚有诸多值得挖掘的空间,需更深入、更细致、更长久的研究。
(责任编辑:张亘)
[Résumé]Par rapport à la poésie de l’entre-deux-guerres, la poésie qui s’écrit après les deux Guerres est marquée par un changement radical en matière de théorie, de procédé et de philisophie. Basé sur le contexte de la crise spirituelle en France, cet article, en invoquant les propos d’Yves Bonnefoy et de Philippe Jaccottet, tente de démontrer comment le pouvoir mystique de Paul Valéry et l’abus des images des surréalistes se transforment en possibilité de dire le monde par une image entre-de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