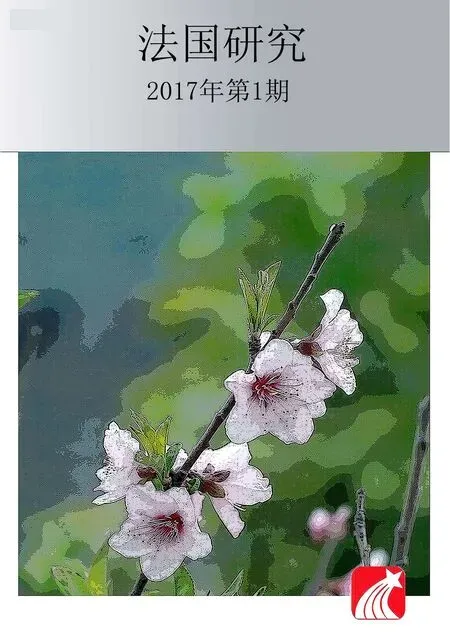戴高乐与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
陈之瑜
戴高乐与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
陈之瑜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戴高乐是当代法国人的精神化身。他一心追求战后法国的“大国梦”,并认为阻碍其“大国梦”的主要因素可能来自德国和美国,为此,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制衡。戴高乐的这一认识与思考对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形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独特的,将法苏关系建立在“第三方”基础之上的“戴高乐外交”。但是,法国与美国的矛盾以及对德国的担忧,终归是同一阵营内部的矛盾,而法苏关系则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外部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互利用性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的脆弱性和反复性。
戴高乐 冷战 法苏关系
戴高乐是法兰西的化身,他的形象仿佛一幅永存的画作深刻烙印在每个法国人的心中。无论是法国的对外事务还是法国的内政治理,戴高乐对其后的继任者都有着深远的影响[1]Valérie ROSOUX. La mémoire du général de Gaulle, Culte ou instrument?. Louvain-la Neuve: Bruylant, 1998, p.10.。作为法国对外的一个国家品牌,即使在戴高乐去世之后,他作为国家外交形象仍然久远地留在国际社会的记忆中。不仅如此,戴高乐还被喻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预言家,他对法国国家地位发展的预测及其对国家未来的展望,一直让法国历史学家们心中充满了景仰与希望。冷战时期的法国外交在西方国家中一直特立独行,尤其是同世界另一阵营——苏联之间的外交博弈,体现了典型的“戴高乐式外交”,把法苏关系建立在德国、美国等“第三方”因素的基础之上。德国威胁消除,就会导致法苏关系变冷;美国压力增大,法苏关系必然回暖。这种独特的“戴高乐式外交”理念贯串于整个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全过程,其核心是在国际外交博弈中追求法国的“大国梦”。
一、对战后法苏关系的前瞻性思考
早在二战尚未结束、冷战尚未开始时,戴高乐就对未来法国和苏联的关系作了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的思考。1944年12月,戴高乐前往苏联访问,当他从巴库(Bakou)前往莫斯科(Moscou),途径莫兹多克(Mosdok)时,面对德国和苏联正在残酷的激战,对身边的亲信发出这样的感慨:“永远别忘了德国人已入侵至此,目前他们还在奋战。这是一个强悍的民族,极其强悍的民族……”[2]Jean LALOY. À Moscou: entre Staline et de Gaulle,décembre 1944. Paris: Revue des études slaves,1982, p.140.法国外交官让·拉洛瓦(Jean Laloy,1912-1994)在书中引述戴高乐这番感概时。还在注释中特地指出,戴高乐对德意志民族的上述评价并非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对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Molotov, 1890-1986)所说,从而澄清了过去一些不实传言。。在同斯大林会面后的第二天,他在回答拉洛瓦对苏联体制印象时说:“值得确定的是,这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党在统治,也不是一个阶层在管控,而是一个男人在掌权。苏联模式并非是一个全民体制,它有悖于人类的本性。”[3]同上,152页。他还特别补充道:“是的,我们都将在整个世纪同这样的人们打交道!……”[4]同上。戴高乐这几句看似无关的话语,恰恰反映了他对战后法苏关系的深刻思考。首先,要高度重视德意志民族的强悍性[5]Thomas GOMART. Double détente : les relations franco-soviétiques de 1958-1969.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2003, p.455.及其可能对法国的损害,必须借助苏联对之进行抗衡。法国同苏联开启双边关系,就是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彻底打败德国法西斯,并在战后有效遏制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重新崛起。未来欧洲的均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巴黎-波恩/柏林-莫斯科”三边的相互制衡。法德关系与德苏关系的任何变动都会带动和影响法苏之间的双边关系。其次,要充分认识苏联体制是一种个人集权体制,要注意与其最高领导人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戴高乐关于苏联个人集权主义的观点影响了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法国的上层和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高度重视与苏联掌权者建立“个人关系”[6]Alain BESANÇON. Nous anllons en Russie…. Paris: Commentaire, n°90, 2000, p.325.,要通过这种“个人交往”来区分苏联领导人的双重性格,突出其实用主义,忽略其独断主义。最后,要同苏联长期保持国家间的往来。尽管戴高乐在话语中对此隐约流露出些许抱怨和无奈,但他认为,二战后的欧洲背负着重建的巨大压力,法国国家政策的推行以及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与立足,都无法离开世界强国苏联的支持,法苏作为欧洲两个核大国必须保持外交对话。这是作为国家首脑的戴高乐为战后法国作出的重要政治选择。
二、从战时结盟到战后的紧张对立
战后法国正是按照戴高乐的外交设计来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与苏联关系的冷热变化首先取决于美国与德国等“第三方”因素,正是美英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法国的轻视和德国对法国的战略威胁,导致战时法国对苏联的高度依重。同样也是由于德国威胁的消失导致法苏关系在战后经历了从结盟到对立的巨大转变。
二战末期,法苏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十分热络,形成法苏关系的一个明显的“高潮”。由于美英两国对法国采取歧视态度,使得法国在一切重大国际事务中根本没有被视为战胜国的一员,对于戴高乐肢解德国的政策主张也一概表示反对。为了打破美、英的藐视,摆脱法国在欧洲的孤立处境,发誓让法国重新跻身于大国行列的戴高乐迫切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因此,当戴高乐1944年当上法国临时政府总理后,第一个重大外交行动便是于当年11月出访苏联,尽管当时法国全境尚未解放。
在法苏两国领导人会谈中,双方都表达了各自对两国间传统友谊的看重。虽然法国和苏联在承认波兰卢布林政府[7]1944年7月18日至8月2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中,卢布林-布列斯特战役是苏军实施的最大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是苏联红军在1944年对德军十次打击中的第五次打击。苏军赢得卢布林-布列斯特战役具有重大的军事政治意义。德军战败,波兰东部地区获得解放,并在波兰工人党领导下,各解放区建立了新的民主政权。问题上依旧存在严重分歧,但最终还是在12月10日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法苏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两国继续协作抵抗德国,绝不与敌人单独缔结停战协定。一旦德国重新发动侵略,两国都应予以军事互助,直至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法苏友好条约的签订是戴高乐外交的重大成就,它扩大了法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回旋余地,并最终争取到了战后参加盟国的对德管制,并受邀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对德和约的基础。
为了彻底打败德国,法苏两国进行结盟。然而,也因为战后对德国事务处理的意见不合,又使得两国关系降温。在双方缔结同盟条约后不久,斯大林就不再支持法国在战后占据德国。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最初甚至不承认法国为共同管理德国的四强之一,这使法国当局相当恼火。1945年至1946年,法国就已经意识到苏联的威胁将超过德国。1947年是东西方大国之间由“战时结盟”转向“战后对抗”的关键一年,冷战全面拉开维幕,以美苏为首的世界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初步形成,双方在政治和外交上表现出全面的对抗、冲突和竞争。法国外交政策也顺势转向,法苏两国在1944年12月签订的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形同虚设。
在此之前的1946年1月,戴高乐由于不满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导致他提出的政策无法贯彻落实而愤然辞职。戴高乐下台后,第四共和国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定,政府频频更迭,使得法国当权者不仅在经济上依赖美国,而且在外交上也完全追随美国。1948年3月,法国与其他四国签订了表面上解决德国问题,实际上是针对苏联的《布鲁塞尔条约》。当时,英国利用西欧各国对苏联威胁增大的不安全感,提出西欧联合加强防务的主张。法英等国考虑到苏联的强大实力,为了“不触怒苏联”,在条约序言中特别申明,联盟的目的在于防止德国侵略政策的复活。条约的签订加快了西欧联合的步伐,但条约本质上是为了对抗苏联。1949年4月,美国和西欧国家正式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法国彻底变成了美国对抗苏联冷战阵营中的重要一员。
1954年10月,法国国民议会批准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伦敦协定》和《巴黎协定》,其主要内容是美、英、法三国结束对联邦德国的占领,但保留三国军队在西德的驻扎。三国同意接受联邦德国加入西欧联盟和北约,允许它建立50万人的军队,但不得拥有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这两项协定激起了苏联强烈的不满,苏联坚决反对重新武装西德的做法,指责法国违背了1944年双方签订的法苏互助同盟条约,单方宣布废除该条约。此时的法国和苏联基本处于冷战氛围笼罩之下,双方关系矛盾重重,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高层往来。到1955年5月,当联邦德国正式加入北约之后,法苏两国的结盟关系就彻底结束了。为了抵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联合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1955年5月也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8]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组织或华约,是为对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成立的政治军事同盟,成立于1955年5月14日。1955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加入北约后,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签署了《华沙公约》,全称《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
法苏关系的变冷正是缘于法德关系的重新开启,从而为法国创造了“双重安全”格局[9]Georges-Henri SOUTOU. L’alliance incertaine. Paris: Fayard, 1996, p.49-53.。战后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法国在联邦德国占得先机与优势,加之联邦德国又加入了北约,大大降低了德国对法国的威胁。同时,法德双方也达成一致,要面对共同的敌人苏联带来的威胁[10]Erica CALANDRI. La détente et la perception de l’Union soviétique chez les décideurs français: du printemps 1955 à février 1956. Paris: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 n°2, 1993, p.165-191.。1956年秋天,经过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11]康拉德·阿登纳于1949年9月15日就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他的政治主张是确保西德过渡到一个主权、民主的国家。1951年占领条例修正后,西德联邦政府成立外交部,阿登纳出任西德第一任外交部长直到1955年。在外交部长任职期内与法国等列强和解,并得到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善意回应,提出舒曼计划。共同掌管成员国煤钢工业,免除相关关税,并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促成西欧进一步经济合作。他推动西德1954年加入了北约,1955年与列强缔结巴黎条约,恢复主权。在同法国的外交关系中,阿登纳极力修补双方在二次大战的破裂关系,并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交好,德法的友好关系促使双方在1963年签订了德法合作条约。阿登纳被喻为“欧洲之父”之一,并且同戴高乐一起,实现了法德和解。和法国总理居伊·摩勒(Guy Mollet,1905-1975)[12]居伊·摩勒是法国社会党政治家,1956年担任法国总理,1946-1969年任社会党总书记,拒绝与法国共产党结成选举联盟,1950-1951年任国务部长,与欧洲委员会打交道,1956年他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一起领导中左的共和阵线赢得大选的胜利,同年任总理,与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谈判政策遭到挫败后,他的政府认为埃及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了援助,因而参加了英国对塞得港毫无意义的占领和对苏伊士运河的封锁。的多次会谈,法德两国完全修复了二战期间破裂的关系,重归于好。两位总理对苏联的观点非常接近。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英法两国为迫使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而轰炸埃及,苏联对此做出了强硬的反击,从而使法苏关系更加恶化。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拉近了法国同德国的距离。
由此可见,法国和苏联在战争后期为彻底打败德国所建立起来的联盟关系,在战后由于法德之间的化敌为友,导致法苏结盟的基础彻底丧失。双方由于战后实力的差距、对战后事务处理的意见不合,特别是东西方冷战的打响,使得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这一进程总体上符合戴高乐当年对法苏战后关系的预判。但是,双方之间的过度紧张显然不符合戴高乐要与苏联长期保持关系的战略构想,而这也与戴高乐的下台有关。正因为如此,随着戴高乐重归法国政坛,双方关系必将要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三、反复多变的“特殊伙伴关系”
尽管战后十余年间,法苏之间由结盟转向对立,但在1950年代后期,法国和苏联在政治党派、社会群体等中间层面还是谨慎地恢复了交流。这也为后来法苏关系的复苏留下了回旋余地。事实上,即使在双方关系持续紧张期间,仍然保持了较为频繁的接触。这种看似悖论的外交现象正好印证了巴黎同莫斯科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双方既有对抗也有合作,两国都在努力寻求稳定和不稳定甚至是战争与和平间的平衡点。
1958年,戴高乐重返法国政治舞台,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再次上台之初,正值第二次柏林危机[13]柏林危机(La crise de Berlin)是冷战时期的一场危机。共有三次,第一次发生于1948年,是冷战开始后最早发生的危机之一,其导火线为1948年6月24日苏联阻塞铁路和到柏林西部的通道。至1949年5月12日苏联宣布解除封锁,停止行动之后危机缓和。第二次发生于1958年,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美法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驻军,后来以苏联让步完结。第三次发生于1961年,苏联重新提出西柏林撤军要求,事件以苏联在东柏林筑起柏林墙作结。,法苏关系极度紧张。面对苏联的威胁,戴高乐采取了极其强硬的外交政策应对。但是,戴高乐始终将“大国梦”的追求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他认为欧洲事务理应由欧洲人来解决,不能依赖美国,更不能任凭其摆布。法国要摆脱美国牵制,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同美国抗衡。在这一思维影响下,戴高乐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外交策略,重新开启同莫斯科的对话。
1959年10月,在美、英、法、苏四大国首脑会议可能召开的背景下,戴高乐主动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法国。1960年3月,赫鲁晓夫接受其邀请,对法国展开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双方在会谈期间,戴高乐向赫鲁晓夫阐述了著名的“缓和、谅解、合作”三部曲政策。虽然两国在德国等国际问题上依旧存在巨大分歧,但是两国领导人的直接接触本身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尽管此次赫鲁晓夫访法期间,双方立场没能完全达成一致,但它显然增进了两国的了解,给之后在政治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然,法苏关系的回暖并非一帆风顺,1960年5月至1963年夏天,法国和苏联之间再次由于柏林墙、古巴危机[14]古巴导弹危机(La crise de Cuba)是1962年10月22日冷战时期在美国、苏联与古巴之间爆发的一场极其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这个事件被看作是冷战的顶峰和转折点。和法德协约[15]1963年1月22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和德国总理阿登纳签署了《法德合作条约》,实现了法德两国历史性和解。以这个条约为基础,法德两国组成了推动欧洲建设的“发动机”,从而一步步地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版图。等因素而使缓和趋势停顿,一直到1963年夏天之后,双边关系才又一次恢复生机。
自1963年开始,法国明显调整了对苏联的政策,由谴责、敌视、抗衡转向缓和、谅解、促进合作。这一转变的背景仍然与“第三方”因素有关。法国为摆脱美国的掌控,首先积极拉拢德国。1963年1月,法国总统戴高乐和德国总理阿登纳签署《德法友好条约》(也称为《爱丽舍条约》),制定了两国交流机制,从而奠定了法德友谊和欧洲整合的基础。但是,由于战后德国经济的迅速恢复与重新崛起,对戴高乐的“大国梦”仍然具有很大的压力。为此,他毅然决然地再次调整对外政策,将目光重新投向苏联。自戴高乐之后的历届法国总统,无论同苏联关系紧密程度如何,都将法苏特殊关系作为牵制德国、抗衡美国,推行全球政策的一张牌。1966年3月,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并限令美国在一年内撤出其在法国领土上的驻军和军事基地。1966年6月,戴高乐应邀访苏,法苏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双方建立“特殊伙伴关系”,从而把两国关系推向一个新高潮。此后的几十年,法苏关系在反反复复中一直维持着这种“特殊伙伴关系”。
但是,法苏两国关系的走近,并非两国之间的真正亲密,而是出于制衡德国和美国的“第三方”因素的需要,双方亲近的背后有着相当程度的互为利用性质。苏联拉拢法国同样也是为了削弱西方联盟,抵抗美国。正因为如此,法苏关系的基础并不牢固,往往会随着“第三方”因素的变化而改变。所以,两国关系常常会出现瞬息万变的奇特现象。例如在朗布依埃(Rambouillet)会谈中两国领导人刚表示合作意向,却在峰会的第二天就风云突变,这足以说明法苏关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口水战”更清楚地表明,双方仍处于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特别是在1968年8月苏联武装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之后[16]1968年1月5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展开了一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8月20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才告终。这次军事入侵导致了约10万人的难民潮,其中包括许多知识分子。该事件也影响了许多西方国家宣扬列宁主义的左翼人士的地位,最终导致这些政党的部分崩溃。,这一性质表现得更加突出。
1969年3月,苏联倡导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17]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现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欧洲国家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非欧洲成员国讨论欧洲安全与合作问题的国际会议,简称欧安会。1973年 7月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阿尔巴尼亚拒绝参加会议。,之后又由法国继续推进。在这一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掌握在勃列日涅夫手中。他的治国风格很受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1911 -1974)的欣赏[18]Michel JOBERT. Mémoires d’avenir. Paris: Grasset, 1974, p.170; J.-B.RAIMOND. Georges Pompidou et l’Union soviétique, dans Georges Pompidou et l’Europe.Bruxelles: Edition complexe,1995, p.180.,蓬皮杜之后的法国继任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也表示愿意与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建立互信关系[19]V.GISCARD D’ESTAING. Le pouvoir et la vie. Paris: Compagnie 12, 1988, chapitre I.。在这段期间内,勃列日涅夫同前后两位法国总统共进行了十次会晤。
法国总统蓬皮杜是戴高乐的忠实门徒和亲信,他坚决奉行戴高乐主义的对外政策和思想。自1969年入住爱丽舍宫伊始,他便视法苏特殊关系为维护法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特殊地位的重要条件,强调法苏协调与合作是国家既定政策。蓬皮杜于1967年7月第一次出访苏联时还是法国总理,此时的苏联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军事实力不断增加,对外,苏联推行“主权有限论”,声称当华沙条约成员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受到威胁时,苏联可以进行武力干涉。勃列日涅夫在“缓和局势”的掩护下对美国推行主动进攻的战略,并同西欧国家建立政治和经济关系,刺激美欧之间矛盾加深,以便从中获利。1974年3月,法苏两国领导人在阿布哈兹会见,将两国间已开启的合作领域进一步落实,促使双方合作步入全面的运作轨道。当时苏联亲近法国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取得法国对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计划的支持。除此之外,苏联并未给予法国其他特别的关注。苏联同美国建立战略对话,德国同苏联加强政治和经济交流,都会降低法苏关系的重要性。这种趋势特别在赫尔辛基(Helsinki)会议后愈发明显,促使法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想要尽力维持尚存的国际缓和局势。
但是,那时的苏联体制已变得更加稳固,对外态度也更加强硬,特别是70年代末苏联出兵阿富汗,导致阿富汗战争爆发。苏联入侵阿富汗彻底葬送了那时的国际缓和局势,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国家反应强烈,纷纷对苏联予以严厉的谴责。此时法国的反应却出人意料。1980年1月,法国总统德斯坦对记者发表谈话,明确表示苏联军事干涉阿富汗未必是事先安排策划的事件,可能是由阿富汗国内局势所激发的。这与其它西方国家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德斯坦“不赞成对苏联进行惩罚”,认为“从外交上孤立苏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20]方连庆等:《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17页。。
事实上,德斯坦只是为了维持早已岌岌可危的缓和局势而已[21]Michel TATU.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et la détente, dans S.COHEN et M.-C.SMOUTS, La politique extérieur de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Paris: Presses de la FNSP, 1985, p.196-217.。德斯坦在登上法国总统宝座之后,虽然在外交上他有别于两位前任——戴高乐和蓬皮杜,提倡“世界主义调和政策”,但他想依旧保持同苏联的“特殊伙伴关系”,突出法苏合作是法国外交政策中不变的因素,这样可以加强法国对美国的地位,实现法国主导下“强大的欧洲”的需求,也是国际缓和的重要条件。因此,法国不仅公开反对对苏联采取任何形式的制裁,而且反对支持阿富汗的抵抗力量。1980年5月1日,莫斯科红场举行传统阅兵仪式,西方国家中只有法国大使出席观礼,这让整个世界政坛为之震惊。事实上,那时的苏联也迫切需要来自法国的支持以打破其国际孤立境况。1980年5月18日,德斯坦赴华沙,并在翌日同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两国领导人的正式会晤。这也是阿富汗战争后,苏联接待的第一位西方大国领导人,足见两国间 “互相利用”的双边“特殊”关系。
但是,在此期间两国关系并非一路唱着高调向前发展,其间仍出现了一些影响两国关系的事件。例如,1978年5月,法国出兵扎伊尔的沙巴地区,挫败了有苏联和古巴背景的雇佣军入侵。对于这次事件,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德居兰戈(Louis de Guiringaud,1911—1982)不但公开指责古巴,而且也指明了苏联的行径。另外,苏联在非洲中部和东北部地区迅猛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直接危及了法国原殖民地国家的传统势力影响。面对错综复杂的对外关系,法国进退两难,既欲竭力维持同苏联的“紧密”关系,保持欧洲缓和形势,又不能忍受苏联在自己的“后花园”抢夺地盘。于是,法国总统德斯坦一方面把“缓和”作为对苏联施加压力的“武器”,企图让苏联有所收敛,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老牌势力范围内直接遏制苏联的扩展势头。
这样的“特殊伙伴关系”一直维持到法国新一任总统选举。1981年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1996)上台后,法国政局由右转左。同前几任法国总统不同,密特朗在一定程度上与戴高乐的泛大西洋主义拉开了距离。在密特朗执政的头几年,法苏关系又重新回到了僵持甚至濒临决裂的状态[22]Pierre GROSSER. Serrer le jeu sans le fermer: l’ Élysée et les relations franco-soviétiques,1981-1984, dans S.BERSTEIN, P.MILZA et J.-L..BIANCO, François Miterrand,Les années du changement 1981-1984. Paris: Perrin, 2001, p.251-281.。密特朗让两国关系经历了“解毒疗法”(Cure de désintoxication),对苏外交政策更加强硬,延续十余年的法苏“特殊伙伴关系”遭受严重打击[23]Hubert VÉDRINE. Les mondes de François Mitterrand. Paris: Fayard, 1996,chapitres V et VI.。密特朗试图通过加强“西方政策”来提高同苏联对话的筹码,这与他的前任想通过“东方政策”提升自我以制约美国的外交思路截然相反。
1982年,当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之后,法苏政治冰河看似有了解冻迹象。1983年2月,法国外交部长克洛德·谢松(Claude Cheysson,1920—2012)还出访了莫斯科。但仅仅两个月之后,法国就以间谍罪一举将47名苏联外交官和记者驱逐出境。法苏关系瞬间又跌至最低点。
但是,1983年11月,当美苏中程导弹谈判破裂,东西方两大阵营再次呈现紧张状态时,法国对苏联的态度却又出人意料地逆转。法国希望与苏联冰释前嫌,重修于好。1984年6月,密特朗作为法国总统及欧洲共同体主席的身份,第一次正式出访苏联,向苏联传达出明确的友好信号,从而恢复了中断三年多的法苏首脑会晤,打破了法国社会党执政以来法苏关系的僵局。由此可见,法国想要在东西方关系中保持特殊地位和作用,仍然需要依靠同苏联的“特殊伙伴关系”。
1985年10月,新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密特朗邀请下抵达法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上台执政后出访的第一个西方大国。法苏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反对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都不允许西德拥有核武器。双方表示要恢复每年一度的法苏首脑定期会晤机制。戈尔巴乔夫此访标志着两国“特殊伙伴关系”的再度重建[24]毕洪业等:《“特殊伙伴关系”的历史复归——析当前法俄关系》。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年第4期,52-53页。。1986年,密特朗再次访苏,虽然外交实际成果有限,但表达双边关系继续回暖的信号明显。
然而好景不长,法国和苏联在之后的很多问题上看法分歧。在欧洲核裁军和人权等问题的立场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导致法苏首脑定期会晤又中断了两年之多。直至1988年,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法国,会见法国总统密特朗,两国才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相互协调,转变各自立场,使法苏关系再次回暖。法国原则上支持莫斯科在1991年举办人权问题的国际会议,同意在两国首都互设文化中心。这是法国在莫斯科建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两国领导人互访机制重新启动,密特朗1988年11月如期访问苏联。双方政治对话不断具体化,合作领域不断扩大。1989年,戈尔巴乔夫再次访法,法苏两国的合作领域拓展至经济、工业、科学和技术方面,法苏关系再次交好。
80年代末,苏联国内政局动荡,法苏两国间的许多协定已无法全面执行。两个国家还不得不面临东德与西德统一的事实,这也意味着法国与苏联之间的戴高乐式双边关系即将结束,两国原有的共同协定已无法适应现有的时局[25]Anthony LESME. François Mitterrand et l’Union soviétique de Mikhaïl Gorbatchev. Paris: Paris I, mémoire de DEA sous la direction de Samy Cohen, 1996.。虽然如此,法国还是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并形成了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个外交小高潮。1990年,就在苏联国内形势极其严峻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再次访法,寻求法国的支持,并获得法国50亿法郎援助。1990年10月,法苏签订了为期十年的《谅解与合作条约》,这是自1944年《法苏互助同盟条约》签订后的第一个双边条约。即便到了1991年苏联“八一九”事件,戈尔巴乔夫受到被废除总统一职的威胁时,法国依旧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并愿意为其提供援助。但是,形势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强大的苏联还是在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下轰然坍塌,法苏之间的“特殊伙伴关系”也在两国外交史上嘎然而止。
结语
“戴高乐将军仿佛既是法国的预言家,也是实现自己预言条件的分析家。”[26]Brigitte.GAITI. De Gaulle Prophète de 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1946-1962).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1998, p.13-15.他对战后法苏关系的前瞻性思考,给整个冷战时期法苏关系提供了兼具建设性和战略性的外交框架。纵观冷战时期的法苏两国关系,始终被双方相互置于“第三方”的基础之上,法国同苏联关系的冷热交替总是同德国因素息息相关,而苏联同法国交好则主要是为了同美国抗衡。左右战后法苏双边关系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始终体现了戴高乐的长远外交构想。战后法国对外政策作为一段神化的历史,也典型地反映了法国将戴高乐的外交理念转变成国家处理外交事务范式的特点。当两德最终和平统一,之前一直影响法苏双边关系的波恩-华盛顿-莫斯科间的三角轴心自然不复存在[27]Georges-Henri SOUTOU. L’alliance incertaine. Paris: Fayard,1996, p.304.。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力明显削弱,也不再具备同美国进行全球对抗的实力,世界已经由两极争霸变成了一极独霸。法国和苏联在彼此外交战略中的占位自然下降,法苏间反复多变的“特殊伙伴关系”必然要让位于新的外交战略。
但是,戴高乐关于法苏关系的外交遗产并没有完全过时,它对法国在新形势下发展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只要看看当今法国与俄罗斯忽热忽冷的外交博弈就能明白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戴高乐的外交遗产作为一种外交哲学将长期影响法国。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欧洲和国际关系研究专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所说,如今的戴高乐主义在实际外交策略运用中的影响虽日渐弱化,但戴高乐主义作为一个国家外交的代名词却是一种无法突破的对外形象。
(责任编辑:许安)
[Résumé]Charles de Gaulle incarne l’esprit des Français contemporains. Il a toujours poursuivi un « rêve de grandeur » pour la France aprè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croyant que l’Allemagne et les États-Unis en constituaient les principaux obstacles. Il serait donc nécessaire de s’allier à la puissance de l’URSS pour contrebalancer leurs influences. Ses idées et réflexions sur les relations franco-soviétiques ont exercé une influence profonde sur la naissance et l’évolution du terme de « Gaullisme », conception idéologieque à la base de la relaion bilatérale entre la France et l’Union Soviétique, autrement dit diplomatie « tier partie ». Cependant, l’opposition entre la France et les États-Unis, de même que l’inquiétude face à l’Allemagne, étaient au final des problématiques qui reposaient au sein d’un même camps. En revanche, les relations franco-soviétiques impliquaient quant à elles, les hotstilités des deux camps, occidental et orien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