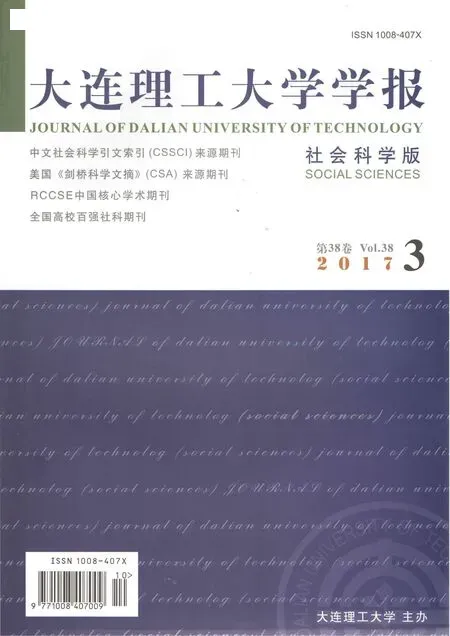论孔子仁学形成的历史逻辑进程
——从“帝”到“天”到“德”到“仁”
林 国 敬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
论孔子仁学形成的历史逻辑进程
——从“帝”到“天”到“德”到“仁”
林 国 敬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
孔子仁学的形成蕴含了三个阶段的文化发展历程。从“帝”到“天”阶段,人的道德追求还未进入关注范围,人的行为以及整个自然界都在“帝”意志的影响下。从“天”到“德”阶段,人的道德伦理追求介入“天命”信仰之中,形成“伦理宗教”,在宗教信仰中转出“敬民”思想,关注善之行为的价值和意义,人文主义得以高扬。从“德”到“仁”阶段,明确人之为人的根本乃是因为“仁”,摆脱道德追求的“天命”主宰,将神性之“天”转化理性道德之“天”,使道德追求成为人自身的自觉行为,从而形成了孔子仁学从“帝”到“天”到“德”,再到“仁”的发生学历程。
“帝”;“天”;“德”;“仁”
孔子仁学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的文化积淀,但如果只是就《论语》本身看则难以窥见孔子将“仁”作为众德之基的原因,更难以看到“仁”的提出蕴含了漫长的文化进程。
一、从“帝”到“天”
“万物关联是一种现象体系,更是一种世界观”。在殷周时期,这种万物关联的世界观是以宗教神学的方式呈现的。现有资料表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后礼。”(《礼记·表记》)殷人的鬼神信仰是一个多元系统,它包含对风雨山川诸神的信仰以及对祖先神灵的信仰,但它们之间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有一个最高的主宰者存在,这个主宰者便是“帝”。从现有卜辞资料来看,“帝”掌管着自然界和人间的方方面面,通过“日月风雨为其臣工使者,”[1]580影响年成。如“今三月帝令多雨。”(前3.18.5)“帝命雨足(年)。”(明 1382 )这里“帝”便是通过风雨掌控人间的农业收成。“帝”还掌控人间和人王的福祸,如“帝其乍王祸——帝弗乍王祸。”(乙1707,4861)“今日风祸。”(上 31.14)“王乍邑,帝若。”(乙1947,6750)[1]562-567帝王的重要作为需要得到“帝”许诺,否则便会有凶害。
“帝”的这一至上性一般认为是从祖先神或宗族神发展而来,然后又超越宗族神成为至上神。如郭沫若认为卜辞中的“‘帝’便是‘高祖夔’”[2]53,也就是“帝喾”或“帝俊”。如果郭沫若的论断为真,那么“殷人的至上神‘帝’,就是从祖灵崇拜中发展起来的。”[3]127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卜辞中至上观念“帝”是指“天”,“天有生育万物之功,故称帝…帝本是对天的别名。”[4]这种说法认为至上观念“帝”源于对天的崇拜。从当代认知科学视角看,人的最初认识都从具体事物开始,进而抽象为对观念事物的认识,因此,远古人最初难以直接认识天的神秘性,需要通过某一具体概念来感知它。“无形的、难以理解的、复杂的抽象概念的概念化是根植于我们对有形的、为人熟知的、简单的具体概念的把握。”[5]这符合古人的认知方式,比如《系辞》便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类万物之情”便是以自身的身体来隐喻万物,也包含以自身对周围的所见和由此所引起的体验来类比万物(隐喻万物)。根据这一看法,卜辞中的至上观念,当源于对祖先的崇拜形成祖先神,进而映射对自然的认识形成自然神,最后,以此两者映射对整个天地之神的认识,形成最抽象的至上观念“帝”。根据这一认知过程,先有对祖先的崇拜,进而有祖先神灵,再有自然神,最后才形成至上神“帝”。这是“人类用自己的身体行为为坐标,把整个宇宙都身体化了”[6]的结果。身体化了的天地便有了人的一些属性,同时又具有超越人之能力范围之外的属性,即神性。这即是古代“取诸身”“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一个隐喻认知方式。祖先是可感知的,可切身体验的,从对祖先崇拜来映射对天地主宰性观念的认识,这是一次飞跃,从具体可感的事物中映射对抽象事物的认识,形成抽象概念,进而以此解释生活世界的原因和依据,大大拓展了人的思维向度。因此,可以说至上观念“帝”的形成是远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结果,也是远古思维的一个重大突破,有了至上观念后,人们便可以用“帝”来解释对天地万物的宏观认识,解释人类各种现象的原因和依据,将对天地万物的认识统一于“一”(“帝”),形成对天地万物的统一认识。
到了西周时期,文献中出现了另一个至上观念——“天”。对于这一概念是否是周时期所创,学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一般认为至上观念“天”为周人所创,如郭沫若认为虽然“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或者也在使用,“但卜辞称至上神为帝,却决不称之为天。”[2]48从文化发展史来看,“天”的概念由殷人“帝”转化而来,而后逐渐代替之。这可以从《周书》中大量保存“帝”的用法可以得知,“帝”的使用数量在周的相关资料中明显不如“天”的数量,《诗经》以“天”为“帝”的用法有118次,而“帝”才只有43次。《尚书》周初的12篇文献中,“天”出现116次,而“帝”才25次。[7]9这一统计数据说明,周人在以“天”代替“帝”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帝”的使用,所以“天”和“帝”在西周时期可以互换,如“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 ”(《周书·多士》)这里的“帝”和“天”便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都具有人格神的特征。陈咏明在考察“帝”和“天”的诸多用例后,认为“至西周以后,出现了一个名之为‘天’的概念,在意义上似乎与‘帝’或‘上帝’完全相同,两者可以互换。”[8]从政治角度看,保留对“帝”的使用是为了安抚商朝遗民,减少殷人对周人的抵触心理;从文化发展角度看,周人继承的是殷人文化,必然会带有殷文化的痕迹和特征,不可能完全摒弃对“帝”使用。然而尽管两者可以互换使用,但周人思想中的“帝”或“天”的概念已经不同于殷人的“帝”的概念。其最大的区别便是周人在“天”或“帝”的概念中加入了“德”的概念,并逐渐淡化“天命”,认为“天命”的维系需要“德”的支撑,主张“天命有德”(《虞书·皋陶谟》),以“德”配天,这就“把不可捉摸的‘上帝’改为有价值标准可循的‘天’”。[9]118可以说这是周人对殷文化的一个重大“损益”,也是一个继承。殷人的“帝”善恶相混,时而做善,时而做恶,既是慈悲的神,也是无情的憎恶之神[10]。它是盲目的神秘力量,在它面前人们只能诚惶诚恐地服从它,没有价值标准可循。换言之,殷人信仰的“帝”与人的伦理无关,而周人信仰的“帝”或“天”因加入“德”的因素与人的伦理密切相关,从而能以“帝”或“天”的信仰来规范人的行为和生活秩序,为西周的德治政治构建坚固的理论基础。
二、从“天”到“德”
“德”是周文化的最核心概念之一。在周人看来,文王之所以能够掌管殷人的江山,乃是殷人不敬“德”。“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书·召诰》殷人一直继承着“天命”,但是后来不敬“德”,以致其失去“天命”。这一解释将朝代的更替与帝王的道德行为联系在一起,从而很好地阐明了周代殷的合法性。基于这样的政治现实,周人在保留“天”的自然神和人格神属性之外,添加了至善的内容,将“敬德”和“保民”纳入“天”的内涵中,“从而将对‘天命’的信仰,转变为统治者对自身行为的自觉,”[9]28发展出一套新的解释模式。殷人仅以“帝”来解释“天命”之在我身,认为“天命”的维系在于天本身,而不在于人,没有危机意识,更不会将“天命”的继承与自身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这大概与商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孙后代有关,如《诗经》中“帝立子生商”(《商颂·长发》)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玄鸟》)皆认为商人是上帝的后代。因此,纣王在面对家国覆亡之际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商书·西伯戡黎》),认为自己的命就在于天,与人无涉。这就将人的伦理之善排除在外,使“帝”成了外在于我的异己者。周人以“德”将“帝”转化为关涉于我的天地主宰者,使我的存在与“天命”的继承有了沟通,从而为之后儒学的天人模式奠定了可能的理论框架。这是周人对殷文化的一个重大创新和发展。
周人所谓的“德”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既有宗教的因素,又有人文主义思想。宗教因素体现为对“天命”的信仰,人文主义思想体现为对“民”的敬畏。因此,“德的观念里纠结着错综复杂的脉络,既折射了宗教传统意识形态的残余,又濡染了人文理性的风尚。”[11]251因为“天命”是帝王治理的天下的合法权利,失去“天命”便意味着失去天下,因此,“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周书·多士》),从成汤到商纣王之父(帝乙)无不行天德,重祭祀,所以上天大力帮助建立殷国。像纣王因不能“明德”,“天”便“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周书·君奭》)殷的“天命”便因此而被剥夺。又如“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下,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周书·文侯之命》)这里的“上”意指“上帝”,人王敬勉其德,便能被上帝所知,上帝则降大命于他。因此,王者“明德”,“天命”才会常在其身。在这一语境下,“德”落实于帝王表现为对“天命”的敬畏和信仰,从而从内心引出对“天命”的敬畏,“德”则与“心”有了相关性。在骨文中“德”无“心”字底,到金文中才有了“心”字底,“‘心’字底的出现是‘德’的伦理内涵不断强化和提升的结果”[12]。陈来进一步认为“德”字“从心以后,则多与个人的意识、动机、心意有关”[3]317,因此,“德”之“心”字底的添加当与周初帝王对“天命”的敬畏有着密切的关联。
“天命”的进一步发展显示为“民命”,以“民命”即显“天命”的方式述说上帝之命。《商书·盘庚》:“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商书·盘庚下》写作年代虽各家说法不一,有“盘庚时代说”(马融、郑玄首倡)、“小辛时代说”(司马迁所创)、“殷商时代说”(王国维力主之)、“殷周之际说”(杨筠如主之)和“西周初年说”(以张西堂《尚书引论》为代表),有“春秋时代改定说”(顾颉刚持此说),李民、王健认为《盘庚》为周初统治者追忆当年盘庚迁都之事,以帮助周初大规模迁徙殷民措施的推行。[13]118笔者比较赞成李民和王健所主张的时间,因文中所表达的“民命”即显“天命”的“敬民”意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是周初人文精神跃动的体现。
在这一段话中,盘庚迁都,殷民反对,盘庚便以“天命”为其依据来教导他们,但在这里盘庚没有直接说“天命”,而是以“民命”来述说“天命”。对“民命”的解释,孔安国以“奉承民命”解释“恭承民命”[14]361,蔡沈以“敬承民命”来解释“恭承民命”[15]105,“民命”是民之令,民之所求。孙星衍以“抍民于溺,以顺天命”[16]解释“恭承民命”,将“天命”解释为“抍民于溺”,李民、王健则直接认为“民命,即天命。”[13]131以“民命”述说“天命”意味着统治者“敬民”意识的极大提升。
到了西周,“敬民”意识越来越凸显,“天”的自然神和人格神特征逐渐淡化,提出“民主”概念,将“天命”显示为“民命”变得更加彻底。其言:“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言:“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周书·多方》)“天”为求民之主,而从诸多诸侯中降命于成汤,接替夏命。《孟子·梁惠王下》引古文《周书·泰誓》言:“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帝,宠安四方。”《周书·泰誓上》孔颖达疏:“为人君,为人师者,…惟其当能佑助上,天宠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难。”[14]405蔡沈:“天助下民,为之君…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宠安天下。”[15]125孔颖达和蔡沈讲得非常清楚,“天”立君王便是因为他能够安定天下四方之民。这反映了周时期“德”内涵中的“敬民”之思已经成为帝王的首要意识,君王的维系不在于“天”或“上帝”,而在于“民”。“天命”的达成落实到对“民命”的达成上,“以德配天”转化为以“民命”配“天命”,“德”最终下落到民心上来。因此,才有了周公“天难谌”“天不可信”(《周书·君奭》)的思想。“天”之所以不可全信,是因为“天命”隐于民心、民意、民情之中,即“民命”之中,从而在宗教“天命”观背景下转出人文主义强音,这是周人对以往文化的一次大转变,徐复观称之为“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跃动”[18]。
可以说,周人所创造的新的“天命”解释模式将宗教、政治、伦理容纳到“德”这一个容器之中,使其联系为一体,既包含了传统的“天命”观,同时又有所推进和创建,是周人对以往文明成果的一次大综合,“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人文理性的高扬,亦空前深广地改变了旧的宗教传统,赋予后者以新的内涵和时代特征”[11]244。周人对“德”的这一发明极大拓展了人在道义上的生存空间,“天”的意义里包含了对他族、他人在德行和道义上的正当性捍卫。“天命”与“德”的结合被赋予一种价值理性的品格,“天”也因此成为后世终极性的价值源头。这与殷之“帝”便有了本质的区别。
从宏观视域看,“德”的意义比“帝”或“天”的意义更加抽象。“天”或“帝”还可以将其设想为一个至高的主宰者,但是“德”就没有这样的形象性,对它的理解只能凭借理性思维。另一方面,从帝到天到德的进路,人心逐渐打破自我的狭隘性,走向广阔的道德之域,追求理性道德家园,它标志着理性的飞跃性进步。在此背景下,人们对社会事件以及对各类现象的探索逐渐转向对伦理意义的关注,以理性的思维探究其背后有关善的思想和善的行为,从而将文化的发展转向一个新方向。
三、从“德”到“仁”
虽然周人注重“德”,讲究以“以德配天”,但是始终是以“天命”作为依归,“天”依旧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统辖人间事务,人的德性行为被视为承接“天命”的媒介。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的道德追求本身还不是目的,而是“以德配天”的手段。因此,西周虽然已经重视人自身的德性行为,提出“民命”和“民主”概念,并将此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但还依旧有待于进一步廓清和推进,让道德追求摆脱外在的“天命”主宰,成为自身行为的目的,而不是继承“天命”的手段。孔子“仁”的提出从根本上扭转了“天命”观的神学色彩,将“天”转化为理性道德之“天”,以“仁”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让道德追求成为人自身的目的。孔子对道德追求的这一转化,伴随西周社会的发展以及春秋时代的动乱得以确立。
西周中后期王室不断衰微,传统“天命”观不断受到理性的质疑,人们对“天”失去了先前的神圣性,疑天、怨天思潮涌现。如“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诗经·秦风·黄鸟》),“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诗经·小雅·节南山》),“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诗经·小雅·雨无正》)在《诗经》中人们直接谴责“天”的不道德行为,他给人降下饥荒、灾祸,残害四方,放过罪人,杀害好人(“歼我良人”)。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周人对“天”的“全善”和“全能”性产生了怀疑,“天”也不再是正义的化身,反而是人世之恶的推动者。在疑天思潮背景下,对“天”的敬畏大大剥落,那么对社会正义和至善的担当不能再诉诸于神性之“天”,需要在神性之“天”外寻求新解释和新的安立之维。
因此,在怀疑“天命”和质疑“天命”的思潮下,天的宗教之维退居一旁,天的自然属性和理性之维不断凸显,并逐渐取代天的宗教之维成为解释人世社会现象的新话语。如西周末期太史伯阳父运用天的自然属性“阴阳观”解释自然和社会变化间的联系,并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解释社会动乱的原因(见《国语·周语》)。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之前,无人以天的自然属性解释社会现象以及自然现象,而是说到了西周末期,以天的自然属性和天的理性之维解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成为社会共识。与之相对,则是礼的“崩坏”,“礼乐征伐”不再自周王出,转而自诸侯出,这也是“天命”权威不复存在之后的后果之一。这一变化给当时社会带来极大的动荡和不安,导致已有社会秩序的失范。这种失范体现为宗法制的破坏,出现了臣弑君、子杀父的不合礼乐伦理的行为。失范了的妄为给社会秩序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给黎明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孔子面对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他明确说:“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说明孔子对这个时代有明确的意识,即他要以周文化为归栖,因为孔子认为周文化继承了夏、商文化的精神又有所损益,可谓至隆至盛,礼乐文明到了周朝已经无以复加。正是基于对周文化的深刻认识,孔子才感叹“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但如何复兴周礼却是一个难题。首先,先前“天命”话语系统已经难以解释社会所生的现象。其次,原有社会结构的合法性地位由上天或“天命”来作为支撑,当上天或“天命”失去其神秘色彩或失去其作为神性主宰者所应有的担当和责任的时候,它的合法性遭到了严重挑战。因此,孔子必须要对此作出回应,对其进行损益,才能够有所发展。孔子对周文化最明显的损益便是以仁的言说方式取代天的言说方式,以仁学的话语系统取代神性“天命”的话语系统。
首先,孔子认为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论语·子路》)“名不正”则一切其他的事务都会失去法度,所以必须要先正名,正名的内容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四项内容几乎涵盖了宗法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规范好这四项关系,让每个人都值守于自己应该做的行为之内,那么这个社会就和谐,礼就可得以复兴。其次,行礼要有内在的基础,因为这四者关系的维系如果仅仅依靠权力来支撑,则难以深入人心。“礼崩乐坏”的直接原因是周王室的衰落,进而才是“天命”权威扫地,社会陷入动乱。因此,回过头来反思周文化就会发现,先前以自然神和人格神的“天”作为礼的依据,以王室的权力支撑礼的有效运行都是不牢靠的,因为“天命”的权威需要王权的保证,而王权本身又是不可靠的,因此,整个周文化用以维护礼之有效运行的支撑点是不恰当的。
因此,恢复周礼需要寻求一个正确的支撑点,将礼的发用立定于具有普遍性的基础上,即它自身不需要别的支撑,而能成为行礼的基础,如此才能保证礼的稳固性。这个普遍的点就是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一个人内心不仁,礼乐也就失去了意义。“仁”《说文解字》解释:“仁,亲也,从人从二。古文从千心,或从尸。”郭店楚简文字中有“心”在“身”之下的字,庞朴认为这个字便是“仁”的古字,便是《说文》的“从千从心”之字。[17]不管是《说文》所言,还是郭店楚简所揭示的,古字之“仁”直接与心相关,这从孟子那便可以得到说明,他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仁在孟子那里便直接是心。孔子之所以以“仁”作为他学说的核心,无疑是认识到人心之善的重要性,只有从内心培养善性,身体的行为才能真正指向善。作为维系社会规范的礼仪只有在善性为其基础的前提下,才能得以自觉遵从,才能摆脱外在因素的干扰,保持它的纯粹性。
“仁”字最早见于《尚书·金滕》的“予仁若考”句,《诗经·郑风·叔于田》和《诗经·齐风·卢令》中有“洵美且仁”、“其人美且仁”句,但此时的“仁”字基本上不包含多种德性之义。到了春秋早期“仁”的观念大量出现,其含义也越来越丰富,其涵盖范围也越来越广,这也意味着“仁”的概念越来越抽象,如《左传·襄公七年》:“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仁在这里便是这三者德行的融合。但在这一时期,人们重视的是礼,而不是仁。《左传》中礼出现了462次,而仁仅出现了33次,这说明仁在当时还是不能与礼相提并论。因此,要将“仁”作为复兴周礼的普遍支撑点,就必需要对“仁”进行创造。在《论语》中,孔子将“仁”提升为一个统摄诸多伦理条目的哲学概念,“赋予‘仁’以‘全德’的意义”。[19]经过孔子对“仁”的改造,“‘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德性,而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20]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为“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同时孔子又把忠、敬、诚、恕纳入仁的德性中来,这样仁就成了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诚、忠、恕、敬等诸德的内在基础。不仅如此,孔子还将“仁”视为人之根本,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论语·里仁》)“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一个人如果不仁那么就不会是君子,不会是仁人志士,其为人也失去了他的根本,所以孔子又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朱熹注之:“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21]“仁”作为人的根本,即是道,故孟子言:“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因此,一个人如果不仁那么便沦为禽兽。经此转换,道德行为的生发根源转向了人自身,摒除了外在的客观神性主宰,从自己的人心中转出“仁”,转出道,从而将人心与天道相贯通。在此背景下,“天”不再是宗教神性之“天”,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主宰之“天”,人之所以要行善不是因为要继承“天命”或别的什么,而是因为人本来就要行善,这是人之为人的本真,而人的这一本真也即是“天”之本真,“天”的要求在此转化为主体之性的要求。如果人不发扬这个本真之“仁”,那么就会逐渐失去作为人的资格,失去作为人的道而沦为禽兽。一个人的内心有了“仁”,也就有了全部的德性于内心。
礼和仁的一个最大区别是,仁指向内心,礼则更多指向行为规范。对于道德主体意识来说直指行为是不够的,“天命”背景下的礼与德更多的是指向人的行为,对人心关涉较少,所以礼、德在“天命”话语系统下不具有心性的意义。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提出“认识你自己”,专注于对心中之“善”的探索,孔子所做的也与此类似。从“帝”到“天”到“德”到“仁”,只有到了“仁”,才由外转而到内,专注于人的内心深处,探索内心的善。内心世界规范好了,发之便是德,行之便是礼,这也是孔子将“仁”置于极高位置,容纳众德的原因。经过孔子的提升和改造,“仁”转化为人的道德归栖,将道德安立于人心,使原本一颗不够开放的心,明亮了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仁”是孔子自家所体贴,正如牟宗三认为“儒家对人类的贡献,就在他对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开始作一个反省,反省就提出了‘仁’的观念”[22]。孔子“仁”的提出,可以说又是一次文化大转变,因为其“开显出人—心维度的精神世界,人因‘仁’而不断向内在超越的方向发展。”[23]
四、结 语
从“帝”到“天”到“德”,再到“仁”是孔子仁学形成的历史逻辑进程,这一进程可谓是“人以天命为道,最终又复归大天的自然”,“仁”便是上天内在于人的“自然”,它使三代文化的发展最终落实于人最理性的地方,从内在唤醒人的道德主体意识。不仅如此,从内心转出的“仁”同化三代宗教神性之“天”,并将其内化为道德理性的本己依据,将对外在世界的探求转向对内在心性的求索,为中国正统文化奠定了基本品格。杨向奎对此评价道:“‘仁’是孔子提出来的新命题,继西周初提出‘德’后而有‘仁’,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伟大转折”。[24]
综合上述,在孔子仁学诞生之前,中国文化经历一个从“帝”到“天”再到“德”的漫长岁月,这一历程完成于商和西周时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象,由身体近处到身体远处的认知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我族类走向融合他人族类的文明历程。这为孔子“仁”的提出以及对仁的思想的构建提供了智力基础和思想准备。孔子仁学乃是接着三代文明的逻辑进程做进一步的推进,从而形成了仁学从“帝”到“天”到“德”,再到“仁”的文化发展脉络,这也是孔子“仁学”发生学的一个逻辑进程。
[1] 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2] 郭沫若. 郭沫若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 陈来. 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4] 詹鄞鑫. 神灵与祭祀[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47.
[5] 吴为善.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39.
[6] 叶舒宪. 神话意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4.
[7] 傅佩荣. 儒道天论发微·余英时先生序[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8] 陈咏明. 儒学与中国宗教传统[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66.
[9] 张立文. 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0] 李亚农. 李亚农史论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561.
[11] 郑开. 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2] 孙熙国,肖雁. “德”的本义及其伦理哲学意蕴的确立[J]. 理论学刊,2013,222(8):61-67.
[13] 李民,王健. 尚书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18.
[14]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 尚书正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5] 蔡沈. 书集传[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16] 孙星衍. 尚书今古文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2010:240.
[17] 庞朴. 庞朴文集·第二卷[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71.
[18] 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19] 白奚. 从《左传》、《国语》的“仁”观念看孔子对“仁”的价值提升[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77(4):10-15.
[20]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53.
[2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1:344.
[22] 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9.
[23] 景怀斌. 孔子“仁”的终极观及其功用的心理机制[J]. 中国社会科学,2012,(4):46-61.
[24] 杨向奎.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81.
The Historical and Logical Evolution of Confucian Benevolence——From Deity to Heaven, Virtue and Benevolence
LIN Guojing
(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
The Confucian benevolence implies three stage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stage, when it develops from Deity to Heaven, moral pursuits are not yet conscious acts. Human behavior and human nature are guided by the will of Deity. During the second stage, when it evolves from Heaven to Virtue, human moral and ethical interests participate in the belief system of Mandate of Heaven. It creates an ethics-based religion from which the great thought of respecting people is derived. Accordingly, people begin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ir own good will and behavior. Thus, humanism became popular. The third stage goes from Virtue to Benevolence. Benevolence is clearly regarded as integral to the concept of humankind, and people get rid of the dominating moral system of Mandate of Heaven, which transforms Heavenly Deity into ethical Heaven. Thus, moral pursuits become people’s conscious acts. The three stages form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nfucian benevolence that goes from Deity to Heaven, Virtue and Benevolence.
Deity; Heaven; Virtue; Benevolence
10.19525/j.issn1008-407x.2017.03.025
2016-06-18;
2016-10-2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先秦道家个体性思想研究”(15FZX016)
林国敬(1984-),男,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哲学研究,E-mail:guojinglin10094@163.com.
B222.2
A
1008-407X(2017)03-016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