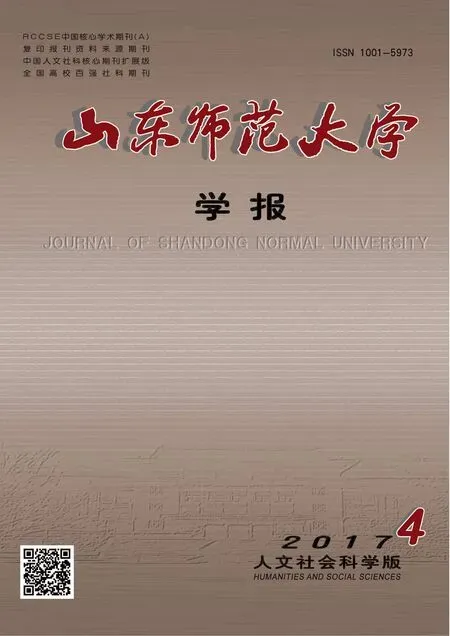书法艺术之人文与生命美学精神初探*①
蔺 若 李天道
( 1.成都师范学院 文学院,四川 成都,611130;2.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611130 )
书法艺术之人文与生命美学精神初探*①
蔺 若1李天道2
( 1.成都师范学院 文学院,四川 成都,611130;2.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611130 )
作为世界文化的灿烂之花,中国书法艺术具有一种浓厚的民族色彩,呈现出一种人文与生命美学精神。正是“人”的审美要求,导致了中国书法审美形态的革故鼎新,不断从繁琐走向简练,并形成多姿多彩的审美形态。中国书法是书写者生命意识的体现。作品审美风貌的形成,与生命意识分不开。其形式风貌足见“人”对艺术审美形态的一种自觉追求。
中国书法;人文与生命精神;中华美学精神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4.009
就中国书法来看,中华美学精神是其突出表现。其中显得最为突出的是人文与生命美学精神。书法艺术史的事实表明,正是由于“人”“任情恣性”(蔡邕《笔论》)言志抒情的审美要求,才导致了书法作品审美形态的吐故纳新、除旧布新和革故鼎新,使其不断从繁琐走向简练,并形成多姿多彩的审美风貌。例如,自上古殷商时期至汉代,“人”的简便实用的记事传意要求,促使了甲骨文、金文向小篆、隶书的演化。又如,两汉时期,统治阶层歌功颂德的需要和边塞军队以及社会基层单纯的书情记事要求,使得规度繁杂和简便自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同时并存。“字以神为精魄”,书法艺术审美风貌的形成,和“神”,即“人”的生命精神,以及书写者的审美趣向与意旨精神分不开。对此,唐太宗李世民说得好:“神若不知,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以副毛为皮肤,副若不圆,则字无温润也。”②唐太宗:《指意》,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21页。所谓“神若不知”的“神”与“心为筋骨”的“心”,即书写者之心性气质、才情旨趣、生命精神。就现今发掘出来的相关文字资料看,最早的甲骨文已经具有相当的审美风貌。后来出现的商周金文,其形式风貌则可以看出其时的“人”对艺术审美形态的一种自觉追求,即如郭沫若所指出的,从“春秋时代的末期”始,在中国书法史上,就出现了一种书家“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的审美意向”③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就其时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看,其一笔一划、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人”的审美意趣,呈现出书写文字的“人”,其独具的匠心,既气韵深沉,又神圣浓重,突显出一种人文与生命美学精神。
一
人文精神是书法艺术审美形态构成的核心要素。文字乃是一种表意的符号,为意义的载体,正是种种表情达意的要求,从而始引发书体的变化,促使其推陈出新,由繁至简,呈现出多样丰富的审美书风。文字书写审美风貌的形成,和“人”的审美趣向分不开。就现今发掘出来的相关文字资料看,最早的甲骨文已经具有相当的审美风貌。后来出现的商周金文,其形式风貌则更能够发现其时的“人”对文字美的一种自觉追求。
从上古殷商时期到魏晋时期,汉字字体日趋成形,而其间文字书写的样式与风格体貌也不再依赖于汉文字的体式,影响书体审美风貌更多的是“人”,即书写者。书写者的审美诉求、指向、趣味和立场,决定着书体风貌。应该说,即使是甲骨文时代,书写者对于审美形式的取向、取舍,也直接影响到书作、书风的差异。就甲骨文看,正如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在《安阳发掘报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所指出的:“盘庚至武丁时,大字气势磅礴,小字秀丽端庄;祖庚、祖甲时,书体工整凝重,温润静穆;廪辛、康丁时,书风趋向颓靡草率,常有颠倒错讹;武乙、文丁之时,书风粗犷峭峻,欹侧多姿;帝乙、帝辛之时,书风规整严肃,大字峻伟豪放,小字隽秀莹丽。”*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3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之五十附册,1965年。这里就表明,在殷商时期,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时期,祖庚、祖甲时期,成辛、康丁时期,武乙、文丁时期,和帝乙、帝辛等五个时期,时期不同,文字书写的风格也各各有异,有的气势雄浑、磅礴,有的秀丽、端庄,有的工整、谨巧,有的温润、静穆,有的颓靡、草率,有的则规整、严肃,多采多姿。盘庚至武丁、祖庚、祖甲早期的甲骨文,“大字”雄伟壮大,给人力拔千钧的感觉,具有阳刚之气;而“小字”则娟秀端正、庄重稳健、 正经严格、 矜重郑重一些,呈现出一种阴柔之美;艺术风貌最显著的是帝乙至帝辛时期,书法严谨有度,八面出锋。这种审美风貌差异现象的出现,显然与“人”相关,时代不同,书写者不同,文字书写风貌自然会呈现出种种差异,林林总总,绚丽多姿,丰富多彩。
到后来,文字则随着时代而不断变易。出现凿刻或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而就西周初期的金文来看,则有的呈现出一种朴茂凝重、瑰丽奇伟的审美特征。用笔藏锋,线条粗细兼施,点面结合,线条丰富,结字严谨,一任自然,如《利簋》《康侯簋》《大盂鼎》等。到西周中期,则呈现出一种典雅平和,装饰意味淡化,更注重线条的质感、韵律与沉稳;章法上疏朗有致、空间意识增强的审美风貌。如:《大克鼎》,其文字风貌就挺拔厚重,线条藏头护尾,圆润遒美,结构均衡,气息幽雅。而西周晚期的金文则文字造型自然抒情,豪迈不羁,创作风格趋于多元化方向发展。如:《兮甲盘》等,均章法整伤、横竖成行贯气,造型优美。粗犷豪放,率意骋怀,有草意,人文个性色彩,极为鲜明。就整体风貌看,其中也呈现出或阳刚、或阴柔的类似书风。
这种阳刚阴柔兼而有之书风的呈现到魏晋时期尤为突出。魏晋时期,人的觉醒导致文的自觉。影响到其时的书作,也导致其从偏重于功用性、实用性向艺术性、审美性的转向。这一时期的书写已经不仅仅作为文字载体,而是超越了实用性,表现出一种审美意趣与自觉的艺术效益追求。其时的书作,受书写者审美风格与个性的影响,体现着书写者的审美取向。如果说汉魏以前,书法中所蕴藉的审美意识还是碎片性的、隐性的,那么,汉魏以后,这种审美意识则呈现出一种系统性和整体性特色。一些书论家也开始对文字书写美学进行理论研究,从理论上对书法审美实践活动进行一种提升。
这种提升的突出标记是文字书写美论著增多。显然,这种现象也体现出魏晋文字书写理论家对于文字书写美的重视。虽然这一时期的文字书写论著还侧重于对技法的总结与探讨,但也有不少内容涉及到书法美学特征。如崔瑗、蔡邕就各在其《草书势》《篆势》中,从审美的立场出发,对草书、篆书作了进一步审视。崔瑗在其《草书势》说:“草书之法,盖又简略……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跋鸟踌,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或黝辫躺韪,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据槁临危,旁点邪附,似蜩螗揭枝。绝笔收势,余蜓纠结,若杜伯楗毒,看隙缘感,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摧焉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时从宜。”*崔瑗:《草书势》,《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17页。在崔瑗看来,书法艺术具有独特魅力。书法艺术的意象,即所谓“法象”,是“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书法艺术由于书写者,即“人”的审美意趣的作用,其“方”、“圆”,均与现实生活中的不能等同,而是生气灌注,多姿多态,不流于整齐划一,避免了呆板、僵化,以及过于规则的形式,而是经过书写者融会贯通、加以创新、个性鲜明,活力与朝气充沛的艺术意象。把书法艺术上升到美学高度的,还有汉魏之际的书家钟繇,在他看来:“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朱长文:《墨池编》卷二《魏钟繇笔法》,《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216页。强调书法之美的形成在于“人”。
三国曹魏时期,刘劭在其所著《飞白书势铭》中对“飞白书”这种书体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云:“直准箭飞,屈拟蠖势;繁节参谭,绮靡循致。有若烟云拂蔚,交纷刻继。”*刘劭:《飞白书势铭》,《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518页。在刘劭看来,“飞白书”的艺术造诣极高,研究达到了“貌艳艺珍”的最高审美境界。所谓“飞白书”,是一种遵循毛笔含墨不丰而形成的虚笔的特点,并以之作为书作基调和外在特征的书法形式。为书家依据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的一种创新书法形式,与那种只重实用的书体完全不一样,更加在意书法的审美价值,注重书法给人审美愉悦。又如西晋时的成公绥,特别推崇隶书的“工巧难传”审美特性,在《隶书体》中强调指出:“虫篆既篆,草藁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规矩有则,用之简易。随便适宜,亦有驰张,操笔假墨,抵押毫芒。彪焕焕骡,形体抑扬,芬葩连属,分间罗行。烂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或轻拂徐振,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渺。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成公绥:《隶书体》,《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0页。所谓“适之中庸,莫尚于隶”,即隶书的应该具有一种中和之美,以“存载道德,纪纲万事”。隶书还应该具有一种只可意会、“工巧难传”之美。正如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所说:“尔乃动纤指,举弱腕,握素纨,染玄翰;彤管电流,雨下雹散,点驻折拨,掣挫安按;缤纷络绎,纷华粲烂,氤氲卓荦,一何壮观!繁缛成文,又何可玩!”*卫恒:《四体书势》,《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这说明,隶书就要呈现出一种实用性,同时,更应该注重审美效应,要巧妙地将实用性与审美性结合起来。
二
大体上说来,中国古代书法美学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书法的审美本质与人文要素,包括审美形式、审美意味、审美范畴、美感特征与人文内涵等。通过此,以深层次地揭示书法的人文本质特征和审美规律。就书法的审美本质看,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人文特性。在中国书法美学看来,书法的特殊审美功用是抒情言志,其审美诉求则为效法天地之道,体道、遵道,进而合道,以呈现书法家心中的生命意识,达成与“道”合一的审美域,也即随心随意、称心如意的审美自由域。进入这种审美域,即书情、人性与“道”一如,天人一体,是为“书之道”。人性的超越,书之法与无法及书之情性的自由性与丰富性,意味着通过书法艺术活动可以使“人”自由地抒发情性,并进而悟道、言道、载道与致道。
就书法艺术的审美本质与审美诉求看,书法在于言志抒情,抒发情志。所谓字如其人。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说:“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者,君子小人所动情乎。”“书”,乃是“人”之“心画”,是书作者心性、性情的一种呈现。对此,宋代的书法美学家朱长文在《续书断·神品》中说:“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朱长文:《续书断》,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页。所谓“鲁公”,即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扬子云”,即扬雄。在这段话中,就以扬雄的美学观点来品评颜真卿的书法,强调指出,其书法作品乃是其内心境界的一种真实写照,其字迹,则是其德行品性的生动体现。书法艺术是书作者的心灵世界的一种呈现,是书作者以线条来表达和抒发自己的情感心绪。所以说,“字如其人”,“书如其人”,人与书,书与人,是二而一,一而二,圆融合一,人书一体。由此,才能达成“书如其人”之审美域。
书法艺术,就是书写人的意志、情趣与追求。清代的美学家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笔情墨情,皆以其人之性为本也。”又指出:“写字者,写志也。”同时,他还以张旭教诲颜真卿的一句话为例,说:“非志士高人,讵可与言要妙?”*刘熙载著,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4页。书法艺术乃“人”之本心本性的一种呈现,是“人”之志向的敞亮,没有远大的志向和高尚的情怀,是不可能获得书法艺术创作的精妙的,也不可能在书法艺术活动中取得极高的成就。的确,隽永的书法作品都是书作者生命情怀的一种呈现,与“志”的澄明,其中都蕴藉着有深刻的生命意义,可以从中看出书作者的审美意趣和审美诉求。对此,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窦臮在《述书赋》中品评任昉的书法艺术时,称其“构牵掣而无法,任胸怀而足凭”。这里所谓的“胸怀”,显然就是书作者的情感,要用书写的技法表达情感,这是书法艺术由内及外的抒发过程。张怀罐在《六体书论》中说:“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知,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以副毛为皮肤,副若不圆,则字无温润也。所资心副相参用,神气冲和为妙,今比重明轻,用指腕不如锋链,用锋链不如冲和之气,自然手腕轻虚,则锋含沈静。夫心合于气,气合于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静而已矣。”项穆在《艺术雅言·辨体》中说:“夫人之性情,刚柔殊禀,手之运用,乖合互形。谨守者,拘敛杂怀,纵逸者,度越典则,速劲者,惊急无蕴,迟重者,怯郁不飞,简峻者,挺掘鲜道,简峻者,紧实寡逸,温润者,妍媚少节……此皆因夫性之所偏,而成其资之所近也。”这些地方所谓的“神”、“神气”、“心气”、“情性”,应该就是现今所谓的书写者的审美意识、审美指向、审美趣味和立场。书写者的“神”、“神气”、“心气”、“情性”,决定着作品风貌的形成。“字以神为精魄”,“心合于气,气合于心”,“手之运用,乖合互形”。书写者所禀赋的“神气”、“心气”、“情性”不同,有“谨守者”、“迟重者”、“温润者”,也有“简峻者”、“纵逸者”、“速劲者”,气质异禀,各个有别,影响及艺术审美创作活动,则形成其各各有异的审美风貌。
中国书法是书写者情性气质、审美感情的生动呈现。蔡邕在其《笔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可以说,正是“人”“任情恣性”、吐露“心声”、“动情”的审美诉求,才导致了作品审美形态的吐故纳新、除旧布新和革故鼎新,使其不断从繁琐走向简练,并形成多姿多彩的审美风貌。自上古至汉代,简便实用的记事传意要求,促使了甲骨文、金文向小篆、隶书的演化。又如,两汉时期,统治阶层歌功颂德的需要和边塞军队以及社会基层单纯的书情记事要求,使得规度繁杂和简便自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同时并存。艺术审美风貌的形成,和“人”的审美趣向分不开。就现今发掘出来的相关文字资料看,最早的甲骨文已经具有相当的审美风貌。后来出现的商周金文,其形式风貌则可以看出其时的“人”对艺术审美形态的一种自觉追求,不少书作,其字里行间、一笔一划中都呈现出书写者的匠心独运,既气韵深沉,又具有浓重的神秘性。文字书写,是书写者“心”、“神”的外显,为其个体生命意识的一种流露。所谓“任情恣性”、“肇于自然”、“造乎自然”等等命题,突出了对个体人文精神与自然精神的强调。
其时,把中国书法上升到美学高度的,还有汉魏之际的书写者钟繇。他认为,书法艺术乃是“流美”。针对他的观点,宗白华进一步解释说:“笔蘸墨画在纸帛上,留下了笔迹,突破了空白,创始了形象。……从这一画之笔迹,流出万象之美,也就是人心内之美。”*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所谓心内之美,包括人的品质、学识、才力、理想、情感等等。书法艺术之美的形成在于“人”,中国书法的内核,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人文精神是艺术审美形态构成的核心要素。书写者的气质精神决定着作品的样式与艺术风貌。影响艺术审美风格形成的是“人”,即书写者。书写者的审美意识、指向、趣味和立场,决定着作品风貌的形成。汉代书写者崔瑗就在其《草书势》中,就从审美的立场出发,对草书、篆书作了一番审视,说:“草书之法,盖又简略。”与篆、隶相比,草书应该打破常规,具有一种创新精神。“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跋鸟踌,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或黝辫躺韪,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据槁临危,旁点邪附,似蜩螗揭枝。绝笔收势,余蜓纠结,若杜伯楗毒,看隙缘感,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摧焉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时从宜”*崔瑗:《草书势》,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17页。。所谓“方不中矩,圆不副规”,就是要求不拘一格,不能按照常规,要有独特创建,既不失规矩法度,又不致落于俗套;必须浅如流雾,浓若屯云,以达成举众仙之奕奕,舞群鹤之纷纷之审美域,给人以彩带飘空、轻纱飞舞、生动奇逸、飘飘欲仙的审美感受。草书独特的艺术魅力离不开书写者的匠心独运,是书写者在创造性审美活动中,运笔结字,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打破常规,从而致使其书作呈现出一种创新审美意识。
与草书不同,隶书则应该具有一种中和之美,以存载道德,纪纲万事。成公绥在《隶书体》中指出:“皇颉作文,因物构思;观彼鸟迹,遂成文字。灿矣成章,阅之后嗣,存载道德,纪纲万事。俗所传述,实由书纪;时变巧易,古今各异。虫篆既繁,草藁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规矩有则,用之简易。”*成公绥:《隶书体》,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0页。所谓“适之中庸”,就是一种中和美学精神的呈现。“中庸”之“中”,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云:“中,内也”,即人之本性情感藏于心内,尚来显露之意。又云:“中,正也。”即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之意;何谓“庸”,《说文解字》云:“庸,用也。”《庄子·齐物论》云:“庸也者,用也。”郑玄《礼记·中庸注》亦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中庸即用中,中庸之道即用中之道。就是不偏不倚的中和之道,也就是中和之美。在成公绥看来,篆书繁复,草书又“近伪”,篆草之间不偏不倚的,具有适中、中和之美的,“莫尚于隶”。隶书“随便适宜”。其艺术结构,点、横、竖、撇、捺,笔画线条均衡适度,“规矩有则,用之简易”,具有一种法度美。所谓“随便适宜,亦有弛张”,表明隶书在作品演变方面,有起有落,有兴有衰,实用和审美、现实和艺术相互融合,适度而不偏执、不外荡。“操笔假墨,抵押毫芒”,既实用又美观,既动又静。“彪焕磥硌,形体抑扬”,文采壮丽,形体有抑有扬,字体错落有致。“芬葩连属,分间罗行”,章法相间,罗列有致。“灿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灿烂如天上的日月星辰放射光辉,华美如锦绣一样富有文采。笔法轻捷地拂掠,扬笔缓慢,节节加劲,笔笔下按,力注其中,动作的恰如其分,力度和姿态一致,“挽横引纵”,“左牵由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工巧难传,善知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只有应会于心,熟练于手,才能意会知晓。字脉行气,贯通浑成。并且,隶书还应该具有一种只可意会、“工巧难传”之美。同时,隶书的书写离不开其实用价值。即如《隶书体》所云:“尔乃动纤指,举弱腕,握素纨,染玄翰;彤管电流,雨下雹散,点驻折拨,掣挫安按;缤纷络绎,纷华粲烂,氤氲卓荦,一何壮观!繁缛成文,又何可玩。”“书”是用来记事的,时代变了,文字也就“古今各异”。而且这种变化由繁到简。篆书繁复,草书又“近伪”,适中的“莫尚于隶”。汉代隶书,具有结构之美,变线条的均衡为点、横、竖、撇、捺等笔画适中和谐,具有“质”的美。且不失法度,“规矩有则,用之简易”,法度与审美一体相融。“随便适宜,亦有弛张”,具有作品的适中之美,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操笔假墨,抵押毫芒”。是艺术写作时的美观实用,具有一种动态之美。“彪焕磥硌,形体抑扬”,文采壮丽,有抑有扬,具有一种形体之美,并且,字体错落有致,“芬葩连属,分间罗行”,章法像香花不断,相间地罗列在每一行,“灿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或轻拂徐振,缓按急挑”;笔法、书写动作,尽皆恰如其分,力度和姿态一致,和谐圆融,“挽横引纵”,逆锋落纸,竖画逆势向上。“应心隐手,必由意晓”。应会于心,熟练于手,手指灵活,臂腕柔和,铺展细绢,濡墨挥毫,笔势如电,行笔如雹,侧点急骤,拔笔方折、挫锋有控、下按稳健。笔势往来,顺逆相成,字脉行气,贯通浑成。“缤纷络绎,纷华灿烂。纟因缊卓荦,一何壮观”!这里就指出,汉隶的书写,就要呈现出一种实用性,同时,更应该注重审美效应,要巧妙地将实用性与审美性结合起来。就中国书法的审美本质看,其独特的审美性生成离不开“人”。艺术的特殊审美功用是抒情言志,其审美诉求则为效法天地之道,体道、遵道,进而合道,以呈现艺术家心中的生命意识,达成与“道”合一的审美域,也即随心随意、称心如意的审美自由域。进入这种审美域,即书情、人性与“道”一如,天人一体,是为“书之道”。人性的超越,书之法与无法及书之情性的自由性与丰富性,意味着通过中国书法活动可以使人自由地抒发情性,并进而悟道、言道、载道与致道。“书之道”即“人之道”。因此,中国书法的核心美学精神就是人性的体现,为“人”审美志向与审美情感的呈现。就中国书法的审美本质与审美诉求看,艺术在于言志抒情,抒发情志。所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也”,中国书法是书写者品德、操行、品性、品藻的一种呈现。
三
在中国美学看来,中国书法,是书写者的生命意识的一种显现,生命精神是中国书法的审美内核。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离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又说:“古文者,黄帝之史仓颉所造也。颉首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孽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诸之书,书者,如也。”按照宗白华先生的解释,仓颉是人类从猿进化到“人”的一种象征。只有“人”,才能够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以体认宇宙天地间的万有大千,领会其中的生命意义。“人”创造了文明,从而产生中国书法*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4页。。
以仓颉为代表的古代先民,取象于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审奎星之势,察龟文之象,辨鸟兽之迹,仿山峙水流,然后化而为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自然万物千变万化,生命形态多样,都是中国书法取法的对象。于草木,法其勃勃的生机,生命的气息;于禽兽,法其跳跃走动,鸾舞凤翔;生命之最高者人,则法其性灵、气质神韵。中国书法取象的过程既是勾勒万物外形的过程,同时又是万物生命的迹化过程。蔡邕《笔论》云:“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其中所谓“入其形”并非要与自然物形似,“有可象”也并非要有具体形象,而是要从自然中攫取生命之象,象之生命。使每一笔、每一字都有动态与生命,使人看到字时便会联想到不同的生命之态,其形可以不真,其象可以不具,但其生命意象,生命精神却生动感人,这便是艺术之道。汉代书写者,主张中国书法必须突出“势”。所谓“势”,可以解释为一种生命力量所表现出来的趋向,在中国书法中,“势”是其表现生命意蕴的重要手段。蔡邕《九势》云:“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 又云:“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作品之势,一笔而成。艺术的空间是灵活多样、变化无穷的,更具有活泼的生命跃动。字之动势展现了生命形象最美丽动人的瞬间,优秀的作品即是创作出汉字最富包孕的时刻的佳作。草书就追求一种“人”的个体生命精神的传达。如崔瑗就指出,草书生成于书写者“观其法象”,以呈现书写者个体生命的艺术。所谓法象,其原本是指人的合乎礼仪规范的仪表举止,引申到草书艺术创作中,则指其书写者书写既要合乎法度,同时还必须要有独具个体生命特色的艺术形象。因此,草书艺术往往“抑左扬右,望之若欹”,在作品上不同于篆隶的对称平稳。并且,草书必须呈现出一种动态美,所谓“兽跛鸟踌,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艺术本是空间艺术,是静止的,但是,草书艺术则有所不同,应该表现出一种鸟兽想要“飞移”,狡兔受惊后将要“奔驰”的动态美,以给人强烈的时间艺术的动态感。所谓“或蜘蛛点蝻,状似连珠,绝而不离”,草书笔势有其自身特色,如“燕”、“然”下面四点,其特色就显然不一样。所谓“若山蜂施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这里就通过种种生动描绘,呈现出草书笔画的曲折、回旋、流畅。表明汉代草书较之篆、隶,线条更流畅,更自由,更具活力,更富意态。
艺术,是表现生命的艺术,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存、发展,成为中国人特别是文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赵壹《非草书》记载云,其时士人“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见腮出血,犹不休辍”*赵壹:《非草书》,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据记载,蔡邕在太学门外正定经典,亲自书写,远近闻之,前去观看,致使巷陌交通堵塞,景象蔚为壮观。宗白华说:美是丰富的生命在和谐的形式之中。艺术,在神秘的线条中展现着生命的活力,在古老的汉字中激活着生命的基因,在黑与白的世界里透视出主体生命的信息,在和谐的形式之中展现丰富生命意蕴。书写者的生命之气、灵性之气和艺术作品的韵味之气在中国书法创作活动中是相互融通、有机统一的。“气”是宇宙万物的生命本原,也是艺术作品“风姿神貌”的生命活力所在,是书写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成的机制,与“气”相通的“生气”、“神气”、“气象”、“气韵”、“气势”、“气脉”以及“风骨”等,构成了一种“气”之审美的动态有机生命意识,呈现于艺术创作中,则为天、道、气浑然合一的、体现出宇宙万物深层生命精神的审美域。
中国书法,是书写者生命意识与审美情感的自然抒发。赵壹《非草书》云:“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中国书法表现“人”内心的生命意识与情感活动。从中国书法的内容和表现来看,“情”既是中国书法表现的内容,也是中国书法独特的魅力所在。“书”以“达情”,“书”以“含情”、“忘情”,中国书法以“情”为本,为抒情之手段。“情”是书写者对自然万物与社会人生的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其中包含有丰富复杂生命意识,需要通过中国书法的创作活动以表现出来。因此,中国书法所具有的抒情性审美特征一直受到人们的认可。如庾肩吾在其《书品》就提出“书尚文情”,指出中国书法乃是书写者内心生命意识与思想情感的抒情性流露,只有内心拥有真实的情感流衍于心,按捺不住,必须形于书表。所以说,“情”的抒发,内心情感的审美诉求既是中国书法的审美本质所在,也是中国书法的独特的审美性所在。
书写者身处一方,情怀万里,宜通过艺术创作以宣扬自己胸中的志向和气概,而中国书法华美的字迹和精神,拆封见书迹,欣然如会面,是可快乐的事。强调中国书法的表情达意的审美效应。
所谓“书以载道”,这里的“道”为“书艺化”了的“道”,或者说是中国书法所指谓的一种生命意识与审美情怀。艺术杰作中,其“艺”、“情”、“道”三者往往圆融一体,完美契合。因此。中国书法又被称之为“书道”。认为中国书法的创作活动就是一种“悟道”、“体道”、“合道”过程,而不是一味着眼于临摹求法,书写的审美诉求应该是宇宙间阴阳合谐,天人一体审美域的达成。一阴一阳谓之道。天地万物,莫离阴阳;阴阳之变,莫过“书道”。“书之道”有如“天之道”,天地自然中的一草一木,皆有“生气”。“生气”,即“天之道”、自然之“道”。“书道”如“天道”。显而易见,所谓的“书道”之“道”,应该就是宇宙间的生命意义。宇宙天地、万有大千,一草一木,一花一树,皆有生命。万物生生不息,化化不已。在这种自然的化生化合中,有生成之生、化生之生;也有创新之生、生存之生、生养之生。万事万物是有生命的,为生命体。整体的生命长河,是同一的,个体的生命,则各各相异。“书道”是书写者生命意识的呈现。其中所蕴藉的生命精神是书写者的个体生命意识与宇宙万物生命意味的相融合一,并通过艺术作品生动的呈现出来,是书写者通过文字符号以呈现生命意识的完美交接。因此,汉代艺术美学推崇“书道”,在艺术创作活动中追求人书一体、书如其人、“书道”如“天道”的审美域。
在中国书法创作中,“书道”是书写者与书作的一体交融。这种交融体现于艺术神奇幻化的审美风貌之中。对于这种审美风貌的形成,庾肩吾称之为“神化”与“参神并用”、“偶合神交”,即自然而然,心手一体,人书一如。中国书法创作活动中这种“神化”、“参神”与“神交”,乃是“合冥契,吸至精”。所谓“冥契”,即天机,天意;“至精”,即天地间至精至微的生气。都是一种天地间的生命精神。可见,“合冥契,吸至精”就是艺术创作活动中作为个体的书写者之生命意识与宇宙间生命意识的合一。在中国书法创作中如何达成这种似“神化”、“神交”审美域是中国书法美学的核心内容。只有达成这种审美境域,才能于书作中生动神妙地传达出宇宙间的感性物态生命。所以说“书道”之“道”,是中国书法形态结构中的最为精深生命精神,也是中国书法魅力之所在。
中国书法的生命力、生机活力都原于“道”,本于“道”。其艺术生命的感性形态最终都根植于“道”。“道”即中国书法的美学精神,体现出中国书法形态所熔铸出的生机勃勃、活力四溅的天人合一、人书合一审美域。所以,“书道”往往是书写者的内在生命意识。的确,人之本心本性就是“天道”的呈现。所以,当艺术家任其自然之情性挥毫舞墨,也就是自身所蕴藏的生命精神流露于书作之中,物我两忘,人书一体审美域的达成。汉字的点、横、竖、撇等八种笔画形状之间的连接方式变化多样,“篆隶正草”等四种字体,等等因素,使得汉字具有繁富的艺术空间,可塑性强,能够通过书写者的艺术创作,成为一种生动多姿的艺术形象,以符指多样的生命体,并呈现出一种生命仪态之美与人情物态之审,于“书道”中达成人道与天道的一体交融。
并且,中国书法推重一种“自然”美学精神。就“书道”看,其中“人道”与“天道”的一体圆融的自然而然的,天然本然,就是“自然”美学精神的生动呈现。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蔡琶:《九势》,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这里就提出“书肇于自然”的命题,认为中国书法应该注重自然、因任自然、返朴归天。自然万物,其生成与存在都是自然而然的,中国书法创作以自然造化为师,当然应当遵循自然,顺其本来的样态。“道”即自然,而书之法“道”,即法其自然,“复归于朴”。“朴”即未受人为损毁的自然,也就是作为生命原初之“道”。“道”本圆满无缺,任天之极,纯任自然。艺术创作的极致是无为无造,一任自然,是“忘我”“丧我”,“物我两忘”的审美域。
所谓自然,有两层意思:一是自然而然,二是山川自然。就第一层意思看,自然,即不假人工雕饰的状态。宇宙间自然万物决然而生,没有任何人为造作的成分。正如《淮南子》所指出的:“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夫有孰推之者?”*高诱:《淮南子注》,庄逵吉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所谓“自然”,就是“不为而自然者也”;乃“自己而然”。因此,“自然”,又谓之天然。就中国书法而言,其生命力的源泉就在其自然精神。所谓“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就此意义看,则自然应该指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汉文字的产生就来自对自然万物的模拟。仓颉造字,即观察天地之形而为之文。而所谓造字“六书”,即象形、形声、转注、假借、指示、会意,等都强调对自然之物的象形。“凡六书之义起于象形”。“象形”就是“观物取象”,即以外部事物为模拟对象为汉字产生的重要途径,所谓“天地之形”、“鸟兽之文”与“山川之类”,为汉字字型构成的核心要素。
汉字的生成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模拟,是上古之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加以创造而成。如仓颉,就“观彼鸟迹”,“博采众美”,以创字。因此,中国书法的内核乃“类物象形”,存在着一种“象形”美学精神,是书写者把自然物象具象化,成为有一定象征意义的艺术符号。
文字产生于自然,中国书法亦然,肇于自然。书写者通过艺术创作,把自然而然、神妙莫测之“道”,艺术地呈现出来。中国书法乃取法自然之象。中国书法的审美风貌也是这样,呈现出一种对立面的变化、运动。所谓“形势”,乃是中国书法中笔画之间连接方式多样变化。这种“形势”审美风貌的形成,生成于书写者对山川自然的体认与模拟,并且通过用笔、结体、章法来加以呈现。因此,中国书法的形式之美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气息的融通合一的。故而,艺术美学认为,中国书法创作,应该以自然为师。对此,宗白华以石涛《画语录》第一章“一画章”里的话,说:“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腕不虚则画非是,画菲是则腕不灵。动之以旋,润之以转,居之以旷,出如截,入如揭,能圆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齐,凸凹突兀,断截横斜,如水之就下,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发强也,用无不神而法无不贯也。理无不入而态无不尽也。信手一挥,山川、人物、鸟兽、草木、池榭、楼台,取形用势,写生揣意,运摹景碌,露隐含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心,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应该说,正是在如何通过中国书法创作,以表现自我、呈现自我自然之心性,进而发现自我、重塑自我的审美意识促使之下,从而致使中国书法逐步走向精致、内敛与静谧。就中国书法的表现形式看,作品不同,作为个体的书写者其表现也各各有异。对此,历代的艺术美学家都有描述。坚持“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审美经验,由此才可以致使力势与神采、黑有与白无等因素和谐一体,以更好地展现中国书法之美。
从中国古代艺术美学思想看,人文美学精神突出体现于有关艺术审美本质与构成要素之中,包括审美形式、审美意味、审美范畴、美感特征与文化内涵等。通过此,以深层次地揭示艺术的审美本质特征和审美规律在“人”。就艺术的审美本质看,其独特的审美性生成离不开“人”。在中国书法美学看来,艺术的特殊审美功用是抒情言志,其审美诉求则为效法天地之道,体道、遵道,进而合道,以呈现艺术家心中的生命意识,达成与“道”合一的审美域,也即随心随意、称心如意的审美自由域。进入这种审美域,即书情、人性与“道”一如,天人一体,是为“书之道”。人性的超越,书之法与无法及书之情性的自由性与丰富性,意味着通过中国书法活动可以使人自由地抒发情性,并进而悟道、言道、载道与致道。
责任编辑:孙昕光
On the art of calligraphy and the spirit of life aesthetics
Lin Ruo1,Li Tiandao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130;2.College of Humaniti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1)
As a brilliant flower of the world culture, th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possesses a strong national color, highlighting the spirit of humanistic and life aesthetics. It is the aesthetic requirement of “man” that leads to the constant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aesthetic form of Chinese calligraphy, going from complexness to concision, and results in colorful and varied aesthetic forms. Chinese calligraphy embodies the life consciousness of the writers. The formation of the aesthetic style of calligraphic works is inseparable from life consciousness. Their forms, styles and features sufficiently show man’s self-conscious pursuit of the aesthetic form of art.
Chinese calligraphy; free and unrestrained; spirit of humanity and life; aesthetic spirit of China
2017-05-06
蔺若(1980— ),女,四川阆中人,成都师范学院文学院副研究员,博士;李天道(1951— ),男,四川彭州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专题研究”(13AZD029)的阶段性成果。
I292.1
A
1001-5973(2017)04-01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