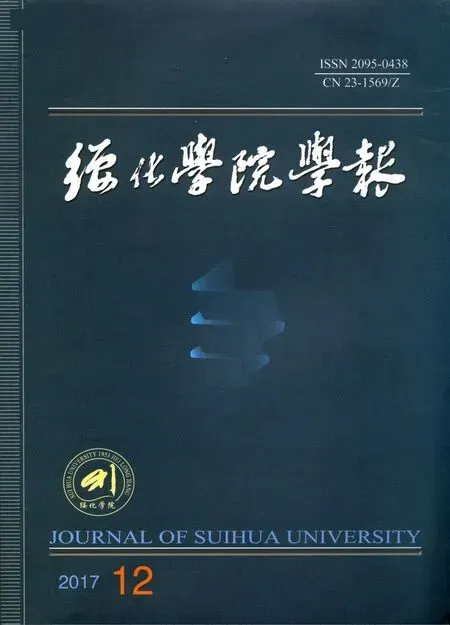《幼幼新书》的量词研究
赵国华
(安阳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河南安阳 455000)
《幼幼新书》的量词研究
赵国华
(安阳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河南安阳 455000)
汉语量词的发展既有共时的语法结构特点,也有历时层面的语法化过程。通过共时层面专书量词的探讨,为其历时发展作铺垫。以《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为参照,研究《幼幼新书》中新兴量词,如“盆”“圆”“停”;较为特殊的量词有“所”“剜耳”“南”。
《幼幼新书》;新兴量词;语法化
量词是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而量词的语法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宋代处在汉语由文言向白话转变的关键时期,就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唐代以来的量词系统,并为后来量词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纽带,所以宋代量词研究也成为汉语量词研究的必需。在各种文献中,医学量词相对丰富,因此我们选取了宋代《幼幼新书》作为专书研究对象。《幼幼新书》是宋代刘昉所撰,刊于宋绍兴二十年,目前通行版本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点校本,是由日本影抄宋本及国内主要藏本相互校勘而成,是最新、最具权威的版本。该书共40卷,676篇,一百数十余成字,是我国儿科学中的一部巨著,主要针对儿科疾病如初生疾病、内科杂病、斑疹麻痘等症状进行治疗,内外治法兼有,以药治为主,兼有针灸外疗治法。正因药治法的普遍使用,该药剂方中的量词非常丰富,通过对《幼幼新书》中的量词进行分类,研究新兴量词的语法结构及其历时发展,希望有利于汉语词汇史研究。
一、《幼幼新书》量词系统的语法特点
《幼幼新书》中共有量词91个,其中名量词77个,动量词14个。我们借助前人和时贤的研究对该书中新兴量词的语法特点进行系统的研究。
(一)量词的增多。我们以《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以及唐五代、宋元时期量词研究成果为参照,总结《幼幼新书》中的新兴量词有“盆”“圆”“停”“剜耳”等 4 个。
“盆”,《汉语大字典》中最早书证是鲁迅的《彷徨·伤逝》,而在《幼幼新书》中“盆”已经作为量词使用,如“即用新水一盆”(《诸寒羸瘦》),并以“名·数·量”的语法结构形式出现。
“圆”在《汉语大字典》中最早的例证是明代《徐霞客遊记·滇遊日记》,而“圆”在《幼幼新书》中作为量词较普遍地使用,如:
(1)放在窟内以纸贴之,其药自熔,其肉自生,一个窟只放一圆药。(《痈疽瘰疬》)
(2)右为末,蜜圆。四、五岁服大豆大十圆。(《五痫异治》)
(3)右捣,合乳和服十圆,即佳。(《求端探本》)
(4)酒服如梧桐子大十圆。日三,渐增至三十圆,以腹中热为度。(《求端探本》)
(5)右为细末,炼蜜搜和,每一两八钱作二十圆,以金箔、银箔为衣。(《惊疾潮发》)
由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这里的“圆”相当于“丸”,“丸”作为量词,用于指小而圆的物体,医书中用于量丸药,如三国魏曹植《善哉行》:“仙人王乔,奉药一丸。”而且多用于指称我国中药的量剂。
“停”在《汉语大词典》中的最早书证是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二:“众僧三百余人,比及扣寺门,十停儿死了七八。”而宋代医书《幼幼新书》中“停”作为量词而存在,提前“始见书”的例证,如“石膏半斤,火煅过如麺,分为三停,留一停为衣。”(《惊风急慢》)“停”当量词讲时,表示总数分成几份,其中一份叫一停,如《水浒全传》第五十四回:“三停中走了两停多路。”而且在现代汉语的口语中也时常应用,如“这稻田十停儿有九停儿是好的”“十停人有八停人去了”。
至于复合量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提出复合量词产生的准确时间,1961年,丁声树先生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一书使用了“复合量词”这个概念,如“架次、千米小时”之类,并解释到,如“飞机出动五十架次”,可能是一架飞机出动五十次,也可能是五十架次飞机出动一次,还有别的可能。同样的,一小时走一千米叫一千米小时。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一书中指出,“复合量词由单纯量词组成的复合单位词”,复合量词的出现是量词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量词系统完善的特征。在《幼幼新书》中的一个新兴复合量词“剜耳”,疑似相当于现代的“挖耳勺”,如“每服一剜耳许,揩牙上一二遍。“(《诸疳异证》),即挖一小耳勺量剂大小的药,涂抹于牙齿上,表示所服用药物的剂量较小。
(二)语法化程度的发展。《幼幼新书》属于方剂医书,多涉及医药配方中不同药物量的多少,所以名量词居多,占总量词数的84.6%。名量词与数词、名词结合得较为紧密,量词前还可受形容词、指示代词的修饰,量词前后还可以加表示约数的词语,如“入盏内约二分许。”(《初生有病》)但《幼幼新书》中有两个系数词的连用,也是表示约数的一个主要形式,如“为使一两颗桃心。”(《方书叙例》)、“每服三、五圆至一、二十圆,人参汤下。”(《惊风急慢》)医书药方虽然在药材大小、重量、数量等方面有严格的称量,但也会经常使用约数的计量方法。
从语法功能角度来看,该书中的数量结构在句子中多数充当谓语,还可以充当主语、宾语。作谓语,如:“川附子一枚”“水八分”“薑七片”(《胎风中风》),从语义指向上分析,数量结构一起修饰前面的名词。作宾语,如:“煮取二合”“煎四分”(《癎论候法》)等,数量结构作宾语在汉代就已经产生,如汉代的《武威医简》:“旦吞七丸,餔吞九丸,莫(暮)吞十一丸。”这里的“七丸”“九丸”“十一丸”在句中作宾语,这种结构在汉代较为普遍。
(三)“名+数+量”结构广泛使用。即使在新兴量词中,已经普遍使用“名+数+量”这一语法结构,如“新用水一盆”、“胡豆大一圆”等,这种语法结构多由药剂方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中药剂方是由各种药材配制而成,所以“名+各+数+量”的结构形式普遍存在,如“杜仲、鹿茸、远志各八铢”、“灸肺腧、心腧、鬲腧各三壮”等,在配方中先写各药物之名称再写药量。
量词“圆”与数词、名词的语法结构“名+数+量”形式已经普遍存在,如:“如大豆二圆”、“如桐子大三圆”(《求端探本》)等,但也有“数+量+名”的语法结构,如:“一个窟只放一圆药”(《痈疽瘰疬》),这时“圆”作为量词已经与名词紧密结合,完全实现了量词的语法化。
(四)俗字的使用。在借用名量词中,“盃”“椀”等一类俗字多有出现,俗字在药剂方中的产生是汉字书写便捷性的一种体现。
《广韵·灰韵》:“盃,杯的俗字”,如“温服,以糜粥一盃,助取汗为度”(《寒热瘧瘴》)。俗体字“盃”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如《汉书·项籍传》:“必欲亨乃翁,幸分我一盃羹。”
《汉语大字典》:“椀,同‘盌(碗)’”。“盌”在汉代属于方言词,《方言》卷五:“盂,宋楚魏之间,或谓之盌。”《玉篇·皿部》:“盌,小盂。亦作椀。”盌后写作“碗”,“椀”与“碗”更换形旁而产生的俗字。在《幼幼新书》中,“椀”字多用于称量水和液体药物成份,如“以水二椀煮一二十沸”(《眼目耳鼻》)、“以水两椀煎至一椀”(《一切丹毒》)、“以生薄荷叶五斤已来,捣取自然汁一大椀”(《五痫异治》)等。
(五)医书所特有的量词。《幼幼新书》中所涉及到的医书中所特有量词,如“刀圭、方寸匕、钱匕、锉、锉匕、匙、匙匕、剜耳、粟、刻、蒸、撮、字、服”等14个,其中较为特殊的量词有“剜耳”,就是挖耳勺,否则工具太大不易在口腔内涂抹或吹入鼻内。又如“粟”是古代的度量单位名,既可以指长度单位,如《淮南子·天文》:“律之数十二,故十二蔈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又可以指容量单位,如《孙子算经》卷上:“量之所起,起于粟。六粟为一圭,十圭为一撮……”。而在《幼幼新书》中“粟”是一容量单位词,如“盐两粟米大”(《初生有病》)、“粥饮滴酒少许,调一粟壳许”(《禀受诸疾》)等,在以上例句中,表示所用之物如去壳小米或如小米壳一样大小的容量。
二、《幼幼新书》的量词系统
量词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类,名量词是对事物量的指称,动量词表示动作作为发生的次数,现兹以分述:
(一)名量词。名量词分为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度量衡量词、借用名量词四类。
1.个体量词。个体量词是计量个体事物的量,又叫天然单位词或天然量词。个体量词有点、滴、颗、粒、块、具、条、只、口、枝、茎、朵、片、叶、丸、炷、柄、件、段、种、文、圆、般、方、夸、枚、个、贴、挺、所等30个。
如上文提到,“圆”作为量词指药丸的个数,也相当于量词“个”如:
(1)一个窟只放一圆药。(《痈疽瘰疬》)
(2)酒服十圆,日再稍加至二十圆,如梧子大。(《求端探本》)
在该书中,把各种中草药混合磨粉并制成大小不等的圆形药丸,称为一“圆”,如“黍大一圆”,说明药丸子如黍、豆、粟米等谷粒一样大的丸子,该义与“丸”指小而圆的物体概念相当,如《禀受诸疾》:“温水下五、七圆至一、二十丸。”
另外,《幼幼新书》中凡提到把药末制作成无具体物可参照的圆时,都用一个符号即“○”来表示,如《惊疾潮发》:“右为末,稀面糊为圆如此○大。”“右件为末,蜜圆如此○大。”在药剂方中这样表述给人一种可比的参照物,提供药剂的大概数量。当然,此类行文中的“圆”字不是作为量词而出现的,而是该书中少有的特例。如果把各种药制作成如豆、黍、米等具体物一样大小时,就会直接表达出来,如《无辜疳》:“右为末,用猪胆为圆如麻子大。”
所,作为量词,犹“处”,指地点、位置;犹“座”,指山、岛等物;也可用于建筑物等,但在《幼幼新书》中相当于量词“个”,如《无辜疳》:“右件药用瓷瓶一所,纳药入瓶中。”指一个瓷瓶。虽然只有一例,但具有“名+数+量”的语法结构,这时“所”已经从名词开始语法化为量词了。
夸,量词。茶叶被焙制成的小方块。金佚名《大金弔伐録·宋主致谢书及报因便附问·别幅》:“与国茶声拣芽小龙团一大角,建州壑源夸茶三十夸(共二百角,每角一夸)。”如《惊风急慢》:“右先研臘茶一夸,入生脑子半钱。”此处的夸指一块茶叶,表示该物的约数。
2.集体量词。集体量词是指表示多数个体的量词,与个体量词相对而言的。《幼幼新书》中的集体量词有“把、捻、堆、双、剂、服、对、握、束、撮、味、停、料、南”等 14 个。
料,用来量食物,但元代仅见量药,如“他有一料药,其效如神,可医百病。”[1]《全元戏曲》第八册)但宋代仍可用来量物,如《禀受诸疾》:“取九家灰一料盛簸箕中。”
依顾亚芹对相关医书的历时考察,[2]如《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药方》四部医书的量词有“贴、味、剂、服、料”,但使用最多的是“服”和“味”,传承性较强,呈现较强的稳定性。“料”在晋代就用如量词,如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卷四:“川芎十两。为末,作两料,每料入麝、脑各一分。”所以“料”作为量词的用例要早于唐代,而彭文芳说“料”作量词在唐代始见用例的观点方可得到纠正。[2]
南,如《惊瘹噤病》:“又面末一南,研入雄黄、朱砂少许。”此句中的“南”大概与“搦”属“音近义通”之词,南属泥母,搦属娘母,依据古声母娘母归泥母,二字属于音近之字,音近则义通,相当于“把”,即表示大概的药量而不是确指。如宋代汪元量《水龙吟·淮河舟中夜闻宫人琴声》:“对鱼灯一点,羁愁一搦,谱琴中语。”
3.度量衡量词。度量衡量词用于计量物体的长短、轻重及容器的容量,有“分、粟、寸、里、尺、围、斗、升、合、钟、匀、斤、两、铢、分、刀圭、 剜耳、刻、字”等19个,其中“围”指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围的长度,如《初生有病》:“甑带一围,烧灰。”可能就是由“围绕”义而来的,没有具体的数值。又“铢”表示重量的单位量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为一铢,如“山茱萸、天雄、人参、茯苓、黄耆、牛膝各五铢”“朴消、牡丹、当归、大黄、桃仁生用各三铢”。(《求端探本》)而“刀圭”就是一个复合量词,表示药物的容量单位,如“右蝇屎以饮,服一刀圭”(《血疾淋痔》)、“米泔浓者煮服一刀圭”(《咳嗽诸疾》)等。
4.借用名量词。《幼幼新书》中有“方寸匕、钱匕、锉、锉匕、匙、匙匕、甕、豆、杯(盃)、盏、盆、钵、碗(椀)、钵”等 14个。盃:在药剂方中也以液体如“粥”为准,如《斑疹麻痘》:“温服,以糜粥一盃,助取汗为度。”盃本为一种容器,多用以盛酒或羹之类。“杯”字从木,“盃”字从皿,二字分别是从物件的材质与类属的器皿来解释“杯子”的含义,二字是使用不同的意符而造成的俗字。正体字“杯”在药剂方中也有出现,如《求端探本》:“作一杯粥食之。”
碗,犹“盏”,用于灯、灯笼等物,产生于宋代,明清通用。[3](P596)如清俞樾《茶香室四钞》二十七:“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载金国遣使过平江排辨司数有云:‘灯笼四百七十一碗。’灯笼以碗称,至今沿之。”但同“盏”相比,“碗”没有作为量词被继承下来,却保留了名词这一词性,所以我们称它为借用名量词,而“盏”被保留为量词,如《身热等病》:“每服一钱,水一盏,入竹叶三片”,一直沿承到现代汉语,是经常用来指称灯的量词,如“一盏灯”,但“盏”作为量词时,也可以这样指称,“一盏酒”“一盏茶”,此时的“盏”作为相当于量词“杯”,即表示一杯酒、一杯茶的意思。
“碗”与其俗体字“椀”,二字是从改换意符而造成的俗字。如:
(1)用水一大碗。(《眼目耳鼻》)
(2)以水两椀煎至一椀。(《一切丹毒》)
也有用“碗”字的,如《眼目耳鼻》:“用水一大碗。”
盆,是计算一般容器盆所盛数量的单位,《汉语大字典》中的最早书证是鲁迅的《彷徨·伤逝》,而《幼幼新书》出现了比它更早的用例,如《诸寒羸瘦》:“即用新水一盆。”
(二)动量词。动量词是表示动作行为的单位,分为专用动量词和借用动量词。
1.专用动量词。专用动量词有“遍、度、返、上、下、壮、行、过”等8个。
行,专指排泄大便的次数,在《本草纲目》中专门指称“利”“泄”两个动词,[3]而在《幼幼新书》中只与“泻”相组合,如《初生有病》:“调粉时点在儿口中极少许,令泻下一、二行,不可再服。”依范崇峰的观点,“行”的这种用法来自佛经,[4]佛经中大便小便分别称“大行”“小行”。“行”由大小便逐渐引申为排便次数义,这种用法仅见于医书中。[2]
返,如《形初保者》:“凡乳母乳儿,当先极挼,散其热气,勿令汁奔出令儿噎,辄夺其乳,令得息息,已复乳之。如是十返五返,视儿饥饱节度,知一日中几乳而足以为常,又常捉去宿乳。”在该句中,“返”相当于动量词“次”,即如此哺乳十次五次。
2.借用动量词。借用动量词就是从其他词类如名词借用来表示动作行为的单位,如“杵、次、遭、转、声、蒸、沸”等6个,一般是借用来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次数。
杵,“在南北朝动量词可借用的范围还相当狭窄。一般说来,它所能借用的还只以名词为限。”[5]如《初学记·墨方》:“捣三万杵”,“杵”是从名词“棒槌”演化为动量词的,一直沿袭到宋代,如《求端探本》:“炼蜜和捣五、七百杵”“炼蜜和捣三、二百杵”。
在《幼幼新书》中多数动词直接与数词组合而没有动量词,如《五癎异治》:“一日一浴,甚者三浴。”《身热等病》:“次于鼻中吹药三两喷效。”这里的“浴”“喷”皆为动词与数词的直接组合。
三、小结
量词是汉语中十分活跃的一类词,但量词并不是一个先在的语法范畴,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实词虚化演变的过程,因此量词多样化的语法功能也是以实词即主要是名词和动词为依托,通过一定的内部句法组合完成某项语法功能,“其语法功能就体现出了多向性,分类、修饰等功能也迅速产生,从而要求量词系统更加丰富、更加细致。”[6]
通过对《幼幼新书》中量词的横向描写和分析,可知在中医药剂方中存在大量的自然单位量词,而且量词使用频率较高,用来指称药剂中的各个成分,这是由药剂方的性质所决定的。“名+数+量”结构普遍存在,名词和量词组合关系还不够密切,还没有成为一种固定的语法范畴。新兴量词的出现,形成了“名+数+量”的语法结构,丰富了中古时期的量词系统。
[1]彭文芳.元代量词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1.
[2]顾亚芹.《本草纲目》量词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3]向熹.简明汉语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4]范崇峰.敦煌医方量词两则[J].中国语文,2009(5).
[5]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李建平,张显成.汉语量词语法化动因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H131
A
2095-0438(2017)12-0065-04
2017-06-10
赵国华(1981-),女,河南长垣人,安阳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文字。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语量词发展史及其语法化研究”(13BYY058)。
[责任编辑 靳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