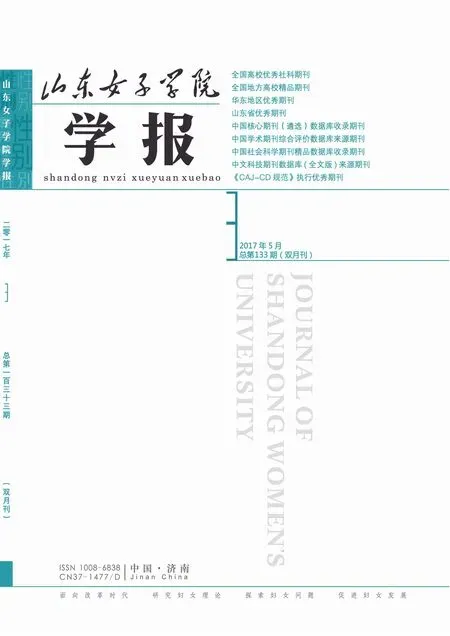近20年来我国家务劳动的社会学研究述评
肖 洁
(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南京 211816)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近20年来我国家务劳动的社会学研究述评
肖 洁
(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南京 211816)
受女性主义对性别平等日益高涨的诉求的影响,家务劳动研究受到多领域学者广泛而持续的关注。通过梳理国内外家务劳动社会学方面的相关研究,可以回顾总结家务劳动意涵、家务劳动性别化相关理论、我国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影响机制、家务劳动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影响,并指出研究不足及未来可探索的方向。
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性别平等;家务劳动性别化
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承担着人口的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功能。而家务劳动则是家庭再生产功能得以维持和延续的关键。传统社会中女性“主内”,承担家务劳动。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解放妇女”的政治诉求与经济领域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双重背景下,党和政府实施的妇女就业政策使女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进入社会劳动领域。女性社会角色由“主内”转而“内外”兼顾。女性不仅总体劳动时间长于男性,而且较男性投入更多时间在无酬的家务劳动上。
女性负责家务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性别差异,它既是两性不平等权利关系的产物,同时也再生产着不平等的两性权力关系。要想实现公共领域内的性别平等,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内的性别不公是一个绕不开的议题。受女性主义对性别平等日益高涨诉求的影响,家务劳动研究受到性别研究、社会分层研究、劳动经济学以及家庭社会学等多领域学者广泛而持续的关注。本文主要在社会学视阈下回顾总结家务劳动的研究成果,以期梳理家务劳动研究现状,了解家务劳动议题的研究趋势,并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性别平等的建构提供借鉴。
一、家务劳动的内涵
家务劳动的研究中,最基础和核心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家务劳动,这个问题看似容易回答,却又不容易得到标准答案。对个体而言,家务劳动司空见惯,存在于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却又因彼此生活经验、所处生命阶段、生活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看法。
学界对于家务劳动的理解和界定,经历了与工作相剥离,继而与休闲活动相剥离的过程。在农耕时代,因为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家务劳动与获取报酬的公共劳动没有加以区分,日常家务劳作混含于生产过程中[1]。在工业化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普及,家庭中的有偿活动与无偿活动被区分开来,人类生活活动被分为两部分:工作与休闲。面向劳动力市场的有偿劳动被视为工作,劳动力市场有偿工作以外的所有活动则属于休闲。在这一阶段,受传统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影响,工作特指与经济收入有关的行为,家务劳动被归于休闲的范畴。随着新家庭经济理论的出现,学界对工作的理解发生改变。与传统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不同的是,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将家庭视为一个“小型生产单位”[2]。家务劳动过程中,家庭劳动力运用外部市场的物品和服务生产出家庭成员生存发展所需的一系列产品,如购买米面肉菜做成可口的饭菜,因此家务劳动也具有工作的特性,属于生产性行为。工作不仅仅是获取收入的劳动,也包含感情和生理上的服务[3]。家务劳动作为带着对家人“爱”与“关怀”的劳动与休闲活动区分开来,被包含于工作的范畴,又因其无偿性而与传统的有偿工作进行了区别。
对于什么是家务劳动,国内定性研究主要从边界、服务对象、目的、内容等方面对其予以阐释。从边界来看,家务劳动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行为[4];其服务对象具有排他性,仅限于家庭内部成员[5];家务劳动的目的是为满足家庭成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6]。
国内定量研究出于评估家务参与情况的需要予以了操作化上的定义,对于家务劳动的测量,绝大多数研究采取了操作化为若干项固定家务劳动项目的方式,询问调查对象是否做过相关项目、花费在其中的时间以及在家中承担的比例,其中以做饭、洗碗、洗衣服、打扫卫生、日常购物、换煤气/维修类重活最为常见。由于研究目的的不同,部分研究侧重于日常家务劳动的测量[7][8],部分研究则注重所有家务劳动项目的评估[9]。
在家务劳动的操作化中,比较有争议的是照顾老人和照料子女的活动是否属于家务劳动。因为养老文化的差异,国内研究中照顾老人通常被视为一项家务;西方研究则区分得非常清楚,并未放入其中。照料子女项目上,有观点认为并非所有家庭都有子女,而且照料子女与其他家务有较大的性质差异,因此不应列入家务测量范畴。一些研究如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均将照料家人的项目单独列出,以获得更为精确的资料。但养育子女所发生的劳动实际是由一件件家务项目所构成的,将养育子女完全划出家务劳动之外在逻辑上并不合理。国内大多数家务劳动的测量都设置了照料子女和老人的项目。
二、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相关理论
家务劳动的性别化是家务劳动的研究中心所在。几乎所有研究都得出一致性结论:作为被建构于性别角色之下的活动,家务劳动存在性别分工。家务劳动的性别化主要表现在家务劳动项目和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上。
为何大多数家庭采取性别分化的劳动力分配方式?相关研究从时间可及性理论、相对资源理论、性别角色理论、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视角出发,对家务分工的性别化展开分析,测量夫妻就业状态、工作时间、相对收入、相对教育程度、性别观念、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夫妻家务分工的影响。
(一)时间可及性理论的解释
时间可及性理论源于新家庭经济学观点。家务分工是家庭成员为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而进行合理分配的结果,由夫妻双方的就业状态和外出工作时间的长短共同决定[10]。新家庭经济理论认为既然家务是生产性行为,那么家庭也会像企业般充分利用资源以追求成本与收益的最佳性价比。时间可及性的解释充分吸收了新家庭经济理论这一思想。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人们有限的时间必须要在工作、家务和休闲三方面进行分配。个人工作时间与家务劳动时间此消彼长,工作上投入的时间越多、工作时间越无弹性,个体在家务上花费的时间就越少。
家庭成员谁花费更多时间在工作上,谁又花费更多时间在家庭中,取决于家庭成员间的比较利益,为让家庭产生最大效用,家庭成员会依据他们外出就业与做家务之间相对产出多寡的比较以及本人工作与家务间性价比的高低来做出家务与工作时间上最有效率的分配[11]。在婚后尤其是生育子女后,由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更多的收入优势,而女性在家内劳动生产方面更为擅长,因而在家务劳动的分工上便形成了女性为主的性别化分工模式。
(二)相对资源理论的解释
相对资源论基于交换论的视角,从“相对资源互惠”和“相对资源议价”的观点出发,主张家务分工是夫妻资源交换和议价协商的结果。夫妻资源是丈夫或妻子可以贡献给对方、以满足对方需求的事物,既包括物质性的经济资源,又包括非物质性资源(包括教育、职业、爱的情感等)。
互惠关系强调个体间的互动建立在彼此互利的平衡基础之上。人与人之间为维持稳定而长久的互动关系,会提供等值的资源给对方,单方的付出难以维持一段长期关系[12]。在家庭中,家务也是一种可以维持家人关系平衡的可交换资源。为维护持久的家庭关系,家中拥有较多资源的一方,主要是经济资源较丰富的一方,可以凭借资源优势,减少家务劳动,另一方则提供较多家务劳动作为资源的交换。现实中,丈夫通常会以相对较高的收入而换取妻子更多的家务劳动付出[13]。
如果说“相对资源互惠”观点视家务分工为夫妻资源对等交换的结果,“相对资源议价”视角中的家务分工则是家庭权力结构下议价协商的结果,强调家务的分配在某种程度是两性间权力关系的反映。夫妻双方资源的多寡决定其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位置高低[14]。家务劳动是一项没有内在价值的工作。在家庭中,能拥有较多资源、较有权力的一方,在家务分配中拥有更大的议价权,通常会负担较少的家务,或者选择较容易的家务,甚至不做家务。而相对资源量较少、权力较低的一方则必须负担较多的、烦琐的家务劳动,当其相对资源增加后,家务分工讨价还价的能力随之提高,会要求对方负担更多家务,减少自己的家务劳动时间[15]。
实证研究中,相对资源的测量偏重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维度,多以夫妻相对收入和教育程度差作为测量指标,其中相对收入被认为是家务分工议价协商中的最关键因素。由于妻子在家庭相对资源分配中处于弱势,在经济上依赖丈夫,她们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便顺理成章。
无论是“相对资源-互惠”的观点还是“相对资源-议价”的观点,两者均强调家庭成员为家庭带来资源的相对量决定了家务劳动的分配。拥有较多资源的男性往往可以免于家务,女性也可以将经济权力运用于她们与丈夫的家务劳动谈判。但夫妻相对资源与议价权的转换受到宏观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16]。在传统父权制强大的社会中,传统性别规范会抑制相对资源的议价作用,虽然女性收入可能高于男性,但这一优势会被宏观层面上的男性权威所抵消,夫妻资源对家务分配的作用不明显;在性别规范趋于平等的文化氛围中,夫妻相对资源的差异较有可能转换为议价能力,影响婚姻权力和家务劳动分工的平等化。
(三)性别角色理论的解释
相对于时间可及性理论和相对资源论视家务劳动为经济及交换行为,性别角色理论主要吸收了符号互动论和女性主义思想对日常生活的解释,视家务劳动为性别象征和社会化的行为,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决定夫妻家务分工方式。
在女性主义看来,家务劳动内在的性别意涵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并嵌入于文化结构中的,它既维护男性特权,又压迫女性接受不平等的现实。男性对政治经济的控制和对意识形态的统治塑造了有利于男性的宏观政策体系和社会分工模式。“女性持家,男性工作”的性别文化规范形成了适合男性和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传统价值观引导着个人去实践传统的性别分工,并不断强化和再生产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家务分工方式取决于夫妻双方性别角色观念的现代性程度[17]。
但夫妻双方经由性别观念所呈现出的家务劳动行为有“无意识呈现”与“有意识展示”的区分。“无意识呈现”型的家务行为模式表现为两性自动社会化成固定不变的性别角色[18],并将之不自觉地、无意识地反映在日常家务分工行为中,自身并未意识到行为背后的性别意涵。“有意识展示”类似于“实践性别”或“性别展示”的概念[19],男女两性会有意识地做出与其社会性别期望相符的行为以获取他人认同。家务劳动并非中性的,而是反映了特殊的性别期待;做特定类型的家务劳动提供了个人表现合适的性别化行为的机会,并借此向他人宣示自己具有某类性别成员的资格。男性和女性通过各自承担的家务劳动量和劳动类型,强化各自的性别身份。女性在婚后尤其是生育子女后会乐意从事女性化的家务劳动,如做饭、清洁、照料并教育小孩,使得她们看起来更像一个好妻子或好母亲。
应该说,三个理论对家务分工的解释各有有力之处,但理论缺陷也显而易见。时间可及性理论和相对资源论偏重于经济层面的考察,将家庭投入产出以及资源全部量化,强调个人决策是理性计算的结果,但忽略了社会文化的影响。个体并非纯粹的理性人,个体决策具有非理性的一面,会因环境和对象而变化;家务也并非纯粹经济化的工作,家务中蕴含着对家人的“爱”与“责任”,这些都是在讨论家务分工时不可忽略的因素。性别角色观念的解释注重测量观念对行为的影响,但两者间的关联也完全可能是因为反向因果关系所导致,行为也有可能反过来影响价值观念。
除了上述三个传统理论外,随着学界对议题的关注,更多的理论被运用于家务劳动的研究,如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
(四)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解释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强调家庭环境会影响家务的供给与需求[20]。不同的家庭发展阶段,家庭结构、子女年龄和个人所扮演的角色都会有所改变,家庭主要任务亦有所调整,家务内容、总量、弹性以及分工模式也会有所差异。婚姻和生育显著增加了家务劳动量,而且这种增加对妻子的影响明显大于丈夫。从孩子出生后到能自立之前,由于传统的母职观念,妻子的家务负担加重,大部分增多的家务量会落在妻子身上,丈夫虽然经历了为人夫、为人父的身份转变,但家务劳动时间变化不大[21]。随着子女长大,自理能力增强,夫妻的家务总量和时间会比前一阶段减少。无子女、离异和单亲的家庭结构会降低家务劳动需求,多子女和低幼子女的存在则会增加家务劳动需求。
(五)社会资本理论的解释
社会资本视角强调嵌入夫妻双方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嵌入其中的资源影响家务分工。在夫妻间社会关系网络各自独立、较为疏离的家庭中,夫妻社会网络重叠度低,彼此间有不同兴趣与活动,双方都能在家庭外部获得精神支持和关系纽带,这种家庭往往会有明确清晰的家务分工[22]。反之,当夫妻社会网络重叠度高,社会支持网络相互重合、有共同的生活圈与兴趣活动时,夫妻间更倾向于采取联合式相处模式,彼此间共同承担家务,不仅丈夫在家务中投入时间相对较多,家务内容上也具有可替换性,如丈夫会经常进厨房做饭,妻子时常负责家庭维修。夫妻双方的社会网络中,当其中一人成为另一人与其他人的桥梁者(Broker)时,也能凭借资讯优势和控制优势,换得家庭事务中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减少家务劳动付出[23]。
三、我国的经验和研究成果
西方对家务劳动性别化与社会经济结构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各种理论取向,拥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内学界家务劳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生活方式研究与家庭研究的兴起,家务劳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价值、社会化、补偿以及时间配置的结构上。2000年以后,随着全国性大规模抽样调查的开展(如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CGSS,CHNS,CFPS),一手大数据的获得成为可能,西方理论视角下规范化的定量研究开始出现,通过OLS回归、Logistic回归、CQR回归探讨两性间的家务劳动分配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家务劳动的影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家务参与,从家务分工视角切入探讨女性权力、地位、公平感和女性群体的内部差异。
(一)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影响因素
家务劳动性别分工影响因素研究的关注点在于中国家庭是通过何种机制进行劳动力分配的,究竟哪些因素会导致男性更多或更少参与到家务劳动中。实证研究从家务分工的理论出发,对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力和理论的解释力进行了检验,得出多元化的研究结论。
1.时间因素的影响。国内研究证明,家务劳动参与受到就业状态(有、无工作)、工作时间(含通勤时间)和工作弹性的影响,影响力因性别而异。
不分男女,无工作者的家务时间显著长于有工作者[20],只有妻子或丈夫工作的家庭,另一方的家务时间均显著增加[24]。工作时间的增加会减少男女自身的家务参与[6][25],且女性的变化幅度大于男性[26]。但也有研究发现,男性工作时间与家务劳动量无关[3]。工作弹性与家务劳动参与成正向关系,工作弹性越大,家务劳动时间越长[8],我国男性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有更多时间参与家务[9]。相较于工作日,两性休息日的家务劳动时间会显著增加;农民的日常工作比非农业人口的工作更富有弹性,前者的家务劳动时间长于后者[20]。
2.相对资源的影响。夫妻相对资源的差异也影响到夫妻的家务分工,但影响力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地域的变化而改变。总体来看,资源因素中收入和教育因素的解释力较强。资源提升所带来的议价能力提高会减少本人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务劳动比例,且对男性的效果更显著[27]。
夫妻相对教育程度的影响方面,丈夫受教育程度高于妻子会显著降低男性的家务参与,但对女性的影响是否显著有不同的研究主张①。当丈夫文化程度低于妻子时,妻子家务时间会明显减少,对丈夫家务劳动时间长短则无显著影响[20][24],此时城镇双职工家庭中更倾向于采取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3]。
夫妻相对收入的影响方面,按相对资源理论的推论,夫妻中某一方收入贡献的提高,会转换为讨价还价的权力资本,从而减少自己的家务投入。但实证研究中,夫妻相对收入对家务分工的影响被分为经济依赖型和性别展示型两类。经济依赖型完全符合相对资源的逻辑,家务劳动时间与家庭成员经济依赖成线性关系,家庭成员经济贡献越少,家务劳动时间越长,表现为经济理性行为。性别展示型的提出则是基于实证研究出现了与理论预期相反的结果,随着男方收入贡献的降低,其家务劳动时间不仅没增加反而持续减少,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增加。原因在于性别文化因素的影响,男性依靠减少家务时间中和其经济角色偏差,展示自身男子气;负担经济的妻子则做更多家事维护男性尊严,弥补双方性别角色的偏差。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男性家务行为接近经济理性[28],女性偏向性别展示[29]。而大陆地区的研究显示,丈夫的家务参与偏向经济依赖型[30]。妻子经济贡献对家务时间的影响,既有经济依赖型的结论,也有性别展示型的观点。城镇女性相对收入的增加可以帮助她们减少家务投入,性别观念越现代的城镇女性,性别展示效应越弱,但农村女性相对经济上的优势并未减少她们的家务时间[31]。
资源并不只是物质性的,还包括非物质性资源。家务是包含着爱的劳动,对配偶爱意更深者家庭权力上的优势会相对较少,会倾向做较多的家务来传递情感。丈夫出于对妻子的爱会在家务上投入更多时间,家务分工模式偏向合作型;妻子则会通过做更多家务表达对丈夫的爱意,家务分工更偏向传统型[3][6]。
3.性别角色观念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性别角色观念影响方面,家务劳动分工主要受丈夫性别观念影响。国内实证研究显示,丈夫持更为平等、现代的性别观念时对家务的投入会增多。妻子性别观念对其家务参与,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不显著或者说并不独立起作用,而是作为经济依赖与家务劳动参与之间的中介变量,使妻子的家务参与呈现为不同类型和程度的“性别展示”[26][30]。在城镇双职工家庭中妻子独立现代的性别观念有助于推动家庭合作式家务分工模式的实现[3]。
除性别角色观念外,子女数量、与长辈同住、健康状况、年龄、夫妻社会资本等均对国内夫妻的家务投入产生影响。多子女通常会并只会加重母亲的家务负担;在无孩阶段和子女6岁前,丈夫更有可能做家务。而与双方老人同住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则有助于减轻妻子的家务劳动量[31]。夫妻中身体健康一方往往会承担更多家务[25];夫妻社会网络重叠度高的家庭更倾向采取联合式家务分工方式[32]。
总体来看,三大传统理论对我国夫妻家务投入及分工进行了有效的解释。就解释力而言,相对资源理论的解释力最强,时间可及性理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作用也得到实证支持。但社会性别文化因素更多影响着男性家务劳动的相对付出,对女性家务投入的影响则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在硬性的工作时间约束以及家庭结构和家庭生命周期的约束下,夫妻间的资源交换和传统性别文化的交互作用决定着女性的家务投入程度。对同一性别群体内部的异质性考察显示,家务劳动三大理论只在家务劳动时间较长的群体中有着较好的解释力;在家务劳动时间较短的群体中需要寻找更强的解释变量[9],现有理论的解释力较弱。
(二)家务劳动产生的影响
除了讨论家务分工影响因素之外,家务劳动研究的另一切入点在于家务劳动的影响,尤其是对家庭和女性个体所带来的影响上。
从家务劳动对家庭的影响来看,基于家务分配所形成的家务公平感作用于夫妻婚姻质量和家庭地位的自我评价,是婚姻质量和家庭地位的重要预测变量[33]。家务分担有助于改善婚姻质量,虽然有女性将承担家务作为婚姻维持的策略[26],但家务参与的时间长短与婚姻满意度并无关联,更多的是夫妻家务的相对量、夫妻双方对家务劳动价值的判断以及家务劳动能否得到家人的认同与尊重[34]决定着婚姻满意度。家务分工的不公平感会随着婚姻的延续而降低,在走出婚姻磨合期后,夫妻家务分工满意度会增加[25]。
国内研究更为关注的是现有家务分工模式对女性自身发展的影响。承担过多的家务劳动,不仅强化了传统性别观念[35],还挤占了女性学习、职业培训以及社会交往时间,影响女性职业素质的提升[36],使之在社会资源占有、机会获取等方面相对于男性处于不利的位置。女性就业领域和就业层次受限,被迫不就业或非正规就业,两性收入差距拉大[37],女性对男性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附属与依赖被强化。最终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持续下降,不平等的社会性别结构进一步恶化。有学者建议,通过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帮助女性摆脱家务的束缚,或者完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以减轻对女性的不利影响[38]。
(三)其他相关研究
家庭其他成员的家务分担也受到关注,尤其是老人的家务分担和子女的家务参与,但研究数量较少。数量有限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家庭中女孩做家务的比例高于男孩,农村学生做家务的比例高于城市学生,中学生做家务的比例高于小学生;学生经常参与家务劳动有助于改善家庭关系,促进其心理健康。祖父母辈参与家务主要是帮助子女照料小孩,料理日常家务,且多以老年女性为主;这种家务劳动代际转移背后是现代社会父权衰落的现实[39],老年女性福利被削弱,家庭权力让渡于年轻女性[40]。
四、小结与讨论
总体而言,国内关于家务劳动的研究,尤其是家务分工影响因素和对女性自身影响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家务劳动的认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和理论观点也日益多元化和精细化,从对传统三大理论的验证拓展到对家庭生命周期的考察,并开始关注家务劳动的情感意涵以及对群体异质性的分析。但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
一方面,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绝大多数研究都以夫妻为主轴展开分析,即便有的也考虑了老人和子女的家务分担,可夫妻仍被认为是家务劳动的主要分配者。但在今天的中国,许多核心家庭的家务劳动不一定是完全由夫妻来完成,其他成员如子女、其他家人(如父母)都有可能分担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家务。家庭还通过雇佣保姆、钟点工的方式,购买社会化家政服务。因此,仅分析夫妻的家务分配完全无法了解中国家庭家务劳动的全貌,家务劳动研究必须考虑到家务劳动的多类型存在。何况多元社会中的家庭形态亦是多元化的,既有传统核心家庭,还有因离异而产生的单亲家庭,因流动而产生的祖孙共居的隔代家庭,以及夫妻分居的家庭。他们的家务劳动及分工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隔代家庭中孙辈是否会承担更多的家务?与传统核心家庭相比,不同类型家庭的家务劳动会呈现出哪些差异化的特点?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还有一点被国内研究所忽视的是,同为女性群体,同样面对家务与工作的双重冲突,她们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宏观或微观的影响因素又是如何在不同的女性群体间发挥作用的?这些也有待进一步的细致考察。
另一方面,目前家务劳动定量研究的数据大多来自妇女社会地位调查、CGSS或CHNS,这些调查本身并非为家务劳动研究而设计,家务劳动的测量指标不能有效满足家务劳动研究的需要。数据的限制导致了研究者在构建家务劳动因变量和解释变量时的困窘,研究者难以对家务劳动展开充分的多视角研究。绝大多数调查仅考察了调查对象自身的家务劳动时间,缺少配偶家务劳动时间的记录,研究模型中并没有在严格意义上测量夫妻家务劳动差距的因变量,也就无从在本质上深入探讨家庭内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差异。在未来的研究中,如果能开展以家务劳动为核心主题的专题性追踪调查,将更有助于人们把握家务劳动分工的动态变化,准确评估解释变量与家务劳动间的因果关系。
注释:
① 运用2010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周旅军(2013)和杨菊华(2014)认为丈夫教育程度高于妻子,不会影响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基于CGSS2006和CHNS2006数据的研究显示丈夫教育程度高于妻子时,会增加妻子的家务劳动参与比率。
[1] 黄宇.家务劳动的女权主义批判考察[J].河北法学,2007,(5):90-95.
[2] 伍伟萍.社会性别视角下“80后”家庭分工模式的研究——以浙江省J市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1-68. [3] 佟新,刘爱玉.城镇双职工家庭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基于2010年中国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J].中国社会科学,2015,(6):96-111. [4] 方英.家务劳动分工:女性的“生活实验”与“性别政治”[J].广东社会科学,2011,(4):219-226. [5] 王金玲.服务于家人的家务劳动也是生产吗?——兼论服务于家人的家务劳动的职业化[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7. [6] 刘爱玉,庄家炽,周扬.什么样的男人做家务——情感表达、经济依赖或平等性别观念[J].妇女研究论丛,2015,(5):20-28. [7] 李亮,杨雪燕.外出务工背景下夫妻资源对农村女性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基于巢湖市居巢区的实证研究[J].社会,2009,(2):199-214.[8] 李芬.关注女性群体内部差异——以家务劳动时间研究为例[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2):53-58. [9] 周旅军.中国城镇在业夫妻家务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发现[J].妇女研究论丛,2013,(5):90-101. [10] Pleck JH,Staines GL.WorkSchedulesandFamilyLifeinTwo-EarnerCouples[J].Journal of Family Issues,1985,(1):61-82.
[11] Becker GS.ATreatiseontheFamily[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1-304.
[12] Chafetz JS.TheGenderDivisionofLaborandtheReproductionofFemaleDisadvantage:TowardanIntegratedTheory[J].Journal of Family Issues,1988,(1):108-131.
[13] Parkman AM.BargainingoverHousework:TheFrustratingSituationofSecondaryWageEarners[J].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2004,(4):765-794.
[14] Blood RO,Wolfe DM.HusbandsandWives:TheDynamicsofMarriedLiving[M].New York:Free Press,1960.1-293.
[15] Bittman M,England P,Flobre N,Sayer L,Matheson G.WhenDoesGenderTrumpMoney?BargainingandTimeinHouseholdWork[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3,(1):185-214.
[16] 福和真子.家务劳动分工和宏观层次的性别不平等[J].国外社会科学,2006,(6):99-101.
[17] Claffey ST,Mickelson KD.DivisionofHouseholdLaborandDistress:TheRoleofPerceivedFairnessforEmployedMothers[J].Sex Roles,2009,60:819-831.
[18] Coltrane S.ResearchonHouseholdLabor:ModelingandMeasuringtheSocialEmbeddednessofRoutineFamilyWork[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2000,(4):1208-1233.
[19] West C,DH Zimmerman.DoingGender[J].Gender & Society,1987,(2):102-117.
[20] 杨菊华.从家务分工看私人空间的性别界限[J].妇女研究论丛,2006,(5):16-21.
[21] Baxter J,Hewitt B,Haynes M.LifeCourseTransitionsandHousework:Marriage,Parenthood,andTimeonHousework[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8,(2):259-272.
[22] Bott E.FamilyandSocialNetwork:Roles,Norms,andExternalRelationshipsinOrdinaryUrbanFamilies[M].New York:Routledge,2014.1-400.
[23] Burt RS.SocialCapital:TheoryandResearch[M].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2001.1-333.
[24] 刘红英.中国城镇家庭家务劳动分工的性别差异[D].上海:复旦大学,2010,1-48.
[25] 徐安琪,刘汉蓉.家务分配及公平性[J].中国人口科学,2003,(3):41-47.
[26] 杨菊华.传续与策略:1990~2010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J].学术研究,2014,(2):31-41,54.
[27] 齐书良.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来自中国双收入家庭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9):78-90.
[28] Nishioka H.Men’sDomesticRoleandtheGenderSystem:DeterminantsofHusband’sHouseholdLabor[J].Journal of Population Problems,1998,(3):56-71.
[29] Ono H,Raymo M.Housework,MarketWork,and“DoingGender”WhenMaritalSatisfactionDeclines[J].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06,(5):823-850.
[30] 刘爱玉,佟新,付伟.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 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J].社会,2015,(2):109-136.
[31] 於嘉.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J].社会,2014,(2):166-192.
[32] 蔡明璋.台湾夫妻的家务工作时间:亲密关系的影响[J].台湾社会学,2004,(8):99-131.
[33] 徐安琪.女性的家务贡献和家庭地位——兼评上海“围裙丈夫”“妻管严”的定性误导[A]. 孟宪范.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390.
[34] 黄河清,张建国.中国当代夫妻家务公平观研究——对上海市2005年抽样调查的一点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86-92.
[35] 李敏.社会性别视野中的城市贫困家庭分工制度[J].学习与探索,2010,(6):191-193.
[36] 杜学元.论家务劳动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及解决对策[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2):35-37.
[37] 付光伟.城镇正规就业女性家务劳动与工资收入关系研究[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4):23-27.
[38] 王歌雅.家务贡献补偿:适用冲突与制度反思[J].求是学刊,2011,(5):80-86.
[39] 沈奕斐.“后父权制时代”的中国——城市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变迁与社会性别不平等历程分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43-49.
[40] 陶艳兰.代际互惠还是福利不足——城市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中的代际交换与社会性别[J].妇女研究论丛,2011,(4):13-19.
(责任编辑 鲁玉玲)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Housework in China in Recent Twenty Years
XIAO Jie
(Nanjing Tech University,Nanjing 211816,China)
Affected by feminism’s increasing demands for gender equality, the study of domestic work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nd sustained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many research fields. Based on th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f housework, the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of housework, theories of gender division of domestic labor,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work, and the impact of domestic work o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direction that can be explored in the future are also pointed out.
housework;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gender equality, gender division of domestic labor
2017-02-28
南京工业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面两孩政策与女性收入获得”(项目编号:qnsk2016005)
肖洁(1979—),女,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家庭社会学研究。
C913.1
A
1008-6838(2017)03-0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