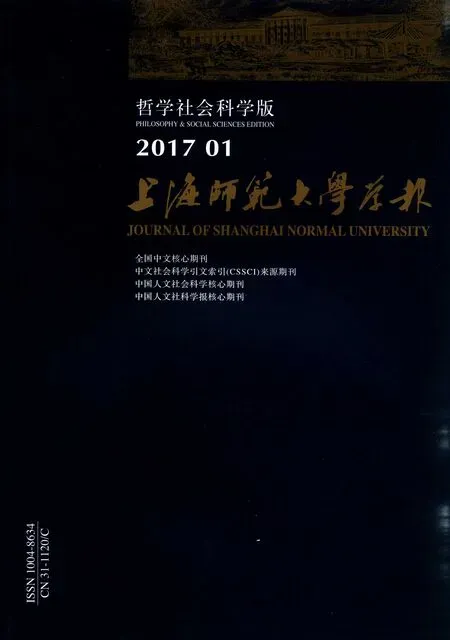也谈“嘉定之变”与上海小刀会起义
——与戴海斌先生商榷
周育民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也谈“嘉定之变”与上海小刀会起义
——与戴海斌先生商榷
周育民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就戴海滨《“嘉定之变”与上海小刀会起义诸问题考论》提出商榷,文章认为该文有关周立春是否经刘丽川动员加入天地会、周立春与罗汉党的关系、周立春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的论析,所依据的史料和推论基本不能支持作者的观点。同时,就戴文质疑是否存在“统一的上海小刀会”问题提出新观点:上海小刀会起义,是以天地会各支派为主干力量,以小刀会为共同名号,在互相支持配合协议基础上,由刘丽川、周立春分别领导城市游民和乡村农民在上海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
上海小刀会;周立春;刘丽川;天地会
戴海斌先生的《“嘉定之变”与上海小刀会起义诸问题考论》①就周立春是否经刘丽川动员加入天地会、周立春与罗汉党的关系、周立春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涉及的有关史料对一些学术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历史上实际存在过一个囊括各股力量、形成整体布局的‘统一的上海小刀会’吗?”戴先生的文章涉及上海小刀会研究中的史料、史实以及研究方法的许多问题,很有必要加以澄清和回应。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两代人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研究付出了巨大努力,1958年出版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在此基础上,1965年方诗铭先生发表了学术专著《上海小刀会起义》(1980年再版)。1993年,郭豫明先生出版了30余万字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对这次起义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详细深入的研究,弄清了许多上海小刀会起义中的史实,但这个“统一的上海小刀会”依然是个问题。我想就戴海斌先生论文中所质疑的有关“嘉定之变”的若干史实做些辨析,并就戴先生所提出的“统一的上海小刀会”是否存在问题谈些看法,请方家赐正。
一、周立春是否加入过天地会
有关周立春加入天地会的记载,戴海斌先生引用颇多,认为均为事后记载,而且查实的若干转抄、误植的证据并不可靠。袁祖志的《随园琐记》写于光绪年间,亦不可靠。他认为可靠的是清政府当时的情报,与后来的地方志记载完全不同,两份情报均出自《忆昭楼洪杨奏稿》,或称周立春拒绝与小刀会约期起事,或称周立春未与“闽广匪首”“同往滋事”。这两份情报均为“嘉定之变”发生之初的报告,戴海滨先生认为这是“可靠”的“反证”。
这里先略谈一下史料可靠与否的判定方法问题。就史料形成的时间关系而言,当然距离历史事件发生越近的记载,要比稍后的记载可靠些。但这并不是我们判断史料可靠与否的唯一依据。除了时间距离之外,历史工作者还需要根据记载人与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程度,事件与记载人的地位、视角、情感态度和利害关系,通过各种记载的综合分析,才能“采信”某些认为是“可靠”的记载。后来的记载,由于记载人可能获得更加丰富的信息,所记载的内容未必不比事件发生时的记载更可靠。
像戴先生所依据的《忆昭楼洪杨奏稿》中的情报资料,一份是1853年八月初轿夫阿毛差往沪[上海]、川[沙]公干,于初七回来,他报告的情形是:“初五情形,系闽粤人勾结乡勇滋事。小刀会匪首者姓李,曾纠合过周立春,约同举事,周正言回绝。”②一个轿夫,并非专业情报人员,按照当时的脚程,一周多时间往来苏州、上海、川沙三地,搞“情报”的时间有多少?讲的又是小刀会与周立春联络的秘密事情,“周正言回绝”,究竟有多少可靠性?这本身就是需要旁证的“史实”。
另一份是在1853年9月17日送达苏州的“松江府禀”报告的情况:“现在嘉定、上海匪徒滋事,民间传言,皆有周立春在内。卑府细加察访,知上邑闽、广匪首,原与周立春交往,是日滋事之时,曾约周立春同往,周立春许而未去。”③周立春已经于9月5日占领嘉定,还以“民间传言”禀报,说明情报叙述相当成问题。“曾约周立春同往”,恰恰说明周立春与上海小刀会已经有了明确联系。“许而未去”,只是说明实际执行情况。这份情报,与前面轿夫所说的“正言回绝”,恰恰是相互矛盾而不是互相印证的。
怎么可以将两份相互矛盾的情报作为互相印证的“可靠”证据呢?
对于第二份情报中周立春“许而未去”,戴先生亦力证周立春当时不可能去。有关记载周立春带队伍的人数、参加战斗与否,也提出了与罗尔纲等先生不同的看法。但周立春有没有带队伍来上海参加起义和周立春是不是带了四千人的队伍来上海、是否参加战斗,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牵涉到“松江府禀”中“许而未往”的情报准确性问题。我就以戴先生力证有误的两条史料进行分析。
一是《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咸丰三年八月初六日记事:
初六日,青浦周立村(春)率兵四千来上海,见闽、广两党不和,遂去。④
二是《北华捷报》1853年9月10日报道:
大批从嘉定和青浦来的人,在周立春的率领下加入广东帮的战斗队伍。⑤
这两条材料,其实互相印证了一个共同事实,即周立春的队伍来过上海。《北华捷报》的报社当时就设在上海英租界,这支队伍来上海应该是记者亲见的。那么,《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的作者与此事的关系如何呢?《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收入此文时未发现作者姓名,现在我们知道,作者就是当时在上海租界居住的王韬。在上海小刀会起事的当天,即1853年9月7日,王韬在其日记中写道:“上海小刀会起事,戕县令,劫道库,据城以叛。元帅刘丽川,粤东人。因作《小刀会起事本末》一篇。”⑥这篇文章不长,王韬写了整整六天,应该是花了很大心思搜集资料用心撰写的。写完之后,把当时亲见和搜集的信息陆续编入“近事述略”,一直记到10月5日(九月初三日)。因此,《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的作者,也是亲见周立春队伍来上海的人。王韬记载周立春队伍来上海的时间是9月8日(八月初六),《北华捷报》记载的时间是9月9日,说明王韬的记载肯定不是根据《北华捷报》。
同在上海的一个外国记者、一个中国文士,共同亲见、记载并报道了周立春带队伍来上海的事实,后来的史学研究者怎么还能说这事不可能?戴先生即使质疑四千人数,也不应该否定周立春带队伍来过上海这一事实。
如果我们相信《北华捷报》记者的报道和王韬的记载,那么,“松江府禀”中关于周立春“许而未去”的情报还有什么可信度?前辈历史工作者或许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小刀会起义的具体论述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没有采信戴先生所提供的这两条“反证”史料,却恰恰是遵循了历史研究对于史料处理的基本原则的。
周立春既与小刀会有联系,并且应约而带队伍前来,那么他是否加入了天地会呢?
郭豫明先生在《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提供了两条证据:一是“嘉定之变”发生后,刘丽川以“义兴公司”的名义发布告示;二是清兵后来从周家抄出“明帝朱洪竹”等红色牌位。郭先生根据这些线索,同时采信《黄渡续志》的记载,对周立春加入天地会一事做了如下叙述:“李绍熙‘导立春赴沪,与刘丽川相结纳’。在刘丽川的动员下,周立春加入了天地会。”⑦
对于郭先生的叙述,戴先生根据他对《黄渡续志》不可靠的判断以及对于清方情报的采信持怀疑态度。而对郭先生的证据,戴先生认为可能是“新成立的农民政权借用天地会组织的一些形式”。如果说用“义兴公司”发布告示还勉强可以“借用”作遁词,那放在家里的朱洪竹牌位还可以说是“借用”吗?
有关周立春加入天地会的证据其实还不止郭先生提供的两条。除了《北华捷报》的报道明确周立春先已加入广东帮之外,在周立春占据嘉定之后,“每人有洋布执照一方,如八卦式样,字句俱不可解”。⑧了解天地会知识的人不难猜测,作者所描写的正是天地会飘布的图形文字。也就是说,参加嘉定起义的都有天地会会员的身份,彼此“以兄弟相称”。周立春在家供朱洪竹牌位,在同党结拜兄弟,在嘉定起义后公开打出“义兴公司”名目,都共同指向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周立春在嘉定起义之前已经是天地会的首领。根据现有材料,周立春加入天地会的途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通过李绍熙、刘丽川等人。
二、周立春与罗汉党的关系
罗汉党在嘉定起义之前的一些活动情况,目前基本史料都是官方文献。从罗汉党的成立到劫财作案、被捕及劫狱的一些经过情况,戴先生都做了比较完整的叙述。罗汉党与周立春的关系,仅根据现有文献的确难以做出定判,但不妨碍我们根据一些史料做出可能更接近事实的判断。
罗汉党与周立春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周立春是否参加了陈木金在南翔仙师庙举行的歃血盟誓、喝“齐心酒”、立三刀会。
戴先生判定周立春没有参加这次盟会的根据是,兼理嘉定县郑扬旌的报告称:“该犯陈木金复往上海,求闽、广人前来入会。即于七月二十四、五、六等日,在南翔庙中宰杀猪羊,祭旆宴饮,歃血为盟,名为‘齐心酒’,亦称三刀会。各人头扎红巾,跪伏地下,不起[知]口作何语,经数时之久才立起来。……幸闽、广来者三十余人,查知卑职新任此地,颇有乡情,不肯入会,已于二十九日经南翔人雇轿送回上海。该犯等见闽广人去,复往青浦纠合匪类救援,已经允许,党羽更多。”⑨
根据这条材料,罗汉党似乎是因上海闽、广人离开,拜盟失败,才求助于周立春的。也就是说,9月初周立春刚与罗汉党人建立关系,而9月5日上午周立春的队伍已经与罗汉党一起进入了嘉定县城。仅依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这样的时间间距实在不可思议。
根据已刊布的其他材料,说明郑扬旌的情报并不准确。清朝官方引用的周立春供词是这样叙述其与嘉定罗汉党关系的:“[周立春]系青浦县已革地保,咸丰三年五月间,该犯纠约邻图地保李章等,带同乡勇,赴县求缓钱粮,哄堂殴官拒捕,旋即外出逃避,至本年七月回家。因署嘉定县知县冯翰拿获抢匪陈木金等,羁押木笼,该犯教令封洪、李章等将陈木金抢出。后闻查拿严紧,该犯探知苏、松、太仓官兵调出防剿,本地空虚,起意谋逆,纠同宁波人王国初、广东人李少卿[即李绍熙]、宝山人杜成斋及王小山等,借宽免钱漕为名,煽惑附近土匪,并勾结闽、广人数千,倡立三合会名目,封王国初为大元帅,杜成斋为军师,并嘱杜成斋书写伪示,刊刻木印盖用张贴。”⑩
清方奏报中将周立春的几次供词混捏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择要概括,难免与事实经过有些出入,但8月17日(农历七月十三日)派人到嘉定参与抢救陈木金的事情却十分清楚。周立春供单称:“本年七月十二[三]日嘉定闹事,是嘉定县人封洪及青浦监生李章与他妹丈戴举人之侄戴砚峰同杨锦廷们因嘉定石角门王裕乾吃官司起衅,后来上海有广东人李少卿并宁波人王国初们前来嘉定。”周立春所说劫狱之后,李绍熙、王国初来嘉定,与南翔庙中歃血为盟的事情在时间上却是相吻合的。郭豫明先生据此认为,周立春倡立的这个团体名称是“三合会”,而不是“三刀会”;所谓“三刀会”是“三合会”之误。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但在我看来更可能是“小刀会”之误。
根据上述材料的分析大体上可以推断,在1853年8月17日之前,南翔罗汉党就与青浦周立春建立了联系。17日救出陈木金之后,周立春、王国初、李绍熙等人在罗汉党的据点仙师庙进行了结拜会盟。会盟三天干什么?不难推断,除了举行仪式之外,主要是商议嘉定、青浦和上海各方面联合起义的事情。
9月4日夜,郑扬旌率乡勇衙役将陈木金拿获处死,5日清晨王国初率百余人冲进县衙企图救人,周立春带队伍占据县城,整个过程基本清晰。
所以,戴先生根据的关键史料,即郑扬旌的报告,闽、广人念乡情不与合作而离去,罗汉党才向周立春求救,除了旁人可以看见的拜会结盟仪式之外,其报告的内幕情况很难令人采信。
对于“嘉定之变”的发生,戴先生说:“实则八月初三日起事具有相当的偶然性。陈木金之被捕杀,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这让读者有点费解。究竟是因为陈木金被捕杀激起了“嘉定之变”,还是周立春们的预定计划?如果预定占领嘉定,那么不管有没有陈木金被捕杀,这事早晚都得发生,就不存在“相当的偶然性”问题,只是可能由于陈木金被捕杀而提前发动而已,这个突发事件也就不是引爆起义的“导火索”。从嘉定起事情况来看,嘉定城内兵丁不过25个,加上郑扬旌带来的30名乡勇,还有一些衙役分散在城门和衙署,王国初带百余人就一下子直接攻进了县衙。周立春与罗汉党大队人马进入嘉定时,兵勇衙役早已逃散,没有“防守”,何来“攻占”?如果事先没有预定计划占领嘉定而且付诸行动,周立春的两千多人怎么可能在陈木金被捕杀几个小时后即一下子从青浦“飞”到嘉定?
至于占领嘉定之时,周立春的队伍头扎红巾,罗汉党人头扎白巾;建立政权之时,罗汉党人并无职务安排,戴先生等据而认为双方心存芥蒂,有一定道理。因为在民众起义过程中,山头派系是个常见现象;罗汉党人随后离开嘉定,攻占南翔,也会加强人们的这种印象。但事情还有另外两种可能:一是罗汉党人不愿承认和服从周立春的主帅地位,导致无法安排罗汉党头目的职位;二是原来的计划中罗汉党就是在上海县城小刀会的系列。后者,从上海县城小刀会起义后徐耀就被封为将军即可看出,在孙渭的供词中有所反映:在罗汉党占领南翔之后,“上海头目陆大哥吩咐,叫陈姓广东人到南翔镇管住居民,不许迁避,且勿抢掠,故此没有杀害的事”。嘉定被官军攻占后,徐耀先往上海,“在广东人刘姓名下为副元帅,小的仍归徐耀处差用”。就陈木金于9月4日夜被拿杀害,周立春心腹王国初连夜纠集百余人赶往县城劫狱救人的真情,我看不出这种“芥蒂”的程度和可靠性有多大。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处理方式是照实记述,存疑与否皆在两可,容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三、周立春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戴先生在文章中引用了不少青浦县“招安”周立春和周立春表示“投诚”的材料,让读者看到了历史人物更加复杂的一面。但就戴先生提供的有关周立春表示“投诚”的材料,也不能证明戴先生所持的周立春有“投诚”清政府意向的观点。
戴先生提供的关于周立春与青浦当局有关“招安”与“投诚”的史料共有三件,时间在八月初二日到十三日。为了说明问题,我把戴先生提供的材料一一抄录下来,做一具体分析。
1.[八月]初二日局函:
青浦抗粮聚众之周立春,现愿投诚报效,已奉抚宪札饬,妥示抚勗。兹经绅士前往晓谕,如果真心,准予免究前罪,随营效力。惟闻周立春以所聚之人率多土著,若调往别处,恐迁地弗良等语禀及,是以又经往谕矣。
2.青浦耆民马大成等禀(原注:八月初十录):
周立春充当地保,舆论素洽,上年因案逃避。今春粤匪窜扰金陵,恭奉上谕,饬令各处自行团练,守望相助,其自行团练,系保卫乡闾,一遇贼匪,即行合力歼擒,则捍御之攻,亦与效力行间同其赏赍,奉宪钦遵分别谕饬地方绅董举办,晓示在案。并有身[免]犯刑章,奉大宪奏准,宽免收录,以备驱策等因。东北乡民心未安,自奉晓谕之后,周立春之兄子即遵谕出劝该乡民,各自团练保卫,得以土匪不致蠢动,守望相安。即奉劝助军饷,亦为辗转劝导有力之户,竭力输将,地方大为得益。伏念前案,周立春等身为地保,先经失于约束乡民,固属咎无可辞,现在其子敌忾情殷,在乡团练,以御外侮,冀赎父愆。可否邀恩详情转奏,网开一面,予以自新……全乡感顶上禀。
3.青浦县禀(原注:八月十三日录):
现在上海、嘉定广匪、土匪纷纷窜扰蠢动,奉闻卑县乡民滋事,案内奉饬缉拿之周立春,匪等约之入伙。周立春久有悔心,坚不从匪。缘周立春先行犯案逃避,嗣因颁贴告示,恭奉谕旨,饬令各处自行团练,并闻宿州招募壮勇案内,有愚民身犯罪名者,曾蒙恩旨。既知感惧,力图报效,亦何不可赦其既往,予以自新等因。是以周立春亲属子侄即在乡团练乡勇,保护闾里,土匪不致窃发。经该处耆老马大成等以闾阎受益,代为环求乞恩自效。卑职窃以事在权宜,当经允其转禀,若将周立春许其出力免罪,当更奋勉自效,实于地方有益等语。
根据上述材料,周立春在嘉定起事之前,与青浦当局的确有过“投诚”表示。而经江苏巡抚批准“招抚”,八月初二日即9月4日青浦县奉札派士绅晓谕之时,周立春的队伍已经出发,准备占领嘉定县城。周立春前后两个南辕北辙的行为如何理解?史学工作者没有特殊的方式做出判定,只能根据一般的社会经验常识。如果周立春脚踩两只船,“投诚”有“船”,为首谋叛,自己就是“船”,一旦自己的“船”翻,即无回踩可能。如果我上文所述可靠,在8月底周立春已经拜三合会,与嘉定、上海方面立誓会盟,这种“投诚”表示更可能是放烟幕迷惑对手。实际行动比口头表示更为重要,“听其言,观其行”的看人方法在这里是同样适用的。
八月初十日(9月12日)马大成的禀文说周立春的哥哥和儿子在接到劝谕之后,已“在乡团练,以御外侮,冀赎父衍”。十三日(9月15日)青浦县还向松江府转禀表示周之兄子有可能为劝回周立春“出力”。这段时间周立春在干什么呢?9月7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周立春的队伍前来上海,在马大成上禀之时周立春已经回到青浦。9月15日青浦县禀松江府还请“将周立春许其出力免罪”的两天后,即9月17日,周立春已经发动了进攻青浦县的行动。那么在周立春进攻青浦县城之前,其兄子在乡劝办团练的目的何在?只能解释为以团练为名,扩大起义队伍!
戴文中毫不怀疑地采信松江府给江苏巡抚的禀文:“八月十五日,据松江府禀:‘卑署府已遣人前往剀切晓谕,劝令投诚自效,免其治罪,果能杀敌立功,一体保奏请奖。及反复开导,该犯颇有悔罪之意,现在已与闽、广匪徒绝迹。其意终虑到官治罪,不肯自投。’”恰恰是松江府禀文到苏的当天,周立春已经拿下了青浦。
戴先生不对这些禀文和周立春的行动做一个简单的时间排列,竟完全采信地方官府的禀文说法,认为周立春依然“投机观望,两面依违”,实在匪夷所思。周立春已经以他的实际行动说明,在9月初向青浦县表示“投诚”的意思只是欺敌之计,它成功地麻痹了官方,扩大了队伍,有效地掩护了进军嘉定、攻占青浦的军事行动。这不是要拔高周立春,而是基于史料得出的合理判断。
历史研究的传统方法,诸如史料比对互证、按时间顺序编列史料(如日期表、史料长编等),有点费力,但却是弄清史实的基本方法。偏执于某方记载,极易误判。地方志史料是中国丰富史料宝藏之一,不能因为其编成年代与历史事件时距较长而忽视。一些文人笔记情况也是如此。就以戴先生批评的袁祖志《随园琐记》中“记袁祖惪事迹”和“袁祖惪传”而言,虽然他是被杀上海知县袁祖惪的弟弟,还是记载了许多与上海小刀会起义相关的“可靠”史实的。我举一例,上海县粮差李祥与潘起亮同伙,稍早的文献大多讳去了李祥的名字,而李祥在激成民变之后“遁浙,更名恒嵩,当勇焉”,这事是袁祖志点出来的。因为李恒嵩后来官至提督,在太平军三打上海时是清军主将之一,并且当上戈登常胜军的副管带,故稍早的文献讳名李祥。而李恒嵩的家乡地方志《相城小志》,在讲到其镇压上海小刀会的军功时,故意只提了潘小镜子即潘起亮。方志编写者碍于李家在当地的势力,虽不敢直书其事,却在行文中留下破绽和线索,其苦心可见一斑。袁祖志在小刀会起义之后依然在上海生活了20多年,熟悉上海历史,他写文章的时候,李恒嵩已死,无需讳言。没有他的这段文字,难免让人以为李恒嵩真是个少有大志的裁缝儿子了。所以,晚后出现的记载,未必不比先出的记载更可靠准确,不能简单地依时间先后来判断史料的可靠性。
四、关于“统一的上海小刀会”问题
戴海滨先生在文章最后提出的“历史上是否实际存在过一个囊括各股力量、形成整体布局的‘统一的上海小刀会’”问题,的确十分重要。我在撰写《中国帮会史》上编部分时,注意到了上海小刀会内部因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各种帮派,上海县城内的小刀会起义和以周立春为主的周边各县起义形成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差异,对这个“统一的小刀会”问题有些困惑,但前辈学者言之凿凿,使我不敢贸然直面这个问题。郭豫明先生发现周立春和刘丽川同称大元帅的证据,更使这个“统一的上海小刀会”是否存在的问题突出了。看了戴先生的文章之后,促使我重新思考这个盘桓脑际多年而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乘这个机会,我简略谈谈自己的一些初步看法。
“上海小刀会起义”作为一个包括上海地区在1853年发动主要起义的历史事件名称,是随着“大上海”的崛起,青浦、嘉定、南汇等均划入上海市以后逐渐确定下来的。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小刀会起义”这个历史事件的名称,也造成了存在一个名为“上海小刀会”的统一社会组织的错觉,然后大家花许多精力去论证这个组织的存在。诚然,在上海县城内起义发生的当天,王韬就开始写《小刀会起事本末》,《北华捷报》的报道也称“the Small Sword Society”,“小刀会起事”在一开始就是当时中外公认的说法。我估计这主要是受到厦门小刀会起义的影响,上海福建帮与厦门小刀会来往密切,积极推动在上海起事,还有些经由厦门来上海的新加坡小刀会员以“大英帝国臣民”的身份公开活动,因此,从上海起事一发生,中外人士很自然地会认为这是厦门小刀会起义在上海的重演。上海县城内刘丽川与闽帮拜盟结小刀会也非空穴来风:“是年春,粤匪犯金陵,全省震动。苏松提镇兵半调防京口,沿海戍守单弱,奸民益肆无顾忌。于是粤人刘丽川、闽人林阿福勾结土匪,私立小刀会名目。”小刀会起义后,也有“义兴公司”钤印的文告。
根据郭豫明先生的发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存在两个军事政治指挥中心,一个是刘丽川,一个是周立春。在上海县城内,刘丽川为大元帅,闽、广两帮虽然同结“小刀会”,但依然保持相对独立性。周立春在南翔与罗汉党、粤帮李绍熙和宁波人王国初等结盟为三合会(一说三刀会),形成了另一个组织系统。我认为,这个清方文献记载的“三刀会”,应该是“小刀会”之误。周立春在嘉定起义后,马上以“义兴公司”的名号发布文告。“义兴公司”名称起源于南洋华侨中的小刀会,厦门小刀会也采用过,周立春用这个名号也是南翔结盟会名为“小刀会”的一个依据。在周立春看来,上海县城的起义是他派李绍熙策动的。罗汉党与周立春结盟以后还保持着相对独立地位,后来进入上海县城附从刘丽川,还依然用“自己人”。这些情况表明“上海小刀会起义”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帮会关系。但无论是刘丽川的天地会、福建帮的小刀会,还是周立春的“小刀会”,同属天地会系统。作为“上海小刀会起义”的主体力量,均属于天地会系统,均采用“义兴公司”这一相同名号,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确存在着一个统一的组织。
但这个统一组织绝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去理解,而要从天地会组织本身的特点去理解。在组织形式、纪律口号、标识暗语相对统一的天地会内部,存在着名目繁多的各个支派,这些支派下的各种堂会均保持着独立性。一个堂会的会员,如果有了自立堂会的资格,与原来的堂会可以是依附关系,也可以是并列关系。一个会员参与多个堂会的结拜,也没有限制。因此,以为这种前近代的社会组织,为共同目标而结盟拜会之后,会消弭原有众多山头,本身就是一个认识误区。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天地会起义中,多个天地会组织联合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几乎多采用山头联盟的形式,或形成一个更高层的军事指挥系统,而不可能形成一个打破原来山头的新的社会组织系统。会党起义军的军事组织系统,也只有在较长的战争环境下才有可能把会党原有组织系统打乱打散。而在上海县城的小刀会起义军,本来就有依乡帮建立的乡勇军事组织,原有的会党很容易调适这种战争环境而顽强生存下来。概括起来,在“上海小刀会起义”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以天地会为基本组织形式、以小刀会“义兴公司”为共同名号的统一组织,但这种“统一”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统一组织。我谈这些,可能有点繁琐,只是要提请注意,“上海小刀会起义”是会党指挥枪,那么,它的领导方式就不可能超越会党本身在历史上形成的多山头主义特点。
在这种以会党为主体而发动的“上海小刀会起义”中,出现了两个独立的军事指挥系统,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是两次独立的起义呢?也不能这样认为。首先,周立春在起义之前,与上海县城内的天地会或小刀会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成了其中的会员,并在嘉定起义之前建立了以自己为大哥的天地会组织,在组织形式上的统一性决定了不能将周立春的起义划出天地会或小刀会起义的范畴。其次,在南翔会盟期间,周立春有明确统一部署上海地区发动起义的考虑,李绍熙前来参加会盟是否代表了上海县城小刀会还有待史料发掘,但从嘉定起义到上海起义在时间上的高度配合、周立春队伍也前来上海支援看,说明双方事先有过协议。第三,周立春的军事行动,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占领嘉定、青浦、宝山乃至进攻太仓,明显担负着扫清上海外围的军事任务,支持着上海县城小刀会起义的发动和政权建立,为上海县城小刀会起义坚持较长时间的斗争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客观上是符合整个小刀会起义大局的。最后,在上海周边各县起义失败的队伍,相当部分都进入上海小刀会占领的上海县城内继续斗争。从起义前的组织关系、军事行动部署,到起义过程中的互相支援乃至起义失败后的最后归属,都说明,周立春所领导的起义,是整个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我认为,上海小刀会起义,是以天地会各支派为主干力量,在互相支持配合协议基础上,以“小刀会”为共同名号,由刘丽川、周立春分别领导城市游民和乡村农民在上海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我是在大体上认同戴海滨先生质疑基础上提出这个初步看法的;但如戴先生那样否认参加起义的各种帮会之间存在“彼此约定,互相支援的同盟关系”,就所看到的上海小刀会起义相关史料,我下不了这种判断。
注释:
①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②《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
③《汇编》,第1171页。
④《汇编》,第41页。
⑤这段报道9月9日上海事态的英文原文为:“a large body of men from Kading and Tsing-poo have come in, under one Chou-lei-tsing, who have joined the Canton party, and enrolled themselves on the side of order.”意为:“大批来自嘉定、青浦的人,在已经加入广东帮的周立春率领下进了城,维持秩序。”原文并没有所谓“战斗队伍”的内容,罗尔纲先生引用的译文(见《汇编》,第55页)不确。需要注意的是,报道已明确指出,周立春在率队进城以前,已经加入了广东帮,也就是刘丽川为首的天地会组织。从报道的上下文关系看,9月9日从道库发现据说有20万两白银,福建帮有人想劫银弃城而去,与广东帮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周立春率队伍进城,“enrolled themselves on the side of order”,意思就十分清楚,是站在广东帮一边,反对福建帮中一些人劫银弃城而去。
⑥《王韬日记》,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4页。
⑦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版,第74页。顺便提一下,在“义兴公司”前面还有四个天地会自造的文字,与上海小刀会文献中出现的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汉字字库中没有这四个字,无法排印,所以郭豫明先生在书中省略了。
⑧诸成琮:《桑梓见闻录》,载《汇编》,第1056页。
⑨《汇编》,第1115-1116页。
⑩同上,第1106页。
(责任编辑:申 浩)
Further Studies on “Occupation of Jiading” and the Small Swords Society Uprising in Shanghai——Deliberation with Prof. Dai Haibin
ZHOU Yum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The paper tends to have a deliberation with Prof. Dai Haibin, the author of “‘Occupation of Jiading’ and the Small Swords Society Uprising in Shanghai”.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provided in Dai Haiping’s paper are not sufficient to prove his opinions that Zhou Lichun was encouraged by Liu Lichuan to join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Lichun and Luohan Par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Lichun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were only inferences. The paper also answers Dai’s ques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 unified Small Sword Society. The Small Sword Society Uprising in Shanghai was launched by urban vagrants and rural peasants, and most of them were the members of deferent branches of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The leaders were Liu Lichuan and Zhou Licun respectively.
the Small Sword Society in Shanghai, Zhou Licun, Liu Lichuan,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2016-11-14
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周育民,江苏启东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K254.42
A
1004-8634(2017)01-0145-(08)
10.13852/J.CNKI.JSHNU.2017.01.019
——嘉定竹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