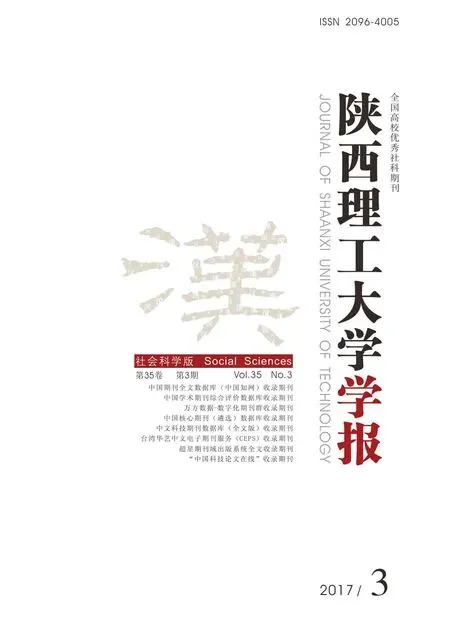对中国翻译学“科学说”争论的再思考
张 倩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对中国翻译学“科学说”争论的再思考
张 倩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翻译学界就翻译学“科学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以往的争论中概念混淆和争论焦点偏移等问题突显,回顾和反思这些问题,尝试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探讨翻译学“科学说”尤其重要,而库恩范式理论又给了研究者关于此话题的全新视角。
翻译; 翻译学; 学科; 科学说; 库恩范式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间,国内学界关于翻译(学)“科学说”的争论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大略浏览相关学术论文标题,可以发现如下的论题:“翻译是一门科学”[1],“翻译不是科学”[2],“翻译到底是科学、艺术、或科学与艺术的统一?”[3],“翻译是具有明显艺术特征的科学”[4]等等。近期,仍有学者发文讨论“关于翻译和翻译学的‘科学’定位”问题[5]。以往的研究和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揭示了翻译活动的本质,推进了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设,然而,这些争论中又存在着概念混淆和争论焦点偏移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些问题,梳理了“科学”一词的概念,尝试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切入翻译学“科学说”这一话题,探索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一、 我国翻译(学)“科学说”争论中存在的问题
1.“翻译”与“翻译学”混用
翻译(translation)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根据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的分类,存在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6]。翻译学界通常所说的翻译是语际翻译这一涉及两种语言文化的翻译现象。在汉语中,“翻译”一词可以指译本(translated text)、翻译活动(translating)、翻译科目(translation subject)以及译者(translator)。此外,人们还经常用“翻译”指代“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7]。
对“翻译”与“翻译学”的混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翻译(学)“科学说”的争论。对这两个概念的混淆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属于使用者对两个概念根本上的误解,用表示翻译活动的“翻译”(translating)指代“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第二种混用属于术语使用上的不严谨,当提到“翻译”的时候,该词的使用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读者应该将其理解为“翻译学”;第三种情况相当于前两种的综合,即,“翻译”一词的使用者时而用该词指翻译活动,时而又用该词指“翻译学”;在这种情况下,争论双方看似讨论同样的问题,实则自说自话,偏离焦点。
谭载喜转述奈达(Eugene A. Nida)的观点,说“翻译是一门科学”[1],张经浩撰文说“翻译不是科学”[2],劳陇在《丢掉幻想联系实际: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一文中指出:“翻译活动是不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所以,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8]。在诸如此类的研究中,翻译到底指的是翻译活动还是翻译学,或有时兼而有之,总是需要读者自己去判断。有些情况下,该词的具体所指通过语境可以判断出来,而有时则无法得出定论。以劳陇的表述为例,我们姑且不论他的“翻译活动是不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这样的断言是否正确,当提到“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的时候,我们不能确定他想表达的是“翻译学不可能成为科学”还是“翻译活动不可能成为科学”。比如,1982年谭载喜发表了引发整个后续大讨论的《翻译是一门科学——评介奈达著<翻译科学探索>》一文,其中第一次提到“翻译是一门科学”,他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一种文学的再创作,而且还是一门科学。这里,所谓的科学,主要指的是翻译的描写性,也就是说可以像描写语言一样,对翻译程序和方法进行客观的、科学的描写,并使之公式化”[1]*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段话里出现了三处“翻译”,读者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解读:第一处的“翻译”相当于“翻译活动”(但是说某个活动是“一门科学”又讲不通);第二处的“翻译”应该指的是“翻译学”,因为只有翻译学才会对翻译活动加以“描写”;而第三处的“翻译”又好像回到“翻译活动”的意思上。
对此种种,王东风与楚至大曾尝试予以澄清,他们说:“翻译与翻译学,如同语言与语言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翻译或语言是实践活动,而翻译学或语言学则是有关该实践活动的理论体系。只有形成体系的理论方可称之为科学。简言之,翻译不是科学,翻译学才是科学”[9]。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讨论中厘清了“翻译”和“翻译学”两个概念的内涵。然而,在“只有形成体系的理论方可称之为科学”和“翻译不是科学,翻译学才是科学”这样的断言当中,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在他们研究发表的1996年,中国的翻译理论是否已经形成体系?其二,即便是这样的体系形成了,科学被定义为“形成体系的理论”,这样的说法本身是否成立?这又引出了对另一组概念的混用或盲目使用而导致的翻译学“科学说”的新一轮争议。
2.“翻译科学”与“翻译学科”混淆
事实上,我国翻译学界早期关于“翻译科学”的争论,其焦点并不是翻译学是不是科学,倒可以称作是翻译学命名问题引发的一场争论:一部分人(如,谭载喜、王东风、楚至大、杨自俭、韩子满)认为应该建立翻译学,于是他们提出“翻译是一门科学”、要建立“翻译科学”[1,7,9-12],另一些人(如,劳陇、张经浩)则明确地反对“翻译科学”这种提法[2,3,8]。由于前一部分人将“翻译科学”等同于“翻译学”,劳、张这种反对的声音则被当成是反对“翻译学”,于是则有了两派之争。其实,劳、张二位反对的是“翻译科学”,或者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反对这个名字、这个提法。马会娟认为:“如果一开始就明确建立翻译学是建立一门学科,而不是研究、探索能够指导翻译客观规律的科学,想必也就不会有劳、张二位先生的竭力反对了。因为,他们反对的并不是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而是反对‘翻译学是揭示翻译活动客观规律的科学’这一命题”[13]。试想,如果一开始就不是用“翻译科学”这样的字眼来指“翻译学”,那么这场争论还会发生吗?是否一开始就称翻译学是一门“学科”而非“科学”,就可使其免遭非议?再假设“学科说”不会导致类似之前关于“科学说”的争论,我们是否可以直接把“学科”一词拿来一用,而不必追究“科学”与“学科”之间的差异了呢?
庞青山和胡卫锋指出:科学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学科是科学的分支或分类,各门学科知识的总和构成了科学整体[14]。根据蔡曙山的观点,科学是第一性的,学科是第二性的。从学科与科学关系的角度,他们总结出了学科的四个特点:第一,科学是学科发展变化的基本指导因素;第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学科,本身不具备知识传递的含义;第三,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或较为成熟的产物;第四,学科是科学研究领域制度化的结果[15]。从中,我们注意到有这样一层意思:一个研究领域可以发展成为学科,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或问题最后都能发展成为新的学科。“一般认为,科学研究发展到成熟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的标志是:独立的研究内容、成熟的研究方法、规范和学科体制”[14]。
这样的论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荷兰籍美国学者霍姆斯(James S. Holmes),他是西方学界最早尝试为翻译学正名的人。在他那篇1972年首次面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中提及两个概念:即“交流渠道”(communication channels)和“准学科”(disciplinary utopia)。文中谈及当时已成为一个独立领域的翻译研究时,霍姆斯引用哈格斯特朗(W. O. Hagstrom)的话表明:就建立翻译学而言,需要分两步:第一,开创交流渠道(如本领域的学术刊物、学术会议、研究和出版机构等等);第二,建立准学科(即上文提到的独立的研究内容、成熟的研究方法、规范和学科体制)。这样才能使科学界人士认同这个正在兴起的新学科,从而在向大学或其他的社会团体呼吁成立这样的学科时具备合理性[16]。再回到国内这场关于翻译学命名的争议上来,我们发现,不论是称翻译学为一门“学科”或者“科学”,都不应该仅仅是抠字眼的问题,而需要切实考察我们当时翻译研究领域的实际是否符合这两个名词所描述的内涵,是否“名副其实”。这样一来,这场名称之争的意义或许会更大一些。
到此,我们就更不能简而化之,擅自替所有曾使用“翻译科学”一词的人解释,说其本意是想指“翻译学”,而那些混用“翻译学”和“翻译科学”的人,也都是在说“学科”而已。奈达作为一个母语为英语的地道美国人,在当初写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的时候,他难道会不知道“science”一词的意思和用法吗?时至今日,各种文献里也仍会不时出现“翻译科学”这样的字眼。这告诉我们,认真地思考和讨论翻译学与科学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二、 “科学”是什么?
根据陈章国的考证,“科学”一词在中国并非古已有之,其起源是拉丁语的“scire”一词,相当于现代英语的动词“know”,表示“知道、认识、了解”的意思。该词的名词形式是“scientia”,相当于现代英语的名词“knowledge”(知识)。后来“scientia”一词进入法语,根据法兰西民族的发音特点,其拼写演化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science”,指“自然知识”。英语吸纳了这一法语词“science”,但一开始,在英语中,该词的意思就是“knowledge”,后专指自然科学。1874年,日本人率先采用汉字当中的“科学”二字翻译了英语词“science”。1897年,中国发生戊戌变法,康有为首次在戊戌奏稿中直接从日语借用了该词*另说该词是1896年梁启超首次使用,见李成秋《“科学”一词的由来》,语文世界,1998年第12期。,从此,“科学”一词逐渐为国人接受。五四运动之后,随着“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的广为流传,“科学”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使用[17]。
经过一百多年的衍沿,汉语中“科学”的含义变得日益丰富,这一点从我们现在常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等表述中可略见一斑。《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科学”作为名词的定义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可见不论“科学”一词如今的含义多么丰富,用法多么广泛,常用工具书中对该词的注解依然是关于其本源的,即知识体系,这也是我们讨论的焦点。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结合的角度,科学通常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系统为研究对象,通常涵盖“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18]。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通常包括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军事学、法学、犯罪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新闻传播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也有人把心理学、历史学之类的学科也包括在内”[18]。人文科学“主要研究人本身、或与个体精神直接相关的信仰、情感、心态、理想、道德、审美、意义、价值等。主要包括现代与古典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神学考古学、艺术等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人文主义方法的学科”[18]。当然这其中有些学科在分类上存在模糊性以及“跨界”的可能,如,语言学、考古学和经济学有时也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历史学既是人文科学又是社会科学;而心理学则可以“横跨三个领域”,可以是自然、社会、人文科学中的任何一种。
然而最令人困惑的是,科学作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上义词,通常在不加修饰和不设特定语境的时候,其语义等同于它的一个下义词“自然科学”。英语中“science”在不加定语时仅指“natural science”。或许正是“科学”一词这样的特点,导致了科学和非科学划分的尴尬局面,即,通常自然科学被认为是科学,而徒有科学其名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却常常被定位为非科学。争议也容易由此开始。
三、 翻译学“科学说”的库恩式解读
翻译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奈达或者某一个人是否认为翻译学是科学没有任何关系[13];也不是靠随随便便的断言,说翻译是(没)有客观规律的,所以翻译学(不)是科学[8];更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人为的或理所当然的给翻译学定位,如“为了和国际接轨,翻译和翻译学应该定位于非科学”[5]。要论证某一研究领域是否可以称为科学,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关涉“科学必须满足什么样的特点和结构”,这涉及到了元科学问题,因此需要借助科学哲学的工具予以考量。
李醒民认为,“从大的原则讲,没有健全的理由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别开来,不论逻辑经验论的可证实原则或可确认原则,还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可证伪原则,都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18]但历史主义学派兴起以后,库恩(Thomas Kuhn)关于科学革命的研究为该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兴起之前,科学作为一种表象的知识而存在;在库恩之后,社会-历史的因素被引入,科学作为一种实践的活动被纳入到历史语境之中加以对待”。[19]库恩开创了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在他1962年出版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当中,“库恩把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描述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这种漫画式图景”[20]。为了尽可能清晰地描述这一模式,他制定了规范这一概念。他认为,“‘前科学’时期无统一规范;‘常规科学’意味着形成了统一的规范,它是科学成熟的标志”[21]。
这里,林定夷使用的“规范”对应库恩的“paradigm”,该词更常见的中文翻译是“范式”。*为了与大多数文献中的术语相符,本文选用后者。也就是说,一个研究领域有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科学地位。那么,究竟什么是范式?范式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学术圈的所有人所达成的一致意见”[20]。根据廖七一的总结,“范式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和形而上学的原则”[22]。库恩认为,范式具备如下的特点:首先,范式所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足以从比邻的研究领域吸引一批稳定的研究者。同时,范式是开放的,可以留给新形成的研究群体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待解决[20]。尽管也有批评说库恩的范式概念颇为隐晦,但是不可否认,在现有条件下,要论证某个领域是否称其为科学,范式理论仍颇具说服力与合理性。那么,就翻译研究领域而言,是否存在范式呢?
廖七一认为:“(翻译)研究范式的演进最明显地反映在翻译理论家划分翻译史的观念上”[22]。廖列举了纽马克(Peter Newmark)所提出的翻译研究的前语言学时期和语言学时期的划分,奈达关于翻译研究的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符号学派的划分,以及根茨勒(Edwin Gentzler)对当代翻译研究进行的五大流派划分,即,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翻译派。同时,廖分析了这些派别之间的更迭所显示出的翻译研究观念、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等的演进[22]。廖七一的分析论证十分有说服力,比照上文库恩所提范式的概念和特点,廖七一已经向研究者初步证明了翻译研究领域的确存在着范式以及范式的更迭。然而,如果说统一的范式才是“科学成熟的标志”,那么,很显然,翻译学界目前还没有实现这样的统一,仍然是多范式并存的状况。
[1]谭载喜.翻译是一门科学——评介奈达著《翻译科学探索》[J].中国翻译,1982(4): 4-11.
[2]张经浩.翻译不是科学[J].中国翻译,1993(3): 39-41.
[3]劳陇.翻译到底是科学,艺术,或科学与艺术的统一?[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6): 39-40.
[4]苏东彦,朱顺.论翻译是具有明显艺术特征的科学[J].宿州学院学报,2006(1): 84-86.
[5]李田心.关于翻译和翻译学的“科学”定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4(10): 94-96.
[6]Jacobson R.“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A].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0:113-118.
[7]杨自俭.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J].中国翻译,2000(5): 4-7.
[8]劳陇.丢掉幻想联系实际: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J].中国翻译,1996(2):38-41.
[9]王东风,楚至大.翻译学之我见——与劳陇先生商榷[J].外国语,1996(5): 8-12.
[10]谭载喜.试论翻译学[J].外国语,1988(3):22-27.
[11]谭载喜.翻译学:新世纪的思索——从译学否定论的“梦”字诀说起[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45-52.
[12]韩子满.翻译学不是梦——兼与张经浩先生商榷[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7):50-52,封三.
[13]马会娟.翻译学论争根源之我见——兼谈奈达的“翻译科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9).
[14]庞青山,胡卫锋.基于知识的科学与学科[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478-480.
[15]蔡曙山.科学与学科的关系及我国的学科制度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2002(3):79.
[16]Holmes, J.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A].L.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72-185.
[17]陈章国.“科学”一词的由来[J].中国翻译,1991(1):42-42.
[18]李醒民.知识的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J].学术界,2012(8):5-33.
[19]何兵.后期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0]Kuhn, T.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21]林定夷.科学哲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22]廖七一.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J].中国翻译,2001(5):14-18.
[责任编辑:王建科 责任校对:王建科 陈 曦]
2016-07-20
2017-04-17
张倩(1982-),女,陕西咸阳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副教授,翻译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
陕西省教育厅2016年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6JK624);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重点项目(byjs201501)
H059
A
2096-4005(2017)03-006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