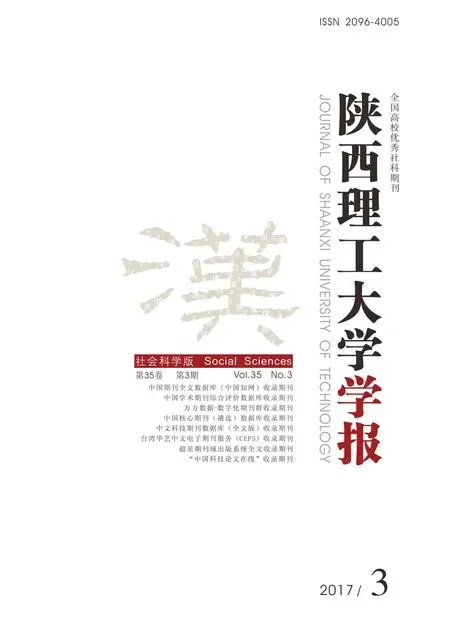少数民族村落空间变迁的个案考察
——以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蝴蝶村为例
念鹏帆, 郭建斌
(云南大学 新闻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少数民族村落空间变迁的个案考察
——以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蝴蝶村为例
念鹏帆, 郭建斌
(云南大学 新闻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街道空间的每一次演变都传递着村落社会变动的信息,少数民族村落的空间变迁与国家的权力有关,空间以不同形式被调试与重组,从而改变了少数民族村落空间的演变逻辑。蝴蝶村建筑以街道为轴分布,村落街道上的建筑布局,既展现着蝴蝶村的历史沿革,也透露着附着在街道上的建筑与村落错综复杂的联系。
少数民族; 村落空间; 空间变迁; 权力
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学界对“社会空间”(英语:social space,法文:1’espace social)概念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地理学等学科都试图从本学科角度讨论社会空间。作为理论概念的“社会空间”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19世纪末创造和使用的,后来列菲伏尔、帕克、索尔以及布尔迪厄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发展了社会空间的概念。本文所指的社会空间是狭义的社会空间,即作为村落社会的社会空间,具有地理与社会的双重含义。借用列菲伏尔的定义,他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空间)的产物”,社会空间是由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生成的生存区域,并被不断地建构。这在他的代表作《空间的生产》中已有论述。在米歇尔·德·塞托看来,“空间就是一个被实践的地点,对空间的划分使空间结构化了。一切都与这种区分有关,它使得空间游戏得以发生。”[2]206并且,“空间结构是以一种微弱但却重要的构造方式与社会关系和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相联系的,空间的生产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结果。”[3]29“空间的社会建构是空间的一种实际转型,其间空间经由人们的社会交换、记忆、影像和对物质平台的日常使用成为传递象征意义的场景和行动。”[4]根据国内学者的著述,“社会空间研究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空间是社会的产物;(2)空间负载着社会性;(3)空间是发展变化的。”[5]本文以蝴蝶村为例,将少数民族村落社会整合于村落空间分析之中,遵循“社会-空间”辩证分析范式,即村落空间是村落社会的产物,村落空间反作用于村落社会,把该村落的社会生活放置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之内,透过历史之镜,分析该村落空间背后隐含的社会意义、影响空间塑造的因素以及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蝴蝶村位于东经103°35′50″,北纬24°41′27″,地处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圭山镇东北部,是一个撒尼、黑彝聚居的彝族村寨,古名“母猪庆”。
相传从前村子里经常会有强盗抢劫,有一次,一个妇女在抱着小孩逃难的时候,因为孩子太闹腾,没有办法逃躲,于是就把小孩放到一个树洞里,并许下承诺,如果回来找寻时小孩还活着,就一定会杀猪祭拜这棵大树。没想到,这个孩子竟然靠着露水甘霖活过了难期,妇女便兑现承诺,在大树下杀了一头母猪并行礼祭拜。村落因此得名“母猪庆”,后据村中金竹成林,谐音雅称“亩竹箐”*为表述起见,文中在不同历史时期采用“亩竹箐村”或者“蝴蝶村”称谓,均指同地,蝴蝶村彝族语言称之为“bu lu qie ”(布路切)。。而撒尼语翻译过来就叫做蝴蝶村,因此得名*资料由蝴蝶村老支书昂某口述,经念鹏帆、钟林芳整理而成。。
2006年行政区划前蝴蝶村为原亩竹箐乡政府驻地。蝴蝶村村委会1949年前属陆良县圭山乡,1950年属路南县圭山区,1957年为亩竹箐乡红旗高级社,1958年为圭山公社红旗管理区,1961年属圭山区亩竹箐大队,1963年属圭山区亩竹箐公社,1970年为亩竹箐公社亩竹箐大队,1984年为亩竹箐区亩竹箐乡,1988年为亩竹箐乡亩竹箐办事处。2000年因村级体制改革撤销办事处,在辖区建立村委会,称亩竹箐村村委会,属亩竹箐乡。2006年行政区划作出调整,“撤乡并镇”,亩竹箐村不再是单独的乡,划归圭山镇所辖。[1]随后亩竹箐村恢复彝语直译汉语地名“蝴蝶村”,2008年亩竹箐村村委会改为蝴蝶村村委会并沿用至今*资料来源:《圭山镇蝴蝶村村情概况》、碑文《蝴蝶村的来源》、《铁厂建村三十年史略》、《石林年鉴》,部分资料由大学生村官王强整理提供。为保护调查者隐私,本文使用的所有姓名均为化名。。
二、 空间变迁——对蝴蝶村不同时期村落空间的阐述
(一)建国之前的村落格局
蝴蝶村自古以来交通便利,古时候是个制高点,战乱年代人们就在此安营扎寨,被称为圭山的小后方。本文关注的村落街道*村落本无街道,街道是城市的产物,但由于2006年之前蝴蝶村是乡镇府的行政中心,不自觉地形成了街道,在“后乡政府”时期街道仍然存在。在当地人看来,他们通常不将其称之为“街道”,一般使用“村路”(乡村公路的简称,彝族话qie guo gao mao)、坝塘边的路、乡政府后面的路来称谓,但是据我们的田野资料,它已经具备街道的基本属性,所以本文以街道通称。是矣木县级公路一部分,约1.5公里。现作为街道的乡村道路在蝴蝶村的历史由来已久,古时候这里便是石林盐道的一段,是古代陆良、师宗、泸西经商马帮过往宜良、昆明的交通要塞。蝴蝶村至圭山镇道路南北贯通,自南向北经村中腹地穿越5公里,是主要的对外交通干道。据当地老人家讲,从建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到20世纪初期,这一段路都是“泥土路”、“石渣子”路,与大多数乡村公路一样,经过村落的部分往往会因缘际会形成街道。从乡村泥土路到硬化成的柏油路,再到街道的形成,我们能够感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痕迹。

图1 蝴蝶村街道示意图
附着在蝴蝶村街道上的社会实践形成了蝴蝶村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空间,形成后的社会空间指导并制约着蝴蝶村社会空间的实践,再生产或创造出新的社会空间。从图1观之,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公共设施,抑或服务性行业,位于街道之上的空间塑造着村落空间的模样,同时也改变着街道本身的形态。这体现了德塞图所谓的“行走”(walking),“‘行走’在城市中,人和周围世界之间是互相作用的,他就在世界之中,他占用了城市空间,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空间,他在空间中的移动模糊了空间的界限,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故事。”[6]“行走”打乱了稳定的村落秩序,使“窥视者”得以从街道的管辖中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空间和意义。崔波认为,“城市的空间是现代性的一个结果,城市本身作为一个媒介,又构筑了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7]笔者认为村落的空间同样是现代性的一个结果,村落本身作为一个媒介也在建构着村民与村落社会的关系。而街道又是村落最主要的媒介,是蝴蝶村的“脊梁”,具有交通和公共空间的双重职能,始终扮演一种整合的力量。“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的诞生真正源于社会的生产时间和它牵涉到的社会关系。”[8]空间是意义和物质的载体,而主体的行为是联结两者的关键,当主体作出行为时,空间便获得了社会意义。过去的街道与现在的街道归属不同性质的社会,人们在当时的空间里不停地寻找自我的定位和归属,从目前再造的蝴蝶街道空间观之,自造空间是被迫改正与主动选择的自为结果。尽管街道两侧基础设施象征的行政权力已经式微,但是基础设施的象征意义依旧还在。国家权力始终是主宰中国少数民族村落社会命运的力量,少数民族地区也正在试图以不同的方式与国家的权力相互整合,比如彝族治彝,努力挽救彝族文字和语言。观察街道空间的变迁,笔者认为只有对基层组织代表的金钱和权力重新审视,才能延续乡村街道的生命力,从而促进街道向公共空间属性回归。中国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公共资源的平等使用,通过组织不同利益团体的对话来对矛盾进行协调,从而在街道上实现一种社会生态的良性平衡。从乡村马路到柏油路,再到现在的蝴蝶村街道,街道空间的每一次演变都传递着村落社会变动的信息。街道作为蝴蝶村主要的空间载体和生命之轴演绎着蝴蝶村过往的历史,也陪伴着蝴蝶村走向不确定的未来。
(二)1949-2006年的村落空间变迁
从1949年始,蝴蝶村分别经历了合作社、人民公社与生产大队时期。顺着道路进入村庄,再从分叉路口进入村落的腹心地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清澈的一汪坝塘水。坝塘子几乎与村落同时存在,位于蝴蝶村村落的中心地带,是蝴蝶村的“生命之源”和“精神之源”。随着坝塘子周边的维修,象征着现代意义的钢筋水泥把坝塘子修建的精致坚固,以前的泥塘子摇身一变穿上了现代化的华丽外衣,从纯粹自然的空间变成了以人工为外壳、自然为内核的公共空间,曾经的泥土坝塘子成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的一枚“功勋章”。与坝塘子相连的还有大礼堂,大礼堂始建于1950年代,是“人民公社”时期遗留的产物。在经历数次翻修之后,现已成为蝴蝶村的文化中心和待客中心。村里的红白喜事悉数在此承办,大礼堂的便利性、实用性和崇高性使其成为村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坝塘子与大礼堂不约而同地连接了蝴蝶村的过去与现在,蝴蝶村的传统与现代在此相遇。公共空间作为基础性的资源理所应当地被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日程之中,公共空间的数次现代化修缮已经表明公共空间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然而,一旦这些公共空间被当作工具性资源使用时,蝴蝶村的社会空间已经脱离了少数民族村落的特质,进入一种同化的建构。我们或许可以在节庆等特别时刻感受到少数民族的独特魅力,然而,在平常时间,这里的“空间”跟其他汉族地区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似乎一些现代化的器物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嫁接”十分“成功”,但仔细一看总觉得喧宾夺主、不伦不类。
19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比拟地理空间的意义上使用“社会空间”一词来表示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所构成的“场域”。“在布尔迪厄那里,社会空间实质上是具有若干权力关系(或资本关系)的空间。”[9]各种各样的社会空间组成了各不相同的场域,布尔迪厄由此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空间图式。然而由权力构成的社会空间在蝴蝶村的不同时期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并深深地改变着蝴蝶村。亩竹箐乡政府行政中心在蝴蝶村的存在是村落发展不能忽视的重大历史事件,行政中心的转移与村落的变迁关系密切。从2006年实行“撤乡并镇”后,亩竹箐村委会属于圭山镇所辖。亩竹箐乡政府时期的基础设施随着行政中心的撤离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基础设施的行政职能已经转移到圭山镇政府所在地海邑村。尽管亩竹箐乡政府时期的基础设施用房仍然还在蝴蝶村,但是蝴蝶村并没有使用权。基础设施的所在地已经用作其他用途,镇政府将包括老医院、农机站、供销社在内的场所租给在蝴蝶村的打工者,如在此维修变电站、架高压线以及种植三七的外地人。1982年,蝴蝶村实行“包产到户”,基层组织村委会由此形成,之前的村委会位于现在的农机站,近几年搬至到公路旁边,使其可以更加便捷地治理村落。行政区划的变革对少数民族生活的影响虽然说不上很大,但是村落空间由此发生的变化与重组却是十分明显的。“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10]13-14从亩竹箐乡政府时期作为行政中心的基础设施到蝴蝶村时期的一般住房,国家行政力量的“进入”与“退出”重构了这个村落的社会空间,并不断地改变着村落社会的公共生活。与此同时,村委会的空间布局反映了村落的社会实践,村委会作为村落社会空间的中心,位于“广场旁”、“街道中间位置”,特定的、优越的空间位置使得村委会更加容易注视村里的一切,村委会里的“人”的一言一行主导着村落的空间实践,村干部的所作所为又重构着村委会的空间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力。“空间变成了一种社会生活的经验事实,构成了经验现象的表征和知识系统,空间构成了浓缩和聚焦现代社会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11]村干部选举触动了蝴蝶村人最敏感的神经,它俨然已经成为村落社会矛盾的导火索。表面上看,国家似乎是放松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给予其足够多的自治权,但扶植地方代理人、行政权力的模糊化*根据我们的访谈,石林县煤矿炭山综合执法队尽管表明他们和蝴蝶村没有关系,但是据我们的调查,一旦这个村落出现“动乱”,执法队会对其进行干预。以及转变治理方式等表明,行政中心的撤离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威的弱化。通过强化基层治理,国家以更为“柔性”与“委婉”的方式将权力以不同形式渗透到蝴蝶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权力在改变村落空间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少数民族村落的日常生活。
(三)2006年至今的蝴蝶村
现在的文化体育广场位于蝴蝶村街道的东侧,背靠原乡政府所在地,面向坝塘子,与村委会隔街相望。广场于2013年修建完成,之前是老百姓的菜园子,后几经改修,成为该地新农村建设的最大成就。与现代都市广场一样,这里有大舞台和大场地,也有黄蓝交织的健身器材,并且面积广阔,与坝塘相映成景。广场的建成标志着蝴蝶村正在走向现代,值得一提的是,村委会还为此举行庆功仪式。但是根据大量观察,广场的健身设施利用率很低,广场通常是空的,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态。调查发现,小孩子从小开始分别在蝴蝶幼儿园、蝴蝶小学以及圭山中学等寄宿学习,平时很少回来,即使回来,也很少在广场玩耍。中年人平日忙于生产劳动,尽管酷爱唱歌跳舞,但通常是选择在某一家户里举行娱乐活动。老人家一辈子都在农村干活,很少有与城市老人同样的健身爱好和娱乐活动,即便是在晚年,甚至七八十岁的时候,通常选择继续下地干活,干活在他们看来就是锻炼身体的最好方式。广场最热闹的时候是村委会举办大型活动时,包括上级领导、临时聚集的商家以及周边村寨的人们会临时出现在这片场地上,文化活动的开展把平日里忙碌的人们组织起来,此时广场便体现了政府建设的初衷,然而这种使用是短暂的、临时的、有目的的靠拢。“现代空间实践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社会行动对空间的改造要求与社会的节奏吻合。”[12]240无论说这样的社会节奏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逐利行为,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题中之义,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主导的思维逻辑彻底重构着少数民族村落的空间,并被强制整合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议程之中。在广场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过度干预打乱了村落本身的日常运作逻辑。“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性特点,就是许多应该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段的事情,被压缩和重叠在同一个时间段内。”[13]3国家试图把少数民族村落的发展卷入到现代化的建设中,但是在没有考虑地方性知识时就武断地作出决策,这是值得商榷的。
服务性行业在亩竹箐乡政府时期开始发展,后几经转折,目前该村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乡村街道。现在的蝴蝶村仍旧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村落社会,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来自一年到头种植烤烟、玉米以及土豆所得,相比之下,经营第三产业收益相对较高,街道以及主要岔道沿线的家庭收入明显高于非街道沿线的。据统计,现有餐饮店7户,商店5户,农资店2户,修理店、村级服务站、卖拖拉机店以及私人医院各1户。这些服务性行业能够在这个村寨长期存在,源于蝴蝶村之前作为行政中心所在地,且交通便利。但调查发现18家服务性行业中有12家的所有者是现任或曾任村干部及他们的亲属,换言之,街道服务性行业大部分被村里面有权有势的人占据。叶涯剑认为,权力对空间形态的操控是显而易见的,土地所有权赋予“空间占据者”的空间控制能力使其在社会互动中获得主动的地位。村干部或者村干部的直系亲属成为服务性行业的既得利益者,一方面通过“获权”之后取得服务性行业的使用权,强化其行政权力,比如现任村干部的餐馆经常用来接待上级来访。另一方面通过服务性行业盈利巩固其金钱与权力地位。在任期内,实现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获益。政治资本决定了是否掌握经济资本,经济资本的积累又反哺于权力,空间本身成为不同的社会权力斗争的戏台,获取利益成为了空间争夺的最终目的。即便是在卸任之后,仍能分到“一杯羹”,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的重叠像一个怪圈左右着村落空间的形成。
空间是一个蕴含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场所,村落的社会结构与村落空间相生相伴,空间的每一次变动都会引起村落关系的改变。街道上的服务性行业与村干部的无意重叠重构着村落的社会关系,在权力资本与经济资本反复滚雪球时,产生了地方之间的空间区隔,由此产生了社会区隔。参与蝴蝶村田野调查的四个小组分别住宿于蝴蝶村四户村干部人家中。昂书记和赵主任是亲戚关系,平日走的近。毕主任与昂主任关系密切,吃饭、活动经常会在一起。尽管在村落集会活动等大场面的时候依然保持和睦,但在非公共场合上传递出来的眼神、表情等非语言符号却不断显示着村落权力集体内部的分裂。我们也在无形之中感到了这种区隔,这种区隔直接反应到对我们的态度上。比如每家主人会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何时何地吃饭,也暗示我们不要去另外一家吃饭。这道无形的墙是由空间建构出来的社会区隔,当然有时我们也会不自觉地超越这种界线,比如同行的L同学有时就会越过毕主任家来赵主任家吃饭,这种触碰是无意识的,也是悄悄的。当然,如果被发现,也是会引起纠纷的。村落社会的空间划分制定了村落社会关系的游戏规则,人们总是自觉地遵守它,并试图在空间的转换下调整游戏规则,不断地营造一种祥和的气氛,然而祥和背后总能感到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迎面扑来。服务性行业是行政性空间与非行政性空间的交叉部分,这种模糊的定位让服务性行业在少数民族地区备受责难。服务性行业所有者的变动影响着村落空间的政治走势,服务性行业主人变更不仅仅是所有权的转变,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建构。“街道及其周边的公共设施在邻里社会网络中犹如一个个关键性的”结构洞“,将各个家庭、院落渐行渐远的关系网络在互动的街道生活中连接与粘合,实现了各个亚文化之间的沟通,避免了社会排斥和空间隔离。”[14]笔者认为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蝴蝶村的情况,表面上公共设施把蝴蝶村人联结到一起,但是由于公共设施的畸形发展以及社会关系对社会空间的反作用,它非但没有避免社会排斥,反而成为隔离村落空间的“篱笆”。服务性行业成为地方掌权者的囊中之物,与此同时,权力的争夺也体现在对空间的占有与争夺上,村干部的换届选举成为了空间争夺的爆发点,等村干部一经调整,新一轮的空间争夺战就此拉开帷幕,村落的具体空间势必发生改变,村落社会由此受到影响。自1950年代以降,权力不断在蝴蝶村进进出出,伴随着权力变更带来的蝴蝶村历史空间的时空转换,的确让今日的蝴蝶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国家对少数民族村落空间的干预从未缺席。
三、 村落空间未来发展走向
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渗透和对地方社会结构的瓦解,蝴蝶村的公共空间日益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一方面,现代性的侵入已经使得完整的彝族传统文化保持与传承变得日益困难。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对现代国家意识和规范的接受与适应仍然需要时间来调整。蝴蝶村被无意识地卷入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计划中,但是这种卷入是边缘的、被迫的,与彝族村落循序渐进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这也导致彝族村落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这一结论与台湾学者刘绍华在凉山彝族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中国少数民族村落的‘介入’操之过急”[15]266。蝴蝶村村落空间的转型并没有与村落社会的发展保持一致,这种错位使得村落的发展既失去了它自在的童真,也慢于其他村落的现代化进程。
蝴蝶村的空间变迁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村落社会发展的结果,蝴蝶村社会空间变化带来的村落社会的剧烈变化,体现了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及的“现代性的断裂”,“传统的文明形态也许比其他的前现代体系更富动力性,但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变迁的程度却是更加神速”[16]5。村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原子,没有村落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发展。纵观蝴蝶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政治权力的不断重组过程中,空间以不同形式被调试与重组,从而构成了该少数民族村落空间的演变逻辑。
[1]石林彝族自治县史志办公室.石林年鉴(2014)[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
[2]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M].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崔波.清末民初媒介空间演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周永明.汉藏公路的“路学”研究:道路空间的生产、使用、建构[J].二十一世纪,2015(4).
[5]张品.社会空间研究的困境与反思[J].天津社会科学,2012(5).
[6]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9(2).
[7]崔波.城市传播:空间化的进路[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8]孙信茹,苏和平.媒介与乡村社会空间的互动及意义生产——对云南兰坪大羊普米族村寨的个案考察[J].云南社会科学,2012(6).
[9]王晓磊.“社会空间”的概念界说与本质特征[J].理论与现代化,2010(1).
[10]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1]潘泽泉.空间化: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7(4).
[12]叶涯剑.空间重构的社会学解释:黔灵山的历程与言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3]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M].谢礼圣,吕增奎,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4]刘佳燕,邓翔宇.权力、社会与生活空间——中国城市街道的演变和形成机制[J].城市规划,2012(11).
[15]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1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陈 曦]
2016-12-26
2017-03-13
念鹏帆(1991-),男,云南陆良人,云南大学新闻学院2014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传播;郭建斌(1969-),云南普洱人,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媒体与云南少数民族现代性建构”(YB2009044)
C95
A
2096-4005(2017)03-0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