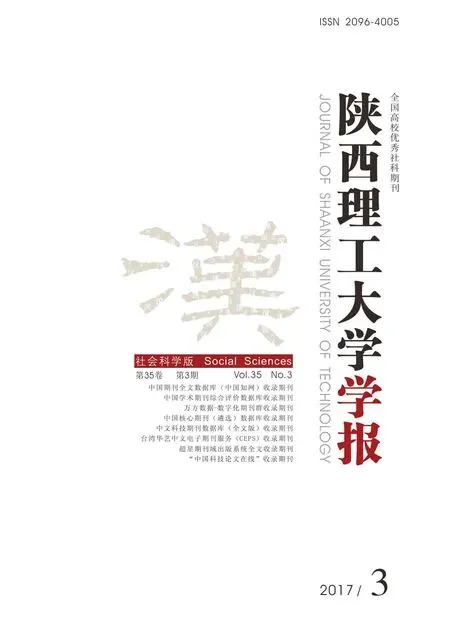《白鹿原》宗法仪式探究
蒋 丽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白鹿原》宗法仪式探究
蒋 丽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宗法仪式是依循宗族血缘关系构建起来的仪式行为,是民间权力场域中维系族群关系的最主要的表现形态。祠堂是宗法仪式的固定场所和象征,乡约是宗法仪式的行为准则和核心,族长是宗法仪式的践行者和执行者,三位一体构成了宗法仪式的完整形态。从宗法意识的存在形态、功能、价值以及没落的必然性等方面进行文化社会学考察可以发现,陈忠实在作品《白鹿原》中成功重现了宗法社会的历史场景及宗法文化的两重性,这不但为感受和理解历史与现实人生开拓了新的视野,也为未来的新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白鹿原; 宗法仪式; 祠堂; 乡约; 族长
文化人类学家格兰姆斯认为,所谓“仪式化”,是指某种类型化的、重复的姿势和姿态,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动物所共有的、具有表现性的行为方式。[1]宗法仪式是承袭裔传族群认同、以宗族血缘关系构建起来的仪式行为。中国自商周到明清是一脉相承的“农业-宗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内核的社会制度体系,形成了民间权力场域中最根深蒂固的维系族群关系的权利场,即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宗法仪式依靠固定的行为场所(祠堂),以仪典(族规乡约)为行为准则,在执行者(族长)带领下,架构起了一个规约族人行为、维护封建礼教秩序的仪式形态,更成为实现政治统治和乡民自治的根源和脉系。这一仪式通过民间信仰得以强化,使之在历史的承袭中愈加丰厚、稳固。《白鹿原》展现了渭河平原中国关中农村二十世纪初近五十年的历史雄伟变迁,正值中国宗法制社会产生变革土崩瓦解的时期;而白鹿原又恰巧是深受宗法影响最重的关中故地。陈忠实正是着眼于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和富有典型性的乡村族群,从宗法仪式的存在形态、功能、价值以及没落的必然性等方面,全面细致地再现了“白鹿原”宗法仪式的存在与衰亡过程,宗法文化的变迁与变化的轨迹,对于当代中国传统宗法仪式的反思具有可贵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一、 祠堂——宗法仪式的象征
《说文·占部》曰“宗,尊祖庙也。”《广韵·之韵》“祠,祭名,泛指祭祀。”“祠堂”是宗族成员供奉神祗、祭祀祖先的场所。白鹿祠堂因祖上约定“白鹿两姓合祭一个祠堂的规矩”,才使白鹿族人同根同源,繁衍生息。“祠堂”在书中出现的次数多达一百七十余次,白鹿原上几乎所有的传奇故事、重大事件和活动都发生在祠堂,可以说白鹿祠堂是《白鹿原》中宗法仪式中最核心的聚集地和象征,更是族长利用宗族法进行管制的法定场所。
白鹿祠堂里供奉着白鹿两姓列祖列宗的牌位和神像,当白鹿原上每一次重大变故发生时,白嘉轩都要带领族人在祠堂进行祭祖仪式,庄严而神圣。祠堂祭祖作为一种仪式性活动,是人类生殖崇拜、求吉避灾心理意识的潜在呈现,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族人后代希望他们故去的族系祖先能够庇佑在世的人平安健康、家族兴旺、吉祥福禄,这一仪式更加强了整个家族内部的凝聚力。而后随着政治等级制度的进一步深化,祠堂由单纯祭祖仪式逐渐增加了宗法、礼仪的社会政治功能,集祭祖、崇拜、管理和权力于一身,主宰宗族一切事物的大权,成为实施宗法仪式无可替代的载体。“管摄天下之人心莫善于立祠堂。盖祠堂立,则报本反始上以敦一本,即下以亲九族,而宗法亦隐寓于其中。”[2]除祭祖外,白鹿祠堂第二大宗法功能是开设学堂,教化族人。白嘉轩和鹿子霖带头修建祠堂,供家族中的学龄子弟上学读书。这在朱先生看来则是“无量功德的大善”,祠堂的教化功能远远重于祭祀功能,通过这种教导使白鹿子孙后代学习知识,知晓礼义,使之行为举止符合传统儒家的教育观,符合宗法仪式行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可见,祠堂对白鹿族人日常行为的控制功能和社会教化功能是十分显著的。
小说中,白鹿祠堂显得神圣而庄严。家族祭祖联宗、议决宗族事务、践行“乡约”、教化乡民、表彰功德等重大事件无一不在祠堂,祠堂极大地发挥着“维护权威”与“净化风气”的作用,但同时也成为惩戒过失的重要活动场所。为了维持家族秩序,保障本村宗法制度稳固,惩戒族人、执行族规家法,也必然是祠堂所具备的基本功能之一。白嘉轩根据《乡约》制定了罚跪、罚款、罚粮及鞭抽板打等处罚条例。陈忠实先生对于这一惩戒场景的描写可谓是淋漓尽致、触目惊心。尤其是在祠堂公开处罚田小娥和白狗蛋的场景更是辛辣狠绝、惨不忍睹。白嘉轩将家族中所有男人召集到祠堂之中,还破例召来了族中成年的女子,用意就在于通过对田小娥和白狗蛋这对族人眼中的“乱淫男女”的处罚,使得族中的其他女子警戒敬畏,恪守族规家法。“白嘉轩从台阶上下来,众人屏声静息让开一条道,走到田小娥跟前,从执刑具的老人手里接过刺刷,一扬手就抽到小娥的脸上,光洁细嫩的脸颊顿时现出无数条血流。小娥撕天裂地地惨叫。白嘉轩把刺刷交给执刑者,撩起袍子走到白狗蛋跟前,接过执刑人递来的刺刷,又一扬手,白狗蛋的脸皮和田小娥的脸皮一样被揭了,一样的鲜血模糊……鹿子霖接过刺刷轮圆胳膊,结结实实抽到小娥穿着夹裤的尻蛋上,然后把刺刷丢在地上转过身去。他再次接过刺刷抽到狗蛋的胸脯上,无数条鲜血的小溪从胸脯上流泄下来注进裤腰。”[3]262最终白狗蛋因伤口发脓溃烂,在喊冤声中死去,这是何其残忍的惩罚!对于儿子孝文的惩治白嘉轩下手特狠,比上次抽打小娥和狗蛋还要狠过几成,孝文一声惨叫接一声惨叫,鲜血顿时漫染了脸颊。这种惩戒仪式活动是非常态的模式化行为,具有超实效和实用目的的表演的性质。薛艺兵认为正如格尔茨所说这是一种“文化表演”,一个仪式的一系列行为组合,就是一系列的表演组合,因而可以说,表演是构成仪式情境的行为基础,仪式情境就是表演的情境。[1]“刺刷”成为典型的道具,在场的施刑者、参与者和受刑者,各具角色,各具目的,共同完成(或参与表演)整个惩戒仪式活动。这在宗法社会中是常态化、模式化和固定化的,目的就是用最残酷的手段,用从肉体到精神双重羞辱的方式打击违反族规的族众,使之不敢复发。在这里,祠堂成为家族暴力的法定场所,它充分暴露出了宗法文化的虚伪与残忍。白鹿祠堂内列祖列宗的牌位以及族规石刻最终被黑娃所砸,这暗示着中国社会传统宗法仪式逐渐走向末路,宗法仪式格局也随着时代变迁被打破。
二、 乡约——宗法仪式的核心
《乡约》作为白鹿原上的乡土法典,是宗法制度下同宗家族制定的公约或曰法规,是由地方制订,形成条文并共同监督遵守。从表层意义讲,《乡约》是“以礼化俗、以礼化民”的民间自治制度,即以具有威望的地方士绅主持,以宗族为单位,以德治为原则,以礼罚并重思想为内核,建立起的“知识-权力”结构形式的一整套地方社会运作模式。从深层意义讲,乡约通过这种教化方式长期渗透和灌输,具有持久性和稳固性,由此内化为普通百姓的心理定势和情感定势, 即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最终形成一种“情-理”的文化心理结构。“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4]
《乡约》作为中国关中乡村重要的自治制度,对人们的德业礼俗、言行举止等行为规范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去自觉遵守与践行。它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款条文为宗旨,实施修身齐家之德,治田持家之术,教民以礼仪,以正世风。这些规则正是儒家伦理、宋明理学关于教化的核心,让族人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乡规民约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白鹿原上历经了“反正”之后,经白嘉轩、徐先生和鹿子霖在祠堂商议,当即就将《乡约》的文本用黄纸抄写出来,第二天贴在祠堂门楼外墙上,每晚召集“白鹿两姓凡十六岁以上的男人齐集学堂,由徐先生一条一款,一句一字讲解。每晚必到,有病有事者须向白嘉轩请假;并要求每个男人把在学堂背记的《乡约》条文再教给妻子和儿女;学生在学堂里也要学记《乡约》,恰如乡土教材。”[3]93就这样,乡约如影随形地渗透到白鹿族人一代又一代的生活和心里,白鹿村果然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至于“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3]94与此同时,乡约里的“过失相规”作为反面也具有强烈的威慑力。对触犯乡约的白鹿族人实施的各种酷刑具有民间独创性,如鞭打板抽、开水烫手、嘴里灌大粪、枣刺毒打,受刑者在众目睽睽之下声声惨叫,缕缕血痕。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民众,净化了风气,但其虚伪和残酷性不言而喻。垂涎着小娥却未得逞的狗蛋儿被打的面目全非、含冤而死,而真正淫乱的鹿子霖却成了行刑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地讽刺。
“乡约”是宗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集体表象和象征符号,是个人心理认同的归宿,从根本上来说是制约民众、实施权力的依靠,维护的是统治者的利益。而“诵读乡约”这一仪式场景的背后则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对当地社会起到了“秩序化”的作用。“在白鹿原上,朱先生的儒家文化观念与白鹿祠堂里刻着的《乡约》与族规构成了一套严密的文化价值体系,负责解释、评价原上的人与事。然而,一旦这些人或事延伸到白鹿原之外的政治社会之中,这套评价体系就丧失了解释能力而显得不知所措,白鹿两家子弟间的恩怨情仇已远远超出了儒家仁义道德的解释空间。”[5]可见,乡约在推行过程中,以儒教为基础的传统道德伦理价值体系在和宗法文化相互融合之后,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所有白鹿村村民心中。
三、 白嘉轩——宗法仪式的践行者
白嘉轩——陈忠实笔下的族长,是白鹿原上独一无二的权力掌控者,是中国宗法文化所造就出的“仁义”典范形象。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存留下来的那一套伦理规范和千年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在白嘉轩的身体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并根深蒂固,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支柱和行事标准。白嘉轩躬耕力作,克勤修身,六娶六丧,忍受苦难,抗击白狼,化解危机,以身作则,以德报怨,努力并严格履行族长的宗法责任。深受儒圣言行影响,洞明世事的白嘉轩,毕生追求的是乡土君子的德化人生观,并用毕生精力重演过去宗族的荣耀。白鹿祠堂里的每一件事他都亲历亲为,翻新祠堂,创办学堂,广施公济,救济李寡妇,不计前嫌多次搭救黑娃,尤其与仆人鹿三的主仆恩情在《白鹿原》的描写中感人至深。这点点滴滴无不浸透着他义薄云天的胆识和仁义精神。正是如此,他在乡民中树立起了极高的威望,与朱先生联手在白鹿原上形成了“权力-道德”式统治,将白鹿原变成“仁义示范村”,以家族文化守成者的姿态实践和保卫着宗法社会儒家文化秩序。
而另一面,白嘉轩那“挺直的腰板”始终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威慑着人们,作为宗法家族权威忠实的拥戴者和严格的执行者,白嘉轩的另一面是“冷”与“硬”。他以牺牲亲情和人性为代价,换来的是他自始至终坚持的传统道德规范。他先后娶过七个妻子,却并未得到或给过她们真正的爱情,只是为了完成“传宗接代,无后为大”的家族使命和耻辱;他利用族长的权威,对违反乡约的族人用最严酷的手段惩治,小娥、白狗蛋就是惨死在他的手上。对儿子孝文的惩治,不仅震撼了白鹿原,也昭示了他在家族中的权威性。他唯一所爱的女儿白灵也因忤逆了他的意愿被断绝了父女关系,直至死后多年他才知晓。由此可见,其人性和亲情在冰冷的封建礼教和宗法仪式侵蚀下已经完全扭曲和异化,一切可能危及这种既定宗法仪式和秩序的思想、行为以及怀疑、触碰和违反现存秩序的人,他更是采取激烈的方式和手段给予无情的打击惩罚,甚至使这些人陷入生存的绝地。正如评论家所说,他“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6]
四、 宗法仪式的落寞
在《白鹿原》中,宗法仪式行为曾在白鹿原上显示了对于农民生存层面最大的最积极的意义和作用。在二十世纪初期那个动乱的时代,白鹿村人在族长白嘉轩的带领下,抵抗种种灾难和困难,发挥了宗法仪式的巨大潜能。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革,“革命”之风在白鹿原上刮起时,宗法仪式日渐衰微,失去了它的绝对权威。当代表进步的革命之风将尊祖与尊儒的传统拉下神坛时,当新的价值结构一次又一次冲击它时,维系着村民之间的单纯的血缘关系不再坚不可摧,那些具有原有文化心理结构的人们就不得不在化茧成蝶过程中裂变,在烈火中涅槃重生,宗法文化精神逐渐走向灭亡。
首先,是以鹿子霖为代表的商业文化对宗法仪式的强烈冲击。鹿子霖一直作为反面人物和白嘉轩的竞争对手出现,他极端自私虚伪、阴险贪婪、作威作福,完全背弃仁义道德。他继承了先人竞争出头的商业文化意识,一方面处心积虑地打击对抗白嘉轩的宗法势力,穷其一生与之明争暗斗;另一方面,趁革命来袭不择手段疯狂向上爬,为获得政治权力屈膝谄媚,依附新的行政机构、借用新的政治势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野心及对抗与宗法仪式行为是矛盾的,不可调和的, 从而加速了白鹿原宗法制度分崩离析的进程。
其次,以黑娃、小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对宗法仪式的反叛。黑娃的背叛缘于敏感的阶级差异感和自卑而自尊的矛盾心理。黑娃与小娥的真爱和婚姻受到了父亲鹿三和白嘉轩的痛斥与拒绝,这使得黑娃对宗法制度更加仇视,宁愿与小娥住在破旧的窑洞也不进祠堂。因此,在后来风云变幻的大革命中,他一跃成为白鹿原上的革命积极分子,率下属打劫,大闹祠堂、摔毁乡约、砸断白嘉轩的腰杆,摧毁象征宗法礼教秩序的神圣殿堂。这种反叛完全是一种快意的情绪放纵和发泄。田小娥则是另一类以毁灭生命与名誉为代价去而反叛宗法的悲剧女性。小娥出于对命运的反抗,不愿做郭举人泡枣的工具,主动勾引黑娃并与之私逃,努力挣脱了性奴的命运,然而却被族人当做“妖女淫妇”挡在了祠堂之外成为异类。在黑娃因发动农运、砸祠堂而被通缉逃跑后,她又再一次沦为鹿子霖的泄欲工具和宗族斗法的武器。她死后的鬼魂带给白鹿原毁灭性的瘟疫隐喻了她对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痛恨,体现了崇尚仁义道德背后“存天理,灭人欲”的残酷性和虚伪性。
第三,以白孝文为代表的宗法文化的内部分化。白孝文是乡约族规调教下的家族新一代掌门人,受到白嘉轩“节欲惜身”理论的禁锢和束缚,表现出正人君子的形象。然而这位被精心栽培出的“正人君子”,却在鹿子霖的策划下,被小娥的美色轻而易举地虏获,滑入道德的深渊。事情的暴露,祠堂前的毒打,残暴的惩罚,让他感到屈辱,他亲身体会到了宗法制度的冷漠无情。由此,他背弃了以前竭力守护的一切家族伦理秩序和宗法仪式行为,违逆父亲白嘉轩的意志和乡约族规,坠入歧途,彻底堕落,变得贪婪、狠毒、自私,沦落为败家子和无耻的政客。正是宗法仪式自身的残缺和伪善将白孝文推向了无底的深渊,使他从宗法制度的信奉者变为背叛者。
最后,第四股势力是革命者的颠覆。以鹿兆鹏、白灵等为代表的革命者,先后以各自不同的抗婚行为,逃离了令人窒息的“家”,实现了对封建家长包办婚姻的反叛。接着,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斗争学说的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积极投身革命,推翻阶级压迫,他们希望彻底颠覆传统文化和宗法秩序。宏大而完整的宗法仪式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分崩瓦解了,宗法家族走向衰亡。
不少学者注意到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心态:“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抵,又在挽悼;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7]我们这个民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近五十年的历史发展中,每一次革命都是权力的不断更替,充满苦难和艰辛,而对民众来说,更是心理和精神承载剧痛,是同传统宗法制度不断剥离的过程。宗法仪式最终难逃社会变革的洪流,由神圣走向了落寞,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累赘。陈忠实先生成功地重现了宗法社会时代的历史场景,揭示了宗法文化的两重性,艺术地阐释了人生的深刻性,这不但为人们获得感受和理解历史与现实人生开拓了新的视野,也为未来的新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1]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上)[J].广西民族研究,2003(2).
[2]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祠堂的控制功能[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3).
[3]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4]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5]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J].文学评论,1993(2).
[6]李星.世纪末的回眸[M]//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白鹿原评论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7]李清霞.从崇高到荒诞:《白鹿原》的美学风格[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责任编辑:王建科 责任校对:王建科 陈 曦]
2017-03-28
2017-05-07
蒋丽(1977-),女,陕西汉中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近现代社会仪式的范型——关于《白鹿原》中仪式行为的探究”(2014I23)
I207.4
A
2096-4005(2017)03-005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