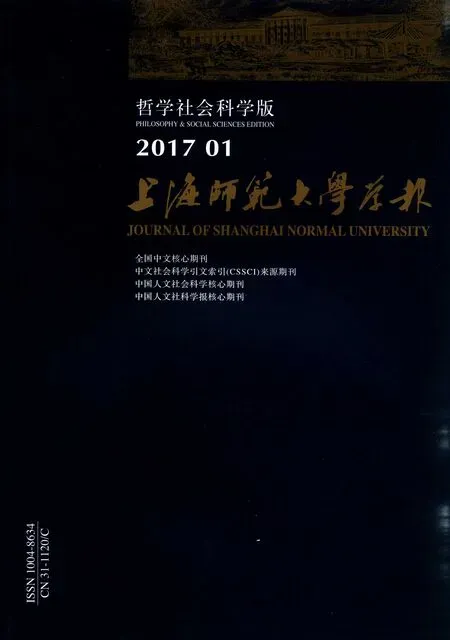重新审视芮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
吾 淳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重新审视芮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
吾 淳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的代表作《农民社会与文化》因其中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而在人类学、历史学以及思想史诸领域极负盛名。芮德菲尔德“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看似简单,内涵实则复杂,且并不完善,甚或会造成错误和混乱。其中就语词来说,以精英与大众来定义“大传统”与“小传统”并非科学。事实上,国家或政府层面的某种价值导向未必就一定是大传统,也并非所谓精英层面的思想就一定是大传统;民间或民俗层面的某种观念或价值取向也未必就一定是小传统;并且国家层面的文化传统与地方层面的文化传统未必就是对立的,它们完全可能是一致的或统一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精英与大众也并无二致。确定“大传统”与“小传统”只有一条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这就是应从主流与非主流的角度来理解。
芮德菲尔德;大传统;小传统;精英;大众;人类学;文明史
一、芮德菲尔德对“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界说
“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或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其《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一书中提出来的。①芮德菲尔德这样解释道:
农民文化是一种多元素复合而成的文化,它完全配得上被称为“人类文明的一个侧面”。如果我们想去深刻地理解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走出我们的第一步呢?如果我们想走出这第一步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先承认一个前提,即: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其实在本书的前面部分讨论文明的一些段落里已经谈到了这个前提了(在这儿我用了“大传统”、“小传统”这样的词:请读者不必对此感到突兀,因为我在前文里其实早就用了像“高文化”、“低文化”、“民俗文化”、“古典文化”、“通俗文化”、“上流社会文化”等等语词。在后面的章节里我还会用到像“等级制文化”、“世俗文化”等语词)。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1](P94~95)
芮德菲尔德也注意到了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两种传统——即大传统和小传统——是相互依赖的;这两者长期来都是相互影响的,而且今后一直会是如此。”并说:“它的这两个‘一半’之间的关联是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1](P90,P96)又说:“其实大传统和小传统是彼此互为表里的,各自是对方的一个侧面。”[1](P116)芮德菲尔德举例道:“不少伟大的史诗作品的题材都是源之于平民百姓一代传一代的逸事传闻的精华部分;而且一旦史诗写完之后也往往会回流到平民百姓中间去,让后者对它再加工和重新融入到种种的地方文化中去。《圣经·旧约》中阐明的诸多道德原则其实原本都是部落社会里流行的一些道德准则。然后许多古代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对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之后就被归纳入《旧约》中去了。于是经过《旧约》,这些道德教诲就又传回到了各种各样的农民社区里去。”“我们可以把大传统和小传统看成是两条思想与行动之河流;它们俩虽各有各的河道,但彼此却常常相互溢进和溢出对方的河道。”[1](P97)
芮德菲尔德并未就如何划分“大传统”与“小传统”做出解释,但“大传统”与“小传统”既是一个分区概念,也是一个分层概念。如芮德菲尔德所说:“一种文化被创造出来了,然后分裂为(甲)上层统治阶级和僧侣阶层的大传统和(乙)世俗人们创造的小传统。”[1](P103)芮德菲尔德也用“高级的”和“低级的”两个语词来表述这样的传统:一个社会制度包含了属于它的高级的“一半”和属于它的低级的“一半”;这两个“一半”凑成了完全的它,即这个大的社会制度。[1](P90)芮德菲尔德还使用“高传统”与“低传统”这样的概念来指代“大传统”与“小传统”,如他叙述道:“外国人就难免产生好奇心,想去探索一下高传统的一些元素是如何经由这些非常特殊的文化形式而被植入到农村居民的思想意识里去的;还想探索一下高传统的一些元素在被植入到低传统的过程中是怎样被改了头换了面的。”“他们还想探索在高传统的元素向低传统移植的过程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机构或文化规章制度’在起着催化剂的作用。”[1](P128)更多的时候,芮德菲尔德也直接使用“精英”和“农民”(或“平民”“百姓”,其实我们也可统称之为“大众”)这样的语词,如:“社会上所有的人是可以分成两大类的:其一是从事耕种的农民,其二是比农民更具有城市气息的(或说是至少比农民更具有庄园主气息的)精英阶层。”[1](P84)这也包括那些更为原始的社会类型:“曾有人类学的调研人员对类似阿尔卡拉镇这样的印第安人的定居点进行过调查,发现在这样的镇子里的居民中存在着两个类型的生活方式,它们分别属于镇子里的两个社会阶级。”“镇子里通常居住这两种人:其一是来自于城市的精英层里的人物,其二是平民百姓;这两者形成了这个镇子的社会结构。”[1](P88)而精英对于农民承担着示范或教育的责任,“在一个完全的、更大型的社会里肯定是要出现精英层在文化方面向农民层施加教育和示范的现象的”。[1](P88)芮德菲尔德又引萧柏格的话说:“精英层把自己所创造出的辉煌成就展示给农民”,并“促使社会制度里的农民的‘一半’主动去理解精英层之所以必须存在和延续下去的深奥的机理”。[1](P90)
从芮德菲尔德上述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所谓的“大传统”就是指精英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而“小传统”则是指大众(在其书中主要是指农民)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并且,在芮德菲尔德看来:大传统自觉,小传统自发;大传统高级,小传统低级;大传统一定是“必欲使之传之后代”,小传统只得靠“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而“跟随着低层次的文化走的人们和跟随着高层次文化走的人们是有着相同的高低标准和是非标准的”。[1](P116)
二、“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的人类学依据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精英与大众就是芮德菲尔德“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的全部依据,那就错了。事实上,芮德菲尔德的“大传统”“小传统”理论有着其自身更为专业的人类学学科依据。
我们知道,人类学首先关注的是小群体、小型群体、小型社会、小型社区,芮德菲尔德作为人类学家也不例外,这是人类学研究的进入方式,也可以说是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起点和特点。人类学家“可以独自一人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扰的情况下深入到一个独立自主的文化的社区里去。这样的一个社区本身就是个完整独立的世界,而当他进入了这个独立完整的世界之后,他就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一个学生”。[1](P114~115)最初,这些小群体、小型群体、小型社会、小型社区是指原始社会的状况;随后,人类学家又发现分散或广布于世界各地的农村社会也具有相似的情形。因此,在芮德菲尔德这里,“小传统”也意味着小型性、区域性、地域性、地方性,如以下这些事例和论述:其一,“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徒的聚居区里,在通常的情况下,伊斯兰的模式都是居于大传统的地位上的。与大传统的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该地区的小传统的地位;因为在伊斯兰教徒的聚居区里,小传统就犹如民间的一支小暗流偷偷形成的小水坑”。[1](P112)其二,“当一个人类学学者对一个孤立的、原始型的社区展开研究的时候,他的全部调研范围就是该社区和当地有直接关系的地方性文化”。[1](P119)其三,“作者在印度的乌塔尔·菩拉德西地方的吉山加希村庄里进行他的调研。这个村庄里的人所遵奉的宗教信仰有着多元的成分;它既包含着梵语区高层次传统的成分,也包括着当地的地方文化的成分”。[1](P122)其四,“村民们把一些梵语印度教的教义元素和宗教仪式改造成了他们地方性迷信膜拜的一部分”。调查者麦克金·迈里奥特也把这一现象叫作“地域化”(parochialization)。[1](P125)
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类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孤立地研究这些小群体、小型群体、小型社会、小型社区是不够的,也是不行的。如克罗伯说:“既往的人类学学者们总是对逐个群体或社会孤立地来进行研究;但到了今天,他们把对一个群体或社会的研究放在它和与它相关联的大群体或大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背景中去探讨。”[1](P49)芮德菲尔德本人也说:“如今,人类学学者们都已普遍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所谓小型社区实际上在社会结构上和文化传统上都和比它们大的社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对于更大型和更复杂的社区变得越来越关心了。”[1](P21)芮德菲尔德设问道:“到底我们今天如何具体地把一个小社区当成一个小的有机体来分析研究呢?又如何具体地把一个包含诸多小社区的较大型社区作为一个较大型的有机体来分析研究呢?”[1](P49~50)芮德菲尔德还说:“一个文明总是既有大的地域上的范围,又有大的历史意义的深度的。也就是说,不论是从时间上来讲,还是从空间上来讲,一个文明就是个硕大的整体。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一个文明需要非常复杂的组织工作,一则是为了保证它的正常运行,二则是既为了给这个文明培育出它的种种传统,也为了把已经被培育出来的它的大传统传播到存在于它的内部的为数众多又各不相同的小型的地方性的社会里去。”[1](P134)这应当就是芮德菲尔德所说的“大传统”,或即其提出“大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传统中包含了诸多小传统,是多个或无数小传统的有机结合,具有广泛性和整体性。这也意味着芮德菲尔德试图“跳出”人类学所普遍关注的小型社会,而建立起指向大型社会的研究视角。
三、“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的文明史依据
也因此,芮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又有了文明史的视域或语境。
下面这段话表明了芮德菲尔德注意到不同学科对于研究“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自然”分工以及对于人类学家共同参与“大传统”研究的意愿和态度:“对一个人类学学者来说,他应该下苦功去阅读历史学家的以及研究艺术和文学的专家们的有关著作。作为一个专攻主流文化的研究工作者来说,他应当去阅读的与他的研究主题有直接关系的书籍和资料通常都是堆得像一座山那样高,而且还不只是这些。有许多他应阅读的资料不是用文字来书写的。比如关于古天竺人的世界观的资料吧,那就不是用文字写下来的;它是用庙宇的建筑体现出来的,当然也有以哲学典籍的形式保存到后世的。一个人类学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要特别提醒自己时时注意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他应该学会把大传统里的一些元素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与他耳闻目睹的、原原本本的平头百姓现实生活联系起来。”[1](P118)芮德菲尔德还特别举了例子:“只要一个人类学学者肯去做文字资料的研讨和对现实生活进行观察,他就会发现,凡是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能典型地体现出文字资料精神的地方,就是真理得到了印证的地方。《罗摩衍那》的文字虽然古老,但它对今天的印度的农村却还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1](P118~119)
事实上,芮德菲尔德在书中就反复提到了几个“大传统”,包括印度、中国、伊斯兰文化以及印第安或玛雅文化。但问题是,这些“大传统”包括“小传统”吗?是否仅仅是指精英文化呢?抑或也指大众文化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呢?从“人们生活的全貌”“社区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把大传统里的一些元素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联系起来”这些表述来看,似乎应当是包括的;但芮德菲尔德在语词或概念上却又未予明确。这恰恰就是芮德菲尔德“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的困境之处——这里的“大传统”究竟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别,还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区别?
芮德菲尔德显然也注意到了不同“大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并存、替代与结合。
芮德菲尔德论及了拉丁美洲或南美洲地区不同大传统的并存现象。他说:“有一些拉丁美洲地域性的文化实际上是西班牙的大传统的残缺不全的表现,但另有一些拉丁美洲地域性的文化则实际上是被西班牙征服的那部分南美洲土著人所创造出来的大传统。可惜我没有机会去调研尤卡坦一带的那些村庄(因为那些村庄的生活状态可以体现出南美洲土著人创造出的文明的一些方面),否则我就会认定那些村庄的文化是既渊源于西班牙天主教的大传统,又渊源于当年由寓居于尤卡坦各种神龛内的充当祭司和天文官的土著们所创立和推广的、但到今日却已不复存在的大传统。我做过调研的那些村落里的萨满教的神巫们一直在那儿鼓捣种种宗教道场、念经念咒。这些玩意儿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们一点也不懂。要弄清它们的意思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们先弄懂在古代的切辰—易莎或库巴(‘切辰—易莎’和‘库巴’是两个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由古代的玛雅人建立起来的最大的城市)城里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的含意以及当时在这两个城市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今天的玛雅人的村庄里还常有人在念一些神秘的咒语。”芮德菲尔德也将此称为“一种‘二级的文明’开始涌现——特别是当一个外来的大传统侵入了一个土著人的大传统,前者虽取代了后者的大部分但仍留下了后者的一小部分而未加以彻底取代的情况”。[1](P104~105)
不仅有并存,而且也有替代。为此芮德菲尔德引用了基德的看法。基德把“二级的文明”叫作“一个外来的大传统砍了一个土著大传统的头”。基德说:四百年前的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征服使欧洲的文明取代印第安土著的文明,是“砍了土著文明的头”。这样的砍头也可以叫作“文化之被铲除”,也就是说,一个大传统被消除掉了。[1](P105~106)可见,这种以“砍头”为特征或命名的“二级的文明”实质上就是传统的替代,即一种新的大传统替换旧的大传统。事实上,这种“砍了土著文明的头”或“文化之被铲除”的传统的替代,在北美洲要表现得彻底的多。
但另一方面,并存也可能导致不同传统之间进一步的适应和融合,尽管这样的适应和融合会遇到种种困难。芮德菲尔德本人就有这样一次经历。“那一次的事情是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一个印第安人的社区里。该社区的天主教的教区神父和该社区的恪守玛雅传统的萨满教巫师携手合作,成功地主持了一次涤罪仪式。在组织和准备这个仪式的过程中,有促进的、有拖后腿的、有疑心重重的,有冲突、有妥协。”芮德菲尔德意识到,“这件事里当然包含有两个更为诡秘的传统。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彼此不相容的,所以,要让它们在整个仪式的过程中表现得让村民不感到失望的话,它们是需要做些相互调整的”。[1](P133)这个例子芮德菲尔德是置于“社会组织工作”名下的,但我觉得它用于传统间的相互适应与融合可能更加恰如其分。
以上例子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不是就精英与大众意义上来论述“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这说明芮德菲尔德也会不自觉地触及讨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正确方向。
考古学发现的诸多史前遗存,由于分布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为了准确的描述和研究它们,需要给遗址进行准确严格的命名,这样就确立了考古学文化。
四、芮德菲尔德“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的错误何在?
由以上考察可见,芮德菲尔德“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看似简单,内涵实则复杂。我们看到,由芮德菲尔德的界说即定义来看,“大传统”与“小传统”只是对应于精英与大众;但在实际论述中,芮德菲尔德显然还有其他考量的标准:人类学中的小社会与大社会是一条标准,文明史中的不同传统也是一条标准,甚至我们还可以隐隐看到潜藏于其意识深处的西方文化标准。这种状况恰恰说明,芮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看似简练、清晰且有标准,实则并不完善,甚或会造成错误和混乱。如我们至少可以从下述方面来考虑它的不足。
首先就语词来说,以精英与大众来定义“大传统”与“小传统”并非科学。通常,当人们讲到或区分精英与大众的时候,其中既有文明程度的因素,也有价值判断的因素。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使用“高级传统”与“低级传统”或“进步传统”与“原始传统”这样的语词或表述显然更加贴切和准确。依据常识即词义,“大”“小”这对语词是关乎“量”的(也关乎与“量”密切的“质”),就此而言,“大传统”与“小传统”从最恰切或最精准的词义来说应当是指某一传统接受者或参与者的规模。总之,“大传统”与“小传统”不应从精英与大众层面来理解,即不应从高低层次来理解。换言之,“大传统”与“小传统”与好坏、优劣的价值判断无关,也即与上层和下层、精英和大众、先进和落后这些内涵无关。说得更彻底一些,这是由“大”“小”这两个语词的词义所规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芮德菲尔德的“大传统”包含有教育、教诲、教化的寓意,即包含有价值统一或归化的功能。应当说,这在西方一神宗教伦理传统中的确是突出的,事实上,芮德菲尔德也是用这样一种范本来衡量东方的宗教和伦理系统的。但芮德菲尔德显然不清楚东西方宗教系统截然不同,很难用一把尺子来加以衡量。另外,更加重要的是,文明或文化的“大传统”又绝非只有价值系统,它还涉及技术系统、知识系统、思维系统、制度系统等,而这些都远不是教育的功能或寓意所能范围和涵盖的。换言之,如果仅仅将“大传统”与“小传统”界定在教育或归化向度上,那真是大大地降低了这两个概念的深刻意义。但上述问题涉及内容众多,需另文展开阐述。
与此相比较,将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形态视作较大的传统,将地方或社区的文化形态视作较小的传统,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至少从规模、面积、体积、数量的角度来说,前者更大些,后者更小些。我们知道,人类学的视野或人类学的学科特征注定了其首先就是关注相对较小的单位即文化单元。芮德菲尔德认为地方或社区的文化形态是较小的传统,与之对应,国家的、民族的文化形态是较大的传统;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这种判断自有其学科依据。但是,这样的判断仍存在问题。芮德菲尔德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地方、民间的文化形态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虽有不同,甚至千差万别,但究其本质,其完全可能是理一分殊,殊途同归;换言之,往往正是无数地方的小传统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大传统、国家的大传统,乃至人类的大传统。芮德菲尔德有见于异、无见于同,这一点很可能是作为人类学家的芮德菲尔德囿于自身的学科或知识训练所致。
芮德菲尔德显然也注意到了不同文明中的不同大传统。如芮德菲尔德举了南美洲尤卡坦地区的土著传统,并承认这也是一种大传统;举了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社区中天主教神父与玛雅萨满教巫师之间的合作,这实际是两种大传统的并存;他还引用了基德的看法,即一个外来大传统与一个土著大传统之间的冲突。但是,这样的不同文明间的大传统与精英大众间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难道尤卡坦地区或以其为代表的整个土著传统只是精英传统,而不包括民间传统吗?又或者外来大传统与土著大传统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只是精英间的吗?还是其乃包括所有大众的整个民族或文化间的呢?对此,芮德菲尔德都未予说明。当然,这已经不单单是人类学问题,而是涉及哲学问题或宗教学问题,也是史学问题,我们无法对作为人类学家的芮德菲尔德提出更多的苛求。
那么,导致芮德菲尔德“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错误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它包含以下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或政府层面的某种价值导向未必就一定是大传统,也并非所谓精英层面的思想就一定是大传统。例如无神论观念,在古代中国出现过,在古代印度出现过,在古代希腊也出现过,并且它一定是出现在精英层面,这完全符合芮德菲尔德所说的“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的标准。但事实上,在全世界的古代社会,无神论观念只能算作是一种小传统,甚至它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都构不成一种传统,因为它往往缺少传统所必须具备的延续性。又如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在宋代之前实际上始终是一个小传统。先秦时作为诸子之一自不必说;汉代至唐代尽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尽管有致力于儒经学习与教育的经学和太学,但仍难堪称大传统,因为它并未普及至民间;并且儒家还一度不敌佛教这个大传统而变得岌岌可危;直到宋代,因家族或宗族制度,儒家思想才成为大传统。总之,儒家传统在仅仅属于精英或官府时只是小传统,而当推广落实于民间之后才成为大传统。
第三,国家层面的文化传统与地方层面的文化传统未必就是对立的,它们完全可能是一致的或统一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精英与大众也并无二致。同样以中国社会的多神与巫术信仰为例,就其基本性质或倾向而言,国家即王朝层面与民间层面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大众信奉多神或鬼神、天命、占卜、巫术,精英也同样信奉。如果说有区别,也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如大众什么都信,拿到篮里的就是菜;而儒家则有所选择,反对淫祀)。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大传统,无所谓国家与地方之分、精英与大众之分。事实上,这也是整个印度社会的大传统,是所有未经历宗教革命的连续性社会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是与另一个经历了宗教革命的一神宗教大传统相对应的。
五、确定“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正确标准究竟是什么?
那么,确定“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正确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不应当依据精英与大众、高级与低级来加以界分;而且也并非国家层面的就一定是大传统,民间层面的就一定是小传统。“大传统”与“小传统”不应当是一种价值判断,而只能是一种事实判断。
确定“大传统”与“小传统”只有一条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这就是应从主流与非主流的角度来理解,或从主流与支脉的角度来理解。这里所说的主流就是指一种传统的实质或基质,它涉及如下两个基本要素:空间上的规模或覆盖面;时间上的影响或持久力。
如前面所举述的例证,尽管从汉代到唐代,国家层面都提倡儒经的学习与教育,但总体而言,这种学习与教育只是“惠及”人数十分局促的精英层,其规模极其狭小,影响也极其有限;同理,古代无神论观念虽然也是精英层面趋于理性的“普遍”现象,但这种普遍之于更为广阔、浩瀚的大众层面来说就如同沧海一粟、汪洋一叶,几可忽略不计,它一样缺少覆盖面和持久力。相反,古老宗教中盛行于民间或社会底层的多神信仰与巫术、占卜崇拜则明显具有广泛覆盖性和持久生命力,它无疑是大传统。虽说精英层面的理性倾向会对此进行约束和限制,但这一定是小传统,它对于一个大传统的作用一定是有限的;更何况,在古代社会,精英小传统也不可能游离或隔绝于大众即社会大传统;包括国家与统治者,其与整个社会的信仰必定是一致的,在这里,只有一个大传统。
对此,马克斯·韦伯对于中国社会宗教信仰的分析就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例证,其中就包括精英与大众也即芮德菲尔德所说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斯·韦伯指出:“就像受过教育的古希腊人一样,有教养的儒教徒带着怀疑的态度对待巫术的信仰,虽然有时也会接受鬼神论。但是中国的人民大众,生活样式虽受着儒教的影响,却以牢不可破的信仰意识生活在这些观念里。”[2](P312)不仅如此,“真正的儒教处世哲学是‘市民的’,就像所有的启蒙教化一样,它也包含有迷信的成分”。[2](P284)显然,马克斯·韦伯注意到中国社会的信仰大传统是在社会底层或民间,儒家的理性主义或怀疑主义只是一种小传统,并且这种小传统不可能绝对对立于大传统,而势必也会包含有大传统中的基本成分。毫无疑问,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或论述是精辟的。而且在我看来,这一分析或论述并非只是针对中国,它也针对印度,甚至可以说针对亚伯拉罕宗教信仰之外的一切古老宗教系统。
但芮德菲尔德在以下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仍具有正确性,这就是大传统是脱胎于小传统的,大传统乃是由小传统而来的。芮德菲尔德说:“一个大传统所包含的全部知识性的内容都实际上是脱胎于小传统的。一个大传统一旦发展成熟之后倒变成一个典范了;于是这么一个典范便被当局拿出来推广,让所有跟随着小传统走的人们都来向这么个典范学习。”[1](P116)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一神信仰最初就是小传统,以伦理的方式或名义将占卜与巫术从信仰中驱逐出去(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一句话,犹太教,即《旧约》,最初就是小传统。但是,由于犹太民族的特殊境遇和犹太先知的卓绝努力,这一小传统逐渐成为犹太民族的大传统,之后它又成为基督教的基石。同样,基督教,即《新约》,则是由于使徒和信众们的不懈努力,才逐渐成为罗马帝国或整个欧洲以及所谓西方的大传统,之后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开来。类似的例子还有:希腊的学者知识范式,最初其相对于古老的经验、技术、工匠模式来说是小传统,但近代以后这种学者方式与思维已经成为大传统;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最初其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集权与专制模式来说是小传统,但千百年后这种民主制度与观念已经成为大传统。这也体现于儒家文化的发展中。先秦时期其是诸小传统之一;汉代至唐代虽有国家层面即王朝或官府的提倡,依旧应当视作是小传统,并且在南北朝与隋唐时期与佛教的比较与较量中更彰显出小传统的地位与特征;但是,宋代,经儒家学者们的努力,儒家文化终于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传统,以后它又贯穿于元、明、清各代,历时千年之久;直到近代,它才在各种力量或因素的作用下趋于湮灭;即便如此,在同属中华文明的中国台湾地区,它至今仍属于一种大传统。但我们又应看到,一种小传统在某个区域甚至极大的区域里成为大传统,并不必然就在所有区域中取代原有的大传统。如多神信仰包括信奉占卜、巫术,对于经过宗教革命的亚伯拉罕宗教系统来说已经成为小传统,但对于那些没有经过宗教革命且保持着顽强生命力的古老宗教系统(如印度和中国)来说仍是典型的大传统;它仍在世界宗教信仰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是巨大的一席之地。
回顾与检讨芮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其之所以产生错误和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或许与囿于人类学学科性质有关。我们知道,人类学的学科性质或特征就是研究人类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特殊性,或即研究地方文化或小型社区的特殊性。换言之,用芮德菲尔德的话说,就是研究“小传统”。然而,对于“大传统”,芮德菲尔德很可能是缺少意识准备与理论训练的。其实芮德菲尔德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如前所见,芮德菲尔德表明了人类学家共同参与“大传统”研究的意愿和态度,他说:“如果我们愿意认可在上面两段里所阐述的关于世界上的几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和几种大传统之间的关系的观念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设法改进人类学学者和历史—人文学者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只有这样才会使后者更深刻全面地理解他所正在对之进行深刻研究的某一种思想与在该思想指导下那种文明主导人们生活的全貌之间的一切关系。也只有这样才会使前者能更确切地描述大传统所蕴涵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来影响他正在对之进行研究的那个社区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那个社区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如何反过来影响大传统所蕴涵的意识形态。”[1](P117)然而,研究“大传统”毕竟需要相应的严格的知识训练、理论素养以及学术视野。但考察表明,似乎正是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小”将芮德菲尔德自限了起来。换言之,芮德菲尔德是囿于自身的学科背景和学术视野的,或是囿于人类学学科的视域与语境的。应当说,大传统与小传统本质上涉及哲学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芮德菲尔德没有哲学训练的本质概念,其不懂在“小”中其实有“大”的东西,未能由“小”见“大”,即:那种贯穿于无限的“小”的东西其实是“大”的,也就是普遍的或普世的。文明传统的研究会涉及大至小各层级的对象与内容,小至部落、村社,中至部族、地域,大至民族、国家。其中,作为“大传统”的民族与民族的区别、国家与国家的区别、文明与文明的区别,通常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现象或问题,同时,也是历史哲学或从事历史研究的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既有人类学身份也有历史学身份的张光直所提出的连续与突破理论对于“大传统”问题的思考,显然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注释:
①罗伯特·芮德菲尔德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PeasantSocietyandCulture)1956年出版,2013年由王莹译成中文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中国出版。
[1] 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 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卷五·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江雨桥)
Re-examination of Redfield’s Theory of “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
WU Chun
(College of Philosophy,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Robert Redfield’s masterpiece,PeasantSocietyandCulture, won wide acclaim in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 history and history of ideas for its theory of “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 Redfield’s concepts of “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 seem concise and clear, but the connotations are complex and imperfect, and even misleading and confusing. When it comes to terms, it is not scientific to define “great tradition” with the elite and “little tradition” with the public. The value orientation at the state or government level is not necessarily great tradition, neither are the so-called elite thoughts necessarily great tradition. Some ideas or value orientations of the folk or public are not necessarily little tradition. Besides, national and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s are not necessarily contradictory, and they may be consistent or unified. In many cases, the elite and the public are not of great difference. There is only one standard of judging “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 that is, whether the tradition is of the mainstream or not.
Redfield, great tradition, little tradition, elite, public, anthropology,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2016-11-10
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上海师范大学哲学项目
吾 淳,又名吾敬东,浙江衢州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哲学研究。
B089.3
A
1004-8634(2017)01-0027-(08)
10.13852/J.CNKI.JSHNU.2017.01.004
——造梦城市中的精神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