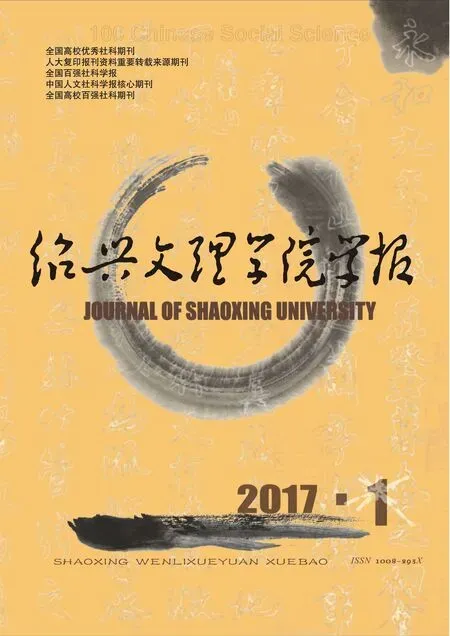中国古代神话碎片化成因再认识
王东辉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252000)
中国古代神话碎片化成因再认识
王东辉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252000)
“碎片化”是中国神话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粗简与散乱两个方面。关于这一特征的成因,历来的各种解释并不是非常准确。根据神话的发展规律,中国古代神话“碎片化”状态的形成源于它始终保持着原始面貌而未得到加工,而这一加工动力与需求的缺失,同中国祖先崇拜与政治实用主义传统有关。祖先崇拜的排他性决定了中国古代神话不会得到全民性的、持续不断的加工整理,也阻断了它广泛吸收新的神话元素的可能。在政治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下,相对于鬼神本体统治者更关注政治的稳定,因此不会费心去建构虚幻的神话。此外,受实用主义及阶级限制的影响,中国古代始终没有形成围绕自然神灵的丰富的神话。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中国古代神话“碎片化”的特点。
神话;碎片化;祖先崇拜;政治实用;自然神
论及中国古代神话,“碎片化”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话题。“碎片化”是中国古代神话最为明显的特征,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神话散见于各种文献中,其记载大多吉光片羽,简约模糊。相对于西方神话(如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等)的丰美华赡,我们的神话要单薄得多。自20世纪初神话学在中国诞生伊始,中外学者对神话“碎片化”形态成因的探索就从未停止。盐谷温、鲁迅、胡适、茅盾、袁珂等都曾对这一特征的形成给予解释,然而其中影响较大的如盐谷温、茅盾的解释并不是非常准确,历来多有学者提出质疑与批判。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神话“碎片化”的成因,对于把握中国神话发展脉搏,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生态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也是当今神话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神话碎片化表征
中国古代神话的“碎片化”特征表现有二:一是粗简,二是散乱。
(一)就“粗简”来说,中国古代神话多记述简略,关于这些神话从来就没有形成诸如《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的长篇史诗,非但没有长篇,即便是一些情节相对完整的故事都少之又少。对神灵的记载往往都是寥寥数语,少则几个字,多则几十个字,集中于对其主要事功的粗笔勾勒。除此之外,神的相貌、性格、情感等等皆无从知晓。与神相关的故事,多趣味淡薄,内容直白而细节缺失。
(二)就“散乱”来说,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多彼此独立,血缘联系淡薄,上下统属关系亦不明确,对他们很难做一个谱系化的梳理。此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从来就没有一部搜奇记逸的神话专著,各种神话人物及其相关故事散见于《山海经》《尚书》《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甚至保存在一些注疏之中。中国古代不仅没有记载神话的专著,即便专门为保存、传播神话而进行的记录也几乎见不到。如保存神话最多的《山海经》,其中对神话相关资料的记录,更像是记录地理方物时的一种顺带说明。
二、神话发展规律
关于中国神话“碎片化”的成因,有两个最为著名的解释,一是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观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援引他的话说:“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具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1]二是茅盾的观点,他认为神话的破碎源于历史化的修改对神话的摧残。[2]
盐谷温认为,神话的散亡源于讲求实用的儒生的回避与舍弃,这种说法并不是特别的准确。神话碎片化固然有中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原因,但这种实用主义在商周时期就已形成,并不是儒家开创的。况且在儒家之前神话就是一种散乱破碎的状态,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茅盾神话历史化观点的形成,是受到了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他根据希腊神话发展的规律来规范对中国神话发展的研究,这种忽视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生硬搬套、比附显然是不合理的。神话历史化只能发生在自然神话中,而中国以祖先神为主的古代神话是不可能被大规模历史化的。[3]
无论是盐谷温观点还是茅盾的观点都默认一个前提,即中国上古时期是有丰富的神话的,只是由于历代散亡才造成破碎的现状。这一前提的正确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它并不符合中国神话发生发展的规律。我们知道神话是上古初民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与人类自身朴素、原始的认识。任何民族的神话都不可能一开始就体系完整,都是从简单到复杂逐渐发展的。作为初民生活的投影,神话必须以初民的生活实践为根基。原始时代简单的社会劳动实践以及相对隔绝的生活状态决定了原始神话也必然是简单而片段的,不会有什么宏阔的叙事,完善的构架,丰富多彩的人物故事。忽视神话产生的现实条件,而侈谈开天辟地、诸神的纠葛等等各种神奇与幻想的宏大叙事,都是错误而不可取的。所以说破碎、朴拙才是神话最为本质的表现。商及周初,华夏民族刚从原始时代的蒙昧状态中脱离出来,在这种方国林立,彼此之间相对隔绝的社会状态之下很难建立一个包容万象的神话系统。如果此时有一个完善的神系,那么肯定会在历史记载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因为中国在商代已经有了文字,具备了记录神话的条件,并且此时社会宗教氛围浓厚,鬼神在人的思想及生活中尚且占有重要地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体系丰富的神话是不可能被大规模破坏的,然而我们却看不到丝毫体系神话的痕迹,所以说中国神话是先天不足的,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个完整的神的系统,更不用说对这一系统的破坏了。
神话是历史发展着的,其存在状态是动态而不是静态的,在被文字记载固定下来之前是不停地演化的。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神话难免要掺入传承者的自我认识,被不停地修改、加工。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不同部落、地域之间的人们经过战争、贸易、婚姻等各种活动联系日趋频繁,不同的信仰与神话也会彼此交融,互相吸收而不断发展,因此神话内容不断丰富,体积不断增大。希腊神话就因为吸收了不同文明的元素才有了今天的规模,其中既有埃及神话中的形象,也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以及东方文明中的神话形象。如赫拉为远古的迈锡尼守护神;阿尔忒弥斯的神话形象来源于小亚细亚;阿弗洛狄忒本是东方之神,其最古老的崇奉中心是塞浦路斯岛;[4]半人半马的喀戎以及人面兽身的斯芬克斯都更像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形象。所以说,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自称可以为每位希腊神找到他的外来名字是有一定道理的。
除了各种社会交流活动对神话丰富与完善的无意识的推动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后世神话记录者对它的有意加工。希腊神话之所以如此丰美很大程度上是荷马及赫西俄德对它精心加工的结果。荷马、赫西俄德对民间流行的神话进行了大量的系统化的加工整理,消除了原来那种驳杂、模糊的状态,建立了明确的神系,给神话中的诸神命名,描绘对应神灵各自的面貌和性格,完成了个性化的整理。[5]126“就此而论,‘荷马创作了希腊诸神’这一古老谚语,堪称某种历史真实的写照。”[4]
由上可知,“碎片化”才是神话最为本真的状态,体系宏赡的神话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不断吸收、熔铸、加工的结果,是经过多次创作才得到的。中国神话一直保持这种“碎片化”的状态而未完成体系化的整理,应归因于熔铸、再加工过程的缺失,从更深层次上说应该是缺少对神话进行加工、创造的需求与动力。
三、中国古代神话碎片化成因
神话作为原始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同原始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一性与浑融性,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界线。卡西尔说:“宗教在它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始终不可分解地与神话的成分相联系,并且渗透了神话的内容。另一方面,神话甚至在其最原始最粗糙的形式中,也包含了一些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预示了较高较晚的宗教理想的主旨。神话从一开始就是潜在的宗教。”[5]112由此可知,宗教同神话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宗教是研究神话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然而在神话研究中我们往往忽视宗教对中国神话形成与发展的作用。
古希腊与古埃及的神话基本等同于二者的宗教。古希腊的宗教并没有明确的教义教规,也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围绕着诸神的大大小小的神话故事构成了古希腊宗教的主体。正如韦尔南所说的“对于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来说,只需相信长篇累牍的各种故事——从童年起就知道的故事——就足够了。”[6]神话构成了希腊人生活的全部,构成了其思维、习惯、生活方式。“它扎根于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与之紧密融合,与之共同包容了希腊文明所有其他的构成成分,以及所有赋予城邦希腊以特有面貌的东西:从语言、手势、生活、感觉、思维方式到价值体系和集体生活规则。”[6]同样,古埃及的神话也是古埃及的宗教,这些见于金字塔、墓葬壁画等处的神话故事就是对古埃及宗教故事的记录。
上面我们提到,体系神话的形成必须经过广泛的吸纳与持续不断的加工,西方神话有着全民性的宗教信仰基础,其体系的建设得益于对它的全民性持续关注。正因为有着深厚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才会有构建、加工神话的动力与需求,才会有诸如荷马、赫西俄德这样的说唱艺人对它予以热心的整理。可以说任何一种体系化的神话,都离不了早期宗教作为其发生发展的推动力量。中国在商周时期也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完整的神话系统构建呢?这应该从中国的祖先崇拜与政治实用传统中去找寻原因。
(一)碎片化与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指对死去祖先及部族英雄的灵魂的崇拜,它是中国古老而传统的宗教信仰形式。将中西方神话稍作比较,不难发现二者神灵形象的明显不同。西方神话中多自然神的形象,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是海神,阿尔忒弥斯是月神等。古埃及神话中自然神崇拜更为明显,他们甚至都没有褪尽自然物的形象。例如拉神最常见的形象是鹰首人身,头顶上有一日盘及一条盘曲在日盘上的蛇;阿努比斯的形象是狼首人身等。
反观中国神话,其神灵表现出来的则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形象。无论是抟土造人的女娲、尝百草的神农、填海的精卫,还是射日的后羿、治水的大禹、追日的夸父,表现出的都是对自然的反抗与征服,对安定生活的追求与实现,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多社会色彩而少自然抽象。他们的所作所为多是为人类服务,处处散发着朴素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些道德化的神灵人物推其本源,应是神话时代的英雄人物或部落酋长,因对部落做出突出贡献而被铭记传颂、附会演绎,并逐渐神化。随着民族融合的推进,他们逐渐被不同人群认可,而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神。当然,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诸如风伯、雨师、烛龙之类的自然神,但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这些祖先神构成了中国神话的主体。
祖先崇拜一直是华夏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形式。由于史料的缺乏,夏朝祖先崇拜的具体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尊奉祖先的传统应该是确定无疑的,有关夏朝祖先鲧、禹治水的神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商朝是一个对巫筮贞卜极度痴迷的一个朝代,在留下的十多万片甲骨卜辞中,能确定为祭祀祖先的有15000多条,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类辞例。[7]除此之外,殷人对祖先的祭祀也极为频繁与隆重,不仅在与祖名相应的十干日时单独祭祀该祖,还要举行遍祀众多祖先的合祭。至此意犹未足,又有将上甲以下先公先王轮番祭祀的周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商朝祖先崇拜的兴盛程度。周朝建立之后,鉴于殷商亡国的教训,虽然削弱了鬼神的地位,然而祖先崇拜的传统却一直保留下来。后来这一传统经过了周公的改造,糅合了礼制的元素,获得了极大的生命力,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并影响至今。
祖先崇拜有种天然排他属性,信众对自己的祖先认可而对他族的祖先排斥。这种排他性使神灵的影响只能局限在本部族之内,其信众也只能是自己的子孙。不同的部族有不同的祖先,因此也就有不同的神灵。不是本族的祖先神是不能妄加祭祀的,即“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国语·鲁语》)实际上,在先民的观念中,对于非本族的神灵,即便是祭祀了也不会得到这些神灵的福佑,即“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历史上,祖先崇拜的排他性一直存在。《国语·鲁语》载:“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8]126夏部族、商部族、周部族各有自己的祖先,也就各有自己的神灵崇拜,所以他们禘、郊、祖、宗的对象也各有不同。无论商周,在建立政权之后都要抬高自己祖先的地位,以证明自己的祖先是顺应天命,代表天的意愿去统治万邦,这样才能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在这一观念影响下,不唯祭祀的对象各有不同,就是祭社里用的木头也是各有不同,“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论语·八佾》)
西方古代宗教信仰中的神主要是自然神,他们超越于一家一族的范围之上,可以为不同种族、阶层所信仰,具有很强的普及性与历史延续性。因此在政权更迭、民族变迁的时候,宗教崇拜依然能够延续下来,并在不断加工的过程中建立一套完整的神的系统。而中国因祖先崇拜的影响,不可能形成一个超越族群的、全民性的宗教信仰,政权更替、部族消亡带来的必然是神灵的更替与消亡,每次都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这种间断性的变化破坏了宗教发展的连续性,对神灵不会形成持续不断的注意,因此也就不会形成一个不断丰富与完善的神的系统,神话在兴替变化的过程中日渐凋零而最终湮灭。
另外,祖先崇拜以祖宗先人作为神灵列次供奉,这样就形成一个封闭的神的系统。在神的殿堂里被供奉以及将被供奉的永远是祖先、时王以及后世之王。这无疑排除了其他神灵进入这一信仰体系的可能,神的世界很难吸收新鲜而多元的元素。这种狭隘的神灵观使宗教信仰变得沉闷而单调,这肯定不符合神话以进取与包容精神为要求的发展规律,反映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就是它减少了那种奇幻瑰丽多姿的色彩,也没有了涵容世间万千事物的厚重气象。由此可见,祖先崇拜作为中国宗教信仰的主要形式,既决定了中国神话的主体构成,又深深地影响了神话发展的进程,是神话“碎片化”现状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二)碎片化与政治实用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家国同构的特点,政治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据核心的地位,统治者最为关注的是如何实现政治的稳定,宗教作为服务于政治统治的工具,从来没有超越于政治之上。实用主义在各种宗教信仰中普遍存在,然而在中国却尤为明显。中国古代神话中没有冥界的鬼神,没有哈得斯,没有三头犬,也没有阿努比斯。中国古代神话只关注今生而少思考来世,同西方神话相比,明显缺少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与探究,那些具有超越色彩与宗教形而上学倾向的遐想在中国并不盛行。
中国古代神话史上有一则重要的公案,即“绝地天通”。《尚书》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楚昭王对此迷惑不解,于是咨询观射父这句话的含义。观射父回答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神异业,敬而不渎。”“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8]530这就是说,古时祭祀的工作由巫觋等专职人员管理,所以神人不杂,社会秩序井然,民生安定。到了少皞末期,社会秩序混乱,祭祀的权力不再为巫觋专有,家家奉祀无度,民生凋敝。所以颛顼命令南正重司天专门管理鬼神祭祀之事,命火正黎专门管理民生之事。“绝地天通”实际上就是杜绝民人过度沉迷巫卜、祭祀无度的行为。因为这种全民性的宗教狂热破坏了社会等级秩序,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由此可知,上古时期的宗教崇拜是以政治稳定为前提的,是为社会治理服务的,过度的迷信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是统治者绝不允许的。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商朝宗教氛围浓厚,对鬼神之事极度痴迷,几乎到了无日不祭,无事不卜的地步。虽然如此迷信鬼神,但商朝并没有形成丰富的神话,如关于至上神——上帝的神话几乎未见。这一现象盖源于中国政治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甲骨卜辞是商人鬼神思想最为直接的体现,据陈梦家的划分,甲骨卜辞可分为六类:祭祀、天时、年成、征伐、王事、旬夕。[9]42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多是围绕着王朝政治生活而进行的占卜记录,是为政治生活服务的。正如陈梦家所说,“殷人对于自然力量的崇拜,对于通过巫术行为与自然发生虚幻的交通,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和当时部落之间斗争的激烈”。[9]561这种立足于现实政治的实用主义,决定了商朝的宗教信仰不可能产生丰富的神话。
周代,随着鬼神信仰的降温,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尚书·金滕》载,武王克商之后第二年生病了,周公向太王、王季、文王祈祷,自己愿意承担武王的病痛,并希望先王能答应自己的请求,并告诉先王“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你们如果答应我,我就把玉璧、玉圭奉献给你们;如果不答应我,我就把它们收起来。向祖先神祈求福佑时,周公用的几乎是威胁的语气。《左传》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10]祝融与鬻熊是夔国与楚国共同的祖先,夔国先王身患残疾,得不到他们的保佑,失去了继承楚国王位的权利。因此,夔子便放弃了对祝融与鬻熊的祭祀。由此可见,此时的祖先崇拜饱含着政治实用的功利目的。
总之,鬼神的地位固然重要,人们对鬼神的关注也似乎无处不在,然而,这些种关注的根本对象是人而不是神。在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如何求得神灵的福佑,如何满足自己的需求,神灵只是一种工具,献祭也不过是一种手段。信众并不在意鬼神本体,关于他们的生活、情感、容貌等并无太大兴趣,人们不愿无中生有地去构思、幻想许多的神话故事,对于流传下来的祖先神话也没有深入整理加工的兴趣与动力。在实用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虽有鬼神观念,但不会围绕它们产生丰富的神话,所以说政治实用也是造成中国古代神话先天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民本意识,人民不再是匍匐在神脚下的奴隶,而逐渐成为影响神决策的重要力量。“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在统治阶级看来,民心的向背会决定“天”对他们的态度,不重民生就不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就不会有政治的稳定。要求得政治统治的稳定,统治者不应该一味祈求神的庇护,要做的更多的是如何赢得人民的拥护。当统治者把相当的精力集中在人民身上时,对于神的关注就减弱了。失去统治阶级这一占有大量经济、文化资源的社会阶层的关注,民间即便有些原始的神话,仅靠口耳相传很难保存下来,它们或改易,或消歇,最终留下来的只是零星碎片。商朝的甲骨文绝大多数是记录占卜的卜辞;周代文献也多是对王朝历史、政治典诰的记载,是政治生活的产品。战国时期,礼乐崩溃,旧的制度不再是束缚思想的桎梏,新的思想各逞其能,这使得尚且留存于普通民众之间的上古神话传说有了被记录的可能。因此,神话在这一时期开始不断见于文献。然而,从商朝到春秋战国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经过社会的变革、战争的影响,本就稀少的神话被冲洗得更加残破、零碎。中国古代神话错过了商周这一记录整理的关键期,任何系统化的希望都变得再不可能。
四、自然神话
在中国神话体系中,除了祖先神之外,还有一部分自然神,如在古代宗教信仰中最重要、地位最高的神,在商曰上帝,在周曰天。除了天之外,还有海神、河伯、风神、司寒之神、山川之神等。然而,围绕这些自然神,并没有形成丰富多彩的神话,相较于祖先神话,自然神话更为破碎、稀少。比如“天”在商周时期拥有极高的地位,然而这一自然神竟然一直没有完成人格化的过程,而始终保持一种抽象的存在。究其缘由,首先是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商周时期,天地山川神灵只是人们祈福禳灾、咨询致问的一个对象,只有对自己需求的满足有帮助的自然神,人们才会祭祀它。“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国语·展禽论祭爰居非政之宜》)所以说凡是列入祀典的自然神灵都必须能造福于人民。反言之,那些对人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自然物是不会得到人民的祭祀的。人们对自然神灵的祭祀也仅仅寄希望于它们满足自己的愿望,同祖先崇拜一样,对于超出这种实用目的之外的神的记述与构建,他们是不感兴趣的。
另外,对自然神的祭祀还存在着等级性的差异,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去祭祀日月山川诸神的。“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国语·观射父论祀牲》)天子可以遍祭天地、日月、山川、祖先等群神,诸侯则只能祭祀天地、日月星以及封国之内的山川,到了士、庶人这里则只能祭祀他们自己的祖先。不仅祭祀的范围存在等级性的差异,就连所用祭品也存在等级的差异,“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国语·观射父论祀牲》)祭祀对象及祭品的不同,是社会阶级地位不同的投影。神话的丰富与发展,依赖于尽可能广泛的社会人群。而这种等级化限制,压缩了信仰人群的范围,失去了对自然神祭祀资格的普通大众,自然也不会对他们加以美饰与加工,神话失去了丰富多彩化的最大动力。
综上所述,零星破碎是神话发展初期普遍的存在状态,中国古代神话的“碎片化”特征只不过是保持了这种原始的形态而未得到加工创造。这一加工动力与需求的缺失,盖源于中国祖先崇拜与政治实用精神的影响。祖先崇拜决定了中国上古时期不可能形成一个纵向前后一贯,横向全民统一的宗教信仰,因此神话不会得到来自全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加工整理。另外,祖先崇拜的排他性也阻断了中国古代神话吸收新的神话元素的可能。在政治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人们对鬼神的崇拜只不过是趋福避祸的一种手段,统治者关注的更多的是鬼神对政治统治的影响,对鬼神本体反而少有注意,所以也就不会费心劳思地去建构神话了。另外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自然神,因政治实用主义及阶级限制的影响,始终没有形成与之相关的丰富的神话。
面对丰赡的西方神话,每论及中国古代神话的“破碎化”特征,总有许多学人扼腕叹息,这其实大可不必。中国神话的这种原始状态并非毫无积极意义,袁珂认为“它的优点是接近原始本貌,便于利用它来做科学研究的材料。”“然而正因为它始终是零星片段,没有定型,它便以别一种形态,转化增生,朝着文学化的道路发展,成为文学化的神话、仙话、历史人物的神话、地方风物及民情风俗的神话等等,涓涓细流,浸润到中国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其影响的普及也是不容忽视的”。[11]碎片化的中国神话同丰赡的西方神话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划分,各是其文化使然,各有各的发展特点、轨迹,如此而已。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0.
[2]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
[3]常金仓.中国神话学的基本问题: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9(3):5-13.
[4](苏).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M].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41.
[5](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26、112.
[6](法)让-皮埃尔.韦尔南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1、10.
[7]晁福林.论殷代神权[J].中国社会科学,1990,(1):99-112.
[8]邬国义、胡国文等撰.国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9]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230.
[11]袁珂,周明.中国神话资料萃编.[M].内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38.
(责任编辑 吕晓英)
Rethinkingthe Cause of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y Fragmentation
Wang Donghu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
Fragmentation,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mythology,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rough and scattered. There have been some inaccurate explanations concerning the causes of this feature.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al law of Chinese mythology, the Chinese ancient mythology fragmentation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it keeps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and remains unprocessed, and the lack of processing is relevant to the Chinese ancestors’ worship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pragmatism. The exclusion of our ancestor worship determines that the Chinese ancient mythology does not get universal, continuous processing, thus blocking the possibility of widely absorbing new mythic eleme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pragmatism, rul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than the ghosts, so they will not bother to construct the fictitious myths. In addi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ragmatism and class limitations, ancient China has not formed rich mythology on natural gods. These factors put together resulted in the fragment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y.
mythology; fragmentation; ancestor worship; political pragmatism; natural god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7.01.012
I206.2
A
1008-293X(2017)01-0083-07
2016-10-10 基金项目: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本事迁移理论与艺术再生产研究”,项目编号:15-ZZ-WX-06。
王东辉(1987- ),男,山东莘县人,聊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