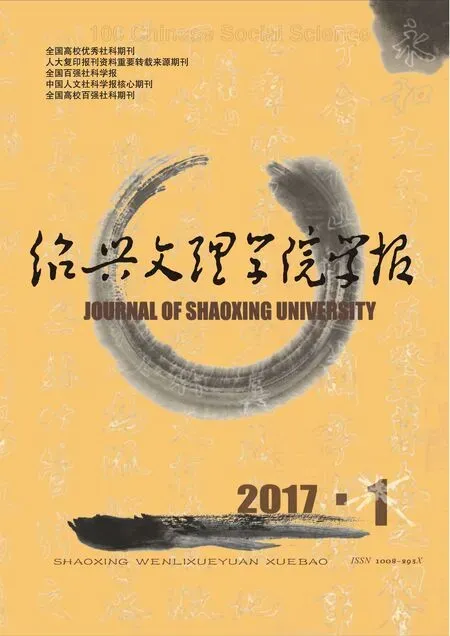论章学诚“文气”说的理论内涵与创新
马兴祥 徐利华
(河北经贸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61)
论章学诚“文气”说的理论内涵与创新
马兴祥 徐利华
(河北经贸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61)
文气说是章学诚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文气的理论内涵及其对作家和创作的意义。从“文德”角度,他把“气”解释为“心气”和“心术”,主张临文时的“气平”“情正”。他把“养气”解读为作家通过读书以“集义”,从而形成“才识”的过程,因为“才识”和学问是写文章的根本。他试图用“文心”说消解文法思想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文心”又是形成作家主体性与个性风格的关键;章学诚文法论的关键词“清真”,对行文和修辞的相关理论都包含在文气的概念之中。章学诚的文气说自成体系,在传统文气说的基础上多有创新,体现了他文以致用、学以经世的学术理念。
章学诚;文气;养气;文学思想;文法
章学诚(1738-1801)作为浙东史学的集大成者,为中国古典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而其文学理论见解也同其史学思想一样,“别出一格”,不少文学批评史家如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张少康等都对此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阐释[1]。“文气”说在章学诚的文学思想中具有特殊而广泛的含义,而目前学界并未就此给予专门的探讨。章学诚的“文气”说涉及文学家心态、文学素养、文法思想,以及文例、文理等内容,构成一个独立的内涵体系,彰显出章学诚对传统“文气”说的大胆创新。
一、“文德”与“文气”
章学诚论史、论文非常强调“德”,在《文史通义》中他专门写了《史德》和《文德》两篇,而“文德”一词却并非章学诚首先提出。章太炎曾说:“文德之论,发诸王充《论衡》,杨彦遵依用之,而章学诚窃焉。”[2]279*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3《文德》注释[一]。章学诚讲“文德”,并非如章氏所说只是矫袭前人成果,而是有其独到的理解。他在《文德》篇中说:
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尝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辞立其诚”;孟子尝论“知言”“养气”,本乎集义;韩子亦言“仁义之途”,“《诗》《书》之源”,皆言德也。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2]278
章学诚他认为古人说的“文德”是道德与文章的结合物,二者之间是内外与本末的关系,暗含以德为内、为本,以文为外、为末的二元对立思想,容易导致对“文”的轻视甚至否定,这与他理解的“文德”不同,他所理解的“文德”即所谓“文辞”中的“文德”。陆机、刘勰、韩愈和苏辙虽有文辞之论,涉及作家的才、学、识问题,却未谈到“文德”问题。章氏认为,写作之时秉持“敬恕”之心,就是“文德”的体现。他特别说明,“敬恕”之心,不是以“修德”为“敬”,以“宽容”为“恕”,这种解释是哲学范畴内的说法,在古代学术中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而这正是孔子、孟子及韩愈“德”论的主题。作为“文德”之体现的“敬恕”之心,是无关道德的心境和心态,就此而言,他才说“知德者鲜”。他说:“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2]219因此,章学诚“文德”论的实质只是一个与道德修养没有任何关系的作家“心术”问题。
章学诚认为,作为作家“心术”问题的“文德”与“气”有密切关系,“气”特指一种“心气”。他曾反思自己作文的心态变化,他说:“仆于学有未至,或文于理有未足耳,若谓著述文字,尚有名心胜气,有若文人相轻者然,则十年以来无此累矣。”[3]643没有了争胜、求名的心气,就是文德的表现。在《文德》篇中,他又提出了“凝心养气、炼识成才”以成“文德”的主张。他说:
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气于水,言为浮物。柳氏之论文也,“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夫诸贤论心论气,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杀,语变而各有当。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心虚难恃,气浮易弛。主敬者,随时检摄于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缉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其为义也广矣。今为临文,检其心气,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2]279
《文史通义》贯通文与史,但在二者之间,章学诚认为史是文的根基,二者犹如稼穑与饮食的关系,没有史,便没有文。“史有三长”,即才、学、识,三者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识”从“心”生,但“心虚难恃”;“才”源于“气”,但“气浮易弛”。“学”可以“炼识成才”,因此,“学”关乎“心”与“气”二者,是“凝心以养气”的功夫。这种功夫,就是要“主敬”,要随时对“心气”进行“检摄”,杜绝其流弊的产生。“敬”能够使“心平”,使“气有所摄”,才能在作文之时,面对“文繁”和“语变”的情况,应对从容,合乎法度,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因为“敬”的心态,才有了圣人的“有始有终”,可见“敬”的重要作用。“文德”就是“心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章学诚认为前人未曾论述过“文德”的看法,也是确有所据的,是可以理解的。
就“文德”而论,章学诚主张要时时“检摄”“心气”,以保持“敬”的心态,这是作家临文之时的“心术”,这在章学诚看来非常重要,他说“心术不可不慎也。”在《史德》篇中,他专门就此加以论述:
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2]220
章学诚认为韩愈和柳宗元等人论养气,“未及天人、性命之微”,未考虑天人之别,而这又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气合乎理是天,但违理自用则是人,这是人的本性,不是总能与天合一的。一旦外事有所感发,则气容易动摇,愤激,容易傲娇,这是阴气太过的体现。情出于性是天,但汩性自恣则是人。一旦为外事所感发,人之情容易失控、陷溺,容易偏私,这是阳气太过的结果。以上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似公而实私、似天而弊人的结果,最终使文章违背道义。因此,为了避免“阴阳之患”,他提出“气贵于平”,“情贵于正”的主张,需要“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的阴阳平衡术。
气分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念,但在文论方面的养气说,并没有具体而明确地划分阴阳,只是笼统讲一个“气”。阳而刚,阴而柔,是气的二重属性。阴阳相合,刚柔相济,是就“气”的层面来寻求并达到一种平衡,形成中和之美。章学诚则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以“阳刚”作为对气的要求,可以使气“平”;以“阴柔”作为对情的标准,可以使情“正”。只有“气平”“情正”,才能做到“气昌而情挚”,从而创作出天下最好的文章。
章学诚认为“心术”是可以培养的。在《史德》中,他说:“心术贵于养也。”[2]221对心术的培养就是“养气”。他特别提倡一种待人接物的平心静气,杜绝“忿气”“骄气”以及“霸气”等不关世道人心的“私心盛气”。他说:“吾辈辩论学术,当有关于世道,私心盛气,何以取后世之平?”[3]645
二、“才识”与“养气”
“养气”论非章学诚首倡,孟子、韩愈、柳宗元和苏辙等人,都有论述。只是他们更多强调道德人格的塑造及其对文章创作的影响。章学诚的养气说有两个含义:一是如前文所论述的,作家“气平”“情正”的的心术修养;二是作家“才识”的养成。他说:“读书广识,乃使义理冲积于中,久之又久,使其胸次自有伦类,则心有主,心有主,则笔之于书,乃如火然泉达之不可已,此古人之所以为养气也。”[3]324他认为古人论“养气”与文章创作的关系,是通过读书,增广见识,以积累义理,然后见之于文章。在《跋香泉读书记》中,他说:
文者气之所形,古之能文者必先养气,养气之功在于集义。读书服古,时有会心,方臆测而未及为文,即札记所见以存于录,日有积焉,月有汇焉,久之又久,充满流动,然后发为文辞,浩乎沛然,将有不自识气所以者矣。此则文章家之所谓集义而养气也。[3]322
文章是“气”的体现,作文需先“养气”。“养气”的过程,就是“集义”,这个“义”,不是道德方面的“正义”,不是通过“道问学”而至于“尊德性”,而是自宋儒以来“格物致知”的认识对象。义理要日积月累,久之,自然“充满流动”,既丰富而又能彼此贯通,形成作家的真知灼见,用文辞表现出来,就是“气”的外显,这就是“文”。章学诚认为这才是文学领域“养气”说的理论内涵。他并不强调古人“养气”说的道德人格修养意义,而是把“养气”与作家的“识见”结合起来,发现“养气”在作家创作层面的认识论价值。他同样从“史有三长”的“才、学、识”三者关系角度分析。《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云:
就三者分途而论,则才、识本于天而学由于人,本于天者不可勉强,而由于人者不可力为。就三者递用而论,即学固所以养才而炼识者也。韩退之谓:“气盛则言之短长高下皆宜。”又云:“沃其膏而希其光,溉其本而俟其实。”苏子由谓:“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皆是勉人力学以养其气,意诚善矣。然不知使人即其天性所近,而闻其入识之所最先,则人将以何者为学而集以为养气之基哉?固愚以为二公所言,亦是偏举而未全之论也。[3]669
才、学、识三者间有两种关系:一个是“分途”关系,即三者产生的根源不同,体现了先天与后天、天赋与人为的关系;一个是“递用”关系,即三者在创作过程中彼此交相作用的关系,“力学”可以“辨识”,“炼识”可以“充才”,“才”可“养”,“识”可“炼”,所谓“养”“炼”,就是“学”。因此,他又说“学”可以“养才”与“炼识”。他认为韩愈和苏辙的养气说本意是好的,即通过读书以养气。但他又认为,二人只强调学,而未能从人的天性出发,指明学的内容,养气也就失去了根基,从而成为“偏举而未全之论”。
章学诚养气论的“气”不但与道德修养无关,而且还有了明确的所指,即才和识,这是对传统“养气”说的重要补充,使得养气论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与作家创作才能的关系更加明确化了。另外,从“分途”关系上,才、识都是先天的,但在“递用”关系上,二者都离不开后天的学,因此,章学诚的“养气”说也具有承认先天禀赋,但更突出后天和人为重要性的特点,从而把前代养气论的内容有机整合在一起。
章学诚的文学批评论可以反映出他在才识与养气问题上的看法。他比较皇甫湜与李翱对韩愈的学习:
湜与李翱,俱称韩门高第,世称学于韩者,翱得其正,湜得其奇。今观其文,句鑱字削,笔力生健,如挽危弓,臂尽力竭,而强不可制。于中唐人文,亦可谓能自拔濯者矣。第细按之,真气不足,于学盖无所得。袭于形貌以为瑰琦,不免外强中干,不及李翱氏文远矣。按二人虽俱学韩,李能自立,不屑屑随韩步趋,虽才力稍逊,而学识足以达之。故能神明韩法,自辟户庭。皇甫则震于韩氏之奇,而不复求其所以致奇之理,藉口相如、扬雄,不知古人初非有意为奇,而韩氏所得,犹为平实,不可袭外貌而目为奇也。[3]69
皇甫湜在中唐文人中确能自成一格,但章学诚认为,他并没有从韩愈那里真正学到什么,只是外在形貌上对韩文“奇”的模拟,是外强中干,原因在于他“真气不足”,即才识不足。李翱虽才不及韩愈,但因为识高,所以能学得韩文精髓,“得其正”,能够“神明韩法,自辟户庭”,远远超过了皇甫湜。
三、“文法”与“文心”
文章创作方面,作家的识见同样至关重要。章学诚认为,通过“集义”的方式形成“真识”,可以解决创作过程中文法多样性和多变性问题。他说:
理则书中之全理也,法则就书中截句为题,实意虚神,来脉去路,偏全轻重,变化无定,题形增减毫厘,而文法差以千里者也。学者胸中,须有真正识解,则千变万化,皆可一以贯之。苟胸中本无真识,惟于逐处仿摩形似,则劳苦而鲜有成功。[3]672
文章创作之“法”注重虚实,讲究来去,有轻重之别,有增减之变,唯有“真识”才能驾驭“法”的“千变万化”。章学诚认为,通过学以养气,成就作家的“真正识解”,才能在作文之时“一以贯之”,以不变应万变,更能够游刃有余。
章学诚充分认识到“文法”自身的矛盾性。一方面,他说“文法”作为一种规律,总是可以被认知和遵循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文境”的概念,认为“文境”总是千变万化,“文法”不能涵盖所有“文境”。他说:“法度资乎讲习,疏于文者,则谓不过方圆规矩,人皆可与知能,不知法度犹律令耳。文境变化,非显然之“法度”所能该,亦犹狱情变化,非一定之律令所能尽。”[3]81因此,在“文法”的有限性与“文境”的多样性和无限性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矛盾。他说:“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则音节变化,殊非一成之诗所能限也。”“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2]288-289。他认为古诗和古文的创作方法,并不能涵盖诗歌音节的变化和文章的变化,因此,“文法”总是有限的。“即以帐簿而论,文法千变万化,惟其是尔,故有似帐簿而失体裁者,亦有似帐簿而得体裁者。”[3]63
文无定法,随时而变,这就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经常提到的“有法”与“无法”“定法”与“活法”之间的悖论。章学诚的“文法”论思想,既承认这种悖论的客观存在性,又积极寻求办法,试图解决这种悖论。这就是他的“文心”说。他说:“深于文法者,必有无形与声,而又复至当不易之法,所谓文心是也。精于治狱者,必有非典非故耳,而自协天理人情之勘,所谓律意是也。文心律意,非作家老吏不能神明,非方圆规矩所能尽也。”[3]81善于断案的高手,不必所有案件都能有所依据,只要本着合乎天理人情的规律,自然可以获得成功,把天理人情作为案件勘验的依据,也是法律的本意,并不需要把所有案件的特殊性都进行归纳,形成条款。同样道理,真正懂得文法的高手,只要能从“文心”出发,自然能够贯通有无,找到恰当而不变的真正文法。因此,“文心”是解决文法矛盾的一把钥匙,是解决“文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矛盾的关键所在。通过读书明理的“集义”方式,于心中形成对“文法”的“真正识解”,即所谓“才识”,才可以不变应万变。因此,章学诚的“文心”说也关乎“文气”问题,因为“才识”离不开作家的“养气”过程。
章学诚虽然肯定了文法有规律可循,但因为作家主体的“文心”不同,这些文法是不能真正被传授和被学习的,文章创作在文法层面上,理应表现出作家的主体性和个性。对此,他并不赞同中国古代文论中对文法的总结和归纳。他说:
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于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于文辞思过半矣。至于不得已而摘记为书,标识为类,是乃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于其书中之本然。……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至于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得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也。[2]288
章学诚认为,诸如《文赋》《文心雕龙》和《诗品》等文学批评著作对文辞技法的理解,只是批评家们一时的感悟,其中“举隅反三、称情比类”的结论不能作为诗歌创作的可信之法加以传授。从“文法”言,可传授的只是其中有限的内容,所谓“规矩方圆”,而作家的心境和意绪,即“心营意造”的内容,带有作家特定心境和特殊情怀的体现,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些是不能在父子、师徒之间进行传递和继承的。这点恰恰与曹丕的“文气”说相近。曹丕强调作家的个性、气质的先天秉性和独特性,他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种气,“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章学诚也继承曹丕“文气”说的先天论内容。曹丕说“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章学诚也说:“尝论诗文有得,而能自成家,古人不皆兼擅长也。”
第专攻文者,不能不作韵语,碑铭传赞之类是也;其不能诗者,韵语率多简质古直,不失古人铭金勒石之意而已。专攻诗者,不能不作散语,题赠小序景物注记之类是也。其不能文者,散语率多古拙疏朴,间或不免冗碎险涩而已。文人不能诗,而韵语不失体要,文能兼诗故也。诗人不能文,而散语间或芜累,诗不能兼文故也,然即为真诗人矣。才虽短于属文,心必通乎文理。[3]83
有人长于作文,有人则长于作诗,各自所擅长不同,这是由于天赋秉性各异,不能强力改变。在《与周永清论文》中,他说:“天质之所良,则事半而功倍;强其力之所不能,则鲜不踬矣。足下于古文辞,盖长于叙情,而短于持论。故仆当时一见,便曰诗人之文,可以自成一家。今十许年,所见足下之文,皆不出此一语,而足下卒不相信,偏好持论,犹好论学论文,真不善用所长也。大抵论学论文之言,非出乡气、稚气,即是矫袭人言,而文失其本旨者也。”[3]86所谓“天质之所良”,就是曹丕所说由先天决定的作家气质和个性,依照先天条件,发挥特长,容易事半功倍,否则,强力而为,必然失败,这也是曹丕“文气”论的内涵。只是章学诚在承认作家性格的先天因素外,也突出强调了作家“文心”“营造”的作用。这样,文章风格的多样性就不仅仅决定于作家的气质和个性,也更在于作家有意识的独创性发挥。因此,“文心”说的意义,在于用“心”突破“法”的种种限制,并用“心”统领和贯穿一切“法”,这正是他所说,“才虽短于属文,心必通乎文理”的原因。以韩愈墓志铭的写作为例,他说:
就韩文碑志而论,如《卢殷李楚金之墓》则有志无铭;《卢浑胡允明之墓》则有铭无志;《张圆之墓》即称散文之志为铭。彼盖心识古人源流,随时通其变化,未闻当日子孙以为欠缺,观者以为疵议也。[3]76
韩愈墓志铭的写作不拘成法,或者有志无铭,或者有铭无志,或者以志为铭,志与铭之间还存在着长短、繁简的不同。因此,墓志铭固然有一定的写作规范,不同于其他文体,但在具体写作中应“相体裁衣”,随时变化,才能无所不当。这源于韩愈能“心识古人源流,随时通其变化”,是其注重“心营意造”,能以无法为法的结果。
章学诚从“文心”角度来解决文法论的思想层面,即有法与无法、活法与定法与实践层面,即相体裁衣、随时变化的矛盾关系,同时又把“集义”而成的“识见”作为“文心”的重要内涵,通过“文心”而建构起了“文法”与“文气”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
四、“清真”与“辞气”
章学诚把“文法”称为“文律”:“仆持文律,不外‘清真’二字。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此二语知之甚易,能之甚难。”[3]81“清真”正是其文法说的关键词,也是其文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概念。[4]429*郭绍虞先生说:“实斋文论之能一以贯之者,即清真二字而已。”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清真”作为章学诚对“文法”的基本要求,指在行文中合乎文体纯粹、文理一贯的要求。“清”是文气纯而不杂,这是对每一种文体自身写作规律和固有写作方式的遵循,如《易》是占卜之书,有自身的写法,不同于《尚书》;而《尚书》隶属于史书,其写法又不同于作为文学的《诗经》,每一种体例都有其独特性,所谓“文各有体”。此外,“清”还包括肯定文体发展的时代性特征。他说:“时代升降,文体亦有不同,用一代之体,不容杂入不类之语,亦求清之道也。”[3]377每一种文体的发展都有其时代性,作家应该对此予以尊重,并保持其纯而不杂的状态,做到这点,就是实现“清”的方法,也是文章“清”的表现。章学诚认为,文体的“清真”表现,受到“辞气”的直接影响:
理附气而辞以达之,辞不洁而气先受其病矣。辞何至于不洁?盖文各有体,《六经》亦莫不然,故《诗》语不可以入《书》,《易》言不可以附《礼》,虽以圣人之言,措非其所,即不洁矣,辞不洁则气不清矣。后世之文,则辞赋绮言,不可以入纪传,而受此弊者乃纷纷未有已也。[3]613
作品内容需要依附于某种特定文体,并以此种文体的叙述方式表达出来。根据“文各有体”的要求,表达方式如果含混不清,也就形成了对此种文体的诟病。比如“圣人之言”,如果“措非其所”,也就不符合“文各有体”的“清真”要求了;又如“辞赋绮言”“入纪传”之中,也就成了纪传之弊了。他评论六朝文学时说:“浮糜之朝,文体破碎,称人不拘名姓,俚言游语,皆入品评,佐以叠韵双声,取适观美,此种文字列于文史之末,听其自为一家之言可也。”[3]81-82所谓“文体破碎”,即不符合其关于文体“清真”的理念,而“称人不拘名姓,俚言游语”,“佐以叠韵双声,取适观美”的表达方式则是“辞不洁”的典型体现。又如在《古文公式》中,他指出苏轼的《表忠观碑》一文,开头用赵抃奏议的“臣抃言”三字,结尾用“制曰可”三字,是从汉代碑文写法而来,因为苏轼太熟悉司马迁《史记》中《秦本纪》的写法,不自觉中运用了这种表达方式,这在章学诚看来,“不免如刘知几之所讥,貌同而心异也。”[2]497他又举汪钝翁《睢州汤烈妇旌门颂序》为例,他说:“汪钝翁撰《睢州汤烈妇旌门颂序》,首录巡按御史奏报,本属常例,无可訾,亦无足矜。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尊时制;秦、汉奏报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2]498“一代之体”是文章“清”的表现,按照“一代之体”的方式写作,则是令文章“清”的方法。章学诚认为,在作家的写作实践中,运用作家生活的时代较为普遍而流行的写法,才是一种文体的“公式”,所谓“公式必尊时制”。如汪钝翁在文中所用“臣粹然言”四字,已经有两处与“近代章奏”的流行写法不符,而结尾一句,“亦非今制”。这是对“清则气不杂”的违背。另外,章学诚也认为,文辞的组织、辞序的安排也会对“文气”造成影响,辞不顺则文气滞,辞顺方能气畅。汪钝翁序文中“明末”一词的顺序不当,是“辞不洁”的体现,所以他从“文气”角度主张加以调整[2]498。章学诚说自己写文章也经常“窜易字句,以就其文气”。[3]641字句与文气的结合,形成文章的“辞气”。
对“辞气”的讲究是一种修辞术,也是行文方法,不仅关系着文体是否“清真”的问题,也关系和影响着文章的风格。在《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中,章学诚说:
汉人云,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深厚存乎所为辞矣。文章称其尔雅,则近正之谓也。近正也者,如俗语云官常说话,不似乡曲土音,难共喻耳。古人修辞,非为观美,谓必如是,始可行远而传久也。故名理以峻洁著之,庄言以凝重敦之,和气以温润含之,厉辞以严肃荐之,隐怀以婉约寓之,深情以往复生之,所谓顺其势而导之也。[3]614
“修辞”不是为了追求看上去的“美”。它有两个作用:一是为了形成典雅的书面语风格,以此区别于“乡曲土音”;二是为了行文中形成前后一贯、内外一致的主导风格,即文章内在的“势”,作家应顺势利导。“势”是文章内在文理的发展趋势,也是文气自然流行的态势,是“真”的体现,也是“气”的显现。从修辞和行文方式角度,章学诚深刻辨析了中国古代文论中“辞达”的理论。他说:
文生于情,情又生文。气动志而志动气也。……文以气行,亦以情至。……今人误解辞达之旨者,以谓文取理明而事白,其他又何求焉?不知文情未至,即其理其事之情亦未至也。……昔人谓文之至者,以为不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夫文生于情,而文又能生情,以谓文人多事乎?不知世人由情而恍然于其事其理,则辞之于事理,必如是而始可称为达尔。[3]54
情感抒发和宣泄的需要,引起作家的创作冲动,形成创作动机,还影响整个创作过程,左右着修辞手段的选择和行文的组织安排,所谓“情又生文”。情与文的这种关系,是“志”与“气”互动的结果。“志”是思想、内容,“气”是情感,是作家行文和修辞的依据。对“辞达”的理解,不能单从表达主旨和叙述内容进行解释,还应该考虑情感表达是否饱满。具有感染力,能够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然后才可能明白文辞中的“其事其理”。章学诚所理解的“辞达”,是“理明”“事白”和“情至”三者的统一,而其对“情”的强调,也是对文气的一种主张。
除了以“情”为“气”,创作中的修辞与行文还需有策略的处理,才能达到文体的“清真”要求。在分析韩愈墓志铭的写作时,章学诚还说:
骈体赋入,成篇自易,如欲清真结撰,摹写传真,自当简削其辞,拟以伐毛洗髓,隐括要节,谋兹短篇,庶知文者,以谓曲折无尽,此竹数尺,而有千寻之势,文短而神味长也。譬之酿酒,少粮则减水而醇浓始发,理亦明也。至于闲情逸蕴,补入铭辞。铭者,诗骚之流,长言咏叹,正为短志传神,所谓繁简各有当也。乃论者以为志短铭长,不合体式。不知论者以何为文体式也。[3]76
如果按照文体“清真”要求组织文章结构,则碑志应简而传神,短而有味,具备咫尺千里之势;墓铭则可以有闲情逸蕴,而以咏叹为长;志与铭不能单以字数多少、篇幅长短作为规范,而应“繁简有当”。以韩愈《刘统军碑志》为例,志文不足二百字,铭文四百七十余字,与一般所谓“志短铭长”的文体规范不符,但章学诚认为,韩愈的处理并不违背志与铭两种文体的要求,而且,“志短铭长”是自汉魏到宋元一直存在的事实,前人从创作实践角度并未规定志一定要短,而铭一定要长。
章学诚对文体要“清真”的主张,是对行文、修辞以及叙事策略的要求,只要行文紧凑,不蔓不枝,文辞与主题相符,叙事前后一致,就是“清真”。他说:“余论文之要,必以清真为主。……清则主于文之气体也,所谓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一例之言,不可有所夹杂是也。”[3]377关于“清真”的理解,郭绍虞先生曾做过详细分析,认为二字分开论,“清”是指文例之严,“真”则是“似乎较偏于文理的见解以说明真的原则”[4]431,但二字合起来讲,则强调“清”与“真”之间的沟通,“清”有理的问题,“真”也有“气”的问题,“清”与“真”本来是不能分的,他说:“清与真原不能分为二事。由文章之体制风格言,宜求其不杂;由文章之内容思想言,宜求其无支。气不杂,易使理无支,理无支,也能使气不杂。”[4]432无论是从文例,还是从文理来说,“清真”思想都是在具体“辞气”的创作实践中得以体现的,同样是其“文气”论的重要内涵。
章学诚论“文气”,既包括关于作家创作态度的文德观念,又包括对文体、文辞和文法的要求,这些都是基于学问对于文章创作重要性的体现。他说:“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2]287学问是写作文章的基础,也是写好文章的关键。这一结论,章学诚是有感而发的,他说:“夫文非学不立,学非文不行,二者相须,若左右手,而自古难兼,则才固有以自限,而有所重者,意亦有所忽也。”[3]85学问与文章关系密切,犹如人的左右手,相须为用,相辅相成,二者结合,能够矫正并挽救学风之弊,发挥文以致用、学以经世的社会价值,这也是章学诚最终能“抱定不随风气为转移”[4]412之学术心态的体现。
[1]钱志熙.论章学诚在文学史学上的贡献[J].文学遗产,2011(1).
[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吕晓英)
Connotations and Brand-new Ideas of Zhang Xuecheng’s “Wen Qi” Theory
Ma Xingxiang Xu Li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The concept of “Wen Qi” (literary spir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Zhang Xuecheng’s literary thoughts. He explains its connotations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writers and their writings from diversified perspectives. He regards “Wen Qi” as a state or intention of mind required of writers so that they can keep a peaceful mood and a right feeling. Cultivating “qi” is a process of accumulation of the arguments and insights which are the bases of writing. He attempts to dis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rammar and the writing practice by means of literary mind, which is also a key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writers’ personality and style of writing. The idea of “Qingzhen” concerning the writing grammar as well as the rhetoric theories is included in the concept of “Wen Qi”. Zhang’s “Wen Qi” theory is a self-contained system with innovations grounded upon similar traditional ideas, embodying his academic philosophy that writing is of practical value and learning is the way to improve ability and obtain knowledge.
Zhang Xuecheng; “Wen Qi”; cultivation of “qi”;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 grammar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7.01.011
I209
A
1008-293X(2017)01-0074-09
2016-10-10 基金项目:2015年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宋代‘春秋’学与正统文学观之嬗变研究”,项目编号:HB15WX024。
马兴祥(1974- ),男,山东泰安人,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意大利威尼斯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