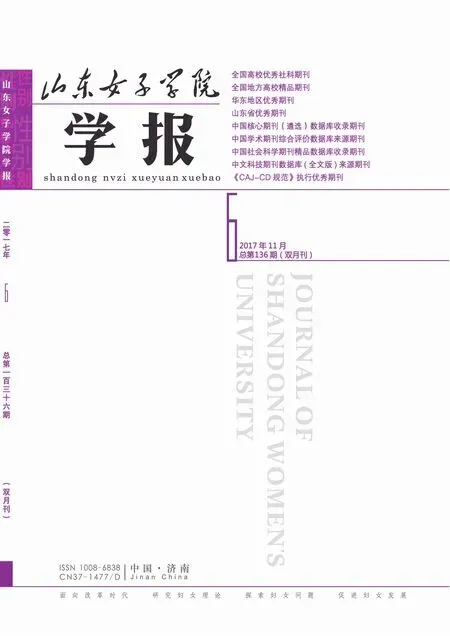论电影《萧红》的女性表达
张珊珊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性别视角下的萧红专题研究·
论电影《萧红》的女性表达
张珊珊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女性在文学艺术与影像声色中的被呈现方式,蕴含了丰富深刻的性别认同与文化意义。由霍建起执导的电影《萧红》,以温暖炽烈、情怀丰沛的女性表达,再现了女作家萧红追求独立的传奇人生。影片的女性表达从女性自我实现的追守、女性生存困境的呈现、女性情感状态的观照三个方面加以体现。
电影;《萧红》;女性表达
电影作为一种叙述语言和大众文化,具有鲜明的再现特征,“‘再现’表明电影影像和任何语言作品一样,是一种建构,是对一个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真实’的世界的‘再次呈现’,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呈现’”[1]。女性在文学艺术与影像声色中的被呈现方式,蕴含了丰富深刻的性别认同与文化意义。长久以来,“电影的凝视是男性的,电影以男性欲念建立叙事,赋予男性掌控的权力,压抑女性,以物化的方式呈现女性”[2](P8),“女性形象只是充当这构成奇观、诱发欲望观看的视觉动机”[3]。20世纪70年代,随着第一代女性主义纪录片《长成女性》《简妮的简妮》《三面夏娃》和《女人的电影》的问世,立足于性别立场表达批判性思考的女性主义电影,在时光的流变中逐步改写着一直被电影工业所压制的女性形象。男人把自己归之于自我的范畴,而把女人建构成他者的惯常性遭遇挑战,女性被拯救、被凝视、被欲望、被塑造的客体身份不再理所当然,女性主体的独立性日益明朗。这些亮点鲜明的女性电影平静地颠覆着电影再现女性时的男权主导意识,女性话语与再现的权力开始在电影场域作用于女性存在的建构中。
“电影产生于意识形态与文化欲望之中,而且会对两者进行反哺。”[4]由霍建起执导,2013年上映的电影《萧红》以影像的方式叙述了民国著名女作家萧红一生追求自由独立,半世历经流离多舛的传奇人生。萧红先因父逼婚离家出走,后因战火硝烟远离故乡。她一路辗转奔波于哈尔滨、青岛、上海、临汾、西安、武汉、重庆,31岁因病在香港玉殒香消,留给世人《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近百万字风格独特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作品。在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之间,抛却影片商业化元素中可待推敲的某些虚构情节,本文仅就影片基调而言,电影《萧红》的女性表达温暖炽烈,情怀丰沛。电影将那个文艺的、倔强的、寂寞的、抗争的萧红绽放在光影的回眸中,她的精神、她的往事、她的气质,她独特的生命历程都带有鲜明的性别标记,电影的视线结构不再是男性角色和男性观众凝视女性角色的结构,女性也不再被作为欲望客体建构于影片中。正如本片导演霍建起所说:“我不愿意拍得过于写实,像雕塑一样,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视角。”“电影的功能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萧红。了解萧红后,有欲望、冲动去看她的作品。”“通过《萧红》,我想让大家看到那个传统、保守、男权主义的时代竟然有这样一个思想解放的女子。”[5]
一、女性自我实现的追守
萧红是一位真正走上社会,追赶甚至超越了她所生存的时代潮流的新女性。正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白薇、谢冰莹所走过的创作道路一样,她们共同拥有许多走出“铁屋子”的经历、话题,对于身为女性所遭遇的不公平社会待遇,也都有切肤之痛。与其他吃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乳汁长大的青年男女一样,这些女作家都有过逃婚、摆脱封建家庭独自到社会上闯荡的经历。她们始终沿着独立自由的个性解放道路,不断前行。作为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召而走出家庭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这种开窗的意义对她们而言无疑更为现实。获得社会工作、经济独立等一系列与现代女性相配套的待遇,仍然是现代女性热切希望得到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些进步男性所期待的新文化运动的旨归。然而在“重男轻女”积习深厚的父权制社会,萧红所面临的还是鲁迅先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女性从父权制家庭出走,又被逼回家的境遇,萧红都曾经历过。
影片中抗婚到北平读书的萧红最终接受了找寻她而来的包办未婚夫汪恩甲的帮助,因为对方答应她可以继续读书。那一年,萧红二十岁。在一个动荡年代,汪恩甲忤逆家人寻她而来,倾尽所能解她经济困窘,支持她最爱的上学读书,尽管对方未必出于懂得或欣赏萧红才情的真心,但客观上这些付出足够感动与打动一颗初入社会闯荡的单纯落难少女的心。他们的情感纠葛,有着命运的无奈,也有一些感动的甘愿,而非简单的资源互换。后来汪家人断了汪恩甲的经济来源,两人被迫回到哈尔滨,在东兴顺旅馆住了大半年。怀有身孕的萧红在经济极端窘迫的境遇中,依然坚持读书写作,不曾放弃精神独立的追求,不肯回家妥协。她的作品更是伴随着她每一处漂泊的足迹,落地开花。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恶劣,她都未改初心,直至在文学雄心未竟的“身先死,不甘,不甘”的遗憾中,结束了寻找自我与归依的半世飘零。影片中萧红说:“《王阿嫂的死》是我第一次发表的小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的写作,无论是痛苦还是忧伤,贫困还是战争,甚至死亡。”
对于萧红来说,她一直有着非常清晰坚定的精神追求与理想信仰,那就是写作。无论遭遇怎样的人生变故,情感沉浮,身体创伤,饥饿贫穷,她写作的精神花火一直激情燃烧,绚美绽放。这份坚毅的守持彰显了女作家萧红独立丰盈的精神人格。她的作品中那些冷静清醒的文字,冲出藩篱的执着渴念,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直面生死的无畏勇气,都标识了其写作的鲜明个人风格。她拒绝套路,反对模式,不近腔调,其所经历过的人生苦乐悲欢都化为文字融入作品,她的文字自由无伪,章法随性而出,似乎没有规矩,而深处则有爱欲的流盼。她的文字极为感性,生活片断的捕捉灵光闪烁,有情绪的涌浪。那些流离失所、痛彻心扉、食不果腹、孤立无援的苦楚,都沁润在文字中。萧红这些亲身经历的刻骨铭心的生存体验,成为其作品里最生动的篇章。与其说那是创作出来的文章,不如说那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记忆,萧红“这个被传奇化的人物,是民国文坛的异类,没有大家闺秀之色,也非大学里的文雅的女子。她的身世颇为普通,又经历了无数次的坎坷。但其汩汩流淌的情感之潮,在灰色的寂静里泛出光亮。完全是天籁般的声音,纯粹而悠扬,带着野草的香气和松林的野味,飘散在词语之间……这个沾着泥土气的女子,穿过污浊的沟壑,从没有笑的原野走过,从欧罗巴的咖啡馆前走过,以自然的谈吐,述说着离奇的故事”[6]。
影片以倒叙和插叙的镜语讲述了萧红的生命段落,并通过人物的服饰加以表现。有萧红经济拮据时的单一落魄,有境遇好转时的得体光鲜。值得注意的是,萧红衣着的得体光鲜开始是因为富足家庭的供养,之后是包办未婚夫的接济,最后是作品得到认可后的稿费版权收入。萧红如逆行精灵般一路野蛮生长,非常自觉地作为女人来写作,并让写作成为谋生的资本,逐渐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成为独立的主体。萧红的一生都在追求、践行着女性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的自我解放与自我实现,尽管这是一段当代女性依然在路上的蜿蜒征程。
二、女性生存困境的呈现
“由于原始和文明的世界都是男性的世界,文化所形成的关于女性的观念也同样是男性设计出来的。我们所知的妇女的形象是由男性创造出来,并为适应他们的需要而改变的……男性已经把他自己确立为人类的标准、主体和所指,相对于男性,女性是‘他者’或异类。”[2](P30)
新文化的现代教育,为曾经被禁锢了几千年的中国女性打开了外面世界的窗口,使她们看到了前面似乎有条新生路,可以尝试着走出家庭强加给她的旧式婚姻。新文化运动透露出的信息是,女性可以走出封建家庭,进而选择自己喜欢的丈夫和独立的职业。女性要独立于社会的呼声,对萧红这批在哈尔滨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来说,既是时尚风潮,也是需要突破的自身困境。萧红是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悬念中,冲破黑暗见到光明的那一位。但在寻找独立的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她也直面了社会现实对女性的不公平,也品尝到经济不独立的女性陷入社会底层的黑暗生活。
影片中,经济窘迫、基本生活空无保障的萧红被迫接受了汪恩甲的援助,辗转回到哈尔滨后,由于没钱交房租,萧红被作为人质关在旅馆的阁楼,若不还钱就被卖往“妓院”。彼时的萧红怀着身孕,饥寒交迫、穷困潦倒,面对着未婚先孕,未婚夫不知所踪的残酷现实,这种境遇对于动荡年代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女而言委实绝望而恐怖。影片中,萧红将刚出世的孩子送人抚养,甚至没敢多看一眼。这一方面是经济条件无力抚养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也有着萧红内心的抗拒,她的理想信念还未实现,只能前进,无法后退。一个正在读书的女孩突然做了母亲,两个人的故事,却只能由女性承担后果,并饱受孕育之苦。送走孩子并非绝情,谁说这不是在抵制一场悲剧宿命的轮回。萧红与自己母亲的关系并不亲密,而她的第一次怀孕又落难于生死一线,无疑让初为人母的萧红身心饱受煎熬,体验到更多的伤痛、恐惧与无助,而很难有生命诞生的欣喜。这份生命体验在她的作品《弃儿》中可见一斑:“一个肚子凸得像馒头般的、简直像被盆子扣到肚皮上的女人,眼如黯淡的黑炭,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家,没有父母,没有朋友,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也不管走到何处她都‘带着’她的大肚子。”[7]“落难的母亲和仍未出世的孩子一样双双孤立无助……弃儿不只是腹中的孩子,也是母亲的隐喻。”[8]在这种自身难保的境遇下,选择给孩子找一个有生活保障的家,而非勉为其难地做一个无法保护孩子的母亲,或许这才是真正对孩子负责任的选择。并且这个选择与遇见谁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最恰合当时实际的一位母亲理性的决定。影片中萧红拒绝了收养人留给她的钱,嘱咐把钱留给孩子用,说明萧红所做的这一切并非为了自己。
对于女性来说,职业往往是在家庭中获得与男性平等地位的唯一途径。直到现在,女性的社会化依然面临与男性的残酷竞争,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孕育之苦与生产之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的生育风险也是女性不可回避的天然存在。与男性共同参与社会竞争面临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促使大部分知识女性退回到传统男权中心体制规约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价值框架中,选择女性生存的轻松模式,结婚“相夫教子”,甚至去充当二房、姨太太的依附生活,延续了传统中国男人“娶妻纳妾”的婚姻型制。我们无意于评判任何一种选择,只要选择本身是自由的,过程是甘愿的,目的是明确的。而萧红的选择,在她所处的时代显然是一个非常前卫、冒险、艰难的模式。
三、女性情感状态的观照
影片通过平静而张扬的揭示人物情感状态的方式来贴近人物,坎坷的情感历程在萧红的人生中亦是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当社会对妇女极少过问时,每一个妇女都只有去听自己的声音,以便在这个变迁的世界中找到自己。她必须从自己的需求和能力出发,为自己规划出一个新的生活蓝图,把爱情、孩子和家庭这些以往限定女性的因素与面向未来、目标远大的工作协调起来。”[9](P352)萧红首先是确立自己不依附任何人、独立生存的社会地位。于是,在大多数知识女性选择了婚姻模式经营小家庭的时候,萧红作为知识分子女性,不可避免地为冲出铁屋子,走出父权制家庭,在社会上闯荡受尽苦难,她自身也为此遭遇种种无可名状的痛苦困境,来为接受新式教育却无法独立养活自己的女性寻找答案,进而探寻解决办法。与萧军在一起后,萧红度过了一段安稳的创作时光。这份情感历程,有过幸福恩爱、琴瑟和鸣,也有过脆弱无助、伤心彷徨,而每一次的情感变化,萧红都是以一种独立女性的姿态来勇敢面对。萧红一直把自己与对方当作平等的个体去经营自己的感情,所以她是拒绝被定义、被塑造的,她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去应对情感中出现的问题,但她不会无视或逃避矛盾,尽管她是一位情感挚烈、细腻敏感的女性。在一个“妇女们没有自我个性是事实,正是这一事实才使得性、爱情、婚姻以及孩子好像是她们生活中唯一的,根本的事实”[9](P381)的年代,萧红一步步地实践着自我超越,她的惊世骇俗曾被世人误读也就不足为怪了。
萧红与萧军的感情是电影中一段浓墨重彩的华章。她在人生最黑暗的绝境与萧军初遇,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萧军为萧红的才华所吸引,他说:“你是我见过女人中最有才华的,你不会死的,因为你遇到了我。”两个志趣相投、彼此欣赏的青年男女就这样相爱了,他们如一对相见恨晚的灵魂伴侣,度过了一段幸福流溢的时光。影片对这段情感的表达是非常浪漫化、梦幻化的,他们一度穷得睡觉没有铺盖,于是漫天飞雪充当了爱情的见证;他们穷得买不起食物,但面包蘸盐巴他们也能品尝出蜜月的甘甜,他们贫穷而快乐,清苦而诗意。当爱火渐熄,浓情蜜意的感情遭遇危机时,心痛的萧红并没有无序失控,他们之间有真实冷静的对话,也有萧红远去日本留给彼此空间处理情感的问题。当所有的努力依然回不到从前时,萧红选择了忍痛离开。她对在这次感情变故中受到伤害的女性,亦是同情的心疼的,没有迁怒与怨怼。她以自尊、成熟、冷静、理性的姿态,考量了自己的感情,并选择依然相信爱情。倾慕萧红已久的端木蕻良给了她人生中第一场婚礼,电影中萧红说:“他给我想要的,疼爱、理解、注视、专一、轻声说话,我要的不多!”男人给了女人他能给的全部,只是在命运的无常面前,人性是复杂的,全部是有限的。电影采用倒叙开篇,战火中破碎的香港,床榻上重病的萧红,营造了全片悲情苍凉的情感氛围。影片借骆宾基之口评价了感情中的萧红:“她是一种很强大的真实,她裸露着,不是身体,而是灵魂。她用她的全力去爱,她的爱,让她爱的男人,变得强大起来,骄傲起来,随心所欲起来。然后,她第一个被伤害。她的强大,让男人下手很重,其实,她是很疼的。所以,她不停地写作。寂寞和抚慰都来自写作。”与其他大家闺秀出身的知识女性善于在社交朋友圈左右逢源地周旋不同,萧红天生的赤子之心和悲悯情怀,使其在闯荡江湖的过程中对随处可见的黑暗浑浊无法释怀,她的作品中有许多揭示社会体制的不公平和人性幽暗的内容,时至今日依然有警示的意义。
一部电影或许说不尽萧红激荡坎坷却又璀璨光芒的一生,但它却通过聚焦这样一位优秀女作家,以光影的形式再现银幕,表达对她的尊重与欣赏。影片由点到面,推而演之,进而让我们思考到传统中国文化对女性的束缚,由女性之间的互为牵涉和截然相反的价值冲突,进而指涉出中国知识女性在社会上获得经济独立与精神独立的步履维艰。此外,电影承续了霍建起导演一贯的诗画电影风格,唯美浪漫,开阔浩荡。清雅怀旧的色调,悠远舒缓的配乐,优美精良的构图,赋予影片女性表达以形式的美感。
[1] [英]吉尔·布兰斯顿.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15.
[2] [英]休·索海姆.激情的疏离——女性主义电影导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3.
[4] [美]罗伯特·考尔克.电影、形式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39.
[5] 张成.“我着重表现自己心目中的萧红”——著名导演霍建起谈电影《萧红》[N].中国艺术报,2013-03-18.
[6] 孙郁.民国文学十五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258.
[7] 周鹏飞.中国现代小说精品·萧红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97.
[8] 林幸谦.萧红早期小说中的女体书写和隐喻[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4):28.
[9] [美]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FemaleArticulationintheFilmXiaoHong
ZHANG Shanshan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arbin 150018,China)
The ways female was expressed in literature,films and television works contain profound sex identifica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XiaoHongdirected by Huo Jianqi represents female writer Xiao Hong’s legendary life of seeking independence with its warm and emotional female articulations.The film embodies female articulation in three aspects: seeking women’s self-fulfillment,exposing women’s survival dilemma and caring of women’s emotional state.
film;XiaoHong; female articulation
2017-09-10
张珊珊(1982—),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化研究。
J904
A
1008-6838(2017)06-0055-05
(责任编辑:赵莉萍)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