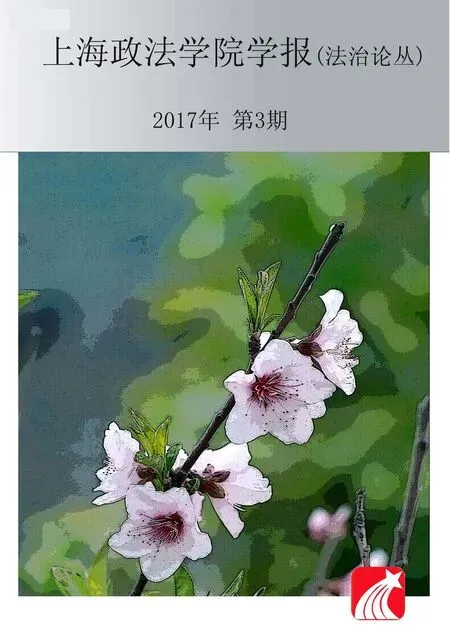欧盟法执行程序双重保护之探讨
朱心怡
欧盟法执行程序双重保护之探讨
朱心怡
为了实现法律目的,欧盟在条约或案例中创设了两种自成一体又互补互助的执行程序——公力执行和私力执行。公力执行程序是以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的公力强制性为保障,自上而下地推动欧盟法在成员国的转化和适用,但这种方式在近年来的实践中产生了诸多弊端。而私力执行程序赋予了成员国国内法院一定的权力,激发公民的监督热情,从底层推动欧盟法落实,弥补了公力程序的不足,显示了自身的优势和发展潜力。这种发展的模式对于国际组织和国内分权设计的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欧盟法;执行程序;双重保护;公力执行;私力执行
作者:朱心怡,华东政法大学。
一、欧盟法执行程序概况
欧盟法是创建欧洲联盟的基础,在欧洲联盟的地位至关重要。欧盟各成员国是否在国内层面落实欧盟法,体现了欧盟作为国际组织的实权大小,也反应了欧洲一体化的程度。而法律的尊严需要通过执行来保障,得不到有效执行的法律,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欧盟法的执行,目前有以下两种途径:
第一种是遵循申请“公力”执行程序。当个人在认为国内权威机构无法保障其权利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去欧盟委员会申诉,之后由欧盟委员会介入调查。个人申诉是委员会获知成员国存在违法行为的主要途径。欧盟委员会作为欧盟法的捍卫者,也会主动监督调查各成员国适用欧盟法律的情况。“公力”执行程序的条约基础来源于经《里斯本条约》修订后的《欧洲联盟运行条约》。该条约第258条规定:“委员会如认为某成员国未能履行两部条约规定的某项义务,应在给予有关国家提交意见(observations)的机会后提出一项附有理由的意见(a reasoned opinion) 。如该成员国在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未遵守其意见,委员会可将该事项提交欧洲联盟法院。”①程卫东、李靖堃:《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第二种是申请“私力”执行程序。这里的“私力”是相对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这个“公力”机构而言,是指各成员国的国内法院有权在审理欧盟法相关案件中直接应用欧盟法。虽然这种程序没有条约基础,但是欧洲法院在案例中所建立的先例和各种原则为该程序提供了法律基础,其中包括直接效力这个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国内法院在解释和适用欧盟法法条上所产生的任何问题或疑惑,都可以应用初步裁决程序向欧洲法院请示,此程序经过多年来的完善也已经相当成熟,具备可行性。
在Van Gend en Loos案中,上述两种申请强制执行途径被称为双重保护(dual vigilance),①See Case 26/62, NV Algemene Transport- en Expeditie Onderneming van Gend & Loos v Netherlands Inland Revenue Administration [1963], ECR 1.这两种程序形成了欧盟法院执行程序的双重武器。这两种程序的建立,目的是为了保证欧盟法得到更有效地实施。即不依赖于欧盟委员会一个机构的监督力量,通过激活各成员国国内法院的能动性,全方位地保障欧盟法在欧洲的实施。
二、“公力”执行程序的实践与发展
(一)“公力”执行程序的实践
“公力”执行程序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行政阶段,第二步是司法阶段。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58条规定,在行政阶段,欧盟委员会应当对违法的成员国进行视察,如果存在不履行义务的违法行为,应当通知成员国并给予机会去改正。在这一阶段中,双方行使外交手段进行协商,这种协商往往是执行程序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只有当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欧盟委员会才会采取发布正式通知(formal letter)和附有理由的意见(reasoned opinion)等措施,进入了后半部分的司法阶段。因此,这种行政阶段也被称为“秘密的外交程序”。②Melanie Smith, “Enforcement, monitoring, verification, outsourcing: the decline and decline of the infringement process”, European Law Review, p.2(2008).
在两个阶段之间没有规定的时间限制,这往往由欧盟委员会设定一个合理期限,且这个期限必须能够给违约的成员国足够时间去改正行为、履行义务。如果欧洲法院认为期限设置不合理,那么就有权驳回欧盟委员会的控告。在Commission v Belgium③Case 533/11 European Commission v Kingdom of Belgium[2013], ECR 659的案件中,欧洲法院认为欧盟委员会制定的15天的期限太短,于是驳回了欧盟委员会的控告。
进入司法程序后,欧盟委员会将发出要求成员国政府2个月内做出回应的正式通知,以及附有理由的意见,该成员国政府应该在2个月内遵守规定。如果欧盟委员会不满意成员国的回应,即有权向欧洲法院提请诉讼程序。这里的“有权”是赋予了委员会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委员会可以放弃提请诉讼程序。④F. Snyder,“The Effectiveness of European Community Law: Institutions, Processes, Tools and Techniques”,56 Modem Law Review, p. 23(1993).因此,公力救济的弊端也暴露出来,正因为委员会享有如此之大的自由裁量权,所以给了政治考量可涉足的空隙。在司法阶段,很难排除欧盟委员会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在裁量过程中添加强烈政治色彩的可能性。在这个阶段,欧盟委员会可以向法院提出处以成员国罚款的建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60条给执行程序以财政武器,该条文第2款规定:“如果委员会认为成员国未采取必要措施执行本条第1款提及的判决,它可在给予其提交意见地机会后将案件提交欧洲联盟法院。委员会应具体说明其认为在相应条件下有关成员国应付罚款的总额或罚金的数额。如法院发现该成员国未遵守其裁决,可对其课以一次性罚款(lump sum)或罚金(penalty)的判决。”①程卫东、李靖堃:《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页。
公力执行程序使用了财政制裁的方式来督促各成员国遵循欧洲法院的裁决、履行自己的义务。逾期罚款是为了给成员国一定的期限压力,一次性总罚款则带有一定的惩罚性质。惩罚金额以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程度和拖延期限长度为判决依据,欧洲法院作为判决主体会参考欧盟委员会的意见,但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去决定最终的赔偿金额。
2009年的《里斯本条约》第260条相较于《马约》有两个变化:第一是在第2款中规定,无需提供附理由意见,委员会就可在起诉阶段直接起诉成员国;第二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例如成员国没有履行自己的通知义务,委员会可以在司法前阶段就采取罚款手段,而无需经过繁杂的行政手段。可以看出,这次改变简化了程序步骤,提高了欧盟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其最大的优点在于缩短诉讼时间,减轻欧盟委员会的工作负荷,避免成员国利用欧盟委员会需要冗长时间出具有理由意见,借机拖延。②陈亚韵:《论欧盟财政制裁措施——以欧盟法执行程序为视角》,《法学评论》2013第2期。
(二)“公力”执行程序存在的问题
1.欧盟委员会接受案件数量庞大
尽管欧盟委员会在简化程序,但过程还是相当漫长。每年欧盟委员会都会收到大量的对成员国潜在违约的指控,据官方年报显示,2011年有3115起指控,2012年有3141起,到2013年攀升至3505起,2014年持续快速上升至3715起,直到2015年才有明显下降,为3450起指控,但总体呈上升趋势。2015年底仍在审理中的案件已达1368起,比起2011年的1775起审理中的案件,近几年有明显改善但是仍然有微弱上升趋势。③European Commission,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Monit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EU Law 2015 Annual Report COM (2016).并且欧盟委员会案件处理周期也非常长,在提交给欧洲法院之前平均需要2年时间进行协商和审查。
2.公力执行程序各阶段缺乏透明度以及指控者的参与度
近几年来委员会的精英态度饱受批评。为了防止媒体曝光和成员国的抗辩,④T. Hartley, “The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ommunity Law”, 5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20 (2003).委员会在最初的行政协商阶段采取不对外公开的政策,进入司法程序后的正式信函和附有理由的意见也采取对第三方保密的态度。委员会是出于对执行程序顺利进行的利益考虑,因此提出“除非涉及到公共利益,或者公开后的利益远远超过保密的利益,委员会和法院都认定程序过程中的信息不应当公开。”⑤Case T-309/97,The Bavarian Lager Co. Ltd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7].这导致了成员国对于欧盟执行程序公正性的不信任,以及对于信息不平等的抗议。另外,即便是参与人和指控人也没有权利去获取这些信息,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导致委员会对于基本事实的正确度也没有十足把握,对于指控人和参与人而言也是一件并不十分公平的安排,在案件处理动辄数年的漫长等待中更易滋生不满。
3.罚款征收机制的缺位,计算程序不一致
财政制裁机制是欧盟执行程序里的一大亮点,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制度设计。虽然法院有判处罚款的权利,但是多年来,无论是《马约》还是《里斯本条约》都没有赋予委员会强征罚款的权利,因此判处经济制裁的主要障碍是如何征收罚款。法院被批评缺乏判决中罚款数额的判决依据和解释,在制定数额的标准中也缺乏一定的透明度和一致性。如果在将来即便法院判处了罚款迫使成员国遵守,而成员国拒绝或延迟支付罚款,强制机制将成为一个问题,可能最后还是会通过政治方式去解决。至今,欧盟也无法解决执行程序“后继无力”的问题。
4.组织的高度政治性
欧盟委员会本质上是政治性组织,难以避免在它的自由裁量权内存在着偏见和倾向。据前文分析,委员会囿于自己的资源有限,不可能对每个投诉的案件都采用公力执行的程序,它有自己的着重点,它可能会放弃某些案件而集中优先审理部分案件。作为政治性组织,它也容易被利益国施压,从而损害到它的公正性和平等性。
(三)欧盟的应对措施与“公力”执行程序的发展
1.“欧盟试点”项目(“EU pilot” scheme)
委员会一贯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成员国遵守欧盟法,希望通过不起诉的方式就能解决不履行义务的问题。“欧盟试点”是委员会创设的一项制度,如有成员国违反条约,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通过双方构建起结构化对话的方式,有效快速地解决该成员国违反欧盟条约的问题。它依靠互联网数据库和交流工具,构建起成员国和委员会的协商对话,能够最大限度地加快问题解决的速度,有利于公众和商业的发展。①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Monit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Union Law 2014 Annual Report COM (2015) 329 final 9.7.15, p 10.
在欧盟试点的程序中,成员国政府在10周之内面对质疑要给予回复,委员会有10周的时间去检验该成员国回应成果,如果委员会不满意结果,可以启动违法诉讼程序。这个项目目前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吸引了28个成员国加入了这个项目。近5年通过该程序解决的指控案件比例维持在70%左右,2014年和2015年都保持在75%,可见“欧盟试点”在处理案件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2.欧盟法国内适用程序的开端
欧盟法的的第二种执行程序是成员国通过行政或司法手段来保证欧盟法在国内的实施。从Van Gend en Loos的案子开始,欧洲法院就给予了国内法院监督欧盟法在成员国国内实施的角色。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欧洲法律一体化能够依靠国内法院在实践中保障欧盟法在该国得以顺利实施。也有利于个人和非政府组织机构作为非常重要的监督者,能够更方便地发挥他们的监督作用,保障欧盟法的实施和执行。更重要的是,国内法院更能将陌生和笼统的欧盟法条翻译和解释成符合本国国情的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和指导,有利于接下来的案件将其作为参考。②Ryall, Effective Judicial Prote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Directive in Ireland,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9.从实用性和有效性来看,“私力执行”程序对于欧盟法在成员国内部实行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果各国国内法院是凝聚了“草根阶级”的力量,如果它们能够积极地行使权利,对于推动欧盟法的实行无疑有巨大帮助。
三、与“私力”执行程序密切相关的三个原则
欧盟法的私立执行程序如上文所述没有条约基础,是通过多个案例确立起来的一系列原则和程序。其中与私力执行最为密切相关的三个原则分别为直接效力原则、间接效力原则和国家赔偿责任原则。
(一)直接效力原则
欧洲法院在Van Gend en Loos案件中确立了欧共体法的直接效力原则。欧盟法律对其成员国的直接效力,是指一定的欧盟法律所具有的、可为任何成员国的自然人或法人创设权利与义务的效力,即该法律的有效条款不需要经过成员国的再立法程序或进一步制定补充措施就能直接为成员国或其公民所援引,其国内法院也必须直接适用。由于具有这样的直接适用性,欧盟法律自动成为成员国国内法的组成部分,成员国不必再采取任何措施。①朱淑娣:《欧盟经济行政法通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95页。
我的大女儿到底飞走了,去陪她奶奶去了。这个讨债的冤家,她才七个月,连大号都冇取啊。我哽咽着说,大梁,你女儿也……她陪她奶奶走了……大梁的头猛地一抬,口唇剧烈地抖动起来,突然像决了堤,喷出撕心裂肺的哭声。
具有直接效力的欧盟法律规范必须具有以下条件:第一,该规范必须是无条件的,在实行过程中,任何欧盟机构或者成员国采取措施都不能附有条件;第二,条文必须充分精确,明确规定义务的内容;第三,条文规范必须定义了某项权利,足以使个人对抗政府。②Case C-236/92,Comitato di Coordinamento per la Difesa della Cava and others v Regione Lombardia and others. [1994], ECR 60.直接效力原则中的政府被扩展性解释,在Costanzo③Case 103/88, Fratelli Costanzo v Comune di Milano, [1989] ECR 256.案件中,欧洲法院判定所有的行政机构都包含在“政府”的概念里,甚至是遵循政府的规定。在政府控制下的、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享有某些特权的私人机构也会被定义为政府。直接效力只有纵向,没有横向的效力。个人可以去控告政府和下属机构,但是个人无法去控告个人不履行欧盟法义务的行为。
(二)间接效力原则
间接效力原则又被称为一致解释原则(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其重要性往往被直接效力原则为所掩盖,但是它对于欧盟法在成员国国内适用有重要意义。由于直接效力原则规定了要排除横向直接效力,即不适用于个体之间的争议,如何保障个人与个人的欧盟法上的权利变成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欧盟法院在这个领域里建立一系列的原则去补充,一致解释原则就是其一。欧洲法院在Von Conlson④Case 14/83, Von Colson and Kamann v. Land Nordrhein-Westfalen, [1984] ECR 1891.一案中阐明了一致解释原则的要求,主张成员国的所有职权机构必须根据相关指令的文字和目的解释它们的国内法。但同时,成员国也有相应的自由裁量权依欧盟法去解释及适用国内法,使国内法与欧盟法保持一致。
间接效力原则的适用范围可以通过典型先例来明确。在著名案例Marleasing①Case C-106/89, Marleasing SA v La Comercial Internacional de Alimentacion SA, [1990], ECR 395.中,法院判决中写道:“无论争议中的国内法条款是在指令之前还是之后采纳的,负责解释的国内法院应当尽可能地根据指令的文字和目的适用国内法和其案例法”,②杨永红:《调和中的强制——论欧共体法中的一致解释原则,《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说明间接效力原则不受法律条款发布时间的限制。其次,案例Pfeiffer清晰表明该原则不仅针对国内法律,还针对成员国整个国内司法系统。最后,不同于直接效力的是,间接效力原则并不“强硬”。在Marleasing的判决中要求,国内法院在解释法律时也要考虑到国内法的承受范围,应该尽可能地去靠近欧盟法要求,因此可以看出,间接效力原则并不是一项强制性的原则。
在 Marleasing案及之后类似案件中,欧洲法院都主张依据欧盟法解释国内法的义务,即排除成员国法院解释国内法的结果与适用欧盟法相悖的情形,该原则在欧洲法院的发展之下大大地扩展了普遍国际法上一致解释所带来的法律效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获得了与直接效力原则相同的法律后果。③See joined Case C-6/90 and C-9/90 Francovich and Bonifaci v Italy, ECR 372.同时,欧盟法中的直接效力原则和间接效力原则相辅相成,共同加强了对成员国个人权利的保护,完善了欧盟法的秩序。
(三)国家赔偿责任
国家责任原则是欧洲法院对欧盟法律的重大贡献。它也没有法条基础,是通过欧盟法院的先例构建起来的一项原则。国家责任原则是在Francovich④See joined Case C-6/90 and C-9/90 Francovich and Bonifaci v Italy, EU: C: 1995:372.案件中首次建立的,是指欧洲法院判定个人有权因成员国违反欧盟法所产生的损失可以向政府索要赔偿。
1991年欧洲法院在Francovich中确立了适用国家赔偿责任的三个条件。首先,条例必须有赋予公民某项权利;其次,该权利可以通过条文的内容识别出来;最后,个人的损失应当要与政府的违法行为有因果关系。一旦满足了这3个条件,国家赔偿责任原则可以独立于直接效力和间接效力原则而直接被使用,是一种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
之后,通过Brasserie du Pêcheur⑤See joined cases C-46/93 and C-48/93, Brasserie du Pêcheur SA v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nd The Queen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nsport, ex parte: Factortame Ltd and others [1996], ECLI:EU:C:1996:79.案判决确立了成员国立法机关违反欧盟基本法律应承担欧盟法上国家赔偿责任的法律。在前者的判决中,欧盟法院进一步发展了适用该原则的条件,最大的区别是将原先的第2条改为“成员国政府的违法行为应当非常严重”。如果成员国以前已经判决有关措施违反了共同体法律,那么这类违反行为就显然是足够严重的,尽管这并非是证明足够严重的必要条件。欧洲法院鼓励成员国自行裁断共同体法律的救济。⑥张千帆:《论欧洲联盟的行政责任及其司法救济》,《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003年更是通过Kobler⑦See Case C-224/01, Gerhard Kibler v Republic sterreich [2003], European Court Reports 2003 I-10239.案进一步明确成员国应就其违反欧盟法的司法不法或者司法行为瑕疵承担欧盟法上赔偿责任,在某种意义上将成员国的全部公权力行为——立法、行政与司法——纳入欧盟法的调整范围内。⑧柳建龙:《略论成员国欧盟法上之国家赔偿责任》,《首都法学论坛(第7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
国家责任原则作为对直接原则和间接原则的补充,进一步完善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使得遭受损失的公民无需经过欧盟委员会案件处理的漫长等待,直接在国内层面获得赔偿。同时也填补了两大原则所涵盖领域的缝隙。从这个角度上说,国家责任原则是欧盟公民的福音,对于制度的完善也有重大意义。当然此原则也导致了一定的混乱。比如,常常会发生下级法院去审理上级法院判决的情况,这是一种法院级别的倒置,对于成员国内部的法院制度是一种挑战。
欧洲法院用目的推理发展了这三个宪法原则。欧洲法院首先定义了欧盟法的目的,以此来解释条约使得欧盟法具有直接效力,由此增强诉讼当事方令成员国法院执行欧盟法的能力,从而促进欧盟共同市场的建立使欧盟的中心目标得以实现。采用以目的入手的推理不仅将欧洲法院从条约为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允许欧洲法院将领悟到的条约的深层意思作为一个动态的法理对欧盟法加以补充和调整来满足欧洲法院观察到的欧盟发展的需要。①陆伟明、李蕊佚:《欧盟法在成员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直接效力和至高效力两大宪法性原则为中心》,《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四.欧盟法强制执行对他国的借鉴意义
欧盟作为一种当下一体化程度最高的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多年来其独特的制度创新和发展,对于其他国际组织或机构都有借鉴意义。欧盟是一个由各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的产物,是主权理论在20世纪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欧盟在追求自身合法性和“权利扩张”的博弈中持续了50多年,而欧盟法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所拥有的自身的独特性和历史性对于国际法而言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
执行机制的法律设计作为欧盟法的一部分,体现出欧盟法的典型特点,也暴露出欧盟机构的内在矛盾。在判决问题上,欧盟法院在已有的法律规范内享有司法独立,但是执行问题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和法律双重因素的影响。
罚款机制作为欧洲法院执行程序的亮点,也是国际法中最先进的强制执行判决的方法。一次性罚款和罚金的双重设定也具有创新性,更好地督促了违法的成员国及时地执行法院裁决,有效防止了成员国政府的拖延。在罚款金额上,欧洲法院采取了一个较为“严厉”的态度,也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该机制有向国际法蔓延的趋势,例如《欧洲人权组织公约》也吸收了向不执行判决的成员国罚款的规定。通过判处罚款和政治监督的有机组合强制执行判决很适合欧盟的法律制度,是一个成功的创举。欧盟的成功经验证明监督和制裁的有机结合是促进遵守的最有效的手段。②吴晓丹:《欧洲法院判决的强制执行:刚柔并济》,《中国国家法年刊》2012年第311-332页。
但如前文所述,罚款机制有不容忽视的缺陷,对于欧盟来说将权力下放给各成员国也是它的内在需求,这跟成员国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欧盟法的直接效力和间接适用原则在不断扩张,直接效力原则扩张了“政府机构”的外延,间接适用原则纳入了个人进入申诉体系。在垂直和水平效力上,欧盟法体现了自己渗入各成员国内部法律体系的愿望。这种“权力的下放”,也合乎欧盟追求一体化的目标,欧盟体会到这种自下而上适用欧盟法的好处,也更愿意将此作为发展的趋势。
同时这种“下放”也合乎欧盟法的辅助性原则。辅助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是欧盟法中与权能划分问题联系最紧密的宪法性基本原则。①回颖:《欧盟法的辅助性原则及其两面性》,《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在《里斯本条约》之前,其主要体现在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修改后的《欧共体条约》第5条中。《里斯本条约》之后,辅助性原则被包含在《欧洲联盟条约》的第5条第3款中。条文内容为“在其非专属权能领域,欧盟应依据辅助性原则的要求,只有在对于拟定中的行动目标,成员国无论是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和区域层面都能充分予以实现,而出于拟议中行动的规模和效果的原因,欧盟能更好地完成时,才由本联盟采取行动”。辅助性原则是超国家机制和民主主权国家博弈的结果,对于双方而言这也是共赢的结果。对于该原则积极的解读是,欧盟给予自身合法性地位,而成员国也给予自己主动让渡出去的主权必要的限度,同时在这种制度的指导下,欧盟让成员国自主适用欧盟法,也大大提升了违反欧盟法的案件解决的效率,因为欧盟本身的资源是有限的。资源的有限和权力的扩张性之间有本质的矛盾。欧盟想要在现实层面上推动欧盟法在欧洲的一体化,就需要调动成员国自身的积极性。这也是欧盟法的执行程序逐渐“下行”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一种思路对于其他的国际组织,甚至对于国家内部的权力分配而言,都有借鉴意义。它体现在欧盟法上的效力就是,使欧盟法的适用更具弹性,充分保障了在欧盟法的统一下,各成员国使自己的主权不过分让渡,限制了欧盟权力的扩张。具体体现在执行程序上,就是把欧盟法适用的主动性逐渐让渡给成员国内部,使得欧盟法的真正执行由国内法院去解决,而欧盟更多地作为一个监督者和协调者,争取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违反欧盟法行为的问题,避免上升到欧洲法院的司法阶段,甚至是公力强制执行阶段。在国际组织层面,东亚共同体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提出。不可否认的是,经过50多年的发展欧盟已经走上了超国家机制的领先位置,早已走向了经济、政治、军事上的综合性的一体化。欧洲更多地愿意探索一体化的合法性,而东亚很少去考虑法的因素。事实上,东亚在法上实现一体化也要面临更多的困难。但是,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不断进步,法的要素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加盟国之间的法规制的不同,不得不作为一种非关税壁垒来认识。②须网隆夫:《推动东亚地区整合之际法律的角色——欧盟法的启示》,《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在未来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首先不应轻视法的作用,其次将国际条约作为一种辅助性法律,更多地调动各成员国的积极性,进行各国国内司法制度的改革,不失为一种值得考虑的思路。在国家内部的权利划分层面,按照这样的思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种具备活力的途径。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应当如何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力划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与欧盟自下而上授权模式不同,我国是自上而下让渡权力。但共同点在于,中央难以兼顾到地方各个方面,因此需要地方调动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制定法律法规。欧盟的辅助性原则在这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经验和借鉴,最终使得任何一个层级的行为主体所行使的权力都可以找到法律依据,都能够依法行政,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满足依法治国的要求,建成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③同注①。
五、结 论
由于不存在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社会,自欧盟诞生以来,强制执行一直是亘古不变的难点问题。欧盟法利用罚款强制执行国际法院判决是国际法中的新鲜事物。公力执行程序以经济制裁为保障,自上而下推动着成员国按时按质地执行欧洲法院的判决。这种强制执行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可观效果的,是欧盟能成为实权组织的一种制度保障,并且该途径也为国际法所借鉴。
但是从实践中看,欧洲委员会积压了大量的公民投诉案件,这说明仅仅依靠公力执行的手段是不足以应对目前的投诉审理需求,并且这样庞大的投诉数量也表明目前的欧盟法在成员国的适用情况并不理想。现在趋势之一是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通过行政程序就解决成员国不适用欧盟法的情况,另一个趋势是通过成员国有关机构自己内部消化法律转化过程中的问题,并且通过多年来的案例建立一个相应的法律原则——直接适用原则,一致解释原则和国家责任原则——以保障私力执行的实行。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成员国内法院融为欧盟法律的护卫者之一,真正实现欧洲法律一体化。当然,每种执行方式都有各自的缺陷,但是这样多元化的选择使得欧盟有机会探索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最终使每一种程序走向成熟。
另外,欧盟法以辅导性原则为基础的“公私结合”的解决途径,对于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和我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都具有借鉴意义。辅导性原则是欧盟与成员国关于主权让渡限度问题的博弈结果。从中,东亚一体化在法律制度上的设计可以学习和借鉴,另外我国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也值得思考,究竟如何才能产生自上而下的活力。欧洲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法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来源于对国际法营养的汲取,也对未来国际法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汤仙月)
DF07
A
1674-9502(2017)03-12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