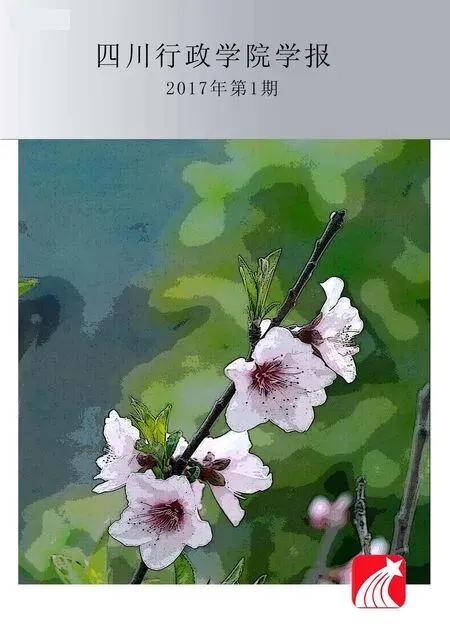村庄权力结构视角下的精准扶贫
文 禄素莹(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 430079)
村庄权力结构视角下的精准扶贫
文 禄素莹(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 430079)
随着精准扶贫到村到户,治理权力的下放,虽然瞄准的区域更小,然而,在“熟人社会”“关系社会”中,村庄内部精准扶贫的整个过程,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到精准管理,其实都是在村庄权力结构的影响下进行的,受到体制内的村两委以及体制外的家族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普通群众的干扰,真正的贫困户受益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精准扶贫的成效,使村庄内部分化更严重。
精准扶贫 权力结构 精英
一、导言
截止2015年,中国农村仍然有7017万贫困人口,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背景下,减贫任务十分艰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治理贫困问题的新思路--精准扶贫,所谓精准扶贫是指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1]。这种扶贫方式是项目直接到村到户的村级瞄准,克服了以往的片区瞄准与县级瞄准机制的缺点,在某种程度上能使贫困人口直接享受到国家的政策,提高了扶贫的精准度和效率。但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主要落在了村级的层面上,从目前村庄的权力结构来看,掌握村庄大部分权力的是村两委、村庄内的各种精英,另一端是则是普通的村民,从精准扶贫政策在村里实施的效果来看,存在托关系依靠权力获得贫困户的帽子,并享受扶贫项目的帮扶,而部分真正的贫困户则没有被识别出来,被排斥在外围。其根本原因在于扶贫工作尽管带有明确的国家意志与中央政府权力的印记,但是在村庄层面仍然无法避免微观权力结构与场域非正式制度和乡村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政府的扶贫资源必须通过村庄层面对接到贫困户手中,因此村庄层面的精准格外重要。因此,本文主要从村庄权力结构的微观角度探讨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分析村庄权力结构对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影响。
二、村庄权力结构分析
在省级、县级、镇级的指标确定后,村庄层面的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事关扶贫资源能否真正用到贫困户身上,本文在仝志辉、贺雪峰提出的 “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的村庄权力三层分析工具基础上,将村庄的权力分为体制内的权力和体制外的权力,体制内的权力由村两委组成,体制外的权力由宗族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普通村民组成。
(一)体制内的权力
改革开放后,村庄的权力结构由一元向二元甚至多元权力转变,村民自治政策的实施,由村民内部选举村干部,由此产生了主要由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共同管理村庄的权力结构。
1.村党支部与支部书记。组成村党支部的成员都是村里的人,在这个“熟人社会”中,村党支部和村书记的选举及权力的维持也离不开其背后的家族和各种精英的支持,当选后也会代表他们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村里换届选举时为拉票发钱请吃饭的现象会存在的原因,如若不是涉及利益,仅靠一年的补贴这个岗位是很难吸引大众的。选举出来的村党支部要对村庄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实际上成为了村庄公共权力的核心,对村庄事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党组织与同级行政组织相比拥有较大的权力。党支部负责上传下达,与上级联系紧密,为村委会以及其他正式村庄组织委派任务,因此村里公共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在一定程度上都掌握在村党支部手里,在很多村庄村支书依然是村里的“一把手”。
2.村民委员会与村委会主任。村民委员会由村民选举产生,与村党支部由村里的党员选举产生不同,村委由广大村民选举产生,其背后的利益团体更为复杂。由此可见村委会的权力来源于村民,少数服从多数,村民会议按规定是村民自治组织系统中的最高权力机构。村委会的权力主要表现在村委会主任在村庄内部的影响力上,在村中日常公共事务方面有决策权力,例如在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等方面。村委会委员与村党支部委员有交叉,在村里的管理上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二者有时存在权力利益之争,但是总的利益在协调之后是一致的。
(二)体制外的权力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村民民主意识的提高,以及村两委为争夺权力资源不顾村民的合法利益,加上体制内权力缺乏经济支撑,往往导致村庄体制内权力在管理村务的过程中力不从心,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村庄体制内的部分权力,激发了一些体制外权力的产生。体制外权力总的来说主要包括诸如宗族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普通村民等。
1.家族精英。家族是基于血缘关系的,虽然现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血缘关系有所淡化,但是村民依然比较重视血缘的亲疏远近。家族精英是在家族中族里人比较认可的人,对村中事务的权力在于表率性权力。村里人遇到婚丧嫁娶、邻里纠纷等情况时,基本都会寻求家族精英帮助调处,家族无疑是村庄内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家族精英往往与村干部交叉,村干部往往来自于这些大姓,这可能是基于传统认知。虽然家族精英在村民个体事情,例如邻里关系调节、婚丧嫁娶等作用明显,但是一旦超出了家族内部,涉及村里公共财产和公共决策时,其作用有限(排除与村干部交叉的个人)。
2.经济精英。经济精英大都是在改革开放后陆陆续续在村庄里先富的一批人,他们在掌握经济资源的同时,为了经济活动的降低风险性,一般会有参与村庄政治的愿望,但也由于经济精英的自身素质和局限性,可能在处理村务中为了自身利益而有失公平。随着商品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深入,村庄的传统文化失去了经济根基,村民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改变,把追逐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对于一个村庄来说也是如此,经济发达程度成为衡量一个村庄幸福指数的唯一标准,在这一评价体制的刺激下,镇政府和村庄都大力发展村庄的经济,所以村庄经济精英也就成为了村庄中颇有地位的体制外权力主体。
3.文化精英。文化精英,顾名思义是指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村民,即知识分子。他们与普通村民相比较而言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和专项技能,主要包括乡村教师、退休老干部、家族有志之士和民间文化的传承者等人群。这群人与外界交流多,且能为村干部出谋划策,所以村民和村干部遇到问题,也会寻求他们的帮助,在村庄里就树立了相应的权威,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正义。不过农村尤其是山区是留不住知识分子的,老一辈的文化精英可能在村庄里威望较高,较多的参与村庄事务,新一代的文化精英根本没有时间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工作也不在村里,只是偶尔会回家看看。所以这个群体处于“式微”的态势,文化精英在村庄事务中扮演的功能比较有限。
4.普通村民。普通村民作为村庄权力结构中数量最大的一环,他们既不是村干部,也不是各种精英,就是靠打工或种地谋生的普通民众,有的对村庄的事情漠不关心,有的则比较激进,对村庄的所有事情都觉得不公平,都要争个所以然,还有一些鳏寡孤独的弱势群体,他们往往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但是总的来说,普通村民由于“原子化”,在村庄权利结构的各种博弈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不占有优势资源和优势地位,在权力结构中相对具有无力感,在村庄场域中,各种权力进行博弈,村干部和精英都具有优势。
三、农村权力结构对精准扶贫的影响
黄承伟、覃志敏认为精准扶贫的实质在于将扶贫资源瞄准扶贫人群,并追求贫困人口规模稳步减少的“精准”要求,并指出“精准”二字是贫困人口识别和扶贫资源(资金、项目)瞄准[2]。村庄层面作为政策的直接执行者,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精准性无疑都会受到上述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和人情关系的影响,或是正面的影响,或是负面的影响。
(一)在精准识别方面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精准识别就是要识别出真正的贫困户,确定村级需要帮扶的对象,如果这一步识别不精准,那么将引发后面一系列工作的不精准。
目前我国的贫困人口基本上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也就是说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但是相对贫困人口收入差距不是很明显,很难识别出来。在一般情况下,村里特别贫困的农户,村干部和村民处于同情和道德考虑,会把这些农户识别出来,例如因病、因残致贫的。除去这些特别明显的群体,剩余的资源就会分配到所谓的“关系户”手中。虽然现在提倡参与式扶贫,在村级层面上,首先由村民申请,然后入户调查核实,再开村民大会进行民主评议,最后在村里公示。首先,村民申请,由于信息不对称,有些住户离村委会偏远,有的山村甚至是翻越几座山才有一户人家,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或是听说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申请,一般逻辑上认为不申请的就不是贫困户。其次,入户调查打分,谁来打分,要怎么打分,除了住房大家都能看见,还有大家公认的特别贫困的,其他的每户的收入孰高孰低怎么判断?这一切都是在村干部的主导下进行的。民主评议有些村民外出打工,在田里务农,很少参加,投票的公正性也有待商榷,也存在关系户,村干部的亲属、大家族的票数多。总的来说,就像邓维杰提出的“识别排斥”一样,这整个过程中有可能把真正的贫困户排斥在外,在调研抽取贫困户名单时,村主任会以这个不在家那个不在家为理由,拒绝访问某些农户,甚至把抽出来的农户偷偷放回换掉,部分村庄存在拆户现象,被问及时,村干部不小心说漏了,由此可见这里面一定是存在问题的。
如果在村庄权力结构的视角下,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农户被排斥在外围,体制内的村两委,在权力上占绝对优势,体制外的家族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他们在村庄有相对的权力,可以作为代表发声,这就让很多不符合条件的农户被识别为贫困户,中国本来就是人情社会。在调研入户访问时,在问及有些贫困户怎么评上的,有些则反映说不知道怎么评上的,干部来家里说我们是贫困户。村里的普通群众太缺乏监督意识了,当然也有些上访户维护自己的权益,但也有上访户尝到了甜头,把上访作为用来争取利益的伎俩,往往村干部会把这些会闹事的农户纳入贫困户的范围之内,以免出现上访事件,影响政绩考核。
(二)在精准帮扶方面精准扶贫下的帮扶将会考虑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实际致贫原因,在此基础上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和手段。贫困户的帮扶措施是根据地方特色以及农户自身的能力和意愿而制定的,实行责任制,每户会安排帮扶责任人。一般的扶贫措施养家禽,种植药材等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准入门槛。一旦涉及到较大的项目,就存在“入门排斥”“专业排斥”“规模排斥”“资金排斥”等。此时,村庄的权力结构就发挥作用了。一方面,考虑到贫困户确实缺乏相应的能力和配套资金,另一方面确实存在精英捕获的现象,体质内的精英与体质外的精英联合。例如在房县的某个村调研时,当地有建立合作社生产黄酒,当问到是否有贫困户参与时,负责人说到会有人贡献技术和资金,享受分红,但是在到户访问时并没有贫困户涉及这个项目,也许是没有抽到参与的贫困户。这种产业扶贫对贫困户的要求较高,无论如何,最终在各种权力和利益的博弈下,会把资源分配给有能力有资金的相对富裕的农户,而不是贫困户。有时候贫困户是缺乏这样一个机会,好的政策不一定落实到贫困户手中,他们拥有的只是贫困户这个帽子和很少的补贴。村庄权力结构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几乎垄断了村里的扶贫资源,即使是真的想为贫困户做点贡献,但是面对老弱病残确实看不到发展的潜力,所以才流传着扶富不扶贫的说法,在效率上来说是高效的,但是失去了精准性,一切等于零,有研究表明,“农村扶贫开发在缓解贫困的同时加剧了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3],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扶贫工作的减贫效果。
(三)在精准管理方面
精准管理首先意味着所有贫困户和贫困村的信息都将运用信息化的手段进行管理,同时通过贫困户关键指标的对比分析与统计,发现导致农户发展能力不足或是贫困状况恶化的关键因素。同时精准管理还意味着对建档立卡农户的扶持将是动态化的,当信息系统监测发现农户已经脱离贫困状态时就可以将该农户调出贫困户范畴,而一些新的贫困农户则可以进入。这就涉及贫困退出,符合什么标准可以退出,由谁来决定退出的农户。
在调研中,贫苦户脱帽大部分都是被动的,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脱贫了,大部分的贫困户是不愿意脱贫的,因为脱贫后就不能再得到各种利益了。所以存在明明已经脱贫的关系户并没有退出贫困,或是本来就不是贫困户,而真正的贫困户没有达到标准被迫脱贫,或是脱贫后面临重大的返贫风险。在入户访问中,某村的一户离村委会较远的住的是临时的安置房,非常简陋,享受异地扶贫搬迁政策,但是目前房子还没建设好,三口人,丈夫有病,一个小儿子,只有一个健康劳动力,因为是临时安置房,没有多余的发展生产养殖的空间,只有种地的收入。刚被纳入贫困户一年就被动脱贫了。另一边是在村委会旁边的贫困户,二层楼房,屋内设施齐全,装修完好,登记的是妻子因病致贫,新房盖好装修好国家补贴了3万块钱,不欠债,而且在后院挖了鱼塘投资10万元,项目验收后国家会补贴。这样的“贫困户”被纳入了,而且没有贫困退出,以上两户存在太明显的对比。这背后肯定是有某种权力的支持,或许是村干部,或许是村庄精英,这对其他贫困户来说是不公平的。这反映出对村级精准扶贫管理方面的疏忽,特别是贫困退出缺乏相应的衡量标尺和有效的监督。
四、结语
总而言之,村庄的权力结构对精准扶贫的影响是各个方面的,精准扶贫政策交由村庄层面实施就决定着并不能避免这些不精准现象的弊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情社会,虽然上层国家权力在乡村经历了无数次的崩溃和重构,但是村庄层面以地方精英为代表的管理系统掌握权力的实质却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这就像有句俗话说的“天高皇帝远”。随着我国精准扶贫治理权力的下放,村级层面的权力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除了上级的监督,最主要的是群众的监督,要想办法发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及群众的参与,这需要一个过程,政策知识的宣传普及,村民的意识觉醒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其次,增强扶贫项目信息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引起的精英捕获等不公平现象。最后,可以购买NGO的服务,发挥NGO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因为作为第三方深入村庄,不代表其他关系户的利益,只代表贫困户的利益。在中国一些事情只要涉及政府、权力、利益就会有扯不清的关系在其中,结果会使某些简单的事情变得很复杂。
本文假定村庄以上层面的瞄准确定后,在村庄层面权力的分析下,讨论了对精准扶贫的影响,但是村庄以上贫困县贫困村的确定同样也受到各种权力场域的影响,且对于村庄权力分层只是理想的类型,并非只有体制内体制外的权力。其次,对于各种权力对精准扶贫的不同影响程度没有做出区分,只是笼统的分析,也没有客观的数据支持。第三,只讨论了村庄权力结构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消极影响,忽视了体制外的权力对精准扶贫工作的积极作用。第四,在分析中把贫困户视为被动的角色,没有考虑到贫困户的行为对村庄权力权威的影响。
[1]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08).
[2]黄承伟,覃志敏.论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01).
[3]王春光.扶贫开发与村庄团结关系之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4,(03).
责任编辑:唐若兰
F328
A
1008-6323(2017)01-0072-04
禄素莹,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
2016-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