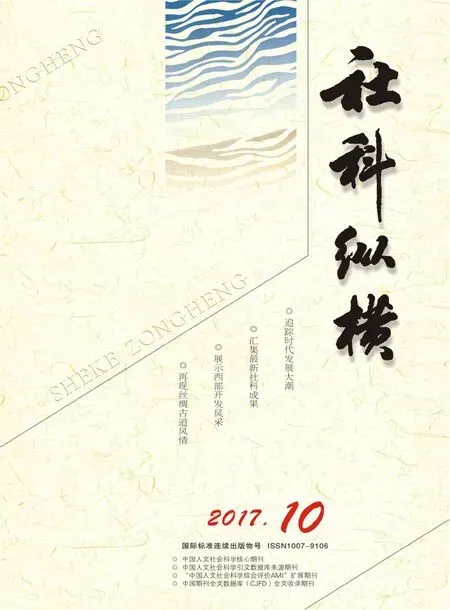田园乌托邦的失效
——阎连科小说的一种解读
艾翔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天津300191)
田园乌托邦的失效
——阎连科小说的一种解读
艾翔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天津300191)
通过对阎连科小说的细读分析,确认其叙事呈现出的田园乌托邦其实是一种假象,作家并不认为这是一条能够带来福祉的值得崇敬的道路,并不断设置冲破田园乌托邦的因素,以此推断作家在文学史链条上的位置。同时指出作家创作中善于运用“暧昧”和“陷阱”的特点,正是这些巧妙地设置为小说文本提供了富有意味的张力。
阎连科田园牧歌乌托邦
通过对《朝着东南走》这一失落于评论界的文本进行解读,据其意义结构基本可以得出两个判断,其一此作对田园乌托邦并无沉醉心态,相反如同对一切形式的乌托邦一样抱有一种冷静客观态度,并在此基础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拒绝;其二此作虽然一如作家其他作品一样使用暧昧的叙述作为情节载体,但并未如一般认识中那样激烈反抗乌托邦,而是对乌托邦精神结构进行细致考察后持一种客观并同情的立场。由于这是一部带有强烈“概念探讨”色彩的小说,因此可以之为钥匙,从上述两点结论作为进入阎连科其他重要作品的途径,开启作家更广阔的精神世界。
一
《日光流年》的故事发生地在三姓村,“地理位置为三县交界之地,然三县上千年的史志记载中,却均无三姓村治来源。据他们自己祖辈代代相传的说法,是明末清初之时,因战乱、灾祸之故,蓝姓从山东、杜姓从山西、司马姓从陕西逃荒至耙耧山脉的深皱之间,见这人烟稀少,水土两旺,于是也就搭棚而居,常住下来,耕地劳作,通婚繁衍,成为村落。”[1](P10)这段叙述交代了三姓村的背景,从形式上看颇似白话版的桃花源。在一个全国范围内都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三姓村没有党员团员也没有地主富农,其与世隔绝甚至延续到了改革时代:“现在地都分了,包产到户了,粮食收成到底和以前比这咋样儿,还问他你们村里地没分,牛没分,农民没有意见吗?”[1](P260、178)相比外部世界似乎总是慢半拍,但作者并未将三姓村完全当作世外桃源来写:“原来外面的世界和耙耧山脉并无多少差异哩,男人们也是扛着锄下地锄冬麦,挑粪施冬肥。女人们大冷天也到河边洗衣裳,怀孕了也挺着大肚在村头拾柴火或在门中带孩娃。狗的叫声也一样汪汪汪带有土黄色,牛哞声也和浑浊的河流一模样,就是连路边的坟地,也都是圆圆的土堆,堆顶偶尔还压着一块去年清明上坟的旧纸。”[1](P449)阎连科拒绝承认彻底隔绝的可能性,他笔下的三姓村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但终究还是世界的一角,外界还时常对这里产生影响。从根本上来说阎连科不是那种纯粹耽于幻想的人,更不是因循守旧的人,不然其小说不会带有拉美和苏俄文学深重的烙印。他不但自己不沉溺幻想,更不会允许这种幻想干扰他观察现实的眼睛。
从小说全局规划上看,为了祛除喉堵症之痛,历代村长进行了不断地尝试,司马蓝的曾祖爷和祖爷两代都致力于外迁人口,蓝百岁通过卢主任借来外村的公社社员深翻地,司马蓝两次发动规模浩大的引水工程,都是求诸外界的方式。内求诸身的只有司马笑笑号召种油菜和杜桑推动村民加快生育,其中前者起因是“闯入”的外村老者称其长寿秘诀是吃油菜,也是在借用外部经验;只有唯一消极御病的加快生育政策是彻底的“自力更生”,并且这种叙事的乌托邦色彩也较弱。在作者看来,三姓村虽然具备了成为桃花源的基本条件,但维持田园牧歌式生活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于一个不仅仅要延续幸福、更重要的问题是突破困境的偏远乡村来说,内向的田园乌托邦的作用只能是消极和乏力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很自然地需要领袖人物的存在和政治乌托邦的建立,而后者这一属于现代社会范畴的理念在根本上与传统性的田园牧歌是格格不入的。
《受活》中受活庄的设计与三姓村十分相像,“说到底,受活是被这世界遗忘的一个村庄哟,地处三县相交的耙耧山脉里,距最近的村庄少说也有十几里。……没有哪个郡、哪个县愿意收留过受活庄,没有哪个县愿意把受活规划到他们的地界里。……从明至清,年年辈辈,辈辈年年,康熙、雍正、乾隆直到慈禧、辛亥、民国,受活庄数百年里没有给朝上、州上、郡上、府上、县上交过皇粮税。周围的大榆、高柳、双槐三县下属的区、堡、村,没有哪一家来受活收过粮和款。”[2](P118)作为精神领袖的茅枝婆在1951年还在向突然“闯入”的一个外乡人询问“日本人打到哪啦?”真是对“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如实翻译。茅枝婆因为有红四方面军①的身份印记和历史经验,后来又因为柳鹰雀的市场化运作发生了从“革命乌托邦”向“田园乌托邦”的转变,义无反顾地带领受活庄人“退社”②,并与双槐县委县政府达成协议由后者发布正式文件。
田园乌托邦的本意当然是为了隔绝外界对自身的干扰,维持内部原有的安定舒适,最终目的是个体的真正满足,但曾与外界发生过频频接触且获得丰厚回报的受活庄已难遂茅枝婆逆向发展历史之愿,并且即使实现了田园乌托邦,那么日后一系列会给村民带来实际好处的乡村建设工程将均与受活庄无缘,村民反而不能获得这个时代应有的满足,田园乌托邦因此形成一个充满讽刺的悖论。
有论者提出:“如果说‘革命日子’的乌托邦时间是指向未来的,‘洋日子’的乌托邦时间是指向现在的,那么‘散日子’的乌托邦时间就是通过指向过去而指向未来的。它在‘从前’与‘未来’的对接中,直接抽掉了‘现在’,否定了‘现在’。由此可见,以不同日子或生活形式为标记的梦想之间的斗争,实质上也包含着不同的时间观之间的斗争。终极即初始,想象即回忆,对受活人的时间意识来讲,过‘散日子’的梦想其实本不是梦想,而是曾经有过的现实,只不过由于圆全人的介入它才变得遥不可及了。”[3]“散日子”正是方言中的田园乌托邦期许,如同前文所论,笔者不否认作家内心深入怀有对田园牧歌的向往,但不能因此否定作家压制情感而做出的客观批判。
随着“散日子”后的絮言就是对“龙节”“凤节”“老人节”的释义,后者实际上是以民间传说形式出现的维护前者的意识形态工具,因为老人“朝着东南走”的预言使受活庄人在本庄过上了“天堂日子(散日子)”,村民的身体缺陷从此转变成了幸福生活的保障。但这则传说并不是一个结构稳定的田园乌托邦,因为篇幅限制这里的“朝着东南走”不能如《朝着东南走》彻底呈现静止时空下生活的乏味干枯,只能通过两处动态的介入性情节设置取消“朝着东南走”的乌托邦有效性:出走的男人们途遇另一位同样“在路上”的老人,得到的却是另一个“朝着西北走”的乌托邦叙述,并且消除残疾的乌托邦正是因同样目的离家的男人们居住的受活庄,前后两种叙述形成反冲从而破解了前之老人田园牧歌的神话;经过一来一回三年离家,“少了胳膊的单手男人却发现,出门经了三年的辛劳后,自己会用一只手割麦子、刨地了,一只手也能干两只手都有的圆全人的活路了;瘸子发现出门走了三年路,练得自己一条腿和两条腿的人一样走路又快又有力;瞎子因为走的路多了,他手里的瞎棍儿这敲敲、那碰碰,竟可以把棍当成眼睛用;聋子也因为走了三年路,和人说多话,看着别人的嘴动,就能猜出人家说了啥;哑巴因为一路上要比比画画,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手势和哑语。”[2](P388)这就指出田园乌托邦存在的巨大漏洞,即单纯依靠维持现状的保守方式在受活庄这样先天不足的地方很难实现其预设的乌托邦理想,只有引入外来因素,在这里是让受活庄人走出本庄参与到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原先的消极因素才可减弱。作家通过这个不同的“朝着东南走”的故事告诉读者,田园乌托邦的巨大欺骗性来自于对“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预先限定,但现实中尤其是在现代中国具备这一先决条件的乡村并不占据多数,因此田园乌托邦不能作为解决乡村问题的普世方案。
二
集中谈论田园乌托邦问题的是上述三部小说,另外在《坚硬如水》和《风雅颂》中也略微涉及至此。由于有强烈的革命气息的衬托,未经革命的程岗镇在高爱军眼里是这样一番模样:“镇上的社员正挑着草粪往小麦地里送追肥,他们拉成一队,老的少的,脸上都有一些悠悠闲闲的红黄色。……还有一只麻雀在母猪的肚上翻着猪毛捉虱子,那景象使人想到这儿离革命的遥远,至少是要从延安到了海南岛。我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失落感,就像从盛夏一步踏进了冬日里。……死气沉沉山区天,沉沉死气乡村地。”[4](P20)透过“革命”的视角,田园牧歌所携带的诗意被剥去,剩下的只有如死水般的沉闷和凝滞,作家的锐利和辛辣在此彰显。
《风雅颂》中杨科离开政府街和在此街上开耙耧酒家的昔日恋人付玲珍就已经预示了后来的情节发展,待其再次从京城回到前寺村老宅时,家中已被村民洗劫一空:“屋里和院里,站满了村人和邻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我的一样东西准备朝外走。还有村里的媳妇们,她们看见我家里没有东西可拿了,就到灶房拿走了我的锅,还有菜刀、面盆和案板、筷篓神的么(抢一样)。其实不是抢,是顺手分着拿一样,如大家到我家和和睦睦地分了我家的家产般。”[5](P250)与《坚硬如水》剑拔弩张的紧张感不同,作家在这里采取一种超然的姿态仿佛旁观者一般冷眼观察,隐隐含着些许嘲弄,将先前杨科刚到前寺村所感受到的那种淳朴民风和怡然自得的生活气息彻底化解。
在关于《日光流年》的各种声音中,有一种观点透露出阎连科在此问题上存在保守姿态:“每次与外界接触,逻辑上都是对封闭的‘三姓村’的巨大冲击,都有可能使‘三姓村’的世界扩大、沟通或融入外面的世界(想一想铁凝如何借一次偶然的坐火车而展开乡村姑娘香雪对外面世界的无穷遐想吧),但实际上,这种接触始终被司马蓝所代表的一股强大的意志力否定着,牵制着,不能充分实现。”[6]如果从表面上看这种情节设计确实令司马蓝有维护田园乌托邦的意图,但首先更因该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司马蓝不让本村女性外嫁?或许为避免本村男人找不到配偶,从而三姓村难以为继。但事实是乌托邦的闭锁根本上是“被闭锁”,如果没有司马蓝的禁令,三姓村的女人在村外就很抢手吗?恰恰相反,公社帮修梯田就是一次明证,许多本村女人跟外村男人私奔,但对方都与“比自己大二十岁”的男人,就是说这是一种极其不公平的交易,吃亏受伤的还是三姓村的女人。这一点在《受活》里更加明显,受活庄与三姓村一样,在外人眼里是谁都不愿接受、偶尔还能随意欺凌的弱势群体。
如果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小说都是本民族的寓言,那么这一判断完全适用于阎连科小说。其笔下以受活庄与三姓村为代表的凋敝小村落无疑是中国的写照,在自身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与外界减少联系是生存的唯一选择,并且在更大范围内,这种减少联系实在是外部强大实力的野蛮封锁。在20世纪田园乌托邦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阎连科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同样看出,其存在也并非毫无根据。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充分激发内部的发展力以维持并推动共同体的生存状态,通过政治乌托邦和道德乌托邦的创构实现艰难环境下“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的复兴目标。因此阎连科是在用小说的形式,揣测上世纪中后期人民共和国的艰难起步并在对乌托邦全面充分的理解上反思其利弊。
曾有学者专门分析过诸如“乐土/乐国”、“小国寡民”、“华胥国”、桃花源、“酒乡”、“寿乡”和“君子乡”等传统文化中的田园乌托邦构想,指出“其共同特点,首先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对立面,从与社会现状相反的方向去构想,表现出鲜明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其次,这些理想中的社会,不是从国家的政治法律、行政组织等方面去设想,而是与之相反,是没有王治的‘无为’世界,那里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追求一种自然无为、和平安逸、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再次,这些理想的设计,皆重在道德的建树,而且是以鲜明的复古思想为指导,提倡远古的道德文明,甚至不惜抛弃一切现代物质文明。”[7]这就是说,虽然同样带有不满现状的自觉,但田园牧歌本身取消了时间性,企图逆转历史发展方向,并且完全倚靠个人德行的修冶而在社会结构重塑方面是无所作为的,因此不可能被阎连科采取作为精神内核。对此作家本人也明确表示:“我不是要学习陶渊明,我活到五百岁,读到五百岁,也没有陶渊明那样的学识。最重要的,是没有陶渊明那样内心深处清美博大的诗境。我想实在一点,具体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生命过程就这么实在,具体,活着就是活着,死亡就是消失。”[1](自序P2)
有一种观点应该可以被认可,即“乡土精神并不是医治个体与群体精神荒芜的救世良药,阎连科不能从根本上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自在,真正的出路仍然是一片混沌之中以至于他内心会禁不住惨痛的绝望。这样,乌托邦叙事便不由自主地黯淡了神圣的光泽甚至步入了穷途末路,终局便只能落入了颠覆的深渊。那是现实生活中他的精神气脉的最真实抒写,也是一种无奈的苍凉。”[8]如此分析能够成立,那么就可以说,阎连科一定程度上凸显出的“反乌托邦”倾向实际是他通过艺术探索发现“田园乌托邦”已无法再生的体现,或者说相比“政治乌托邦”,更令阎连科灰心失望的是“田园乌托邦”,照此理解也符合“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这一广为流传的论断。
对于田园乌托邦的立场,笔者相信是可以放之阎连科多数作品而皆准的。“在《丁庄梦》中,作者对人性是绝望的,这种群体性格的劣根性深深地根植于乡土文化中。在文学对乡土中国和人性的想象中,乡村常常是精神的家园,医治着现代人的精神焦虑,是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灵魂最后的栖息地,乡土人性是纯朴、善良的代名词。阎连科的叙述完全解构了这种文学想象的虚幻性,他笔下的乡村是沉滞、压抑和贪欲的,人性是不可救赎的。其实,什么是乡土生活的真实,田园牧歌或者藏污纳垢,显然取决于作家的审美选择和价值取向,阎连科以这样一种绝望而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他笔下的丁庄人时,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挣扎。”[9]也有论者更加明确地指出:“正是出于对乡土精神不足和缺陷的深切认识,阎连科也不能不对乡土精神拯救世道人心的效用有着清醒的犹疑。”[8]如果要将阎连科的乡土题材放入文学史发展脉络,当然应该归其入鲁迅开辟的乡土小说系列而不是“周作人—沈从文—废名—汪曾祺”这一谱系。在作家看来,乡土社会乃至整个现代中国的既有设计都是不尽如人意的,乡村建设甚至至今为止的整个现代化方案都是一种未完成态,他所做的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寻求一个更加合理的答案。通过前文分析,阎连科在根本上反抗市场乌托邦的道德,同时顺带反抗田园乌托邦的保守性不作为,后者的温和气质难敌市场侵蚀,要制衡市场似乎仍然应该考虑到驱除暴力因素的“革命”传统。
注释:
①阎连科的暧昧又通过“红四”的形式出现,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很微妙的“丙子年秋”,即1936年。由于《受活》采用天干地支纪年,许多重要或敏感的年代被模糊化。从年份上来说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生在1935年,并且在“丙子年秋”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茅枝婆已经离开红四走向耙耧山脉,因此“红四”是预先巧妙设置好的“陷阱”。他曾说“优秀的作家,应该是才能丰富的阴谋家,总能给批评家设置陷阱的人。”见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阎连科文学对话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9。
②阅读阎连科作品会不断遇见“暧昧”和“陷阱”,其实在情节所处的改革时代是全国“退社”,只不过没人使用这种表述。茅枝婆的“退社”实际是要求彻底的村民自治。
③孟繁华认为,“在《发现小说》里,阎连科显然对周作人的这个传统更表示亲切。但事实上,阎连科自己坚持的恰恰是鲁迅的传统,无论是战斗的姿态,还是洞察世界的深刻性和自我反省的内心要求。”孙郁亦作如是观。见程光炜、邱华栋等.重审伤痕文学历史叙述的可能性——阎连科新作《四书》、《发现小说》研讨会纪要[J].当代作家评论,2011(4):54-55。作家的文论和创作显示出不同倾向也是个有趣的问题。
[1]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2]阎连科.受活[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3]王鸿生.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读《受活》[J].当代作家评论,2004(2).
[4]阎连科.坚硬如水[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5]阎连科.风雅颂[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6]郜元宝.论阎连科的“世界”[J].文学评论,2001(1).
[7]孟二冬.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8]卢逍遥.论阎连科小说的乌托邦叙事[D].上海社会科学院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9]吴雪丽.暧昧的叙述——阅读阎连科新作《丁庄梦》的一个视角[J].当代文坛,2007(1):113.
I207.42
A
1007-9106(2017)10-0133-04
艾翔,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