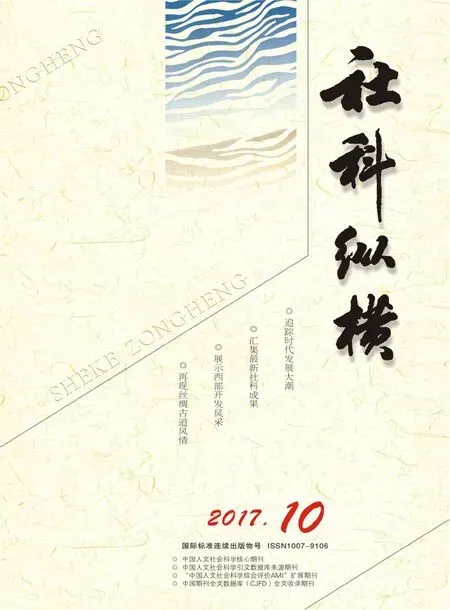由石刻的起源于秦地说到陇南石刻的文献价值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史学研究·
由石刻的起源于秦地说到陇南石刻的文献价值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今存真正的石刻文献为原在凤翔三畤原的石鼓文,其次是发现于泾水、渭水流域的《诅楚文》。另有一发现于洛水流域的《诅楚文》,学者们已指出为后代所伪造。则最早的石刻文献皆见于秦地。《穆天子传》中言穆天子“升于弇山,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弇山即崦嵫山,在今礼县东北部。秦地之早有刻石,因其地多石。以石刻字至秦代开始,才逐渐风行全国。东晋至刘宋、齐梁,皆禁私人刻石,而陇南属北朝,不受其约束,故石刻文献也较其他地方为多。
陇南秦石刻文献崦嵫山泾水渭水
我国目前发现的石刻文字,最早有1935年在安阳殷墟出土的一片石刻,上面镌刻有两行文字,共十二字,属记事类。再则三件商代石磬上分别刻有“永”、“永余”、“大余”等字。这能说商代文字记事除铜器上铸、刻,竹木上刻写、缣帛上书写之外,也用石头以书写或镌刻。但由于石头难以加工成较薄的刻字材料,中原地带可用于刻字的石头也比较少;而竹简的可以编而成册,储存携带方便,因而不断扩大应用范围;铜质礼器、食器因其特殊的用途可永久保留,因之常在铜器上铸刻具有纪念或证明意义的文字,故刻字多的石器便极为少见。
真正的石刻文献应起于秦地秦人。著名的石鼓文,在十个鼓形圆石上刻满了文字,每一个石鼓上刻一首四言诗,共有四百多字。内容都是歌颂秦国国君狩猎盛况的。这些刻满字的石鼓原在陕西凤翔三畤原,笔者1998年11月曾至石鼓出土处考察,原是一个坡形地带。关于《石鼓文》产生的时代,大部分学者认为是在春秋战国之时。
时代较早的再一石刻文献是《诅楚文》,内容为秦人诅咒楚国的,反映了秦楚对抗中秦人采取的宗教神灵手段。北宋初年董迪《广川书跋》中说:“秦《诅楚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于泾,又得《巫咸文》于渭,最后得《亚驼文》于洛。”今存这三碑之拓片,上面主要文字全同,应是秦人告神灵诅咒楚国之文。泾、渭俱在今甘肃,当春秋战国时秦国地域范围。洛水在今河南省范围。但得于洛水流域的《亚驼文》中的“驼”字,左面“马”字末笔为“灬”,近于隶书的四点,有失古文之体。而且宋刻《绛帖》与《汝帖》收有《巫咸文》与《大沈湫文》,而无《亚驼文》。看来《亚驼文》是后人所伪造。那么,可靠的《诅楚文》两碑都是在甘肃,为秦人所刻。关于《诅楚文》的产生时代,从欧阳修以来多主成于楚怀王时,郭沫若《诅楚文考释》认为是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前312)作品。
至于秦始皇之时的《封泰山碑》《峄山颂德碑》《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碣石石刻》《之罘东观大篆》《稽山颂德碑》及秦二世的《二世诏文》等碑刻,将这个风气推向原秦地之外,不用多说。
立碑碣之风始于秦地,还有一个证据,便是先秦文献《穆天子传》卷五所载穆天子在弇山刻石纪事的情节:
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三槐。
“纪其迹于弇山之石”即在弇山立碑碣。郭璞注:“弇山,弇兹山,日入所也。”“弇兹”在后来的文献中多作“崦嵫”。《山海经·西山经》:“鸟鼠同穴之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崦嵫山”为神话中说的日入之山,古今所有的辞书和有关注疏都注其地“在甘肃天水西南”。这正在秦人早期发祥地一带。该山应在早期秦人居住地之西,秦人每天见日落于该山,因而产生了日落于崦嵫的神话。秦统一全国前后,该神话便成了全国性的神话传说。周穆王纪其行程于弇山之石,是有关石刻文献的最早记载。周人发祥于陇东,至平王东迁,秦文公才“收周余民而有之,地至岐”(《史记·秦本纪》)。《穆天子传》中这个记载至少是秦人刻石纪事的曲折反映。因为周秦两族毕竟比较靠近,有所接触。
现存的陇南石刻中,也有时代很早的摩崖。成县黄渚镇太山村大崖洞的洞口有一幅岩画。岩画右上二米处,有二字横列,篆字体式,似为“言愚”。主体人物的两侧下部又有几个字,不甚清晰,看来应是西汉以前的摩崖。(又右上有“杨忠元”三字,明显为后人所刻画,不论)。岩画同刻字不一定是同一时期的遗留,但从其中一些字和部件的结构、笔形态来说,文字应是先秦时所刻,或者说西汉以前所刻。另外,成县西狭中段、《西狭颂》以西约一公里南侧崖壁上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的《西狭汉将题刻》,也是全国最早的石刻之一。
由以上这些来看,文字刻石应起于秦人。
春秋战国之时秦人盛行刻石,笔者认为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
第一,秦人早期所居陇南天水一带及后来的雍(今陕西凤翔)、平阳(今宝鸡市以东平阳镇)皆多山多石。直至20世纪40、50年代,陇南、天水农村中有的人尚以石片盖房,有的将石片架于火炉之上烙饼。大的石头则更多,很多地方有石山,为碑碣、摩崖都较方便。如清光绪《重纂礼县新志》卷二《物产》有“青金石”,这是刻碑碣最好的石料,耐风化,可以用来制造砚台。民国二十五年印《新纂康县县志》卷十四《物产》载:“碑板石,其质坚韧,专用以做碑碣者,能刻文雕画。”
第二,春秋战国以前虽然炼铜工艺已较发达,但铜多用于礼器和兵器,可以刻较长文字的很大的铜器毕竟少,用石头则成本较低,置于山上、水边也可避免被人偷盗铸锻他器。
刻石纪事之俗达到全国风行有一个过程。故西汉时的石刻文字,极为罕见,而且所见者上面刻字也极少,上面只几个字,最多也不过数十百字。至东汉石刻才多起来。欧阳修《集古录·宋文帝神道碑跋》中说:“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宋代以后也发现过几个西汉时碑碣,但是极少。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石刻的使用对象已开始从朝廷向诸侯王大臣以至一般人过渡。
东汉时社会上承儒家重孝道的思想,学人又重师承,子女为逝去的父母立碑,门生故吏为老师、府主立碑,便逐渐形成风气。
到魏晋之时,朝廷又禁止私人立碑。《宋书·礼志二》载:“汉以后,天下送死者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东汉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故在东汉末已有埋于墓中、类似后世墓志的石刻文字,至曹魏之时即有以“墓志为题名者”。
晋承魏大统,晋武帝咸宁四年(278)下诏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晋帝义熙年中,因有大臣长吏私立碑之事,裴松之又议禁断,直至南朝梁代(见《宋书·礼志二》)。
这里要说的是:东晋偏安于江南之时,陇南一带属前秦;南北朝之时陇南先后属于北魏、西魏、北周。故尽管东晋与南朝亦有碑禁,却与北朝不相干。所以,陇南在历史上是碑碣石刻文献最丰富的地域之一。
由于五代以后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南迁,陇南一带渐成偏僻之地,加之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人口稀少,文化不太发达,虽然在军事上有很多大事发生,但是政治文化方面有不少事未被所谓正史留存,见之史家学者的书面记载极少,所以其石刻文字可以补史书记载的缺失,有其特殊的文献价值。
陇南各区县石刻文献从内容上说包括地方建置、军事活动、政治、经济、交通、教育、自治公约、宗教、名胜古迹、名人碑铭等。有很多是反映了活生生的一般老百姓的历史,而同所谓“正史”只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者不同。由各类石碑、摩崖等可以看出几千年历史中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社会的稳定、生活的方便、文化的发展,所作的种种努力。这也就是近些年西方史学界所兴起的“微观史”研究的具体材料。它比很多史书更接地气。在地方史、地方文化研究的方面,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极宝贵的材料。其中有些碑文也反映了一些重大的事件。
注释:
本文所引金石文献见赵逵夫主编,赵逵夫、崔阶编纂《陇南金石校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
K877.4
A
1007-9106(2017)10-0101-02
赵逵夫(1942—),男,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文学遗产》编委,甘肃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甘肃省文化发展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