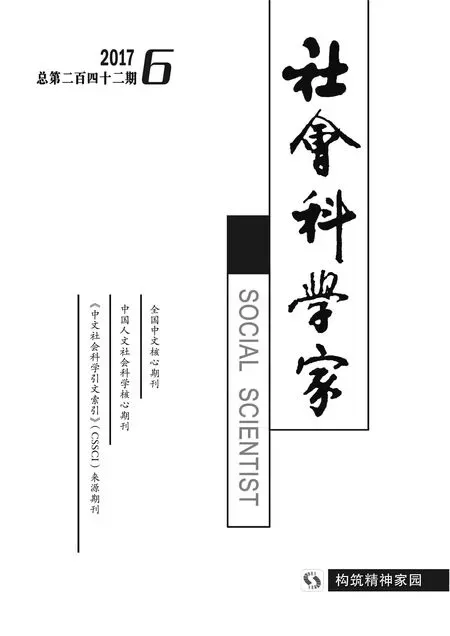当代人类学转向研究中的“神话历史”问题
孙凤娟,,公维军
(1.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00;3.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当代人类学转向研究中的“神话历史”问题
孙凤娟1,2,公维军3
(1.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00;3.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时至今日,“神话”与“历史”已然被现代学科体系人为分离开来,由此产生的弊病显而易见。事实上,两者本非一组对立概念,神话作为一种特有的智慧表述与文明基因,对原初先民的观念信仰、行为礼仪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文化编码作用,而早期中国历史恰恰具有鲜明的“神话历史”特点。华夏文明传统基于一套天人合一的神话思维方式建构起来,故而以文学人类学者为代表的人文学科研究者开始积极倡导大传统的通观式研究视角,意在通过促使历史记忆回归本初状态,明晰中国历史叙事源于“神话式历史”这一被遮蔽的事实,有效发挥神话历史的整合性阐释效力,进而能够前往文学文本之外的文化传统中探寻华夏文明的源流问题。
人类学转向;神话历史;大传统;历史记忆;神圣叙事
1903年,“神话”一词假道日本传入中国之后,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如今的神话仅仅被人为归类在民间文学之一隅,勉强被现代学科体制所接纳。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视界如此褊狭的划归之举显然不合情理,毕竟神话的概念远大于文学,存在时间也要比文学更为久远。诚如弗莱所言,整个文学也无非古老神话生命体的变相延续或置换,文学与神话之间应该是一种从属与被从属关系。因此,从文学人类学的大传统视域出发,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智慧的自我表述,代表着人类早期历史的文化基因,与史前的宗教信仰、仪式表演共生共存,发挥着最原初的神圣叙事功能。
一、神话的“信”、“驳”之辩
从哲学本位观出发,神话成为非理性的代名词,被理性所驱逐排斥;从历史本位观出发,历史学又将神话视为不科学、不可信的伪史,二者形成鲜明的二元对立。卡西尔借助于神话思维得以建构起“象征形式哲学”,而列维-斯特劳斯则意在通过印第安人神话研究证明“野性”与“科学”两种思维方式的同等重要性,这都使得神话作为人类思维编码的文化符号,正在突破“神话非理性”的错误哲学观。新历史主义要求将历史从“历史科学”的瓶颈中成功释放出来,重新恢复历史与神话这两种叙事所具备的相同虚构、比喻性质,海登·怀特同样也希望能够实现从“历史科学”向“历史诗学”的革新转向,从而回归历史本真,这也就无怪乎米歇尔·德·塞尔托敢于发出宣言式的声音:“历史可能是我们的神话!”[1]
在中国学术史上,神话遭遇了诸多文人乃至学术流派的强烈抵制。刘勰曾有一段关于神话传说与历史关系的论述,足以代表绝大多数“信史派”的观点,他们将神话传说视为随意、杜撰乃至不足信的同义词:“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词’,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旁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2]尽管如此,学术流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依然属极力主张疑古辨伪的“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为顾颉刚、钱玄同、童书业等人。他们通过爬梳考据,提倡所谓“深澈猛烈的真实”精神,[3]致力于分割“神话”与“历史”,坚称二者必是完全对立的,此举意在将视同伪史的神话剔除出信史的学术范畴。其对待古史的态度主要有两种:一是“上古无史”,因为上古时期所流传的神话传说多数并不可信,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应当缩半;二是秦汉时期多系伪史,主张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辨派过分依赖文献史料的记载,以至于形成了将文字材料视作唯一可靠来源的偏颇性判断标准,这些观点主张自然也很快招致了各方的批评。
钱穆曾对疑古派教条对待古史的观点进行过尖锐的驳论,他指出若创建新的古史观,就应当对前人极端的怀疑论加以修正,各个民族的历史不可能脱离开“传说”与带有“神话”意味的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假造和传说的区别明显,后世史书中的整段记载或者描写,或可归为假造,但散见于古籍中的“零文短语”,则往往是上古传说,这不是后世某一个体或某一流派所能伪造的;欲将某一传说排斥出去,就需要找出与之相反的确凿证据,否则不能主观臆测其系伪造抑或不存在,当然,如果两种传说确实难以并立,则需“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4]显然,钱穆认为上古历史是无法脱离神话传说的,这在其修正意见中已表露无遗,同时,神话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多少会有增减修饰之嫌,但却不能与“假造”、“伪造”直接画上等号。鉴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极富理性,迫近事实”,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有所不同,所以许多传说理所应当成为研究上古史的史料证据。此外,徐旭生亦指出了极端疑古派的错误所在,他们没有做到将“掺杂神话的传说”与“纯粹神话”两者区别待之,更是以恩格斯叙述雅典国家起源的例子来力证他们“将神话关进保险箱”的举动荒唐之极。
然而,这些批评对于顾颉刚而言,多少还是有些无辜的。顾颉刚既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民俗学家,他在研究孟姜女传说之后,其中一个重要结论即“传说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于玉蓉对此有着透彻而独到的理解。她通过顾颉刚对《大雅·生民》篇所载姜嫄生后稷“履帝武”的分析,得出了顾颉刚对于神话与历史关系的几点思辨性认识,非常值得学人思考:首先,他认为神话、历史在汉代以前是合一不分的,二者间区别的出现实乃汉以后人为划分使然;其次,对于古史文献的态度,他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即信则愚钝,驳则废言,释也无非以“今人理性”去生硬衡量“古人想象”;再次,他认为如果透过民俗学视角予以审视,那么神话即具备了故事性质;最后,他希望以后面对神话时,能够遵循其自身性质,避免陷入武断“信”或“驳”,甚至于将“今人理性”强加于古人的误区,如此方能发掘出“当时传说中的真相”。[5]由此可知,顾颉刚并不认为传说全都是荒谬无稽的,中国历史的性质应当是神话与历史的彼此交织,可见“极端古史辨派”的许多学者并没有完全领会顾颉刚所做的深入思考,进而导致观点上的失之偏颇也就容易理解了。
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并非发生于两个事物之间,而是在同一个事物中发生的,二者关系从对立逐渐趋向整合。不幸的是,当代研究范式人为规定了神话与历史的划分依据,使得人们的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己框定的无解怪圈:神话历史化?抑或历史神话化?其实这样的探究意义不大,因为神话自创世始延续至今,与历史同生共长,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持观点一样,神话在所有文化中都是必需的要素,加之神话能够不断再生,因而“一切历史的变化产生于历史连贯的神话”[6]。除此以外,艾利亚德对神话特点的总结概括,其实也足以代表神话历史领域的显著特征,他认为神话能够揭示出世界、人类与生命的起源和历史,而这种超自然的历史具有珍贵性和典范性特征,神话必然与创造联系起来,被视作重要的“人间行为典范”,能够在展示事物来源的同时,展示出行为形态、制度与劳动方式的确立过程,而人们正是由于知晓神话,才能够了解、统治并操作事物,“无论通过什么方式,人都活在神话之中”[7]。因此,在他们看来,神话叙事本身就蕴藏着深刻的历史内涵,换言之,神话叙事中本来就包含有“历史的真实”。
如若将历史和神话人为割裂分开研究,就等同于在后现代知识背景之下,将神话历史这一打通文、史、哲诸学科并提供通观式研究的可能性突破口重新封堵起来。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看,神话历史的本质实为一种集体记忆,从多学科视野审视,不难发现这种记忆中其实暗含着根本性的价值判断,包含有诸多证明与阐释。张光直认为,天人之间的断裂是西方文化史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然而这种“断裂”并未在中国文化里发生过,因此,天人合一始终是早期中国思想里面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需要明确的是,天人合一是出于神话想象,而非哲学思辨,张光直曾这样诠释玉琮这一神圣器物所代表的天人合一意义:“‘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笠以写天。天青黑,地黄赤,天数之为笠也,青黑为表,丹黄为里,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能掌天握地的巫因此具备智人圣人的起码资格。”[8]可见,内圆外方的玉琮恰恰充当了神巫“掌天握地”的法器,成为其身份的最佳象征物。叶舒宪认为,如果为天人合一寻找一个形而下的原型的话,那就是史前的玉人了,因为根据目前学界的一般性解释,此类形象要么是天神形象,要么就是巫觋、萨满一类的通神者形象,基于此,“玉人形象与天的宗教神话联想,以及逝去的祖先灵魂升天,与天帝及诸神同在的宗教信念”[9],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玉人形象的物质基础是玉,能够代表天,所形塑的是人,此种玉石神话信仰所建构出的天人合一观念对文化符号生产发挥着支配性作用。
其实,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并非中国所专有,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中也有与之相类似的信仰,只不过在他们文化史的某一个阶段中神圣与世俗之间发生过断裂,不像在中国能够一直延续至今。张光直曾参照理查·汤森的观点,将15世纪墨西哥阿兹忒克人的信仰作为典例,进行过专门性的阐释,即把他们的都城及其环境的关系视作一个有秩序的整合性宇宙结构,同时,将其中的自然现象从本质上奉为神圣且有生命的,他们会以一种参与意识来对待这些自然现象,把宇宙看作各种生命力间相互关系的反映,而生命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这个内部关系彼此影响的宇宙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0]如此看来,无论中西,神话建构下的天人合一思想犹如深藏于文化表层之下的深层建构一般,在人类文明史中永存不衰。
二、神话历史视域下的经典文本重释
随着神话与历史间相互关系的逐渐融合,国外很多学者都倡导以全新性视角对二者予以重新审视,这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学者的代表性著作相继有了中译本,诸如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杰克·古迪《偷窃历史》、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等。直到2009年,叶舒宪正式在《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一文中明确提出“神话历史”的概念,指出“表达的符号形式和思想观念的统一,为中国式神话历史留下了书写的见证,但是探寻其根源或现实原型,则需要解读文字文本之外的文化文本”[11],这同时也宣告了文学人类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又一关键环节的对接成功。
其实,以弗莱为代表的文艺批评流派对文学人类学一派研究的影响甚大。他们声称文学作品中的叙事结构、情节意象等,都可以在流传的神话中找到原型,这与该派“文学源自神话”的一贯主张完全吻合。1987年,叶舒宪负责编译的《神话-原型批评》问世,文艺批评流派的基本观点被一一介绍到国内,这对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学派起到了基础性建设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体认到“文学的”神话观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时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使得神话俨然已经成为“虚幻”与“幻想”的代名词,进而导致神话在当前中国学术语境中的定位趋于褊狭和虚化,因此,积极倡导走出文学本位观,到文化大传统中解读神话,进而以神话的宏阔视角去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探寻华夏文明起源问题。这就使得强调四重证据法成为“神话历史学派”的显著特征之一,他们力求借助先于语言思维而存在的神话思维线索,研究那些属于语言形成以前的实物与图像,以此追溯远古时期先民的文化编码以及历史记忆。[5]
自此以后,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力倡神话不应依旧处于边缘化、破碎化的状态,也不应该甘于在民间文学课程的讲授中作壁上观,彻底打破神话偏安文学一隅局面的时机已然成熟。在叶舒宪的引领下,文学人类学领域的青年新锐们倾力研究,开始了从神话历史角度释读中国文化原典的全新尝试。可喜的是,成绩的取得显而易见,《神话历史丛书》的出版问世,成功检验了在神话历史视域下进行中国文化原型编码解读的成效,与此同时,不断积累着对神话历史理论实际操作层面的具体经验。毋庸置疑,该丛书的编撰初衷显然将治学眼光放在了更长远的未来,如何将局限在传统文学课堂一隅的神话释放出来,使其成为贯通文、史、哲诸学科的有效概念工具,引领研究者自觉超越现存的学科偏见与学术成见,从而真正反思中国文化研究问题,重新进入到中国深厚的思想和历史传统之中。[12]
《神话历史丛书》主要涵盖《文化记忆与仪式叙事》、《礼制文明与神话编码》、《断裂中的神圣重构》、《神话叙事与集体记忆》、《宝岛诸神:台湾的神话历史古层》、《儒家神话》、《韩国神话历史》、《苏美尔神话历史》等,神话历史视角新颖,文化阐释效力十足,以下择选其中三部予以简描:
荆云波的《文化记忆与仪式叙事:〈仪礼〉的文化阐释》,主要借助神话仪式理论以及四重证据法,从仪式视角对《仪礼》进行阐释研究,在文本、仪式以及器物图像的多重证据观照下,深入挖掘仪式背后所潜隐的神话原型、思维与信仰,探究玉礼器的文化象征意涵。此外还有权力在仪礼之中的渗透效力,在考察古代社会生活中礼仪功能的同时,尽可能阐释礼仪对华夏文明的符号价值。唐启翠通过《礼制文明与神话编码:<礼记>的文化阐释》关注神话、仪式与“物化”符号之间的内在联系,从知识考古视角出发,进行廟(庙)与明堂的原型解码、冠礼仪式的象征探源、“五方之民”话语模式的还原再释等研究,意在揭示被书写文化所遮蔽的仪式行为元语言以及认知编码,得出《礼记》问世乃是话语统治者借助礼制文明维护权力合法性产物的结论。而谭佳在《断裂中的神圣重构:<春秋>的神话隐喻》中,通过神话历史视角系统解读《春秋》的来龙去脉,发掘出该书是对王制神圣性的重构,其产生渊源、发生机制以及功能意义都是一种特定的神话隐喻。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王权阶层意图改变局面,于是致力于运用所有可用资源沟通天人关系,进而借助于天人合一的神性效应,重新建构神圣的王制。
从神话历史角度对中国古代原典进行文化阐释,无论是已经得到初步释读的“三礼”、《春秋》、《淮南子》,抑或后续将不断得到阐释的《吕氏春秋》、《墨子》、《管子》等,都绝非鼓吹奉行文化原教旨主义,而是探索中国神话历史的脉络轨迹。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神话历史理论同样适用于世界神话历史的解读,前述《韩国神话历史》、《苏美尔神话历史》就是最好的典例,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诸如《日本神话历史》、《印度神话历史》、《埃及神话历史》等系列著作沿着神话历史这条研究路径相继问世。文学人类学研究者正是在广泛汲取国际神话学研究最新成果之后,着眼于神话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努力从神话历史的角度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学人类学者在神话历史视域下,对传统经典文本进行重释的努力,既是对于经典文本的思考,又是对传统思维定向模式的“突破常规式”尝试,显然有意识地避开或者跳出传统经典优劣的价值纷争怪圈,摆脱既有的主观评点。我们进行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潜藏在现象之后的非经验对象,或者说无意识的东西,如果事件本身不足以揭示神话思维或者行为模式所代表的意涵,那么它自然失去了充当文化研究对象的价值意义。叶舒宪很早就注意到,中国文化的传统思维定向模式“并未随着现代文明的到来而从中国文化中消失,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惯性力作用导致了新的文化偏至现象”[13],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在神话历史视域下所开展的文本重释工作,也正是有意避开此类“文化偏至”现象。
三、“偷窃历史”的反思与“历史记忆”的回归
世界上许多族群原本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是后来在有意无意间就被“偷”走了,这就造成了部分族群没有历史的不必要误解。针对这种现象,杰克·古迪极为透彻地分析了问题所在:欧洲人自19世纪初期开始在世界各地出现,此后世界历史的建构便处于欧洲支配之下,但是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在内的其他文明,同样是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大多数文化并不缺乏过去和其他地区彼此联系的观念,只是呈现得相对简单,即便如此,很多研究者还是更愿意将这些观念置于“神话而不是历史的标题之下”。[14]时间与空间“偷窃历史”问题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反思,历史被西方接管,一度被概念化,乃至被局限在欧洲狭小的空间范围内,后来又以历史事件的形式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文学人类学者如今期盼的最理想结果在于,“不只是全球各族群的神话历史都被承认为历史,就连西方人曾经自以为是科学的历史,也照样被还原为神话历史”[15],而通过循序渐进的努力,这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目标。
不可否认,神话传说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记忆,我们可以将传说中的某些成分视作虚构的,但在很多情形下,这是由于人们自身所恪守的方法论立场以及科学观等与传说相对立使然,其与“无事件境”记忆所呈现出的情况如出一辙,因此,赵世瑜提醒我们应该反思自己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立场,不应始终将“科学观念”奉为圭臬,应当积极借鉴福柯的知识考古范式,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判断作为历史记忆的传说,哪些成分是虚构的,在什么意义上可被视作虚构的。[16]他的观点更近于后现代主义,换言之,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学实证主义并非真理阐释的唯一路径,传说和“小历史”同样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达方式,他所提及的“事实”,意同“历史的真实”,而这与“台湾清华大学”胡万川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胡万川指出,对于生活在神话传说时代的人们来说,神话、传说所要传达的都是“关于真实存在的真实叙事”,这与人们对于外界以及自身的认知度有着密切关系:传说如同神话一样,有想象的,也有真实的,而对于讲述它们的人们而言,皆是“与人的定位与认知有关的真实”,无论其中包含多少想象成分;此外,目前仍然在流传的古老神话母题,依旧是人类所关心的课题,只不过其中一些被吸收转化成了体系化宗教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传说的涵盖范畴更为宽泛,从英雄人物、历史事件到宗教感应、圣徒行谊,以至于个人灵异遭遇等皆在此列。[17]虽然部分古老的神话母题已然被转化为体系化宗教的组成部分,有些古代传说在今天亦不再流传,但是它们对于历史记忆的真实表达却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图像作为视觉诠释学与物质性诠释学的重要阐释工具,能够有效弥补文本缺失和语言表达的不足,真实还原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偏见”,进而提升对于非书写、非语言的神话信仰现象的阐释效力。安琪结合阿嵯耶观音图像、《南诏图传》中《祭柱图》等展开具体的图像叙事研究,借助于视觉符号体系,清晰再现了南诏大理国开国神话的叙事结构,也使得诸如后世一度沦为民俗景观的“社祭”传统,能够在神话历史视域中恢复其本真面貌,在南诏大理国的神话历史溯源研究中,图像遗产及其神话传说也必将成为“重新定义南诏大理国族群身份的关键要素”[18],有助于文化认同的形成。同样,口述史同样能够发挥类似于图像叙事的补缺和证成作用,保罗·康纳顿认为应该把社会记忆与历史重构区分开来,尽管两者之间能够产生互动,“即便历史学家不能根据连贯的传说,从见证人那里得到有关一个事件或者习俗的陈述,他们依然能重新发现完全被遗忘的东西。”[19]而事实也证明,那些或多或少可归入非正式范畴的口述史,都意在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活动,而这些也被视作所有社群记忆的特征。[19]
基于此,无论是赵世瑜、胡万川,还是安琪、保罗·康纳顿,他们共同启示当下的中外学人,应该将神话与历史置于同等价值层次上进行针对性研究,二者也只有从历史记忆意义的视角出发,在价值上才是平等的,传统上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已经不再完全适用于今日的学术研究。从这个意义出发,神话历史是促进历史记忆回归文化大传统的最佳选择。
结论
“神话历史”理论的提出与运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解历史与神话的截然对立,突破神话学研究的文学本位观,把神话从传统褊狭的学科概念中成功解放出来,真正呈现出其打通文、史、哲诸学科的整合优势,同时发挥出自身的文化编码与神圣叙事的方法论功能。以文学人类学者为代表的人文学科研究者所主张的大传统视域,是将自身研究置于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以及与书写传统并行的口传文化传统之中,强调一种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由此可见,追求历史记忆的文化大传统回归,掌握神话历史的话语阐释权,最终目的依然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认知与重新整合。同时特别需要明确的是,神话历史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能够助推并指引学人发掘探索华夏文明本源的“密码”所在。
[1]MICHEL DE CERTEAU,TOM CON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
[2](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丛书集成本之2624)[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钱穆.国史大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5]于玉蓉.从“神话与历史”到“神话历史”——以20世纪“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演变为考察中心[J].民俗研究,2014(2).
[6](英)马林诺夫斯基,徐大永.原始神话论[M].首尔:民俗苑出版社,2001.
[7]MIRCEA ELIADE,WILLARD R.TRASK.Myth and Reality[M].New York:Harper&Row,1963.
[8](美)张光直.中国古代青铜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9]叶舒宪.从玉教神话看“天人合一”——中国思想的大传统原型[J].民族艺术,2015(1).
[10](美)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1]叶舒宪.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J].百色学院学报,2009(1).
[12]叶舒宪.神话作为中国文化的原型编码——走出文学本位的神话观[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8-12(12).
[13]叶舒宪.文化研究中的模式构拟方法——以传统思维定向模式为例[A].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文化研究方法论[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4](英)杰克·古迪,张正萍.偷窃历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15]叶舒宪.“神话历史”:当代人文学科的人类学转向[J].社会科学家,2013(12).
[16]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3(2).
[17]胡万川.真实与想象——神话传说探微[M].台北:里仁书局,2010,自序.
[18]安琪.阿嵯耶观音图像与信仰:再谈南诏大理国的神话历史叙事[J].云南社会科学,2016(1).
[19](美)保罗·康纳顿,纳日碧力戈.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校:阳玉平]
C912.4
A
1002-3240(2017)06-0135-05
2017-02-10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6CMZ024)、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术领域文化专项项目(项目编号:16TCWH11)阶段性成果
孙凤娟(1987-),女,山东泰安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人类学、民俗学;公维军(1986-),山东临沂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