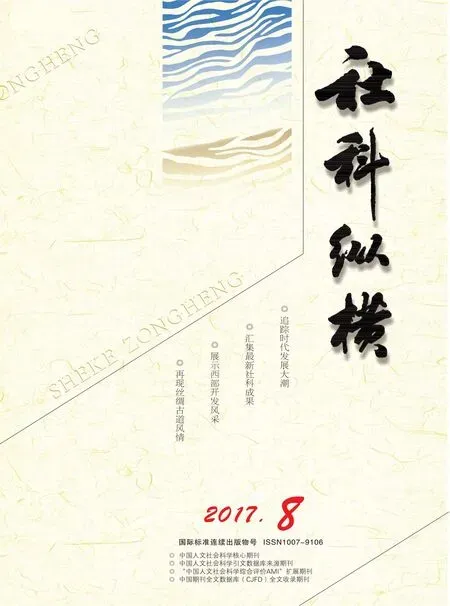《申报》与杨乃武案:近代审判公开理念启蒙的表达
陈华丽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10)
《申报》与杨乃武案:近代审判公开理念启蒙的表达
陈华丽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10)
在《申报》创刊前,国内报刊发展萎靡,缺乏将审判公开理念广为传播的渠道。“杨乃武案”与《申报》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杨乃武借助《申报》洗冤,《申报》则借助“杨乃武案”提高销量。然从司法制度角度看,《申报》在“杨乃武案”的最大成就是首次全面提出近代史上的“审判公开”,正是《申报》办报人的特殊身份、办报地点的特殊位置、言论自由的特殊背景、良好销量的助推,使得《申报》将西方“审判公开”的司法理念首次全面引进,包括对庭审不公开与阻止公众力量参与的批评,也包括对审判公开的呼吁与公众参与司法的渴望。
杨乃武 《申报》 近代 审判公开
一、为什么是《申报》首次提出近代审判公开理念?
在杨乃武案发生前,中国报业发展零散。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外国传教士主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然其主要作为传播宗教之用。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清政府禁教政策被废,教会报刊随之兴起,如1833年《东西洋考》、1861年的《上海新报》、1868年的《中国教会新报》等。然此类报纸目的都是为了宣传教义,读者群为教会成员,销量较差,缺乏酝酿“审判公开”的群众土壤。《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是英国人美查所办。美查表示办报要立足民间,尽管“夫新报之开馆卖报也,大抵以行业营生为计”,但其本意是“劝国使其除弊、望其振兴”。[1]美查的这个理念使得《申报》在中国近代萎靡的报业中迅速脱颖而出,使得其在杨乃武事件发生后,以第一时间介入。《申报》很快捋清杨乃武案的来龙去脉——一个举人被指以通奸之实、愤而杀情人之夫,经举报,罪证确凿,县官拟判死刑,举人的家人到处呼吁。举人到底有没有杀人,《申报》不敢坐实,只能持续跟踪报道,在这跟踪过程中,《申报》无意中发现中国审讯之弊——秘密听审,阻止旁听,《申报》进而逐步批评。而在报道杨乃武事件上为什么是《申报》而不是其他同期报刊作为传播审判公开理念的有影响力的媒体,主要与办报地点的特殊位置、言论自由的特殊背景以及良好销量的助推有关。
(一)办报地点的特殊位置
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国家,原本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上海在1843年开埠。外国商人的涌进让近代上海成为了商业都市,但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人与国人就“土地租赁、造房、开展贸易等方面”的矛盾开始产生。[2](P14)为了解决此问题,中英就上海地势民情,于1845年11月29日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赋予了商人租赁中国土地的合法性,“商人报明领事官存案,并将认租、出租各契写立合同,呈验用印”[3]。
近代上海的政治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其一市三治,即公共(英美)租界、法租界与华界各自治理,治权独立,界与界互不干涉,作为治权组成部分的司法审判权亦跟着独立出来,于是形成了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租界会审公廨。这是根据1869年的《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第1条“管理各国租地界内钱债、斗殴、窃盗、词讼各等案件”所制定的,“凡有华民控告华民,及洋商控告华民,无论钱债与交易各事,均准其提讯定断”,第2条则规定“案件牵涉洋人,必须其到案者,须领事官会同委员审问,或派洋官会审。若案情只系中国人,并无洋人在内,即听中国委员自行讯断,各国领事官无庸干预”。从此规定可看出,会审公廨机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审判机构,凡涉及外人利益,不管其属原告或被告,外国领事都可参审。
在各租界内的审判机关由领事法庭、领事公堂和会审公廨等组成。[4](P134)领事法庭审理作为民、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在华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领事公堂则类似行政法院,会审公廨审理领事法庭与领事公堂管辖权之外的案件。但久而久之,租界内纯属中国人间的诉讼外国人也参与观审和裁决。会审公廨所适用的法律程序与上海华界并不相同,其主要适用近代西方的法律程序,如律师辩护、陪审、公开审判,而同期的上海华界审判机关则适用重视口供、刑讯逼供、秘密审判。会审公廨制度的存在使中国丧失了部分司法主权,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是西方近代司法文化的冲击,如禁止刑讯、审判公开、律师参与、陪审。
而《申报》办公地点,就在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一定程度上,正是《申报》办公地点位置特殊,致使清政府无法有效控制,于是在对杨乃武案的报道中,《申报》可以对清政府的秘密审判、刑讯逼供进行言辞激烈的批评,如1874年12月10日头版的《论余杭案》所载“该民既已被原官刑迫,而使之再经刑迫,此事实如杜禁上控……惟望日后各官慎之又慎,无效如此办案”,类似批评可见《申报》1875年8月14日《论覆审余杭案》、1875年12月24日《书邸抄胡学政奏办理案件均须原报现供明晰声叙夹片后》、1876年2月5日《书初九日本报录杨乃武案诸件后》、1876年2月9日《再论浙绅公禀事》、1876年2月11日《书浙江诸绅公呈后》等。
(二)言论自由的特殊背景
上海租界不受官府直接管辖,为《申报》提供了言论的自由空间。通过《申报》对杨乃武案时评的作者考察,所署皆为笔名,且笔名性质天马行空,如1875年4月10日的《天道可畏》作者鹫峰老世,1875年4月12日《杨氏案略》作者湖上散人,以及其他作者如六桥主人、武林生等。这种对真实身份的藏匿一定程度上给了作者无所顾忌的写作自由,能够表达自身真实想法,从而展现不同舆论,进而在争议中借助公众的力量挖掘事件真相。《申报》对杨乃武案的报道类型包括新闻、时评、官方奏折或谕旨、民间来信,从这个类型可以分析出其目的一是传递官方声音,让公众及时了解官方态度;二则借助民间力量,向官方转达公众意见;三则通过局外人眼睛,去发现事件中新闻热点。同时,因为办报地点特殊,在洋人控制的租界里,到处是西方的自由与民主的政治氛围,这在无形中庇护了《申报》,至少未对其报道加以干涉,毕竟不符合“言论自由”。除此以外,租界当时缺乏新闻法规,“无禁止则自由”,这为《申报》在报道上取舍有度提供了保证。
(三)良好销量的助推
1873年12月24日《申报》开始报道杨月楼案,不过是富家女爱上戏子、戏子违背“良贱不得为婚”规定娶了富家女、戏子被判刑的故事,在当时这并没有什么特别此处,因彼时清朝人有等级、贵贱之分,戏子连平民都不如,但对于关注民生的《申报》而言,这是一次展现自己的良机。在杨月楼案中,《申报》立场客观,“视各方人如一,毫不偏袒”[5],这种立场实际上正是西方公平的法制观念的一次潜意识流露,其实质是站在了民意一边,从而将在上海报界崭露头角的《申报》一炮打响,为了拓宽销售渠道,《申报》采用了如下策略:(1)雇人分送或沿街道零卖,我们从《卖报歌》“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边走一边叫”的歌词中完全可以想象此场景;(2)组织家庭订报;(3)定点销售,类似我们今天的报刊亭,《申报》第二号登告“本馆新报定价每张八文,因本馆未便零星拆卖,欲于上洋各大街寻代为卖报之店……如有卖不完仍退回,本馆分文不取”,对代售点而言,这其实是无本生意,并且没有风险,导致《申报》零售店大幅扩增,包括杂货店、刻字店、烟膏铺等;(4)信局发售,类似由今天的邮局发售,通过邮寄,将销售网铺向全国。增加销售渠道的同时。《申报》还采用了适当的促销手段,如随报附送赠品,其附赠物品包括精美图片、月份牌等略带文艺又不乏实用之物。[6](P49-50)“其初创时销数为600份,三年后日销6000份,到1877年初,《申报》已在‘各省码头风行甚广’,发行量日销近万份”。[7]
《申报》作为民办报纸,良好销量意味着读者群的日趋上升,这就为杨乃武案从发酵到爆炸提供了群众基础与传播渠道,通过对杨乃武案等社会热点的追踪和报道,让读者产生共鸣,《申报》继而成为舆论喉舌,成为民间遏制权力机关的工具。
综上可观知,要让舆论能够监督司法权力,审判公开是形式与手段,民众是基础和扩散,这一点,同期报纸只有拥有广大读者的《申报》能做到。
二、《申报》在杨乃武案中关于审判不公开的批评
《申报》对杨乃武案的第一次报道在1874年1月6日,当时纯粹出于一种对桃色新闻的猎奇心理,“禹航谋生者,素以风流放宕自豪不拘”,“卖豆浆之妻,小家碧玉”,“调谑眼波,眉语相视”。
但《申报》很快发现该案的疑点,一周后以《详述禹航某生因奸谋命事案情》提出四疑,此后,《申报》分别在1874年1月15日、1874年4月18日、1874年7月25日零零散散写了三篇新闻报道,分别叙述了禹航生(笔者注:即杨乃武)自杀、禹航生非自杀、禹航生姐姐走上京控之路。案件报道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1874年12月5日所转载的《十月初九日京报全录》,其中记载了都察院左都御史广寿等的奏片,简单陈述了杨乃武家人京控一事,其中申诉的主体为杨乃武的妻子“小杨詹氏”,代理人为“姚士法”——杨乃武表弟,申诉的理由为“杨乃武乃被葛毕氏诬陷”,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有用信息,更别提公开申诉者对自己蒙冤的具体控诉理由了。于是《申报》一针见血地发现了本案疑点产生的关键,一语见地指出秘密审判之弊。
(一)批评秘密审判
在杨家人京控的第二个阶段,湖州知府锡光等四人共同审理时,1875年1月28日《审杨氏案略》是《申报》在杨乃武案中第一次对秘密审判的反对:
“余杭杨氏京控一案,已于初十日改在水利厅衙门晚堂讯问,仅提抱告进内,口供与京控呈底相符,问供后即退堂,并未提讯他人。嗣于十五日亥时,又在水利厅衙门提集人犯封门讯问,约有一时之久,严密谨慎,外间无从闻知,讯后口供亦尚难以访悉。”[8]
京控第二个阶段的第二次讯问情形,《申报》亦有刊登:
“浙省已革举人杨乃武一案曾在水利厅衙门,已覆审四次。每当审讯之时严密异常,故一切口供外人无从探悉。……至于录口供时,系龚太尊与许邑尊亲笔同录,于录罢后彼此各藏诸袖,两不阅视。故口供如何余人均未能访得,第闻此事亦尚无端绪。”[9]
从《申报》的两篇叙述可以窥见主审官本次覆审的小心翼翼,“封门讯问”,“严密异常”,甚至连录口供时,承审官员都各自掩藏证词,且不交流,以防泄露。当然,如此秘密庭审,至少可以保证如果错判或误判不被他人抓住把柄,可以防落人口实。至于判决是否能产生公信力,承审官并不是那么在乎。
而在1875年3月29日《余杭杨氏案又审》中《申报》第三次客观阐述了庭审秘密的情形:
“余杭杨氏一案,前经浙省中丞派委龚太守等公,司在水利厅衙门覆审,嗣以封印,停止本馆备列。前报兹悉龚太守现已晋省,会齐各官仍在水利厅衙门审问,惟此事严密异常,无从探听口供。”[10]
这种秘密庭审在案件交由胡瑞澜覆审后,依旧没有改变,据《申报》1875年8月2日记载:
“余杭谋夫一案,胡侍郎于上月二十一日始进行辕,计当差者共有三十余人,并设有启闭之官,每逢放水办菜时始准开门进出一次,然亦有号牌限定时刻,不得混杂稽迟也。侍郎于二十四日晚堂在辕,提讯各犯口供,因关防严密,故无从探悉。”[11]
除了庭审不公开,在当事人之间、证人和被告人之间,信息亦是不公开的。决定本案的关键证据并不是杨乃武与葛毕氏是否有奸情,而是杨乃武是否向钱宝生买了砒霜,但《申报》发现,钱宝生和杨乃武并没有当堂对质过。作为最关键的证人,杨乃武没有在庭审现场见过钱宝生。且见1874年12月8日的《浙江余杭杨氏二次扣阍底稿》:
“钱宝生乃卖砒要证,理应当堂审问,何以县主在花厅接见?且应将钱宝生解省与氏夫对质,方无疑窦,何以放令回家,仅取供结由县送府?府署问官何以不提钱宝生到省,但凭县主所送供结即为买砒实据,刑逼氏夫定案?现在覆审,甫经府宪亲提,县主方令到案,岂知钱宝生不肯到案。”[12]
此叩阍底稿为杨乃武亲写,属于直接证据,故可证明杨乃武尚未与钱宝生对质过。1876年1月11日尚书崇实等人的奏折中也提到此问题:
“况钱宝生系卖砒要证,检阅现供,系初审时仅在本县传讯一次,伺候该府向以未经亲提覆鞫,是否曾与杨乃武当堂对质,案中亦未叙及。”[13]
《申报》一见针血地发现了庭审不公开之弊,此举同时也妨碍了《申报》对案情的报道,阻碍了《申报》对案情的参与;而法庭调查不仅不对外公开,在当事人之间、当事人和证人间也不公开,此举直接剥夺了杨乃武最有利的翻盘机会。所谓只有质证过的陈述才能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在当时完全不可能体现。
(二)批评拒绝公众参与
在杨家人京控的第二个阶段,湖州知府锡光等四人共同审理时,1875年4月10日《申报》刊登了作者鹫峰老樵的来稿《天道可畏》,先叙述“听说”了的覆审两个多月的庭审情况:
“前后共审过十数堂。闻邻证人等及药材店户,均云并无此事,即葛毕氏亦已翻供,剖吐实情,竟云‘前系刘大老爷叫妇人一口咬定杨乃武,便可免我死罪,妇人因与杨某向有宿嫌,遂尔仇攀。现妇人自知万无生理,何苦害人,反结来世狱冤仇,是以翻供’等语,方谓‘从此追问究系何人毒害,可以水落石出’。然闻问官得该妇口供后,忽又加以重刑,似深恶其翻供,曾经昏绝二次,均用冷水喷醒,而妇人仍供如前。二月十三夜复又审讯,事甚秘密,未能知其究竟。”[14]
《申报》对与报馆有关的立场,用词谨慎,因不是亲历庭审,故全部用“闻”,以表明客观立场,同时对舆论也不至于误导。其中真假,由读者自己判断。
两日后,《申报》又登载了笔名为湖上散人的来稿《杨氏案略》,内容也是道听途说的湖州知府锡光等四人共同审理时的庭审内容:
“余杭杨氏覆审口供一时无从探知,顷闻葛毕氏所供,其大略谓‘当未嫁时本欲与死退婚,为杨乃武逼勒不准,以是积忿于心,因夫渐贫窘,故不能安于室,夫曾有杀妻之举,经人劝止未行,诚恐性命难保,遂起谋夫之见。以杨乃武新登桂,籍思借作护身符,故攀诬之,非真同谋也’。钱宝生亦供,药非杨姓所买,书差教我,如此供法保无他虑。县主又不加细拷问,至上省时县主新对我言‘不可翻供。若经翻供,尔必死矣’,因此含糊答应。及提杨乃武哉,问监役,又以病重不起对官云事。既如此,何得妄为攀诬?想此亦未见实情,候杨某病痊再行质审。当时各加重责,而实则杨某无病,为监役所捏造也,姑即所知者备录众鉴。”[15]
比较以上两则庭审报道,鹫峰老樵的《天道可畏》记载内容明确表明是“听说”,湖上散人的《杨氏案略》用词则较为笃定,但显然都不是二者亲历庭审旁听说得。但民间传闻是真是假,《申报》表达自己也无法判断。《申报》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允许旁听,特别是准允媒体听审,则报馆无需选择民众来稿,完全可以根据记者所闻所观来对庭审现场进行报道,即“有闻必有录”,如此又可以保持公正。
但这种对公众参与的排挤直到主审官换成胡瑞澜依旧如此。1875年7月16日第2版《申报》继续载道:
“本应将一切颠末在公堂研鞫,稗大众咸知,以解群惑。果克如是,则本馆照录其事,亦不至轻听传言矣。”[16]
《申报》态度很明确,案情始末应当在公堂呈现,此即公堂存在之价值,通过公开不仅可以消除公众的疑虑,也可以防止《申报》因听信传言对案情进行误报,一举两得。但这种批评是无力的,在1875年10月19日《申报》又载道:
“兹闻杭友述及此案,仍经杨乃武照原供招认,已经拟罪定案矣。夫此案前既翻供不认,兹何以忽照原供乎。惜乎屡次讯问各情,外人终不得而知也。”[17]
《申报》敏锐捕捉到公众参与有利于司法民主化,也有利于增加判决的可信度。中国古代立法上并没有对公开审判的支持,或者说当时的执政者完全无此审判公开的司法意识,于他们而言,秘密与否,并不是通向公正审判的路径。
三、《申报》在杨乃武案中关于审判公开的呼吁
(一)沿袭旧朝,或学西方
《申报》在刊发杨乃武家人京控的全部底稿后,为了督促当局司法公开,在1874年12月14日《申报》论述中国其实也有陪审历史:
“余闻诸先辈此厅(笔者注:即赞政厅)尚系明朝所设,今则有名无实矣。盖明制县令听讼,必延请同僚以及绅耆入赞政厅一同听之。是则公是,然后定案。尚有一人非之,则其案必须覆讯。此赞政厅之所有名也。闻国初亦尚如此,后则不知何时始废此例矣。”[18]
《申报》的评论者肯定了中国“赞政厅”的司法价值,即在明朝,具有一定地位的人如官吏与绅耆可以旁听审判,如果都认为有罪,才判决有罪,只要有一人认为无罪,则要重审。
关于赞政厅,又叫参政亭,赞政亭,“一般设在知县大堂两边,知县可在这里经常听到各里坊耆老、乡绅、告老返乡的官员等对县里各方面事情的意见”[19](P18)。甚至有学者在考察古文化遗产还能发现赞政厅在今天的踪影,“在大堂东侧的赞政厅,是知县的僚属,师爷在此参赞政务,文告、政务多在这里起草签发,门上十四个大字告诫同僚“不求当道称能吏,愿共斯民做好人”。[20](P28)
但赞政厅的功能并不等同于现代的审判开放,其并非真正的审判公开,只是部分人群可以参与政治,如耆老、乡绅、退休官员等享有话语权之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无法触及;其所谓公开并非真正的司法公开,而是一种政治监督,此乃中国古代法制行政司法不分所致。
这是《申报》在杨乃武案当中第一次领会到审判公开的正面价值,甚至在内容上,《申报》捕捉到了审判公开与陪审的某种微妙联系,即审判权要向公众开放。《申报》坚持着该意识,持续呼吁陪审的引进。在胡瑞澜接手杨乃武案后,《申报》继续表达了其对陪审的观点:
“中西之讯案也与西国异。西国之讯案无事不在公堂,在官长,且有陪审之员;在两造,又有各延请公正之人与夫律师状师。并许通国之人前往观讯,而且准令各新闻纸馆之人一同抄录。……若中国则异是。尝见中国州县衙门虽有大堂,而讯案时未见坐也。内外左右执事之人除门丁书差地保之外,未尝有人也。两造之人除阶族干证之外亦未尝有人也。讯案之地不在二堂则在客厅,除在官之役与在案之人外他人不准往观也。是以案虽重大官亦无从访问,不过全藉一己之聪明以揣测之。……故每遇讯案之时往往即求了结,故致畏人见闻、恐人议论又须费心再行审讯,不如禁人观瞻,免致多费周章也。”[21]
《申报》选择在胡瑞澜提审杨乃武与葛毕氏前夕提出西方审讯方式,并抨击中国审判之弊,其背后的深层意义应当是希望胡瑞澜覆审能改变此前秘密审判格局,尝试陪审,或者只是庭审公开,只要能解众人之疑。但《申报》此次倡议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胡瑞澜庭审依然秘密。
但是,对陪审的要求、对审判公开的提倡、对学习西方司法文化的坚持,在杨乃武案中《申报》由始至终都没有放弃。所以,在胡瑞澜维持原判、户科给事中边宝泉等人为杨乃武进行声援的同时,1876年2月11日《申报》载道:
“西国之讯案,有陪审之多人,有代审之状师,有庭审之报馆,有看审之万民。使讯此案之时,亦皆如此,则钱宝生之结何能取?沈喻氏之押何能代?吴玉崑之禀何能匿?杨乃武之罪何能定乎?中国立法何尝不善,各官听讼当在公堂。公堂者,大堂也,亦欲使百姓周知,不至令民有冤耳。且平日慎选守令,诸官亦为重视民生也。乃不意世风日下,竟至如此耶。……所以特为论列者,不过奉劝世之州县,以后如遇此大案,均遵成例,出坐大堂,秉公审讯,使合邑之人皆观听。一有舛误,必能规谏。”[22]
在《申报》看来,如果杨乃武案可以采用西方审讯方式,有陪审官,有律师,有媒体,有旁听者,则杨乃武必是无罪的,中国虽然要求承审官要在公堂庭审,所谓公堂,即向老百姓公开审判的场所,但却没有实行,尽管这并不难。
在刑部决定重审杨乃武一案后,《申报》再次表达报社对审判公开的观点:
“西国之无待刑讯者亦有故。设状师,以代两造之辩驳;设陪审,以观各人之是非;准上报,以采局外人之议论;准听审,以取众人之见闻。及至状师词穷、众证确实,而承审官即耳援乏以定罪焉,不必泥定犯人之供与不供。”[23]
然而《申报》这些口诛笔伐都没有入得官方之心,因为杨乃武案最终并没有因《申报》的呼吁而公开审判或者引入陪审,连媒体旁听也没有实现。尽管陪审制当时在西方早已践行。公元前6世纪,梭伦就在古希腊建立了赫里埃——陪审法院,只要是雅典公民就具有成为陪审员的资格,可参与案件审理。但在19世纪的中国,陪审这种民主的词汇对中国官员乃至中国公民,都是新鲜的。
(二)允许公众旁听
1870年左右的清末王朝举步维艰,一方面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已显得精疲力尽,另一方面又要继续面对西方对中国冷热暴力的攻击,租界的扩大化、会审公廨这种特殊司法机关的逐渐制度化,国人开始看到中国审判与西方审判的明显区别:中国式审判原、被告须下跪,而英国不用;如果原被告是外国人,公众可以旁听,而租界以外的中国式审判,公众不得旁听;西方有辩护律师,国人没有;国人注重口供,西人注重形成逻辑严谨的证据链;西人有陪审,国人根本没听过“陪审”,等等。自由与约束,民主与专制,理念的差异使国人犹如醍醐灌顶,西方民主的司法文化不自觉侵入,潜移默化,以至在杨乃武一案中,《申报》一直纠结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能旁听,非但公众不能参与旁听,媒体亦不得参加庭审活动。
当《申报》于1874年12月7日、1874年12月8日接连两天刊登杨乃武家人二次扣阍原呈底稿后,其于1874年12月10日载道:
“此案众心为之大疑,所求于各上司者,于覆审之际,毋为同僚情分所惑,须彻底研鞫,使水落石出。若果系案犯图脱其罪,则宣示其细底,以期释解群疑。设使查明为冤案,务必体恤民隐,使知虽为官者,犹必负罪,以昭公正也。本馆屡经说及刑讯之弊,今犹不惮质言厥大事,盖令藉此大案,以明刑讯之理,实不枉也。夫临民各父母官,内自由廉明公正者,顾人性不一,百官之内,亦有其秕必矣,任之以刑讯之权,小民既每难于上控。故遇肆私之官,而犯人辄迫于忍屈吃亏而已。案己类是,而不闻于外者,思之不免一叹……惟望日后各官慎之又慎,无效如此办案,民定谓于共再世,龙图复生也。”[24]
《申报》认为,既然公众对此案已生疑,不管杨乃武是否有冤,应当及时向公众公开,公众有知情权,必须“宣示其细底”,使公众了然于心,更劝承审官不能通过刑讯是非不分、黑白颠倒。
当然,《申报》关于审判向公众公开的建议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是故第二次京控所换来的覆审依旧维持杨乃武死刑的原判,杨家人再次伸冤,上层给的回应《申报》转载在1875年6月7日的《谕旨预录》,“着派胡瑞澜提集全案人证卷宗,秉公严讯确情,以期水落石出”[25],这是胡瑞澜在本案当中的第一次出场。
当时,《申报》和公众在知道杨乃武案可以再次覆审时,对胡瑞澜寄予了希望,是故在确定开庭日期前,1875年7月26日的《申报》继续呼吁:
“此搬审案不同往昔,定期水搭石出,俾此狱得成信谳也。但不知临讯之时,准进看与否。若又如从前秘密,则各犯口供,外人仍难探悉,即本馆亦无由登录,以供天下人之览。而天下人之疑信,约莫定其是非,是则本馆之所重虑也。”[26]
《申报》希望胡瑞澜覆审能向公众公开,至少向媒体公开。如果媒体能旁听,那么基于新闻人的关注事件、尊重事实的职业要求,做到“有闻必录”,那么公众在判断时至少可以进行参照,不至于无端揣测,进而干扰审判。尽管“定纷止争”是司法的目的,但公平才是司法的追求。而公平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这种判断不能以法官一人说了算,也不是法律条文说了算,它需要考虑公众的情绪与公众的接受程度,这同时也是诉讼产生“既判力”背后的价值支撑。“既判力”要有权威性,除了当事人遵守,还包括公众的认可。这也是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审判公开”的深层意义,将审判和犯罪证据公开,公众才会信服,权力才能被制约。
胡瑞澜依旧维持原判。
直到刑部决定重审,旁听依旧没有实现。于是《申报》感叹,“噫益信听讼之不易、人情之难测矣”。[27]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审判公开理念的第一次系统表达,显然是借助杨乃武事件。并非1873年只发生了杨乃武案,而是《申报》倾尽财力、人力、物力,并顶住压力,全面对杨乃武案进行了报道,从而使得审判公开在1873年至1877年间得以细小的脚步开始在中国行走,陪审权、旁听权等民主性权利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特别是销售量的上升使得《申报》读者日渐上涨,民主权利的传播在不可预期中越走越宽。倘没有《申报》在这标志性的冤案中持之以恒地努力,也许中国的审判公开之路,会滞后多年。是故,杨乃武案与《申报》乃至与近代审判公开,都是相互相成、相惜相生的关系。
[1]论本馆作报本意[N].申报,1875-10-11.
[2]姚远.上海公共租界特区法院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1845年11月29日上海《土地章程》第1条。
[4]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C].上海:上海书店,1984.
[5]本馆劝慰香山人论[N].申报,1874-1-21.
[6]庞菊爱.跨文化广告与市民文化的变迁[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7]陈璇.被忽略的“上海书写”:早期《申报》[C].所载词人词作研究[J].社会科学,2010(11).
[8]审杨氏案略[N].申报,1875-1-28.
[9]续述杨氏案略[N].申报,1875-2-11.
[10]余杭杨氏案又审[N].申报,1875-3-29.
[11]审余杭葛毕氏案杂闻[N].申报,1875-8-2.
[12]浙江余杭杨氏二次扣阍底稿[N].申报,1874-12-8.
[13]光绪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京报全录·刑部尚书崇实等奏折[N].申报,1876-1-11.
[14]天道可畏[N].申报,1875-4-10.
[15]杨氏案略[N].申报,1875-4-12.
[16]审案传闻[N].申报,1875-7-16.
[17]问杨乃武案已定[N].申报,1875-10-19.
[18]论听讼[N].申报,1874-12-14.
[19]杨学军主编.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10)[M].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
[20]李丁富.老百姓经济学——温州人经济发展启示录[M].上海: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21]论中西讯案之异[N].申报,1875-6-11.
[22]书浙江诸绅公呈后[N].申报,1876-2-11.
[23]论刑讯[N].申报,1876-3-14.
[24]论余杭案[N].申报,1874-12-10.
[25]谕旨预录[N].申报,1875-6-7.
[26]余杭葛毕氏案提讯有期[N].申报,1875-7-26.
[27]余杭大案[N].申报,1876-12-19.
D929;G219.29
A
1007-9106(2017)08-0097-07
* 本文为2016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6BXW008);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诉权概念史”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6FFX034)。
陈华丽(1985—),女,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讲师,华南理工大学2016年访问学者,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