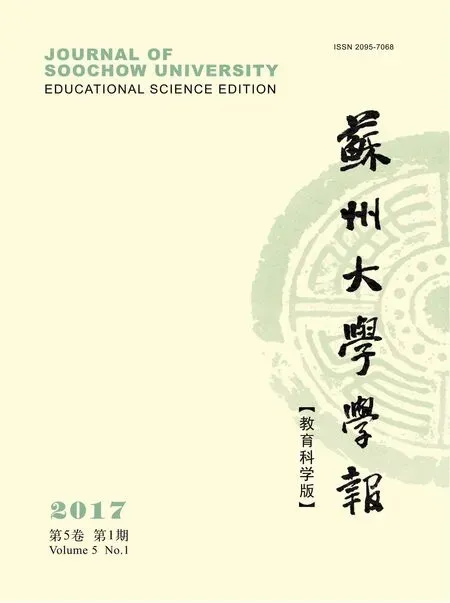临终关怀的整合模型:精神、心理与生理的关怀
李永娜范 惠李欢欢陈俊峰曹文群时 勘*
(1.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学系,北京 100872;2.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 200040)
临终关怀的整合模型:精神、心理与生理的关怀
李永娜1范 惠1李欢欢1陈俊峰2曹文群2时 勘1*
(1.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学系,北京 100872;2.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 200040)
人们在生命的终点不仅要应对身体上的痛苦,而且都会产生恐惧、焦虑、抑郁、无助等许多心理变化,也会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临终关怀可以让临终的人舒适、宁静、详和、满意地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临终关怀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都是围绕满足临终之人的这些需要展开的。在已有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精神、心理与生理关怀的整合模型日益受到大家的重视。同时,这个模型扩展了临终关怀的对象,包括了临终者及其家属和医护人员。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临终关怀实践中尝试实现整合模型的观点,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关怀对象的心理与精神需求。临床实践中通过生理疼痛的管理措施减轻临终者生理上的痛苦,通过倾听陪伴、建立联结、鼓励互惠的方法缓解临终者的心理焦虑;同时采用教育培训和团队支持等方法对家属和医护人员进行心理支持。当然,临终关怀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的综合领域,需要有更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们共同努力,来解决理论和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临终关怀;临终照顾;精神性;心理照顾
一、国内临终关怀的研究概况
临终关怀作为一种思想以及个体的实践活动由来已久,但以专业组织机构的形式进行临终关怀活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西瑟莉·桑德斯(Cicely Saunders)博士在伦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医院,临终关怀运动由此在英国及世界上的其他几个国家(如美国)开展起来。[1]20世纪80年代,临终关怀的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天津医学院在1988年成立了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标志着我国临终关怀研究与实践的开始。[2]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临终关怀的理解也在发生着变化:从开始对病人单纯的身体照顾到后来的生理、心理、社会、精神需求的关心;从只关注临终之人到关注他们的家属。现在很多研究者都同意,临终关怀是对临终病人及其家属进行的全人护理,包括顾及并尽量满足病人及家属所有的生理、心理、社会和精神的需要;关怀的过程要一直持续到丧亲悲伤阶段,目的是使病人及家属拥有最高可能的生命质量。[3]中国的临终关怀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但也涉及了其中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本研究首先从不同的角度对发表在核心期刊中有关临终关怀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进行了探索,以便把临终关怀中的心理和精神性需求深入探索下去。
(一)临终关怀的东西方比较
1.东西方临终关怀研究的差异
有国外调查显示,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国家的“死亡质量”最高,而中国则位居倒数几位。[4]这和临终关怀起源于英国并在西方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不无关系。国外的临终关怀事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有大量相关理论和实践,各方面较为成熟和完善。相比较之下,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起步晚,发展滞后,且质量不高。张鶄等对京津沪三地社区老年人的临终关怀服务需求进行调查,发现只有34.1%的老年人了解临终关怀知识。[5]相比之下,澳大利亚2011年的死亡人口中,有高达70%的人享受到了临终关怀服务[6],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从数量来看,我国13亿人口,全国只有百余所临终关怀机构,这其中除了独立的临终关怀医院外,还包括普通医院的临终关怀病区。而美国的人口是我国的四分之一,却拥有数千所专业的临终关怀机构。[7]从人员来看,我国临终关怀的实施者主要是医护人员,数量不足并且多数未接受过临终关怀的专业训练,相关知识较为缺乏。而国外的临终关怀实施者除了受过专门训练的医护人员外,还有心理学家、神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工作者以及广大志愿者。从服务环境和设备来看,我国的临终关怀机构多依托医院而建,病房环境差强人意,缺乏隐私保护以及配套的家属陪护服务设施,设备也较为老旧。[8]对北京2所登记注册的临终关怀机构的调查研究显示,我国虽然提供心理疏导咨询服务,却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关怀室”和“谈心室”。[9]而发达国家的临终关怀机构服务全面,设施和病房布置都很温馨,可以让临终患者感受到家的温暖。除此之外,政府参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国内的一些调查研究显示,政府在临终关怀事业上的投资有限,有些设在医院中的临终关怀病房需要靠医院的业务来维持运营,这严重阻碍了临终关怀在我国的推广普及。而很多西方国家把临终关怀纳为公共卫生事业的一部分,政府大力支持和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
2.传统文化对我国临终关怀的影响
对中国人来说,临终关怀是个舶来品。从1988年天津成立第一所临终关怀机构以来,临终关怀在我国逐渐开展,但发展并不均衡。为数不多的临终关怀机构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根本没有临终关怀机构,很多人甚至听都没听说过。高茂龙等人对北京市社区老年人的调查显示,临终关怀知晓率仅为22.1%。[10]在实际临终关怀工作中,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家属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并不愿意为临终患者实施临终关怀。究其原因,一方面,对医护人员来说,将病人从强行治疗状态转入临终关怀状态,意味着治疗失败,这对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来说,是最大的挫败感体验。郑悦平等人的研究显示,医护人员虽然能接受病人死亡这一自然规律,但只有20.6%的人表示“病人快要死去时我愿意告诉他”[11]。王小曼等人对肿瘤医院护士的临终关怀态度的调查研究表明,大多数护士认为自身临终关怀知识欠缺。[12]当医护人员缺乏与临终患者进行交谈的技能时,就不可能实施高质量的临终关怀。另一方面,从家属的角度来看,对病人实施临终关怀意味着放弃治疗,而他们往往不愿意接受家人即将离世的事实。库布勒·露丝说:“家属往往比病人本身更难接受死亡的事实。”尤其是当临终患者是老年人时,作为子女,受传统孝道影响,更加不愿意对患者进行临终关怀,明知治疗无望,也要竭尽全力延长患者的生命,并且往往会要求采取过度医疗的方法和手段,以表达自己的孝心,而这本身可能会加重患者的痛苦。他们没有意识到,让患者有尊严地度过人生的最后一程,享受家人爱的关怀,提高生存质量,才是真正的孝道。
上述现象与中国自古以来固有的死亡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说明我国急缺与现代文明相适配的死亡教育。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老龄化的加剧,对临终关怀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刘丹丹等对梅州市社会群体的临终关怀态度进行调查发现,55.1%的人认同临终关怀是目前临终者离世的最佳途径,其中患者和家属较普通群众而言,对待临终关怀态度更为积极。[13]董晓梅等人对广州市市民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医护工作者和高学历人群对临终关怀的知晓率较高,同时,多数市民赞成开展临终关怀服务。但是,在接受过临终关怀服务的患者家属中,赞同率仅为64.2%,这说明我国目前的临终关怀服务质量和人们心中的理想情况有差距,也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14]如果能针对我国国情,全民开展死亡教育,提高民众临终关怀的意识,同时加强对医护人员的相关培训,势必能建立起专业的医务工作者队伍和强大的志愿者队伍,为我国临终患者提供高质量的临终关怀服务,让他们在温馨祥和的氛围中体面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二)对重病儿童和老年人的临终关怀
1.儿童的临终关怀
随着卫生水平的提高,世界各国儿童的死亡率大幅下降。但是,仍然有许多疾病严重地影响到儿童的生命质量。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超过16万名儿童被诊断为癌症,约9万患儿因此死亡。[15]中国每年新增的儿童癌症患者可能达6万~28.8万。[16]除癌症之外,因艾滋病、先天畸形、神经系统病变等疾病死亡的儿童也不在少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中国有至少40 000名艾滋病儿童。[17]由此观之,针对儿童的临终关怀服务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都有着迫切的需求。在国外,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儿童临终关怀机构,如苏格兰东部的“瑞秋之家”和南部的“罗宾之家”,英国的儿童收容所协会、儿童姑息治疗协会,美国的儿童宁养中心,等等。在中国,仅有一家专门的儿童临终关怀医院,即2009年成立、位于长沙的和英国联办的“蝴蝶之家”。[15]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表明,针对新生儿的临终关怀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疼痛管理及舒适护理,包括提供安静、舒适的病房环境,音乐疗法、提供舒适的体位和治疗性抚触,维持身体清洁干燥,停用一切有创护理操作,给予镇静和止痛药;帮助父母为患儿实施临终关怀护理,如温柔的爱抚和拥抱,保留患儿遗物等;提供家庭支持,减轻父母伤痛。[18]稍大龄一些的儿童,由于已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但对死亡的认识又不够清晰,因此,更加需要重视和关怀。研究表明,娱乐能使儿童重拾自信和自尊,帮助儿童应对焦虑和悲伤。[19]因此,针对非新生儿的儿童的临终关怀不可忽视娱乐的作用。除此之外,因为儿童的离开比老人的离开更加难以接受,应尤其重视对家长的关怀和支持,如引导其进行悲伤疏导,保留儿童的遗物,或捐献儿童的可利用器官,等等。
2.老年人的临终关怀
儿童作为临终患者毕竟是少数,我国81%以上的临终患者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此,对老年人的临终关怀成为重中之重。[20]17-27在内容方面,主要针对不同患者的病症和现状进行关怀和护理,如有创治疗和内置医疗器械(如导尿管、引流管)的处理,疼痛的控制,呼吸和睡眠障碍的改善,等等,主要是为了让老年患者尽可能地感觉舒适,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21]薛静等对22例高龄临终患者的临终关怀体会进行总结,发现所有患者均平稳而有尊严地度过临终期,相对舒适地接受死亡,全部家属对护理工作表示尊重和感激,心理应激情况明显减小。[21]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患者本人想要放弃治疗,而家属尤其是子女怕背上“老人临终前都不愿意给治疗”的舆论压力而不愿意进行临终关怀,医生也往往会顺着家属的意思,继续给老人强行使用各种医疗手段延长生命,老人的尊严却被严重忽视。这说明针对老年人的临终关怀首先要从人们的认识上改变观念,其次才是护理手段和内容的改进。
(三)临终关怀与宗教文化
1.临终关怀在西方宗教中的缘起
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临终关怀中的应用历史悠久。最早记录的宗教徒从事临终关怀的文字是公元260年罗马帝国的主教狄奥尼修斯书写的复活节信札,其中详细描述了基督教徒如何不顾自身安危,治疗和照顾感染瘟疫的病人,甚至因此染病,牺牲自己生命的情形。中世纪以后,在基督教的支持下,英法等国家出现了临终关怀医院的雏形。而桑德斯博士创建的第一家现代临终关怀医院的基本理念—“你是重要的,因为你是你,你一直活到最后一刻,仍然是那么重要,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安详逝去,但也尽一切努力,令你活到最后一刻”—也与基督教密不可分。从临终关怀在西方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提供临终关怀的机构大多具有基督教背景。在基督教的生死智慧中存在三个基本概念:上帝创世说、原罪救赎说和末日审判观。相对应地个体的生命有三种:肉身的生命、灵里的生命和永远的生命。死亡也有三种:肉身生命的死、灵里生命的死和末日审判后堕入地狱永远的死。对于基督徒而言,死亡不是结束,而是更好的复活之路。总的来说,在基督教文化中,人是借助神灵(上帝)的力量,通过死这一赎罪形式,进入天国,永享福乐。因此,在临终关怀中,信仰基督教的患者及其家属,较少地感受到焦虑、愤怒、抑郁和孤独等负面情绪,平静地接受死亡的到来。[22]
2.我国的宗教文化与临终关怀
与西方信徒不同的是,中国人对神灵的依赖基于敬畏感而非罪恶感,“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这和西方宗教有着本质区别。除基督教外,对中国人影响较大的宗教还有佛教和伊斯兰教。佛教认为,色受想行识五蕴皆苦,一切皆为虚幻,死亡不仅不可怖,反而是从人世苦海的解脱。通过称颂佛号等仪式性的行为,人在死后通过佛菩萨的接引,可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信仰佛教的临终患者及其家属,对死亡也较为看得开,认为死亡只不过是这一轮生命的结束,同时也是下一轮生命的开始,众生“生生于老死,轮回周无穷”。[23]伊斯兰教的生死观以及临终关怀的形式和内容主要是由其前定观、平等观和“两世吉庆”的思想所决定的。穆斯林一般都较早地接受了死亡教育,珍惜生命,努力生活,宁静坦然地对待死亡,接受死亡。除此之外,伊斯兰教临终仪式中的信仰关怀和情感关怀,对临终患者及其家属更平静地接受死亡也起着重要作用。[24]尽管不同的宗教教义对死亡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各大宗教所倡导的慈悲、博爱等精神在临终关怀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实践中,如果能善用宗教文化的力量,对临终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精神和心理的关怀和抚慰,无疑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四)临终关怀中的管理与政策问题
1.临终关怀的保障方式
临终关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其发展和推广需要各方面的参与和支持。国外临终关怀的研究表明,要想提高临终关怀的普及率和质量,往往需要政府和民众共同积极参与。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大对临终关怀事业的资金投入,加强对民众的死亡教育,都有利于建立完善的临终关怀制度,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王宇等通过对澳大利亚慢性病患者临终关怀政策研究发现,澳大利亚早在1994年就出版了《澳大利亚临终关怀标准》,该标准每年都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以适应时代需要。其政府也制定了完善的临终关怀服务框架,投入了大量资金。调查显示,2012—2013年,澳大利亚政府在慢性病患者的临终关怀服务上共投资近2 500万澳元,这极大地促进了澳大利亚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6]在美国,多数临终关怀照料由医疗保险提供,相比之下,我国的临终关怀多数还需要自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临终关怀在我国的顺利推广。从民众的角度来说,提高临终关怀的意识,认识到服务临终患者就是服务自己,建立志愿者和义工队伍,自发捐助,也能很好地促进临终关怀事业的普及,从长远来看,每个人都将成为受益者。
2.针对安乐死的态度问题
与临终关怀紧密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安乐死。安乐死是指为解除病人无法忍受的肉体痛苦而采取的一种结束生命的行为。二者相互联系又有不同。[25]首先,二者的宗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提高生命的质量。其次,二者的服务对象也有很大重合,都是身患重症、治愈无望的病人。最后,采取的手段也类似,不过度治疗,减少医疗资源的消耗。不同的地方在于,临终关怀更看重病人生的质量,而安乐死更看重病人死的质量。临终是每个人都将面临的阶段,但未必每个临终者都适合被实施安乐死。在法律和伦理面前,安乐死仍面临着较多争论,而临终关怀则在各个层面都是被接受和欢迎的。但二者并不是对立关系,有些病人在临终关怀的后期,如果仍有较大的身体上的痛苦,安乐死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因此,重点在于如何找到临终关怀和安乐死的融合点,共同提高病人的生命质量,使其在活着和死去的时候都更加有尊严。
(五)小结
临终关怀运动在西方国家开展的时间比较久,其成果和经验可以成为我国学习的重要资源。虽然临终关怀被介绍到中国的时间不到30年,但从前面的总结中可以看出,相关的医护人员和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临终关怀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他们介绍了西方主要国家的研究与实践,从存在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角度探讨了具有中国特点或者说适合中国文化、传统习俗的临终关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讨论了不同群体的临终关怀的差异,尤其是对儿童和老年人群体有更多的思考。另外,他们还从宏观政策、法律法规、机构制度等方面考察了临终关怀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法。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国内的学者将临终关怀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思考,谈论了不同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等关于临终关怀的相关内容以及对临终关怀实践的启示;还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来阐述中国文化是如何理解临终关怀的。虽然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理论思辨的水平上进行的,但也有少数学者开始进行一些实证的研究,例如调查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临终关怀服务的需求等。
临终关怀需要有不同训练背景的多学科人员的努力,但目前国内好像只有受过相关医学训练的人在进行临终关怀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因此,囿于从业人员的专业背景,临终服务的主要内容还是更强调生理疼痛的管理和提供适合的场所。这些帮助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临终者的生命质量,而要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就需要考虑临终者除了生理需求之外的其他需要,例如心理上的需要和精神上的需要。
二、临终心理和精神关怀
(一)临终心理关怀的理论研究
1.我国临终心理关怀研究的发端
临终心理关怀是整合的临终关怀模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心理学本身的繁荣,在心理障碍和心理治疗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成果,这些成果也比较容易被应用到临终关怀中。而研究者们要讨论的问题可能就是临终关怀中是否存在特殊的心理问题。有人指出,临终之人的心理需要可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确定感、如何了结自己曾经耿耿于怀的事件、感觉自己是家人的负担、对采取何种医疗方式及生活结构的控制感、面临死亡所带来的孤独感、不放心亲人的生活、未了的心愿等。[26]177-185徐云等人回顾了临终关怀中的心理支持系统,分析了国内临终心理关怀的不足。他们认为国内从事临终关怀的人多是医学出身,没有受过正规的心理学训练,由此导致的问题首先是对心理关怀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其次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很好地处理病人的心理问题。[27]临终之人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死亡恐惧,因为文化传统会影响到死亡恐惧的过程和具体的表现形式,所以相关人员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探讨临终关怀中死亡恐惧的特点。研究者认为,临终关怀不仅涉及病人,还涉及关怀服务的提供者和病人家属。张秋霞在讨论临终关怀中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就谈到了病人、医护人员、家属的心理健康。[28]2014年4月,在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倡议下,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上海市社区卫生协会、上海市癌症俱乐部等联合举办了“临终关怀(舒缓疗护)伦理与实践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巴西、伊朗等国家的近400名专家学者讨论了世界及中国的临终关怀和舒缓治疗的现状与挑战。会议强调要形成包括生理和心理关怀等多维度的人性化的临终关怀模式。[29]
2.临终心理关怀的干预方法和策略
以上研究虽然都提到了临终心理关怀的重要性,但均属于较概括的论述。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谈到了相对具体的问题,即讨论临终者的内隐自尊修复。内隐自尊指的是无意识的自动化的自我评价,临终者在经过疾病的折磨,面临死亡的关头往往会产生一些不合适的自我评价。临终心理关怀可以针对不同病人的内隐自尊的缺陷进行干预。[30]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指出具体的干预方法和策略。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有越来越多从事临终关怀的人开始意识到临终心理关怀的重要性,指出临终关怀不能只是关注临终者的生理痛苦,还应该帮助他们面对并解决相关的心理问题。并且,临终心理关怀的范围不能只局限于临终之人,还应该涉及他们的家属以及与此有关的工作人员。但是,目前研究者对临终之人的心理需要仍然认识不足。有人谈到了死亡恐惧及其他的心理问题,可是都很少是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死亡恐惧可能是很多人会面临的问题,但根据伊丽莎白·罗斯的理论,在走向死亡的最后过程中,人们需要经历否认、愤怒、讨价还价、绝望和接受的心路历程。死亡恐惧会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个体之间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对死亡的接受程度不同,经历这些阶段的进程也不同,从而导致的心理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更多有心理学背景的人来关注这个领域,从理论上来界定临终关怀中的心理问题是什么,并提出相应的可行方案。心理学研究者在从事临终关怀的相关研究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比较难接触到临终的病人。这个现实的问题往往让很多人知难而退。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倡导心理学与医学背景的人合作,双方可以结合前者的专业知识优势以及后者的临床获得被试优势,共同关注临终关怀过程中的心理问题。[31]
(二)临终精神性关怀的探索层面
面对死亡,心理不安可能不是最主要的煎熬,心灵或者精神上的拷问往往是更大的挑战。国内虽然有人讨论到宗教与临终关怀的关系,其中会涉及精神方面的问题,但并没有多少人直接来讨论临终的精神关怀。这方面在国外有很多的积累,学者们从精神关怀的各个层面进行了讨论。
1.“精神性”“宗教性”与“幸福感”
要研究临终精神关怀,首先需要明确精神性这个概念。大家之所以会对精神性有不同的理解,是因为精神性的含义会随着文化的发展变化而改变。人们经常会混淆“精神性”“宗教性”“幸福感”这三个概念。通过文献综述,可以对这三个概念有更清晰的认识。宗教性指的是参与传统宗教的特定信念、仪式和活动。世界上流传比较广泛的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对传统宗教的信仰和参与相关的宗教仪式与活动,都可以看作是宗教性。宗教性与精神性不是同义词,而只是精神性的一种形式。精神性是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人都有的一种主观体验,与人们对自己的核心信念与价值以及人活着的终极意义的理解方式有关。精神性包括了人们寻求关于生命、疾病、死亡的意义等终极问题的满意答案的需求。学者们对精神性的理解各不相同,可能正是因为不同的理解才使他们倡导不同的对待病人的方式,从而可以适应不同病人的需要。幸福感也是一种主观体验,它是在特定情境中个体如何知觉与感受自身状态的主观情感体验。幸福感是在特定情境中,对自己生活的某一方面的主观感受。对于一个临终病人来说,幸福感和不幸福感可以同时存在。例如,癌症晚期病人如果可以得到家人与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会产生幸福感;但同时又会因为自己受到病痛的折磨而觉得不幸福。幸福感产生的条件限制性特点,对于临终关怀实践有重要的意义。有研究者提出,他们正在寻求幸福感的一个特定的方面,即精神上的幸福感。当人们的宗教性和精神性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自己的经验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从而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获得希望以及内心的和谐与平静。
2.精神性的测量方法
科学研究很难对抽象的概念进行探讨,抽象的概念必须要转换成操作性概念,才可以被用到实证研究中去。概念的操作化指的是从具体的行为、特征、指标上对变量的操作进行描述,通常包括对抽象概念的测量。主要有四种方法被用来测量精神性。第一种方法是确定有哪些与精神性有关的问题。研究者会采用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来评估精神性对个体的重要性和个体拥有的或者可以接触到的关于精神性的资源。第二种方法是对精神性和宗教性的直接测量。这些测量工具起初不是专门为临终关怀的目的设计的,而是讨论精神性和宗教性与得某种疾病的风险及存活期的关系的。第三种是采用叙事与传记的方法,它与第一种方法类似,都是关于精神性对个体的重要性的讨论。不同的是这种测量采用的具体形式不是开放性的问题,而是个体的叙述或者人生故事。叙事的方法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看到在个体的整个生命中精神意义的追求与理解是否发生了变化。第四种方法是特定范围方法,即将精神性看作生命的一个独立的方面,或者是在评价生命的每个方面的时候都考虑到精神性的问题。只是采用这种方法开发的测量工具很少被应用到临终精神关怀的研究中。
3.精神需要与精神痛苦
除了精神性的概念和测量外,还有研究者关注的是精神需要和精神痛苦。精神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不同国家文化的影响。例如,美国的研究者更多地会从宗教的角度来描述精神需要,他们列出的精神需要中,可能与精神性有关的只有一小部分,如意义、生命的目的与价值、内心平和与自然的体验等。而英国的研究者更多从“共同人性”的角度来描述精神需要。有研究提出了六种精神需要:有时间思考、有希望、处理无法解决的问题、为死亡做准备、自由地表达真正的感受和讨论重要的关系。[32]而在英国牧师的临终和舒缓照顾标准中,精神需要是这样界定的:探索个体的意义感和生命的目的;探索与生命和死亡问题有关的态度、信念、想法、价值及顾虑;通过鼓励个体回顾过去来肯定生命的价值;探索个体关于自己和家人的现状与未来的希望和担忧;探索人为什么要面对死亡和受苦的问题。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精神需要可能具有个体差异,比如病人和照顾者可能有不同的精神需要。有研究表明,有的从事临终关怀工作的员工是不太愿意讨论关于精神需要的话题的。因此,为了与病人进行良好的沟通,照顾者应该熟悉一些沟通的技巧。精神痛苦在临终关怀的实践中也经常可以观察到,对于造成精神痛苦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死亡过程中的寂寞感,有人认为是死亡过程中自我同一性的变化,有人认为是人生的缺憾,即生活并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样,而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自己对生活的改变已经无能为力了。美国有研究认为精神痛苦是关于死亡的思考造成的,主要是想到自己至死也没有得到上帝或他人的原谅。精神痛苦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自杀,所以临终关怀可以通过让病人讨论疾病的精神意义来处理他们的精神痛苦。
4.精神干预及其理论模型
一些研究还探索了精神干预问题,即在对精神性需要进行测量的基础上,如何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病人的精神性问题,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干预有两种,一种是问题干预,另一种是促进干预。但是,目前讨论干预的有效性的研究还很少。为了在临终关怀的实践中包含精神性的关怀,研究者们提出了临终精神关怀的理论模型,将精神性看作是临终关怀的一个根本维度。从总体上看,有的理论侧重概念解析,有的侧重工作人员的培养,有的侧重从人的整体性角度讨论精神性的作用,有的侧重倡导通过多学科的合作来满足病人的精神需要,还有的侧重从组织管理和发展的角度讨论在制度建设中涵盖精神关怀的要求。这些理论模型的提出,可以使人们对精神性和精神关怀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为临终关怀的实践提供可以依据的理论框架。
5.精神关怀的技能要求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临终关怀中精神关怀的重要性,但如何提供病人需要的精神关怀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是提供精神关怀所需要的技能。有人提出,主动和热情的倾听技能是必需的,在倾听的时候要能够识别病人是否谈到对自己所受折磨的忧虑,是否认为自己成了他人的负担或者被所爱的人抛弃,是否对一些未完成的事情感到遗憾,以及是否害怕孤独地死去。其次就是陪伴的技能。工作人员有时候可能要突破自己的职业限制,以朋友或者其他的身份来与病人进行精神需要的交流。另外,与病人一起祈祷、沉思、冥想,可以帮助病人想明白意义追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题。更高级的技能包括在病人要求的任何环境中能进行顺利交流。当然,要提供好的精神关怀,所需要的能力可能不止以上所列的这些,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可能也有所不同。其次是如果要培养合格的工作人员,有哪些培训的要求。第一个要求当然是要识别病人有哪些需要并且知道如何去满足这些需要;第二个要求是提供实践的机会,让受训的工作人员可以找到与病人相处的最自然的方式;第三个要求是工作人员与病人可以组成小组来讨论人生意义的问题;第四个要求是有经验的从业人员可以帮助新人,传授有用的工作方法;第五个要求是相应的机构中含有此类的培训项目。最后,应该有一套标准来评价教育和培训的效果。目前,在英国和美国已经建立了几套标准,这些标准有的比较概括,有的相对具体,但都是在各自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三)临终精神关怀的元分析研究
我国香港的一些研究者曾对临终精神关怀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临终精神关怀包括如下几个主题:精神性、精神需要、精神痛苦、精神关怀、精神关怀的促进和阻碍因素。[33]这些研究主要从病人和工作人员两个视角进行总结归纳。
1.有关病人的精神性研究
在关于病人的研究中,研究者不会直接使用“精神性”这个概念,而是让病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将精神性理解为与自我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自然和音乐的关系以及与上帝或者更高级存在的关系。大部分的文章会提到希望、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病人会对精神性和宗教性进行区分,有人报告即使面对死亡也不想被迫去信仰某种宗教,也不想听到别人对自己的宗教信仰问题说三道四。关于精神需要,有几篇文章直接进行了探讨,提到了完成未竟事业的需要、参与和控制的需要以及积极的人生观的需要。相比较而言,对精神痛苦的描述就没有精神需要清晰,很多文章中会将精神痛苦与生理、心理、社会、经济方面的痛苦混合在一起。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不确定感等),还有其他的消极感觉如无望感、无助感、空虚感、抑郁以及失望、自我和关系与意义的丢失等。关于精神关怀,病人们关心的是精神关怀的方式、他们与工作人员的关系、沟通以及沟通中的困难以及谁应该来提供精神关怀。病人们觉得会影响精神关怀的一些因素有时间和时机、友好的精神性环境、思考、教育、训练和意愿等。
2.有关工作人员的精神性研究
关于工作人员的研究中也显示,工作人员和病人一样,觉得界定“精神性”是比较困难的,他们也将精神性理解为各种关系,如与自我、他人、自然与音乐以及上帝的关系。工作人员在讨论精神关怀的时候,更多会提到精神关怀的方式,以及如何将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强调与病人建立一种相互信任、亲密的、有意义的关系,主动倾听病人讲述的故事,并且与病人进行互惠的分享。他们认为如果将自己的信仰与职业生活相结合,不断反思自己的精神状况,并且愿意花时间去倾听,再加上团队的支持,那么就可以提供给病人较好的精神关怀。但是,一些组织和个体因素也会阻碍精神关怀的实施,如病人数量太多,工作压力太大,自己缺乏自信,不想讨论关于精神层面的问题,或者是在语言上、文化上和宗教上与病人的背景不同,没有接受系统的教育与训练,对病人的精神需要了解不够等都不利于为临终患者提供恰当的精神关怀。
3.小结
不管是病人还是工作人员,都认为与家庭及重要他人的关系与联结是精神性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进行精神关怀的方式可以参考身体关怀的方式,主要是陪伴、共同的心灵之旅、倾听、建立联结、鼓励互惠的分享等。合适的时机、教育、培训、经验、意愿和团队支持是促进精神关怀开展的有利因素,而时间的限制、个体因素、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限制问题则不利于精神关怀的开展。除了护士之外,很多人如家人、朋友、邻居等都可以给病人提供精神关怀。虽然精神关怀的一个目的是满足病人的精神需要,但真正的精神关怀不能仅仅局限于病人的需要满足,而是应该在与病人建立亲密且有意义的关系过程中照顾到病人的需要。如果有的精神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可能就会转变成精神痛苦,因此要创造安全的环境使病人和工作人员可以自由地讨论他们的精神性问题,公开表达他们的恐惧、怀疑和焦虑情绪,提高精神关怀的水平。
三、临终关怀的调研进展
以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讨论了临终精神和心理关怀的各种问题。但国内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还是不够系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临终关怀涉及不同的学科,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对临终关怀问题不够投入。为此,本研究试图从心理关怀和精神关怀的角度探索基于身体、心理、精神的整合模型,以便为开展临终关怀提供一些理论和方法依据。为此,研究者与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初步的合作探索。根据以前的研究,心理需求中最重要的就是应对死亡恐惧。所以,本研究采用死亡态度描绘问卷测量了晚期癌症病人、病人家属、医护人员的死亡态度,并与社区居民的死亡态度进行了比较,除此之外,还采用了访谈法对晚期癌症病人进行深入访谈,以掌握他们的精神性需求。
(一)被试
为了解临终关怀过程中各方人员的心理需求,首先对中心的所有医护人员、社区内前来就诊的居民及舒缓病房收治的晚期癌症患者的家属进行了问卷调查。由经培训的调查小组阐明调查目的和内容,在目标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发放问卷,在其填写后当场回收检查,如有遗漏则及时补齐。共发放386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61份,有效回收率为93.5%。其中病人家属46人,医护人员102人,社区居民213人;男性139人,女性222人;青壮年人(60岁及以下)246人,老年人(60岁以上)115人。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测量工具为唐鲁等人修订的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Death Attitude Profile-Revised,DAP-R)。[34]该量表既包含了对死亡的负面态度,也包含了对死亡的正面态度,共32个题目(如“想到自己会死亡,就会使我焦虑不安”),采用五级评分,从1~5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题目均为正向计分,分数越高,则代表在该维度的认同度越高。五个维度分别是:趋近接受,认为死亡是通往极乐世界的大门,对死后的世界持积极态度;自然接受,认为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既不欢迎也不逃避,只是简单地接受;逃离接受,认为人生充满苦难,唯有死亡可令人解脱;死亡恐惧,指对死亡和濒死充满害怕的情感反应;死亡逃避,即对死亡本身或象征死亡的事物采取回避的态度,尽量不去想有关死亡的事情。在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6,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52~0.912之间。
(三)结果及分析
采用SPSS 16.0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分析了每个群体的死亡态度量表五个维度的得分差异;其次对三个群体在每个维度的得分进行了比较;最后是对两个年龄组在每个维度的得分进行了比较。
1.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死亡态度
图1显示的是癌症晚期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在死亡态度描绘量表每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患者家属在五个维度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4,225)=28.849,p<0.001。事后多重比较发现,自然接受维度得分最高(4.21±0.41),逃离接受(3.41±0.86)、死亡逃避(3.24±0.93)、趋近接受(3.06±0.77)得分居中,死亡恐惧(2.55± 0.73)维度得分最低。同样地,医护人员在五个维度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4,505)=50.662,p<0.001。事后多重比较发现,自然接受维度得分最高(4.21±0.41),死亡逃避(3.06±0.77)、趋近接受(3.05±0.59)、逃离接受得分(3.02±0.71)居中,死亡恐惧维度得分(2.79±0.66)最低。而社区居民在五个维度上的得分也存在显著差异,F(4,1 060)=62.771,p<0.001。事后多重比较发现,自然接受维度得分最高(3.67±0.65),死亡逃避(3.24±0.75)得分居中,而逃离接受(2.90± 0.77)、死亡恐惧(2.85±0.72)、趋近接受(2.69± 0.67)的得分最低。
2.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死亡态度比较
对每个被试在五个维度上的得分分别计算平均分,然后在每个维度上,按照被试类型进行比较,结果如图2所示。
在趋近接受维度上,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得分之间有显著差异,F(2,358)= 13.15,p<0.001。事后多重比较表明,患者家属得分(3.06±0.77)显著高于社区居民得分(2.69± 0.67),医护人员得分(3.05±0.59)显著高于社区居民,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得分没有显著差异。
在自然接受维度上,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得分之间有显著差异,F(2,358)=21.33,p<0.001。事后多重比较表明,患者家属得分(4.21± 0.41)显著高于医护人员得分(3.97±0.48),患者家属得分显著高于社区居民得分(3.67±0.65),医护人员得分显著高于社区居民得分。
在逃离接受维度上,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得分之间有显著差异,F(2,358)=8.26,p<0.001。事后多重比较表明,患者家属得分(3.41± 0.86)显著高于医护人员得分(3.02±0.71),患者家属得分显著高于社区居民得分(2.90±0.77),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得分没有显著差异。
在死亡恐惧维度上,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得分之间有显著差异,F(2,358)=3.44,p=0.033。事后多重比较表明,患者家属得分(2.55± 0.73)显著低于社区居民得分(2.85±0.72),患者家属得分和医护人员没有差异,医护人员得分和社区居民也没有差异。
在死亡逃避维度上,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F(2,358)=1.93,p>0.05。
3.青壮年人和老年人的死亡态度比较
按照被试年龄划分,60岁以下(含60岁)为青壮年人,60岁以上为老年人。在不同的被试人群中,对青壮年人和老年人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行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图1 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在死亡态度描绘量表每个维度上的得分
在患者家属中,老年人在死亡恐惧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青壮年人,其他四个维度得分没有显著差异。老年人比青壮年人更加害怕死亡。在医护人员中,老年人和青壮年人仅在自然接受这一维度上有差异,老年人的得分低于青壮年人,说明了老年人对死亡的自然接受程度较低。而在社区居民中,老年人在自然接受、逃离接受和死亡逃避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青壮年人。

图2 死亡态度每个维度上三个群体的得分比较

表1 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中青壮年和老年人在各维度得分(M±SD)比较
结果显示,三个群体的总体死亡态度是类似的,尤其是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在死亡态度不同维度上的得分模式是一致的:即对死亡的自然接受程度最高,而其他维度的得分比较低一些,并且各个维度之间差异也不太明显。但是具体到每个维度上,三个群体的得分又是有差异的,尤其是在死亡的自然接受、趋近接受和逃离接受维度。这说明在临终关怀中,不同的群体对死亡的具体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实践中进行关于死亡恐惧干预的时候应该根据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措施。当临终者的数据收集完毕之后,可能得到更为不同的结果,这样就可以使临床的干预更有针对性。
四、临终关怀实践模式的探索
静安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舒缓病房针对晚期癌症患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医护人员到志愿者队伍,在探索中建立临终关怀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的全方位关怀模式,具体如下。
(一)中医药参与舒缓疗护
2015年中心利用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复核评审的契机,与中医科合作探索运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参与到舒缓疗护的服务中去,减轻患者的生理痛苦。目前,病区已开展的中医特色服务有:芳香疗法、情志疗法、针灸止痛、中草药等,采用的“穴位针刺按压用于缓解癌症晚期恶心、呕吐症状”技术,缓解了多位晚期肿瘤患者消化道症状,提高了病患的生存质量。
(二)安宁护理方法尝试
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来说,在身体遭受病痛折磨的同时,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都比平常人多。病区的护士每天深入病房为患者细致地做基础护理,还耐心温婉地为患者做心理护理,消除他们的焦虑和忧伤感,帮助他们树立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有些晚期癌症患者身体较弱,无法起身到浴室洗发沐浴,病区为了方便患者,特意添置了沐浴床和洗头车,这样患者躺在病床上也能享受到沐浴和洗发服务,不仅让他们感到清洁舒适,也让他们体验到在生命的最后还能活得有尊严。为了方便患者和家属以及医护们进行有效沟通,病区的安宁护士每周都会进行护理日志的记录,将患者不方便说的话、心里的想法和需求记录下来。工作人员会通过护理日志及时了解患者的所需所想,并尽最大努力满足患者的需求,让患者和家属感受到体贴入微的关爱和帮助。
(三)志愿者服务方法探索
中心成立了一支由青年团员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他们以朝气蓬勃的精神和热情为舒缓疗护病房里的患者提供服务,为部分癌症晚期患者制作“生命回顾”的光碟。与此同时,病区与大学生志愿者进行合作为患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心理和精神关怀,为患者进行读书、读报、讲笑话、唱歌、陪患者聊天等活动,帮助他们减轻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
2015年,中心与“手牵手”专业志愿者机构开展合作,制定了志愿者管理制度、服务流程及服务内容。在此基础上,病区内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志愿者服务活动,举办新年联谊会和端午节等主题活动,让部分患者与家属可以参加,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浓浓的节日氛围。每季度举办家属座谈会,邀请家属、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共同讨论患者病情发展、志愿需求及改进措施,深受患者及家属的欢迎。专业志愿者还利用自身优势,探索将表达性艺术融入哀伤辅导的工作方法,协助临终者平静度过生命最后时光。同时,中心还有为患者搜集喜爱的音乐、为患者进行心理减压、为患者与家属打开心结、对信佛教的患者搜集佛经、对信基督教的患者联系牧师做祷告等一系列措施,对患者进行心理和精神上的关怀。除了晚期癌症患者,中心对医护人员也有相应的减压和心理疏导方案。2015年病区与专业志愿者机构“心缘俱乐部”进行了磋商,并于2016年与其合作运用音乐疗法缓解晚期患者及医务人员压力。
五、综合讨论、研究结论和未来发展建议
(一)综合讨论
纵观英文的文献,开始的时候,人们使用Hospice Care,强调的是有一个地方或者建立一种机构可以提供给临终的人来度过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Palliative Care,主要是针对重症病人的,关注在生命的最后如何减轻病痛;而现在随着对临终关怀的深入认识与研究和经验的积累,研究者们在发表的文章中比较常见的是The End-of-life Care,认为不是只有专业的机构才能提供临终关怀服务,在家庭中或者其他的机构如养老院、医院等地方也需要临终关怀。减轻身体上的痛苦虽然是临终关怀的主要内容,但除此之外还应该关照到临终者的心理和精神的需求。而且,临终关怀在以临终者为中心的基础上,也应该顾及与此有关的医护人员和家属。临终关怀概念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临终关怀本质认识的不断完善,从而可以更好地实现让临终之人在生存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有尊严地离开的终极目标。
为了把理论研究结果转化为实践经验,在上海市静安区卫生计生委的大力支持下,本研究者与静安区静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将生理、心理和精神的临终关怀整合模型在临床实践中进行运用和探索,并收到良好效果。这说明该模型是有效的,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可以进一步在中国其他地区进行推广,用实践不断检验和修正理论模型。正如前文所述,要构建涵盖生理、心理和精神关怀在内的整合临终关怀模式,需要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们共同努力。虽然死亡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话题,但同时也是每一个人必须要经历的生命过程。希望更多相关专业的学者至少可以从帮助自我的角度出发,关注临终关怀的研究与实践。
(二)研究结论
根据本研究的实证研究结果和静安区的实践经验,可以归纳出如下几条结论:
第一,不同的人群对死亡有着不同的态度,在进行心理干预的时候要有针对性,不能一视同仁。
第二,临终关怀的对象不仅是患者本人,还应包括家属和医护人员,尤其是在进行心理和精神关怀的时候,临终者家属和医护人员的需求也应该得到满足。
第三,生理、心理和精神的整合模型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结果,可以进行推广。
第四,临终关怀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如下问题:社会接受度不够,服务内容有待完善,医务人员紧缺以及政府和社会支持不足。
(三)未来发展建议
在倡导健康型社区建设的大背景下,临终关怀在社区工作管理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这对于提高民众的生命质量也有着重大意义。而要把这项工程做好,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引导与广大群众的支持。根据本研究的研究成果和体会,提出如下五点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加大财政投入,完善硬件设施。
第二,加强相关人员的专业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临终关怀的理论知识,包括专业及心理疏导等相关知识,建立起一支专业的临终关怀队伍。同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做出上海特色、中国特色的临终关怀事业。
第三,引导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参与到临终关怀当中来,以科研工作为依托,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探索临终患者对症治疗的适宜技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在生理关怀的基础上,建立心理关怀和精神关怀的整合模式。
第四,建立更为强大的社工及志愿者队伍,培养院内心理咨询师及积极招募院外专业心理咨询师,为病患及家属提供更好的心理疏导工作,同时减轻舒缓疗护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
第五,加大临终关怀的宣传,提高社会知晓率及认同感,加强患者及家属死亡教育,开展社区居民生死观教育。
(感谢上海静安区卫生计生委、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终关怀团队对于本研究的大力支持!)
[1]王星明. 西方主要国家临终关怀的特点及启示[J].医学与哲学,2014,(35).
[2]张鹏. 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J].求索,2007,(11).
[3]Liu C F. Palliative and hospice nursing[Z]. University of HK,Oncology nursing course,1997,1.
[4]刘英团.“临终关怀”让生命有尊严地谢幕[N].燕赵晚报,2012-11-21(B02).
[5]张鶄,施永兴.京、津、沪三地社区老年人健康状况及临终关怀服务需求的调查[J]. 中国全科医学,2010,(7).
[6]王宇,黄莉.澳大利亚慢性病患者临终关怀政策研究[J].医学与哲学,2015,(36).
[7]徐勤. 美国临终关怀的发展及启示[J].人口学刊,2000,(3).
[8]陈瑶,王峻彦,施永兴.成都、昆明、杭州三地注册临终关怀机构的服务功能及资源的调查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1,(1).
[9]潘毅慧,王俊琪,施永兴.北京市登记注册临终关怀机构的资源及服务功能的调查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1,(1).
[10]高茂龙,王静,王进堂,等. 北京市社区老年人临终关怀知晓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2014,(19).
[11]郑悦平,李映兰,王耀辉,等. 医护人员对死亡和临终关怀照护的态度及影响因素[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24).
[12]王小曼,董凤齐,郑瑞双. 肿瘤医院护士对待死亡及临终关怀态度的调查研究[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3,(25).
[13]刘丹丹. 梅州市临终关怀现状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D]. 广州:暨南大学,2011.
[14]董晓梅,王声湧,王弈鸣,等. 广州市民对临终关怀服务的认知、态度和需求的调查[J].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2004,(3).
[15]冉伶,许毅. 儿童临终关怀的发展[J]. 医学与哲学(A),2014,(1).
[16]王玉梅,冯国和,肖适崎.儿童患者临终关怀的研究进展[J].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07,(2).
[17]Oleska J M,Czarniecki L. Continuum of palliative care:lessons from caring for children infected with HIV-1[J]. Lancet,1999,354(9186).
[18]卢林阳. 130例濒死新生儿的临终关怀与姑息护理[J].中华护理杂志,2009,(9).
[19]Darnill S,Gamage B. The patient’s journey:palliative care:a parent’s view[J]. BMJ,2006,332(7556).
[20]李义庭,李伟,刘芳,等.临终关怀学[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21]薛静,胡杰,马丽. 高龄患者的临终关怀护理[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8,(24).
[22]黄剑波,孙晓舒. 基督教与现代临终关怀的理念与实践[J]. 社会科学,2007,(9).
[23]吴素香. 宗教与临终关怀[J].世界宗教文化,2008,(2).
[24]严梦春. 伊斯兰教的临终关怀思想[J].中国穆斯林,2013,(3).
[25]孟晶秋. 安乐死与临终关怀的和谐统一[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1,(3).
[26]孟宪武,崔以泰.临终关怀[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27]徐云,秦伟,霍大同.临终关怀中的心理支持系统的现状与问题[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12).
[28]张秋霞. 临终关怀中的心理问题[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5,(25).
[29]陈德芝.临终关怀:为临终患者提供生理和心理的全面照护:上海临终关怀(舒缓疗护)伦理与实践国际研讨会撷英[J].医学与哲学,2014,(35).
[30]潘元青.临终关怀与内隐自尊的修复:现象、机制及意义[J]. 医学与哲学,2013,(34).
[31]Chang H T,Lin M H,Chen C K,et al.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article publications:an analysis of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from 1993 to 2013[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2016,79(1).
[32]Universities of Hull,Staffordshire,Aberdeen. Spiritual care at the end of life: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Z]. UK:Department of Health,2010.
[33]Edwards A,Pang N,Shiu V,et al. The understanding of spirituality and the potential role of spiritual care in end-oflife and palliative care:a meta-stud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J]. Palliative Medicine,2010,24(8).
[34]唐鲁,张玲,李玉香,等. 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用于护士群体的信效度分析[J]. 护理学杂志,2014,(14).
[35]Rhondali W,Berthiller J,Hui D,et al. Barriers research in palliative care in France[J/OL]. Support Palliat Care,2013. http://spcare.bmj.com/content/early/2013/04/18/bmjspcare-2012-000360.full.html # ref-list-1.
[责任编辑:杨雅婕]
An Integrated Model of the-End-of-Life Care: Focusing on Spiritual,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are
LI Yong-na1FAN Hui1LI Huan-huan1CHEN Jun-feng2CAO Wen-qun2SHI Kan1
(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Jingansi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Shanghai 200040, China )
People at the end of their life often suffer from physical pain that is accompanied by fear, anxiety, depression, and helplessness. When death is near, many people try to rethink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The end-of-life care can help people cope with physical and mental problems, so that they can die with comfort, peace, and dignity. The go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end-of-life care focuses on satisfying needs of the dying people. Based on studies conduct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rs, an integrated model (integrating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care) of end-of-life care has been proposed and highlighted. The model assumes that the end-of-life care is designed not only for dying people but also for peopl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such as close family members, doctors and nurses in charge. The present work reported how the integrated model of end-of-life care was applie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of Jing’ansi, Shanghai. They take reasonable measures like pain management to relieve patients’ physical pain. The mental and spiritual needs were identified by surveys. The dying patients obtained professional help to cope with anxiety. The coping techniques included listening, making connection, and encouraging reciprocity. In addition,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s and team support were available for medical staff and family members to deal with their mental challenges. Theoretically, the end-of-life care is afield integrating many disciplines, such as medicine, nursing, psychology, sociology, just to name a few. Researchers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should work together in the future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nd-of-life care and provide appropriate theories for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hospice care; the-end-of-life care; spirituality; psychological care
李永娜(1978— ),女,山东招远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讲师,主要从事死亡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研究;时勘(1949— ),男,湖北枝江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工业与组织心理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3&ZD1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B849;C91
A
2095-7068(2017)01-0061-13
2016-04-28
10.19563/j.cnki.sdjk.2017.01.006
* 通讯作者:时勘,E-mail:shik@ucas.a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