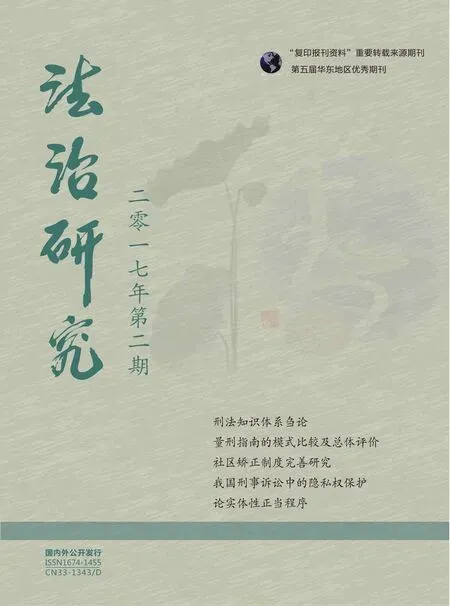论实体性正当程序*
刘东亮
论实体性正当程序*
刘东亮**
“实体性正当程序”要求权力的行使必须具有正当的目的。实体性正当程序是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权利保护和权利生成机制,它在程序性正当程序的基础上揭示了正当法律程序的完整内涵。由于实体性正当程序具有防范、揭露权力滥用的功能,它对于当下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正当程序 实体性 程序性 权力滥用
一、引言
近年来,在很多地方,“萝卜招聘”“火箭提拔”等违法滥权事件层出不穷。面对公众的质疑和追问,有关部门的回应通常是“符合程序”——“符合程序”成为明显、公然的滥权行为和堂而皇之的挡箭牌。这不仅反映出当下中国的程序制度建设存在问题,同时也暴露出我们的程序观念在某些方面尚有严重的缺陷和不足,以致给当事者留下了上下其手的空间。
古今中外,人性皆然。当下中国发生的这些问题(当然不限于招聘和提拔领域),在别的国家也曾经出现过或者正在发生。然而,先进法治国家都有其解决类似问题的办法。其中,美国的“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就是一种非常值得研究的制度。本文将在追溯实体性正当程序的起源与历史发展的基础上,阐述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本质和价值,分析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审查与判断方法,进而探讨这种制度和观念对当下中国有何参考借鉴意义。
“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国内学界亦有人译为“实质性正当程序”。本文暂将其直译为“实体性正当程序”。在中文语境中,“实体性正当程序”和“实质性正当程序”存在细微差别:当强调正当程序中相对于“程序性正当程序”的实体性内容时,可称其为“实体性正当程序”;当强调其程序的正当性之本质时,即其程序并非仅仅形式上正当而是具有内在的、实质性的正当性时,则可称其为“实质性正当程序”。不过,“实质性”一词的对应英文词汇是“substantial”而非“substantive”,为避免中外学术交流中可能发生的语义失真,将“substantive due process”直译为“实体性正当程序”可能更为恰当。
国内学界对“实体性正当程序”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在2000年以后这一问题才引起关注,例如张千帆教授在其《西方宪政体系》(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曾介绍过“实体性正当程序”。其他学者的研究内容上大多与此雷同,泛泛而谈,普遍不够深入。举例来说,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介绍这一制度构成对立法权的制约(因为在新政时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频繁运用实体性正当程序宣告国会的经济立法无效),而忽略了实体性正当程序作为分权制衡原则的具体体现,实际上是一种全面的权力制约机制,它不仅制约国会的立法权力,而且也制约行政权的滥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实体性正当程序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功能,其重要性日益突显),甚至对司法权也构成制约,如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多次运用实体性正当程序宣告“严重过度”(grossly excessive)的惩罚性赔偿之判决违宪。简言之,国内学界对实体性正当程序的研究多是低水平、重复性研究,对于这一制度的学术理解相当粗糙、肤浅,对该法律制度的价值挖掘还远远不够。①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以下。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言,其他比较有价值的中文文献,可参见余军:《正当程序:作为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6期;齐延平:《论美国的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6期;谢维雁:《论美国宪政下的正当法律程序》,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
相比之下,由于“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在美国法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对实体性正当程序的研究热度从美国建国之初直到今天都丝毫未减。实体性正当程序也因而成为美国法上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尽管法院曾经运用实体性正当程序作出了很多重要判决,但是,直到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内部还有人坚称根本不存在“实体性正当程序”这种东西。例如前不久刚刚逝世的宪法解释原旨主义的代表人物大法官斯卡里亚(Justice Scalia)就始终不承认实体性正当程序。因此,对实体性正当程序的研究,在美国有其现实的必要性,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著述自然也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至今,《耶鲁法学评论》《哈佛法学评论》等美国著名法学期刊仍然不时可以见到探讨“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文章,诸如Laurence Tribe 、Richard A. Posner、Akhil R. Amar、Erwin Chemerinsky等等这些被评为对美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法律思想家排行榜上的头面人物都参加过对实体性正当程序问题的讨论和争辩——他们的讨论和争辩中所闪烁出来的法律智慧和思想火花对解决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二、实体性正当程序的起源与发展
正当法律程序如何被赋予了实体性内涵,这是一个必须在理论上加以澄清的问题,否则,人们总是会对“实体性正当程序”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而要说明这一问题,历史溯源是必不可少的。
(一) “实体性正当程序”之滥觞
众所周知,“正当法律程序”并不是由美国宪法制定者发明的术语,而是他们从形成这一术语的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英国宪政传统中发掘出来的概念。②John v. Orth, Due Process of Law: A Brief History,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6 (2003).在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获得批准时,“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已经在英国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早在1354年,“正当法律程序”一词就在英国成文法上出现。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八号法令第三章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进行答辩,不论其财产和身份如何,任何人都不得被驱离其土地或者住所,不得被逮捕或者监禁……。”③28 Edw. 3, c. 3 (1354) (Eng.), quoted in Keith Jurow, Untimely Thought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Origins of Due Process of Law, 19 AM. J. LEGAL HIST. 265, 266 (1975).
根据对英国法律之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的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的解释,这项条款是对更早的、一个多世纪之前制定的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第三十九条的阐释和说明。1215年的《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
“非经其同辈依法裁判并根据王国的法律(legem terrae),任何自由人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④J.C. Holt, Magna Cart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6~327 (1992).
在这一条款中,原文为拉丁文的“legem terrae”一词被英译为“王国的法律”(the law of the land)。柯克认为,“正当法律程序”是对《大宪章》中“王国的法律”一词“真实含义的解释与说明”(true sense and exposition)。⑤See Edward Coke, 2 INSTITUTES OF THE LAWES OF ENGLAND 50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2002) (1642), quoted in Ryan C. Williams, The One and Only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Clause, 120 THE YALE LAW JOURNAL 429 (2010).在柯克看来,这两个术语是同义的。⑥See Orth, supra note 2, at 8.因为“王国的法律”意味着普通法和经恰当制定的实在法,而它们都要求“正当程序”。⑦当然,也有人怀疑柯克将这两个术语视为同义是否正确,但是,普遍性的观点是,由于柯克对美国建国时期的法律思想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他是否正确地描述了17世纪的英国法与解释美国宪法上的正当程序条款之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干的。See Williams, supra note 5, at 429.另一位英国普通法权威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对这两个术语作出了与柯克相同的解释。⑧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318 (Clarendon Press 1765), quoted in Williams, supra note 5, at 432~433.
柯克和布莱克斯通的法律思想对殖民地和建国时期的北美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很多殖民地的自由宪章和独立革命后颁行的邦宪法所使用的“本省的法律”(the law of this province)、“本邦的法律”(the law of the land)等用语,以及很多州法律所使用的“正当法律程序”,法院认为这些术语是一回事,可以相互引证交替使用。⑨See Orth, supra note 2, at 8; Williams, supra note 5, at 435~444.不过,由于《权利法案》的起草人采用了“正当法律程序”一词,⑩《权利法案》的主要起草人麦迪逊(James Madison)为什么选择“due process of law”这一用语而不是人们更熟悉的“the law of the land”,原因不是很清楚。美国学者威廉姆斯猜测有可能是为了避免与“本国的法律”相联的潜在的实证主义内涵,并希望避免使宪法第四条中的“优先条款”(the Supremacy Clause)成为冗余,该条款规定联邦宪法和法律以及国际条约是“本国的最高法律”(supreme Law of the Land)。See Williams, supra note 5, at 445~446.因而,“正当法律程序”此后成为标准的美国用法,并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正当法律程序概念源于“王国的法律”,即普通法和经恰当制定的实在法(duly enacted positive law),⑪Blackstone, quoted in Williams, supra note 5, at 433.因此,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实体性因素的种子。不过,虽然柯克曾经指出过,正当程序原则可以作为限制议会立法权的根据,⑫See Orth, supra note 2, at 15.但由于英国的政治发展走向特别是“议会至上”原则的确立,使得正当法律程序的实体性因素没有能够在英国得到充分发展。相反,在美国,由于独立革命同时也是一场观念上的深刻变革,比如,在由杰斐逊主持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在对英王几乎是声泪俱下的声讨特别是对以其名义颁行的侵犯殖民地人民权利的“伪法案”(pretended legislation)的控诉声中,议会至上的观念在北美殖民地烟消云散,正当程序遂在美国找到了合适的土壤而逐渐生发出实体性内涵。
当然,受正当法律程序中“程序”的字面含义所限,对于正当法律程序是否仅仅指程序保障,这一概念究竟有无实体意义,在美国建国初期,人们在认识上存在显著的分歧。争议双方似乎都可以从柯克和布莱克斯通关于正当法律程序原初含义之解释的著述中找到“合理的”根据。⑬See Williams, supra note 5, at 432~434.对实体性正当程序持批判态度的人坚称,程序(process)就是程序(procedure),并无实体性意义,至少,在1791年第五修正案获得批准时,正当法律程序的内涵仅仅指合法的程序(procedures)。⑭See John Harrison,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Text, 83 Va. L. Rev. 494 (1997); John Hart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 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5 (1980).这种意义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即后世所谓的“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⑮“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如同该短语所表明的,是指政府在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者财产之前必须遵循的程序(procedures)。典型的程序性正当程序问题是政府在采取某一行为之前必须提供什么类型的通知(notice)和什么形式的听证(hearing)。See Erwin Chemerinsky, Constitutional Law: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New York: 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 557 (2011).
然而,在1791至1868年间,正当法律程序的观念在美国逐渐发生了演变。在此期间,正当程序的概念通过联邦和州法院的裁判之解释,特别是通过著名的斯科特案(Dred Scott v. Sandford)发生了显著的变化。⑯60 U.S. (19 How.) 393 (1857) ——事实上,早在斯科特案之前,在第五修正案颁布后的头二、三十年,就有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等州的法院对州宪法上的“本州的法律”(the law of the land)条款作出了实体性解释。See Williams, supra note 5, at 446~448, 460~470. 另外,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856年的怀尼哈默诉人民案(Wynehamer v. People)中(该案涉及公民是否可拥有非用于销售的烈性酒的财产权),纽约州上诉法院对正当法律程序作出了实体性解释,这意味着实体性正当程序在州法院系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施瓦茨教授认为,该案标志着“正当法律程序发展史的新起点”。See Wynehamer v. People, 13 N.Y. 378(1856);另参见[美]施瓦茨:《美国最高法院史》,毕洪海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当然,在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实体性正当程序”问题,标志性的案件还是斯科特案。在该案中,奴隶制存废之争的双方围绕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的合宪性展开了激烈论辩,双方均寻求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的支持,一方强调除了惩罚犯罪之外国会立法不能剥夺任何人(person)的“自由”,另一方则强调未经正当程序国会立法不能剥夺主人的“财产”。首席大法官坦尼(Chief Justice Taney)则宣布,《密苏里妥协案》在北纬36.5°线以北禁止奴隶制的规定不符合正当程序。坦尼写道:
“仅仅因为他自己或者带着他的财产进入美国的一个特定地区就剥夺一位美国公民的自由或者财产,而他从未违反过法律,这种国会立法很难被美其名曰正当法律程序。”⑰60 U.S. (19 How.) 393, 450 (1857).
在这段判词中,正当程序明显被赋予了约束国会立法权的实体性内涵。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正当程序条款被坦尼等七名大法官用来否定《密苏里妥协案》禁止在美国北部地区蓄奴的合宪性。这是继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Marbury v. Madison)之后联邦最高法院第二次运用司法审查权宣告国会的立法违宪,但是,这一判决成为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一个极不光彩的污点。虽然如此,正当程序蕴含有实体性内涵的观念却日渐为人广泛接受,从而为实体性正当程序在20世纪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科特案的判决结果激发了美国内战,退一步讲,它至少是激发美国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奴隶制的存废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如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法庭和政治论坛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能通过枪炮来解决。⑱早在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颁布时,奴隶制存废双方就对该法案是否违反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存在激烈的争辩。该法案本身即是奴隶制存废双方斗争、妥协的产物。关于围绕奴隶制存废的政治辩论,参见 Willliams, supra note 5, at 470~477。
南北战争结束后,到1868年第十四修正案颁布之时,一种可识别的实体性正当程序之形式已经被当时存在的37个州中的至少20个州的州法院,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和一批杰出的宪法学文献的作者包括第十四修正案的主要起草人宾厄姆(John Bingham)欣然接受。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说,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的含义已足够广泛而涵盖了实体性正当程序。⑲See Willliams, supra note 5, at 495.
由于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中正当程序条款的表达句式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尽管适用的对象不同,制定时间在后的第十四修正案的含义影响到制定在前的第五修正案的含义,也就是说,第五修正案反向吸收(reverse incorporation)了第十四修正案。⑳关于反向吸收理论,可参见Akhil Reed Amar, Intratextualism, 112 HARV. L. REV. 747 (1999).这种反向吸收理论的例证是,1869年,即在第十四修正案获得批准的次年,最高法院在赫本诉格瑞斯沃德案(Hepburn v. Griswold)中再次对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作出了实体性解释。㉑75U.S. (8 Wall.) 603 (1869) ——该案的案情是,一项联邦法律规定联邦政府发行的纸币可以作为清偿债务的合法货币。有人根据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对该法的合宪性提起诉讼。首席大法官蔡斯(Chief Justice Salmon Chase)撰写的判决书声称,“该法会使那些合同原本规定用金银币获得支付的人被迫接受价值较低的货币获得清偿”,因而,“除非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被解释为直接禁止这项立法,否则它就不能具有完全的、预期的效果”。
1873年,即在第十四修正案获得批准后第五年,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解释了该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在声名狼藉的“屠宰场判例”(Slaughterhouse Cases)中,最高法院拒绝了正当程序条款可用于保障从事某一行业或者职业免受政府专断干预的论点。不过,大法官菲尔德(Justice Field)和布拉德利(Justice Bradley)二人强烈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正当程序条款中的“自由”(liberty)和“财产”(property)可以被解释为保护从事某一行业或者职业的权利,专横地干预这些权利违反第十四修正案。尽管这种观点被屠宰场判例中的多数大法官所拒绝,但是,它后来很快成为联邦最高法院中的多数意见。㉒83U.S. 36 (1873). See also Chemerinsky, supra note 15, at 626~627.
(二)洛克纳时代(1905-1937)的实体性正当程序
在第十四修正案获得批准后的二十多年间,联邦最高法院没有根据实体性正当程序宣布任何州法律违宪。这与其说是在将新制定的正当程序条款视为实体性保障的来源方面存在观念上的分歧,不如说这是最高法院还不适应由于第十四修正案的通过而赋予它的新角色的结果。㉓Willliams, supra note 5, at 489.因为,尽管从187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政府管制的大幅增加,最高法院受理了一系列针对政府经济管制提起的正当程序诉讼,最高法院在这些案件中一再提到经济上的实体性正当程序(economic substantive due process),但是,最高法院并没有使用这一原则宣告任何一项法律违宪。㉔See Chemerinsky, supra note 15, at 627~628.
不过,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发生改变,实体性正当程序开始被法院频繁运用于经济领域以保护个人的经济自由(economic liberties)。㉕Id. at 621 .1897年,在阿尔戈耶诉路易斯安那州案(Allgeyer v. Louisiana)中,联邦最高法院运用实体性正当程序宣告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项法律违宪,该法律禁止支付不在路易斯安那注册或者获准在该州经营的外州公司出票的海事保单。㉖165 U.S. 578 (1897).最高法院使用后来几十年经常被援引到的语言宣告:“我们认为,第十四修正案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自由运用其全部才能的权利、以所有合法方式自由运用其全部才能的权利、在自己喜欢的地方生活和工作的权利、通过任何合法职业谋生的权利、从事生计或者业余爱好的权利,以及为此目的签订为成功实现上述目标可能是适当的、必需的和重要的一切契约的权利。”㉗Id. at 589.
阿尔戈耶案成为更重要的1905年洛克纳诉纽约州案(Lochner v. New York)的先声。在洛克纳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告纽约州的一项针对面包工人的最长工作时间作出限制的法律违宪。㉘198 U.S. 45 (1905).该法律规定,“任何在饼干、面包或者蛋糕烘烤厂或者糖果企业工作的雇员,任何一周内工作不得超过60小时或者任何一天内工作不得超过10小时”。最高法院宣布该法违反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因为该法干预了契约自由,且并非出于正当的警察目的(police purpose)。由于洛克纳案反映了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哲学思想和信条,因此,这一时期常常被称为“洛克纳时代”(Lochner era)。㉙Chemerinsky, supra note 15, at 630 .
在洛克纳案中,最高法院声称,契约自由是根据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作为自由和财产权利而受到保护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只有在出于正当的警察目的,即保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或者公共道德时才能干预契约自由;法院需要严格审查立法以确保其真正出于警察目的。这是最高法院在洛克纳案中所阐述的一直到1937年为止都被遵循的三项重要原则。这种观念是典型的实体性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条款不单单用于确保政府遵循适当的程序,而且确保法律具有充分的目的。法院既要审查法律的目的,以确保真正存在正当的警察目的,同时又要审查其手段,以确保法律能充分实现其所声称的目的。概括而言,洛克纳案的判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没有明确提到的权利,虽不见于联邦宪法之正文,但如果遭到州政府的侵犯,仍然可以通过第十四修正案中“自由”(Liberty)概念的解释而受到联邦宪法的保护。
其二,契约自由属于第十四修正案中的“自由”之范围。纽约州的法律对面包工人工作时间的限制侵犯了这种自由,因而构成违宪。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仔细审查干预契约自由的立法,确保其真正出于正当的警察目的是法院的职责。
上述两方面的内容,第二项在 1937年以后被法院放弃(参见下节详细论述);第一项内容为法院保留下来并一直沿用至今。而且,第一项判决内容在正当程序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确立了“实体性正当程序”作为宪法未列举权利之渊源的地位。尽管在洛克纳案中实体性正当程序保护的是“经济自由”,但之后以正当程序条款为依据推导出来的未列举权利却包含了涵盖个人生活各方面的诸多权利。换言之,经过联邦最高法院和各州法院的解释,“实体性正当程序”逐渐成为一种适用范围非常广泛的“超级”概括性权利保障条款。㉚Id. at 632. 另参见余军:《正当程序:作为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6期。
洛克纳案判决作出以后,在接下来的30年里,最高法院遵照洛克纳案阐明的原则,认定很多法律因干预契约自由而违宪。据估计,将近有200部州法律因违反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而被宣告违宪。㉛Benjamin Wright, The Grow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154 (1942), quoted in Chemerinsky, supra note 15, at 632.这些被宣告违宪的法律包括:保护工会的法律、确定最长工时和最低工资的法律、价格管制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法律,以及管制行业准入的法律等等。
实体性正当程序在洛克纳时代的兴起与蓬勃发展不是偶然的。从187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大企业经济权力的迅速集中,工农阶层要求政府采取经济管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大企业的代表则强烈主张针对管制措施应保持高度警惕以保护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法院则深受过去几十年甚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思潮的影响,相信避免干预“最优秀者”(the best)的进步才能使社会整体更趋向繁荣,因而倾向于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当然,在洛克纳时代,实体性正当程序也并非全然用于保护个人的经济自由,它用于保护其他基本权利例如家庭自主权(family autonomy)也开始初露端倪。在1923年的迈耶诉内布拉斯加州案(Meyer v. Nebraska)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内布拉斯加州的一项法律违宪,该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除了英语之外的任何现代语言(实际立法意图是针对德语)。在该案中,最高法院不是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是运用实体性正当程序认定该法律侵犯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作出决定的权利,因而宣告该法律无效。最高法院在保护基本的家庭自主权的正当程序条款中对“自由”(liberty)作了宽泛的界定。最高法院声称:“毫无疑问,自由不仅仅意味着身体免受限制的自由,而且也意味着个人签订契约的权利、从事任何普通的谋生之职业的权利、获取有用的知识的权利、结婚的权利、成立家庭与抚养孩子的权利、根据自己的良心要求敬拜上帝的权利,以及普遍享有那些长期以来被普通法承认为自由人所必不可少的有序追求幸福的权利。”㉜Meyer v. Nebraska, 262 U.S. 390, 399 (1923).另外一个类似的重要判例是1925年的皮尔斯诉姊妹会案(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俄勒冈州的一项法律规定所有儿童都只能入学公立学校。一家教会学校被获准具有第三人资格代替孩子父母提起诉讼,指控该法律侵犯了父母掌控子女教育的权利。See 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 268 U.S. 510 (1925).迈耶案对“自由”的扩张性解释为日后各种未列举权利逐步得到承认打开了方便之门,特别是为后来实体性正当程序走向衰落以后到1960年代又重新复兴埋下了生生不息的火种。
(三)1937年以后实体性正当程序的衰落
在洛克纳时代,实体性正当程序处于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法院常常根据实体性正当程序而不是契约条款(Contract Clause)来保护契约自由,以至于使宪法第一条第十款中的契约条款显得多余。不过,到1930年代中期,法院面临着放弃洛克纳时代的自由放任思想的巨大压力。大萧条产生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是必不可少的普遍观念。㉝当然,也有人认为,情况正好相反,恰恰是政府对经济过多的管制导致了大萧条的出现。参见[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页以下。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和工资低得可怜的在岗者,使得雇员根本没有真正的机会在职场和雇主讨价还价。正如特赖布(Laurence Tribe)教授所言:“在很大程度上,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现实极大地削弱了洛克纳案的前提,契约和财产方面的法律‘自由’(freedom)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幻象而受制于冷冰冰的经济势力。人们日益广泛地承认,积极的政府干预是经济复苏必不可少的条件,法律原则需要在这一前提下运作。”㉞Laurence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Foundation Press, 578 (2d ed. 1988).
与此同时,也存在要求法院作出改变的强大的政治压力。由于最高法院将好几项重要的新政立法宣告无效作为捍卫自由放任思想之使命的一部分,罗斯福总统对此大为光火,他提出一项“法院填塞计划”(Court-packing plan),试图改组联邦最高法院。1937年,在西海岸宾馆诉帕里什案(West Coast Hotel v. Parrish)中,㉟300U.S. 379 (1937).大法官罗伯茨(Justice Owen Roberts)改变立场投下了维持新政立法的第五票。或许这是对法院填塞计划的反应,或者早在了解到这种威胁之前他就打定了主意。不管怎样,在这个案件中,最高法院释放出了支配宪法几十年的自由放任法理学宣告终结的信号。
在西海岸宾馆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了华盛顿州为女性雇员制定的最低工资法。首席大法官休斯(Chief Justice Hughes)撰写的判决书表明最高法院放弃了洛克纳案确立的原则。休斯指出,这项最低工资法因为干预契约自由而受到质疑。他回应说:“契约自由是什么?联邦宪法并没有提及契约自由。联邦宪法提到了自由并禁止未经正当程序而剥夺自由……与其主题有关的合理的管制措施,并且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制定的管制措施是符合正当程序的。”㊱Id. at 391.在该案中,最高法院毫不含糊地宣称它不再将契约自由作为基本权利对待,政府可以出于任何正当合理的目的规范契约自由,而且,只要立法机关的选择是合理的,法院就予以尊重。㊲Chemerinsky, supra note 15, at 64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法院填塞计划”从未真正实施,但是,在1937年至1941年间,联邦最高法院的人员组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四位保守派大法官主动离开了最高法院而被罗斯福总统提名的大法官所取代。事实上,在1937至1941年间,罗斯福有机会任命了八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从而创造了承诺拒绝洛克纳时代的法理学而遵从政府经济管制措施的稳固多数。㊳Id. at 641.
1937年以后,没有一项州或者联邦的经济管制措施因侵犯正当程序条款所保护的契约自由而被认定违宪。最高法院声称,只要与正当的政府目的存在合理关联,经济管制措施就应当被维持。此后,对经济权利的保护,如同过去一样,根据宪法第一条第十款的契约条款和第五修正案中的征用条款而展开。㊴Id. at 641~645.实体性正当程序走向衰落。㊵1937年到1965年,联邦最高法院运用到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唯一案件是1952年的罗钦诉加利福尼亚州案(Rochin v. California)。下文会讨论该案。
(四)1960年代中期以后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复兴
从经济自由领域全面撤退以后,直到1965年,联邦最高法院还竭力避免运用实体性正当程序。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例证是格瑞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㊶381U.S. 479 (1965).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康州的一项禁止销售、分发、使用避孕用具的法律无效。由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执笔的判决书开宗明义地宣布:“就本案所涉问题的是非曲直而言,我们遇到了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涉及到的很多问题。有些论点的言外之意认为洛克纳案应当作为本案的向导。但是,我们拒绝了这种提议。我们不能作为一个超级立法机关(super-legislature)裁判处理经济问题、商业事务和社会情势的法律之智慧及其必要性和妥当性。”㊷Id. at 482.
接下来,道格拉斯话锋一转,“不过,这项法律直接涉及到夫妇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医生对这种关系所发挥的作用”;他接着说,很多权利,比如父母为子女选择何种学校教育的权利、学习任何特定科目或者外语的权利等等,虽然联邦宪法和第一修正案都没有提到这些权利,但是这些权利还是被迈耶诉内布拉斯加州案(Meyer Nebraska)和皮尔斯诉姊妹会案(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等判例解释为包含在第一修正案之中。㊸Meyer v. Nebraska, 262 U.S. 390 (1923); 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 268 U.S. 510 (1925).道格拉斯推论说,隐私权同样也暗含在《权利法案》的很多特定条款之中。他宣称:“前面提到的案件认为,《权利法案》的特定保障存在着半影地带(penumbras),这种半影地带是由那些帮助赋予其灵命的保障向外散发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保障形成了隐私权的半影……虽然我们对处于这些半影地带的隐私和宁静权曾经有很多争议,但是这些案件表明,在本案中迫切要求获得承认的隐私权是正当合理的权利。”㊹381U.S. 484 (1965).道格拉斯大法官在《权利法案》的“半影地带”中找到了公民的隐私权。易言之,由于适用于联邦政府的《权利法案》通过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适用于各州和地方政府,道格拉斯大法官运用实体性正当程序推导出了公民的隐私权,即便当时他所拒绝的恰恰是他之所为。㊺See Erwin Chemerinsky,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15 TOURO LAW REVIEW 1506~1508 (1999).八年以后,在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宣布,隐私权通过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和第九修正案受到保障。毫无疑问,罗伊案是一个实体性正当程序案件。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裁定,旨在挽救生命而一概禁止堕胎的法律没有考虑母亲的妊娠阶段,也没有考虑涉及到的其他方面的利益,因而违反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㊻410U.S. 113 (1973).
1965年的格瑞斯沃尔德案成为实体性正当程序复兴的标志。该案开启了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新时代,一个保护经济自由以外的权利和自由的新时代。此后,联邦最高法院在很多案件中都运用到实体性正当程序。只是,与洛克纳时代相比,实体性正当程序主要不再适用于经济立法,而是适用于社会立法;主要不是用来保护经济自由,而是用于保护经济自由以外的其他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结婚权、监护权、探视权、保持家庭团聚权、生育权、堕胎权、购买或者使用避孕用具的权利等等很多宪法上并未明确列举的权利和自由。时至今日,实体性正当程序已经成为美国宪法制度和宪法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本质与价值
如前所述,实体性正当程序是美国法上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批评者指责这一理论“在语言上是自相矛盾的”、属于“重大赝品”“虚构的文字发明”,如此等等。比如,伊利(John Hart Ely)教授嘲弄其就像“绿色的淡红”(green, pastel redness)。㊼See Ely,supra note 14, at 18; Willliams, supra note 5, at 411.还有人批评实体性正当程序既在文字上不合情理,又与民主自治的基本原则相悖。例如,博克(Robert H. Bork)辩称,实体性正当程序被那些想要贯彻自己个人信念的法官们无数次极其生硬地在司法裁判中掺进了个人的“私货”。㊽See Robert H. Bork, The Tempting of America: The Political Seduction of the Law, New York: Free Press, 31 (1989).尽管法院运用实体性正当程序作出了很多重要裁判,但是,直到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内部还有大法官坚称根本不存在“实体性正当程序”这种东西。㊾前文指出,前不久刚刚逝世的大法官斯卡里亚(Justice Scalia)始终不承认实体性正当程序。See Chemerinsky, supra note 45, at 1525.因此,对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本质与价值作进一步的解释与澄清,实属必要。
(一)实体性正当程序是一种权力制约机制
众所周知,美国联邦宪法中并没有“权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这一术语,然而,分权原则是联邦宪法的一部分,因为宪法用语阐述的逻辑结构内在地包含了这一原则,并且在美国立国时期的很多文件中都可以发现这一用语。仅仅因为这一原则在宪法文本中并没有明文规定而抛弃这一原则或者讥讽它所依靠的逻辑是一套主观的价值判断,是违反常情的。㊿See Timothy Sandefur, In Defense of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or The Promise of Lawful Rule, 35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350 (2012).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情况也是这样,而且,它恰恰是权力分立原则的具体体现。(51)Nathan S. Chapman & Michael W. McConnell, Due Process as Separation of Powers, 121 Yale L.J. 1276 (2012).
早在1856年的莫雷承租人诉霍博肯土地开发公司案(Murray's Lessee v. Hoboken Land & Improvement Co.)中,(52)59U.S. (18 How.) 272 (1856).在论及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的含义时,联邦最高法院声称“正当法律程序”和“本国的法律”是同义概念,并断然拒绝了正当程序条款无意限制国会权力的主张。由大法官柯蒂斯(Justice Curtis)撰写的判决书声称:“非常明显,这一条款并未授予国会制定任何可能被设计出来的程序的立法权。该条款是对立法权的限制,也是对政府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的限制,而不能被解释为授权国会仅仅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制定任何‘正当法律程序’之程序。”(53)Id. at 276.
由于实体性正当程序在洛克纳时代曾经被频繁用于宣布各州的经济立法无效,很多人(尤其是中国法学界),误以为它仅仅适用于限制立法权,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认识。实体性正当程序不限于对立法权的制约,而是用于防止一切权力的专断滥用,包括司法权自身。例如,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多次运用实体性正当程序推翻下级法院过度严苛的惩罚性赔偿之判决。(54)See F. Patrick Hubbard,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Limits on Punitive Damages Awards:“Morals Without Technique”?, 60 FLORIDA LAW REVIEW 349 (2008).在1996年的宝马汽车北美公司诉戈尔案(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一项针对宝马公司因对汽车重新喷漆而未告知消费者的两百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属于“严重过度”(grossly excessive)。(55)517U.S. 559 (1996) ——该案的案情是,戈尔医生花四万美元购买了一辆崭新的宝马汽车,后来发现,由于受到酸雨腐蚀,这辆车在出售前作了重新喷漆,而买车时商家没有告知他这一情况。戈尔对宝马公司提起诉讼,陪审团判给他四千美元的补偿性赔偿和四百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后来,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减少到两百万美元。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严重过度的惩罚性赔偿违反正当程序,并提出了评估惩罚性赔偿是否严重过度适用的三项标准。(56)这三项标准是:首先,被告之行为“可责难性”(reprehensibility)的程度如何?其二,惩罚性赔偿与原告遭受的实际损害的比例如何?最后,根据其他州的法律类似的非法行为应当受到的制裁如何?详细参见 Chemerinsky, supra note 15, at 610~611。在2003年的州农保险公司诉坎贝尔案(State Farm Mutual Aotomobile Insurance Co. v. campbell)中,联邦最高法院对戈尔案阐述的三项标准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与说明。(57)538U.S. 408 (2003).
实际上,就目前而言,由于立法机关之立法,至少在州或者联邦层面,通常都经过详细讨论,大多数立法都很难以专断和反复无常为由对之成功提起诉讼。而且,为了避免“洛克纳化”(Lochnerizing)的危险标签,法院常常高度遵从立法机关的决定,要求起诉人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58)See Rosalie Berger Levinson, Reining in Abuses of Executive Power Through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60 FLA. L. REV. 526 (2008).因而,洛克纳时代以后,实体性正当程序对立法权的制约已经退居到次要地位。同样,由于司法权和司法程序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司法权的滥用(特别是在美国的制度环境中)相对比较少见。因此,除了有陪审团参与的惩罚性赔偿之判决,实体性正当程序对司法权的制约可运用的空间相当有限。相比之下,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时最易发生滥权情形,实体性正当程序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更为明显。
1952年,联邦最高法院确认,实体性正当程序保护公民免受政府官员非法行为的侵害。在罗钦诉加利福尼亚州案(Rochin v. California)中,最高法院援引实体性正当程序排除了警察对被告人进行强制洗胃获得的证据。(59)该案的案情是,洛杉矶县的三名警察到罗钦的住所进行检查,当罗钦被问到床头柜上的两粒胶囊是什么东西时,他立即吞下了胶囊。警察遂把他带到医院进行强制洗胃并从中发现了吗啡。罗钦据此被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罗钦根据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提起上诉。上诉法院认为在本案情形下非法获得的证据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警察的行为异乎寻常,但是该证据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判决驳回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则以8:0推翻了原判(大法官Minton投了弃权票)。342 U.S. 165 (1952)。最高法院声称,警察的行为“震憾良知”(shocks the conscious)因而违反实体性正当程序。“震憾良知”作为确定行政机关的非法行为是否如此严重以至于违反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标准应运而生。(60)Id. at 172.
1998年,联邦最高法院在萨克拉门托县诉刘易斯案(County of Sacramento v. Lewis)中重新讨论了作为对行政权之限制的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含义。(61)523U.S. 833 (1998).最高法院确认实体性正当程序可用于起诉行政权的滥用:“自从我们很早以前对正当程序作出解释之时起,这一概念的核心就是保护公民免受专断、任意的行为(arbitrary action)之侵害……。”(62)Id. at 845~846.
此外,在涉及审前被羁押人、被强制送院治疗的精神病人的案件中,以及涉及政府雇佣、公立教育、土地规划与建筑许可的案件中,最高法院都运用到实体性正当程序。在所有这些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实体性正当程序构成对行政权力的制约(a check)。(63)See Levinson, supra note 58, at 529~535.
(二)实体性正当程序是一种权利保护和权利生成机制
实体性正当程序对权力的制约,归根到底,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大法官哈兰(John M. Harlan, J.)在1961年的波诉乌尔曼案(Poe v. Ullman)中说:“如果正当程序仅仅是程序性保障,那么,当生命、自由或者财产被通过立法予以剥夺的情况下,正当程序对此将束手无策,即使将来的立法将最公平的程序适用于个人,也会使这三种权利荡然无存。”(64)367U.S. 497 (1961).哈兰的这段评论深刻地揭示出实体性正当程序对保障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65)后来,大法官苏特(Justice Souter)把哈兰的意见称为现代实体性正当程序复兴的起源。See Washington v. Glucksberg, 521 U.S. 721 (1997)。
实体性正当程序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包括下列几种情形:(1)对于宪法上明确规定的权利和自由,通过对政府行为是否具有正当的目的之审查,实体性正当程序一般可以单独发挥保护作用。(2)对于宪法上明确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实体性正当程序与宪法上的其他条款相结合共同发挥保护作用。例如,对于契约自由和财产权利,虽然宪法上已经存在契约条款和征收条款,但是,实体性正当程序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对此,有学者称,实体性正当程序从正当程序条款的运河中横溢出来而成为契约条款和征收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66)Eric Pearson, Some Thoughts on the Role of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in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l Law of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25 PACE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4 (2008).(3)对于宪法上明确规定的某些权利和自由,宪法上的既有条款之保护捉襟见肘时,实体性正当程序可起到填补作用。比如,最高法院承认,不受宪法第八修正案保护的审判前的被羁押人(pretrial detainees)在免受专断惩罚方面具有自由利益,实体性正当程序创设了为被羁押人提供保护和其所需要的医疗的义务。(67)City of Revere v. Mass. Gen. Hosp., 463 U.S. 239, 244 (1983); Bell v. Wolfish, 441 U.S. 520 (1979).再如,对于非自愿住院的精神病人,最高法院确认实体性正当程序为其创造了要求获得考虑更为周到的医疗待遇和禁闭条件的权利。(68)Youngberg v. Romeo ex rel. Romeo, 457 U.S. 307, 315 (1982).(4)实体性正当程序在保护宪法未列举权利(unenumerated rights)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前述格瑞斯沃尔德案和罗伊诉韦德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实体性正当程序推导出了宪法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公民的隐私权。鉴于实体性正当程序在保护未列举权利方面的作用极为重要,兹详述之。
自1923年迈耶诉内布拉斯加州案以后,特别是1965年实体性正当程序再度复兴以后,最高法院明确裁决某些家庭自主权属于基本权利,政府干预只有在满足严格审查时才能获得准许。这些权利包括结婚的权利(特别是族际通婚和同性婚姻权利)(69)Loving v. Virginia, 388 U.S. 1 (1967); United States v. Windsor, 570 U.S. 12 (2013).、对子女的监护权(70)Santosky v. Kramer, 455 U.S. 746 (1982); Stanley v. Illinois, 405 U.S. 645 (1972).、保持家庭团聚权(71)Moore v. City of East Cleveland, 431 U.S. 494 (1977).、掌控教养子女的权利等等。此外,最高法院又借助实体性正当程序通过一系列判例发展出了生育权,堕胎权,购买、使用避孕用具的权利等生育自主权,以及自主决定性行为和性倾向、拒绝医疗救治等等许多在宪法文本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利。(72)See Chemerinsky, supra note 15, at 833~866; Lawrence v. Texas, 539 U.S. 558 (2003); Cruzan v. Director, Missouri Department of Health, 497 U.S. 261 (1990).由于法院通过对正当程序条款中的“自由”之解释把很多未列举权利确定为应当给予特别保护的“基本权利”或者“核心自由利益”(core liberty interest),(73)Levinson, supra note 58, at 522.这使得实体性正当程序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权利生成机制。
实体性正当程序何以能生成新的权利,什么情况下可以生成新的权利?有人概括总结了三种理论:历史传统理论、理性判断理论和不断演化的国民价值观念理论。(74)See Daniel O. Conkle, Three Theories of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85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63 (2006).
历史传统理论(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tradition)认为,实体性正当程序对那些“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deeply rooted in this Nation's history and tradition)的自由利益提供推定性的宪法保护。不过,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在华盛顿州诉格鲁兹堡案(Washington v. Glucksberg)中所表明的,(75)521U.S. 702 (1997).只有在受到严格界定的权利主张在美国社会和法律史上具有广泛的、源远流长的支持时,该理论才允许承认某种未列举的宪法权利。
理性判断理论(the theory of reasoned judgment)则认为,实体性正当程序之权利不受历史传统的限制,相反,法院可通过近乎哲学分析或者政治道德推理的过程独立、自由地识别基本权利。根据这种方法,法院可评估个人的自由利益并衡量相冲突的政府关切,据此确定这种自由利益是否值得作为宪法权利予以保护。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和1992年的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都运用了这种方法。(76)See Roe, 410 U.S. at 153;Planned Parenthood of Se. Pa. v. Casey, 505 U.S. 833, 849 (1992).不过,何谓“理性判断”是一个较难确定的问题,即使是头脑和人品各方面都无可挑剔的大法官们也常常对某种自由利益是否值得保护意见不一,这也是造成实体性正当程序理论一直饱受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来,印第安纳大学毛勒法学院的考科尔(Daniel O. Conkle)教授根据大法官哈兰和苏特等人的思想概括出了实体性正当程序的第三种理论:“不断演化的国民价值观念”理论(the theory of evolving national values)。该理论认为,对于特定的权利主张,法院必须确定是否存在一种广泛的国民共识。如果并且仅当某种被严格界定的权利主张,既受到当代国民共识的支持又受到法官独立作出的政治与道德判断的支持时,法院才应当承认这种宪法上的未列举权利。(77)另外,威灵顿(Harry H. Wellington)教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也阐述过这种思想,参见Harry H. Wellington, Common Law Rules and Constitutional Double Standards: Some Notes on Adjudication, 83 Yale L.J. 221, 284 (1973); Conkle, supra note 85, at 145.与前两种理论相比,不断演化的国民价值观念理论的优点在于,一是与历史传统理论相比,它所信奉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不断进步的政治道德,这更适合、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二是与理性判断理论相比,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当代国民共识”的约束,从而把法官限定于适当的司法角色。毕竟,正如卡多佐(Benjamin N. Cardozo)所说,法官仅仅是法官,他们并非“居无定所、随意漫游而只顾追寻自己美善理想的游侠”。(78)Benjamin N. Cardozo, 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41 (1921).
的确,宪法上演化出来的很多未列举权利,并不纯粹是法院自己所作判断的结果,而是给法院提供了外部判断标准的多数主义行动(majoritarian actions)的产物。这从近十年来法院对待同性婚姻的态度之转变和多数国民从反对同性恋到赞同“民事结合”(civil union)再到支持同性婚姻的民意流变之曲线的高度吻合,得以鲜明地反映出来。司法与民意的互动关系属于另一个值得专门探讨的问题,此处不赘。
(三)实体性正当程序在程序性正当程序的基础上揭示了正当法律程序的完整内涵
尽管联邦最高法院从未对实体性正当程序作出过明确的定义,不过,一般认为,实体性正当程序提出的问题是,当政府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者财产时是否具有充分的目的证明其是正当合理的(justified by a sufficient purpose)。而程序性正当程序提出的问题是,政府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者财产时是否遵循了适当的程序步骤。(79)See Chemerinsky, supra note 45, at 1501.换言之,程序性正当程序关注的是政府是否通过某种程序对当事人的利益提供了充分保护,而实体性正当程序关注的是权力是否被滥用。(80)Levinson, supra note 58, at 555.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曾经指出,程序性正当程序之要求是为了提高公平性(to promote fairness),而实体性正当程序旨在防止政府权力用于压迫之目的(for purposes of oppression)(81)Daniels v. Williams, 474 U.S. 327, 331 (1986).。由是观之,可以说,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体性正当程序,一个是正当程序之矛,一个是正当程序之盾,一用于主动进攻,一用于被动防御,二者是矛盾的统一体,但是并不自相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举例来说,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战斗中同时持有矛和盾,他并不是要用自己的矛攻击自己的盾,或者用自己的盾抵御自己的矛,他的矛和盾都是为了对付敌人,以达到作战胜利的目标,在正当程序的语境中,就是为了实现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之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程序性正当程序和实体性正当程序似乎出现了融合的趋势。比如,传统的正当法律程序即典型的程序性正当程序要求政府在采取某一行为之前必须提供通知(notice)和听证(hearing),(82)See Chemerinsky, supra note 15, at 557.而不包括说明理由之要求。但是,从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颁布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判例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必须说明理由(reasons)。(83)See Gary Lawson, Federal Administrative Law, Thomson Reuters, 761 (2009), n.4.由于实体性正当程序关注的问题正是政府对个人生命、自由或者财产的剥夺是否具有充分的实体性正当理由(a sufficient substantive justification, a good enough reason),(84)See Chemerinsky, supra note 45, at 1501.这意味着,或许,并不需要再明确区分程序性正当程序和实体性正当程序,程序性正当程序和实体性正当程序都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应有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在行政法领域,程序性正当程序和实体性正当程序开始从分化走向融合。
四、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审查与判断
在涉及实体性正当程序的诉讼中,案件的裁判结果常常取决于法院所使用的审查标准(level of scrutiny)。审查标准提供了衡量、判断的指导,它告诉法院在评估特定的行为时在宪法和法律的天平上如何安排(各部分的)权重。(85)See Chemerinsky, supra note 15, at 551.
1998年,联邦最高法院在萨克拉门托县诉刘易斯案中指出,识别什么是极为严重的专断行为之标准,根据审查对象是立法还是政府官员的具体行为而有所不同。(86)Lewis, 523 U.S. at 846.兹分述之。
(一)行政行为违反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审查标准
前文指出,1952年,联邦最高法院正式承认,实体性正当程序保护公民免受政府官员非法行为的侵害。在罗钦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最高法院援引实体性正当程序排除了警察对被告人进行强制洗胃获得的证据。(87)342U.S. 165 (1952).最高法院声称,警察的行为“震憾良知”(shocks the conscious)而违反实体性正当程序。“震憾良知”作为确定行政官员的非法行为是否如此严重以至于违反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标准应运而生。(88)Id. at 172.其后,有多个判例相继援引、重申了“震憾良知”标准。(89)See United States v. Salerno, 481 U.S. 739, 746 (1987); Whitley v. Albers, 475 U.S. 312, 327 (1986).
1998年,在萨克拉门托县诉刘易斯案中,(90)523U.S. 833 (1998).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补充、完善了罗钦案所确立的标准。最高法院推理说,故意漠视(deliberate indifference)宪法权利的政府官员之行为是“震憾良知”的。例如,监狱看守故意漠视审前被羁押人的医疗需要。(91)Id. at 849~50.最高法院又援引了扬伯格案(Youngberg v. Romeo ex rel. Romeo),该案确定,一家州立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未向非自愿住院的精神病人提供最低限度的适当的康复训练护理而违反了实体性正当程序。(92)Id. at 852 n.12.不过,由于“故意漠视”暗含着存在实际考虑的机会,最高法院裁决该标准不能适用于要求立即付诸行动之情形的警察。因此,在重申“震憾良知”标准的同时,刘易斯案又说明,“故意漠视”标准适用于非紧急情况下声称存在行政权之滥用的诉讼。(93)在很多案件中,下级法院都遵循了在非紧急情况下适用“故意漠视”标准。See Levinson, supra note 58, at 532 n.76。
此外,在执法情形之外,联邦最高法院又确认了针对专断的雇佣和教育决定而提起实体性正当程序之诉的有限权利。比如,在哈拉独立学区诉马丁案(Harrah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v. Martin)中,(94)440U.S. 194 (1979).最高法院认定,与家庭、婚姻和生育领域的选择自由不同,就业权并不属于基本权利。因而,法院应当根据传统的“专断和反复无常”(arbitrary and capricious)标准而不是严格审查标准分析校董会的雇佣决定。(95)Id. at 198~99. See also Levinson, supra note 58, at 533.
(二)立法行为违反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审查标准
在洛克纳时代,最高法院声称,政府只有在出于正当的警察目的即保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或者公共道德时才能干预契约自由;法院应严格审查立法以确保其真正出于警察目的。法院既要审查法律的目的以确保存在正当的警察目的,又要审查其手段以确保法律能充分实现其所声称的目的。(96)Chemerinsky, supra note 15, at 632.洛克纳时代的前提假设是,政府只有为了实现警察目的时才能调控经济而法院需要严格审查法律以确保它们真正出于警察目的。(97)Chemerinsky, supra note 15, at 638.
193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西海岸宾馆案中宣称,政府可以出于任何正当合理的目的规范契约自由,而且,只要立法机关的选择是合理的,法院就应当予以尊重。(98)300U.S. 379 (1937).这表明最高法院放弃了洛克纳案所确立的对经济管制立法一律适用严格审查的原则。1938年,在美国诉凯若里那乳制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中,联邦最高法院重申了司法遵从政府经济管制的新政策。(99)304U.S. 144 (1938).最高法院声称,只要经济管制存在可以相信的合理根据的支持,即使不能证明这是立法机关的实际意图,也应当予以维持。最高法院在该案判决书中用一个著名的脚注(Footnote 4)阐述了司法审查的双层标准:通常,只要立法是合理的,法院就应当遵从立法机关的选择而维持法律的合宪性。但是,这种遵从不会扩展到干涉基本权利的立法或者歧视分散的、孤立的少数族群(discrete and insular minorities)的立法。(100)304U.S. at 152~153 n.4.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法院会遵从立法机关的选择,对法律实行“合理根据”之审查;但是,如果涉及到基本权利,则应实行“严格审查”。
“合理根据标准”(rational basis test)是最低程度的审查标准。所有根据正当程序条款被起诉的法律都必须至少满足合理根据之审查。根据这一标准,如果某项法律与正当的政府目的存在合理关联,该法律就会被维持。事实上,这种目的不需要是立法的实际目的,任何可设想的正当目的就足够了。同时,所选择的手段只要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合理方式就可以了。由于合理根据标准是对立法机关的高度遵从,因而,联邦最高法院以不满足合理根据之审查为由宣布法律无效的情况非常罕见。(101)See Chemerinsky, supra note 15, at 553.
最严格的司法审查是“严格审查标准”(strict scrutiny)。根据严格审查,只有当某项法律是实现重大迫切的政府目的之所需时,该法律才能被维持。简言之,政府的目的必须是“重大迫切的”(compelling)。而且,系争法律必须是实现其目的“必要的”(necessary)手段。这就要求证明该法律必须是具有最少限制性的或者最少歧视性的选择。如果该法律不是具有最少限制性的选择,那么,它就不是实现其目的所“必要的”。(102)Simon & Schuster v. New York Crime Compensation Bd., 502 U.S. 105 (1991).
在适用严格审查时,政府一方负有举证责任。除非政府能证明系争法律是实现重大迫切的政府目的所必需的,否则该法律将被宣告无效。自然,由于严格审查的严格要求,当适用这一标准时法律通常会被宣告违宪。因此,有学者声称,严格审查“在理论上是严格的,在实际上也是致命的”。(103)Gerald Gunther, Foreword: In Search of Evolving Doctrine on a Changing Court: A Model for a Newer Equal Protection, 86 Harv. L. Rev. 1, 8 (1972) ——此外,美国法院在少数情形下还会运用到“中等程度的审查”(intermediate scrutiny)。关于中等程度的审查,可参见Chemerinsky, supra note 15, at 553, 769-802.
五、实体性正当程序对当下中国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重实体、轻程序乃至程序虚无主义一直是中国传统法制的一大痼疾。不过,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法制程序化”的论题之后,法律程序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法制建设和学术研究的焦点问题,(104)参见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司法实践中甚至出现了运用正当法律程序的精神判案的先例。(105)参见“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8)海行初字第142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一中行终字第73号,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第139~143页。随着人们对法律程序的意义的认识日益深化,程序的价值被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和地步——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程序”差不多成了“合法、合理”的代名词。然而,另一方面,各种程序空转乃至程序滥用现象又极其严重。例如,在有关公用事业价格调整的听证会上,“逢听必涨”似乎已成为一种惯例和常态,甚至可以说,听证会已沦为必然涨价的服务性“手续”。这反映出在我国的程序制度尤其是在人们的程序观念中缺失“实体性正当程序”,并由此造成很多问题。因此,研究实体性正当程序对当下中国的参考、借鉴意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型: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方向引领作用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当中,对“法治”的基本内涵及其价值的理解是一个本源性、基础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形式法治主义”与“实质法治主义”这对概念和范畴,正是学术界基于理念差异、价值偏好、推理方式、制度安排等因素对法治所作的类型化区分,它们为探讨法治的特征及发展规律创设了科学的视角,是学术研究经常依托的概念载体和理论平台。(106)参见江必新:《论实质法治主义背景下的司法审查》,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6期。
对于“形式法治主义”和“实质法治主义”的概念,目前尚无权威性定义和一致意见,例如,也有人称之为“形式意义的法治观”和“实质意义的法治观”,(107)参见陈新民:《法治国公法学原理与实践》(中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4页。但对其基本内涵和价值的理解仍然存在高度共识。一般认为,形式法治只寻求形式合法性,以符合实在法为限,而实质法治则强调实质合法性,追求法律背后的道义原则的实现。(108)参见陈新民:《德国十九世纪“法治国”概念的起源》,载《政大法学评论》1996年第55期;高鸿钧:《现代西方法治的冲突和整合》,载《清华法治论衡》(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以下。易言之,前者是任何法律体系要有效实施都必须具备的条件,它仅是一种浅度的法治(thin rule of law),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包含了某些特定的价值要素如保障个人自由、约束国家权力恣意滥用等等,它是一种深度的法治(thick rule of law)。(109)参见前引,陈新民书,第127页;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从法治的发展形态来看,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都呈现出由形式法治主义向实质法治主义转型的趋势。
反观我国,前述“符合程序”的说法暴露出当下中国典型的形式法治主义特征。当然,形式法治主义并非一无可取,相对于纯粹的人治,形式法治是巨大的进步;形式法治还是实质法治的前提,实质法治离不开形式法治的基础性支撑,否则就会导致擅断和恣意。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形式法治,固步自封,裹足不前,则有违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要求。诚如有学者所说,“法治如果仅是强调政府一切作为依循现行法却不能防止政府滥用法治来侵犯人民,此法治即无任何意义可言”,或者说,法治国家只剩下一个“合法性的空壳”。(110)英国学者瑞兹(Josepf Raz)和德国学者萧勒(U. Scheuer)的评述,参见前引,陈新民书,第104、127页。因此,我们的法治国家建设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治的品质亟待提升,即需要从形式法治主义向实质法治主义转型。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不难发现,其中的“良法善治”之论断和表述,提出了我国的法治建设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型的任务。(111)参见李树忠:《迈向“实质法治”:历史进程中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1期。
在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型的过程中,实体性正当程序可起到沟通、连接二者的桥梁作用。因为,从程序的视角来看,程序性正当程序强调的是形式法治,而实体性正当程序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一切政府行为不仅需要在形式上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必须具有正当的目的和充分的理由。简言之,实体性正当程序要求实质上的合法性。这与实质法治主义的内涵及内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引入实体性正当程序的理论和观念,有助于我们摆脱形式法治主义的思维惯性,有助于克服形式法治主义的局限性,从而破除其种种羁绊。有理由相信,引入实体性正当程序的理论和观念,可以从法治模式的高度,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从形式法治主义向实质法治主义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实体性正当程序可以发挥的方向性引领作用,值得进一步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深层次的挖掘。(112)在法治的类型判断和方向探索问题上,中国的实际情形非常复杂,因为当下中国面临着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形式法治并未完全建立,另一方面实质法治又显然不足。因此,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既要向实质法治转型,又要加强形式法治。在程序问题上,或许还需要防范已经初露端倪的程序法制形式主义倾向。这一问题需要另外专文探讨。
(二)如何保证“良法之治”:可作为违宪审查根据的实体性正当程序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论及“法治”的内涵这一本源性问题时曾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这种“良法之治”的思想源远流长,并在前述《决定》提出的“良法善治”命题中得到了呼应。《决定》同时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良法之治”呢?
张维迎教授在讲到行政审批制度时曾说,很多东西是用法律来规范的,但如果这个法律与天理不符、与自然法的精神不符,这样的法治充其量只是秦始皇的那种“法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比如)现在的审批制,政府权力都会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非常糟糕,但“冠冕堂皇”,说这就是“法治”。政府制定的法律本身,并不能为政府的审批权提供正当性,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点。(114)张维迎:“市场秩序的形成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第二期北大博雅公法论坛上的发言),北京大学法学院,2013年9月26日。
张维迎教授的批评所针对的正是形式法治主义的倾向和做法,他的批评一点也不为过。日前,有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发言说,“连饮料换个口味都要重新审批”。(115)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发言说:“我们企业做饮料,其实按照道理来说,一张牌照也就够,但是现在换个口味都要重新审批过,实在太过于繁琐。”参见王曦煜:《宗庆后:行政审批改革要更彻底》,载《钱江晚报》2015年3月7日。其实,情况并不限于行政审批领域。用“法律”的形式攫取权力、侵犯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做法并不鲜见。而行为主体都还振振有辞,因为它有“法律”作为凭据。形式法治主义往往片面放大法律的形式意义,其绝对化表现就是所谓的“恶法亦法”。(116)参见前引,江必新文,第48页。不难发现,很多充满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法律”都被坚称为“法律”。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亟需建立能够有效识别、过滤违宪之立法并将其从现行法律体系中排除出去的违宪审查机制。
我们知道,根据现行立法体制,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法律外,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有权制定规章,根据《立法法》拥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可以颁行司法解释,“出释入造”。如此庞大的法律规范体系是否会与宪法发生抵触,发生抵触后如何来认定和处理违宪之立法,值得研究。毋庸讳言,当前,违宪的法律法规确实存在。但是,由于缺少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迄今尚无一例违宪的法律法规被撤销。(117)参见韩义雷:《还有多少违宪的法律没有修改》,载《科技日报》2014年5月5日。暂且不论狭义之法律,以前曾受到千夫所指被称为“中国21世纪初的最大恶法”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还是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沟通、协调”下,最后由国务院自行将其废止并另行颁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了事。(118)“沟通、协调”的说法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傅莹于2015年3月4日在首场新闻发布会上的用语。
应该说,目前,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制还是有的,但是在整体上显得非常粗放,可操作性不强,实际效果不彰。(119)陈云生教授指出,现行的宪法监督体制从根本上违背了一般的监督规则。中国的宪法监督体制存在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我监督”的根本性缺陷,这是它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甚至运作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参见陈云生:《违宪审查的原理与体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240页。有学者甚至称其基本上处于植物人式的“休眠状态”。(120)参见章剑生:《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件(1985~2008)为例》,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故而,当前的宪法监督体制需要进行重新考虑,特别是需要改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我监督”这种违反程序理性的根本性缺陷。我们认为,由全国人大制定《宪法监督法》,成立专门的宪法审查监督机构,专司宪法审查监督职责,是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的必要路径,也是落实前述中共中央《决定》提出的“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的内在要求。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015年3月修订通过的《立法法》大幅度扩大了地方的立法权,将原来49个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市(省会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扩大到全国所有设区的市,其总量达到284个。(121)另外,广东省东莞市、中山市,甘肃省嘉峪关市和海南省三沙市这四个未设区的市也获得了地方立法权。参见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015年3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年3月15日修订通过)第72条。而前不久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53条已经明确将“规章”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之外。(12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失有效的针对立法行为的违宪审查机制,地方立法权的扩大可能会导致的立法滥权之后果令人堪忧。
在对各级立法进行审查时,实体性正当程序是一项非常有用的审查标准,通过审查立法是否具有充分的正当目的,特别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干预是否为某种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之所需,以及立法所选择的手段与其目的是否相适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那些形式上合法的违宪、违法之“法律”。仍然以前述拆迁条例为例,即便国务院颁布了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但是,从实体性正当程序的视角来看,新法规还是存在严重问题。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的房屋征收中,真正的征收标的并不是当事人的房屋,而是房屋下面的土地。房屋不过是土地上的附着物而已。政府征收当事人的“破房子”有何用?征收过来的直接目的就是将其拆除,然后将房屋下面的土地转用作他途。因此,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真实名称其实应该称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与补偿条例”,所谓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掩盖了对土地使用权进行征收的事实,并为不予补偿或者少补偿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施放了掩人耳目的烟幕。(123)参见刘东亮:《拆迁乱象的根源分析与制度重整》,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由此说明,“沟通、协调”具有一定作用,但是作用有限。这也从反面证实了建立切实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的必要性。
总之,实体性正当程序对那些无论是否符合《立法法》规定的立法程序的各级立法都可以起到约束作用并在事后作为违法、违宪审查的根据,从而为实现“良法之治”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如何实现“行政善治”:可作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实体性正当程序
前述中共中央《决定》不仅提出了“良法之治”,还强调了“善治”。(124)“善治”(Good governance)是上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针对普遍存在的“治理失效”提出的一种新的治理理论,之后在西方公共管理学上蓬勃兴起。中国学界俞可平、陈广胜等人率先将西方的善治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对善治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和发展。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陈广胜:《走向善治:中国地方政府的模式创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模式。善治有利于充分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有利于权利的保障,有利于调节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良性关系,并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125)杨春福:《善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模式》,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5期。由于善治是立基于法治基础之上的, 因此,善治的运用应当考虑到作为其背景框架的法治主义。(126)同上注,第27页。这种背景框架无疑是我们在前文讨论的实质法治主义(良法善治)。
具体到行政领域,可以说善治即“行政善治”,它是在实质法治主义层面对“行政法治”提出的更高要求。
那么,如何实现“行政善治”呢?我们认为,将实体性正当程序贯彻、落实到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等各个环节是实现“行政善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尤其是在行政诉讼制度中,实体性正当程序的要求可以反向作用于行政领域,这对于促进“行政善治”的实现,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127)鉴于行政立法在前文已有涉及,行政决策问题我们另有专文论述(参见刘东亮、房旭:《行政决策的实质性正当程序之规制》,载《行政管理改革》2015年第1期),故本节主要阐述实体性正当程序对一般行政行为的要求和作用,特别是其如何通过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行为产生反向影响。
具体而言,在行政诉讼制度中,实体性正当程序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在实体方面,行政行为应当具有正当的目的,即具有“合目的性”(Zweckmässigkeit);二是在程序方面,行政行为程序本身不仅应当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即符合“法定程序”,而且还应当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即不存在“程序滥用”之情形。
检视现行《行政诉讼法》,中国目前事实上已经形成以合法性审查为主、以正当性审查为辅的司法审查格局。(128)参见江必新:《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司法审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这可以从《行政诉讼法》第6条关于“合法性审查”这一原则性审查标准和第70条关于“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等具体适用性审查标准之规定得出结论。(129)其中,“明显不当”在原《行政诉讼法》第54条中的用语为“显失公正”。不过,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了“滥用职权”“明显不当”标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援用上述规定作出裁判的案件非常罕见。(130)据不完全统计,在《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1992-1999年合订本)所选录的270个案例中明确适用“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的只有6个案件;在《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2000-2004年合订本)所选录的242个案例中明确适用“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的只有5个案件。参见沈岿:《行政诉讼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之议》,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另据何海波教授的统计,从《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初到2005年在《人民法院案例选》所选录的614个行政案例中,有297个案件属于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其中将“滥用职权”作为唯一司法审查标准的案件只有10个,使用频率仅为3%。参见何海波:《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兼议行政司法审查根据的重构》,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当法院遇到涉及行政机关滥用职权问题的案件时,往往采取规避策略,要么以“协调”方式与行政机关沟通,促使其作出让步以满足原告诉讼请求,最终以换取原告撤诉的方式结案而回避对滥用职权的判断;要么将本属于滥用职权的情形转换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处理,试图根据这些标准从直观层面增强判决的权威性。至于程序滥用情形,以滥用职权或者显失公正标准进行审查并予以撤销的几乎没有。(131)参见前引,江必新文,第135页。
对于这种罕有运用“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的现象,有学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并不是滥用职权引发的案件少,而是法院倾向于使用更客观的审查标准的策略所致(可称之为“转换型审查策略”),或者说是审查标准“转移率”高的缘故。(132)参见余凌云:《对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从若干判案看法院审理的偏好与问题》,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因为,对于滥用职权,很难适用具体的法律条文直接衡量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作出判断。在学理上,对于何谓滥用职权,始终存在极大的分歧,学界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33)参见朱新力:《行政滥用职权新定义》,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 3期;关保英:《论行政滥用职权》,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再加上刑法中规定的“滥用职权罪”有如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法院对适用“滥用职权”都心存忌惮。结果,“滥用职权”成了一个没有确定内容、任人解释的“面条”条款,(134)参见前引,何海波文,第60页。这一标准也因此被束之高阁,很少使用。
我们认为,引入实体性正当程序理论,可以解决“滥用职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拿捏适用的尴尬困境。实体性正当程序所蕴含的“合目的性”审查,(135)虽然论述角度和切入点不同,已经有学者提出我国行政诉讼需要增加“合目的性审查”的问题。参见解志勇:《论行政诉讼中的合目的性审查》,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可以使司法审查暂时抛开滥用职权是否存在“主观恶意”的问题,而将对动机、意图的主观判断尽可能转换为是否“违背法定目的”的客观性判断。(136)参见前引,江必新文,第136~137页。另一方面,实体(质)性正当程序对行政行为的程序所要求的实质上的“正当性”,对于无论是否存在“法定程序”的情形,都可以进行正当性审查,从而避免那些所谓的“符合程序”的程序滥用行为成为法治的“漏网之鱼”。(137)从技术角度讲,法院对行政程序进行正当性审查,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为对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判断所涉及的专业技术性问题和政策含量都远低于行政实体问题。参见前引,江必新文,第124~127页、第137页。
六、结语
我们在研究法律程序时,总会遇到一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健全、合理的程序为什么不一定能保证得出公平、公正的结果?不难理解,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二是程序运用者本身怀有不正当的目的。再度借用张维迎教授的话来说,一是“无知”,二是“无耻”。(138)张维迎,前引。在现实生活中,称得上“无耻”的行政行为不胜枚举。(139)比如,为了给庞大的超编执法队伍发放工资福利,河南某地运政、路政执法部门对过往车辆进行巨额罚款、多头处罚,并实行罚款月票、年票制,致使已经缴纳过罚款并购买了罚款月票的车主仍然再度受罚以至于实在不堪重负而服毒自杀。当地执法部门称其处罚“符合程序”。参见《河南永城公路乱开巨额罚款 车主不堪重负自杀》,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出时间:2013年11月30日21:30时。而实体性正当程序恰恰是防范这种“无耻”的屏障和揭露“无耻”的利器。在实体性正当程序的聚光灯下,一切所谓的“符合程序”的做法和谎言都会原形毕露、无处逃遁。从正面来说,正当性审查(特别是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司法审查),作为法治国家建设在当前应当被深入挖掘的增长点,是刺激政府权力不断向善的新的动力源。(140)参见前引,江必新文,第123页。换言之,通过实体性正当程序充实、完善现有的法律程序理论和相关法律规定,可以为我国现阶段的行政法治走向“行政善治”创造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条件。
总之,与传统的程序性正当程序不同,实体性正当程序要求权力的行使必须具有正当的目的。由于其具有防范、揭露权力滥用的功能,它对于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特别是行政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
参考和借鉴价值。当然,由于实体性正当程序毕竟属于先进法治国家的舶来品,其发生、发展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制度环境,如何利用本土文化资源,使这一理论和观念能够为人们在思想上所接受并与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相对接、整合,是需要学界进一步研究的未尽课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YJA820012)、浙江省社科规划“之江青年学者”项目(项目编号:13ZJQN054YB)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东亮,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