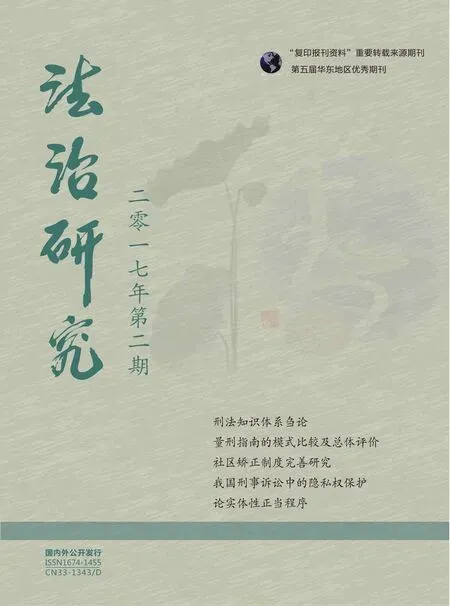非传统安全犯罪:范畴厘定与刑法教义学转型*
阎二鹏
非传统安全犯罪:范畴厘定与刑法教义学转型*
阎二鹏**
非传统安全观是安全领域的一场思想革命,其在安全的指涉对象、涵括范围、主体表现、实现路径四个方面与传统安全之间存在质的区别,价值层面亦可将其诠释为“人类社会共同体共同面临的威胁”;非传统安全犯罪是非传统安全观的法学视角展现,但两者之间并非等置关系,非传统安全犯罪范畴之确定取决于其对非传统安全之侵害程度或者危险是否达到了“安全化”之高度;我国当下刑事立法已然呈现出“综合安全观”之思维,非传统安全犯罪概念之提出亦使得传统刑法教义学体系面临普适刑法学、刑法学与刑事政策的贯通、预防型刑法等逻辑转型。
非传统安全 国际关系学 刑法教义学
冷战的结束与两极世界的瓦解,代表着以军事对抗和政治对立为特征的传统安全大大缓解,而伴随全球化趋势,来自军事、政治领域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的威胁成为比传统安全威胁更常见的不安全因素,因此,将安全重点转向超越国家差异之上的社会和人的安全的非传统安全观念正深入人心。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为一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命题,嗣后新《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将这种总体国家安全观予以法律化、制度化,标志着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关乎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是刑法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刑法存在的根基”①陈兴良:《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及其理论基础》,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7年第5期。尽管学理上对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与社会保护机能之逻辑优位关系尚存争议,但对此两种机能作为刑法的基本机能是没有异议的。的共识性命题意味着“安全”亦应构成形塑刑法学体系的重要参数,故围绕非传统安全犯罪的刑法学理分析自其产生伊始即应肩负刑法教义学转型的使命。
一、安全思维的演化——安全理论发展的谱系考察
安全问题历来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传统重点领域,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国际关系学视域下,人们的安全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安全已不单纯是人们所理解的基于传统军事威胁所可能引发的领土主权安全,一种超越国家之上或曰人类社会均可能面临的共同安全威胁观念正逐渐被学理及国际社会实践所证实。
(一)情境确定: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脉络梳理
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视域下,无论是传统安全抑或是非传统安全观念都源自于对“安全”的思考,“安全”作为任何安全观建构的逻辑起点既是学理归纳更是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实践使然,“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与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发生发展方式紧密相连”。②于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二战之后,人类社会经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使得“和平”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价值取向,嗣后伴随冷战结束及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逐渐取代“和平”成为人类社会主导的价值选择,故此,学理上将冷战结束作为非传统安全观产生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二战虽已结束,由于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对峙,使得就一国之国家安全而言,来自于军事、战争威胁自然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而“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最为明显的就是以美苏对抗为标志的两极格局的瓦解和随之而来的安全气氛的缓和”,③何忠义:《“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军事威胁的缓解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契机,长期以来被冷战所掩盖的危及人类发展的其他矛盾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等逐渐凸显,有别于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的新的安全问题被提出是顺理成章的,而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个国家的依存度不断增强的同时,亦使得“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的命题成为可能,上述影响人类发展的普适性问题形成威胁人类安全的普遍性因素。而“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明确提出则肇始于冷战后西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界,1983年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理查德·乌尔曼(Richard H. Ullman)在《重新定义安全》一文中率先提出将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自然灾害、疾病、环境等问题纳入安全范畴,从而被学理上普遍公认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鼻祖。其后学理上关于非传统安全的研究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学术研究文献既有针对宏观层面的诸如非传统安全的理论流派、研究范式、价值内涵、与传统安全之分野等内容,亦不乏微观层面的诸如经济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具体非传统安全内容之拓展。国际安全问题知名专家英国学者巴里·步赞(Barry Buzan)将“后冷战时期”国际安全研究的学理路径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端,前者仍然围绕冷战时期传统之战略研究、军备控制研究等以“和平”研究为内核而展开,后者则完成了由和平向发展的价值转换,亦形成了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等所谓“后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不同理论流派,④参见[英]巴瑞·步赞:《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这些学术文献成为当今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学术资源。⑤此一演进过程不仅得益于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若干理论流派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亦是国外非传统安全研究制度化的结果:当今发达国家通过官方、半官方成立有关非传统安全的专门研究机构的做法相当普遍,国际上较为知名的研究机构如美国加州大学的“非传统安全事务中心”、匹兹堡大学的福特研究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等借助其各自侧重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主题,通过定期举办国际会议,发布针对世界各地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等多种形式为各国政府提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政策咨询。
非传统安全之于中国虽“出现”较晚,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弱势地位,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更加突出”,⑥张伟玉、陈哲、表娜俐:《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兼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载《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2期。且更多地呈现出某种政策导向: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与经济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从而直接促成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唐家璇在第七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首次提及“非传统安全”。以此为契机,学理研究逐渐呈现出由非传统安全价值层面的基础问题研讨向实践问题导向的转变,以前者作为基本研究范式的代表性观点如“非传统安全观念的提出是安全观念的一次革命,并将非传统安全提炼为基于‘共患意识’的‘共享安全’的伦理高度的主张”⑦参见于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抑或将非传统安全解读为以“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为基础的一种安全新语境;⑧参见王逸舟:《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载《人民日报》2003年5月22日。后者从具体非传统安全领域出发进行对策探究式的研究范式则获得了更多学者的青睐,更多的具体非传统安全议题诸如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网络安全、海上通道安全等,以此为基础着眼于中国的立场对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具体研讨,“非传统安全是一个政策性的概念”是对此种研究进路的高度概括。
(二)价值论争: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分野
尽管早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就已出现突破片面强调军事、政治因素的安全观念和安全研究,“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安全研究”等同于“战略研究”的公式化表征早已备受诟病,取而代之的非传统安全观念获得了学理和国家外交实践的共识,但时至今日,安全概念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⑨Barry Buzan, People , States, and Fear :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2nd ed. ) . Lynne Rienner, 1991, pp.3-5;有学者甚至悲观地认为“安全天生就难以被给出统一、明确和无争议的定义”。(Arnold Wolf 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67, no. 2 (Fall1952) , pp. 482~511)就非传统安全概念而言,亦然。当今国际学术界不仅对非传统安全的类型、领域等具体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对非传统安全的独立地位、性质、定义等基础问题亦存有争议,但学理上的聚讼非但没有引发对此一概念的价值怀疑,反而使得,“对任何一种安全的全面理解只有在与另一种安全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获得,局限于单一的层次或领域审视安全的尝试将招致严重的曲解”,⑩[英]巴瑞·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这样的观念获得了共识。故在分析路径上,从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比较的视域下,对非传统安全的内涵、边界等进行描述已成为当今学界一种通行的做法。
学理上一般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分野归结为安全的指涉对象、安全的涵括范围、安全的主体表现及安全的实现路径等四个方面:就安全的指涉对象而言,传统安全起源于冷战思维,故在其视域下,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此亦形成国家作为指涉对象的思维范式,与之相反,非传统安全在“和平”与“发展”的理念支配下,抛弃了以国家、地域划界的传统思维,更侧重将个体安全作为指涉对象;具体到安全的涵括范围,亦即威胁安全之风险源,传统安全在冷战思维下将威胁安全的来源局限在军事冲突领域,国家安全与军事安全等置自是其逻辑归结,非传统安全的覆盖范围则延伸至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非军事因素引发的跨国性、全球性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将国家视为唯一的安全主体,其着眼点是国与国之间的主权、领土与利益差别,故国家安全亦可与传统安全等置,而非传统安全着眼点在于超越国家之上的无差别的人类个体,个体安全亦是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就安全的实现路径而言,传统安全着眼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来自于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威胁,故其安全化的实现路径只能通过政治谈判、军事战争等手段解决,而非传统安全因其根植于个体性安全的思考,故必然超越传统意义上一国一域内的国家安全概念,安全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成为可能,消除危及全人类的安全威胁自然必须通过各国之间的合作。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关系,究其实质就是非传统安全的独立定位问题,此一问题的研讨在非传统安全概念产生的西方国家早已展开,国际关系学领域对冷战后非传统安全理论流派的梳理正是围绕该种理论学说如何解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关系这样的核心建构的,无论是“后冷战传统主义”流派抑或是所谓“正统派”均强调“应该以国家间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对军事威胁的使用、控制和管理的研究为主体”,⑪朱峰:《非传统安全解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然而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的研究范式不仅逐渐为嗣后的“扩展派”甚至是“全球派”等建构主义安全研究所取代,而且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所提出的“人的安全”概念更是宣告传统安全研究的全面败退。简言之,学理上虽然对非传统安全的定义仍存有争议,但伴随全球化进程与若干影响全球的共性难题的出现,使得这一概念不仅在学理上形成了一种共识,亦通过各国的外交实践得到印证,一种超越“利益划线、人权划界”的跨国性场域正逐渐建构,无论是从价值层面、政策层面抑或是具体问题层面出发,“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然成为一种人类社会共同体共同面临的威胁”的观念成为一种共识性命题。
二、非传统安全犯罪基本范畴厘定
与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针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如火如荼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传统安全的法学视野可谓空白地带,与之相应,针对非传统安全所衍生之非传统安全犯罪在学术文献中亦难觅其踪。中外学理及实践中虽然对具体的非传统安全犯罪如海盗罪、恐怖主义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等进行了卓有成效之研讨,但在这些有限的学术文献中,热点导向型、问题导向型的研究占据了主流,如近年来我国边疆恐怖主义势力抬头,学理上则因应对恐怖主义犯罪、有组织犯罪的规制对策进行分析。同样,海盗、海上恐怖主义一度甚嚣尘上,此问题也随之成为法学视野中的热点问题,针对这些犯罪的文献亦集中出现。⑫其实,域外有关非传统安全犯罪的研究亦呈现出相似之规律:域外文献中随处可见的是诸如 maritime piracy (海盗犯罪)、environmental crime(环境犯罪)、terrorism crime(恐怖主义犯罪)、oil crimes(石油犯罪)等表述,亦可见non-traditional security(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非传统安全威胁)等类似表述,但并未出现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rime(非传统安全犯罪)这样的词汇,作为各种具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犯罪的上位概念,非传统安全犯罪的内涵与外延之廓清无疑是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不可否认,这些问题的研讨已经使非传统安全问题渗入了法学视角,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对策性研究为主的态势无法形成体系化、系统化的思维,而宏观上建构一种非传统安全犯罪的观念不仅是学理探讨亦是实践应对所必须的。
(一)非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犯罪之逻辑关系
非传统安全犯罪这一概念的提出既然由非传统安全衍生而来,那么逻辑上从非传统安全导出非传统安全犯罪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换言之,非传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犯罪的上位概念是没有异议的,但这种逻辑上的上位、下位关系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传统安全所指涉的具体内容都可能与非传统安全犯罪形成关联,而是可能呈现出重合、交叉、排斥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一,影响非传统安全的因素或者说非传统安全威胁本身即表现为某种犯罪类型。在国际关系学界,对非传统安全所指涉的具体内容中本就包含若干犯罪形式,如毒品走私、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海盗、跨国洗钱、武器走私等被公认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之一,并成为各国外交实践中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重点内容;其二,更多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其安全威胁因素包含多个方面,某种犯罪类型只是其威胁因素之一,如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常常提及的经济安全,影响经济安全的因素既可能是各国的经济政策、金融政策,也可能是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犯罪,这些经济犯罪中既有局限于一国领域内的经济犯罪,亦有可能表现为跨国性质的经济犯罪。能源安全亦如此,影响能源安全的因素一般是能源结构、能源消费水平、能源供给渠道、能源价格机制等,⑬参见迟春洁、黎永亮:《能源安全影响因素及测度指标体系的初步研究》,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但若考虑到能源安全是一个集生产、供给、运输等为一体的综合体系,影响这些环节的因素均可能威胁能源安全,故像我国这样高度依赖海上运输保障能源安全的国家而言,诸如海盗罪、海上恐怖主义犯罪等亦可能对能源安全形成威胁;其三,某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与犯罪没有关联,最为典型的是自然灾害,其本身并不会与任何犯罪类型产生关联,故不属于非传统安全犯罪的基本范畴。
通过关于非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犯罪的上述逻辑梳理,可以发现,非传统安全犯罪范畴之确定必须厘清两个问题:一方面,非传统安全犯罪来源于非传统安全之概念,前者是后者的衍生,某种犯罪类型被归类为非传统安全犯罪必然是对某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危险源;但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与非传统安全存在关联的犯罪类型都可归类为非传统安全犯罪,如上文所述,威胁非传统安全之因素与非传统安全犯罪并不完全等同,当非传统安全威胁来源直接表现为某种犯罪行为时,将此种犯罪类型归类为非传统安全犯罪自然无异议,但如果某种犯罪类型只是影响非传统安全的因素之一时,是否能视为非传统安全犯罪则需谨慎判定。其实,从前述关于具体非传统安全的指涉对象可以看出,除自然灾害等极个别之非传统安全领域外,其他非传统安全总是与犯罪之间呈现出某种联系,如具体的经济犯罪、环境犯罪、网络犯罪等都是对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网络安全之侵害,即使如人口安全、非法移民、重大传染性疾病等本身表现为某种社会现象的非传统安全亦可能与非法偷越国边境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特定的某种犯罪发生关联,如此无限推演下去,非传统安全犯罪将如非传统安全概念一样成为无所不包之范畴,如果说非传统安全之概念的泛化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视域下有其必要性,那么,在刑法学视域下非传统安全犯罪之范畴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
(二)非传统安全犯罪确定之关键
非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犯罪之逻辑关系表明,两者之间并非完全等置,影响非传统安全之威胁因素即使表现为犯罪形态,亦须以相应的附加条件限制,一者与国际关系视域下的“安全”观对应,二者与刑法学自身的目的性相合。
对此,笔者认为,某种犯罪类型能否被视为非传统安全犯罪关键在于其对非传统安全之侵害程度或者危险是否达到了“安全化”之高度,⑭部分学者提出“涉非传统安全犯罪”的概念用以指称与非传统安全相关联之犯罪,同时将非传统安全范畴之甄别标准归结为“涉非传统安全犯罪的安全化”命题,此一命题极具启发意义。参见王君祥:《非传统安全犯罪解析》,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此一甄别标准意味着:首先,“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的常识性命题转换为非传统安全犯罪的情境,则意味着某种犯罪类型被界定为非传统安全犯罪,其一定是对某些非传统安全领域整体或某个环节形成直接危险的风险源。其次,“安全”就国际关系学视域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在当今国际社会实践的综合安全观之下,非传统安全犯罪意味着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将“涉非传统安全犯罪的安全化”界定为“该犯罪危害性得到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政府机构、社会机构以及公众普遍认可的,对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威胁或者侵害的情形”⑮参见王君祥:《非传统安全犯罪解析》,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固然没错,但在国际关系视域下安全必然指向了跨越地域之上的人类共识,当某种安全上升为国际性、整体性的安全高度,相应的这些领域的犯罪在犯罪手段或者危害后果上必然具备跨国性特征,其危害程度亦为国际社会所公认时才应被归属为非传统安全犯罪,如毒品走私、恐怖主义犯罪、跨国洗钱等犯罪行为;相反,当某些犯罪类型其危害性仅局限于地区性、局部性时自然无法形成对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威胁。换言之,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对人类社会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观从其诞生之日起即呈现出超越国家间利益的特性,非传统安全在地域上的弥散性和跨国性亦使得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形成紧密联系的整体,而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安全犯罪自然因应具备“侵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特征。再次,“非传统安全不是国家之间的相互安全威胁,而是国家群体乃至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⑯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精髓,这就注定了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是某个国家制造抑或独有之难题,“国内安全外溢”与“国际安全渗入”伴随国内安全国际化与国际安全国内化演化为非传统安全观之下的必然结果,同理,应对此种安全问题自然不可能由某一个国家完成。非传统安全犯罪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在危害手段、后果上的跨国性、弥散性特征决定了其应对措施亦不可能单纯依靠片面化、单一化的一国力量,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既是逻辑必然亦是实践必须。虽然在当前的国际实践中,希冀通过超国家的刑事法院应对非传统安全犯罪的措施更多地具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是,非传统安全犯罪的跨国性、国际性现状又必须借助一定的“超国家”层次上的应对,治理非传统安全犯罪的现实需求与国家主权因素妥协的结果便是,“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前提,又适当考虑国际共同利益保护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就充分体现出自己适应国际刑法‘两重性’特征的优越性”⑰张旭:《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现状、问题与应对》,载《刑事法评论》2000年第1期。,从而在尊重各国司法主权与惩治跨国犯罪之间寻求到了一条更为理性的衡平路径,此亦成为现阶段惩治与防范洗钱、贩毒、国际恐怖主义等诸多跨国性犯罪的主要形式。
通过上述逻辑梳理,对非传统安全犯罪之范畴可厘定为“危及人类整体安全的在犯罪手段或者危害后果上具有跨国(境)性质的一类犯罪”。⑱参见阎二鹏:《海上非传统安全犯罪与中国刑法之应对》,载《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4年第8期。
三、非传统安全犯罪与刑法教义学的转型
非传统安全犯罪概念的提出是新安全观视野下对犯罪类型之再审视的结果,而新安全观之理念已经在我国刑事立法的实然层面得到回应,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将“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完善刑法的相关规定”作为此次刑法修正的目标和任务⑲参见李适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1年第2期。。而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提出正是以非传统安全为重心的集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为一体的综合国家安全体系,“作为社会安全的最后和最重要的保障法,刑法的整体机制将对这一新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⑳陈璐:《新国家安全观要求刑法转变整体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1日。非传统安全犯罪作为一种新类型犯罪的出现,不仅对刑事立法产生重要影响,亦对关注逻辑自洽与原则演绎的传统刑法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在刑事立法的现实框架下,刑法教义学亦面临转型之必要。
(一)普适性刑法的证成
传统刑法学研究方法执着于教义刑法学的范畴,即“以刑法规范为根据或逻辑前提,主要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将法律规范、概念、原则、理论范畴组织起来,形成具有逻辑性最大化的知识体系。”㉑周详:《教义刑法学的概念及其价值》,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6期。这种意义上的刑法教义学使得刑法学的研究范式强调以“法条”为中心采取注释与逻辑推理的方法,去找寻刑法规范的真实含义,以现行立法作为绝对之信条被奉为教义学之基石而无法动摇。教义学偏重于解释功能的现实导致其批判机能被有意无意的弱化,对良法建构的推动价值阙如,亦使得其难以关照法条本身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实际效果,从而更关注刑法适用的国别主体性。由于非传统安全犯罪概念的提出,拓宽了刑法学的视野,并使得跨国性场域中的“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威胁”成为可能。虽然国际刑法学界对如何阐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仍存有分歧,但当下的国际社会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早已从以往的封闭状态转变为开放与交流的常态,改善经济环境的内在需求使得各国之间在人员交往、物资交流与信息传递等方面日益频繁,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等诸方面的依存度空前提高,这使得国际社会本身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获得了现实基础,世界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并没有妨碍国际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的事实本身。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犯罪的跨国性特征亦决定了对其的应对措施亦不可能单纯依靠片面化、单一化的一国力量,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既是逻辑必然亦是实践必须。从当今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现状来看,区域性与国际性的刑事司法合作发展迅猛,合作领域亦不断扩展,跨国洗钱、有组织犯罪、经济犯罪、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渐成各国刑事司法合作的主要领域,不仅如此,在合作内容上亦不断丰富,从文书送达、调查取证、证人和鉴定人出庭,赃款赃物的移交、刑事判决的通报、引渡等司法协助措施到信息交流、人员交流与培训、执法协作和共同研究等辅助合作方式,遍及司法协助、警务合作、情报交流、案件协查等多个层面。总之,非传统安全犯罪的出现使人们的关注重点自然而然地从国内的法律规范转向区域性甚至世界性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等,刑法教义学在此层面实现“普适刑法学”的建构亦成为可能。㉒参见[德]乌尔里希·齐白:《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周遵友、江溯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页以下。
(二)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贯通
由古典刑法教义学知识体系所建构的传统刑法学体系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解读为分立的二元式逻辑结构,前者基于“法治国”的一般构想,将罪刑法定原则视为刑法教义学、解释学之依归,通过客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亦通过构成要件论、违法论、罪责论等层面进行微观建构,意在追求古典刑法教义学自成体系,纯法学技术分析方法及刑法解释学成为其代名词;与之对应,刑事政策则代表刑法之立法目的在于法益保护机能的实现,如果说教义学之分析是以行为为中心,那么刑事政策之成立则是以行为人为中心进行建构,其分析范式以因应“ 合目的性”作为其最终旨趣。在此逻辑前提下,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被解读为性质不同、目的各异的分离体系,这种二元式的逻辑架构亦被称为“李斯特鸿沟”㉓[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第二版),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译者注。。而非传统安全基于“安全”观的省思,拓展了安全的覆盖范围,相应地,非传统安全风险成为一种“全球性风险”,在逻辑内涵上与“风险社会”理论的解读完全一致:从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背景来看,其逻辑基点在于对后工业化时代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学观察,按照其逻辑演绎,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所体现的现代性有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之别,前者以地域上的民族国家为单元,其间的社会关系、社区及国民生活方式等均以地域为界,而后者则突出地体现为跨越地域限制的风险全球化特征,这与非传统安全观的倡导者一直以来解读的非传统安全风险的跨国性、全球性特性暗合;不仅如此,风险社会理论所强调的“风险”概念,究其实质亦可归结为“安全”风险,按照贝克的说法,“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我怕!”㉔[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此一关于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区别的生活化用语表述,清晰地揭示了“工业社会时代的‘发展’导向的政策基调,到了风险社会为‘安全’导向的政策基调所取代”,㉕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公众的不安感甚至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也正是非传统安全观的支持者所特别强调的非传统安全的价值所在。换言之,通过对“安全”的阐释使得风险社会理论与非传统安全理论达致了逻辑上的一体性。总之,无论是非传统安全风险抑或是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其化解途径或许是多元的,但无论如何刑事法律在面对这一社会现实时不可能无动于衷,通过刑法手段控制风险不仅是刑法功能主义的品格所决定,亦是公共政策影响刑事立法、司法及刑事法理的必然体现,通过“安全”观念的建构,公共政策成为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体系外因素,这一影响显然促成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逻辑贯通。
(三)预防性刑法的形成
古典刑法教义学体系是在批判欧洲中世纪刑法的罪刑擅断的基础上形成的,这自然形成了其偏重“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罪过责任、个人责任、报应刑观念等诸多共识性命题亦围绕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展开。但在现代风险社会下,非传统安全风险的普遍存在使得弥漫于社会中的制度性风险、技术风险等人为风险成为造成公众“不安感”的主要来源。面对公众对风险带来的不安感的加剧,通过控制、消除风险为公民提供制度性的安全保障必然成为主导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思维路径,而“刑法由此成为国家对付风险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借此大举侵入刑事领域也就成为必然现象”。㉖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简言之,人为风险作为现代社会的特质,而社会公众则笼罩在风险无处不在的不安感中,这种保障民众安全秩序的诉求直接主导了国家公共政策的走向,继而决定了刑法由权利保障向风险预防的功能性转向。风险预防的价值取向深刻地重塑了刑事立法实践与刑法学体系,刑事立法更加侧重于解决预防或者安全的问题,在犯罪圈的划定层面诸如“实体刑法中可罚性的前移”㉗[德]乌尔里希·齐白:《刑法的边界——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最新刑法研究项目的基础和挑战》,周遵友译,载《刑法论丛》2008年第4卷。、抽象危险犯的设置、持有型犯罪的设置、预备行为实行化的规定等新的立法动向都在表明“有危险就有刑罚”㉘[日]关哲夫:《现代社会中法益论的课题》,王充译,载《刑法论丛》2007年第2期。、“行为方式本身可罚,而不是行为所引起的结果被认为是可罚的”㉙[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安全刑法:风险刑法的社会危险》,刘国良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等类似的预防本位的刑法理念。而在刑罚之目标设定上亦呈现出报应刑、特殊预防刑及威慑理论的没落,“借规范适用的固化为建构法的信赖竖起一面旗帜”㉚积极的一般预防论甚至被英美法系学者视为德国刑法学的两个重要成就之一。参见[美]马库斯·德克·达博:《积极的一般预防与法益理论》,杨萌译,载《刑事法评论》2007年第2期。的积极的一般预防正成为主导各国刑事立法实践的思潮。面对上述刑事立法变动,刑法学界不可能无动于衷,既然认可风险社会作为刑法学叙事的前提或者背景是成立的,那么,建构一种合乎现代社会特质的新型刑法体系就是必然的,风险刑法抑或安全刑法、预防刑法等学说流派正是伴随上述立法动向因应而生的,这些刑法学新体系的建构或许仍存在不足之处,但毕竟在传统刑法教义学关注逻辑体系内在的自洽性的同时切入了合目的性与实效性的思考,这也正是非传统安全风险观念对刑法学体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价值所在。
四、结语
“长久以来,无论是注释法学还是理论法学取得的进步,从历史、大社会、大法学的排列角度来看,大都存在视域过窄或方法单一的问题”㉛王作富、田红杰:《中国刑法学研究应当注意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古典刑法学体系通过刑法教义学的张扬不仅使得刑法学自身之教义学知识更为丰满和理论体系更显系统性,亦为刑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逻辑基础,但将刑法学建构成自为一体的逻辑体系作为古典刑法教义学的价值倾向亦可能异化为单纯追求刑法逻辑体系的自洽为目的,从而将刑法学视为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的危险。此一倾向已初露端倪:刑法学研究中呈现出的以部门法之间保护目的之不同为由所造成的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阻隔局面仍不时出现,刑法学者与其他部门法学者之间的对话仍未完全展开,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视角渗透更是付之阙如。晚近以来,我国刑事立法面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型犯罪,进而在立法中呈现出的犯罪圈扩张,立法技术中的预备行为实行化、帮助行为正犯化、犯罪构成要件扩充等诸多法律文本已使得古典刑法教义学体系的实践困境暴露无疑。多年前储槐植教授提出的“在刑法之外研究刑法”㉜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的理论命题在今天社会转型的现实下尤为必要,非传统安全犯罪作为一种新类型犯罪的出现,对关注逻辑自洽与原则演绎的传统刑法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刑法学研究不仅应破除与其他法域的学科壁垒,亦应跨越整个法学领域到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汲取必要之营养,最终实现传统刑法体系的结构性调整。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上非传统安全犯罪的刑事规制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3BFX06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阎二鹏,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