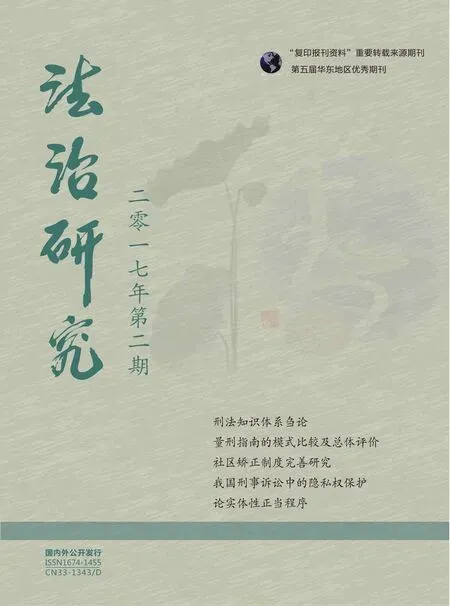刑法修正常态下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具体运用
肖中华
刑法修正常态下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具体运用
肖中华*
只有当新旧法律对于同一行为进行评价存在实质性的结果差异(而非条文形式变化)时,才有讲求从旧兼从轻的余地。刑罚以处罚具体的人和行为为对象,因此应当将有待评价的行为分别置于新旧刑法规范中进行具体的模拟裁判,得出分别的裁判结论后予以比较刑罚结果的轻重,而不能仅仅从形式上比较法定最高刑或最低刑。对于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实施的“特别严重情节的”贪污罪、受贿罪,只有当按照行为时的刑法规定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按照修正后的刑法规定应当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时,法院才可以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同时决定死缓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
从旧兼从轻 处刑较轻 规范解释
从旧兼从轻是我国刑法确立的、用以解决“行为时法与裁判时法不一致如何选择法律适用”问题的原则,其基本理论依据是罪刑法定蕴含的“行为时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如果公民的行为任凭事后国家制定的法律予以评价,则刑法便无任何安定性可言,公民也无任何安全性可倚,即使立法上确立罪刑法定亦仅流于形式而无限制刑罚权的实质意义。当前,通过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典进行修改补充,已成为我国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后刑事立法的常态。刑法频繁修正无疑带来新旧法律内容的变化,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具体运用问题便因而凸显且具有普遍性。由于刑法规范内容复杂多样、发生变化的形态或类型也有所区别,有的刑法规范还经历数次修正,一些待裁判的行为自其实施至被裁判时跨越了两次以上的修正,这些状况都给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具体运用带来了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讨有关问题。
一、正确把握从旧兼从轻原则运用的基本前提——刑法规范对事实的评价发生实质差异
从旧兼从轻原则以“从旧”为法律选择的基础规则、以“从轻”为法律选择的例外规则(当新法评价行为对行为人更为有利时因新法较轻而从轻),所以,只有当新旧法律对于同一行为进行评价存在结果差异(落脚点是处罚轻重的差异)时,才有讲求从旧兼从轻的余地;如果没有结果差异,从旧兼从轻则无从谈起(在新旧法律没有变化时无必要将适用行为时法特别表述为“从旧”)。因此,面对刑法修正,在发现新旧法律发生变化时,应当正确把握从旧兼从轻原则运用的基本前提,即确认对案件事实的规范评价有无发生实质变化从而带来评价结果差异。笔者认为,在刑法修正案频繁出台的情势下,特别须注意的是,对于以下情形不能不假思索地、单纯地从形式上判断法律有无变化及如何发生了变化,从而不恰当地“从旧”或者“从轻”,据以作出错误的法律适用结论:
第一,当刑法条文被修正但规范无实质变化时,应当认为新旧法律没有任何变化,在修正案施行后处理修正案施行前的行为,径直依照修正前的刑法规定评价即可。尤其是修正案仅仅在形式上增加构成要件要素、行为类型或者量刑情节时,不得将新增内容解释为实质上的新增类型(要件要素、情节),从而判断在修正案施行前,新增内容对应或包容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无罪或法律没有规定的情节,最终依据所谓“从旧”准则作无罪或无该情节处理。
例如,强迫交易罪在修正之前规定了两种行为类型——“强买强卖商品”和“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修八”)在保留该两种类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财产”和“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三种类型。笔者认为,上述三种新增行为类型中,至少“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拍卖”作为强迫交易罪的行为类型属于形式上、文字上的修正,规范内容与修正之前相比较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因为“拍卖”显然属于买卖的一种方式,拍卖的对象无疑是“商品”,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拍卖的行为,原本就可以解释到“强买强卖商品”之中,因此,对于修正案新增的“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拍卖”,应当理解为是对原有条文“强买强卖商品”的分立结果——或者说,刑修八不过是将“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拍卖”从“强买强卖商品”中独立出来、明确出来,作为一种新的类型。由于对于“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拍卖”这种行为事实,刑法规范评价在修正案出台前后并不存在差异(包括法定刑也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对于1997年10月1日之后、2011年5月1日(刑修八施行之日)之前实施的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拍卖行为,不能认为无罪,只要未过追诉时效就应当径直依照修正前的刑法予以追诉,而不能以所谓“‘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拍卖’属于刑修八新增行为类型”为由,对之宣告无罪——在刑修八施行之前,其被“强买强卖商品”类型所描述,在刑修八施行之后,其被具有完全针对性的、与“强买强卖商品”相提并论的“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拍卖”类型所描述。遗憾的是,理论上和实务中均有人纯粹地从文字形式上作出错误判断,认为“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拍卖”的行为在刑修八施行之前“法无明文”,因而刑修八施行之后对刑修八施行之前实施的该等行为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从旧”裁判无罪。殊不知,即使没有刑修八的出台,将“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拍卖”解释到“强买强卖商品”之中既是秉持规范目的的解释结论,也是符合文义基本含义的解释结论。而上述错误判断结论首先完全是形式主义的解释立场,其次也违背刑法修正的目的——为惩治“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拍卖”这种强买强卖商品行为提供更加明确、有针对性的法律依据。①在实务中,有人认为,如果“强迫他人参加或者退出投标、拍卖”是司法解释的内容,那么,在2011年5月1日之后将之前实施的强迫他人退出拍卖的行为解释到“强买强卖商品”之中是没有疑问的,但问题是将“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是修正案独立出来的类型,因而是一种完全崭新的行为类型。这种观点貌似合理,其实不然。因为构成要件、刑法用语的含义具有相对性,所以如果刑法不将“强迫他人参加或者退出投标、拍卖”从“强买强卖商品”中独立出来,后者就是包括前者的;一旦刑法将“强迫他人参加或者退出投标、拍卖”从“强买强卖商品”中独立出来,两者就是并列的。
在《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修九”)中,形式上增加条文而未实质上改变规范意义的也不乏其例。例如,刑修九增设的刑法第307条之一第3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即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虚假诉讼行为——笔者注),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里主要指的是诉讼诈骗行为构成诈骗罪、此时依据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可以十分肯定的是,诉讼诈骗原本就属于诈骗;刑法第266条虽然没有明确诈骗的形式包括“诉讼诈骗”(其实也无明确的必要),但在解释论上诈骗可以是包括诉讼诈骗在内的任何方式的诈骗。因此,对于诉讼诈骗成立诈骗罪,修正前后的评价没有变化。也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刑修九施行后,对于尚未裁判的、刑修九施行之前实施的诉讼诈骗行为,亦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而不能以所谓“诉讼诈骗在刑修九才被规定为犯罪”为由对之所谓“从旧”(形式上没有被明确为诈骗罪)而裁判无罪。
第二,有的刑法条文和罪名被修正案废除了,但是,根据待评行为的性质和修正后刑法典的有关规定,刑法被修正案废除的原条文所包含的禁止规范并非不复存在,而是为其他条文和罪名(既可以是修正案出台前刑法已有条文和罪名,也可以是修正案增加的其他条文和罪名)所表达。此时,不能罔顾规范的实质而在形式上将刑法修正内容理解为“非犯罪化”,在修正案施行后对修正案施行前的行为以所谓“从轻”而作无罪处理。此类修正最为典型的就是刑修九删除了原刑法第360条之第2款有关嫖宿幼女罪的规定。应当认为,嫖宿幼女罪虽然取消了,但嫖宿幼女的行为仍然成立犯罪——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此款完全可以评价嫖宿幼女的行为——“嫖宿幼女”无非是在该当“奸淫幼女”的强奸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多余了“支付嫖资”的要素。因此,刑修九施行后,对于刑修九施行之前实施的嫖宿幼女行为,应当认识到新旧法律均认为成立犯罪,视案件具体情况选择处罚较轻的犯罪定罪处罚,②由于嫖宿幼女罪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法定最低刑为5年有期徒刑,强奸罪法定最高刑是死刑、法定最低刑为3年有期徒刑,虽然总体上嫖宿幼女罪轻于强奸罪,但在个案中不排除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较轻。而不得以所谓“嫖宿幼女罪已被废止、新法进行了非犯罪化”为由,“从轻”评价为无罪。当选择以嫖宿幼女罪定罪处罚较轻时(从旧),也不得以罪名已被废止为由排除已经被废止的法条适用。
第三, 刑法修正案增设的一些罪名和不法类型,其包含的全部或部分行为并非在原刑法规范中得不到评价,而是被其他条文和罪名所描述、表达。对此,亦应当注意对新旧法律进行处罚轻重的比较,不能从形式上判断认为新罪名对应的行为在修正前法无明文规定,从而对修正案施行前实施的相应行为以所谓“从旧”评价为无罪。例如,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为他人组织考试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以及非法出售、提供考试试题或答案的行为,在刑修九施行之前可能成立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或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在刑修九施行后成立组织考试作弊罪或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不能认为组织考试作弊和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的行为在刑修九施行前无罪。③201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第6条对于为他人组织考试作弊提供作弊器材等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是,仅就《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而言,类似的法律适用问题也很多,司法解释并未一一予以规定。以非物质形式帮助恐怖活动的,修正前符合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罪或者因具体实施恐怖活动而成立的杀人、绑架、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帮助犯的,以这些犯罪的共犯论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行为,以前相当一部分是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罪或者杀人、绑架、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罪的预备行为,视情况判断是否具有可罚性。这些修正内容带来的并不完全是行为从无罪到有罪的变化,而是罪名和刑罚轻重的变化,存在考虑从旧兼从轻的余地。
总之,基于不同的目的,刑法修正案对刑法规范的修正,有的仅仅是语言、文字及其表达方式的变化,有的则改变了对行为的性质评价、定罪量刑标准,因此,修正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形式的修正和实质的修正。前者表现为刑法条文、用语发生变化,但规范内容没有实质变化;后者则表现为刑法条文和规范的意义均发生实质变化。当然,还有的修正部分内容为单纯的形式修正,部分内容则为实质修正。在具体运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时,应当从规范目的和可能含义角度对修正内容进行仔细甄别,判断对待评行为的评价有无实质差异。④判断构成要件及其要素的变更是实质性的还是形式上的,应当综合考虑刑法在保护法益方面的态度是否发生变化以及目的解释的要求。在形式变更的情况下,应当对规范内容进行实质解释。详见拙作:《构成要件的形式与实质变更及其合理解释——尤以〈刑法修正案(八)〉为例》,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8期。
二、准确认定“从轻”之“轻”——裁量结果较轻
从旧兼从轻之“轻”,指的是新法对行为人的处罚、处理结果较轻,广义上包括旧法认为有罪而新法认为无罪、旧法新法均认为有罪但新法“处刑较轻”。行为自实施到裁判时期跨越多部法律的,从旧兼从轻是否应当考虑中间法的评价?当适用中间法比适用行为时法和裁判时法都要有利于行为人时,可否适用中间法?有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刑法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只涉及行为时法和裁判时法,并没有规定中间法的适用问题。笔者认为,“新法”与“旧法”,不能简单地被认为只有两部法律,只要发生法律变更,存在变更的法律之间都存在“新旧”之别。只要行为实施后、裁判时国家制定过的新法,无论一部还是多部,无论在裁判时是否继续有效,都有必要予以全面考虑,因为这些法律都是“可能被选择”的、只须条件成就就属裁判时的“轻法”。之所以说“可能被选择”、只须条件成就就属裁判时的“轻法”,是因为如果案件在其中某部中间法有效期内被裁判,而该中间法较之于行为时法要轻,则司法机关必定适用该中间法处断案件。不考虑较轻、最轻的中间法评价,本身也是不公正的,因为那样必然导致司法裁判的“偶然性”缺陷——在法律不断变更过程中,行为人能否获得最有利的结果,取决于司法机关能否在最有利的法律有效期内裁判。如果司法机关未能在最有利的法律有效期内作出生效裁判,较不利的又一新法一经施行,行为人便“偶然性”地面临较严重的处理结果。这是不可思议的!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2月31日《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之规定精神,“处刑较轻”是指刑法对某种犯罪规定的刑罚即法定刑比修正前刑法轻;法定刑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较轻;如果法定最高刑相同,则指法定最低刑较轻。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法定最低刑是指该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有两个以上的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法定最低刑是指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也就是说,当存在几个法定刑档次时,比较刑罚轻重应当有针对性地将案件事实、行为具体到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内进行。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对实务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有较大局限性的,也未必合理。因为法定刑存在主刑和附加刑,即使主刑中法定最高刑或最低刑相同,新旧法律分别规定的作为法定刑的依据的因素往往也存在差异,因此,纯粹进行形式上的法定最高刑、法定最低刑的比较而不考虑刑罚的具体根据,是明显存在缺憾和不足的。比如,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以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而1997年刑法以销售金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假设行为人于1994年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其销售金额5万元、违法所得4万元,至1997年10月1日之后进行裁判,按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有关“处刑较轻”的规定,应当适用《决定》即行为时法,因为依照《决定》以违法所得数额标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和依照1997年刑法以销售金额标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其最高刑和最低刑完全相同(最高刑2年为有期徒刑,最低刑为拘役)。应当注意到的是,虽然新旧法针对行为规定的法定刑相同、没有轻重之别,但是,如果分别考虑法定刑设置的依据(是违法所得数额还是销售金额),以罪刑均衡为指引,在不考虑其他情节的前提下,则裁量的刑罚结果,依照新法裁量要轻于依照旧法——依照新法刚刚达到定罪标准、可处以拘役或毗邻拘役的较低有期徒刑,而依照旧法违法所得数额超出定罪数额标准(2万元)较多,裁量刑罚时基本上考虑拘役的可能性较小。由此看来,仅仅比较“法定”最高刑或最低刑来判断新旧法的轻重,有时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从轻”。刑罚以处罚具体的人和行为为对象,因此,具体运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应当将有待评价的行为分别置于新旧刑法规范中、根据新旧刑法规范定罪条件和量刑依据进行具体的模拟裁判,得出分别的裁判结论后予以比较轻重——“处刑较轻”,应当是根据新法裁量的实际刑罚要比根据修改、修正前的刑法(行为时法)要轻。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所带来的刑罚轻重变化,有时并非呈现“单调递减”特征,而是存在有减有增的多元化变化结构,这种现象也给“从轻”的判断带来问题。以贪污贿赂罪为例,由于刑修九将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的标准(不只是数额标准)总体上提高了,因此,对于同样数额、情节的行贿行为,新法处理总体上要比旧法轻,但是,刑修九对贪污贿赂罪的修正,并不是单一地降低处罚力度,而是在总体上提高定罪量刑标准的基础上,在刑种设置、情节设定和刑法运用方式上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比以往立法处罚更为严厉的修正。比如对于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设立了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死缓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的规定,增加了行贿罪的必并制罚金刑并提高了行贿罪减免刑罚条件等等,这些不利于行为人的规定在修正前刑法中并不存在。对此,笔者提出以下见解:(1)对于刑修九施行之前实施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罪行极其严重”包含于其中)贪污罪、受贿罪,如果按照当时的和修正后的刑法规定都只应当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即使按照修正后的刑法规定可以决定死缓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也不得依照修正后的刑法决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因为终身监禁的规定导致修正后的刑法重于修正前刑法;只有当按照行为时的刑法规定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按照修正后的刑法规定应当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时,法院才可以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同时决定死缓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⑤2015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对于2015年10月31日以前实施贪污、受贿行为,罪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可以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383条第4款的规定。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足以罚当其罪的,不适用修正后刑法第383条第4款的规定。”这个司法解释表述内容容易引起误解、引起不必要的争议——似乎指引司法人员,可以对刑修九施行前之罪行极其严重,但原本就只应当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裁判时可以决定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前提是“罚当其罪”)。事实上,这一司法解释的意义在于减少对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立即执行,因此,其中所谓“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情形,应该解释为“根据修正前刑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对于刑修九施行之前实施的行贿行为,如果按照新旧法均成立犯罪,相对合理的做法是依照修正后的刑法第390条裁量主刑,但忽略该条规定的“并处罚金”。亦即,根据修正后的刑法裁量主刑、根据修正前的刑法对待附加刑。有观点认为,只有主刑是值得重点考虑和比较轻重的刑罚,附加刑可以忽略不计,修正后的刑法之主刑较轻,就决定其总体上刑罚较轻,因此,依照修正之后的刑法规定对行贿罪“从轻”,不得否定罚金刑的并处,况且,这种做法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导致新法的罪刑规范“割裂”、行贿罪主刑与罚金刑分离。但在笔者看来,作为财产刑的罚金,具有与自由刑不同的惩罚功能,而这种惩罚带来的痛苦和不利并不亚于自由刑,特别是短期自由行。⑥按照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依照修正后的刑法第390条行贿罪并处罚金的数额在10万元以上。这对于一些情节一般的行贿者来说,罚金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利远甚于自由刑。本着彻底“从轻”的宗旨,理应主刑“从轻”(新法)、附加刑“从旧”。至于所谓“罪刑法定”,并不成为依照新法适用主刑必须同时适用罚金刑的理由——因为旧法没有规定罚金刑、新法规定罚金刑都是“法定”的内容,主刑和罚金刑不得分离适用,完全可以理解为只针对新法生效之后实施的行为,而不约束其生效之前实施、生效之后尚未裁判的行为,也就是说,从旧兼从轻运用时,可以在旧法、新法中兼采较轻的主刑和附加刑规定。此种结果是对新旧法“法定”内容的合理解释结论。基于同样道理,对行贿罪“从轻”适用修正后的刑法裁量主刑时,对于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条件,也应当适用修正前的刑法的有关规定,因为修正后的刑法将行贿罪减免处罚的条件规定得更加严格、更不利于行为人了。而且需要注意,不得以行为人主动交待行贿的“交待”行为发生在刑修九生效后为由,来否定修正前刑法的适用,从而适用更加严厉的修正后刑法。换言之,只要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了行贿行为”,即使交待时间在刑修九生效之后,对行贿人从宽处罚也应适用修正前的刑法(较轻、较有利的行为时刑法)。
从旧兼从轻具体运用中,还存在刑罚轻重的变化影响追诉期限的问题。当新法对应同一行为的法定最高刑降低而缩短其追诉期限时,对其施行前的行为进行评价,毫无疑问,应当按照新法来计算追诉期限,如果已过追诉期限,应当不予追诉。实务中存在争议的是,原审时案件依照修正前刑法定罪处罚了(当然,司法机关是在追诉期限内予以立案的),案件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在再审中按照新法的规定涉案行为已过追诉期限,究竟是按照修正前还是修正后的刑法规定处理追诉期限问题?如果按照前者,则是视为未过追诉期限,在此基础上定罪量刑按照新法“从轻”作出裁判;如果按照后者,则对行为人不予追诉。例如,行为人2003年7月至2004年7月间受贿95000元,2006年2月贪污32000元,立案时间为2013年4月15日,2015年1月作出二审裁定,当时没有过追诉时效(15年)。2016年6月,此案因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审认定的受贿和贪污事实在数额上均存在错误(其中受贿被错误地多认定了5000元、贪污被错误地多认定了2000元),从而进入再审。此间,刑修九已施行,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行为人的贪污和受贿行为法定最高刑均为3年有期徒刑,追诉时效为5年。对此如何处理?笔者认为,考虑到只有行为事实对于追诉期限的长短具有决定意义,对于再审案件,如果再审查明事实认定确有错误(无论是否以事实认定错误为由而被提起),应当按照查明的事实,依照较轻的新法计算追诉期限,如果已过追诉期限,自然不应予以追诉。但是,如果再审查明原审事实认定没有错误,即使因为法律适用存在错误而被认为需要改判,对涉案行为的追诉期限则应当按照修正前的刑法规定计算。当然,在按照修正前的刑法规定计算追诉期限的基础上,应当按照新法“从轻”作出裁判,以兼顾事实对追诉期限长短的决定意义、法律裁判的稳定性和从轻宗旨的遵从。由此可见,上述案件应当视为追诉期限已过,再审程序中终止审理。
三、非刑事法律法规、有权解释的变化与从旧兼从轻的关系
在大量的经济犯罪中,违法类型往往由经济法律法规“先决”设定。经济法律法规缺少违法类型的规定,便阻却刑法中空白罪状描述的构成要件之成立。比如,非法经营罪的成立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如果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为“非法经营”的违法行为,情节无论如何严重也不得解释到非法经营罪之中(当然,只要有非法经营的违法类型规定即可,定罪处罚并不以有附属刑法条款为前提)。鉴于刑法空白罪状表述的构成要件,其内容需要依据非刑事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解释,因此,行为时和裁判时的经济法律法规等非刑事法律法规对违法类型的规定发生变化的,有可能引起空白罪状描述的构成要件解释结论发生变化,当这种变化属于实质性变化时,就涉及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运用。
实务中,当裁判时相应的经济、行政规范出现较行为时规范而言更有利于行为人的调整时,应否遵从新的规范进行行为评价,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刑法评价?比如,行为人在实施走私行为时涉嫌偷逃关税,而在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中该税目已被取消或税率下调,或者在侦查立案时涉嫌偷逃关税,但是在有效裁判作出之前该税目已被取消或税率下调,就涉及“偷逃应缴税额”这一走私犯罪定罪量刑重要因素的评价变化。例如,我国财政部宣布自2016年11月1日起调整煤炭、铁合金等进出口商品的暂定关税税率,将煤炭、成品油、氧化铝等26项资源类产品的税率由3%~6%降低为0~3%。如果行为人于2016年11月之前走私成品油偷逃的应缴税额达到“较大”的定罪标准,而按照调整后的税率计算就可能不成立犯罪。对于因税率调整等行政规范发生变化应否考虑从旧兼从轻,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有人认为,税率调整不属于法律变更、税率变化不等于新法,海关总署于2004年发布的《关于转发办理走私案件期间发生税率调整是否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有关文件的通知》(署缉发[2004]292号)也明确指出:“部分海关在办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案件过程中,连续遇到因在办案期间国家关税税率、税种发生变更,当地司法机关以适用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为由,相继作出不起诉或建议海关缉私部门撤案的决定。总署认为该类案件不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并就此问题函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明确。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明确答复我署,在办理走私案件期间发生税率调整不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案发后,国家关税税率、税种发生的变更,不影响对该行为人的走私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认定……”。
笔者认为,海关总署、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上述意见是值得商榷的,理由很简单:涉案行为是否成立走私及走私犯罪,与客观上是否偷逃关税税款(是否应缴税款)及偷逃应缴税额大小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是否偷逃关税税款及偷逃应缴税额的大小是评价行为是否成立刑法所规定的走私犯罪的(客观)决定性因素,而有关税目税率的规定及其变化在实质上影响到这一因素的考量;既然税率是计算“应缴税额”的依据、作为最终影响构成要件(用空白罪状表达的)评价的行政规范内容,在解释构成要件时,对待税率调整的变化情况,就犹如对待刑法规范的变化情况,应当考虑从旧兼从轻。
当然,依照行为时的非刑事法律法规作出的、被刑法或有权解释确定为定罪量刑依据的终局性处罚决定,并不因刑事司法裁判时非刑事法律法规的调整而失效,此种情形下,不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例如,依照刑法第153条的规定,一年内因走私普通货物、物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属于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相并列的、成立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情形之一。如果作为行政处罚依据的行政法律法规,在走私犯罪追诉过程中发生变化、假若按照新的行政法律法规该等行为不应再被行政处罚,先前作出的行政处罚仍然继续有效,并应当作为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要素考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维护有效行政处罚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的需要。
包括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在内的有权解释,是否如同刑法规范一样,必须考虑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运用?笔者认为,刑法有权解释虽然具有法律效力,但并非刑法规范本身。刑事司法的法律依据只有刑法规范,刑法有权解释的价值在于指引司法人员理解、应用刑法规范,因此,刑法溯及力问题原本与刑法有权解释是无关联的范畴。有权解释之于刑法规范的从属性特征决定,即使属于“不利于被告的”有权解释也完全可以适用于其出台之前的行为,只要行为实施的时候有权解释所解释的刑法规范存在即可。即使认为有权解释明显扩大了刑法的处罚范围,也不能将有权解释及其所解释的刑法规范比照新旧法关系进行所谓“处罚轻重”的比较,从而排除有权解释的适用。当然,如果针对同一刑法规范内容先后出台过不同的有权解释,而其中有的解释评价有利于行为人,则应当参酌刑法规范从旧兼从轻的适用,选择有利于行为人的有权解释,即使该有权解释是行为时有效的、于裁判时已被废止的解释。
肖中华,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