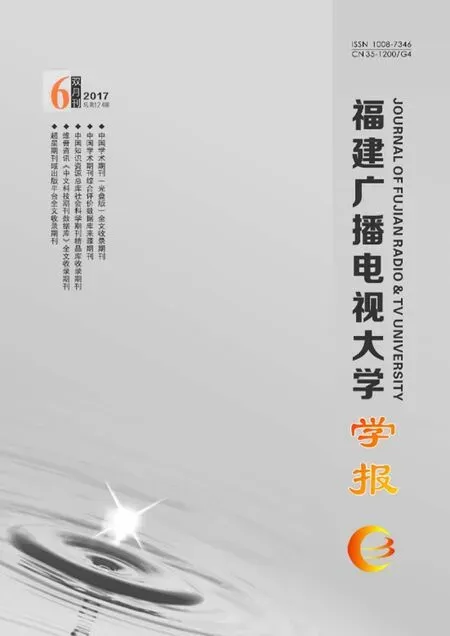论钟敬文游记的情韵美
陈邑华
(闽江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山以贤称,境缘人胜。”奇丽的山水作为自然景观,具有自身的审美价值,如果有人文因素丰富其内涵,山水自然与人文景观共同构成审美对象,让游者在欣赏自然美的同时,亦得到文化的熏染,使游览者进入富于人文内涵的丰富多彩的审美境界。这样的人文山水往往富于无穷的魅力,吸引一代代游者流连忘返。现代游记对人文山水的记述中,民俗学家、散文家钟敬文的游记独具特色,善于捕捉山水名胜的意趣神韵,善于抒写山水的诗情文趣,富于情韵美。
一、善于捕捉山水名胜的意趣神韵
钟敬文喜爱自然山水,流连于名胜古迹,游历了金陵、太湖、莫干山等诸多风景名胜。对“古迹”与“名胜”有着清晰的认识,“名胜,大都是因为实际上有那奇丽的山水,或巨大的建筑,一旦身临其地,不必别有所因缘,自然地能够唤起游者种种的快美之感。古迹则不然,它的激荡游客情感的力,不在境物的本身,而植根于过去的历史。假使游者是一个不熟悉当前境物的历史的人,即使他是怎样丰富于情绪的,终无缘唤起其蓬勃的感兴。……也有些处所,既负着深浓的历史的意味,又饶于自然或人为的风物的胜概的,那自然于不曾明了这境物的历史的人,也可赐予以美感了。”(《金陵记游》)名胜,以其自身外在的绮丽、雄奇,自然吸引人;而古迹,则需要游者具备相关的历史文化,才具吸引力。这一段表述显然是来自钟敬文自身经历的经验之谈,可谓是一语中的。钟敬文在旅居杭州时期,常与友人游赏西湖,流连于西湖的湖光山色、人文胜迹。西湖是名胜,亦是古迹。唐朝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首次采用人工浚湖,在湖上筑长堤。宋朝苏轼任杭州知州时,也派人筑堤蓄水。南宋定都杭州时,西湖十景已初步形成。西湖边还安葬着岳飞、于谦两位民族英雄。西湖自然风光秀美,历史悠久,人文气息浓郁,吸引骚人墨客吟诗咏叹。钟敬文的《西湖漫拾》、《湖上散记》中的游记就是以西湖为主要纪游对象。
钟敬文的游记,注重游历的感受与体验;描画山水,善于捕捉山水的神韵。深山小邱、沧海溪涧,只要有机会,钟敬文都要“为它留连我的步履与情思了”。“有时,只小小的一方古池,池面点缀着暗绿的藻荇;在幽谧中,时有青蛙从丛草中跳入水里的声音。如果在月夜,岸边两、三株老树的影子,浓黑地倒写在地面。这样,这样简单的景致,就已够我的索心玩味了。”(《海滨》)钟敬文学养丰厚、兴趣广泛,加上对自然天然有着一份亲近、欣赏的情怀,在别人看来平淡无奇的景物,钟敬文往往能以独到的眼光去观照而有新的感受与新的发现,可以“索心玩味”。游历时,钟敬文注重身心的专情投入,“和自然入于同化之境”,“一切都使心里感到幽窅的怡愉”。(《怀林和靖》)
钟敬文注重整体感觉,善于捕捉其中的情趣。游记中,常常出现这些字眼:情趣、意趣、清趣、美趣、风情、意味等。如“西风吹来,败叶萧瑟作响;水藻也带寒意,一种衰颓的情调,在水上重重地笼罩着,想水底的鱼虾们,也应该感到而愁思了。”(《残荷》)“稍远,见诸山围列,苍碧晴岚,扑赴心眼。一种高寒旷朗的感觉,令人一切的意绪飘销。”(《金陵记游》)“楼虽不很高,但上下布置颇佳,不但可以纵目远眺,小坐其中,左右顾盼,也很使人感到幽逸的情致。”(《太湖游记》)“墓园内外,都种植着高古的梅树,老干秃枝,纵横穿插着。这时,没有别的游客,我一个人在岑寂、清静的景象中,深深地,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幽渺、古旷的情趣。”(《怀林和靖》)对自然山水的描写,钟敬文大多采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捕捉其情韵,情动于衷,流淌其间的情怀往往使人感同身受。这一效果,正如余光中所说,“写景叙事的文字,有的时候与其描写感性的来源,不如描写感性的后果。”[1]钟敬文渴慕山间高士独善野居的生活,游赏中,欣赏着、玩味着清寂、幽窅的情调,其游记呈现清朗幽逸的特点。
二、善于抒写山水名胜的诗情文趣
钟敬文是个知识广博、兴趣广泛的人。他研究民俗学,对历史、哲学、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喜读诗词,且擅长作诗填词。他说,“我是一个有嗜诗之癖的人。”(《重游苏州》)钟敬文的游记富于诗情,富于情韵。诗词常常是信手拈来,或用来描述眼前景,或借以表达心中情,或画龙点睛,或渲染烘托。钟敬文常常由于诗文的诱惑,饱含兴致,前往名胜古迹游览,去体会、感受、印证诗文中描绘的景致,去探寻、发现山水名胜的美。因而,每到一处,总自然而然忆起相关的诗词。如《西湖的雪景——献给许多不能与我共欣赏的朋友》四千余字的游记,就有十处引用诗文,有三百字之多,约占全文篇幅的百分之十。开篇先略谈游客通常游览春夏的西湖,引用“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浴晴欧鹭争飞,拂袂荷风荐爽”,概述春夏西湖的景致。而四时的烟景不同,真赏者各能得其佳趣。随即引用高深父先生的一段言论,“若能高朗其怀,旷达其意,超尘脱俗,别具天眼,揽景会心,便得真趣。”显然,钟敬文切身领受这前人深于体验的话。于寒冷的大雪天游览西湖,这雅兴正是《四时幽赏录》的激发,对于文中多种富有情趣的雪中赏玩的方式,钟敬文不禁心驰神往。游览途中,每看到颇有情调的一景一境,总情不自禁联想起契合此情此境的诗文,如《陶庵梦忆》中的《湖心亭看雪》、《四时幽赏录》中山窗听雪敲竹的文辞、渔洋的五言诗《雪中登泰山》、柳宗元的《江雪》等等。一路玩赏,或清寒或悠然或渺溟或静寂的景致,总吸引着钟敬文饶有兴味地驻足细细体味,情因景生,清朗幽寂的诗情与情调幽逸的诗文相得益彰,汩汩流淌笔端,由此创造了一个个清朗幽逸、诗意盎然的情境。
如徒步去划船处,踏着雪泥前进,“我迟回着我的步履,旷展着我的视域,油然有一脉浓重而灵秘的诗情,浮上我的心头来,使我幽然意远,漠然神凝。郑綮对人说他的诗思,在灞桥雪中,驴背上,真是懂得冷趣的说法!”行走在寒冷、寂静的雪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本是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差事,可这段平常不过的路程,在善感、饱读诗书的钟敬文眼里,却有着颇多的情趣。一路走来,饶有情致地体会着“玉坠冰柯,沾衣生湿”、“诗思在灞桥风雪中”的情景与趣味。正所谓“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自然是自在的,无意识的,不能自彰其美,其美需要人的发现与宣传。因而,审美主体的心境、文化素养对美的彰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钟敬文有着“独善的野居的梦想”,了解西湖的历史、文化,喜爱吟咏西湖的诗文,游览西湖时,尤能体味西湖的情韵。即便是行走在空旷的雪地,“一脉浓重而灵秘的诗情”也油然而生。
钟敬文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对历史文化亦有着浓厚的兴趣。钟敬文说,“所以人类要读历史,要追念过去的故事,为实利的成分固然有,但单要求满足其神智、情思,作兴趣的游泳、开拓者也正占多数。吾人乐于摩挲古物,凭吊废墟,这种事实的心理上的根据,就全在于是。”(《怀林和靖》)钟敬文读历史,流连于古迹,兴趣使然,趣味使然。其游记不仅富于诗情,也饶有文趣。游记中,对所游之处的相关历史典故、文人逸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常常信手拈来,与所游胜景相辉映。《重阳节游灵隐》叙写古代遗留下来的风俗习尚,回忆昔日写的寄友的诗。一路游玩,一路引述古人的诗文,种种联想与回味,意蕴丰富、情趣盎然。钟敬文的山水游记,不同于古代以陆游为代表的文化型游记,只注重人文历史,亦不同于当代余秋雨的文化游记,重心在于智性的思考。其游记更多的是眼前景与心中情的交融,吟咏、引用的诗、文用以抒发心中的感慨与情怀。情感、景观、诗文相互交融,营造了一个个饶有诗意与趣味的审美境界。
通常山水游记的结构布局,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侧重摄取一物一景,细致刻画,小中见大,抒写性灵。如唐朝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及晚明的山水小品。一类是移步换景,根据游览的顺序逐步展现宏阔的山水,如陆游的《入蜀记》、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等。钟敬文的游记综合了这两类游记的长处,既展现了游记的过程,又凸显了个性化的景物描写。此外,还擅长运用转笔,使游记颇有婉曲摇曳的风致。如《钱塘江的夜潮》文势峰回路转,情感跌宕起伏。以议论开篇,由人类是富于夸大性的动物,例举日常的事例引出观钱塘江夜潮的失望情绪。而后描述观潮前的心境,无限期待、驰慕的情感,来自宋朝周密《武林旧事》对浙江之潮的生动描绘、钱王“三千强弩射潮低”的传说、伍子胥“魂压怒涛翻白浪”的神话、高濂《四时幽赏录》“十万军声半夜潮”的抒写。这些热蓬蓬的兴趣加上周遭游客兴奋的谈笑,心情欣然、高兴。“我”悠然欣赏窗外的景致,到观潮处,亦怀着美好的心境欣赏月夜下的自然。游记酝酿了饱满的情感,期待、欣喜、兴奋之情可谓是达到了顶峰,观潮时,情绪陡然跌落,竟是如此的平常,“当潮之奔驰过我们眼前时,其高不过数尺,形状如釜里怒沸的开水,跃乱不可止息。奔驰过后,则江水增高了量度,而色样变得格外浑浊。”“我已包围在失望和疲倦中了。”“文似看山不喜平”,先抑后扬再抑,情感随着游程而富于变化,摇曳多姿。《怀杭州》时抑时扬,描述其好处,亦数落其缺点,褒贬穿插其间,曲折跌宕,摇曳多姿。
三、富于清朗幽逸的情韵美
钟敬文喜爱山水名胜,善于捕捉山水名胜的意趣神韵,善于抒写诗情文趣。其游记情韵悠长,清朗幽逸。
钟敬文的游记多为清、幽、寒、静的境界,所热衷的景致、意象多是秋意、冬雪、落叶、清风、流水、残月等。钟敬文欣赏、领略《西湖的雪景》的“宇宙的清寒、壮旷和纯洁!”《残荷》里“衰颓的情调”,《金陵记游》中“高寒旷朗的感觉”,《太湖游记》“幽逸的情致”,《怀林和靖》中“幽渺、古旷的情趣”。这般清朗幽逸的情韵来自钟敬文的个性喜好,亦是其境遇、时代环境使然。钟敬文说,“但论到我个人特别的癖好,那似乎是在情思幽深不浮躁,表现上比较平远、清隽的一派。这没有什么多大的道理可说,大约只是个人性格、环境的关系罢了。”[2]钟敬文性格内向,自幼喜好读书,尤爱“读诗写诗”(《忆社戏》)特别喜欢宋朝隐逸诗人林和靖的诗文。“这时,我深刻地认识了一位精神挚好的良友,那就是林和靖。他的那部散佚之余仅存的心调(诗集),没有一天不把在我的手上,吟在我的口中,刻在我的心底。我和他简直成了一时精神上的恋人了。”(《怀林和靖》)钟敬文将林和靖看作是精神挚好的良友,不仅思想,诗歌也深受其清冷幽静、闲淡深远的风格的影响。钟敬文喜欢岑寂、清净的景象,欣赏幽渺、古旷的情趣。“我是喜欢自个儿在幽冷的地方徘徊和思索的人。”(《海滨》)到杭州那段时间,钟敬文喜爱读神韵派清初诗人王渔洋的作品。王渔洋论诗以“神韵”为宗,强调淡远的意境,亦契合钟敬文当时的心境。当时,钟敬文因编书被“停职”,情感方面亦陷于苦恼中,自己已有所爱,而家里却要为他包办婚事。而当时处于“四一二”事变之后的中国社会处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时期,不准知识分子发出正义的声音。内外环境的压迫,使得陷入苦闷与失望中的钟敬文来到杭州,寄情山水,其游记着上了浓郁的个性色彩,淡雅敦醇、清朗绝俗,“这类文字真如山间高士,松下逸人,是会有人喜欢的,特别是处于纷扰的年代,使人们暂时忘怀那厌倦的尘寰。”[3]
钟敬文喜好山水,向往“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期望在畅游中沉醉其间,陶然忘我。然而,现实世界的黑暗污浊总像挥之不去的影子,如影随形,沉重地压在身上。游历时虽有陶然忘我之时,但总难以做到真正的超然物外。钟敬文欣赏着西湖的清寂幽逸的雪景,亦只能暂时忘却现实的纷扰、污浊。“看了那种古朴清贫的情况,仿佛令我暂时忘怀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纷扰、繁遽了。”(《西湖的雪景》)游金陵,历史上帝王都城的故地,“我所收拾得的,除了湫溢嚣尘,污浊颓败之感,此外实在说不出还有什么!”(《金陵记游》)重阳节游灵隐,虽然高兴能去作一回清游,可心头难抑悲情,“此刻,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我个人自己的身世、家庭,想了起来,要教极端的乐天主义者,都禁不住泪珠儿如雨般淌下,顿消了一切的欢意。”(《重阳节游灵隐》)钟敬文寄情山水,为了疏解郁闷的心情,却难以忘怀现实。社会现实的黑暗、百姓生活的愁苦,使得钟敬文即便身处清净超然的景致中,仍难谴愁思忧患之情。
“雅人胸中胜概,天地山川无不自我而成其荣观”。[4]钟敬文徜徉于自然山水,抒写流连名胜古迹的幽情别趣。游记诗意盎然,情韵悠长。其情感或浓或淡总与现实联系在一起,寄寓着自我对于社会、人生的感慨,涵容着对灾难深重的祖国与贫苦民众的热切关注,忧国忧民的情怀与山水诗情交织交融,形成一种极大的张力,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