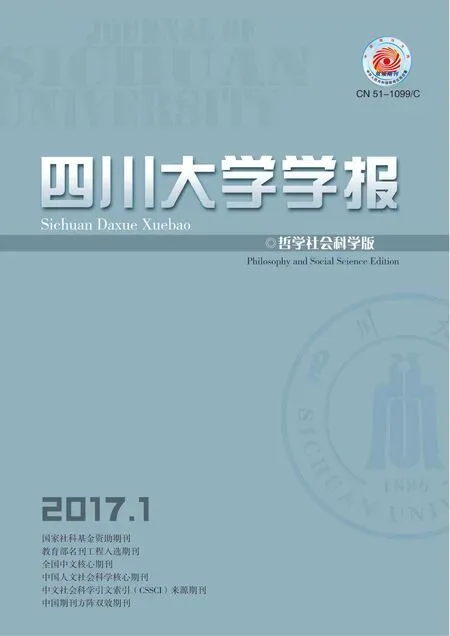语义何以足够最小:非语境敏感语义学的新进展
刘利民,傅顺华
§语言文学研究§
语义何以足够最小:非语境敏感语义学的新进展
刘利民,傅顺华
针对语义研究主流的语境主义倾向,H·卡培朗和E·勒珀尔提出了非语境敏感语义学,也称为“语义最小论”,认为一个句子一经说出就具有一个不受语境影响的最小语义内容。E·博格和G·普雷尔则在坚持句子语义最小论的基本立场上进一步提出了“语义如何足够最小”的问题,在严格区分意图行为与语义内容、坚持命题主义立场、索引词类型的概念模型建立等方面做了新的理论尝试,力图说明句子的语义内容完全由其句法结构和词项内容所触发,与意图、情境等因素无关。这一理论新进展,值得讨论。
语义最小论;非语境敏感性;语义内容;言语行为
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认为词项、句子的意义是语境敏感的,因而语言意义的解释必须相对于说话人和语境。语义的语境依赖性在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成为了关于语义研究的思想主流,即使在形式语义学领域中也已展开,渐成主要倾向。①沈园:《形式语义学领域的语境研究》,《当代语言学》2015年第4期。而卡培朗和勒珀尔(H. Cappelen & E. Lepore;以下简称C-L)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非语境敏感语义学(insensitive semantics;也称“语义最小论”②“语义最小论”英文原文为“semantic minimalism”,亦可译为“语义最简论”。鉴于semantic minimalism的核心关注是如何将语用因素对语义内容的影响减到最小,旨在确定并形式化地描述不受意图、语境影响的句子最小语义内容;故本文采用“语义最小论”这一译名。),反对把语义做相对于意图、情境等的解释。语义最小论秉持弗雷格语义学传统,认为句子的语义内容就是由其组成词项的意义按照句法规则组合而成的规约性意义,无论语境如何变化、无论说话人带有什么意图,句子都有着同样的最小语义内容,且此内容具有理解的先在性。③E. Borg, “Minimalism versus Contextualism in Semantics,” In G. Preyer, et al,eds., Context-Sensitivity and Semantic Minim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340-341. 同时,这里须说明:弗雷格的“语境原则”与现代语义学研究中的“语境主义”在术语上容易搞混,但两者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词项意义的语境定义,即词项是由于作为有意义的完整句子的一部分才有意义的,强调的是句子在语义上的首要地位。(参见W·V·O·奎因、张金言:《经验主义的五个里程碑》,《 世界哲学》1983年第6期)这与语境主义的句子意义相对于言语行为语境而确定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
语义最小论在西方语义学和语言哲学界引发了一场颇大的争论。意图、情境等是否构成语义成分?意图意义与句子字面意义是否同时触发?能否真正确定、如何确定一个语境敏感词项的基本集合?知识是不是语境敏感的?对语义学和语用学我们应当清晰地划界,或寻找两者的结合界面,或干脆否定语义学的价值?这些都是语义学和语言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关于语境主义和语义最小论,国内学术界已有一些讨论。④如,张绍杰:《后格赖斯语用学的理论走向》,《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费定舟:《对语境敏感性的不完全论证的辩护》,《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张瑛:《论语义最小论的三项测试》,《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等等。但相关研究不仅量小、零散,也尚未涉及语义最小论的新的理论进展。博格、普雷尔(E. Borg, G. Preyer)等人在支持C-L语义最小论的同时,对C-L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以图更彻底地坚持语义最小论。如何理解这一新的理论进展,本文打算就此做一番讨论。
一、语义内容不是言语行为内容
著名的语言哲学家格赖斯(H. P. Grice)区分了句子意义和说话人意义,但认为说话人意义是更为根本的意义。他指出,说话人U说出句子x,并且希图听话人H识别自己的意图p,如果x确实在H那儿产生了U希图的效果,那么U就成功地通过x意味了某个内容。*H.P.Grice, “Meaning,” In M. Baghramian(ed.),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 1999, p.131.按此观点,交际成功取决于听话人对说话人的意图的理解。如,某说话人U对听话人H说“你们寝室真整洁”,而事实上H的寝室很脏乱。由于U的意图是挖苦,而不是赞扬,因而H成功理解U说话的意义在于识别出U的挖苦意图。这解释了H的反应为何不仅不是高兴,反而是很尴尬。因此,会话交际的意义是由语境和意图来确定的。须注意的是,格赖斯虽然没有使用“语义”和“语用”两个术语,但他其实也区分了“说的是什么”(What is said)和“隐含的是什么”(What is implicated)。*H.P. Grice,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A.P. Martinich, 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66-167.要理解隐含的是什么,需要先理解所说的是什么。这意味着格赖斯承认一个句子具有不受说话人意图、语境左右的最小语义内容——正是这一内容启动了关于隐义的格赖斯语用推理机制。就此点而言,语义最小论与格赖斯所论并无分歧。事实上,C-L的语义最小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与格赖斯观点是契合的。C-L的“言语行为多元论”(speech act pluralism)认为,一个说出的句子所陈述、宣称的内容与它语义地表达的命题不能等同;一个句子的说出原则上可以表达数量无限的命题,而在这些命题中,有一个是最小的命题;虽然该命题并不一定是听话人意识到的或者感兴趣的,但它构成了句子语义内容,该语义内容将成为更大的言语行为内容的一部分。*H. Cappelen & E. Lepore, Insensitive Seman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p.190-192.
C-L的言语行为多元论观点受到了以博格为代表的语义最小论者的批评。他们指责这一观点极其容易滑入最小论者自己反对的语境主义,因为多元论虽然与语境主义不同,认为句子表达了命题,却又承认句子表达的许多命题中至少有一个命题抓住了说话人的心理内容这一观点。*E. Corazza & J. Dokic, “Sense and Insensibility,” In Preyer, et al,eds., Context-Sensitivity and Semantic Minimalism, pp.184-186.这就与语境主义的意图论立场很接近了。事实上,雷卡纳蒂的“弱语境主义”就并不否认字面意义,但认为句子字面意义与交际派生意义地位相同,在“构建整个话语的理解中是同步处理的”。*F. Recanati:《字面意义论》,刘龙根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27页。地位相同、同步处理将导致字面意义的解释需要相对于语境、意图而做出,这恰恰是语义最小论所反对的。
博格、普雷尔等指出,语义最小论并不需要接受C-L的观点,即一个句子的语义内容是对于所有涉及该句子的言语行为所共有的命题内容。*Borg, “Minimalism versus Contextualism in Semantics, ” pp.352-354;G. Preyer, “The Power of Insensitive Semantics,” p.48, https:∥www.academia.edu/23173121/,2016-8-7.其原因有二。首先,一般地说,说话人并不陈述这类命题,而听话人也并不把握这样的命题。比如说,说话人U说出了句子S:“张三养着一条狗。”U说这句话时所带有的意图可以不同:为听话人H提供一个信息,或者是给H一个警告,让H当心恶狗。假定U的意图是后者。这里须注意的是,即使H把握了U的意图,并在脑中形成了命题(q):“张三的狗是只恶狗”,但是1)命题(q)并不是U已经说出的句子S的语义内容,因为其语义内容是(p):xy[x=张三,y=狗,x养y];并且2)命题(q)也不是U的意图意义,因为其意图是警告。警告是一种行为,这一行为并未给句子S增加新的语义内容或者改变S的字面意义。因此,句子的字面语义内容与言语行为的意图内容必须严格区分开,前者绝非后者之一部分。
其次,在信息不足或意图缺乏的情况下,听话人可能无法对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中说出的某句话做出完全解释,但是却能完全把握句子本身的意义。这不是因为句子的语义内容是整个言语行为内容的一部分,而是因为最小命题内容是任何一个语言使用者所具有的语言能力保证的,即他仅需要看到或者听到一个写出的或说出的句子,就能够从中提取出句子语义表达的命题。正是这个事实保证了在句子的语境信息不足、不可靠或者不稳定的条件下,最小命题能起到传达语义内容的作用。例如,甲知道乙说了“张三个儿很高”这句话,但不知道乙的心目中是在把张三跟什么人群进行比较,然而甲却能够报告说乙说的是张三是高个子这件事。甲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一报告,凭借的就是乙的句子本身所表达的最小命题。再如,说话人U说了一句话:“李四可好了!”意图挖苦刚离开的李四。但是听话人H并未意识到U在挖苦李四,因而稍后转述说U说的是李四可好了。此例中,H没有(能力、意愿等)把握U那句话传递出的意图。不过,H已经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好的理解:即准确地做出了按U说出的句子的字面语义内容进行了转述。这意味着,说话人的意图、情境等等一系列言语使用因素都不能想当然地改变句子本身的语义内容。句子意义的理解只有语词解读(word-reading),无需心思解读(mind-reading)。*E. Borg, Pursuing Mea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4-5.
因此,与C-L不同的是,博格等人认为语义最小论并不需要将句子的语义内容作为涉及该句子的所有言语行为共同的内容。*Borg, “Minimalism versus Contextualism in Semantics,” p.325.人使用语言说出的是句子,一个句子一经说出,就具有一个超语境的最小语义内容,即该内容不因言语情境的不同或说话人意图的不同而变化。句子的最小语义内容遵守弗雷格的组合原则,即是由其中各词项的意义按照句法规则组合而表达出的命题意义。句子是语义内容的首要承载者。言语行为,即说话人意图做什么事,则不属于语义的内容。意图、语境与言语行为有关的是说话的目的、推断的依据等,而不是句子语义的组成部分。因此,博格和普雷尔反对把句子语义内容和言语行为杂糅在一起;内容和行为两者性质不同,应该分开来解释。如普雷尔所说:“我使用咖啡机来煮咖啡,但我无法使用语言或句子来下断言或给建议。我说出来的只是句子。”*Preyer, “The Power of Insensitive Semantics,” p.51.他坚决反对把“情境、意图”等塞入句子的字面语义内容中进行语义分析。这并非是说语义最小论者否认说话人说话时带有种种不同的意图,因为说话毕竟是有目的的,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说出的句子只有一个语义内容,任何意图都不能为该语义内容增加什么进一步的内容。一言蔽之,说话人说话或写作有其意图,但语言本身并无目的。
按奥斯丁的言语行为论,句子的意义实现关键在于听话人对言旨的把握。如,在天气不好的时候,说“今天天气真好”显然不会被理解为报告一个事实,而会被理解为抱怨、挖苦等。这意味着,语义的理解本质上是心思解读。对此,语义最小论指出,这并不等于说句子语义内容中加载了言旨行为内容。*Preyer, “The Power of Insensitive Semantics,” p.48.就人的语言能力而言,无论一个听话人是否有足够的经验从给定语境中获得说话人意图,句子的语义内容(格赖斯的“说的是什么”)都是跨语境的。至于说话人的意图是否被听话人所识别、遵从或拒斥,这取决于听话人是否能够或者愿意把进一步的信息加入他对所听到的句子的语义内容的解读之上。因此,语义最小论坚持认为,存在着一个由语词意义和句法结构决定的内容层面,且相对于不同情境中言语行为所意图的意义,这个层面内容是不变的。这是言旨行为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也是语言习得之必须。“没有语境敏感性的词汇-句法清晰证据,就没有语境敏感性”。*Borg, Pursuing Meaning, p.88.
二、坚持命题主义立场
如上所述,语义最小论确定句子语义如何最小的理论策略是反对把言旨行为作为“意图意义”加入句子语义内容之中。一个句子一经说出,就具有一个由词项意义和句法关系所决定的字面语义内容,任何语境、意图都不能任意处置这一字面的语义内容。那么,这个语义内容是什么性质呢?仍以“张三个儿很高”句为例。语境主义认为,这个句子的意义无法独立地确定;不同的时间、场合下,说话人表达的意义不会相同。用这个句子来谈论一个篮球运动员或一个四岁孩子时,就会出现其命题意义在一个语境下为真,而在另一个语境下为假的情况。甚至可能因说话人的意图不同而表达了赞美或轻蔑。比如,在回答“张三作为系主任能力如何”的提问时,说话人说出了这个句子事实上表达了他认为张三没有能力这样一个意图意义。因此,语境主义认为句子意义是相对于语境而确定的。
然而,在语义最小论看来,目前语言研究中这种占主流的意义分析已造成句子语义不可独立确定的后果,最终导致意义相对主义。这是不可接受的。语义最小论坚持命题主义立场,即句子语义内容就是由词项意义-句法规则所决定的最小命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语义最小论与乔姆斯基的内在论都把句子意义视为语言内的联系,但是不同之处在于乔姆斯基内在论不接受词项意义的外部世界指称性。乔姆斯基明确提出,“词项本身并不指称,……但人们可以用词指称事物,从特定视角看待事物”。*N. Chomsky,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6.此看法把指称性质归于词项的使用而不是词项意义,这就有可能导致语言意义的使用论。语义最小论反对乔姆斯基的这一观点,认为词项意义至少有一部分是指称性的,词项的属性与词项之间关系的属性应当参照语言单位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进行系统性描述。*Borg, Pursuing Meaning, pp.166-167.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滑入语义使用论,也可以避开知识唯我论的嫌疑,因为把词项意义理解为分离的、独立于语境的实体有利于说明基于词项-句法而表达的就是最小命题,即语言使用者为了理解字面意义而需要掌握的东西。
博格指出,这并不是说句子表达的最小命题p必须保证对于所有的可能世界w,听话人如果理解了p就能知道w是否满足p,也不是说最小命题p足以决定,对于任一可能世界,p在那个世界中为真或为假,而是说基于最小命题p或其真值条件,语言使用者可以进一步努力弄清楚哪些世界以哪种方式区分、以及它们能否满足命题内容。俗言之,句子“猫在席子上”表达的最小命题并没有确定是哪一只具体的猫、以什么具体姿势在席子的什么位置、席子在哪儿、“在……上”代表何种关系(接触还是悬浮等等),也并未确定该命题相对于某个语境c为真或为假存在着一个事实。听话人还须做出更多的努力,如寻找事实、确定是什么猫、以什么方式跟席子之间具有何种关系等。但是,正是句子表达的最小命题构成了使得听话人能够去做到这些事情的条件。反过来看,听话人由于把握了句子语义内容本身而能够去做更多的事,这先行地保证了最小命题存在的合理性。*Borg, Pursuing Meaning, pp.106-111.
普雷尔采用的策略则是严格区分句子、陈述、命题,而后以类型-例型(type-token)关系论证来把“意图意义”“使用意义”之类的内容挤出语义学的分析范围。他关于句子、陈述和命题的区分是这样的: 1)句子是一个自然语言中任何一个语法正确、完整的序列,按组合性原则由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组成;2)陈述是一个说出来的或写出来的句子所具有的内容,即“说的是……”;3)命题则是同义陈述句的集合,如果两个句子意义相同,那么它们表征了同一命题。*Preyer, “The Power of Insensitive Semantics, ” pp.27-30.无论在语义学还是语言哲学中,这三者的区分已经是常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语义最小论以此来拒斥语用因素的思路。
首先,句子的意义由词项意义按句法组合而确定。一个句子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下用来说不同的事情,但是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的句子只是一个类型的真值或满足条件例型。这应当是例型,例型是物理实体,实现为纸上的符号或一连串声波。*Preyer, “The Power of Insensitive Semantics, ” p.28.同一句子类型的S(如,“张三是高个儿”)的意义由原初的词项意义(如,张三、高个儿)按句法组合(SVbA)而成,具体情境下说出的句子则是该类型的例型:S′、S″……。S′、S″等等具有真值(陈述式)或满足条件(祈使式、疑问式等等)。说出的句子是否为真或是否满足,取决于事实。例如,“张三是高个儿”即是例型,可用来说一个篮球运动员或一个幼儿园小孩。该例型陈述的内容为真,当且仅当所说的对象确实具有个子高的属性。这里无关乎意图,语境不过提供了条件,使得该句子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型,但句子的鉴别方法仍是句法的。
其次,陈述的理解与常识也没什么不同,同一陈述可以用不同句子做出、也可以表征不同命题。所谓陈述,语义最小论强调的是关于同一件事说出的同样内容。例如,甲对乙说“你很伤心”、乙说“我很伤心”或者乙用外语说“I'm sad”,这三个句子的形态或主词都不相同(关于“我”之类的索引词,下文会谈及),但是它们表达了同一个命题。陈述的鉴别标准不是句法,而是事实。陈述是真值的承载者,其真值就是某个事实对于一个命题的例证。要说这三个句子具有“同义性”可能导致问题,但由于事实是可确定的,这些句子陈述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是“是相同的”。在语言交往中,听话人要把握说话人想要表达的意义,当然需要语境信息,如意图行为、社会文化等等方面知识,但是如果没有识别出一个句子的意义,没有所言之事实内容“是相同的”的把握,那么语言交流无从谈起。*Preyer, “The Power of Insensitive Semantics, ”p.26.显然,这里也没有意图、语境对句子语义内容所做的贡献。
最后,语义最小论关于同一命题可以有不同句子、不同陈述的认识也与常识无异。不过,与主流语义学小心翼翼地拒斥命题作为某种抽象存在的观点不同,语义最小论承认命题是必要的。关于什么是命题?普雷尔提出了三个解释:1)命题是同义陈述句的集合。如果两个句子的意义相同,那么它们表征了同一个命题。如前述甲、乙二人关于“很伤心”的句子,尽管句子形态不同,但都表达了同一命题。而如语境主义指出的那样,前述“张三是高个儿”一句在不同情境下意义是不同的。语义最小论指出该句子不一定表达同一命题,其原因是该句作为例型,说的是关于不同对象的不同的事情,因而其意义不同。意义不同,当然就不属于同义陈述句的集合。2)命题是可能世界对真值条件的函项。这是一个独立于语言的定义,它把命题视为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语义学鉴别的对象。例如,“杰克和吉尔共有母亲或父亲”这个句子表达的命题与“杰克和吉尔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相同;在任一可能世界中,前者若真,后者也真;反之也是一样。陈述是作为类型的命题的真值或满足条件的例型,正如个体示例了共相性质一样。命题意义需要陈述是什么事实使之为真,而陈述需要由句子做出。例如,即使命题“有辆车是红的”为真,但并未说出是哪儿的哪一辆车是红的,而句子“那辆奔驰是红的”做出的则是一个可以凭借非语言的事实判定真假的陈述,后者是前者的一个示例。3)命题是句子的内容或不同语气中的言说行为。普雷尔举例说,“詹姆斯关了门。”“詹姆斯,关门!”“詹姆斯关了门吗?”这三个句子语气不同,分别是陈述式、命令式和疑问式,但三者都表达了詹姆斯关门这一命题。与博格一样,普雷尔强调,命题内容不是真值承载者,也不由满足条件来确定;语旨力之所以可能,是基于不同语气的句子一经说出就具有一个表达了命题意义的最小语义内容。*Preyer, “The Power of Insensitive Semantics, ” p.29.
普雷尔的这种对句子、陈述和命题的严格区分避免了把命题作为抽象的实在,也避免了把真值/满足条件视为命题的属性。他们的分析无需牵涉意图之类“说话人意义”或“使用意义”。语境的作用是为真值判断提供非语言性的条件,使得语言使用者可以据此而进行更多的真值确定、满足条件确定的努力,但语境并不为句子的命题意义本身做出什么贡献。
三、建立作为语义类型的索引词概念特点
前文论及语言词项中有些词项(如,“我、这里、现在、从此以后”等等)是索引性的,即这些词项的所指必须相对于说话人、交流情境才可确定,这就是所谓“说话人指称”“语境性指称”等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新见,如卡普兰就对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等语境敏感的词项做了分类概括。*D. Kaplan, “Demonstratives,” In J. Almog, et al,eds., Themes from Kapl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481-504.如果要坚持句子最小语义的立场,语义最小论需要应对这个挑战。
C-L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承认确实存在着极小量的语境敏感语词,且会对句子的意义产生一定影响,但认为用一个极小的基本集就可以把语境敏感词项放进去。为此C-L提出了语境转换论证,以跨语境测试的方式确定这一基本集合中的词项。*Cappelen & Lepore, Insensitive Semantics, p.108.这一论证及其可能的问题国内已有人做过讨论,*张瑛:《论语义最小论的三项测试》,《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此不赘。但从语义最小论的宗旨看,仅仅确定出语境敏感词项的集合本身并不重要;真正要紧的是对语境敏感词的意义给予合理的语义描述。鉴于此,语义最小论新近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路。关于存在少量语境敏感词,博格赞同C-L的观点,不过她认为重要的不是有多少词项是语境敏感的,而是什么机制使得这些词项语境敏感。博格认为C-L以数量的多少来划分激进语境论和温和语境论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语境无需句法触发就能进入语义内容,那就不仅是在基本集中增加一两个词项的问题,而是整个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关系将全然不同了。因此,她坚持认为一切语境敏感性都是句法地触发的,且语境对语义内容的贡献都是可形式地处理的。*Borg, “Minimalism versus Contextualism in Semantics, ”pp.342-346, 355.
博格指出,在任一语境中,一个包含索引词的句子(如,“这是红的”)中,处于主词位置的单称词项已经穷尽了说话人所指的内容,既如此,听话人不必实质性地鉴别出指示词如“这、那”等的所指,而只需依据概念的特点(类型意义)来思考说话人以例型词项“这、那”所指称的实际对象。因此,尽管说话人在种种不同的语境下可能意图指称无穷大数量的对象之一,但是其所说的句子例型(这是花、这是蓝色的、这是老王……)都具有同样的概念特点内容(这是F)。*Borg, Pursuing Meaning, pp.140-142.例如,例型“那是F”可以被说话人意图用来指称A对象而不指称B对象,但是例型“那”的语义内容已经为A对象所穷尽(不可能指称A之外的任何对象),因而听话人为了理解该例型所必须掌握的内容即是命题:那个A是F。这个命题中并没有提及说话人意图。典型的索引词“我”也是如此。甲说“我牙疼”、乙也说“我牙疼”,那么“我”的指称不同,但是该句子类型的这两个例型却有着相同特点,决定了相应于不同语境的同样的语义内容。博格指出:听话人听到“我是F”这句话时,会断言这句话为真。如果a是例型“我”的说出者,那么a就是F;但词项“我”的引入先在地保证了无论a是一个什么对象,都必须是例型“我”的说出者。*Borg, Minimal Semantics, p.166.因此,指称的确定、指称的识别是语言使用者的意向、语境问题,而语义内容则是他们理解句子所必须掌握的命题。指称对象的识别是非语言性的,是听话人理解了句子命题意义之后能够进一步去做的事,但不属于句子的指称性内容。因此,意图等因素只能影响说话人使用索引词例型意义,而对句子内容本身并无影响,因为句子的理解依据的是索引词作为类型的概念意义。这样,索引词对句子语义内容的影响就被减低到了最小的程度。
对于语义最小论,作为类型的语义概念特点起着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普雷尔进一步提出:指示词、人称代词等词项具有索引性可由句法触发而对句子语义内容产生微弱的影响,但是这些索引词项本质上是语义类型,它们具有语义统一特征。他的基本思路与前述句子、陈述、命题意义的讨论如出一辙,即把说出或写出来的句子中的索引词项视为真值/满足条件例型,并基于此而选择概念的共性特点以确定这些词项的语义类型,即能够解释索引词的意义的理论模型。具体而言,既然索引词项的指称有赖于具体的语境,那么如果把可能的情境的相关特征作为存在的复合实体予以固定,就有可能确定一个情境的集合,即一个在时空框架内索引词或曰参照点元素与其相配对的情境实体元素构成的集合。设每一个参照点x是存在于y上的实体组成的集合yx,那么如果对于每一个参照点x,常量的外延是固定的,其内涵也就固定了。*这个问题语义最小论尚未给出具体的证明。Preyer认为下一步应当是以蒙塔古过程来研究确定语境集合的具体方案。参见Preyer, “The Power of Insensitive Semantics, ” p.29.限于篇幅,这一点我们或将另文展开。
用这一方法将索引词定义为语义类型意味着,在不同语境中的索引词可能空间坐标位置完全不同,但语言使用者能够以情境集合所给出的索引词类型的概念特点想到具体的索引词例型所指的实际对象。这使得“这些(语境敏感的)表达式都表现得仿佛属于指称性词项的一个单一语义范畴”。*Borg, Pursuing Meaning, p.138.这样做既避免了索引词语义确定的本质论之嫌,就理解而言,又使得对索引词给予语义学描述成为可能,而无须涉及说话人指称、语境指称。
概言之,虽然索引词的指称对象是什么有赖于具体情境,但是情境依赖性只是真值/满足条件例型的属性,而不是作为指称意义类型的索引词的属性。因此,少量语境敏感的表达式对语义内容确实会产生微弱的效果,但语境敏感表达式对语义真值的确定并不改变由句子表达的命题意义。如果语义最小论能够最终建立起这样一个索引词的概念特点模型,确实将会为他们所坚持的语义学与语用学严格划界、语义学理当以形式化为宗旨的理论立场提供很有分量的支撑。
四、对语义最小论新进展的评论与思考
语义最小论对当前语言学研究、科学哲学反思中占主流地位的语境主义进行批判,这有其存在理由。从哲学上讲,语境主义者提出,知识最终是语境敏感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辩护,*曹剑波:《“知道”的语境敏感性:质疑与辩护》,《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4期。但知识的语境敏感论也有很大的困境,对此也有反思。*魏屹东:《语境认识论的困境与可能出路》,《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这些争议实质上涉及作为真理性知识是否存在统一的客观判定标准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从语言学上讲,如果不将语境依赖性纳入研究,自然语言语义分析是否真的不可能,*沈园:《形式语义学领域的语境研究》,《当代语言学》2015年第4期。语义学和语用学到底是应当划清界线以及如何划界,还是应当寻找接口界面并且在哪儿寻找等,都是目前争议很大的问题。*张绍杰:《后格赖斯语用学的理论走向》,《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在这些问题上,语义最小论的思考肯定会推动相关的学科研究。宏观地看,这有助于人们思考语言形式表达的意义具有什么性质以及语言意义生成、表达与理解的机制是什么等语言学的重大问题,进而推动人们思考科学知识的本质等更为根本的认识论哲学问题。而微观地看,这对于诸如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推进也意义重大,因为其形式化进路至少能够提供具有简单性、确定性、普遍性和可操作性的语义学知识基础。
当然,语义最小论的论证能否取得最后成功,还有很多事要做。本文在此提出如下几个问题,并非为了挑战语义最小论,而是为了促进问题的深入思考。
第一,语义最小论承认句子做出的陈述之真假取决于事实,因而是语境给出了陈述句例型的语义内容的真值条件。这就使得语义最小论的理论有空子可钻,因为要知道是什么事实能确定句子语义内容的真值,语义内容与事实就必定有联系,而这就为对意义进行语境的相对解释提供了入口。语境主义者完全可以不反对说出的句子是语义类型的例型而同时坚持句义的确定相对于语境,如,“这朵花是红的”经验地为真,当且仅当“这朵花”指称一个特定话语情境中的实在对象,该对象具有红的属性,且说话人和听话人同时知觉到了同一个实在对象的同样的事实;而这又涉及光线、观察位置、知觉特性、背景知识等等一系列因素(即所谓“杜恒-蒯因原理”*“Duhem-Quine thesis”,参见W. Lyc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124-127.)。这样一来,说话人和听话人在此情境下的心理表征中语境因素到底是概念意义的一部分还是仍为非语言性事实是难以确定的。困难恰恰在于概念的心理表征内容。如果最小命题存在,它必定只能由最小概念按组合性原则构成。那么,最小概念必然具有什么内容?如何确定其为最小?语义最小论着眼于语境敏感性的触发机制,这不失为明智之举,但还没有论证该机制如何确定了哪些元素属于语言使用者为了理解命题意义而必须掌握的概念内容。
第二,按布兰顿的分析语用学,对概念、命题意义的理解,关键在于说话人说出的内容是否是基于一系列前提做出的推论结论,并且同时能以该内容作为前提做出进一步的推论。语义最小论显然反对这样的观点,因为这一观点力图把语义建立在推论能力之上。但是布兰顿的观点却提出了一个有趣、无法回避的问题:什么构成了关于“意味着什么”的“理解”,亦即掌握了“概念内容”?*R. Brandom, Between Saying and Do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5.比如,在35℃左右,一个人可能说出“好热”这句话,一台设定好程序的电脑也能在35℃时播发“好热”这两个音节,但是由此说两者表达的都是同一命题意义却是很可疑的。人根据自己的感受或看见他人出汗等等得出了热的结论,且能进一步把热作为前提,进行后续推论,如需要休息以防中暑、开空调可以降温等等;但电脑只是按照事先设定的恒温器读数加上发音指令而做出精确的机械反应,如果不加其他程序设定,电脑即便是因过热而崩溃也不会进行任何进一步推论。因此,我们可以说人把握了热的概念内容,理解了“热”表达的意义,却不能说电脑也把握了同样的概念内容。电脑下棋赢了人类对手并不意味着电脑理解了下棋的意义。功能相似不等于本质相同。这意味着,语义最小论须要说明:机器“说”出的句子是否具有最小语义内容?对谁而言具有语义内容?无论回答是还是否,都涉及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概念的形成及其本质。到底什么可算作构成了句子语义内容以及对该内容的真正把握?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却又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三,技术上讲,语义最小论关于索引词解释概念的模型,虽然思路或许可行,但会面临很大困难。语言使用者被给予的是具体实在之物,而任何物体都必须处于空间坐标系的一个位置,这很好理解。但由于语义最小论是以“参照关系”来确定索引词的概念特点并由此建立索引词的语义类型模型,这必然涉及物体所在的是此点还是彼点的划界模糊性难题。例如,“这、那”等索引词或许可以从空间坐标参照来确定各自的语义类型,但诸如“这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之类是否一定是关于处于不同坐标参照点的实体对象,恐怕纯粹从概念特点难以定论,因为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索引词语义的模糊特征(空间位置上哪个点算作“这”、哪个点又算作“那”等),还涉及到了说话人的视角选择(甚至包括亲疏之类态度)。或许这个问题用模糊学的概念隶属度或认知主义的心理空间参照等理论可以得到说明,但是隶属度的确定只能是经验式的,而这不仅难以建立索引词或参照点的固定联系,还会引起诸如知识背景、甚至社会文化等等问题。这又恰恰是语义最小论力图避免的。而认知主义的心理空间参照理论则不符合语义最小论的思路,因为界标、射体等等恰恰属于语境认知的结构,语境因此成为句子意义的一部分。这也是语义最小论所反对的。因此,如何能够核查所有可能的参照点,从而确定位于其上的集合将是语义最小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最后,后格赖斯语用学倾向于寻找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面,尤其是关于规约性意义与非规约性意义之间存在的交叉意义,即所谓“话语类型意义”——既包含语义内容也包含语用内容的一般会话含义。*张绍杰:《后格赖斯语用学的理论走向》,《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如果话语类型意义层面确实存在,那么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句法、词项意义都是非语境敏感的,而话语类型意义却包含了语境敏感的信息。这些信息很难被彻底否定掉,因为一般会话含义既有规约性又有非规约性,这种两面性可以同时从意义系统层面和言语使用层面进行分析。话语类型层面的语义载荷中如何加入语境敏感信息、何时加入等等,这些都是目前悬而未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庞 礴)
Is Semantic Minimalism Minimal Enough: New Development of Insensitive Semantics
Liu Limin, Fu Shunhua
Against the predominant tendency of contextualism in meaning studies, H. Cappelen and E. Lepore have proposed the insensitive semantics, or semantic minimalism, claiming that an uttered sentence has a minimal semantic content that is independent of contextual factors. Later, E. Borg and G. Preyer have raised the question of how minimalism can be minimal enough and pushed the minimalist effort still further, attempting to prove that sentence meaning is determined by its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its component words' meanings, while intention and situation etc have no contribution in this respect. To establish this point, they have newly advocated a rigorous distinction of intentional behavior and semantic content, adhered more strictly to propositionalism and proposed to set up a conceptual model for indexical term type.
semantic minimalism, insensitive semantics, semantic content, speech act
刘利民,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四川大学语言与语言服务研究所研究员(成都 610064);傅顺华,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 61006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开明的自然主义研究”(16BZX020)
H0
A
1006-0766(2017)01-004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