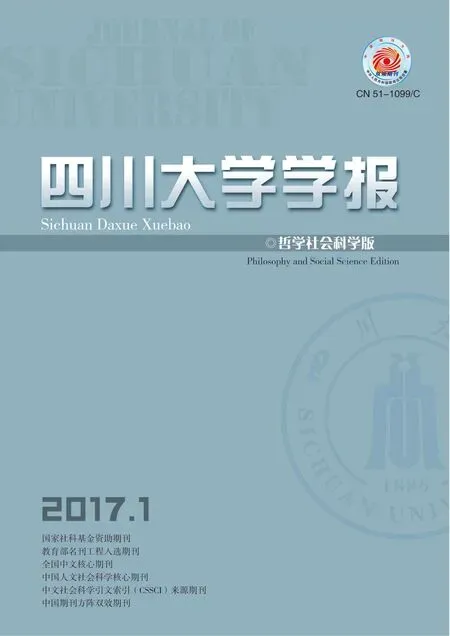《药师经》真伪问题新论
王飞朋
§宗教学研究§
《药师经》真伪问题新论
王飞朋
《药师经》宣传东方药师如来信仰,在中土流传很广。由于其第一译来源不明,僧祐认为该经是“依经抄撰”的伪经。但在费长房、慧矩对勘梵本之后,尤其是后三译出现后,佛经目录学家均倾向于认为《药师经》为翻译佛经。现代的佛教研究者因该经中有一些中国文化因素而认为其是中土所撰之伪经,并认为后三译是《药师经》梵本回流中土后翻译而成的。这种说法固然很有新意,但忽视了佛教“抄经”与“伪经”的区别,也对当时的中印文化交流状况认识不足。其实,《药师经》有着一系列的佛经渊源,汉译《药师经》也有着梵本依据,其中的异常处均能得到很好地解释。因此,目前尚不能认定《药师经》为中土所撰之伪经。
《药师经》;《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大灌顶经》;伪经;中印文化交流
《药师经》①鉴于《药师经》前后四译属于同一系统,除特别指出外,本文把《大灌顶经》卷十二《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隋达摩笈多所译《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唐玄奘所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及义净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统称为《药师经》。是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部佛典。其宣扬供养药师如来可以免除九横、增算延寿、福德无量,对庶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自南北朝以来,药师信仰就一直兴盛不衰,在中国民间信仰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佛教信徒除了抄写《药师经》、造药师如来像以祈福外,还举办药师斋会,利用《药师经》进行忏悔。②关于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药师信仰可参考傅楠梓:《中古药师信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玄奘大学,1989年;关于敦煌地区的佛教信仰可参考党燕妮:《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民间佛教信仰研究》第二章“药师信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9年。南朝陈文帝写有《药师经忏文》,说明《药师经》在当时已经流传至社会上层。隋唐时期,药师信仰更为流行,义净翻译《药师经》时,唐中宗亲为笔受。据不完全统计,敦煌遗书中《药师经》写卷多达六百余号,属于数量最多的几部佛经之一,敦煌藏经洞中药师经变画也蔚为大观。明代中期以后,民间出现了多种版本的药师忏法。而且,该经之影响还不止于汉地,六卷本《佛说消灾延寿药师灌顶章句仪》是明代以来云南阿咤力僧常用科仪。
《药师经》本身义理内容十分浅显,具有浓厚的人天教性质,但千余年来,一直流行不衰,显示了其殊胜之处。只是,关于该经之真伪却自南北朝时期便存在着争议。《药师经》初译本——《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翻译时间、地点、译主等均不明朗,且与《大灌顶经》之关系扑朔迷离,致使后世佛教目录对该经的记载歧异较大。僧祐在撰写《出三藏记集》时没有看到该经原本,只看到了慧简的抄撰本,便把其归入疑伪经录。隋费长房在比勘梵本《药师经》后,认为《药师经》是真经。之后,隋达摩笈多、唐玄奘及义净又三次翻译《药师经》,这三次翻译的时间、地点均很清楚。因此,后世佛经目录虽对《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译者与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但均把《药师经》看作真经。
二十世纪以来,日本佛教学者对这部经又重新起疑,不少人因其内容上羼杂一些看似道教的元素,便重新回到僧祐的观点,认为《药师经》是在中国伪造的经典,如日本学者望月信亨、长部和雄、阿纯章③望月信亨:《佛教经典成立史料》,京都:法藏馆,1946年,第409-416页;长部和雄:《道密管见》《唐宋密教史论考》,京都:永田文昌堂,1982年,第211-233页;阿纯章:《灌顶经の成立について》,载《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四一,1995年,汉译本名为《关于灌顶经的成书》,载《华林(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73-182页。等。其后,这样的认识为不少佛教学者认同,如台湾林福士*Lin, Fu-Shih, “Chinese Shamans and Shamanism in the Chiang-nan Area during the Six Dynasty Period (3th-6th century A.D.),” Ph.D.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4.及美国Michel Strickmann(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司马虚): The Consection Sutra: A Buddhist Book of Spells,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Edited by Robert Buswell,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75-118.等。在佛学研究者中,似乎只有印顺法师意见相左,他在《读〈大藏经〉杂记》中指出《大灌顶经》“是晋人编集的,也有印度传来的内容”,“第十二卷是《药师经》的古译”,*印顺:《读〈大藏经〉杂记》,载《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十二卷《华雨集》(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2页。即认为《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是《药师经》的第一译,《大灌顶经》是中土在翻译佛经的基础上编集的,但印顺法师并没有具体说明如此判断的原因。
中国大陆学者对此经的真伪一直未作细致的考索。近年来,伍小劼先生致力于《药师经》真伪问题之研究,其博士论文《〈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探颐索隐,深入考察了《大灌顶经》中各经经文、咒文的来源及其中的“中国”因素,是主张《药师经》为伪经的集大成之作。*伍小劼:《〈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第3-33页。此外,他还先后发表了三篇相关论文:《〈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与“文化汇流”》,《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大灌顶经〉的宗教理想》,《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日本古写经与〈大灌顶经〉研究》,《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7期。其导师方广锠先生在季羡林先生文化回流说的基础上,加入新的例证以支持其弟子的研究结论,*方广锠:《再谈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敦煌研究》2011年第3期。认为《药师经》为中土所撰,后传入印度,翻译为梵文,再倒流回中国。这种说法虽有新意,开人耳目,但也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忽略了《药师经》初译本与后三译本之间的相异之处(详见下文),逻辑论证也并不严密。之后,为《药师经》翻案的有杨维中教授《〈药师经〉翻译新考》*杨维中:《〈药师经〉翻译新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6期。一文,但杨文仅从佛经目录、梵本存否等方面立论,不够深入,缺乏较强的说服力。因此,关于此经的真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笔者拟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一些新的发现,对《药师经》的真伪问题加以辨析。
一、《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之译者及与《大灌顶经》之关系
判断佛经真伪,佛经目录是直接依据。但由于《药师经》原本的缺失,造成了后世佛经目录学家对该经真伪认识的严重分歧。中古时期各家目录关于《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翻译情况的记载较为混乱,且多前后抵牾之处。僧祐说慧简“依经抄撰”,很可能认为慧简就是该经的杜撰者。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七根据《杂录》认定九卷本《大灌顶经》翻译者为〔东晋〕帛尸梨蜜多罗,但同时,卷十又记载《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刘宋慧简所译。此后,静泰《众经目录》、道宣《大唐内典录》、明佺《大周勘定众经目录》均直接认为十二卷本《大灌顶经》译者也是帛尸梨蜜多罗。而《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本身出自《大灌顶经》第十二卷,因此这两种说法具有明显矛盾。智升在《开元释教录》中折衷众说,认定《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是《大灌顶经》的别生经,把其译者定为东晋帛尸梨蜜多罗,暂时解决了这一矛盾。
帛尸梨蜜多罗本为西域国王之子,以国让弟后于东晋永嘉初来到建康,住建初寺,与丞相王导等相善,被称作“高座法师”。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记载,尸梨蜜(即帛尸梨蜜多罗)“性高简,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语言,蜜因传译,”“善持呪术,所向皆验”,翻译有《大孔雀王神呪》《孔雀王杂神呪》各一卷。仆射周顗遇害时,蜜往省其孤,“对坐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次诵呪数千言,声高韵畅,颜容不变。”*僧祐:《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练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22页。可见,帛尸梨蜜多罗之“善持呪术”非常有名。只是,帛尸梨蜜多罗不通汉语,与人交流尚需传译,很难想象其会选择翻译十二卷本的《大灌顶经》,何况里面还掺有诸多中国文化元素。而且,《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均无帛尸梨蜜多罗翻译《灌顶经》的记载。鉴于《历代三宝纪》所载《别录》之内容多不可信,此处关于帛尸梨蜜多罗翻译《灌顶经》的说法也值得怀疑。
因此,一切需要回到源头。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疑经伪撰杂录》中说该经是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秣陵鹿野寺比丘慧简“依经抄撰”而成的。*僧祐:《出三藏记集》,第225页。秣陵县,刘宋时属丹阳郡。但据现有资料,南朝并无“鹿野寺”之名,“鹿野寺”出现于北朝。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八记载,北魏孝文帝皇兴五年(471),“昭传位太子,徙居崇光宫称上皇,建鹿野寺,与禅僧数百习学禅定。”*《大正藏》第49册,第355页。可见,僧祐的记载也并不可信。而查阅资料,发现当时有两个慧简存在:
1.跟随法显去印度求法的慧简。据《法显传》,法显行至张掖时,“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殷勤,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大正藏》第51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第857页。此后,一行人至乌夷国,因当地“人不修礼仪,遇客甚薄,”故“智严、慧简、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资。”然而,奇怪的是,此后的《法显传》中再也没有关于慧简的文字,无从得知此慧简是否和法显一起游历天竺并返回中土。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此时距离大明元年有五十八年之久。假设此慧简二十多岁跟随法显西行,大明元年若还在世已经八十余岁,很难想象一个八十余岁的老僧人会去翻译佛经,或者有意“抄撰”佛经。
2.《续光世音应验记》中所载之慧简。《续光世音应验记》载:“荆州厅事东有别斋三间,由来多鬼,恒恼人,至王建武时,犹无能住者。惟王周旋慧简道人素有胆识,独就居之。……简住弥年安稳,余人犹无能住者。”*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页。董先生认为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二十五中转写了《光世音应验记》中慧简的事迹,但是说慧简“梁初在道”是没有依据的。王建武即王忱,《晋书·王忱传》载其“太元中,出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建武将军、假节。”*房玄龄等编:《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73页。太元(376—396)为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年号,在大明元年前五六十年。此慧简当时已经是王建武的旧相识,因此肯定不会是在秣陵抄撰《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慧简,其活动时间反倒跟上面所说的跟随法显西去印度的慧简相近。
因此,从时间上看,上述二慧简均非大明元年翻译《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慧简。诡异的是,在僧祐《出三藏记集》中,慧简只是“依经抄撰”了《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而到了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中,慧简已经成为了众多佛经的译者。《历代三宝纪》卷十依据《别录》记载慧简于鹿野寺出《药师瑠璃光经》《商人求财经》等二十五卷佛经,但没有直接说明翻译时间。唐靖迈《古今译经图纪》根据僧祐所记《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之翻译时间而认定其他佛经也翻译于大明元年。智升延续了这种认识,其在《开元释教录》卷五中还详细地考察了各经出处,认为《阎罗王五天使者经》等十部为翻译(其中大部分是大部头佛经中小经之同本异译),《真伪沙门经》等十五部是别生经。费长房云其著录慧简所译佛经是依据《别录》,此《别录》究竟指的是哪一部佛经目录且有无根据今已无从知晓。因此,关于早期佛经目录中所记载的慧简译经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祐录》之时间记载有误;二是《房录》所载《阎罗王五天使者经》等译经依托慧简之名。限于资料,目前还不便定论。只是,费长房依据《别录》记载认定慧简翻译《药师琉璃光经》具有一定可能性,至少表明慧简与《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有特殊的关系。
那么,《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与《大灌顶经》的关系又如何呢?伍小劼详细考察了《大灌顶经》前九卷的咒语,认为其大部分是从中土早期翻译的佛经改编杂抄而来,编撰者在改编的同时,还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思想。比如,前九卷充满了末法的紧迫感,甚至还屡次提到恶王灭法,说明这九卷是在北魏太武帝于太平真君六年(445)灭佛后作成的。*伍小劼:《〈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第260页。《大灌顶经》第十、十一卷亦为中土所撰。笔者赞赏其考证功夫,也相当认同这一结论。但伍先生对《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与《大灌顶经》的关系失于考察。笔者认为《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很可能是《大灌顶经》中最早出现的一卷,理由如下:1.《大灌顶经》第一卷中已经出现了“九横”一词,但其解释却在《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中,其他卷中,“横”之意义均和“九横”之“横”相同;2.前十一卷的内容,如鬼神护命、命终八菩萨相迎、幡灯供养、素食戒杀、阎罗王疏记善恶、往生十方净土等内容在第十二卷中均有出现;3.据《出三藏记集》记载,《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又名《灌顶经》,而《大灌顶经》中的其他十一卷经文则没有如此称法。从名称上看,《大灌顶经》很可能是因《灌顶经》而得名。4. 《大灌顶经》前十一卷经文只出现于《大灌顶经》中,而《药师经》先后有四次翻译,“药师如来”之名号也出现于其他佛典之中(详下)。因此,《大灌顶经》前十一卷很可能是在第十二卷《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基础上撰写的,在完成后一起编成十二卷本《大灌顶经》。据此,即使《大灌顶经》前九卷全是伪经,也不能证明早于其出现的《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是伪经。*如上述推论成立,《大灌顶经》很可能根本没有九卷本这一形式,《出三藏记集》中“从《梵天神策》及《普广经》《拔除过罪经》凡三卷是后人所集,足《大灌顶》为十二卷”之说可能有误,僧祐本人也应该没有看过九卷本。《大灌顶经》第一、六、七卷中都有“《灌顶》十二部经典”几个字,如果是九卷本先出,就会是“《灌顶》九卷经典”,二者的不同十分明显。此后的佛经目录学家基本上沿袭僧祐的记载,都应该没有见过九卷本。因此,《大灌顶经》前十一卷之内容本于第十二卷,即使前十一卷全部为伪经,也不能轻易否定第十二卷为真的可能性。
其实,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来梳理《灌顶经》及《大灌顶经》的形成过程。既然《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大灌顶经》及慧简、大明元年四者之间关系密切,可以做如下两种推定:1.慧简在翻译《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同时对其进行了一些改编,形成摘译本;稍后,在北魏太武帝灭法的阴影下,有人依据其内容杜撰了前十一卷,在大明元年编为十二卷《大灌顶经》,并假托善咒术的“帛尸蜜多罗”之名流通。2.《药师经》在大明元年前已被译出,但尚未流传;其后,慧简修改《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又依其内容杜撰了前十一卷,在大明元年编为十二卷《大灌顶经》,并假托“帛尸蜜多罗”之名流通。虽然,这只是笔者根据佛经目录的记载所作的推测,受材料限制,还有一些问题无法彻底解决,但至少可以说明不能直接把《药师经》看作中土所撰之“伪经”。
二、《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梵本根据及佛经渊源
判断佛经真伪,有无梵本存在也是很重要的依据,尤其是《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这种佛经目录记载不明确者,有无梵本来源就显得更加重要。费长房就是在对勘了梵本之后,认定《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翻译佛经。大业十二年(616年),慧矩曾协助达磨笈多于洛阳上林园翻译《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其在译经序中说:“矩早学梵书,恒披叶典,思遇此经,验其纰谬。开皇十七年,初获一本,犹恐脱误,未敢即翻,至大业十一年复得二本,更相雠比,方为楷定。遂与三藏法师达磨笈多,并大隋翻经沙门法行明则、长顺海驭等,于东都洛水南上林园翻经馆重译此本。”*《大正藏》第14册,第401页。说明其也是在校勘梵本后才认定《药师经》为真。唐永徽元年(650)五月五日,玄奘于大慈恩寺翻经院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沙门慧立笔受;神龙三年(707)夏,义净于大内佛光殿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唐中宗笔受。后三次翻译之时间、地点、译主、笔受等都历历在案,毫无疑问是从梵本翻译而来的。更有说服力的是,时至今日,还有《药师经》梵本留存于世。20世纪初,斯坦因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地区发现了一批梵文佛经,其中就有四部药师经典。据研究,这些《药师经》梵文残片应是在公元5-6世纪在吉尔吉特地区抄写的。杜特比勘了相应的汉文和藏文译本后认为,这批经典实际包括两部《药师经》。*日本学者新井藤慧认为包含三个不同藏本的《药师经》,见蔡耀明:《吉尔吉特(Gilgit)梵文佛典写本的出土与佛教研究》,《正观杂志》2000年第13期。与汉文译本相比,这两部《药师经》的文字与藏文大藏经中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与《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最为接近。而《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与玄奘所译《佛说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基本相同;《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与义净译《佛说药师如来七佛本愿功德经》也基本相同。此外,钱德拉(Chandra)、邵朋(Gregory Schopen)、真田由美、松元恒等学者都对《药师经》的梵文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伍小劼:《〈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第20-23页。日本学者新井慧誉就根据这批梵文《药师经》的出现,认为《药师经》不可能出于汉地之伪造。而除《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之外,《大灌顶经》前十一卷没有其他翻译版本,也未发现有关梵本。
其实,除了先后四译的《药师经》外,其他佛经经文中也有“药师如来”出现,证明其非中土杜撰。隋北印度三藏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第十四中提到“药师王佛”。隋阇那崛多译《五千五百佛名经》卷三云:“南无药师琉璃光王如来,若称彼佛如来名者,一切殃罪悉皆除灭。”*《大正藏》第14册,第328 页。直接指明了诵持《药师经》的功德。唐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卷五云:“又值增益佛,奉上众宝盖,又见药师佛,奉以胜妙座。”*《大正藏》第3册,第567页。唐天竺沙门般剌蜜谛译《首楞严经》卷七提到药师如来之梵文音为“吠疏璃唎耶”,*《大正藏》第19册,第134页。而《首楞严经》汉译本经名下注云“中印度那兰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其中的“灌顶”二字也和《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中的“灌顶”二字遥相呼应。唐玄奘所译之《胜幢臂印陀罗尼经》云:“善男子,我念过去曾于药师琉璃光胜观等诸佛所,闻此神呪,受持读诵,正为他说。”*《大正藏》第21册,第883 页。其中“药师琉璃光王佛”自然是“药师如来”无疑。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二收录有关“药师琉璃光佛印”的一段内容,来源于《药师经》,宋代法护所译《大乘集菩萨学论》卷二、卷十一、卷十二也有三处引用《药师琉璃光经》,但这些引文和现存四译本之文字均不相同,当是直接从梵本翻译而来。这就更加证明了《药师经》应该产生于印度。
此外,通过爬梳佛经,还可以追溯药师如来及《药师经》产生的渊源。《妙法莲华经·药王药上菩萨品》云:“若有人闻是《药王菩萨本事品》者,亦得无量无边功德。若有女人闻是《药王菩萨本事品》,能受持者,尽是女身,后不复受。若如来灭后后五百岁中,若有女人闻是经典,如说修行,于此命终,即往安乐世界。”讲述了诵持《药王菩萨品》的巨大利益,又云:“说是《药王菩萨本事品》时,八万四千菩萨得解一切众生语言陀罗尼”,把药王菩萨的作用跟陀罗尼呪语联系到了一起。《陀罗尼品》中,释迦牟尼佛赞药王菩萨说“善哉!善哉!药王!汝愍念拥护此法师故,说是陀罗尼,于诸众生,多所饶益”,*《大正藏》第9册,第54、58页。药王菩萨与陀罗尼呪的关系更加深入。而从上面所引《法华经》经文可以明显看出,药王药上菩萨与陀罗尼以及祛灾获福等现世利益的关系非常密切。
和《妙法莲华经·药王药上菩萨品》相比,《佛说观药王药上菩萨经》中药王药上菩萨的身份加入了新元素,为药师如来最终出现奠定了基础。《佛说观药王药上菩萨》云:“彼时有佛号琉璃光照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正安隐’,国名‘悬胜幡’。”这里,琉璃光照如来国名“悬胜幡”,而幡灯供养正是《药师经》所提倡的重要修行手段。《佛说观药王药上菩萨经》中还提到了信众中有一比丘名“日藏”,有一长者名“星宿光”,此二人名字和药师如来的二胁持“日曜”“月净”非常相似。经中又说:“我得菩提清净力时,虽未成佛若有众生闻我名者,愿得除灭众生三种病苦:一者众生身中四百四病,但称我名即得除愈……愿此众生消除三障,如净琉璃内外映彻,见佛色身亦复如是,若有众生见佛清净色身者,愿此众生于平等慧永不退失。”这里出现了药上菩萨发愿的场景,与药师如来相似,其发愿也是为众生现世利益的实现。此外,经中还记载药王菩萨摩诃萨在说呪后白佛言:“佛灭度后,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闻此呪者、诵此呪者、持此呪者,净诸业障、报障、烦恼障,速得除灭,于现在身修诸三昧,念念之中见佛色身,终不忘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若夜叉若富单那、若罗剎、若鸠盘茶、若吉遮若毘舍阇,噉人精气一切恶鬼,能侵害者无有是处。命欲终时,十方诸佛皆悉来迎,随意往生他方净国。”*《大正藏》第20册,第665、661页。持呪可以消除恶鬼之害,可以往生十方净土,这样的描述和《药师经》的内容更为接近。
综上,《佛说观药王药上菩萨》中佛的名号“琉璃光照如来”,和本经主要宣传的药王药上菩萨,构成了药师如来的原型,经中提到念药王、药上二菩萨名号可以“得见东方无数诸佛”,把琉璃光和东方联系到了一起,而当时其他一些佛经宣扬药师具足王如来存在于东方,*吴支谦译《佛说八吉祥神呪经》载:“(东方)去是五恒沙,有佛名药师具足王如来。无所著,最正觉,今现在说法,其世界名曰满一切珍宝。”(梁代之前所译)失译《佛说不思议功德诸佛所护念经》云:“东方满一切珍宝世界药师具足王如来。”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出现了“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之名号。此外,《药师经》的内容与《妙法莲华经·药王药上菩萨品》、《佛说观药王药上菩萨经》均有一定的关联。因此,“药师如来”之名号及《药师经》的产生均有着印度佛教渊源,无法轻易否定。
三、《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被僧祐列入疑伪经录之原因
《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被僧祐列入疑伪经录很可能与僧祐对抄经的态度有关。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抄经录》中批判了当时“肆意抄撮,或棋散众品,或爪剖正文”的现象,认为这样“既使圣言离本,复令学者逐末”,说明僧祐十分注意区别佛教抄经和译经,对佛经文本的纯洁性要求相当严格。当时,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有多部抄经,僧祐虽与其交好,但仍对其抄经行为进行了批评。此外,僧祐在《出三藏记集·疑伪经录》对齐武帝时比丘释法愿“抄集经义”*《出三藏记集》,第226页。所出之《佛法有六义第一应知》一卷及《六通无碍六根净业义门》一卷评论说:“虽弘经义,异于伪造,然既立名号,则别成一部。惧后代疑乱,故明注于录”,对齐武帝时比丘释王宗所撰之《佛所制名数经》五卷评论说“抄集众经,有似数林,但题称佛制,惧乱名实,故注于录。”*《大正藏》第55册,第37、39页。其实,以上两种均属抄经而成,不同于通常所说的伪造,但僧祐还是因“惧后代疑乱”“惧乱名实”而把其列入疑伪经录。慧简“依经抄撰”的《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被列入“疑伪经”的理由恐怕也在于此。
只是,慧简本乃《药师经》的第一译,僧祐说其是“依经抄撰”的根据何在呢?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后世佛经目录学家也只注意考察其真伪和译者,而没有关注此问题。伍小劼从《药师经》为中土所撰的立场出发,发现《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有两句经文抄自伪经《高王皇帝尊经》,*伍小劼:《〈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第193页。另一些内容与《七佛八菩萨经》相似。但这些相似很可能是因梵文相同而翻译时借用,或翻译后依该经所作的修改,并不像《佛所制名数经》那样是“抄集众经”而成。
僧祐说慧简本“依经抄撰”,说明其不仅仅是“抄”,也有“撰”的部分。认真对照慧简本和后三译,可以发现慧简本确实增添或改变了一些语句,可以作为证明其为改编本或编译本的关键。这些均是伍先生没有注意到的,故在此具体列出。
(一)慧简本中“救蚁”一词不见于其他译本
《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中“昔沙弥救蚁以修福故,尽其寿命不更苦患,身体安宁,福德力强使之然也”*《大正藏》第21册,第535页。一句,不见于其他诸译本。查找藏经,“沙弥救蚁”之典故出自《杂宝藏经》卷四“沙弥救蚁子水灾得长命报缘”:“昔者有一罗汉道人,畜一沙弥,知此沙弥却后七日必当命终,与假归家,至七日头,勅使还来。沙弥辞师,即便归去,于其道中,见众蚁子,随水漂流,命将欲绝,生慈悲心,自脱袈裟,盛土堰水,而取蚁子,置高燥处,遂悉得活。至七日头,还归师所,师甚怪。寻即入定,以天眼观,知其更无余福得尔。以救蚁子因缘之故,七日不死,得延命长。”*《大正藏》第4册,第468-469页。《杂宝藏经》乃北魏延兴二年(472)吉迦夜共僧正释昙曜翻译,刘孝标笔受。此经翻译时间在慧简本所出现的大明元年(457)之后十余年,照理慧简本不应出现此一故事,但《经律异相》卷二十二“沙弥救蚁延寿精进得道四”中也有此故事,注云“出《福报经》,又出十卷《譬喻经》第七卷”。*《大正藏》第53册,第119 页。按:《福报经》,《出三藏记集》列入“失译录”,《历代三宝纪》认为是外国沙门康孟详于汉献帝世翻译,现已佚,而现存两种与《福报经》相似的两部佛经——失译的《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里均无“沙弥救蚁”情节。因此,“沙弥救蚁”故事显然是取自康法邃所编十卷本《譬喻经》。据《出三藏记集》,十卷本《譬喻经》是晋成帝时沙门康法邃抄集众经所撰,而《开元释教录》未录该本,可能唐代已佚。由于“沙弥救蚁”故事不见于其他两本,当是慧简本在编译时或收入《大灌顶经》时所增加的文字。
(二)慧简本中提到的“善信二十四戒”与其他译本有异
慧简本“若男子女人,受三自归,若五戒,若十戒,若善信菩萨二十四戒,若沙门二百五十戒……”一句经文中出现了“善信二十四戒”的说法。此处,达摩笈多本作“菩萨一百四戒”,玄奘及义净译本作“菩萨四百戒”,*其中,义净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宋、元、明、宫本均作“四百戒”,而高丽本作“二十四戒”,很可能是因慧简本而改写,因为义净本《药师经》在翻译时与玄奘本大同,很可能是参考了玄奘译本,而玄奘译本此处作“四百戒”。均与慧简本不同。鉴于藏经中并没有“菩萨二十四戒”的说法,因此此处“善信二十四戒”的来源还需另寻线索。唐代,法宝《俱舍论疏》卷一在讲到佛经因传译而致误者时,认为宋本(即慧简本)善信菩萨二十四戒和隋、唐本菩萨四百戒,“根本是一,传不同故”。*《大正藏》第41册,第455页。事实上,此处的不同并非翻译所致。北图藏敦煌文献中有《善信菩萨戒经》一卷,编号为BD.01048(北6787),其副标题为《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下有注云:“出方等□□□经”(中间三字残缺)。逐一比照《善信菩萨戒经》中二十四戒的内容,可以认定其所谓的二十四戒乃是出自北凉法众翻译的《大方等陀罗尼经》。但《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一中只有二十四戒,并没有“善信菩萨”这一名号。现存佛教文献中,既有二十四戒,又有善信菩萨的是梁宝唱编纂的佛教类书《经律异相》。《经律异相》卷三十八“善信女少悟无常秉志清白为天帝所试”条讲到佛化身美色男子试探善信女却为善信端正拒绝,“佛与大众俱即飞行到善信家,父母兄弟见佛飞空,莫不欢喜。善信前礼绕佛百匝,佛便微笑,无数光出,语以戒法。绕身百匝,还从顶入,即授二十四戒。佛言:‘是为我优婆夷高行三八二十四戒’。”文末注释说此文出自“《善信摩祝经》卷上”。*《大正藏》第53册,第205 页。《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安公疑经录》中有《善信女经》二卷(或云《善信经》),而没有《善信摩呪经》的信息。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八据《李廓录》,认为鸠摩罗什翻译《善信摩诃神呪经》二卷。*《历代三宝纪》卷十还载有求那跋摩《善信二十二戒》一卷,亦名《离欲优婆塞优婆夷具行二十二戒》,亦名《三归优婆塞戒》,和善信二十四戒不同。不管记载怎样混乱,善信二十四戒很可能跟善信女的故事以及《方等陀罗尼经》有关。慧简本里面出现“善信二十四戒”,*日本传教大师最澄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入唐,其《天台法华宗学生式问答》卷四在讲述了《药师经》的五次翻译后说:“已有二十四戒,又一百四戒,又四百戒,众本不定,又无条文,迈法师云‘梵本随诵者不同,有此三别,是故译经三藏称本而翻,故有此不同也’”,说明最澄注意到了《药师经》翻译中存在差别的现象,但没有注意到慧简本二十四戒前有“善信”二字,《善信二十四戒经》应是当时中土依据佛经所编的“抄经”。说明作者为了增强宣传效果而化用了当时流行的说法。
(三)后三译中没有“八菩萨”的具体名称,且慧简本“八菩萨”之名称有异文
《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宣扬诵持《药师经》、供奉药师如来者命终时,有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至菩萨、无尽意菩萨、宝坛华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及弥勒菩萨等八菩萨“飞往迎其精神,不经八难,生莲华中,自然音乐,而相娱乐。”而后三译中均只有“八菩萨”这一笼统的说法,没有具体名称。敦煌文献《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中有些卷子中的“八菩萨”与现藏经本异。这些卷子如:S.162、S.1968、S.2444、S.3903、S.4083、S.5037、S.5200、S.6383、ДX01500、BD00602、BD03407、BD04407、BD06674,共13号。*伍小劼:《〈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第171页。八菩萨的名字在上述13号中基本相同,有时略有小异。如S.1968号八菩萨名字为“跋陀和菩萨,罗邻那竭菩萨,悟目兜菩萨,那罗达菩萨,须深弥菩萨,摩诃萨伽菩萨,用垣达菩萨,和瑜论菩萨”;S.3903号八菩萨名字为“拔陀和菩萨,罗邻那竭菩萨,矫越觉菩萨,那罗达菩萨,须量弥菩萨,摩诃萨和菩萨,同抵达菩萨,和偷轮菩萨”。这种八菩萨组合和《般舟三昧经》中的八菩萨组合相似,而且也见于《光赞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佛说八吉祥神呪经》《佛说佛名经》《佛说华手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呪经》等多部早期大乘经典,可见这种八菩萨组合是早期大乘经典较为流行的组合。可以想像《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最初也是这种组合,后面在慧简本中或被收入《大灌顶经》时修改成了较为知名的文殊师利等八大菩萨,以广流传。
(四)慧简本中的“五官”也是其他各本所没有出现的
慧简本在讲到阎罗王料简罪福时,提到了五官,其文如下:“又有众生不持五戒,不信正法,设有受者,多所毁犯。于是地下鬼神及伺候者奏上五官,五官料简,除死定生,或注录精神,未判是非,若已定者,奏上阎罗。阎罗监察,随罪轻重,考而治之。”但此处之“五官”在后三译中均没有出现。达摩笈多译本作“阎摩使人引其神识,置于阎摩法王之前,此人背后有同生神,随其所作,若罪若福一切皆书,尽持授与阎摩法王”,出现了“同生神”的说法,而没有出现“五官”,玄奘译本和义净译本均作“若诸有情,不孝五逆,破辱三宝,坏君臣法,毁于信戒,琰魔法王,随罪轻重,考而罚之”,没有出现“五官”和“同生神”字样。一般来说,佛教中没有五官的说法。*唐般若斫羯啰译《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云:“若欲知地狱文案吉凶者,即呼五官使者。”这和本经说法相近。然而,据费长房《历代三宝纪》记载,慧简所译《阎王五天使经》*后世藏经中作《阎罗王五天使者经》。一卷就提到了“五天使者”,这“五天使者”为生、老、病、死、恶五者的形象化说法。《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中“五官”也许是慧简对印度五天使者和中土三官(天官、地官、水官)的融合。
除了上面所举的例子,还有一些是慧简本独有而后三本没有的。如《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云:“佛告文殊若欲生十方妙乐国土者,亦当礼敬瑠璃光佛;欲得生兜率天见弥勒者,亦应礼敬瑠璃光佛。”其他译本中均没有后面一句,说明慧简本把药师信仰和弥勒信仰联系到了一起。在宣扬信奉药师如来的功德时,《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云:“求长寿得长寿,求富饶得富饶,求安隐得安隐,求男女得男女,求官位得官位。”“求官位得官位”,也不见于其他三本,当是“慧简本”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需要而增加的。
可见,《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了吸引信众,扩大药师信仰的传播,增加了一些当时熟知的故事、典故以及中土化的内容。*因此,隋代参与翻译《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的慧炬认为《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梵宋不融、文辞杂糅”。僧祐很可能是根据这些内容认为其是“依经抄撰”,从而把其归入疑伪经录。慧简本的增加和改编有两种可能:一是佛经翻译中的添加,这样的话,慧简本本身也是翻译而来,属于编译本;二是慧简之前有一部《药师经》翻译本存在,慧简本对其进行了加工改造。而如果依据《药师经》回流说的思路,《药师经》为中土所撰,那么慧简本就是该经最早的本子,在经过梵文转换后,后面的汉译本中也应该有这些内容,然而上述内容在后三译中均没有看到(或内容有异)。因此,《药师经》后三译是由《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翻译为梵文后重新译为汉文的推论是有问题的。
四、从印度密教的兴起看《药师经》的真伪
《药师经》由汉译梵的可能性必须建立在那些来源“可疑”的内容完全属于中土文化的前提下,但事实上,那些看似属于中土文化的内容在佛经中也可以看到。比如,关于阎罗王“料简罪福”,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菩萨处胎经》卷第五云:“尔时阎罗王以五事问,即勅狱卒随罪轻重付令治之。”*《大正藏》第12册,第1038页。元魏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第十七云:“若有众生造诸恶业,时阎罗王即令此鬼录其精神。”卷六十八云:“或以天眼,过前大海,见阎罗王决罪福处,一切众生证业果处,是阎罗王所住境界,阎罗王法治诸罪人。”*《大正藏》第17册,第98、402页。这些经文对阎罗王作用的说明和《药师经》大致相似,而二经是翻译经典当没有疑问。
关于达摩笈多本译本中的“同生神”,敦煌写卷S.2551《药师经疏》解释说:“‘同生神’者,即阿赖耶识,以赖耶识是寿生之意,与身同时而生,故名同生。随其所作,若(祸?)福一切皆书者,谓随诸众生所生罪福,皆悉熏在阿赖耶识中。”*《大乘义章》卷三谓“识乃神知之别名”。此句中“若福一切皆书”意思不通,似漏抄“如罪”两字。认为“同生神”是阿赖耶识之比喻说法,而其记录善恶罪福,便是八识的熏习作用。唐代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卷上载:“为求子故,即便祈请大自在天、四大海神、毘沙门天、帝释、梵王,诸天神等悉皆祈请求其男女,诸园林神、旷野等神、四衢道神、受祭神、同生神、同法神,常随神等,悉皆求之。”其中也出现了“同生神”之名。虽然此处之“同生神”并非指阿赖耶识,但至少证明了佛经中存在着“同生神”*《大正藏》第37册,第124页。《华严经》称之为“同生天”,“如人从生,有二种天,常随侍卫,一曰同生,二曰同名,天常见人,人不见天。如来神变,亦复如是,非诸声闻所能知见,唯诸菩萨乃能覩见。”吉藏在《无量寿经义疏》卷一中云:“一切众生皆有二神:一名同生、二名同名。同生女在右肩上书其作恶,同名男在左肩上书其作善。四天善神,一月六反,录其名藉,奏上大王。地狱亦然,一月六齐,一岁三覆,一载八校,使不差错。故有犯者,不赦也。”则是融合了民间思想的新讲法。这一讲法,也说明《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中“同生神”的讲法不是无源之水。
虽然上述材料并不能证明《药师经》中所有那些看似中土化的内容都是在印度文化情景中产生,但毫无疑问,不能肯定地说这些思想只有中土才能产生。《药师经》中疑似中土文化特色的内容较多,很可能跟其密教性质有关。不管是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密教发达志》,还是大陆学者吕福建《中国密教史》、李小荣《敦煌密教论稿》、彭建兵《敦煌石窟早期密教状况研究》、*彭建兵:《敦煌石窟早期密教状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6年。台湾学者萧登福《道教与密宗》等著作,都把《药师经》作为密教经典来讨论。的确,《药师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宣扬陀罗尼神威力量,这是早期密教(杂密时期)佛经的特点。密教佛经通过呪语、仪式等神威力量宣传自己,体现了婆罗门教向佛教的渗透。《药师经》应该是杂密早期印度佛教受婆罗门教影响而产生的一部佛经。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密教又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及民间信仰存在着较为亲近的关系。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乍看起来,密宗似乎是印度传到中国的舶来品,但是更细致地考察年代,我们就会考虑到,整个事情至少很有可能真正是属于道教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56页。具体论述可参考该卷第十五章第六节“密教及其与道教的关系”;还可参考该书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之第五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内丹》第三十三章第七节“中国的内丹与印度的瑜伽和哈达瑜伽体系”。据日本长部和雄教授统计,在《大正藏》第18-21册593部密教经典和仪轨中,受到道教影响的有70部。其认为道密融合不但表现在教义内容,更表现在行事实践方面,这种融合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1.密教吸收了道教以前先行的思想和信仰,如阴阳五行说,五脏六腑说、谶纬、神仙方术、六甲、巫祝、鬼神等;2.道、密在传播过程中摄取并融合了对方的教义内容、仪礼、符呪、印法等,采用了对方的术语、文句、呪声等;3.道、密全盘吸收了对方思想和内容,甚至名称也很雷同。*长部和雄:《唐宋密教史论考》,京都:永田文昌堂, 1982年,第213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也对中国道教和印度密教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张毅先后发表《试论道教对印度的影响》《试论密宗成立的时代与地区》*伍加伧、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8-96页。前文原载《南亚与东南亚资料》1984年第5辑;后文原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第20-27页。等论文,阐述道教对密宗的形成以及对印度化学发展的影响。黄心川在《道教与密宗》一文中引用了印度P·C·雷易教授的观点来论证上述观点。P·C·雷易《古代中世纪印度化学史》中提到,印度泰米尔文献中的十八位密教“成就者”或大师中有两位是中国人,他们的泰米尔名字叫博伽尔(Bogar)和普利波尼(Pulipani)。博迦尔原是道教徒,公元三世纪时去印度,最先住在巴特那、伽耶,嗣后迁居南印度,皈依了密教。他撰写了不少炼金术和医药学的著作,并为印度培养了大批学生,后带着一批弟子回到中国,这些弟子在中国学成之后又回到南印度的纳德,传授“中国道”。另一个大师普利波尼与博迦尔一起到印度,定居于纳德。他根据密教的观点,用泰米尔文写了不少有关巫术、医药、炼金术的著作。博迦尔和普利波尼的材料虽然在中国史籍中没有记录,但他们的事迹是确凿无疑的。*P·C·雷易:《古代中世纪印度化学史》,转引自黄心川:《道教与密教》,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中华佛学学报》1999年第12期。虽然这种说法仅来源于密教的传说,没有其他文献佐证,但鉴于当时中印文化交流之密切,这种说法的流传当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此外,李南、朱越利、萧登福等也都认为道教对印度密宗的产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朱越利:《藏传佛教和道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萧登福著有《道教与密宗》(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3年)一书力证道教对密宗的影响,对密宗受道教影响状况做了详细的论述。但萧先生的一些观点仅仅依靠汉译佛经中的说法,忽视了有些佛经可能是中土所造之伪经。李南对道教与印度密宗的关系有很好的总结:“道教与密教根植于不同的土壤,沿着各自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等轨迹发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的密宗与中国的道教曾经有过相互之间的交流、影响、借鉴、融合,而在公元2-6世纪时期则较为频繁,达到过一个高潮,并对印度密宗与中国道教的理论及其方术仪轨等实践活动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作用。它造成二者之间的不少相似共通之处。”*李南:《略论印度密宗的真言呪语》,《南亚研究》2005年第2期。可以说像佛教影响中国一样,中国的道教以及民间宗教也对佛教尤其是密教的产生有激发和促进作用。虽然其中的具体影响状况还需深入考察,笔者目前力有未逮,但至少可以认同李约瑟先生的看法:“尽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道教对密教的支配性影响似乎已清楚地得到了确认。”*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五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内丹》,第257页。因此,《药师经》中那些看似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内容产生自印度也并非不可能。
五、结 语
《药师经》内容独特,*《药师经》中不少内容为该经独有。如讲到戒律时,慧简本云“菩萨二十四戒”,达摩笈多本云“菩萨一百四戒”,玄奘及义净本云“菩萨四百戒”,内容并不一致,但不管是菩萨二十四戒、一百四戒,还是四百戒,都不见于其他佛典。此外,《药师经》用“九横”表示九种会导致丧命的自然或人为灾难,讲到命终时可悬长四十九尺之“五色幡”续命,主张放生修福等也仅见于与《药师经》相关的个别佛典及少数密教经典,而不见于很多大乘佛经。版本复杂,影响深远,理应引起学界更多关注。二十世纪以来,不少中外佛教学者发现《药师经》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大灌顶经》中包含了一些看似具有中土文化因素的内容,遂判定其为中土所造之伪经。这种认识目前尚不能成立。笔者认为《药师经》非中土所撰佛经,理由如下:
1.有梵本根据。隋费长房、慧矩在对勘梵本后才认定《药师经》为真本,且《药师经》后三次翻译之时间、地点、参与人物均无疑问,都是从梵本翻译,且现在还有梵本存世。
2.在佛典中,《药师经》的出现有一系列的铺垫。《药师经》之前的不少佛典已经蕴含着药师信仰的要素,药师如来之名号出现于多部佛经中,且药师信仰的出现也有着明显的发展脉络。
3.印度密宗也有产生《药师经》及药师信仰的土壤。印度密宗在吸收中土道教、民间宗教及印度原有的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形成看似具有中华文化色彩的内容是有可能的。
4.《大灌顶经》前十一卷(尤其是前九卷)很可能在《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之后才出现,因此即使《大灌顶经》前十一卷是中土所撰之伪经,也不能认定《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同样是伪经。
5.慧简本与后面三本存在着文字差异,而这些内容上的不同很可能说明了慧简本是在翻译时添加入中土内容而形成的编译本,或者《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是在其之前存在的《药师经》基础上形成的改编本。
而《药师经》回流说除了无法回应上述证据外,其自身的成立还需要面临一系列的诘难。首先,《药师经》回流说只是一种假说,缺少直接证据,还有很多问题未能很好说明。比如,梵本和“慧简本”都出现于公元5、6世纪,时间过于接近,与“佛典在产生一段时间后传入汉地”之规律不合。其次,该经译者为谁?传入印度之渠道如何?费长房、慧矩等为什么都没有指出梵本中之“中国化”特色?印度人又如何能够接受宣传东方净土的药师信仰?“慧简本”名为《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何后面的名字却都翻译成了《药师琉璃光经》?印度人为何在全盘接受药师信仰的基础上,从一佛增加为七佛?最重要的是,在梵本回译为汉文时又为何把我们上文所列举的那些内容去掉?这些问题没有直接的证据,恐怕都很难解决。再次,季羡林先生在《佛教的倒流》一文中所举的几种佛教典籍倒流回印度的例子时代靠后,且多为佛教义理的回流,像《药师经》这样民间性、世俗性很强的佛典翻译为梵文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最后,该说没有注意到慧简本与后三译之间的相异之处,忽视了《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属于编译佛经或在翻译佛经的基础上改编的这两种情况,也没有认识到印度密教自身或受中土文化影响而具有产生《药师经》这类佛经的可能性。因此,此说虽然极有创见,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以资说明。
其实,笔者的考察力图使研究者能够更加全面地思考《药师经》的真伪问题,并没有完全否定《药师经》为中土人士所撰的可能性,也意识到这种推论一旦成立会极大地改变目前学界对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些固有认识。但正如纪赟先生在评论那体慧(Jan Nattier)“《心经》是疑伪经”的研究时所指出的那样:“我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说我认为梵语《心经》不是从汉语回译,其实我已然表述过了,《那文》恰好回答了我多年前读梵文《心经》时的疑问。但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对于学术研究谨慎绝对不是一件坏事。”*纪赟:《〈心经〉疑伪问题再研究》,福严佛学院编:《福严佛学研究》2012年第7期。那体慧认为心经是中土所造的伪经,后随着玄奘西行,流入印度,被翻译成梵文,见Nattier, J., 1992. The Heart Sutra: A Chinese Apocryphal Text?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Vo1.15 (2) 1992, pp.153-223.文章的主要观点在纪赟论文中有详细的引述。笔者在思考《药师经》真伪问题时与其感受相似。初读方先生和伍先生的文章时,也有眼前一亮、豁然开朗的感觉,但学术研究必须十分谨慎,佛教疑伪经研究涉及到中印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等深层次问题,下结论时更需慎重。《大乘起信论》《楞严经》《梵网经》《楞伽经》等的真伪问题争论了一个多世纪,至今还没有人人信服的结论,就是一些涉及中印两种思想融合的佛经真伪难定的最好说明。因此,目前还是把《药师经》看作真经为妥,最多只能说其是疑经,而绝不能武断地认为其为中土所造的伪经。
(责任编辑:曹玉华)
A New Understanding on the Authenticity ofBhaisajyaguruSutra
Wang Feipeng
BhaisajyaguruSutrais very popular in China. However, it is considered by some scholars a forgery because of the obscure origin of its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After comparing it with the Sankrit scriptures by Fei Changfang and Hui Ju, and especially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another three Chinese translations, Buddhist bibliographer are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BhaisajyaguruSutrais a translated work. But modern Buddhism researchers believeBhaisajyaguruSutramust have been created by Chinese monks as it contains some elements of Chinese culture; at last, they think the appearance of the later three translations is "backflow culture" phenomenon. This statement seems fresh and convincing, but it fails to explain some problems. In fact,BhaisajyaguruSutrahas a number of Buddhist sources,an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BhaisajyaguruSutrahas corresponding Sanskrit edition, from which some textual problems can be clarified. So, for the moment, we cannot decide thatBhaisajyaguruSutrais a forgery created by Chinese.
BhaisajyaguruSutra,guandingbachuguozuidedushengsijing,daguandingjing, a forgery sutr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王飞朋,四川大学图书馆馆员(成都 610064)
B952
A
1006-0766(2017)01-0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