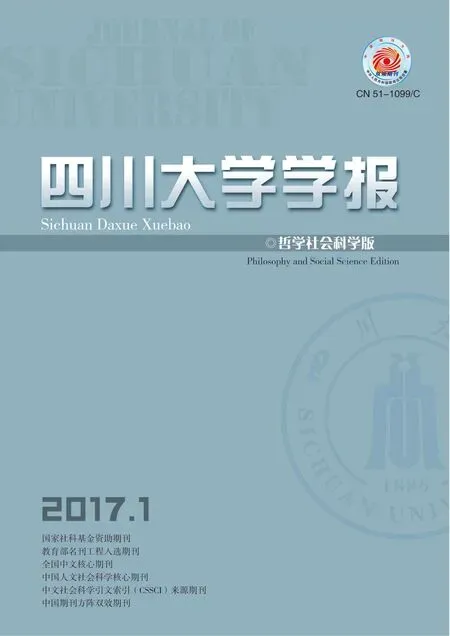“在传统中变”:清季安徽的学术沿承与“存古”履迹
郭书愚
§中国近代史研究§
“在传统中变”:清季安徽的学术沿承与“存古”履迹
郭书愚
晚清最后几年,中国传统学术整体上呈崩坏断裂之势,但经典的研习在安徽仍蔚为风气。官绅皆有意追寻传统的兴学理念和方式,更在文化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上深度契合。古学的保存和传承,文教事业的发展,乃至学术风尚的嬗替,固不乏开放而前瞻的一面,但大体仍是“传统中变”的演进脉络。重建清季安徽的“存古”履迹,可见当时皖省官绅对于接续和传承中国传统学问的独特思考和选择;而由文教事业的兴办视角,关注当时皖学的传承脉络和特色,可以观察到注重师承“家法”,而又开放包容的学术传统在近代特定时空中的承续,并为进一步研究相关精英士人,以及清季民初的学术与文化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保存国粹;晚清“新教育”;存古学堂;清季安徽;皖学沿承
近代中国在“西潮”冲击下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学在与西学的激烈竞争中惨败,导致日益严重的文化危机。至清季,士人中普遍弥漫着对国家衰弱的焦虑情绪,以及急于追赶西方“文明进步之大势”,“争存于世界”的紧迫感。尊西趋新的世风愈演愈烈,传统则在整体上逐渐从社会的主流思想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淡出。①关于“经典的淡出”,参见罗志田:《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11页。“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radition)乃至有意“背离传统而变”(change against tradition)成为主流的社会风尚。在这样一幅动态纷呈的复杂历史图景中,古学研习和保存方式的消逝、兴学理念和举措的改变乃至学术风尚的转移,皆是相当值得注意的面相。
另一方面,区域发展的不同步和多歧性是近代中国的又一显著特征。传统固然在整体上呈崩坏断裂之势,但在个别地方,经典的研习直到晚清最后几年仍然蔚为风气。即便是主要参照外国榜样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全面推行之际,仍有官绅在“新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意图追寻传统的兴学理念和方式。在这些地区,古学的保存和传承,文教事业的发展,乃至学术风尚的嬗替,当然有鲜明的时代印迹,但大体仍是“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的演进脉络。②这里的“传统中变”是鉴取柯睿格(E. A. Kracke)教授对宋代社会的观察和表述。参见E. A. Kracke, Jr., “Sung Society: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4, No.4, Aug.1955, pp.479-488.四川即是其中之一,③一些初步的考察和讨论参见郭书愚:《官绅合作与学脉传承:民初四川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嬗替进程(1912—1914)》,《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安徽可能是另一个相当有特色的例子。
清季安徽从省城到基层普遍有较浓郁的“存古之风”。官绅对于保存国粹有相当强烈而共同的关怀。他们以明显不同于当时主流风尚的方式兴办安徽存古学堂,视其为皖学④“皖学”一词虽已较频见于既存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中,但其所指仍较模糊而宽泛。本文尝试从地方文教事业的角度关注清季安徽的学脉传承和学术风尚。为便于考察,以下所用“皖学”一词意在标识学术的地域范围,除特别注明外,大体可说是“皖省学术”的简称,特此说明。传承的希望。该校作为皖中各学术流派以及部分非皖籍学人交流互动之地,正是清季皖学风尚的缩影。相关面相此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笔者迄今未见专门以此为题的研究。*存古学堂是清季“新教育”体系中保存国粹以迎应文化危机的主要办学形式,有全国性的办学规模,相关研究参见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6期。
进而言之,安徽存古学堂的办学员绅中不乏清季民初学林的重要人物,如沈曾植、冯煦、姚永概、马其昶、程朝仪、胡元吉、李详等。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他们在近代学术风气嬗变以及思想文化论争中的地位,但相关研究似乎仍有较宽广的拓展空间。葛兆光教授早在十年前即有专文谈学术史研究对沈曾植的长期“遗忘”。*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读书》1995年第9期。唯据葛先生新近的观察,这样的“遗忘”似乎仍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葛兆光:《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读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再说学术史的遗忘》,《书城》2008年5月号。程朝仪、胡元吉师徒相承的理学在晚清安徽一度相当盛行,但程氏为办存古学堂病故,胡氏辛亥鼎革后“学伯夷归隐”。*1917年初,姚永概应后学贺葆真(贺涛之子)请求,举“当今海内为宋儒之学者”三人,胡元吉是其中之一。姚氏并为贺葆真讲胡元吉民元后“学伯夷归隐”之事。详见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389页。这一学脉甚早即处于明显“失语”(voicelessness)的状态。
桐城派是清季民初安徽的学术重镇,马其昶、姚永概是其头面人物。学界较多关注他们在辛亥鼎革及民初时政治上的“保守”,以及文教学术上与章太炎弟子和新文化派的论战。但据桑兵教授新近的观察,五四前后桐城派被章太炎弟子和新文化派“猛烈抨击”,“大有被妖魔化之势”。实际章太炎本人后来对桐城派及“桐城义法”多有肯定。*桑兵:《从北洋军阀史到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而由“桐城谬种”一词的广为人知即可见桑先生所言“妖魔化之势”的确甚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时人及后之研究者对桐城派的整体认知。*王达敏教授也注意到,曾对桐城派有“持久而深刻”批判的周作人,在1930年代同样正面肯定桐城派是新文学的开端和导引。参见王达敏:《论桐城派的现代转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这些民元后多以“保守”著称甚至被“妖魔化”的“旧人物”,在清末实际的思想观念和作为,是过去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尤其是当时他们兴办或参与文教事业的相关活动,多数既存研究或忽略不言,或一笔带过。本文以相关档案和当时报刊、文集、日记、年谱等资料为基本依据,尝试重建安徽兴办存古学堂的部分史事,侧重由文教事业的兴办视角,关注清季皖学的部分特色和传承脉络,希望能有助于我们深入认知剧烈动荡的清季中国社会那些“不变”或是“在传统中变”的层面,并为进一步研究相关人物和清季民初的学术与文化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一、“延见古先不坠之绪”的办学努力
晚清士林普遍将兴学视作救亡图存、追赶西方的关键,教育由此而成为清末“新政”最重要的“政务”之一。就建制层面(institution)整体上概而言之,当时制订并颁行的一整套“新教育”规章明确以外国为榜样,传统教育从办学理念、思路到具体形式和举措,几乎尽皆成为被摒弃和批判的对象,说其是“在传统之外变”,应不为过。作为“新教育”体系中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存古学堂正是要用“学堂”这一新形式造就“研精中学”之才,“养成传习中学之师”。首倡者张之洞即相当强调该校与任何新式学堂无异,而“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62-1766页。安徽兴办存古学堂的努力固不乏开放而前瞻的面相,整体上则呈现出一幅明显更贴近传统的历史图景。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安徽提学使沈曾植(时兼署安徽布政使)命士绅姚永概、吴季白草拟存古学堂章程。*姚永概:《慎宜轩日记》,沈寂等标点,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下册,第1067页。此后不久,沈氏与新署安徽提学使吴同甲联名向安徽巡抚冯煦提议兴办存古学堂,得到冯氏支持。*《皖省创设存古学堂(安徽)》,《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总第496号。同年九月中旬,名儒程朝仪应邀由黟县故里至省城安庆商办存古学堂事宜。*沈曾植:《致胡元吉书》,载程希濂述,胡元吉、王立中合撰:《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薛贞芳主编:《清代徽人年谱合刊》下册,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848页。本文所用程朝仪年谱,皆为此版本,以下仅出以页码。但此后筹办工作因故中止。*《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48页)载: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慈禧太后去世,安徽存古学堂“暂行停办”。但当时中央政府似并无暂停新政办学的政令。皖省的其他学务事项似乎也未受慈禧太后去世的影响。相关情形只能阙疑待考。
至宣统二年四月(1910),时任安徽巡抚朱家宝决定“重行兴办”安徽存古学堂,程朝仪再次应邀至安庆商订该校章程并出任监督。虽然程氏在筹办该校期间病逝,*《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51页。但在朱家宝、沈曾植、吴同甲等热心官员以及缪荃孙等名士的共同努力下,*缪荃孙与沈曾植、李详交契。沈曾植托缪氏将聘书转交李详,并请缪氏“代致拳拳,劝友驾临为荷”。参见李详:《记与沈子培先生定交事》,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下册,第967页;沈曾植:《致缪荃孙》(宣统二年六月四日),载《艺风堂友朋书札》,顾廷龙校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上册,第176-177页。安徽存古学堂聘请到朱孔彰(仲我)、姚永概(叔节)、李详(审言)、胡元吉(静庵)分任经学、词章学、史学兼《文选》学、理学教员,*参见李稚甫:《李详传略》,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469-1470页。吴同甲以提学使身份兼任该校监督,*《皖省又将开办存古学堂(安徽)》,《申报》宣统三年三月五日。王咏霓(子裳)出任提调。*李详:《闻天台王子裳先生咏霓下世(有序)》,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348页。这一精萃的师资阵容有相当的吸引力,尹炎武即因仰慕朱孔彰、李详二人而赴皖求学,得偿所愿。*尹炎武:《朱李二先生传》,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四)》卷53,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5》,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371-378页。尹炎武(1889—1971),又名文,字石公,号蒜山,江苏丹徒人,历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河南大学教授,先后充任江苏通志馆、国史馆纂修。参见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7页。
安徽兴办存古学堂,一个明显贴近传统的兴学思路是对整个皖省士风与学风的注重。该校招生便打破清季“新教育”的常规(即由州县官、教育会或“学界”保送至省城参加复试),而延用“古观风试”。具体作法是由沈曾植、吴同甲会衔将经、史、文学、理学试题札饬各属地方官出示考试。凡“家世清白、年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皖籍士子,皆可应试,“三艺完卷,经、史必作一题方为合格”,限期将卷纸寄到省城。*高正芳:《安徽存古学堂——清末安徽新教育中之一节》,《学风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4月15日。此举显然便于直接了解各属士林风气,在沈曾植而言,或不无履行“观风”这一清代学政重要职责之意。而无需具结保送还可最大限度地“鼓舞多方、网罗殆遍”,但据李详所述,也出现“倩替者多,不辨真伪”的情形。*李详:《汪本楹》,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上册,第702页。
安徽办学员绅对于皖省的古学风气颇为乐观。当时即便是“新教育”体系中也不乏对中国传统学问有浓厚兴趣的读书人,故安徽存古学堂除正额取录外,还招收“肄业他种学堂、不妨碍应修学科而愿兼习经史文理者,为附课生”。*高正芳:《安徽存古学堂——清末安徽新教育中之一节》,《学风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4月15日。按,张之洞固然是因“各学堂经史汉文所讲太略”而办湖北存古学堂,却并未将其他新式学堂在校生直接纳入该校的教学计划中。类似安徽这样力图直接提升“新教育”体系的中学水平的办学思路,也见于广东和浙江两省兴办存古学堂的努力中,但具体作法明显不同。广东学务公所“普通科副长”陈佩实便着眼于新式学堂的教师而非学生,提出应准许新式学堂教员报考存古学堂,取录后单独成班。*陈佩实:《考查湖北存古学堂禀折》,《广东教育官报》宣统三年第5期,总第15号。而浙江官书局总纂姚丙然拟令该省所有“中学毕业而于经、史、国文分数不足者,须入存古学堂补习后,方予奖励”。*《禀办存古学堂》,《大公报》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总第2362号。这样的存古学堂已变为普通中学堂经、史、国文课的辅助教育机构。安徽办学员绅则仍然秉承张之洞造就“研精中学”之才,“养成传习中学之师”的“存古”初衷,只是基于对皖中古学风气的预判,为学有余力的在校生提供自愿兼习中学的机会,与姚丙然的强制性“救弊”举措适成鲜明对照。
实际上,“附课生”的设置渊源有自。清代安徽声名最著的敬敷书院自乾隆十七年(1752)即在“内课、外课”生之外设有既无膏火、也无定额的“附课生”,*朱之英修、舒景蘅纂:《怀宁县志》卷8,第13页B,1918年铅印本;《安徽通志馆教育考稿》卷3,第5页A,1934年铅印本。后更形成皖抚亲自“按试”书院,甄别优劣,“升降内、外、附课之士”的传统。安徽存古学堂的“附课生”同样没有正式的编制和定额限制,但招录范围则限于新式学堂的在校生群体。显然,安徽办学员绅变通了传统书院的“附课生”制度,赋予存古学堂直接而速效的为“新教育”服务的功能。
能够“附课”的,当然是与存古学堂同在省城安庆的新式学堂在校生,但安徽办学员绅对于存古学堂的期许并不止于此。该校还招录“省城外各县通信学习者为校外生”,力图将影响扩及基层州县。按,清季中央政府不准基层州县兴设存古学堂以免“有碍新机”。*详见郭书愚:《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在此情形下,确有省份试图将“存古风气”推展至基层州县。光绪三十四年刘师培呈请两江总督端方奏设“两江存古学堂”,即提出“将教师所编讲义月刊成册,颁发所属各州县,使官立、民立各校奉为参考之资”。*刘师培:《上端方书》,《刘师培全集》,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3册,第534-535页。宣统二年底四川存古学堂监督谢无量移请全川各府厅州县查收一份“募捐启”,意在“导扬风气”,希望各地“有道君子”能够为学校捐助钱款、图书、金石器物等。*谢无量:《四川存古学堂募捐启》(宣统元年七月),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四川存古学堂档案,第2卷,第36页。“观风”之后“导扬风气”,正是清代学政于基层州县通常的兴学理路。唯就具体举措而言,安徽存古学堂力图通过“通信学习”的渠道将省城的教学活动延展到基层州县,这一多少有些类似“函授”的方式“新”意十足,正是时代风貌的体现。
实际上,安徽存古学堂相当有吸引力,从一个侧面印证当时皖省确有相当浓郁的“存古”之风。该校“附课生”与“校外生”皆无定额限制,但“正课生”只有50个名额,是目前所知清季各存古学堂中最少者。“观风试”总计收到650多份试卷,*吴同甲:《致程朝仪书》(宣统二年八月十九日),载《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51页。录取比例不到1/13,淘汰率高达92%以上,竞争显然相当激烈。
尤为不易的是,校方“以通经学古,为道德名誉之事,不导人于利禄之途”,规定学生毕业后不奏请奖励。*高正芳:《安徽存古学堂——清末安徽新教育中之一节》,《学风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4月15日。这也是该校与其他存古学堂的另一重要不同之处。盖“奖励”意味着比照旧功名的资格,正是当时学子们普遍看重的。安徽存古学堂在没有“毕业奖励”的情形下,仍能吸引到众多考生,其入学考试的淘汰率甚至是目前所知清季各存古学堂中最高者。这样的情形在清季“新教育”中即便不是唯一特例,也相当罕见。安徽存古学堂“不导人于利禄之途”的作法,与嘉道以降兴起的“不课举业、专勉实学”的书院,在办学精神上或不无相通之处:让“古学”的研习和传承摆脱官方的功利导向,回归其学术的本位。*有关嘉庆、道光以降“不课举业、专勉实学”的书院之兴起,参见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胡适等编:《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81-321页。
但与诂经精舍、学海堂等书院以考订训诂为宗不同,安徽存古学堂特别推重理学。沈曾植以元儒程端礼所撰《读书分年日程》为办学蓝本,试图将理学灌注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另一方面,沈曾植又主张鉴取“外国大学高等教法”,更有明确的模仿目标。他心中理想的“存古”之路是以“中法”为根基,以“世界眼光”沟通中西间可通之处。参见郭书愚:《“书院日程”与“世界眼光”:沈曾植的“存古”努力及文化观》,《学术月刊》2015年第11期。这样一整套旨在以中国传统“教法”保存“古学”的思路,与清季“新教育”的规章和导向明显不同,其背后隐伏的“中西学各有体用”的文化观,尤与当时主流的“中体西用”论大异其趣,在实际运作中面临的阻力和压力已到“为时流大哄”的程度。*沈曾植在宣统二年四月十四日致缪荃孙的信(《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174页)中说,安徽存古学堂“微与部章略存通变,与鄂章亦不尽同,大旨科学宜用西国相沿教法,古学宜用我国相沿教法。书院日程,源流有自。此意发表,将为时流大哄”。
该校实际的筹建工作进展也不顺利,更一度引发争议而险些半途而废。宣统二年七月,沈曾植卸任离皖。次月,安徽即出现对存古学堂的“异议”,矛头直接针对沈氏在任时筹定的办学款项。在朱家宝竭力维护下,该款终得以保全。沈曾植得知此事后,感叹:“欧日政策,不随人改,我则政以人移,长此纷纷,其何能淑?”*沈曾植:《致缪荃孙》(宣统二年八月廿七日),《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178页。“政随人改”在清季保存国粹办学努力中并不鲜见,吴庆坻办湖南存古学堂即是另一典型例子,详另文。筹建工作并未照沈氏原计划在当年暑假后就绪,经朱家宝催促,大约在同年十一月完成。*沈曾植、吴同甲:《致程朝仪书》,载《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49页;朱孔彰:《致李详(第一函)》,苏晨主编:《学土》卷3,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7页。翌年三月一日,该校始正式行开学礼。*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下册,第1182页。
安徽存古学堂从办学理想到实际运作,能够冲破重重阻力付诸实践,该省浓郁的“存古之风”,尤其是热心士绅的鼎力支持和配合,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安徽官绅为办存古学堂有较充分的讨论和商议。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底,沈曾植曾招姚永概同程朝仪、胡元吉、马其昶、姚永朴“谈自治及存古事,甚畅”。*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册,第1087页。至宣统二年上半年,沈氏的办学方案得到姚永概、马其昶、程朝仪的认同,具体办学章程则由程朝仪、姚永概、朱孔彰三人商订,沈曾植最终定案。*本段及下段所述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22-850页。若说官绅的共识与合作是该校虽明显不同于清季主流办学风尚而仍得以开办的基石,应不为过。
皖省官绅看重安徽存古学堂并为之付出相当心血,体现出较强烈而共同的“存古”关怀。程朝仪数十年“不慕时荣、不事酬应”,专意于学问和课授之事,晚年以古稀高龄两度应邀筹办并主持存古学堂,未必有多少出占馆地之欲,恐怕更多是名利以外的关怀所致。姚永概也对安徽存古学堂情有独钟,他在阅完存古考生观风试卷后,即将70元薪金交还吴同甲。翌年三月(1911)他以身体不佳请辞安徽师范学堂监督一职,但仍愿意出任存古学堂讲席。姚氏看重的,显然不是薪金所得,而是以“师”的身份践行自己的“存古”关怀。*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宣统二年八月十七日、宣统三年三月十三日,下册,第1162、1184页。
类似的“存古”关怀并非程、姚二人独有。姚永概在安徽存古学堂开学典礼上的演说,即“颇为众所称许”。*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下册,第1182页。吴同甲在宣统二年夏致程朝仪的信中也明确指出,“贵省士林,笃信旧学”。而“古先不坠之绪”,正要通过安徽存古学堂“延见”。*吴同甲:《致程朝仪函》(宣统二年八月十九日),载《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51页。最后一语大体可说是当时皖省官绅对安徽存古学堂的普遍认知:作为当时安徽唯一的国学高等专门研究和教学机构,该校承载着皖学传承的希望。
二、“有余于古文之外”:清季皖学的沿承和风尚
在兴办者眼中,安徽存古学堂实为传统学术在皖中薪火相传的事业。冯煦即明确指出,安徽“为晚周哲学发生之地,南宋大贤踵毓之邦。入国朝来,魁儒大师,项背相望,盖道德之渊薮,文艺之林囿也”。办存古学堂,是“横舍宏图,缵绵前绪”。*《皖省创设存古学堂(安徽)》,《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总第496号。沈曾植、吴同甲在致程朝仪的信中也说,安徽“为国朝斯文枢纽”,程氏出任存古学堂监督,是“继乡前哲婺源(朱熹)之遗徽,续令先德伊川(程颐)之道绪”。*沈曾植、吴同甲:《致程朝仪书》(宣统二年四月),载《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49-850页。
该校的招生考试题目相当注重皖学的学术渊源和特点。其中一题为“昔朱颍川问士于郑召公,韩吴郡问士于刘圣博,王景兴问士于虞仲翔,濮阳兴问士于清河,皆言本郡人物。皖邦旧多英俊,试效其体作答一篇”。另一题是:“徽郡经学,桐城古文,名家甚盛,试叙而论之”。*高正芳:《安徽存古学堂——清末安徽新教育中之一节》,《学风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4月15日。地域学术文化的特色也体现在科目配置上。张之洞的存古方案将“小学”课附于经学科内,“诸子学”则是经、史、词章各科学生的“通习课”。*张之洞:《湖北存古学堂课表章程》,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4386-4396页。而安徽存古学堂则将上述两门课都归入文学科,似乎更看重并强调二者对于研习文学和写作的辅助作用,从一个侧面提示着文学的特殊地位。
由安徽存古学堂师资的“家法”,可以初略梳理出其源流有自的学脉传承轨迹。经学教员朱孔彰传其父朱骏声之学,年少时师从程朝钰(字伯坚,程朝仪长兄)。程朝钰、程朝仪同为朱骏声弟子,朱骏声最重要的学术著述《说文通训》即由程朝仪校录而行世。*参见朱孔彰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为程朝仪著述所写叙言,载《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46-847页。朱骏声则承乾嘉学术大家钱大昕(竹汀)之学。*据朱骏声《石隐山人自订年谱》(载《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43册,第596页)所记,嘉庆七年(1802年)五月,朱氏“入紫阳书院附课肄业,时宫詹钱竹汀夫子主讲席,……初谒时有传授衣钵之语,极蒙奖惜,以国士目之,并许受业”。程朝仪力倡“以诂训为明经之本,诂训通而义理自无空谈”,正与钱大昕“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的主张一脉相承。*《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35页;钱大昕:《〈左氏传古注辑存〉序》,《潜研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87页。
程朝仪而立之年讲求性理之学,固然是其个人际遇和性情使然,*程朝仪同治二年“偶于先代藏书中得《程子遗书》《性理综要》二种,读而爱之,始讲求性理之学”。参见《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19-820页。可能也多少与其师承特点有关。朱维铮教授已注意到,钱大昕倡导“实事求是、不主一家论”,实非“所谓汉宋门户之见的偏执者”。*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中国经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有意思的是,安徽存古学堂理学教员胡元吉(程朝仪弟子)早年任敬敷书院学长,与邓绳侯、王蔚岑、马通伯、姚永朴、姚永概、方守彝、赵伯远等“博学能文之士”交游,其治学也有变化,“虽笃志程朱,颇亦博涉古今学说以自广”。*《黟县名宿胡敬庵先生逝世》,《学风》1936年第6卷第6期。如果说“笃志程朱”是在守护“家法”,则“博涉古今学说”显然是无“门户之见”的互动交流所致。
文学教员姚永概以及参与筹谋该校的马其昶皆是近代桐城派大家。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的汉学与反汉学之争中,桐城派与乾嘉汉学原为对立双方,且多有过节(尤其钱大昕对方苞批评有加,而后钱氏又成为方东树着力攻击的对象),*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中国经学史十讲》,第157页。但在清季安徽兴办存古学堂的文教事业中则有较密切的共事与合作。他们皆看重各自的“家法”,且论学不无分歧,但显然没有势如水火的“门户之见”和争斗。*朱孔彰在光绪三十二年为程朝仪著述作叙时说,程氏“所著诗古文,皆有家法”(《徵君程抑斋先生年谱》,第846-847页),说明“家法”正为朱、程等人所看重。实际上,姚永概与程朝仪虽交往不多,但关系似较睦,*光绪三十四年九月程朝仪曾造访姚永概,姚氏四天后回访。当月底程氏归里,姚永概为其送行。翌年程朝仪子希濂又至姚永概家赠茶。参见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九日、九月二十三日,宣统元年九月十四日,下册,第1086、1127页。尤与胡元吉过从甚密。*姚永概为胡元吉母亲撰有墓志铭,还为胡氏先祖胡国泰撰有墓表,参见姚永概:《胡府君墓表》《节孝胡母孙孺人墓志铭》,《慎宜轩文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91册,第363-364、380页。
这样“和而不同”的图景大体可说是当时皖省开放而多元学风的缩影。王遽常在《沈寐叟年谱》中说,沈曾植出任安徽提学使,“先后招致耆儒桀士程抑斋、方伦叔博士(守彝)、常季、马通伯主事(其昶)、邓绳侯、胡季庵、徐铁华、姚仲实(永朴)、姚叔节解元(永概),时时相从考论文学。人谓自曾文正公治军驻皖以后,数十年宾客游从之盛,此其最矣”。*王蘧常编:《沈寐叟年谱》,《民国丛书》第76辑,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50-51页。最后一语是注引姚永概在《慎宜轩诗·自序》中的观感。而前引胡元吉与诸多“博学能文之士”交游后的治学变化,正是清季皖学风尚影响个体学人的典型例子,也揭示出当时皖中学人“时时相从考论”的,应不限于文学。
除聚集皖中学人外,沈曾植还敦请王闿运、缪荃孙、李详等名儒宿学至皖。而李详更以非皖籍身份,且对桐城末流之弊颇有微辞,仍被礼聘为安徽存古学堂史学兼《文选》学教员。清季学林对桐城派固然有不少质疑和批评,但多有其特定所指,未必皆取与桐城精英对立的立场,实与五四前后钱玄同等章门弟子和新文化派学人对桐城派几近“妖魔化”的攻击明显不同。如李详当时引起较多关注且对后之研究者影响深远的《论桐城派》一文,即主要针对一味拘守文章形式而与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缺一不可”之义背道而驰的桐城末流之弊。李氏在文尾特意申明:
余与今之能治古文者,皆在相知之列,其学又皆有余于古文之外,余之所言盖专为救弊而发。*李详:《论桐城派》,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第887-888页。
李详自视甚高,平生论学不轻许人。所谓“其学又皆有余于古文之外”,大体可说是他对清季桐城古文家学术取向的整体观察,相当值得注意。实际上,李详和姚永概、马其昶等桐城派精英不仅在清季安徽存古学堂中共事与合作,私下更有较密切的交游和唱和。*宣统二年八月李详到皖之初,姚永概即邀其与朱孔彰饮于长啸阁,方守彝陪座,李、方、朱三人皆有诗。翌月九日,李详又应邀与方守彝、朱孔彰游大观亭,“作重九之会”,后又至“清水塘观”等登高胜地“小饮”,姚永概后到,众人皆有诗。参见朱孔彰:《致李详》,苏晨主编:《学土》卷3,第97页;李详:《学制斋诗钞》卷2,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236页;方守彝:《网旧闻斋调刁集》卷8,《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6册,第292-293页。唯就个人性情和文风而言,李详对桐城文章一直颇不以为然,这一学术倾向并未因其与桐城派精英交契而改变。*李详在《与张江裁函(第二通)》(载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070页)中自述,“为文,蚤从永嘉甬派入手。桐城派不喜用事,不喜色泽语,不喜用偶字”,自己“皆犯之。且好考据之学,宁有冗长不检处,而不可不通”。但这或许正从一个侧面提示着:安徽存古学堂的办学取向和当时皖省学风,确有超越地域区隔且包容歧见的一面。
开放而包容的学术风尚也体现在学堂的实际办学运作中。招生工作即放宽了原拟“正课生”限招皖籍士子的规定,籍隶江苏的尹炎武即以客籍身份报考,终被取录。在教学方面,教师的执教风格和授受理路迥异其趣,学生则反应不一。朱孔彰相对简明而易见成效的授学思路似乎颇受学生欢迎。其“教士之旨,大致谓雕版既兴,载籍愈夥,穷赅毕览,日不暇给。先秦两汉之书为学术根柢,苟志于学,当知所先务,于《尔雅》《说文》溯其原,于释文义疏尽其义。百家诸子,观其流别;《通鉴》《通考》,得所据依,旁及《骚》《选》古文”,学生“随才性之所近”研习,“数年之间,可以自立。从之者如被甘雨和风,有陶然自得之趣”。*尹炎武:《朱李二先生传》,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四)》卷53,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5》,第371-378页。李详则“以‘四刘’之学教士。‘四刘’者,《汉志》《世说》《文心雕龙》《史通》也。而于《三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厌饫优柔;子部杂家之学,唐宋笔记之流,如瓶泻水”。虽然“生徒敛衽”,但“能传其学者盖寡,惮其繁难,无速效也”。*尹炎武:《李审言先生传》,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册,第1448页。尽管如此,李详与汪本楹、尹炎武等安徽存古学堂学生有较深厚的师生情谊。尤其汪本楹,颇得李详器重,民元后两人“时通书问”,“议论”也相合,李详将其储在“心胸间,不能忘去”。*李详:《药裹慵谈》,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上册,第702页。
结 语
概而言之,安徽存古学堂开放而不失其故的办学大方向,与当时多数存古学堂并无不同,但其办学思路和具体运作在“不失其故”方面,明显走得更远。在清季盛行的“中体西用”言说中,“新教育”的建制和教学管理方式普遍被归入“西用”范畴。如果说张之洞倡言以新式学堂办法保存国粹,是在以“西学之用”较根本地改变“中学之体”的保存、研习和传承方式;则安徽存古学堂坚持以中国传统的“教法”和文教理念为根基,大体可说是“在传统中变”的办学履迹。前文所述无论是“古观风试”的招考办法、“附课生”与“校外生”的设置,还是“毕业不奏请奖励”的规定,皆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当时皖省官绅对于接续和传承中国传统学问的独特思考和选择。
就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汉学与宋学由对立到息争的演进是清代学术发展的一大脉络。作为道咸以降“新学”的重要趋向之一,“调和汉宋”对晚清安徽学风的影响相当值得注意。光绪十三年吴汝纶(挚甫)曾训谕弟子姚永概:“为学宜撤藩篱。汉、宋之篱撤而义理与考证兼收矣;文章、道学之篱撤而义理与词章兼收矣”。所谓“撤汉宋之篱”,正有“调和”二者之意。沈寂教授已注意到吴氏此言对姚永概的重要影响。*吴汝纶所言见光绪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慎宜轩日记》(上册,第509页),沈寂教授认为姚永概在日记中记下吴氏之言,“指明了他后半生应走的路”。参见沈寂:“前言”,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上册,第7-8页。前文所述清季姚永概与程朝仪、朱孔彰等人的交游和共同的办学努力,原本精研小学的程朝仪中年后笃志理学的治学道路,胡元吉与诸多“博学能文之士”交游后的治学变化,皆提示着“汉、宋之篱”在清季安徽即便不是全无踪影,也相当式微。
“撤汉宋之篱”大体可说是摒除门户之见的另一种表述,却并不意味着放弃或改变本学派的核心学术理念和文化观。姚永概、马其昶等人对理学和“桐城文法”的坚守,程朝仪对“家法”的倾重,朱孔彰对家学的传承,揭示出清季安徽的“调和汉宋”趋向,基本以“撤汉宋之篱”或者说摒除门户之见的方式展开,与不通“家法”的“汉宋调和”论者异趣。*当时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即对提倡“调和汉宋”而不通“家法”者的浅薄颇不以为然,罗志田教授已注意及此。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76页。不仅如此,清季皖中学风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学人对各自“家法”的护持,适与“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的流弊形成鲜明对照。*晚些时候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51页)中明确反对“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固然是就“从事比较语言之学”而言,或不涉“汉宋”。唯陈先生言辞相当考究,此言似有所指,多少提示着背弃“宗统”(“家法”)之弊不仅存在,而且恐怕已严重到“认贼作父”的程度。
进而言之,“撤汉宋之篱”固然能体现清季安徽学风开放而少门户之见的重要面相,但却并非全部。本文所述李详与桐城派精英“和而不同”的学术交游、安徽存古学堂打破省域界限的招生运作和多元的教学氛围,便基本无涉“汉宋”,同样是当时皖学风尚的写照。尤其非皖籍学者李详对“桐城文法”颇不以为然,且曾公开批评桐城末流之弊,仍被礼聘为安徽存古学堂史学兼《文选》学教员,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清季安徽学界超越地域区隔、包容歧见的气度和胸次。
就学术因应时变的层面言,近代中国因中西“学战”的惨败而出现日益严重的文化危机。在此语境中,清季朝野皆有超越既存学术派别从而整合中国传统学术的努力。但中学内部并未由此而完全息争,在一些地方,“内斗”不仅在继续,其激烈程度甚至不逊于中西“学战”。崇尚理学的清流名臣赵启霖宣统元年出任四川提学使伊始,即以“讲经学离奇怪诞”为由,将深研今文经学的蜀中名儒廖平从高等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经学教员任上辞退,引发川中学绅“群起反对”。赵氏借学部之力才压制住川省学界的反对声浪,随即立“宋四先生祠”,并于祠内设存古学堂,意图以理学“转移”蜀中学风。*赵启霖:《复学部丞参诸公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案卷号469;赵启霖:《瀞园自述》,《赵瀞园集》,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337-338页。
而安徽的特点则是沈曾植、冯煦等官方大员从学术倾向到办学理念,乃至办学背后的关怀与寄托,皆与皖省学绅有相当的共识。说其是一幅官绅在区域文化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上深度契合、在文教事业上通力合作的历史图景,似不为过。姚永概等桐城精英“撤中外之藩”以兼收并蓄的文化观,沈曾植办安徽存古学堂时沟通中西的“世界眼光”,皆提示着清季安徽学风的开放而多元不仅仅体现在中学各流别发展的内在理路上,还有颇具前瞻性地开放对待西学、积极因应时变的一面。
如果以“长时段”的眼光概而观之,在近代中国“经典淡出”的局面形成以前,注重师承“家法”而又不失开放包容,正是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注重“家法”的传统至少可以远溯至秦汉时“博士”的设立。而据沈曾植的观察,“清代汉学”的特点正是“讲家法至严。旧学家亦绝无门户之见”。参见沈曾植:《致缪荃孙》(宣统三年五月二日),《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180页。这里所谓“绝无门户之见”的“旧学家”或有所指。但若说清代汉学“讲家法”和“无门户之见”是渊源有自,应不为过。清季安徽“在传统中变”的“存古”履迹和学术风尚部分留存了这一学术传统,说其是传统中国的“国性”(national identity)在近代特定时空中带有鲜明时代风貌的承续,似乎也不为过。
安徽存古学堂开办一学期后,辛亥革命爆发,民初教育部通令废止存古学堂。*参见教育部:《通令各省停办存古学堂文》,引在1913年6月江苏、广东教育司回复教育部的信函中,台北“国史馆”藏清学部档案,目录号195,案卷号134、142。另据姚永概1913年6月3日在日记(《慎宜轩日记》,下册,第1238页)中说,安庆文昌阁改为“图书馆,旁存古学堂改国学社”,则安徽存古学堂在民初似乎一度有某种形式的变体存在。由于历时较短,安徽存古学堂似乎没有多少令人瞩目的成效。但相关员绅的“存古”关怀却并未因该校停办而终止,类似的办学理念和取向似乎也在辛亥鼎革后延续。严复1912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力主将中西学“分二炉而各冶之”,故拟合并经、文两科大学,作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605页。这样的办学理念及其背后隐伏的“中西学各有体用”的文化观,与安徽存古学堂有明显的共性。实际上,严氏为践行其办学方针而为北大聘请的“教务提调”,正是姚永概。以“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眼光,将相关精英士人的文化观念和活动回置到当时的历史现场,或许可以让我们的历史记忆摆脱此前可能存在的“妖魔化”倾向,而更贴近于历史实况,进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知清季民初的时代特性以及“中国文明的传统特征”。*在“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盛行之时,已有学者提醒我们“不要一窝蜂地寻找‘草根’的课题”,中国文化自有“崇尚精英”的传统,故仍应注重对“文化精英”的研究。参见王晴佳:《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学历史?》,《新史学讲演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
(责任编辑:史云鹏)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the Academic Inheritance and the Trace of “Preserving the Ancient Learning” in Anhui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Guo Shuyu
Despite that the breakdown of the Chinese Ancient Learning was generally getting wor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was still popular in Anhui for scholars to study the classics. The officials and the gentries preferred to pursue the traditional ideas and manners of running schools, and, furthermore,they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inner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academic. This open and forward-looking characteristic can be found in preserving and inheriting the ancient lea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and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styles. But all of these were still “changing within tradition” on a whole. By reconstructing the trace of “preserving the ancient learning” in Anhui of Late Qing, we can find out how people had thought and acted so as to inherit ancient learning. Moreover, by studying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of that time, we can als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ademic inheritance in Anhui: being open and inclusive on the one hand and emphasizing the succession of teachings (“jia fa”) on the other. A thorough study of this subject will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related elites and the academics and culture in Anhui of that period.
preserving the National Essence, New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the School for Ancient Learning, Anhui in Late Qing, the academic inheritance in Anhui
郭书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成都 61006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季民初的保存国粹办学努力——以存古学堂为中心的考察”(12FZS0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清代的学术与教育及其近代转型”(SKGT201204)
K252
A
1006-0766(2017)01-008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