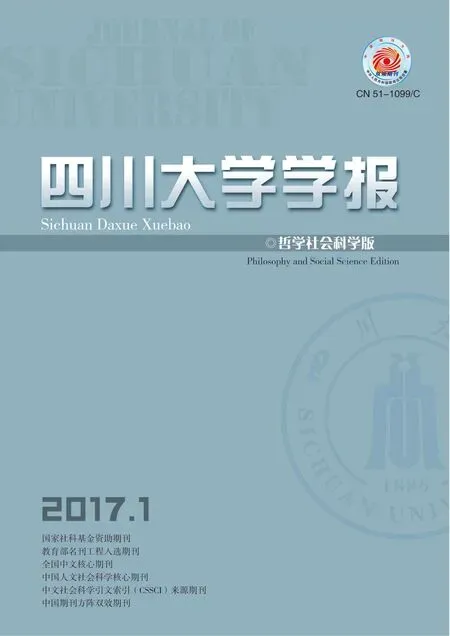任卓宣与左翼文学思潮
姜 飞
§现当代文学研究§
任卓宣与左翼文学思潮
姜 飞
任卓宣是台湾1950年代反共文化运动和文艺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人,然而从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中,任卓宣的文学思想却属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或许由于任卓宣呼唤和就范的文艺政策的强大存在,在其1966年出版的文集《文学和语文》中,他篡改了当年的左翼痕迹。任卓宣的文学思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标本,显示出意识形态的选择性和思想结构的稳定性。
任卓宣;左翼文学思潮;文艺政策;历史改写
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史和意识形态斗争史上,任卓宣是一个特别的人物,也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人物。任卓宣曾是国民党所倚重的来自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也是共产党所认定并宣布的投向国民党的叛徒和战犯;①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830页。同时,他还是一个在文学思想方面有特别表现的理论家和批评家。
海峡两岸的学者在文学论域提及任卓宣,大抵是将其视为1950年代反共文化运动和文艺政策的倡导者或执行人:②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266页;古远清:《“为政治而文学”的叶青》,《武汉文史资料》2001年第8期;等等。有事可征,他做过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部长以及台北市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倡立中国文艺协会,志在反共;③任卓宣:《我底文学撰述之回忆》,《文讯月刊》(台北)1984年第7、8期合刊。有文可查,他写过《今后的文艺路线》《三民主义与文学》《战斗文学底问题》,旨在反共。④任卓宣:《今后的文艺路线》,《中央日报》(海口)1950年3月24日;叶青:《三民主义与文学》《战斗文学底问题》,《文艺创作》(台北)1953年第28期、1955年第47期。任卓宣的“反共斗士”⑤潘寿康:《共产主义的克星——叶青》,《新闻评论》(台北)1951年第25期;《赞反共斗士任卓宣》,《民族晚报》(台北)1955年3月27日;王黎明:《反共思想斗士任卓宣先生》,《国魂》(台北)1957年第147期;等等。形象确立之后,他的复杂性即被遮蔽。然而他的确是复杂的,不论是其哲学观念、思想经历还是其政治和整个人生履历。尤其是任卓宣的文学思想历程,其间既有人们习焉不察的遮蔽,也有任氏有意为之的遮蔽,所遮蔽的事实便是:从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中,任卓宣声援了中国共产党人主导的左翼文学运动,甚至他当时的文学思想本身就归属于左翼文学思潮。
任卓宣虽在历史上与左翼文学思潮有深刻的关系,但在台湾所谓的“戒严”时期,在任卓宣所倡导和推行的国民党文艺政策⑥任卓宣:《文艺政策论》,《文坛季刊》(台北)1959年第4号。之下,他又几乎是不露痕迹地篡改了那段历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任卓宣的文学思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标本,显示出意识形态的选择性和思想结构的稳定性。
一
任卓宣的文学思想曾经归属于左翼,这与其早年参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活动和理论宣传有关,也与其在自首脱党之后企图再次参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有关。
任卓宣原名启彰,主要笔名是叶青。1896年4月18日*任卓宣的生日有两种说法,均在4月:其一为“民前十六年农历的三月六日”,即阳历的1896年4月18日。(参见《任卓宣少年习作手稿》,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年,第1页;江月:《任卓宣先生年谱》,见黎明编:《当代文化诸大家传谱录 》,台北:交通报导杂志社,1982年,第69页)其二为4月25日,据李敖日记所引《中央日报》1986年4月24日的消息:“明天是大思想家任卓宣教授九秩荣寿,蒋总统经国先生特别题赠‘教绩延庥’五尺长寿轴向他祝寿。”(参见《李敖大全集·李敖秘藏日记》,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第130-131页)此处取4月18日说。出生于四川南充三会乡,1990年1月28日病逝于台北中和场。早岁家贫,依靠族人的帮助才得以在任氏祠堂的私塾接受旧学教育,后来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接受现代教育。1918年任卓宣北上北京,考入法文专修馆,学业完成后,赴法国勤工俭学,起初是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学徒,随后成为正式的锉工。
贫农出身的任卓宣,在法国期间同情贫苦工人,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曾加入法共,且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1922年6月成立“少共”(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少共”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欧洲支部。按照任卓宣的回忆,当时他在国共“两个团体内俱编杂志,主持宣传工作”。*任卓宣:《我为什么反共》,见《任卓宣评传续集》,台北:帕米尔书店,1975年,第1-2页。实际上,任卓宣在此期间还曾担任“少共”训练部主任,*赵云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沿革》,《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编辑过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方面的教材和图书,在与党内同志的理论探讨中,展示了突出的法语水平和理论能力。*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 》(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188-192页。在曾琦等旅法无政府主义者攻击共产主义的时候,任卓宣则撰文予以义正词严的反击,*T.S.:《甚么是无政府党人底道德》,《少年》(巴黎)1924年第10、11号。当时周恩来也与任卓宣并肩战斗,共同维护唯物史观的真理和共产主义者的荣誉。*伍豪:《实话的反感》,《赤光》(巴黎)1924年第7期。此际的任卓宣对四川南充老家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也有过贡献,据《南充县志》记载:“中共旅欧支部主办的《少年》月刊,由留法学生刘伯坚、任卓宣寄回南充,在进步师生中传阅,在其影响下,县中、女中等学校先后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四川省南充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南充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页。1925年“五卅”事件之后,任卓宣在巴黎领导旅法华人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冲进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胁迫公使陈箓对法国政府发出通牒,要求法国“撤退在华军队,放弃其既得权利,让中国人民自决,并予集会自由于旅法华人”。*任卓宣:《巴黎狱中写来的一封信》,《向导周报》(广州)1925年第130、131、132期。事后任卓宣被巴黎警方逮捕,囚禁三月,驱逐出境。
之后,任卓宣到了苏联莫斯科,加入苏共,且在1925年11月成为中共“旅莫支部”的核心领导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第一卷第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698页。据张闻天、乌兰夫、孙冶方等人的回忆,“旅莫支部”的任卓宣主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党团员学生的思想和组织生活,其思想甚左,独断专行,粗暴强硬,令人畏惧,“在党的组织生活中纠缠生活上的小事,要求党员互相打‘小报告’,搞得不少人心理紧张,谨小慎微”。*马文奇等编著:《张闻天》,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45-46页;《乌兰夫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4页;孙冶方:《关于中共旅莫支部》,《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80-183页;廖麟:《风雨沧桑六十秋》,《淮南文史资料》(第8辑),淮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7年,第68页。然而在任卓宣之前,罗亦农等“旅莫支部”领导人便已在严厉地管理和训练旅莫党团员学生:“我们用集体化的口号反对个人主义,用纪律化的口号反对天然的无政府主义,用系统化的口号反对浪漫。集体化、纪律化和系统化的人,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须自觉的合于集体化、纪律化和系统化三个口号,意见要能一致。小组组长与执行委员会应发生密切的关系。小组组长对于该组组员,须绝对执行纪律之责。执行委员不一定参加小组会议,但是执行委员会每礼拜须召集小组组长会议一次,小组组长报告各组一礼拜经过的情形。执行委员会应于必要时,得召集比较明瞭比较积极作工的同志开会。每个团员至少须与两个团员以上的团员发生极密切的关系”。*罗亦农:《在中共旅莫支部第二次大会上的讲话》,《罗亦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任卓宣应该是沿袭此前的惯例,或许是更严格地执行。任卓宣在此期间针对革命的现实需要而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或许与其在文学思想上一贯反对个人主义而推崇集体价值有深刻的关联。其实,集体主义是革命的必然要求:“在军事行动和革命行动中,‘最先消失的是个人主义’,这千真万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强大的集体一致性。”*汉娜·阿伦特:《关于暴力的思考》,见《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高红、乐晓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任卓宣受命回国,在上海拜会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后即赴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宣传部长,常在《人民周刊》《向导周报》《工人之路》《中国工人》《黄埔潮周刊》《少年先锋》等杂志上撰文,并且也常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著有《共产主义问答》。1927年,国民党“清党”,中共湖南省委遭重创,任卓宣调任湖南,曾与毛泽东共事,任中共“湘南特委”委员,后任湖南省委委员和宣传部长,参与指挥湖南各地暴动。在“灰日暴动”(1927年12月10日,长沙)之后不久被捕,忠诚不屈,被湖南惩共法院判处死刑,于旧历除夕当日行刑(1928年1月22日)。然而在枪决时“子弹从后背打进,穿右胸之上而出”,*《任卓宣评传》,台北:帕米尔书店,1965年,第94页;徐业道:《刑场生还忆往事——记与任卓宣先生一席谈》,见《任卓宣评传》,第285-287页。未伤要害而幸存。伤愈之后不久,任卓宣再次被捕。关于再次被捕,一种说法是沙汀提供的,任卓宣“把责任归之于组织,说不该在他伤愈后用他所隐蔽的住所作通讯联络地址”,*沙汀:《杨伯恺与辛垦书店》,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最终导致他被国民党特务侦悉。另一种说法是任卓宣自己提供的,他认为是共产党的“盲动主义”,造成“大批党员被捕,甚且被杀”,盲动主义“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于是,任卓宣“脱离了共产党”。*任卓宣:《我为什么反共》,见《任卓宣评传续集》,第1页。
1928年4月和5月,《申报》曾经两次报道任卓宣的事:“现被惩共法院捉获共党省委常务任卓宣,秘书蔡增准,因自首带路,破获要案数起,除免死刑外并任为侦缉员”;“自首共党军长苏先峻,省委蔡增准、任卓宣,三人举发巨案,准恢复自由,送清乡署工作”。*《湘省军政要讯》《长沙近闻》,《申报》1928年4月5日,第9版;5月20日,第7版。同年,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撰写的文件中,也提到“李涤生、袁达时、任卓宣、符向一等在湘鄂各地为敌人的统治阶级做那最无耻最卑鄙的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见《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8年9月—1929年2月),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印,1985年,第328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任卓宣自首之后,被安排到川军驻湖南的向时俊部,任少校政治教官,化名任复生,曾为川军讲课。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任复生”批判道:“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明明白白说的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是修改不平等条约,这是违背孙中山意旨的反革命行为。”*邹隐樵:《任卓宣在长沙枪毙未死》,见《永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永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4年,第106页。这一历史细节或许表明,当时的任卓宣在苟全性命于乱世之际,尚有所坚持。
川军向时俊部解散之后,任卓宣于1928年下半年回到四川,在成都大学校长张澜的帮助下,创办《科学思想》杂志,用青锋等多个笔名撰文。据中共川西组织观察,其思想倾向仍属“进步”。有历史当事人回忆,任卓宣1928年下半年到成都之后,曾给中共川西特委上万言书解释自己的行为,要求重回共产党,虽未被接纳而徘徊于党外,但也未被严厉拒斥。任卓宣表示愿意在文化方面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共产党。*《刘披云同志忆在四川地下党工作情况谈话纪要》,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2年,第46-47页;邹隐樵:《任卓宣在长沙枪毙未死》,见《永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07页;陈离:《我与辛垦书店的关系及其活动的经过》,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揆诸《科学思想》旬刊上的文字,当事人的回忆应属可靠。杨伯恺在上海创办辛垦书店的时候,拟将任卓宣带到上海并任命其为总编辑,为此,杨伯恺曾征询四川省委的意见,四川省委表示同意,允许其到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辛垦书店是左翼文化机构,其成员多为共产党人,包括王集丛等人,都曾反对任卓宣加入,只因考虑到四川省委的意见,方才接纳,但给出的条件之一是,不得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沙汀自传》,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3页;沙汀:《杨伯恺与辛垦书店》,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3页。若干年后,任卓宣回忆道:“我从民国十九年春夏间到上海,系应友人王集丛约,参加辛垦书店,任总编辑。”*任卓宣:《我在上海反共之回忆》,见《任卓宣评传续集》,第10页。在辛垦书店期间,任卓宣主编《二十世纪》和《研究与批判》,从事学术研究。
虽然任卓宣在193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抗战以后的生涯是以思想反共为“职志”,但从成都的《科学思想》到上海的辛垦书店,在1928年到1935年期间,任卓宣虽然在组织上不是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却很难说不是倾向于共产党方面,至少可以称之为左翼知识分子,这也构成其文学思想归属左翼文学思潮的缘由。
二
1966年,在台北中和场资料齐备的书房里,任卓宣将其有关文学和语文的文章整理成书,在序言中谈及文学研究的历史,称其“最早的一篇”文章是《文学与思想》,“发表于三十七年前之民国十八年”。*任卓宣:《文学和语文》,台北:帕米尔书店,1966年,序第1页。1983年11月,任卓宣再次提及,“我谈文学,早在民国十八年”,“时在成都创办并主编《科学思想》旬刊,在其第十二期(同年三月三十日出版),有题为《文学与思想》一文,不长,因我之涉及文学方开始也”。*任卓宣:《我底文学撰述之回忆》,《文讯月刊》1984年第7、8期合刊。至于最初“谈文学”的那些文章,是否有政治倾向性,以及是倾向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任卓宣并不提及,但他特意说到了1930年代中期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的一些文学论文遭到了“共产党”的“反对”和“批评”,从而暗示出他当年的文学思想与共产党似非一路。
然而检阅文献可知,任卓宣对其文学撰述的事后回忆和收集并不可靠,有刻意修改历史之嫌。其实,任卓宣“最早的一篇”文学论文,不是“民国十八年”发表的那篇“不长”的《文学与思想》,而是长文《语丝派底阿Q时代存在说与思想界底科学观点》,*青锋:《语丝派底阿Q时代存在说与思想界底科学观点》(上、下),《科学思想》(成都)1928年第6、7期。分为上下两部分发表于《科学思想》“民国十七年”第6期和第7期。相形之下,不论是搜索之广还是思虑之深,这篇1928年发表的长文都远逾其次年发表的次要短文《文学与思想》。那么,为何任卓宣反而厚待后者而无视甚至否定前者的存在?推其缘由,或许是那篇长文整体性的共产党观点在台湾的语境中显得过分突兀,且根本无法改为中性文字,而如果重刊该文,也可能让人对其多次宣称的在1928年便“脱离了共产党”一事产生疑问。在整理文学论文集的时候,博闻强识的任卓宣收罗了不少既无思想价值也无史料价值的文章,却将更早发表也更有深度的文字遗忘于文集之外,似乎不欲人知。对于离开共产党、投奔国民党的文人而言,任卓宣此举,实非孤例。任卓宣的同乡和妹夫、国民党的文艺理论家王集丛,在1930年代曾以王集丛、林子丛等署名发表过共产党立场的文学论文,*林子丛:《艺术——其本质、其发生、其发展及其功用之理论的说明》《艺术与科学》,《二十世纪》(上海)1931年创刊号、1931年第2期;王集丛:《一年来中国文艺论战之总清算》,《读书杂志》(上海)1933年增刊。也翻译过日本共产党人的论文,甚至,据罗瑞卿、沙汀等人的回忆,本名王义林的王集丛早在1928年离开四川去上海之前便已经是共产党人,且曾参加共产党的秘密行动。*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7-36页;《沙汀自传》,第86-91页。可知王集丛曾是有共产党人身份的“左翼作家”。然而在台湾时期,王集丛的这段重要经历却被修改为与共产党之间绝无葛藤缠绕,而是岿然独立:“‘九一八’前夜,中日关系紧张,背叛国民革命遭到惨败的中共,在上海租界里拉拢‘左翼作家’,搞‘普罗文学运动’”,“王集丛亦注意其活动,但终有自己见地,不接受其宣传、引诱”。*《王集丛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第2页。既然如此,《王集丛自选集》自然也就不选其1930年代前半期在上海所写的文字,任其湮灭,似乎也望其湮灭。
且回到任卓宣的历史现场。在1928年下半年和1929年间,任卓宣虽然身在成都,但却密切关注上海的文化和文学动向,既细读共产党人主持的、由创造社和太阳社出版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洪水》和《太阳月刊》,也细读非共产党人的《北新》《语丝》之类,由此捕捉到了发生于上海的革命文学论争的相关信息。在上海发生的论争中,郭沫若、成仿吾对文学进步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沫若:《文艺家的觉悟》,《洪水》(上海)1926年第2卷第16期;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上海)1926年第1卷第3期;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以及成仿吾和钱杏邨对鲁迅《阿Q正传》的时代意义和小资产阶级趣味文学的否定,认为中国农民大众已经觉醒、进步和革命了,从而“阿Q的时代”和“《阿Q正传》的技巧”都“已经死去了”之类的观点;*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洪水》1927年第3卷第25期;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上海)第3期,1928年3月。蒋光慈所谓“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第2期,1928年2月。的观点;李初梨模仿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提出的所谓“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的观点,及其对北新书局、周氏兄弟闲暇、趣味的攻击,对无产阶级文学作为“斗争的文学”“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的断言;*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上海)第2号,1928年2月。凡此等等,不仅在当时唤起了任卓宣的战斗冲动,而且在以后深刻影响甚至塑造了任卓宣的文学思想,即便他的政治立场从共产党转到了国民党,也只是换了意识形态和“中心思想”,但理论结构未变:强调文学的宣传功能,为政治而文学,为反共而文学;强调“思想正确”,为三民主义而文学;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等等。
1928年论争初起时,任卓宣在长沙已经被捕,论争激烈和延伸时,任卓宣已在党外,他无法得知这场论争是否与共产党中央的文艺政策和指示有关。任卓宣只能在成都读到数月前甚至是1926年的上海杂志,他从郭沫若、蒋光慈、成仿吾、李初梨等一大批参与者的共产党人身份,从文章援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从文章表述的无产阶级(即所谓“第四阶级”)革命文学主张,以及这些共产党文人突然地成规模地展开对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家的激烈批判,等等事实,“合理推论”其为共产党方面号召的有组织的文化行动。任卓宣其时已对中共川西特委表态愿为共产党的革命文化事业“奉献”,于是在成都以《科学思想》为无名阵地,独力声援远在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当然,任卓宣的判断并不准确,共产党中央处于国民党严峻的军事压力之下,当时并无组织革命文化、革命文学的政策和指示。*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139页;冯乃超:《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新文学史料》(北京)1986年第3期。然而,上海的革命文学论争毕竟影响到了共产党与鲁迅等人的关系,终究导致中共中央派员干预。*冯夏熊:《冯雪峰回忆中的潘汉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武在平:《潘汉年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当年9月,冯雪峰发表了《革命与智识阶级》,*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级》,《无轨列车》(上海)第2期,1928年9月。批评创造社等人对鲁迅的攻击是“狭小的团体主义”,对革命不利。任卓宣并未注意到冯雪峰的文章,他身在党外,也无由得知党内指示,他看到的都是过期杂志,而且不全,于是从1928年底到1929年,任卓宣依据自己的判断,持续攻击鲁迅等人的“保守”“闲暇”和“趣味”。
正是为了声援钱杏邨等共产党人在1928年5月对鲁迅《阿Q正传》时代意义的否定,任卓宣在1928年12月撰写了《语丝派底阿Q时代存在说与思想界底科学观点》。其实任卓宣只是读了《语丝》各期,并未看到钱杏邨发表于《太阳月刊》的文章,他只是依据《语丝》对钱杏邨文章的引用和响应,而对当时的中国是否处于阿Q时代的问题发表议论。任卓宣认为阿Q时代问题的争论“是中国革命深入文艺界所显示出之革命主义和保守主义底抗争”,“在钱杏邨们,因为阿Q时代过去了,所以文学应该革命,破坏旧文学,建设新文学”,“在鲁迅们,因为阿Q时代还存在,所以反对革命文学,主张保守”。任卓宣首先清晰界定“阿Q已死”和“阿Q没有死”的意义分野:“《阿Q正传》是用阿Q代表中国农民来描写辛亥革命时代中国农民如何受封建思想封建势力底压迫,如何没有觉悟否认革命,如何被动地卷入革命漩涡”,“说阿Q已死,阿Q时代过去了,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农民有了觉悟,他的智识,组织,对政治底了解,对革命底态度,都不像从前,总括一句,中国底时代是进了步,已到‘黎明之前’,我们的革命任务因而也是向前走去”,“说阿Q没有死,阿Q时代没有过去,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农民仍然与从前一样,对于时局,也就认为与从前一样,我们就没有新的任务和希望”,“阿Q时代存在与否底问题,是中国革命底问题,关系于中国的前途与我们底人生观,中国底历史进程与我们底努力方向”,这是“民主革命派与社会革命派”的分歧所在。在此,所谓“民主革命派”是就鲁迅等人反封建而言,所谓“社会革命派”则是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
在解决阿Q时代的存否问题上,任卓宣主张用所谓“科学的思想”,首先,从“革命科学”的观点看,“被统治阶级不能同时间同程度一致觉悟起来”,“有创造历史任务底被统治阶级,必需其觉悟部份底领导”,“被统治阶级底解放,只要其中相当数量底份子,即可完成”,“被统治阶级参加革命与否,不是智识多寡底问题而是觉悟有无底问题”,“估量被统治阶级,要注意全般的实际,不可只注意片面的事实”;其次,从“历史科学”的观点看,“历史是前进的,不会有什么停留”,“历史是日新月异的发展,决不重复”,“在平常时代观察历史底演进要注意经济,在革命时代则当看重阶级关系底转变和政治底属性”,等等。其实任卓宣的所谓“科学的思想”,在国民党反共的历史语境之中显得含混不明,他的本意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科学的思想”,认为中国农民中出现了觉悟分子,而历史是前进的,新的经济基础只会导致觉悟分子越来越多,从量变到质变,农民终将在自身的进步中实现自身的解放;同时,在觉悟的先进分子领导下,参与政治革命,加速自身的解放。《语丝》社诸人持形式逻辑:即便中国南方有一些农民进步了,但是中国农民的大部分依然愚昧、迷信、落后、没有知识,而只要中国农民中还大量存在阿Q,阿Q时代就远未过去。任卓宣则持辩证逻辑:中国既然有了觉悟和进步的农民,阿Q时代就必然过去,甚至从革命已经展开的角度看,阿Q时代已经过去了。
任卓宣呼应远在上海的左翼文人一年前对鲁迅等人“闲暇”文学、“趣味”文学的攻击,也对处身其间的成都文学界的“‘闲暇’人底‘趣味’文学”施以批判,认为成都文学界“思想干枯平凡,因而也就无精透的,系统的和继续不断的作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讲‘普罗列塔利亚特文艺’”,“成都底文学青年”不应该学习《北新》和《语丝》那种“为文学而文学”,“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作风,而要“追随时代潮流,研究科学的革命理论”。*亦鸣:《文学与思想》,《科学思想》1929年第12期。在此,任卓宣所谓“科学的革命理论”,也就是所谓“否认了私产权,旧礼教和民主主义”的“北欧底新精神”,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青年人应当“明白这种革命化底现象和非资本主义的趋势,才不致成为思想落后者”。*亦鸣:《世界青年思想底革命化及其趋势》,《科学思想》1929年第11期。
在《科学思想》旬刊上,从1928年到1929年,任卓宣一直在讽刺以鲁迅等为核心作家的《语丝》和《北新》,认为他们“形式虽有,内容却无,实不能再有革命作用”。*编者:《文学与思想》,《科学思想》1928年第4期。据任卓宣讲,1929年9月28日,他“到西御街与祠堂街之间某新书店去买书”,“卖书人说,‘北新底书不好卖’”。由此,任卓宣想起,“成都自去冬迄今共添有八九个新书店,都不见代售有甚么北新底书”,而成都“去冬方成立底北新书局,不久改为长江书局,代售北新以外各新书局底新书”。于是,任卓宣断言:“这是个人主义文学崩解底表示,那位卖书人居然指示出来了成都读者底嗜好,成都文化底倾向。小布尔乔亚汜底文学领袖——鲁迅们底市场,居然为一年多来之普罗列特利亚特底文学战士们所占领了。”*冷眼:《“北新底书不好卖”》,《科学思想》1930年第41期。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任卓宣批判的成都文艺界热衷“‘闲暇’人底‘趣味’文学”,那么,“闲暇”而“有趣”的《语丝》和《北新》便有其市场,为什么成都的书店反而不卖《语丝》和《北新》的书?此且不论,从中可见任卓宣在创办《科学思想》时期,其文学作为的确是在声援上海的左翼文学思潮,并试图推动成都文化界和文学界的“进步”。
然而在一篇《由上海到成都》的文章中,任卓宣写道,“上海到成都有好几千里路”,“上海在太平洋岸上,交通十分便利,而成都是在巴山岷山和五岭底包围中,如像偏僻地方一个乡村式的都市”,“于是上海成为文化的中心,成都就成为无思想的枯寂地了”。*勉之:《由上海到成都》,《科学思想》1928年第2期。任卓宣大约不想再在成都“枯寂”地看过期杂志,1930年春天,他决定东行,“由成都到上海”,参与左翼文化机构辛垦书店的工作。
三
在辛垦书店工作时期,任卓宣勤于研究、翻译和著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渐有成就和名声,随后,他不但与文学界的伍蠡甫等人有所交往,而且违背与共产党的约定而与国民党方面的陈立夫、康泽等人有所来往,*陈离:《我与辛垦书店的关系及其活动的经过》,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编),第391页。参与了国民党方面策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起草和讨论,*叶青:《〈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的经过》,《政治评论》(台北)1962年第8卷第11期。他的学术思想也受到了共产党方面的艾思奇、周扬等人的批判。除此,或许还有其他缘由,导致任卓宣与共产党渐行渐远甚至以共为敌,在抗战前夕发表了攻击共产党“分裂割据”的长文《统一救国的途径》,*叶青:《统一救国的途径》,《文化建设》(上海)1937年第3卷第5期。之后又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问题》《毛泽东批判》等反共著作。有共产党人认为那是任卓宣对共产党的“又一次叛变”。*沙汀:《杨伯恺与辛垦书店》,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3页。
从1930年到“又一次叛变”之前,任卓宣在文学方面的成绩主要分布于1933年到1935年间,出版了《胡适批判》,其中包括《在文学方面的胡适》,发表的重要文学论文有《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政治》《世界文学底展望》,以及文学批评《徐志摩论》和《郁达夫论》,等等。任卓宣这一时期的论文,确定了他的基本文学思想,他给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含有艺术意味的,它用美的技巧来从具体的事物上表现思想和感情。”他认为文学包括三个要素:“(A)艺术的美;(B)经验的事实;(C)思想。”只有思想,则是哲学;只有事实,则是科学;文学除了思想和事实,还要美。任卓宣关于美的观念略有机械唯物论的色彩:“美是实在的,客观的,不能离开感觉,文学上的美,首先就是感觉”,“描写出来的故事,读者看了就像亲历其境”,“人物则传达其个性,风景则观照其情势,无不逼真,活像,这就叫做美”,“要具有描写之美的文学作品,才能抓着读者底感情,使他受其感染”,“至于句子底漂亮、痛快等,虽属必要,却是枝节”。*叶青:《文学与哲学》,《文学》(上海)1935年第4卷第2期。在任卓宣写作文学批评的时候,他的基本考察方法和评判标准,不外乎此,而这些观点,也是当时一般的观点,与胡适等人并无太大差异。不过,在考察文学史的时候,任卓宣比在《科学思想》时期更加准确和熟练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显示出左翼文论家的深刻思想和解释能力,理当归入郭沫若、成仿吾等人构成的左翼文学思潮序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文学的思想问题和功能问题上,任卓宣明显受到了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左翼文艺阵营的日本共产党人藏原惟人、青野季吉等人的影响,譬如,他认为是未来文艺发展方向的所谓“新自然主义”或“新写实主义”,他所谓的“组织社会生活”“指导社会生活”,以及所谓从“自然生长”到“目的意识”等等,无论观念还是术语,几乎都是来自藏原惟人的《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和无产阶级》《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路》《再论新写实主义》,*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论文集》,之本译,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以及王集丛翻译、辛垦书店出版的青野季吉的《普罗列塔利亚艺术概论》。*青野季吉等:《新兴艺术概论》,王集丛译,上海:辛垦书店,1930年。凡此足以证明,在1930年代,任卓宣确曾加入左翼文学思潮的合唱,虽然他在组织上与中共和“左联”没有关系。
在1935年以后,任卓宣十余年间几乎未曾论及文学,其1943年发表的《关于三民主义文艺奖金办法》虽然收入文集《文学和语文》,但不成其文,更不成论。1946年他有过一次《关于诗》的演讲,由他人记录发表,*果人:《关于诗》,诺逸笔记,《华侨学生》(曼谷)1946年第6期。但未收入文集。随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自1950年起,至1981年止,任卓宣又发表十数篇文章,基本是在三民主义、反共文学的范围里转圈,即便是谈到“乡土文学”也是如此。*任卓宣:《三民主义与乡土文学》,《夏潮》(台北)1977年第17期。退居台湾时期的任卓宣呼唤文艺政策,也就范于文艺政策,“党国”文艺政策的核心是反共,任卓宣对此多有论述,而蒋介石于1953年发表的《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也在谈及文艺的时候声讨“匪共”,认为他们“把阶级的斗争的思想和感情,藉文学戏剧,灌输到国民的心里”,使“中赤色的毒”。*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见《三民主义》,台北:三民书局,1965年,第52页。既然有反共的文艺政策,任卓宣在1966年编订《文学和语文》的时候,便大量修改了其1930年代的文学论述,今是昨非,与时俱进。譬如,在1933年批判胡适的文学进化论的时候,任卓宣的原文是:
中国底经济进化,我以为是采取如此的辩证历程:“古代资本主义——中世封建经济——近代资本主义”。所谓古代,是由西周到汉武,可统称为奴隶时代的。由西周而春秋而战国,虽可细分为三期,但在其与中世封建时代相对而言,可就其最高的资本主义的战国期来说,并且资本主义在春秋也发生作用的。所谓中世,即汉武到清道,可称为封建时代,胡适虽在谈政治主张时说“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可是在论文学历史时,还处处表明汉以后有贵族统治底存在。所谓近代,即清道以后迄今,是中国以外在的原因而促进其内在的发展,重上资本主义,可称为资本时代的。不过这个资本主义异于古代,以“近代”为特征。前者是原始的而后者是高级的。
因此,与经济相应的文学,它底分期和进化也完全相应。就工具和体裁而言,在散文是:
古代语体文——中古文言文——近代语体文。*叶青:《胡适批判》,上海:辛垦书店,1933年,第974-975页。
1966年修改以后的版本是:
中国人民生活底进化,我以为是采取如此的辩证历程:“古代社会——中世社会——近代社会”。所谓古代,是由西周到汉武,相当于欧洲古代奴隶时代的。由西周而春秋而战国,虽可细分为三期,但在其与中世封建时代相对而言,可就其最高的战国期来说,并且工商业在春秋也发生作用的。所谓中世,即汉武到清道,注重农业,普通称为封建时代,胡适虽在谈政治主张时说“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可是在论文学历史时,还处处表明汉以后有贵族统治底存在。所谓近代,即清道以后迄今,是中国以外在的原因而促进其内在的发展,注重工商业,趋于近代化的。不过这种工商业异于古代,以“近代”为特征。前者是原始的而后者是高级的。
因此,与时代及其生活相应的文学,它底分期和进化也完全相应。就工具和体裁而言,在散文是:
古代语体文——中古文言文——近代语体文。*任卓宣:《文学和语文》,第197页。
任卓宣1933年的版本运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式,以经济基础解释文学演变;而对经济史和文学史,均使用辩证法正反合三阶段的解释模式。综合起来,可以认为是唯物辩证法的解释方法,这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中的基本方法。然而在1966年的修改版中,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都被替换了,剩下“辩证”一词,任卓宣可以辩解为黑格尔的术语而不专属马克思主义,*任卓宣:《我为什么反共》,见《任卓宣评传续集》,第4页。但是“古代资本主义——中世封建经济——近代资本主义”有明显的辩证法三段论色彩,而“古代社会——中世社会——近代社会”的罗列方式则毫无辩证法的意义,显得莫名其妙。至于把“中国底经济进化”改为“中国人民生活底进化”,把“资本主义”改为“工商业”,则显然是试图让台湾的读者朝民生史观的方向理解。在此,术语虽然被替换,而唯物论的解释架构却依然存在,如同坦克蒙上油布,依然显出战车的轮廓。然而,任卓宣有的术语替换却意味着对自身历史的彻底修改,譬如,任卓宣曾认为世界文学在未来必然走向“新写实主义”,而其“新写实主义”的思想在1934年的版本中是这样表述的:
(A)在人生哲学方面 集体主义,史的物质观,科学的社会理想;
(B)在一般哲学方面 物质论——认识上,感觉论、经验论、实践论;本体上和宇宙上,新的物质一元论。*叶青:《世界文学的展望》,《世界文学》(上海)1934年第1卷第1期。
1966年的修改版则是这样的:
(A)在人生哲学方面 集体主义,历史的民生观,科学的社会理想;
(B)在一般哲学方面 综合主义——认识上,感觉论、经验论、实践论;本体上和宇宙上,物心综合论、进化论。*任卓宣:《文学和语文》,第105页。
在1930年代国共敌对的情势之下,在国统区的公开出版物上,所谓“史的物质观”,即是唯物史观,或者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物质论”,即是唯物论。然而任卓宣将其分别换成了所谓的“历史的民生观”和“综合主义”。虽然文末注为1934年发表,然而已非原有的文字和思想。如果依据《文学和语文》研讨任卓宣的文学思想,有可能认为任卓宣在1934年已经彻底抛弃了一元论的唯物史观,而接受了毛泽东批判其为“二元论”的民生史观。其实,从1920年代末在《科学思想》上的论述,到1930年代中在《世界文学》上的思想,任卓宣一直怀疑孙中山所谓的“民生”作为“史观”能否成立,*青锋:《 “民生史观”论评》,《科学思想》1929年第14、15期。但是在后来的文集编订中,任卓宣轻巧地让当年的自己拥抱了三民主义的民生史观,无声地抹去了唯物史观和左翼的痕迹。于是,任卓宣的“三民主义文学思想”,从1930年代到1980年代,仿佛真是“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而与左翼无涉。
也许篡改历史乃是无奈之举,然而文献可征,最终无法遮蔽历史的真相。不过任卓宣的修改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的基本架构是工具主义的:不论是“意识形态真理”与“经验真实”组成的理论结构,还是“新写实主义”的方法论结构,*姜飞:《左右同源:新文学史上的新写实主义》,《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1期。本质上都是中性的工具,当年的左翼作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组织文学的经验叙述,而国民党方面的文艺理论家(譬如任卓宣、王集丛和刘振涛等)在当年以及后来也可以用三民主义宰制其文学的经验叙述。于是,任卓宣多年以后的篡改只需要更变术语而非替换结构。相对而言,更变术语是微创手术,而替换结构则意味着重写。
对任卓宣以及从左到右的其他国民党文艺家而言,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可以选择,或者投机,然而在思想结构的层面上,却显示出稳定性和一般性,他们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不论是在左翼,还是在右翼。
(责任编辑:庞 礴)
Ren Zhuoxuan and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
Jiang Fei
In Taiwan of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Ren Zhuoxuan was known as a promoter of the Anti-Communist cultural movement, and an executor of the Kuomintang literary policy. His identity at that time covered up an important fact: From the end of the 1920s to the middle 1930s, his literary thoughts belonged to the Left-wing literary trend. Perhaps because of the intense pressure of the literary policy formulated by himself, he erased the traces of his history in the Left-wing literature group by rewriting when he published his bookLiteratureandLanguagein 1966. Ren Zhuoxuan's literary thought is a meaningful and important specimen, showing the actual state of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sphere of literature.
Ren Zhuoxuan, the Lef-Wing literary trend, literary policy, the rewriting of history
姜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成都 610064)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国民党文艺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skzx2015-sb81)
I206.6
A
1006-0766(2017)01-0074-09